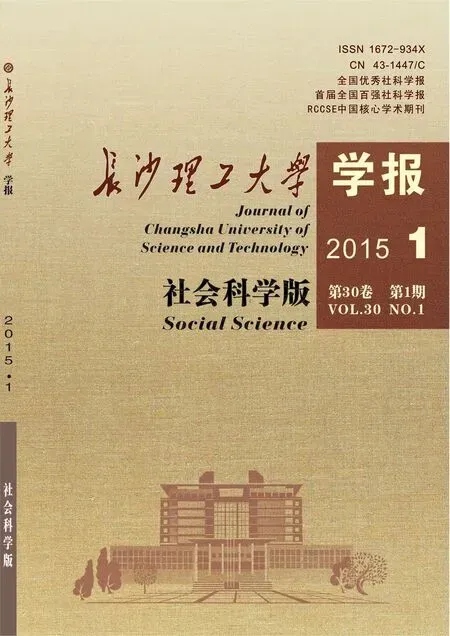西美尔生命哲学中审美救赎的理论来源
江文富
(广东医学院 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 东莞 523808)
西美尔生命哲学中审美救赎的理论来源
江文富
(广东医学院 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 东莞 523808)
西美尔面对现代文化的危机,试图用审美救赎的方式使人们回归到本真意义的生命中去。这种将个体性的审美上升到普遍性,以试图达到整体性的绝对的路径正是康德和谢林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经典路数。同时,在面对注重个体生命性的现代审美主义时,西美尔仍然坚持对于一致目标的追求,他从康德对于崇高的理论中获得启发,提出了审美距离的概念,使人们避免物化的沉沦,重新回到个人的内心中。通过这样的方式,西美尔保证了整体性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现。
生命;文化;艺术;价值;审美
一般来说,西美尔美学思想被认为是建立在波德莱尔浪漫主义美学基础上的,诚然,西美尔对于文化碎片、时尚和流行理论是波德莱尔对于现代性美学的时间性的分析的深入发挥。不过西美尔美学的基本构架和逻辑还是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和谢林的美学思想。西美尔希望通过审美的方式来使人们摆脱现代文化危机,以达到对于生命悲剧的拯救,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如何能够达到作为整体的绝对只能在康德和谢林美学思想中去寻找。通过审美救赎,西美尔试图实现直指个人的生命体验与可传达的普遍性之间的协调统一。
一、生命沦落造成的现代文化危机
西美尔将文化视为是生命所创造出来的形式,而文化又被细化为主观文化和客观文化。主观文化指的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教化、智慧以及品德、幸福之状态,本质上来说就是个体之灵魂,因此西美尔也将文化理解成为是一种对于灵魂之改进。而客观文化又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人们生产和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也可以被称之为是物质文化;另一种是表现为“客观化的精神”或者说“物化的精神”的精神产物,包括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以及科学等等。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不断地细化,客观文化逐渐开始脱离与主观文化之间的联系,而在技术的领域中获得膨胀式的发展。而与之相对的是,体现主体精神的主观文化却日渐式微。西美尔认为正是由于劳动的分工才造成了这种局面的产生。因为面对着越来越专门化、精确化和细化的生产过程,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也只是能够片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占有,而原本是丰富的人们的精神特质一旦被对象化在产品之中,就会成为局部的和片面的。于是这种对象化的客观精神也就缺少了原本的生命之灵魂,“专门化生产的产品的意义既非主体性的反映,也不是创造性精神的反映,而只能在远离主体的客观成就中找到。”[1](P368)西美尔在这里指出了客体性文化的过渡膨胀导致了对于主体生命自身之忽视。生命主体本来应该通过吸收客观文化的产物从而提升自身,但是由于现代文化不断地客观化、独立化和复杂化,面对着日新月异的客观文化,由于个体之接受性总是有限的,因此主体所吸收的客观文化占客观文化自身发展规模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小,而且客观文化形成了具有自己规则和逻辑的不断膨胀的封闭整体,主体也就越来越跟不上客观文化的步伐,两者之间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不对等状况,这就产生了现代文化的危机。而分工细化和客观文化复杂化所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主体的本真生命被遮蔽和终极目标被消解。生命主体的进步只有通过外化的文化形式的发展和把握才能够实现,而因为这个目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模糊性,就需要细化为不同的次级目标,于是本来作为终极目标的手段也被暂时地赋予了目的性。而分工所造成的形式、阶段和手段之中介环节的不断增加,使得生命原本的目的被遗忘,而手段却变成了目的。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要把人当作目的看待,而不是手段看待”的要求,这是因为只有将人当成一个单一性的目的,道德才能够实现其普遍性。而现代文化危机造成的手段篡权成为目的,这种僭越肯定是不合法的,因此它也就不具有能够被普遍的推行的有效性。
主观文化同客观文化之间的“分道扬镳”造成了“文化悲剧”,人们生命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竟然调转头来控制生命、压抑人的本性,这在西美尔看来无疑是“精神的最基本的不幸”。西美尔忧心忡忡地描述道:“文化客体日益发展演化成一个互相连接的封闭世界,这个世界越来越少地指向带有其意愿和感情的主体灵魂。”[1](P373)这种不同封闭整体的各自为政会使它们失去共同的方向性,没有单一的指引目标的各种文化客体最终就会像无头苍蝇一样跌跌撞撞,因此没有生命保证其统一性的文化继续盲目地发展下去的结果必定会是灭亡。而且,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也会导致人类感情的丧失,越来越精致的文化使得人们的感情也越来越精细,从而带来一种情感共通上的困难,不能够融入到集体之中的个人无疑会更加孤独。文化之所以会落入这样的悲剧命运之中,是因为生命本身就带有悲剧性色彩:“生命是文化的源头,文化应为生命服务。而文化的趋势则是要让生命解体,变得没有意义,这里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生命最根本的动力统一体一次又一次地保卫自己,与这种趋势相对抗……这场危机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也并非不可理喻。因为无论是否意识到,这是每一个人灵魂的危机。”[2]生命与文化这种固有的矛盾使得人们不得不沦入“文化悲剧”的命运。
“文化悲剧”体现在多个方面,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货币这种文化形式对于个体形成了全面的控制,货币将它体系之中的规则施加于世界之上,造成了平均化和数量化的一种倾向。西美尔将货币为代表的文化方式比作桥,货币这座桥本来是为了文化和生命之间的沟通而建造起来的,但是人们在通过本来是作为手段存在的桥时却将之视作为目的,忘记了桥彼岸的生命之目的,这就造成人被困在桥上而下不来的境地。这使得人们的理智凌驾于直觉和感情之上。理智主义也造成了人们精于算计:“不仅是物质世界,需要用测量和衡量的方式在精神上加以征服,就连生活价值本身,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同样都想通过快乐和痛苦相互抵消来加以规定,至少把在数量上确定这两种因素当最理性来追求。”[3](P38)这种对于数量化和精确化的算计也使得人们失去生命本真的活力,变得越来越平庸。
二、审美活动与心理主义
现代文化危机还造成了人们的生活浮躁庸俗,人们丧失了理解与欣赏深刻的艺术的能力。人们的内心不再宁静,从而无法领会高雅艺术的精髓和灵魂。正是由于工具化、专业化、精确化、制度化及合理化,人们原本丰富多彩的生命被磨平了棱角,这就是现代性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因此要拯救这种危机,我们必须要回到生命本身,试图去达到生命的整体和大全。而实现这个理想的途径就包括摆脱概念的束缚,获得一种关于生命的情感的体验,这就是审美救赎的方式。西美尔建议,“人类已变得苍老、离异、世故,他们已不能再拥护下述见解了:把世界中的实在、爱、意义、精神价值等等转换为抽象概念的逻辑结构和形而上学本质的类似物,并把这种转换视为精神的最大幸福;将逻辑思维及其颤栗性的敬畏关系与诸事物的根据充分连结起来;以后的时代要获得这些根据只有拒斥纯粹思维才有可能,只有通过把逻辑结构与活的情感性的存在割裂开来才有可能,要懂得这种活的情感性存在的直接性,既不能靠柏拉图的概念,也不能靠我们的概念,只能去体验这种存在的内心深处。”[4]在这段话中,西美尔指出正是由于异化的文化形式才使人们变得死气沉沉,生命中的情感和爱等内容不能够通过逻辑化的形式完全被表达出来,要理解活生生的情感性的存在,我们只能撇开概念,直接进入到生命存在的本身中去体验。
这种由客观化、对象化回到主体内心体验的方式就是审美活动,审美主义也就相当于心理主义。西美尔认为人的主观心理世界就像是由艺术搭建起来的一个自在的独立世界一样,与他人和它物没有直接的联系。“艺术是我们对世界和生活的报答。在世界和生活创造了我们意识的感性和精神的理解形式以后,我们就用艺术来报答它们,同时凭借它们的帮助再次创造一个世界和一种生活。”[5]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艺术的优点在于它虽然也是一种外化的文化形式,但是我们在对这种外化形式进行把握时,也就是在进行审美活动的时候,能够返回到自身中去,并在主体性中也创造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就与生命之原本的世界相接轨了。可以说,审美活动首先是一种私人的活动,也就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西美尔认为现代性的本质也就是心理主义,心理主义就是通过内在心理活动来对世界进行解释和体验,因此也就建立在直观而非概念之基础上。康德指出我们的审美活动面对的是个体的具体事物,比如我们在审美时说:“这朵花是美的”,而不会说“花是美的”,因为前者才是一个鉴赏判断,而后者就是概念性的规定判断了。马尔库塞也指出:“审美方面的基本经验是感性的,而不是概念的;审美知觉本质上是直觉,而不是观念。……正是借助这种与感性的内在联系,审美功能才获得了其核心的地位。”[6]西美尔进一步进行阐释:我们无法对于别人的灵魂进行直接的观察,因为我们的知觉只是一些感官印象,所以心理认识也就是对于自己灵魂感受到的意识过程之解释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事物进行知觉的过程,其实是用内心去把握外部世界的过程。这种审美主义就是感性冲动对于理性束缚的挣脱,通过审美活动,人的感性和生命获得解放,得到自由。谢林在《先验唯心论体系》中也指出,艺术是现实同理想的统一性整体,也就成为主客统一的大全。艺术作品的双重性在于它既是人们精神活动之产物,又被客体化为物质性的感性对象之中。艺术就是实践的意识创造的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当艺术家想象世界的时候,就会通过创造艺术的物质性形成来对世界进行再现,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就能够正确认识世界。谢林认为,“既然在一般理念者中的反映=构拟,艺术哲学亦应=艺术之构拟”[7]这也就是说,相对于认识的反映,艺术一种主动创造的方式实现了对于世界的认识。在谢林看来,认识之最终意义就在于对于整体性的本质实现直观,而通过艺术构拟的方式能够实现这个目的。这个构拟的过程实现了抽象同具体、普遍同特殊以及主观同客观之间的统一。德国古典哲学中对于艺术的这种定位成为了西美尔对于文化危机进行审美救赎的理论性前提。
西美尔认为艺术的形式是来自于生命的创造性的,其中也包含着生命之力量。而这种生命的力量进入到艺术形式中之后不断地发展和充盈,艺术形式之中保留了生命活力之本性,因此我们常常能够在优秀的艺术作品中体验到强大的生命力量。而艺术形式也为这种力量的表达提供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外在形式,艺术形式位置的恰得其所和各个形式部分相互间的联结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统一整体。这个整体是由各个形式部分构成的,但是又大于各形式部分相加的总和。但是,西美尔又指出现代审美主义中形式与内容不再是那么和谐的了,生命内容在破坏和颠覆着形式,那么这样的话还能够达到康德所提倡的那种普遍性吗?
三、距离:现代审美主义达到普遍性的方式
康德指出审美判断的本质就在于从个别性中能够归摄出普遍性,这一点是不能够改变的。西美尔也承认“进行审美观察时,我们在个别事物中看见其普遍性,而我们在逻辑上的普遍概念中只思考普遍性。”[8]现代审美主义中艺术的形式不再具有以前的稳定性,差异和个性的张扬体现了对于生命力的热爱,审美关注之对象集中在了个体之生命体验以及身体感觉之上。超验的普遍性的美被个体性的、生命性的和感性的美所替代。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否定了审美的普遍意义,因为西美尔也明确地阐明了审美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处在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以及个体性与超个人之集体性间的独特性的游戏。谢林也指出艺术的这一特点:“美既不是普遍者或理念者(它=真),又不仅是现实者(它呈现于行中)。由此可见,美无非是此与彼的相互渗透或复合。美所在之处,特殊者(现实者)与其概念相应,以致后者作为无限者纳入有限者,并被直观in concreto(具体地)。”[9]
对于审美是如何达到这种个人性与超个人性之间的统一,康德和谢林都给出了自己的理论论证。在康德看来,审美判断中认知是不起作用的,因此也就不能通过确定的概念来保证审美判断的普适性。但是审美判断作为一种判断必须涉及到普遍性,只不过概念逻辑判断涉及的是客观有效性,而审美判断涉及的是主观有效性。康德将这种主观有效性的基础建立在一种共通感之上,这种共通感是对美的对象进行鉴赏的时候想象力与知性之间的和谐而引起的。共通感作为一种情感保证了我们在价值上的一致和可沟通性,这一点无疑也是西美尔生命哲学所宣扬的。西美尔认为,“在个体精神的有限范围之内,情感的力量与节奏仍是比外在世界重要的多。”[3](P160)因为情感是充满着价值性意义的,它附着于我们的生活以及终极目标之上,所以情感应该成为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和最内在的属性。西美尔认为情感之内带有着生命之意义,或者也可以说生命应该是情感性的生命。但是由于作为手段的文化形式的膨胀,这种情感在现代社会中日渐消弭。就像货币这种中介一样,它不偏不倚,不带有任何的感情。对于无情的货币的崇拜使得人们真挚的情感不断衰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也在不断地生疏。因此,也就有必要通过审美救赎唤起人们在感情和价值上的一致,实现向生命本真意义的回归。
但是由于现代艺术形式的破裂,个体精神的膨胀,艺术风格的差异化、多样性和易变形,永恒之美也就沦落成为瞬间的、个体的和差异性的美。如何回归艺术的整体和超越的理性,西美尔提出了审美维度上的“距离”的概念,这种艺术上的距离主要是艺术同生活及主体同生活之间的一种关系。艺术作为主体的内在精神之表达,其中的距离彰显了内在精神对于外在物化对象之远离。距离表现了艺术对于现实性生活的一种审美性维度,距离的本质就是“自我同事物、他人、观念、兴趣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艺术使我们离现实更近,艺术使现实独特的最深层的含义与我们发生了一种更为直接的关系;艺术向我们揭示了隐藏在外部世界冰冷的陌生性背后的存在之灵魂性,通过这种灵魂性存在使存在与人相关,为人所理解。然而在此之外,一切艺术还产生了疏远事物的直接性;艺术使刺激的具体性消退,在我们与艺术刺激之间拉起了一层纱,仿佛笼罩在远山上淡蓝色的细细薄雾。”[1](P384)一方面,艺术距离拉近了自我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使主体更加贴近日常的生活;另一方面,艺术距离又疏远了主体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是因为人们在远距离对于外在生活和世界的观看,使得人们能够进行一种似乎是作为局外人一样的沉思。主体也就从客观文化的外在性和物化之中将自身抽离出来,避免了在客体物化刺激之下自身的沦落和沉陷,也就摆脱了同外化事物之间的世俗的和功利性的接触,重新回到个体的内心之中。其实早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就提出了我们只有与事物保持适当的距离时,才会产生一种崇高的感情。康德举例说,但我们面对着似乎要毁灭一切的火山以及无边无际的汪洋的时候,只有我们自己觉得自身是安全的,它们的力量越可怕,我们就越会觉得有吸引力,并对它们产生一种崇高的感情。而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指出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距离的话,那么面对深渊我们似乎感觉到它要吞噬我们,而使我们倾向于掉下去。这也就是质料性的刺激吞噬人自身,而这就是西美尔提出审美距离来试图避免的。
西美尔生命哲学中处处显现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子,我们不能够切断这两种哲学理论之间的联系,而生命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德国古典哲学。西美尔以德国古典哲学理论为武器,对于社会现实的批判,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西美尔通过提出审美救赎的方式,试图将人们从物欲纵横的局面中拯救出来,重新获得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以及对于整体性的终极目标的追求,使人成为本真意义上的生命性的个人。
[1][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德]西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65.
[3][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顾仁明,刘小枫,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4] 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M].魏育青,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272—273.
[5][德]西美尔.桥与门——西美尔随笔集[M].涯鸿,宇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215-216.
[6][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36.
[7][德]谢林.艺术哲学[M].魏庆征,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17.
[8][德]西美尔.叔本华与尼采——一组演讲[M].莫光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1.
[9][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M].梁志学,石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37.
Source of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Salvation in Simmel's Philosophy of Life
JIANGWen-fu
(LifeCultureResearchCenter,GuangdongMedicalUniversity,Dongguan,Guangdong523808,China)
Facing the crisis of modern culture, Simmel tried to use the aesthetic redemption as a way for people to return to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The way of leveling individual aesthetic to the universal was consistent with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just like Kant and Schelling.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ace of focus on Modern, aestheticism of individual life, Simmel still persisted to pursue for consistent goals. He learned from Kant for the Sublime Theory for inspir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aesthetic distance, making people avoid materialism in corruption, and return to one's inner self. In this way, Simmel ensur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grity of the valu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life;culture;art;value;aesthetic
2014-11-21
江文富(1956—),男,安徽省安庆人,教授,主要从事生命文化学、生命科技的哲学研究。
B516.49
A
1672-934X(2015)01-0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