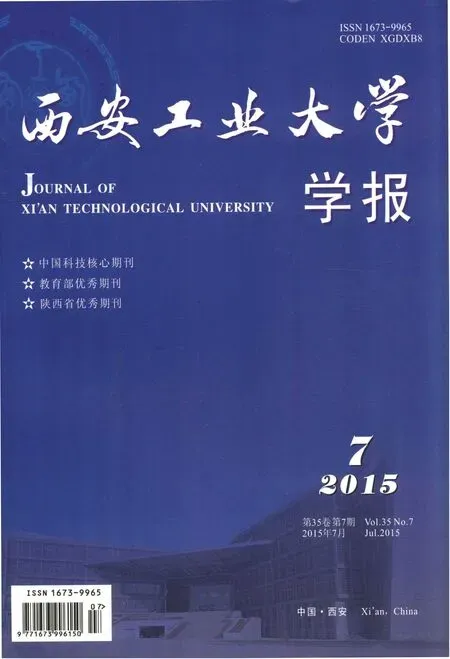冯积岐小说中宗族、政治和多元身份关系研究*
师 爽
(西安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西安710021)
冯积岐作为陕西当代著名小说家,其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乡土中国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磨难和困境,尤其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建国后的精神历程,此历程在其小说中有多重表达,尤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就是对身份之间复杂关系的表达.冯积岐小说中有许多身份标识,在他的《沉默的季节》[1]、《大树底下》[2]、《遍地温柔》[3]、《村子》、《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4]、《敲门》等小说中总出现一些代表身份的高频词,如“党员”、“村长”、“乡镇干部”、“社员”、“贫下中农”“地主”、“地主狗崽子”、“富农”、“黑五类”;“爷爷”、“父亲”“叔叔”、“弟弟”、“母亲”、“舅舅”、“弟媳”;“告状人”、“包工头”、“农民工”、“老板”、“记者”、“作家”等.在对这些身份高频词进行分析时,可发现冯积岐小说中所出现的这些高频词,可归为三类,即一,以阶级身份为主作为划分身份标准的政治身份,包括“社员”、“贫下中农”“地主”、“地主狗崽子”、“富农”、“黑五类”等;二,以血缘关系作为划分标准的宗族身份,“爷爷”、“父亲”“叔叔”、“弟弟”、“母亲”、“舅舅”、“弟媳”等;三,以现代职业作为划分身份的多元身份,“法律人”(告状人)、“经济人”(包工头、农民工、老板)、公共知识分子(记者、作家)等.可以说,冯积岐小说中的故事架构、情节、主题都是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展开的.因此,对于这三者关系的研究就成为了解冯积岐小说,甚至当代陕西小说的一个关键视角.
1 统一和转换:宗族身份与政治身份
在冯积岐的小说《大树底下》、《沉默的季节》、《敲门》、《村子》中,基本上都涉及到明显的政治身份标识,即按照阶级成分来划分和识别身份的身份词语.如“地主”、“地主狗崽子”、“富农”、“贫下中农”、“黑五类”、“社员”等,这些词语在其小说中多次反复出现,并以无产阶级的“社员”、“贫下中农”与其对立面的“地主”、“地主狗崽子”、“富农”、“黑五类”等的对立形式出现.在冯积岐的小说中,在政治身份旁,往往还有一种身份,那就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来划分身份的中国传统宗族身份.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统一和转换的关系.
政治身份与宗族身份之间的统一关系,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表现为两种样态.一是当政治身份为无产阶级身份时,政治身份与宗族身份之间以一种互相团结的形式出现,并且往往政治身份的获得就是以宗族身份为基础的.如在他的小说《村子》中,田广荣的村支书被罢免后,他鼓动松陵村党员写告状信,状告公社党委书记江涛打击老干部,“在这封告状信上签名的有田兴国、田水祥、田壮壮、田根根、田得安、田劳劳等三十三名党员,占了松陵村六十四名党员的一半还多.告状的党员全都姓田.在这些田姓党员中,有解放初起和田广荣一起入党的老党员,有六十年代田广荣培养的积极分子,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突击入党的年轻人.在党员会上,他们都是田广荣的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则是田广荣的兄弟、侄儿或孙子辈,田广荣是他们的二哥、六爸或五爷.生活在松陵村庄稼人都处在家门户族之中,田广荣也一样.况且,他是田姓的长辈,不仅仅是支部书记.”而江涛到松陵村后,拿到该村党员花名册,“他一看田姓党员竟然有四十四名,占党员人数的70%.江涛合上花名册,不由得骂道:‘他娘的!田广荣把松陵村搞成田家党了’”[5].由这一段描述,看到这样的事实,即田广荣是村支部书记,又是田姓的长辈,维护田广荣的政治身份——村支部书记,就是维护田姓人的威望和利益.在此,政治身份与宗族身份之间没有任何障碍地融合在了一起.一是当是无产阶级的对立阶级时,政治身份和宗族身份也是一致的,都是作为要打倒和消灭的对象.如《大树底下》的罗世俊一家被划为地主阶级,其在政治身份上已被打倒,“罗”姓随之也被打倒,其大哥罗世堂打断他父亲的墓碑,改姓“牛”,就是宗族身份被打倒和被消灭的表现.这种被打倒和消灭的情形在《敲门》中的马汉朝一家,《沉默的季节》中的周雨言一家中都有体现,他们直接就被划定为人民的对立面,受到了无情的镇压,他们的宗族身份和政治身份是一致的.总之,政治身份与宗族身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统一状态,要么宗族身份与政治身份一同被认可,要么宗族身份和政治身份一同被打倒和消灭.
在冯积岐的小说中,政治身份和宗族身份之间除了统一关系外,还存在着转换关系.这种转换关系表现为一种样态,即个体所在的一类“姓氏”的宗族身份与政治身份对立时,宗族身份成为自身生存的障碍,被个体抛弃,个体转而进入另一个被政治身份认同的的宗族之中,通过改姓,获得生存权甚至进步的政治身份.这在冯积岐的长篇小说《大树底下》有非常典型的体现.当要给罗世俊补订地主身份时,其“大哥”(虽然这个大哥并非亲生,但是却是罗世俊父亲认的干儿子,可以说在宗族关系中,他们之间的兄弟之情是具有合法性的.)做了伪证指证了他家是地主成分.于是其大哥罗世堂成为了社交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罗世堂成为社交运动的积极分子之前,冯积岐在小说中具体描写了身份的转换策略,卫明哲跟罗世堂谈过三次话,第一次直接说让罗世堂指证罗家是地主,罗世堂没有答应;第二次,卫明哲用成为贫农之后,所得到的利益利诱罗世堂,罗世堂仍然没有答应;第三次,卫明哲用地主及其子孙悲惨的生活来恐吓罗世堂,罗世堂答应了.紧接着,他就改了姓,说自己叫牛世堂.从这样的转换过程中,可以看到,宗族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互换是这样的,即个体通过抛弃一个与政治身份对立的宗族身份,选择一个与政治身份一致的宗族身份,就可以实现自身身份的转换,并获得自身身份的合理性.
2 对立:宗族身份、政治身份与多元身份
在冯积岐的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1979年前后主人公的境遇完全不同,这个时间节点成为其架构故事的分水岭.在其小说中,1979年后的身份标识与1979年前全然不同,当他描写到1979年之后时,其小说中出现的身份高频词是“告状人”、“老板”、“包工头”、“农民工”、“记者”、“作家”等,这些身份词语显然与以往的宗族身份、政治身份大为不同,他们都是新的身份标识,主要以职业性质作为划分身份的标准,具有多元特性.可将他们归类为三种,法律人(告状人),经济人(老板、包工头、农民工等),公共知识分子(作者、记者).在冯积岐的小说中,这一类多元身份与宗族身份、政治身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统一和转换的关系,而是对立关系.
这种关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表现.一种是发生在农村内部,主要以阶级身份与经济人身份之间的对立为表征.这种冲突,在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中的田水祥身上可以看到.当1979年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阶级斗争不再是主要中心时,村领导田广荣任命祝永达来管账,田水祥表示反对,当反对无效后,他到父亲的坟头上大哭了一场,此一场景,看做是政治身份(无产阶级身份)丧失和无效之后的迷茫之哭,他无法将自己从一种单一的宗族身份或者是无产阶级身份转为现代的管理者身份,他认为祝永达进入村委,是地主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攻,也是田广荣不看重宗族身份的表现.他反对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无法将自己从政治身份挂帅的情境下转为经济人身份为主的情境,他的生活陷入拮据,也不知如何解决.他将祝永达管账、联产承包责任制看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这是经济人(管账人)与政治身份之间的对立具体体现.
另外一种身份上的对立发生在农村和城市的冲突之中,这主要表现在传统宗族身份和多元身份之间,即以宗族身份与以契约为基础的理性经济人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以及宗族身份和法律人身份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情形我们依旧可以在冯积岐的小说《村子》中的两个典型事例中窥得.一是,村民与乡镇办事人员发生冲突时,祝永达鼓励村民去告状,而村民不告时,他对自身和农民的失望.二是,在处理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的冲突时,包工头不给农民工工资,并殴打农民工时,他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采用了破坏机器,使机器停工,殴打包工头的方式来对抗.从这两个事件中,可看到这样的矛盾性.即在第一个事件中,祝永达在处理乡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冲突时,用的是法律,可以看到他此时有似乎是有公民意识(即每个公民拥有法律权利)的,期望通过法律来寻回公正.而在第二个事件中,祝永达的公民意识全无,他采用使机器停工、殴打包工头的非法方式来讨要工钱.其实这两个事件背后折射出的恰恰是祝永达对现代的法律人、经济人等现代身份认识不足的事实.他看到了由法律所带来的人人平等,但却对法律所赖以成立的基础——即契约关系认识不足,所以才会导致他在碰到经济纠纷(第二个事件)时,作出违法的行为,并且认为农民工的凄惨生活,是因为包工头心太黑导致的.他后来跟马秀萍说:“我不想受制于老板,人一当老板心就黑了.”[6]正体现了这一点.由此,基本可以看出祝永达对于法律人和经济人的认识,即祝永达将农民工凄惨生活的原因归为包工头的道德品质坏,而没有看到现代经济关系其实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生产关系,他有一套区别于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和技术特征以及控制手段,这是一整套的现代经济运作机制,农民工要不到工资,并不是因为包工头品质坏,而是这一整套的生产机制有着马克思所讲的追求最大剩余价值的本性,若没有一套有效的法律机制去制约这种机制,那么即使换一个品质好的包工头,也改变不了农民工受剥削的命运.因此说,他在意识中抛弃了现代经济赖以维持其运转的契约关系,但仍然要寻求由契约关系所带来的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独立等许诺,显然是不可能找到的,所以“他深深感到,庄稼人要到这个城市来吃苦卖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6]当将两件事联系起来,继续探究祝永达的深层意识时,就发现祝永达鼓励农民告状,为农民工出头等行为,认为人当了老板,心就黑的意识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道义意识,这种意识在世俗的生活中,尤其是在农村中,是以宗族身份为核心形成的乡邻之间互相协作、守望相助的意识,以替弱者伸张权利、追求公正为目的,这种意识不仅表现在同族同姓的互帮互助上,而且会扩展为对同乡、甚至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帮助上.承担此“道义”的人一般具有传统伦理道德上所限定的具有“君子”人格的人.而此意识并非我们上面所谈到的现代法律人、经济人得以形成的契约意识,而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道义意识.所以,当祝永达用道义意识来认识和统摄现代社会的法律人、经济人身份时,结局就是他自己从城市失败而归.如果说祝永达到城里打工所遇到的这种身份认知上的不足是底层农民从乡村走向城市所必然遭遇的境况,那么,其短篇小说《这块土地》中的冯秀坤、长篇小说《遍地温柔》中的潘尚峰,这些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作家,代表的则是知识分子阶层所面临的在身份认同上的不足.这种认识上的不足表现为其从城市回到农村,无法理解乡村随着经济大潮而来的宗族身份、以及以此为核心的各种乡村伦理关系的崩解,同时又希望通过宗族身份或者是新的现代身份(小说中往往是记者、作家)来对由经济所带来的一切进行对抗,这种对抗也往往以失败而告终,主人公要么隐居于深山老林(潘尚峰),要么无可奈何(冯秀坤).他们身上折射出的仍然是将自身身份定位为传统意义上的恪守“道义”的士阶层,而非现代意义上的多元身份.因为记者、作家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的产生机制是在知识的竞争中产生的,而不是在伦理道德的高低中产生的,可以说一个在求真中产生,一个在求善中产生,这两种身份的产生机制截然不同,且二者之间是对立的,因此,他们用现代的多元身份来拯救传统伦理道德显然不可能成功,而另一方面,宗族身份已经在经济大潮中,无力拯救传统伦理道德和传统文化,所以无论是哪种身份来拯救传统伦理道德,其结局只能是溃败,要么隐居,要么无奈.因此,可以说宗族身份与法律人、经济人之间的关系仍表现出对立的特性.
3 原 因
当进一步去探究以上关系产生的原因时,发现造成以上叙述模式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作者自身的意识,二是社会身份机制的不同.从作者自身意识来看,冯积岐小说中的身份关系是被作者建构起来的,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主导了关系的建立.就第一种关系而言,冯积岐在其《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中谈到作为地主狗崽子的心理体验,他说“我开始了不是人的人生.我的生活状态如同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地洞》中的老鼠,即是在地洞中也是惴惴不安.在以后的青年和中年的前半期,我左冲右突,总是冲不出心理上的囹圄.”[7]这可以看做是他对他的小说之所以塑造了统一和转换的身份关系的一种解释,这种惴惴不安、不是人的人生表现在“地主娃”、“黑五类”等主人公身上,表现为在那个时期永远不可能改变的阶级身份所带来的心理上的惴惴不安以及在身份认同上的无所适从感.而1979年之后,他自身生活状态的变化,也使得其小说中人物身份关系发生了变化,他从农村走向城市,可是目光和作品仍然关注着乡村.他发现,“上个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间,乡村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分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热情,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等原来归属于“资本主义”的胚芽开始在农民心中形成、生长.儒家文化中的绅士文化、伦理文化受到了严重冲击.乡村的和谐局面自然而然被打破了,穷富差别拉大了,农民的经济地位在变化,心理在变化.特别是,强权使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陷入了心理灾难.乡村向城镇逼近的同时,原来的比较和谐的农村受到了冲击.住上了大瓦房的农民精神上走向贫困.我所渴望的青少年时期的贫穷而温馨的乡村形象不会复而再现了.我眼中的乡村已不伦不类了.”[8]这段话典型地体现了冯积岐对1979年后乡村的基本体验和认知,其中夹杂着对身份冲突的认识,即“资本主义”(现代多元身份)与乡绅文化、伦理文化(传统身份)的冲突.这在其小说中还涉及到了阶级身份与多元身份之间的冲突.他也将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对立表现了出来.但是这种对于对立的表现,因为他自身对于传统乡村的眷恋而未能更加深刻,正如其所言,“乡村已不伦不类了”.而这不伦不类的乡村及生活在这样乡村下的村民将如何来面对自身的现代身份,冯积岐并未给出满意的答案,他正如自己所言,再次逃离了这个问题.这一方面说明作者自身对于传统身份的眷恋,另一方面说明作者自身对现代身份的认知有限.他不能看到现代的多元身份强调的是异质性,人的自由、平等、尊严要在契约基础上来实现.这就涉及到了他的小说中身份关系之所以如此表述的第二个原因.
从身份机制上来看,在第一种统一和转换关系中,可看到,政治身份机制与宗族身份机制之间存在某种同质性.政治身份机制是以阶级出身为核心,以阶级斗争为动力,通过吸收无产阶级成员,教育、斗争非无产阶级成员,在斗争中实现身份同质化,个体通过获得政治上的身份,来获得自身身份认知,从而获得稳定和连续的身份.这种机制以“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的对立形式被组织起来.在农村中,则以“社员”和“非社员”为表现形式被组织和编码.宗族身份机制则以血缘亲疏远近为标准,将个体按照等级序列编码进入这种系统,通过相同姓氏组织成为家族和宗族的身份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每个个体的身份标识码是“姓氏”,个体通过获得“姓”以及名字中的辈分获得自身的身份认知,从而获得自身稳定的和连续的宗族身份.这两种身份机制虽然不同,但有某些同质性.即这两种机制间具有相同的运行模式,即都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标准,将个体编码进入一定的序列中,通过控制同质个体,转换吸收、打击消灭异质个体,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控制.在这样的机制中,个体的存在以集体的存在为前提,并以集体的利益为旨归.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二者的关系不可能表现出对立状态,而只能是统一和转换状态.在第二种对立关系中,政治身份机制、宗族身份机制与多元身份机制之间存在着异质性.当强调同质性的政治身份机制、宗族身份机制遭遇强调异质性的多元身份机制时,其对抗性就表现的特别明显.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所面临的身份问题更为复杂,也就是说,1979年后的身份识别机制已与1979年前的身份识别机制大为不同.1979年后的身份识别机制表现为以契约关系为基础之上的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体的独立、平等、价值等都需要在此机制中不断得到界定.而这个机制的大前提是承认个体的差异性,个体在此机制中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权力和利益,形成契约,在契约的基础上实现个体价值.所以,当同质化的单一身份机制遭遇强调异质特性的契约关系机制时,农民若仍然用单一身份机制下的智识结构来会解多元身份,那么单一身份与多元身份之间就只能表现出对立的特性来了.
4 结 论
冯积岐小说中所呈现的身份问题,其实向我们彰显了这样的事实.即1949至1979年间,农民所面临的身份问题是单一身份内部的关系问题,即传统身份与政治身份之间的统一和转换关系,由于二者运行模式大致相同,所以相对而言,身份认知较为容易.而1979年之后,农民所面临的身份问题更为复杂,他们要面对传统身份、政治身份和经济人、法律人、公共知识分子等现代身份之间的对立关系,因此相对而言,身份认知较为不易.可以说,冯积岐的小说基本呈现了中国自建国以来的社会身份的变化及其关系,但是他的小说也有自身的局限,即他小说中并未对单一身份内部的宗族身份与政治身份的统一基础进行有效地、具体地表达,即宗族身份与政治身份为什么能够统一没有具体的表达出来,也对单一身份与多元身份之间为何会呈现对立认识不足,所以他的小说给出的解决这种对立关系的方法大都是遁世(隐居深山)或无可奈何.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当代小说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作家所面临的问题,因为他涉及到了中国如何进行现代转型的问题,即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新的经济形势带来了现代化的问题,他不仅将广大农村纳入到了新的以科技、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进程之中,使得物质极大丰富,同时也将农村中的精神生活纳入到了现代性的进程之中[9],他迫使农民开始正视自身新的生存环境,以及由这种生存环境所带来的新的身份问题.与前期的单一身份不同,此时的身份不会以一种稳定的、固定的形式出现[10],他会以经济人、法律人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多元身份出现.这种身份迅速瓦解掉了支撑中国社会得以运转的传统道德意识和阶级意识,将个体抛入到了一个强调异质性、对立、个体价值相对自由的契约关系之中,若个体或者群体仍用单一身份下的智识结构来思考身份和选择身份,那么个体或群体体验到的将是无法整合自我,理解自我的焦虑感,其结局必然也是像冯积岐小说中所描述的,农民走出乡村到了城市,成不了城里人,也再不是农民(冯秀坤、祝永达、潘尚峰皆是如此),其身份认知上会出现缺失和真空,进而失去身份认同.
[1] 冯积岐.村子[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FENG ji-qi.Village[M].Xi’an:Taibai Press,2007.(in Chinese)
[2] 冯积岐.村子[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FENG ji-qi.Village[M].Xi’an:Taibai Press,2007.(in Chinese)
[3] 冯积岐.村子[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FENG ji-qi.Village[M].Xi’an:Taibai Press,2007,(in Chinese)
[4] 吴妍妍,冯积岐.写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冯积岐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2(3):75.WU Yan-yan,FENG Ji-qi.Writing is an form of Liv-ing-An Interview with FENG ji-qi[J].Criticism of Fictions,2012(3):75.(in Chinese)
[5] 拉雷恩,戴从容,译.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Jorge Larrain.Ideology and Cultural Identity:Modernity and the Third World Presence[M].DAI Congrong,Translated.Shanghai:Shangha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5.(in Chinese)
[6] 马克思,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MARX K,ENGEIS F.The Communist Manifesto[M].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Bureall,Translated.Beijing:Renmin press,1997.(in Chinese)
[7] 冯积岐.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这块土地[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FENG Ji-qi.My Father and Mother are Farmers[M].Beijing:Yanshan Publishing House,1999.(in Chinese)
[8] 冯积岐.大树底下[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FENG ji-qi.Under the Big Tree[M].Xi’an:Taibai Press,2007.(in Chinese)
[9] 冯积岐.遍地温柔[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FENG Ji-qi.Tender Everywhere[M].Beijing:China Society Press,2008.(in Chinese)
[10] 冯积岐.沉默的季节[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FENG Ji-qi.The Silent Season [M].Wuhan:Changjiang Literature & Art Press,2008.(in Chinese)
【相关参考文献链接】
潘婉莹.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边缘人物分析[J].2011,31(6):575.
王凌.古代白话小说“重复”叙述技巧谫论[J].2013,33(9):768.
吴妍妍.可读性的重视与陈忠实的文学观念[J].2014,34(7):598.
都晓晶.论詹姆斯·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J].2014,34(9):771.
曹小娟.许地山的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J].2014,34(5):411.
臧 文 静.鲁 迅 杂 文 的 否 定 性 意 象 [J].2013,33(11):930.
寇瑶.人道价值论与天道价值论述评[J].2013,33(3):253.
王素.洪州禅宗要辨义[J].2012,32(1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