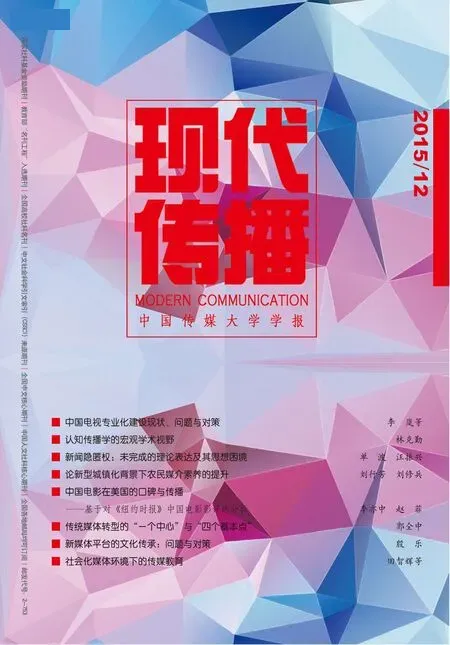影像叙事语言对当代文学叙事语言的转换困顿
■ 江逐浪
影像叙事语言对当代文学叙事语言的转换困顿
■ 江逐浪
近年来,影像语言在符号层面上取得了迅猛的发展,可是某种程度上说在影像叙事技巧上的成就却裹足不前。一些举世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文学作品,如《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喧哗与骚动》等至今未被移植为影视作品,即源于当代文学作品在叙事技巧上取得的重大突破,至今却未能被影像语言成功转化。目前用影像叙事语言转换文学叙事的困顿,主要集中在如何移植文学发展出的多种内聚焦叙事特征上。要突破这个困顿,影像创作者既需要作出更多的技术探索,也需要突破对受众影像的认知能力和思维习惯的理解。
影像语言;影像叙事;文学叙事;隐藏叙事者;内聚焦
2013年戛纳电影节上展映的电影《我弥留之际》,是对威廉·福克纳(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著《我弥留之际》的一次实验性改编,但导演詹姆斯·弗兰克用影像来展现原著立体叙事魅力的尝试却没有获得一致认可——它获得的是旨在鼓励小众的、艺术影片的“一种关注奖”,而非完全承认其成果的金棕榈奖或导演奖。与原作相比,电影的确未能真正展现出原著叙事魅力的精髓,反倒凸显了影像叙事语言对当代文学叙事语言转换的困境。
关于文学语言与影像语言之间关系的讨论一度中止。虽然以巴赞为代表的电影理论家指出影像语言具有暧昧性、多义性的特点,缺乏从整体上、本质上把握世界的能力,但当代人们更看重影像语言的感官直接性、形象具体性等特点,从而利用数字特效技术发展各种视觉奇观,来扩张影像语言表现世界的外在形态时所具有的优势。与之相比,人们对影像语言在叙事层面的探索却是比较罕见的。究其原因,人们对影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研究,关注的重心是在“文字”与“影像”这两个符号层面。“电影的美学的丰富性来自这样的事实,它包含了记号的三个方面:指示性、肖似的和象征的。”①新的特技手段、视觉奇观都是在指示性、肖似的和象征性上丰富影像符号的表现力,而较少将两种语言置于叙事的层面上进行更综合、全面的比较。因此,面对发展的日益复杂的文学叙事,影像叙事显露出简单、薄弱的疲态。
一、意识流叙事:影像叙事语言转换文学叙事语言的一次成功
20世纪以来,文学语言充分意识到了影像语言所形成的挑战,放弃了用文字来努力还原世界的外在形态的特点,从自身的特点出发,从叙事手法上探索文学叙事的各种可能。其具体表现,就是文学从19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自然主义中脱离出来,令“现代小说”以创作手法新颖、众多著称。
20世纪文学叙事技巧的一大显著成就,是意识流写作手法的出现。意识流叙事将人物过去的意识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用跳跃的叙事时序来破坏生活中的线性事件发展时序,故意制造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分离,提请受众有重组时间感。这种文学叙事手段是对文学叙事特点有意识的利用,它蓄意加大了时间、意识对叙事的干涉,在叙事过程中频繁、明显地中断叙事的自然存在性。而且,由于“读(听)一部叙事作品,不仅仅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读(听)下去,也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读(听)下去”②,它事实上也再造了文学作品的叙事等级,产生新的审美效果。
面对文学叙事在20世纪的这一突然转向,影像叙事最初也做了很多探索。从格里菲斯计划拍摄《资本论》到20世纪20年代的先锋派电影运动的各种实验,影像叙事的叙事理念、叙事能力等被探索了一番。此后,瑞典的英格玛·伯格曼和法国的左岸派电影人都探索了用影像语言转换文学语言中的意识流叙事的手法、特点和效果,利用“闪回”“跳接”等传统剪辑手段来展现文学中意识流叙事的动态性、无逻辑性、非理性特点,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经过数十年来的发展和积累,影像语言已不仅仅能够进行自己的意识流叙事,进而由此将非线性叙事的叙事技巧发展成熟,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商业片(如《低俗小说》《云图》等)正是以非线性叙事特征而被人称道——虽然这是文学意识流叙事早在20年代就已经发展成熟的特征。例如,1929年出版的《喧哗与骚动》就打乱了整体叙述的时间线,是《低俗小说》等非线性叙事电影的先驱。
意识流是文学叙事立足于文字语言的特性之上绽放的鲜花,意识流电影、非线性叙事电影却是这朵鲜花结出的另一颗硕果。这是影像叙事对当代文学叙事转换的成果。但是,影像语言至今却未能成功地转化20世纪文学叙事的另一个重要突破:内聚焦叙事。
二、叙事视角:影像语言转换文学语言的瓶颈
传统的经典文学作品,通常采取零聚焦的叙事视角,即“上帝视角”。在这种视角下,叙事者与被叙述的人物形象分离,可以从所有的角度观察被叙述者的故事,任意从一个位置移向另一个位置,体现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优越性。
但是20世纪却出现了大量以内聚焦型视角来叙事的作品,其中既包括古已有之的固定内聚焦叙事(被叙述的事件通过单一人物的意识现出,视角自始至终来自同一个人物),还包括大量不定内聚焦(采用多个人物的固定内聚焦视角来呈现不同事件)和多重内聚焦(采用多个人物的固定内聚焦视角来呈现相同事件)。③
以内聚焦为代表的叙事视角的改变,是与用意识流来改变叙事时序同等重要的文学叙事的发展。许多优秀的当代文学作品甚至是同时结合了这两种叙事手段,营造了复杂深奥、幽微繁复的审美效果。但是,影像叙事语言在应对当代文学的叙事视角转向时却撞到了隐形天花板——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当代影像语言能够创作成功的意识流文学作品,却至今未能成功转换以内聚焦叙事的文学作品。《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尤利西斯》等兼具意识流和不定内聚焦或多重内聚焦叙事特征的文学作品甚至从未被试着搬上银幕,《我弥留之际》也未获得一致认可的成功。这些空白或不成功的尝试揭示了当代影像叙事语言面对文学叙事语言的转换困顿。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影像语言是有能力模拟内聚焦特征的。只要摄像机的机位、角度合适,镜头影像可以与人物的视域相吻合,甚至于,影像的推拉运动虽然看似与人眼观察事物的物理特性不同,但与人观看的心理感觉过程相似。例如,推镜头的心理基础就是“寻找者的视野突然收缩,思想意识也就更明确,他不仅看到了那个人,他的感觉在这时候已经强化了,视野越显有限,这种强化程度也就越高。就能使观者感到自己是受到了影响,身临其境。”④可见,影像叙事缺少的不是影像语言的能力,而是用内聚焦进行叙事的意识。绝大多数电影中都会片段地出现一些具有内聚焦叙事特征的“主观镜头”,但从整体上尝试用内聚焦来进行影像叙事的却少之又少。例如,电影《罗生门》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电影《罗生门》的主要情节来自芥川龙之介192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竹林中》,小说的全文就是七个人物的七段叙述,是多重内聚焦叙事的典范。电影把叙事人减为四个,在每个人物的叙事段落中都尽量展现原作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的特点,让镜头角度、机位、构图、光影都尽量与叙事者贴近,强烈地暗示每个叙事者的个人感受。然而,这个尝试却并不彻底。原作通篇没有任何陈述性语言,可以说是一个由七段“主观镜头”组成的叙事。而电影中却有大量客观镜头存在。例如,原作小说并不需要交待鬼魂如何借助巫女之口诉说,可是电影却花了一段篇幅去展示巫女作法招魂。而拍摄招魂段落时,影像的镜头是没有“人称”的,是脱离影片中任何一个人物的视点的,明显是外在于人物的视角。因此,这部电影并不是一个多重内聚焦视角叙事的电影,而是将旁观的外在视角与多重内聚焦视角结合起来的作品,这种不充分的努力使得电影的影像视角仍然是传统的零聚焦视角。
将影像的视点与人物视点统一起来的“主观镜头”是早已进入观众的影像认知结构的叙事语言,当代观众已经熟练地可以从主观镜头中分辨出看和被看的关系,有些电影因此尝试着用“一镜到底”的方式,以“人物在看”代替“叙事人在看”,模拟文学中内聚焦视角的叙事效果。
“一镜到底”的尝试自1948年希区柯克的《夺魂索》开始,已经出现过若干次。《夺魂索》的最初目的只是对长镜头理论的一次极致的尝试,但随着数字长镜头的出现,“一镜到底”的技术障碍解决之后,这种拍摄手法在影像叙事视角上的意义反而更显著。但是,几部“一镜到底”的电影对零聚焦叙事视角的突破都不够彻底。其中,《夺魂索》的视角是第三人称外聚焦,只展现人物的动作,而封闭人物的内心。外聚焦叙事所具有的客观性、直观性、具体性等艺术特点恰恰与影像符号特点相一致,并不能视为影像叙事语言对自身叙事能力的突破。这种影像叙事似乎是以“纯客观记录”的方式来“退出叙事“,看似能够深度隐藏创作者的主观痕迹,尽量保证影像叙事的客观性和多义性,但这是19世纪福楼拜小说的叙事特色,而非20世纪的。20世纪作者“退出叙事”的方式不是以外聚焦的方式远距离观察,而是以内聚焦的方式真正地融入角色之中。
2008年的《俄罗斯方舟》和2014年的《鸟人》也都是“一镜到底”代表的作品。《鸟人》的叙事视角与《罗生门》相似,从瑞根第一次出现在画面中开始,观众就能够感受到隐藏叙事人的存在。《俄罗斯方舟》以牺牲叙事人形象的方式通片模拟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的特征,但画外音中的两个叙事者虽然在一边“看”一边议论和争吵,却在共用同一个主观镜头,没能展现出多重内聚焦的叙事优势来,只能作为固定内聚焦叙事的一种变体。
与固定内聚焦相比,不定内聚焦和多重内聚焦叙事被转换成影像语言的难度更大。法国叙事学家兹维坦·托多罗夫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叙事的时间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是立体的。在故事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则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一个复杂的形象就被投射到一条直线上。”⑤多重内聚焦叙事使线性—立体的矛盾增加了一个维度,更增加了影像叙事转化的难度。
不定内聚焦通过不同人物的视点接续故事,其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实现去中心化,能够把创作者的主观性成功地隐退到错综复杂的线索帷幕之后。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就是这种叙事视角的成功典范,整部小说由15个人的59段内心独白构成,分散的视角使得小说空缺出一个权威的声音,从而成功摆脱了作者这个隐藏叙事人的痕迹(完全摆脱隐藏叙事人是不可能做到的,实际上是隐藏叙事人藏得更深了)。小说的叙事建立在各自为营的角色内心之上,通过不同人物的心理独白表现出本德伦一家彼此都处在看与被看的位置上,彼此观察与被观察。电影《我弥留之际》以分屏的手法来还原这个叙事特征,画幅的左右部分分别采用不同的景别、镜头视角来展现相同的被摄主体。但即使如此,电影仍未摆脱“隐藏叙事人”的存在:大量镜头常常在没有交待“谁在看”的情况下自由运动,暴露出“上帝视角”的特点,暗示着一个无所不在的全知全能的隐藏观察者的存在,而这个观察者的存在,恰恰使电影作品丧失了原作小说最大的叙事特色。
《我弥留之际》不彻底的尝试暴露出影像语言遇到由不定内聚焦或多重内聚焦构成的立体叙事时的悖论:一方面,第一人称内聚焦强调叙事人的个人感受,而影像语言却拙于表现角色的内心情感。影像语言所具有的具体、直观的特性,要求角色抽象的情感、思绪必须被外化成具体可感的动作、表情或象征性场景。当代影视技术手段的发展虽然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人物情感、思维的外化,但这些手段运用得越丰富、越频繁,创作者主观介入的痕迹就越明显,就越与多重叙事所追求的去权威、去中心相背离。另一方面,如果影像语言较少借助技术手段,而采取传统的手段(闪回、跳接、内心独白等),却又常常要以打破线性叙事为代价,多角色共同进行非线性叙事又会为处在线性接受状态中的受众增加更多接受上的困难。同样,多人内心独白的使用,也常常是对观众声音记忆的挑战——一般来说,人们对声音的分辨能力远不如对图像的辨识能力。
当代的影像叙事习惯性地大量使用着客观镜头,而“客观镜头”事实上是影像创作者的“主观镜头”。“在银幕上,起决定作用的是艺术家的主观个性和客观现实的结合,而这种个性在电影中则表现在画面构图和镜头的选用上。”⑥影像创作者的主观性正是借“客观镜头”充分表现出来的。当前,不仅影像观众们习惯了经过隐藏叙事人选择的“客观”,连影像创作者自身也未有更深隐藏自己主观性的成功尝试,对比20世纪文学叙事所取得的成就,这是影像叙事的滞后,也应该是影像语言叙事需要突破的局限。
三、影像叙事语言需要借鉴文学叙事,突破局限
电影诞生已逾百年,但当前绝大多数影片的叙事仍沿用着半个世纪前的探索成果,这不仅与影像符号表现力的迅猛发展不相称,更与和它同为叙事艺术的文学的叙事发展相差甚远。借鉴20世纪文学叙事的成果来发展影像语言的叙事能力,至少有以下两点裨益。
首先,影像叙事可以从文学叙事所取得的成果中找寻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冲破自身发展的瓶颈。
20世纪文学叙事的语言之所以能取得突出成就,与影像语言对它的冲击有很大关系。电影在形象化叙事方面展示出的巨大潜力促使文学作者有意识地改变写作的方法和内容。从詹姆斯·乔伊斯开始,许多作家从影像语言的技巧和特点中汲取灵感,形成了自己的叙事风格。例如,擅长多重视角立体叙事的福克纳从1932年开始为米高梅、福克斯等电影公司写过20部电影剧本;张爱玲在《金锁记》中所写的句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⑦俨然就是一次电影中的蒙太奇相似转场。
与文学的发展相似,五十年代左岸派电影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也与电影人从文学中借鉴其叙事方式、拓展影像语言的修辞手段,丰富影像语言的表现力相关。而那场半个世纪前的先锋实验,其经验一直滋养着当代的影视作品,直到现在,许多深受好评的电影依旧在沿用当年阿伦·雷乃、博格曼、费里尼等人的探索成果。
当代电影的发展固然少不了纯熟、明朗的传统叙事,但影像语言仍然需要被丰富、拓展、扭转甚至再造,影像语言需要更富有表现力的新语汇、新修辞,从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其次,影像语言对自身叙事能力的探索,有助于人们对“文学改编”作出更深层的理解。
传统上,影像对文学的改编都是指用影像语言透过文字叙事去转换文学中的人物和故事,以获得文学作品的内涵为影像改编的旨归。这种改编思路使影像创作脱离了文学语言的存在,有时甚至视文学语言的特点为改编的劣势。用这种思路来改编20世纪之前的传统文学经典尚可,但20世纪出现的那些举世公认的文学名著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们突破了主题深刻、人物形象复杂饱满等传统优点,《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喧哗与骚动》《墙上的斑点》等作品的成功首在其叙事手段本身的复杂,如果剥离掉它们的叙事方式,这些作品或者主题无所附着,或者显得情节简单松散,其艺术魅力丧失殆尽。
因此,当代人应该发展对影视作“文学改编”的理解与期待,文学改编不应仍旧停留在再现原作故事情节的层面,影视语言应该尽力呈现出文学原作固有的文学美感。事实上,这种要求也一直是观众的隐性需求。例如,中国观众对《红楼梦》的影视改编的评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探讨影视作品是否还原了原著小说故事情节之外的意境、情韵。20世纪以来,由于影响叙事语言发展的滞后,那些以叙事成就为特色的文学巨著至今未能被影像叙事成功转化,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如果影像语言能够发展自身的叙事能力,成功转化这些文学作品,将有助于人们对“文学改编”作更深层的理解。
相对于文学叙事,影像叙事之所以发展滞后,创作者的观念顾虑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一直被视作经典艺术,而电影却被视为文化工业的重要一环,电影艺术也被列入到大众艺术的行列之中。有一种观念认为,大众艺术的艺术水平必须迎合观众的审美能力,不能越雷池半步。因此,即使从理论上看影像叙事语言有可能成功转换当代文学的叙事特点,但这方面的尝试却寥寥无几。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尝试与其说是对传统影像语言叙事能力的挑战,不如说是对观众观看习惯的挑战。
这种理解忽略了观众对影像的接受能力并非一成不变的。影像语言对于观众来说,既具有先在性,又具有生成性。“当我们体验世界时,我们是通过语言的范畴来体验世界的,而语言又帮助我们形成了经验本身。……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的语言范畴。”⑧观众对影像语言读解与接受的能力,是被长久以来所接受的影像塑造的,影像语言系统以及由此而来的叙事方式为观众塑造着对象世界,同时也以一种无形的力量支配和制约着用这种语言理解事物的观众的认知能力和思维习惯。如果影像作品不断为观众提供新的视听经验和新类型的影像叙事,是能够提高观众对影像叙事的读解能力,进而有可能让一些先锋的影像语言进入观众对影像语言的认知结构之中的。例如,用闪回、跳接手段进行意识流叙事的电影在五十年代是先锋、实验,打破线性叙事的《云图》所获得的高票房,充分证明这种当年的叙事实验已经被当代大多数观众理解、认可甚至喜爱,影像语言的生成性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影像语言的每一步新锐探索,也都在同时培养着能够理解、接受、鉴赏自己的受众。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像叙事语言对当代文学叙事语言的转换困顿,不仅是技术上的,更是观念上的,而后者,是更急需被突破的。
注释:
① [法]克里斯丁·麦茨等:《电影与方法——符号学文选》,李幼蒸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8页。
②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董学文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4页。
③ 相关概念参见[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137页。
⑤ 张寅德编选:《叙述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4页。
⑥ [法]亨·阿杰尔:《电影美学概述》,徐崇业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58页。
⑦ 张爱玲:《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8页。
⑧ 转引自[英]布莱恩·麦基:《思想家》,周穗明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67页。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刘 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