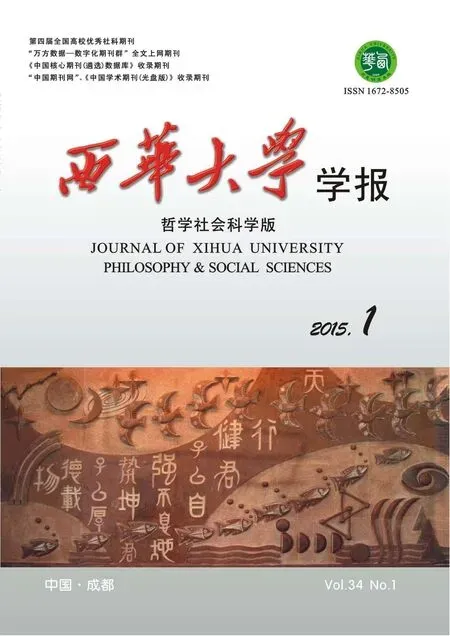四川盆地先秦时期农业考古研究述论
于孟洲 夏 微
(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2.西南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四川成都 611130)
四川盆地是我国中亚热带的一个独特而完整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区域。盆地边缘被一系列海拔2000~3000米的高山和高原环峙,形成封闭的盆地地形,加上特殊的地表组成物质作用,形成终年温湿,云多雾重,以及巨厚紫红色砂岩和页岩沉积的特点。该区动植物种类多样,动植物区系具有东西和南北交汇的特点。因自然景观差异,盆地内部又可分为成都平原、川中盆地和川东平行岭谷三部分。成都平原主要是肥沃的水稻土,灌溉便利,是四川盆地著名的农业稳产、高产地区;川中盆地地表丘陵起伏,丘陵坡脚和槽谷土层较厚,土质酥脆,结构优良,是一种比较肥沃的土壤;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的向斜谷地地形为局部平原及低丘缓岗,气候优良,是川东农业和人口的中心[1]226-231;[2]286-291。
四川盆地内河长超百公里以上的有50余条,因地形地貌特点使得各河流均由边缘山地汇聚到盆地底部各河流的总干——长江。盆地以西的川西高原和川西南山地是自古以来众多族群和民族来往的交流孔道,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3][4][5]以及童恩正先生提出的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6]17-36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上述地理特征,看似封闭的四川盆地在历史上不断与东、西、南、北方向的文化和人群发生多种形式的文化交往,特别是先秦时期西北甘青地区的旱作农业和长江中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均对四川盆地的农业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特点已在四川盆地发现的农业遗存上体现出来。
以往学界主要根据文献记载来大体考察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的农业生产状况,但是相关文献记载本身就很少又多为后世的追述且记载简略,所以依据文献,我们并不能勾画出四川盆地先秦时期农业发展过程的完整轮廓。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四川盆地尤其是成都平原和三峡库区的考古工作有了大规模进展,出土的越来越丰富的考古遗存使我们对四川盆地与外界的文化交流有了更多认识,特别是植物遗存的发现在不断补充文献记载的同时,也在不断修正我们对于四川盆地先秦时期农业历史的认识。下文将概述已发现的植物遗存资料,并在学界相关研究基础上谈谈我们对四川盆地先秦时期农业种植情况的认识,希望对从事四川盆地农史研究的学者有所帮助。至于该区域发现的动物遗存及学界对该区域渔猎经济和家畜饲养业的研究情况,限于篇幅拟另文探讨。
一、植物遗存的考古发现
1.重庆地区
忠县中坝遗址是重庆三峡库区最为重要的遗址之一。1959年,在现称为中坝遗址的何家院子第三层发现已腐烂的小米。据出土陶器看,小米的层位年代当为商周时期[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实验室对中坝遗址送交的主要年代约公元前2500~前200年间的86份浮选样本进行了植物种属鉴定和分析,发现炭化植物种子1235粒,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农作物遗存,包括黍、粟和稻谷3种谷物1166粒。其中黍629粒,粟509粒,稻米28粒。还有紫苏、商陆、豇豆属、蓼科等植物的种子。另外,还有大小不等的炭化块茎残块55块,总重1.51克,很可能是人们留下的某种实物遗存[8]394-400;①。巫山双堰塘遗址发现了类似小米和狗尾草籽粒的炭化颗粒,不见稻谷遗骸,年代为西周中晚期。发掘者提出“当时居住在长江边上的古代巴人是以吃小米为主”[9]。
云阳大地坪遗址出土的植物遗存有水稻、果核,并且该遗址还发现留有水稻印痕的陶片等②。水稻印痕表面可以清晰看出稻谷乳头状突起的压痕,水稻实体表面较光滑,保留有5%的水稻乳头状突起,无论印痕还是实体均未见芒,性质类似现代的栽培稻。大地坪遗址时代大致为距今4500~5000年之间[10]。万州中坝子遗址发现商周时期的水田遗迹。揭露出一片凹凸不平的原水田耕作面,清理出人脚印2个,牛蹄印6个和1条可能是排、放水口的小水沟(G2)。又发现几条平行的断面呈“V”字形凹槽,其中一条凹槽旁清理出两个保存较好的人脚印,连脚趾痕迹也清晰可见。发掘者推测这些凹槽可能是水田的犁沟遗迹。至于发现的小面积排列有一定规律的灰白色圆点,可能是水田作物的植株遗痕[11]351。
2.成都平原
什邡桂圆桥遗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一期(距今约5100~4600年)H43中黍的数量占绝对优势,有少量的苋科种子和粟,未发现水稻。水稻出现于一、二期(二期年代距今约4600~4300年)之交,到了二期偏晚阶段,水稻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仅有零星的黍、粟伴出[12][13]。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14]。在2009年度宝墩遗址试掘中采集浮选土样14份,其中属宝墩文化一期2段10份,宝墩文化二期2份,汉代2份。提取到炭化植物种子1430粒,包括食物类种子水稻、粟、薏苡属、野豌豆属和豇豆属。其中稻谷种子643粒,除G1中的样品外,所有的样品中都发现有水稻。莎草科在杂草类植物种子中出土概率最高,进一步证明了宝墩遗址的水稻是在本地种植和收获的;粟的数量为23粒,集中出现在宝墩一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薏苡属种子总苞片18片,仅出现在宝墩一期的地层和遗迹单位中;野生物种及杂草种子中,野豌豆58粒,其他种子共688粒。根据这一浮选结果,研究者认为宝墩遗址无论在宝墩文化阶段,还是到了汉代,都以水稻种植为主;粟在宝墩文化一期有少量种植,后期则逐渐趋向绝迹[15]68-80。同时,研究者对宝墩遗址部分地层堆积进行的植硅体分析发现典型的水稻扇形植硅体[16]。同属于宝墩文化的都江堰芒城遗址,在1998年T5941H13和1999年遗址发掘的晚期灰坑土样内,经检测都发现有水稻植硅体,说明当时可能已种植水稻[17]89;[18]99、126。
在成都金沙遗址金牛区5号C地点商末周初、西周早期和西周中晚期三个时期的15份浮选土样中发现炭化植物种子298粒,其中水稻201粒,粟粒58粒,还有少量的稻谷基盘和小穗轴。其他可鉴定的植物种子有属于禾本科的黍属、稗属、狗尾草属和黍亚科计15粒,以及野大豆1粒和紫苏3粒。另有未知10粒[19]。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送检的9﹟样品为炭化稻谷,属粳稻类。在船棺葬内还发现有梅核、普通桃核和薄皮甜瓜籽。10﹟样品可能为腌菜[20]168-169。
3.川中丘陵地区
阆中地处川中丘陵区向川北低山区过渡地带。阆中郑家坝遗址商周时期地层堆积中发现炭化种子果实35个种属,共计4476粒,其中农作物种子3756粒,粟3050粒,黍563粒,稻142粒,还有大麦1粒。非农作物又可分为杂草和果实两类,果实类种子仅4粒。杂草中豆科种子66粒,包括豇豆属种子44粒,野大豆种子1粒,以及经鉴定为豆科的种子21粒。豆科外其他杂草类种子650粒,主要有禾本科260粒,蓼科302粒,唇形科13粒,藜科10粒,莎草科11粒等。其他的杂草类种子出土数量都相对较少[21]。
除上文提到的三个区域之外,在追寻四川盆地旱作农业起源时川西北地区发现的史前农作物遗存值得关注。营盘山遗址发现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可分为炭化木屑、核果果核和植物种子三大类。清理出7992粒各种炭化植物种子,分属于农作物、杂草类和其他植物三大类共19个不同的植物种类。农作物包括粟(2350粒)和黍(2161粒)两个品种。综合出土农作物和杂草遗存看,营盘山遗址的浮选结果反映的农业具有典型的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特点[22]。文化性质与营盘山遗址相近的理县箭山寨遗址东部文化层断面暴露的一灰坑中发现有炭化的黍[23]。大渡河上游马尔康县的哈休遗址(距今5500~5000年)发现了粟等作物品种[24]。
二、研究概述与讨论
长期以来,四川盆地的植物考古研究都未能引起足够重视。除了因为这里与旱作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无缘之外,还与考古工作的开展状况以及考古遗存体现出的文化发展水平有关。上文提到的四川盆地三个小区域经过系统鉴定的植物遗存资料多属于近年发表的新资料,虽然数量仍偏少,但相比上个世纪,情况已经明显好转。并且,已有一些学者利用或多或少的农业遗存资料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相关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从事植物考古的学者对相关遗址浮选结果进行系统的鉴定分析,并根据鉴定结果探讨相关问题;另一类研究在结合植物遗存发现的同时更多依据四川盆地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对外交流情况进行分析。还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业生产与四川盆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间的关系,或者在进行其他科技考古研究中部分涉及当时的农业情况。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四川盆地先秦时期农业发展历程的了解。下文以学界探讨的问题为中心进行概述,同时谈谈我们的看法。
1.早期农业的发生背景与开始时间
有关四川盆地先秦时期农业生产信息的文献记载很少,且年代均较晚。《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童恩正先生推测杜宇族主要活动在西周至春秋中期[25]69。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为杜宇时代的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否则文献记载不会特别重视这个阶段。对于“杜宇教民务农”,童先生认为并不是事实,因为农业生产经验是劳动人民世代相传所积累,不是个别帝王的业绩。但在杜宇族统治的时代,特别是其初期,可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蜀国的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25]70。张莉红先生认为杜宇进入成都平原后,致力于农作物的选育栽培,史载江原县“小亭有好稻田”,杜宇又恰好与江原女结合,反映了蜀人对水稻生产的重视程度[26]。至于杜宇之前四川盆地农业种植情况,以前由于文献与考古资料缺乏,学界的研究推测成份过大。目前,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四川盆地的农业是外来而非原地原生的。那么,四川盆地的农业从何而来?农作物种植的时间从何时开始?从已经发现的植物遗存资料看,西南地区农业出现最早的地方应当是四川,其中川西北早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有从西北迁徙而来的马家窑文化人群,最早年代大致在距今5000年左右,学者推测其应当带来了旱作农业[27][28]。这一认识在出土的农作物遗存和考古学文化交流方面都有较为充足的证据。除前述茂县营盘山和理县箭山寨出土的植物遗存外,陈剑先生的研究还揭示了岷江上游地区和甘青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以及本土化形成过程。他将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三个演变阶段:(1)波西下层遗存,年代可上溯至距今6000年前后,受到庙底沟类型的强烈影响,是仰韶文化对外传播的产物;(2)营盘山遗存,距今约5300~5000年间,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亲缘关系;(3)沙乌都遗存,距今约4500年左右,表现出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29]。此外,还有一条旁证,就是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粟[30]168,其也属于这一条传播路线,年代大约在距今 4500 年前[27][28]。
和川西北地区相比,成都平原农业种植的历史要稍晚,什邡桂圆桥一期遗存H43出土的农作物遗存以黍为主,粟很少,根据碳十四测年,可能近于距今5000年。万娇等认为桂圆桥一期遗存是一群来自西北的人群,在适应成都平原生态环境的探索中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文化。桂圆桥二期晚段已转为以水稻为主[13]。宝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一期二段种植稻和粟,以水稻为主。江章华先生认为茂县营盘山新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与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特征基本一致,这类遗存当归入“马家窑文化”,宝墩文化很可能与岷江上游的马家窑文化有关系[31]。也有学者提出宝墩文化很可能就是由营盘山文化发展而来的[32]。由于这种文化间的联系,学者多认为宝墩文化的粟作农业当来源于西北甘青地区,并且川西北地区处于两者间的中介位置③。至于成都平原的稻作农业从何而来,学者多追溯其源头至长江中游地区[28],张弛等认为宝墩文化的稻作农业是从长江中游经过川东重庆地区传播而来。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向南拓张到曾是采集渔猎文化的峡江地区,四川的稻作农业文化是在随后发展起来的[27]。这种认识也同样从两地稻作农业的出现时间差以及两地间存在文化交流两方面得到支持。玳玉博士指出现在还很难说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人群实行的稻作和粟作农业是人群流动或仅仅是思想和技术传播的结果[28]。因为目前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研究虽已取得巨大进展,但谱系研究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比如,我们并不清楚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及更早的桂圆桥遗存和峡江地区新石器各支文化的形成机制与具体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因素变迁和人群流动情况,所以想要回答玳玉博士提出的问题还为时尚早。除桂圆桥遗址外,最近在宝墩遗址也发现有早于以往被划分为宝墩文化一期的遗存④,这类遗存发现的增多对宝墩文化起源和形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会间接促进宝墩文化农业起源问题的深入研究。
重庆地区先秦时期遗址中体现出的渔猎经济比重始终较大。白九江先生推测玉溪上层文化时期(距今6300~5300年)兴起台地旱作农业,并且这一时期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已较玉溪下层文化时期(距今7600~6300年)大大下降。他认为这一生产方式的转变,可能与四川盆地中、西部更早的,尚未被考古发现证实的原始土著文化东移有关,也不排除与西北地区的以旱作农业为生的人群南下东渐有关[33]250。由于这一认识缺乏植物遗存的直接证据,所以只能作为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推测。因为目前发现的玉溪上层文化遗存很少,对于这类遗存的认识无法深入。但是此后的哨棚嘴文化却在重庆峡江地区有大量遗址分布。据研究,哨棚嘴文化可能源于嘉陵江流域的原始文化,而后者中有些因素与马家窑文化有相似之处,哨棚嘴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相似的因素可能是通过白龙江和嘉陵江流域交流的结果[31]。这种间接或直接与马家窑文化间的交流或许解释了重庆地区旱作农业产生的原因。霍巍先生认为中坝遗址粟类作物的来源,或有可能还是通过成都平原东向传入,同时应联系到气候与环境变迁的影响[34]。此外,还有一条文化传播通道也需要引起注意。湖北巴东发现的楠木园文化遗存(约公元前5480~前4500年)是城背溪文化进入三峡地区向西扩张过程中,与陕南关中一带南来的老官台文化相遇,在巫峡以西地区形成的一类遗存[35]28-41。因为老官台文化已经发展了旱作农业[36]122-123,楠木园文化中又发现有三峡地区最早的石斧、石锄、石镰、磨盘、磨棒等农业生产工具[35]41,所以老官台文化的旱作农业是否对峡江地区产生影响值得关注。但目前已经发表的重庆地区旱作农业遗存的最早证据只有中坝遗址,年代在约公元前2500~前1750年间。因为中坝遗址是处在一种比较发达的农业经济阶段[8]402,所以我们推测旱作农业出现于重庆地区的年代应该在此之前。重庆地区目前最早的稻作遗存发现于云阳大地坪遗址,年代在距今4500~5000年之间。但是从重庆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历程看,稻作农业的出现时间可能还要更早。长江中游地区至迟在距今6300~5300年间的大溪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经取代采集狩猎成为当地经济的主体[37]。大溪文化分布的西界已经突破瞿塘峡天险,进入峡西地区。在玉溪上层文化早、中期可以看到明显的大溪文化的影响[33]97-98。这样的文化交流能否将稻作农业的信息输入?又或者还要在更早的年代既已输入稻作种植信息?孙华先生曾经推测水稻种植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可能就已传入四川,但种植的区域可能局限在重庆市区以下的长江沿岸地区[38]。由于目前一些遗址的浮选样品还未进行系统的鉴定工作,所以我们期待能有年代更早的植物遗存发现。
2.农作物种类
《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据蒙文通先生研究,此篇是古巴蜀的作品,成书年代不晚于西周中叶[39]43-62。这里提到的作物品种,除稻外,还有菽、黍、稷。《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古代巴族之“诗”:“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穀,可以養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穀旨酒,可以養母。”任乃强先生认为是阆中地区的民歌[40]5、8。从上述记载看,古代巴族是种植黍、稷的,这与考古发现是相符合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坝遗址的旱作农业特点与中国北方早期旱作农业特点略有不同,就是黍的地位略高于粟。由于黍的耐逆性强于粟,所以推测这种现象是由于当地土壤中含盐量较高造成的[8]404-406。这种情况当属于特殊现象,但对于探讨四川盆地农业种植的区域性特征具有启发意义。
从目前已经发现的农作物遗存看,还无法确定菽在四川盆地开始种植的时间。但是新津宝墩遗址发现有野豌豆和野豇豆,成都金牛区5号C地点发现有野大豆,阆中郑家坡遗址发现豇豆属和野大豆的种子,中坝遗址有豇豆属的种子,这些发现说明四川盆地史前和商周时期人群可能已经利用豆类作为食物。由于目前经鉴定属东周时期的植物遗存资料太少,所以四川盆地菽的种植历史还要等相关资料增多后才能解决。另外,阆中郑家坝遗址商周时期地层中出土大麦1粒,数量虽少,但值得关注。现中国境内发现的大麦遗存还不多,学界对大麦的来源尚存在争议。除中原地区的陶寺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中发现大麦遗存外,西北地区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距今4230±250年)和青海互助丰台遗址(距今 3660±150年)都发现大麦粒[41]184-185,[42]。川西北高原炉霍县宴尔龙石棺葬墓地发现有大麦粒[43]221-234,年代上限可到殷商早期,下限不晚于西周中期[44]32。茂县城关石棺葬墓地出土谷物经鉴定是皮大麦,盛放在釜、鍪、罐内[45]48,理县佳山石棺葬 IM2、IM4 中也发现有皮大麦[46]233,两者的年代处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末年范围内。而且,理县当地羌族至1980年代仍在种植皮大麦[46]。现代的成都平原也少量种植大麦⑤。由上述资料看,郑家坝遗址大麦的来源以及四川地区大麦种植历史的研究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3.农业种植的发展历程及区域性差异
战国时期成都平原包括农业在内的经济生产已达到较高水平。《史记·张仪列传》曾记述司马错对秦惠王所讲的一段话:“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公元前316年,秦伐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47]2283、2284灭蜀在秦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华阳国志·蜀志》,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可见,在战国末年秦灭关东的过程中,巴蜀地区提供了粮食等军需物资。李冰为蜀郡守后,兴修水利,“又溉灌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40]133。文献所述虽为秦灭巴蜀后之事,但蜀地的农业在此前肯定有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过程。这从桂圆桥、宝墩和金沙等遗址发现的植物遗存资料上可以得到较为明确的佐证。
桂圆桥遗址一期遗存的资料还太少,目前也无法对其作全面探讨。进入宝墩文化时期,除发现8座城址外,还有众多的非城遗址存在⑥,其显示出聚落等级分化加剧,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当已步入文明的门槛。另外,宝墩文化发现的石器多为磨制,偏于小型化,以斧、锛、凿为主,另有少量的刀、铲、钺、镞和矛等[48]104。这些现象都显示出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有较大发展。张弛等还指出,农业在西南地区一开始出现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早期稻作农业的单一体系,而是混杂有旱作农业的成分,很可能是以十分成熟的形态传入的,因此可以适应西南多种多样的区域生态环境。这是造成此后西南文化迅速发展、人口大量增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27]。不过,虽然能明显感觉到农业生产使成都平原史前文化快速发展,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但是,农业生产在当时的生计经济中到底占有多大比重还不好估计。一方面,宝墩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仅以石质的形式呈现,但是当时的工具种类当不止石器一种。金沙遗址“芙蓉园”北地点出土一件通体由一块整木制成的商周时期木耜[49]118-119,因为木质工具很难在考古遗址中保存下来,所以这一重要考古发现提示我们木器很有可能是当时成都平原生产工具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因目前考古发现中木器的数量很少,还无法估计木器在生产工具中所占的比重有多大。由此可以想到成都平原在宝墩文化时期也可能有木质生产工具。冯汉骥先生认为青铜时期的巴蜀文化已有相当发达的农业,不过在考古中很少发现当时的农具,想其主要为木制所致[50]138-139。童恩正先生在谈及西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地方性特点的形成原因时提到,这里茂密的森林向人们提供了大量加工方便、易于携带、取材容易、使用效率高的制造工具的原料——坚木和硬竹。木制的掘土棒,竹制的标枪,箭头和割刀,竹索或藤制的圈套,在本地区的使用一直延续到历史时代,其有效程度不但超过石器,有时连青铜也难以与之比拟[51]。所以在不清楚宝墩文化时期工具类型整体面貌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农业遗存外的其他食物来源的更多发现以便作更全面的估计。另一方面,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十二桥遗址商周时期遗存中虽以家畜作为最重要的肉食来源,但是野生动物也被作为日常生活肉量的补充[52]。我们推测宝墩文化时期,采集与狩猎经济也当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目前这方面的证据还亟待加强。
三星堆文化的农业种植情况因未见系统发表的植物遗存鉴定资料故无法作出判断,但是该文化却因为发现有规模宏大的城墙体系以及品类丰富的祭祀礼仪用器、宗庙重器等多种遗迹遗物使得学界认为其社会发展程度要高于宝墩文化,进入了古国阶段[53]。此时的农业生产也当比宝墩文化有更大的发展。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迎来古蜀文明发展的再一次高峰。春秋时期由于遗址发现较少,情况不很明确。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成都平原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生产再次迎来辉煌阶段,这也与相关文献记载大体相合。
目前,关于成都平原农业种植的发展历程有两种看法。其一,认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农业种植有一个从种植小米到普遍种植稻米的转变过程。宝墩时期的农业种植主要是种植小米。从宝墩文化三期始明显受到长江中下游的影响,推测这时起宝墩时期的人可能跟长江中下游人学习了水稻种植技术,开始种植水稻,但此时仍然以种植小米为主。从三星堆文化开始,成都平原可能开始大量种植水稻[54]。其二,认为水稻种植至迟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可能就已传入四川,但种植的区域可能局限在重庆市区以下的长江沿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甘青地区古代族群南下,四川盆地很可能是以种植粟黍为主。三星堆文化时期,四川盆地农业种植结构经历由粟黍为主到稻谷为主的转变。到十二桥文化时期,四川盆地已经转变为以种植稻米为主,粟黍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四川盆地史前农业中水稻和粟黍并存的发展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古蜀国开明王朝时期。到了战国晚期,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到秦灭巴蜀后,四川盆地的谷物种类种植集中到了水稻上,人民的主要食物名单中已经缺少了粟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明代[38]。上述两种观点都认为成都平原的农业种植结构有一个从以粟(黍)为主到以水稻为主的转变过程,但两种观点提出时可用的植物遗存鉴定资料还很少。从现有资料看,这种转变过程可能在宝墩文化一期就已经完成了,比以前设想的年代要早许多。金牛区5号C地点的鉴定结果显示这种农业种植结构一直持续至西周中晚期[19]。至于此后稻作与粟作在农业种植结构中的比重变化及其原因还需要我们结合更多的植物遗存发现与成都平原的环境变迁作综合考虑。
川东地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这里地貌复杂,背斜成山,向斜为谷,沿江台地活动空间有限,限制了人群的规模,社会结构也比较简单。面水背山的环境又使人们有十分丰富的陆生动植物资源和水生动物资源,人类的生存条件较为优越,缺少发展农业、改进技术的原动力[33]。所以,先秦时期重庆地区的农业生产始终发展水平不高。各遗址中发现的渔猎工具和打制石器都明显多于成都平原,便是这种状况的一个反映。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发现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从早期到晚期,石制品中磨制石器比例有所增加[33],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
忠县中坝遗址浮选结果总体显示出该区域以种植旱地作物黍和粟为主,稻作可能属于一种辅助性地位,甚至不排除稻谷属于舶来品的可能[8]404。对中坝人类牙釉质中C和O同位素进行测试,样本的 δ13C值主要在 -4.4‰ ~ -2.0‰之间,说明中坝先民所吃的食物中水稻、小麦等C3植物含量较少,而以粟等C4作物为主[55]。计算植物遗存的出土概率,中坝遗址黍的出土概率是65.1%,粟为59.3%,而稻米仅为16.3%,这与使用绝对数量的统计结果基本吻合。但是,按照不同层位分别进行统计和计算,却发现属于年代最早的第一期(约公元前2500~前1750年)样品中,黍的出土概率为72.0%,粟为44.0%,稻谷为4.0%。而年代较晚的第三期(约公元前1100~前200年)样品中,黍的出土概率为61.7%,粟为 65.0%,稻谷增加到 21.6%[8]404。除了黍和粟的出土概率有所变化外,稻谷的出土概率有了明显增加。重庆地区已发表的经过系统鉴定的植物遗存资料太少,前述中坝遗址表现出的农业种植特点完全有可能属于个例。
另外,重庆地区各遗址间表现出的农业种植情况远较成都平原复杂,大地坪和中坝子发现稻作遗存或水稻田遗迹;双堰塘遗址发现小米遗存;中坝遗址发现的农作物遗存以旱作为主,水稻很少。这种复杂的情况与本地多样的地形和土壤条件相符。作为重要的文化交流走廊,不同时期与周邻地区的文化交流也对农业种植产生较大影响。至于气候环境的变迁与农业种植结构间的关系,我们觉得还需谨慎判定。川中丘陵地区郑家坝遗址以旱作为主,表现出与同时期成都平原不同的特点。因为该区域地表丘陵起伏,地貌特点与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都有所不同,在农业种植结构上或许表现出另外的特点。现在的川中盆地实行精细耕作,谷地多为双季稻连作冬小麦或油菜。丘陵坡地上的梯田常为水稻、小麦(或油菜)两熟制。丘顶则为旱作一年两属,夏季以甘薯或花生为主,冬季种豌豆或小麦[1]230。所以,仅凭郑家坝一处遗址还不足以全面地说明问题,我们需要不同小区域不同地形条件下的遗址资料,才能把川中丘陵地区的农业种植情况搞清楚。四川盆地农业种植存在区域性特点是可以肯定的,地貌复杂的地区应该还存在遗址间的差异,这种特点也说明了古代先民能够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系统以适应不同的地理环境。
结语
开展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的农史研究存在巨大潜力,也具有深远意义。这里是先秦时期独具特色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区。盆地内部地貌多样,古代人群复杂,不同时期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于这样独特的区域,先秦时期开始农业种植的动机,不同阶段农业种植的特点及总体发展历程,都应当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特点,这些都是我国农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往的考古工作多未进行浮选和植物遗存鉴定工作,所以有大片的空白区域亟需填补。近年发表的宝墩、金牛区5号C地点以及郑家坝和中坝等遗址的植物遗存鉴定报告为四川盆地先秦时期农业考古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这些散点式的发现和研究还无法勾勒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时空框架,缺环依旧很多。曾有学者指出四川盆地长江及其支流的沿岸,分布着无数由一、二级阶地组成的冲击平原——“坝子”,这些平坝大小不等,连同周围的方山丘陵,形成一连串绵延不断、而又相对间隔的农业村落小区,并称之为“坝子文化”[56]124。在地形条件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处于不同区域的不同遗址完全有可能在农业种植上体现不同的特点,比如在对于旱作或稻作农业如何选择,两者的种植比例,农业种植与采集渔猎间如何互补等问题上。也有的遗址并不适合农业种植,而可能完全以渔猎经济为主⑦。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先秦时期单个遗址植物遗存分析结果以便详细归纳和探索四川盆地农业种植的统一性和区域性特点。
四川盆地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在近些年有了飞跃发展,考古工作者已经开始密切关注各遗址透露出的农业种植信息,一些史前和商周时期遗址发掘中都进行了植物浮选工作。可以相信,四川盆地先秦时期的农史研究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有更大的进展。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样品的年代是根据404页正文获得,在总数为86份的样品中,有25份属于第一期(约公元前2500~前1750年),60份属于第三期(约公元前1100~前200年),详见《中国盐业考古》第三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②2014年1月2日,笔者参观重庆三峡博物馆时,在“远古巴渝”展厅看见云阳大地坪遗址出土的两片留有水稻印痕的陶片。
③张弛等认为西南地区现在有很多证据表明,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已经有西北种植粟类作物的农民进入了川西北,但在川西北的移民和传播路线目前所知还一直限于有黄土分布的区域,影响到四川盆地的时间应该在宝墩文化时期。详见参考文献[27]《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
④蒙成都博物院左志强先生见告,在此致谢。
⑤比如温江、大邑等地在1911~1985年间还少量种植大麦,见四川省温江县志编纂委员会:《温江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6页;四川省大邑县志编纂委员会:《大邑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⑥已发现的遗址数量较多,不便逐一列举,可以参见《成都考古发现》1999—2010卷中的相关简报,科学出版社,2001—2012年。
⑦奉节老关庙遗址可能属于这类遗址,详见参考文献[33]《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第252—253页。
[1] 任美锷主编.中国自然地理纲要[M].(修订第三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3] 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4] 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M]//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5]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6] 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C]//文物与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7] 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等.四川忠县井沟遗址的试掘[J].考古,1962(8).
[8] 赵志军,等.中坝遗址浮选结果分析报告[M]//中国盐业考古·第三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9] 梁中合,等.巫山双堰塘遗址考古发现典型西周陶窑[N].中国文物报,2002-06-14.
[10] 席道合.重庆云阳大地坪发掘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N].中国文物报,2003-07-30.
[11] 西北大学考古队,等.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C]//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四川什邡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2013(9).
[13] 万娇,等.桂圆桥遗址与成都平原新石器文化发展脉络[J].文物,2013(9).
[14] 江章华,等.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J].考古学报,2002(1).
[15] 姜铭,等.新津宝墩遗址2009年度考古试掘浮选结果分析简报[M]//成都考古发现(2009).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16] 宝墩遗址第三掘4500年前古蜀城轮廓现世[EB/OL].[2012-04 -06].http://cd.qq.com/a/20120406/000031.htm.
[17]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M]//成都考古发现(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8]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市芒城遗址1999年度发掘工作简报[M]//成都考古发现(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9] 姜铭,等.四川成都城乡一体化工程金牛区5号C地点考古出土植物遗存分析报告[J].南方文物,2011(3).
[20]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商业街船棺葬[M]//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植物残体鉴定报告·附录六.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21] 闫雪,等.四川阆中市郑家坝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兼谈四川地区先秦时期炭化植物遗存[J].四川文物,2013(4).
[22] 赵志军,等.四川茂县营盘山遗址浮选结果及分析[J].南方文物,2011(3).
[23] 徐学书.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初步研究[J].考古,1995(5).
[24] 陈剑,等.大渡河上游史前文化寻踪[J].中华文化论坛,2006(3).
[25]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26] 张莉红.成都平原稻作农业区的形成与经济社会影响[J].社会科学研究,2005(4).
[27] 张弛,等.华南和西南地区农业出现的时间及相关问题[J].南方文物,2009(2).
[28] Jade d'Alpoim Guedes.Millets,Rice,Social Complexity,and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to the Chengdu Plain and Southwest China[J].Rice,2011(4):104 -113.
[29] 陈剑.波西、营盘山及沙乌都——浅析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演变的阶段性[J].考古与文物,2007(5).
[30] 吴玉书,等.卡若遗址的孢粉分析与栽培作物的研究[M]//昌都卡若·附录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1] 江章华.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遗存新发现的几点思考[J].四川文物,2004(3).
[32] 黄昊德,等.宝墩文化的发现及其来源考察[J].中华文化论坛,2004(2).
[33] 白九江.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以三峡地区为中心[M].成都:巴蜀书社,2010.
[34] 霍巍.成都平原史前农业考古新发现及其启示[J].中华文化论坛,2009(增刊).
[35] 余西云.巴史——以三峡考古为证[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37] 赵志军.栽培稻与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资料和新进展[J].南方文物,2009(3).
[38] 孙华.四川盆地史前谷物种类的演变——主要来自考古文化交互作用方面的信息[J].中华文化论坛,2009(增刊).
[39] 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M]//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
[40]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1] 刘长江,等编著.植物考古——种子和果实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42] 赵志军,等.陶寺城址2002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J].考古,2006(5).
[43] 高官广土.宴尔龙遗址及本家地遗址出土的炭化种子[M]//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44]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炉霍县宴尔龙石棺葬墓地发掘报告[M]//西南地区北方谱系青铜器及石棺葬文化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45] 四川省文管会,等.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M]//文物资料丛刊(7).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46] 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等.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M]//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47] (汉)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宝墩遗址[M].日本:有限会社阿普,2000.
[49]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金沙——21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
[50] 冯汉骥.西南古奴隶王国[C]//巴蜀考古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51] 童恩正.略论我国西南地区的史前考古[J].四川文物,1985(2).
[52] 何锟宇.试论十二桥文化的生业方式——以动物考古学研究为中心[J].考古,2011(2).
[53] 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J].中华文化论坛,2006(1).
[54] 江章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农业的转型与聚落变迁[J].中华文化论坛,2009(增刊).
[55] 田晓四,等.牙釉质碳和氧同位素在重建中坝遗址哺乳类过去生存模式中的应用[J].科学通报,2008,53(增刊I).
[56] 宋豫秦,等著.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