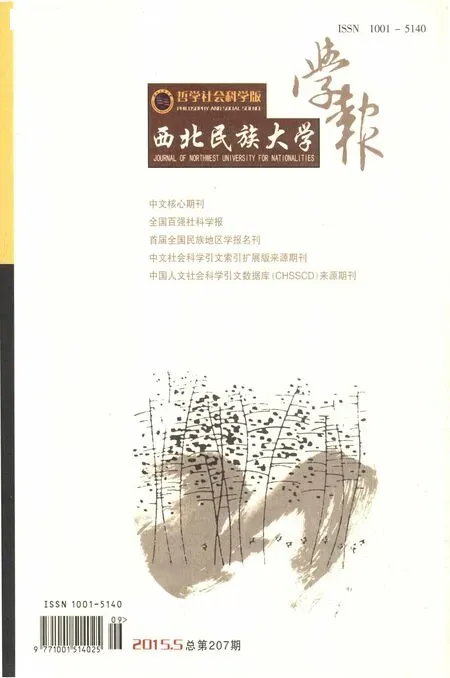清末“藏俗改良”:一个文化认同的个案研究
陈鹏辉
(1.西藏民族学院 学报编辑部,陕西 咸阳712082;2.陕西师范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 西安710062)
作为西方现代性引发的一个现代社会问题,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随全球化浪潮及西方后现代性引发的“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而出现的,并与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紧密相关。虽然这一研究的旨趣以当代及未来为视角,但其对国家社会秩序的哲学关怀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维启示。从文化认同理论视之,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文化认同体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除文化认同的自在发生发展外,文化认同问题突出表现为儒家“大一统”思想强调的“华夷之辨”。历代统治者以儒家“大一统”思想“教化四方”,积极构建以儒家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价值信仰体系和社会行为规范,以统一思想来实现政治一统,即以文化认同构建国家认同。清代统治者通过崇儒重道、移风易俗等方略加强国家凝聚力,特别是在边疆治理中注重“教化四方”的方略,这无疑对增强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有积极意义。
20世纪初,清王朝内忧外患,面临着严重的“认同危机”。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武装侵藏战争,导致西藏边疆危机空前。在此情势下,清廷派张荫棠“查办藏事”。1907年,张荫棠在其以“挽回主权”为核心的全面藏事改革中劝导“藏俗改良”,对此,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外突出的成果鲜有见闻,而国内成果颇丰:王辅仁[1]、伍昆明[2]、郭卫平[3]、曾国庆[4]、苏发祥[5]、许广智[6]、冯丽霞[7]、牙含章[8]、恰白·次旦平措[9]、多杰才旦[10]等诸位学者以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予以研究。其中有肯定意见,亦多有诸如“藏俗改良”是“大民族主义”等否定意见。顾祖成[11]、康欣平[12]等的研究中注意到了“藏俗改良”的积极意义,扎洛[13]的研究中认为“藏俗改良”具有构建文化同质化的国族的意义。文化认同理论为再认识20世纪初张荫棠在西藏劝导的民俗改良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在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藏俗改良”是以文化认同,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清王朝国家认同的一个典型个案,然而尚未有从文化认同视角对此进行研究的专题性成果。笔者以下尝试作一初步探讨。
一、“藏俗改良”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对藏族文化的浸润
文化认同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文化间长期交流的坚实基础。已有的考古成果有力地揭示出,西藏远古文化绝非是一种封闭孤立发现起来的“独特”文化,它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与中原华北地区的远古文化发生了文化上的联系,到新石器时代,这种联系进一步加强,呈现出一种文化上的深刻渊源性关系[14]。“青藏高原在地势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大势,不仅在民族形成与发展上,而且在人种与文化类型上,导致了对黄河流域文明的内倾向,从而造成语言上的汉藏同一语系,人种上同属蒙古利亚人种,以及政治与文化上藏族是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一员的现状。”[15]
在中华民族自在的发展阶段,藏族与中原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中原文化对藏族文化的长期浸润为“藏俗改良”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后,以“甥舅关系”为核心的吐蕃与唐王朝的关系全面发展,使得藏族文化全面地受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浸润。“唐王朝作为中原文明核心的这种强大地位,它的富庶,高度发达的文化以及所拥有的强大政治、军事实力,注定它必然要对与之相接而又借力想打破地区限制向周边发达文明汲取营养来发展自己的西藏吐蕃文明产生强大的影响和凝聚力。”[16]其中唐蕃“和亲”“为儒家伦理思想在藏族地区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亲缘条件”[17],“极大地促进了双方文化交流,尤其是极大推进了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在藏民族中传播和影响”[18],使“藏民族对儒学及儒家伦理思想的认同亦由此加速了进程。”[19]文成公主带去《诗》、《书》,继文成公主之后,730年金城公主派使臣到长安请求儒家经典,唐玄宗“从其请”,命“有司写《毛诗》、《礼记》、《左传》各一部送给吐蕃”[20],这些儒家文化载体以及两位公主本人和随行“杂技百工”,对藏族的生产生活、人生礼仪、丧葬祭祀、婚姻家庭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藏族后来的不少习俗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比如,丧葬习俗,“吐蕃过去对死去的大臣们,没有祭奠的习惯。金城公主说道:‘我们汉地佛法弘扬,对死者有七日祭的习惯。吐蕃佛法不昌盛,人死后享受不到祭奠,实在可悲可怜!’以后,便倡兴七日祭”[21]。吐蕃分裂至13世纪初,西藏与中原经济文化互动更加频繁,为儒家文化对藏族文化的浸润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分布于今青海、云南、四川、甘肃广大地区的藏族,与该地区各民族之间广泛的政治、经济联系密切,使藏族文化充分吸收了各地区的文化因素。此一时期,儒家文化通过藏族内迁、汉族西迁得以在藏族广泛传播。13世纪中叶,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迈向确立阶段之际,西藏地方归属于推进全中国大一统的元王朝。元代及此后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对西藏全面施政,大力加强西藏地方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政治认同无疑促进了文化认同。此外,中央政权在西藏施政中注重以儒家文化进行教化,特别是清代的驻藏大臣对儒家文化在西藏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对藏族文化的浸润是多方面的。藏族伦理经典代表著作《礼仪问答写卷》中大量反映社会准则、人伦关系等的伦理文化,“在思想认识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而“《萨迦格言》和《论语》二者在道德观念、治学态度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22]。反映在教育上,从松赞干布“遣诸豪子弟入国学,习《诗》、《书》。又请儒者典书疏”[23],到清末驻藏大臣兴办学堂,“藏族教育的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藏汉杂居地区的藏族教育,都有过儒家思想或多或少的影响”。反映在藏传佛教上,“藏传佛教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哺育及历代中央政府的呵护与支持下形成与发展起来的”[24],“藏传佛教在其形成过程中,深受汉地禅宗修行思想的侵染,尤其是对宁玛派大圆满和噶举派的大手印法的渗透和熏染就更深广、更浓厚”。反映在君臣伦理中,“儒家的君臣伦理思想随着汉藏高层经常的相互往来而逐渐被藏族高层及知识阶层所认识和接受,从而进一步强化和改造了藏族原有君臣伦理思想,丰富和发展了藏族伦理思想的内容”;儒家文化对藏族文化影响还反映在国家观、人生观等方面,比如,“在儒家‘大一统’思想观照下的藏民族‘倾心向内’的爱国意识”等[25]。在儒家文化的长期浸润下,藏族形成了诸如重信仰轻物质、重理念轻实践、重农牧轻工商等与儒家思想有很大相似性的传统文化,但是,藏族传统文化与藏传佛教的结合,形成了如重神灵轻科技,重神话轻创造,重来世轻今生,重精神轻物质等反映自身特点的伦理文化。可见,从远古文化的多元分散发展,到7世纪青藏高原迈向区域统一,再到13世纪正式进入全国“大一统”的每一个历史阶段,儒家文化对藏族文化的浸润是全面细微的,这种浸润使藏族文化饱含了儒家文化的因子。比如,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藏族传统伦理文化中,诸如“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思想与儒家所主张的“仁”、“天人合一”等价值取向有内在的共同点。
藏族进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亦是藏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历史上,中华文化对藏族传统文化的浸润,很大意义上就是儒家文化对藏族文化的浸润。藏族传统文化很早就吸收融入了诸多儒家文化,饱含儒家文化的因子,与其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这种内在根据就在于中原古代汉族与青藏高原藏族伦理思想的彼此通融[26]。上述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藏族文化的长期浸润,使得西藏文化饱含儒家文化的因子,为20世纪初张荫棠以创新的儒家文化劝导“藏俗改良”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藏俗改良”的向导:创新的儒家文化
以文化认同理论视之,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元文化并存状态下,文化认同的前提是在特定时空中,存在一种能够被不同文化普遍接受认同的文化。一般来说,这种文化是在与其他文化的长期交流中,其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基本准则、规范等,能逐步得到普遍认同,具有统一思想认识、形成普遍性社会风气、促进文明进步的功能。具体而言,这种文化至少须同时具备两大要素:一是自身的先进性,即在多元并存的文化环境中,因其自身的先进性能对其他文化产生吸引力。二是自身的一般性,即在特定的时空中,易于被其他文化接受认同,不至于曲高和寡。从文化认同实际发生角度言,除文化自觉外,常常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力来推广普及,这个推动力一般表现为国家政令、大家讲学、士子游学等,其中以国家政令来推广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文化变迁角度言,这种文化如果要长期保持领先地位,须有兼容并蓄的气质,能随时代变迁而不断丰富完善,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即处于不断发展革新的动态变化之中。如果说这种文化是“一般性”文化,与她相对的“特殊性”文化则是指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乡村文化,就边疆地区而言,这三者的主体往往是一致的。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文化认同体现出自身鲜明的特点,突出表现为儒家“大一统”思想强调的“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从其“天下”观出发,把“天下”之民按是否接受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行为规则等,划分为“化内之民”和“化外之民”,“华夷之辨”的核心主要体现为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但是,在严格划分“化内之民”和“化外之民”,的同时,儒家思想强调“中国有恶则退为夷狄,夷狄有善则进为中国”以及“有教无类”,所以,“化外之民”可以通过教化转变为“化内之民”,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随着历代统治者“大一统”观的深入以及各民族的融合程度加深,“华夷之辨”逐渐为统治者的“华夷一家”观取代。费孝通教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论断中认为,在大一统格局中有“华裔之防”,又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便是中国古代由“华夷之防”到“中华一体”的辩证过程[27]。
从中国古代文化认同的实际看,一直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中的诸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忠恕”、“中庸”、“亲亲尊尊之恩”等主张,尤其是“关于以‘礼’维‘德’的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关于由‘孝’而‘忠’或由家庭伦理推衍社会伦理的道德思维方式;关于仁义优先的道义论立场”[28],逐步成为社会主流文化,进而成了文化认同的向导,即文化认同主要是其他文化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接受。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儒家文化本身既有恢弘气度,又面向世俗,饱含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理性[29],具有超越民族和地区的“和而不同”的兼容并蓄的气质并有对外传播的愿望和要求。其二,儒家思想与政治密切结合,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国家统治意识,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伦理政治思想体系,这是帝制时代统治者维护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权的一切统治手段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在依靠一整套道德教化体系对民众教育引导之外,也依靠儒家思想的国家意识形态功能影响民间社会秩序,将儒家伦理向社会大众广作传播”①参见任剑涛:《伦理王国的构造——现代性视野中的儒家伦理政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48页;又见姚建文:《政权、文化与社会精英——中国传统道德维系机制及其解体与当代启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9-120页。。其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凝聚核心的汉族,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持有者在内部通过以“科举制度”为主的一整套完备的传承体系,广泛传播,使得儒家文化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庞大的文化传承体。历史上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过程中既有汉族向四方分布,亦有各少数民族向内发展,这其中汉族把儒家文化传播给了所接触的各少数民族。此外,由于儒家文化的先进性,不少少数民族民族政权主动接受推行,如北魏孝文帝“立孔子庙于京师”、“幸鲁城,亲祠孔子庙”[30],严禁“胡服胡语”,推行汉语汉服,这些措施促进了其政权之内的崇儒之风。由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正是以儒家文化为向导的文化认同所产生的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中国古代以儒家文化为向导的文化认同并非是单向的。儒家文化兼容并蓄的气度,容许与各民族文化共生并存,民族文化自愿汲取和接受儒家文化的精华提升自身,二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儒家文化在自身不断创新发展的同时,吸收各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得以不断丰富完善,始终保持先进性地位。儒家文化吸收某一民族文化后,在此后的文化认同导向中,引领各民族吸收习得,实际上所吸收的这一民族文化就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费孝通教授指出,“中国各民族特点与特长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共同性的发展,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某个或某些民族的特长,一旦为全国各民族或许多民族所接受,就变成为共同的特长,亦即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了。”[31]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吸收儒家文化,但又保留自身的精华,文化特色不变。儒家文化与各民族文化间的互动,使得各民族文化向儒家文化趋同,但又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特色鲜明。儒家与文化多样性并不矛盾,不抹杀各民族文化的特性。从中国古代文化认同的作用和结果看,文化认同拉近民族情感,促进民族融合,推动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认同,进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体来说,一方面,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先进性,对发展相对滞后的各民族文化发挥了带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带动着儒家文化所倡导的社会价值信仰、行为规范的普及,进而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被各民族普遍认同接受,在精神层面发挥了统一思想认识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以儒家“一统”思想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强化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这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长期稳固的根基。
鸦片战争以后,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儒家文化一度遭到空前冲击,一批有识之士倾力引入西方先进文化,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浪潮。洋务运动期间,形成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特定思想,儒家文化中传统的“重本抑末”、“重义轻利”、商为“四民”之末等受到冲击,中国传统的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开始变化。维新派继洋务派之后,突破“中体西用”的局限,促动清廷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系列新政,尽管“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但其影响深远。与此前后,《天演论》等一批强烈震撼国人思想的各种译著先后问世,助涨思想解放的潮流,国人逐步接受西方先进文化。辛亥革命再掀思想解放高潮后,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了几千年的固有文化彻底被打破,“剪辫易服”、革除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倡导讲文明讲卫生等社会新风深入人心。尽管儒家文化一度受到“全面批判与清算”,但是“其本身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存在价值和留传后世的精华所在,任何人、任何社会集团都不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将其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中彻底清除”[32]。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劲冲击下,没有全盘西化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的“文化自觉”②费孝通教授多次提出,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见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第22页。潘一禾教授进一步阐述“文化自觉”,指出“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尤其对自己的局限和缺陷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文化自觉”,指的又是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了“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见潘一禾著:《文化与国际关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从文化认同角度视之,儒家文化不以“传统文化”、“特色文化”等为借口而推辞西方文化,能毅然决然地进行去粗取精的改良,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创新性。
1907年,张荫棠在其全面藏事改革期间,劝导的藏俗改良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进行的。以《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为核心改革内容的藏俗改良,是认识这场西藏民俗改良的关键。《藏俗改良》①全文见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355-1358。全篇34条,共计2 369字,涉及生活常识、忠孝、礼仪、诚信、信仰、工商、经济、军事、科技、卫生等方面的内容,从反面折射出当时西藏文化的滞后。《训俗浅言》②全文见吴丰培编:《清代藏事奏牍》,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1353-1355。把“教之紧要有数件”之“教”分为“中国古学”和“中国新学”两大部分。其中,“中国古学”的内容涉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博学”“审问”“慎思”“明办(辨)”“笃行”“智”“勇”“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国新学”的核心内容包括“合群”“公益”“尚武”“实业”4个方面。“《训俗浅言》倡导适应维新改良的伦理道德,不仅体现于‘新学’,就是‘古学’,也不是一成不变地因循传统的纲常说教和封建伦理道德,而是赋予了一定的新的时代内容。”[33]综上,儒家文化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文化认同的向导,在文化认同中,西藏文化长期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是藏俗改良的坚实基础。清末张荫棠劝导的藏俗改良,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期,儒家文化受到空前冲击情势下,以创新的儒家文化为向导进行的。
三、“藏俗改良”的意义:从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
文化认同理论强调文化认同对构建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依靠文化认同来实现,并由民族认同做保障。”[34]从“认同”理论视之,清朝皇帝继承历代的“大一统”观,高度重视以文化认同增强国家认同,最突出的方略是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来推崇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圣谕广训》。③顺治九年,顺治帝借鉴明朝治国经验,将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即“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颁行八旗及各省(《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七,“礼部·风教·讲约一”)。强调“这六句包尽做人的道理,凡为忠臣、烈士、孝子、顺孙皆由此出”(《輞川里姚氏宗谱》卷三,“宗规”)。康熙帝发展“圣谕六言”,于康熙九年,“特颁圣谕十六条(“圣谕十六条”的内容是:一曰:敦孝弟以重人伦。二曰:笃宗族以昭雍睦。三曰:和乡党以息争讼。四曰:重农桑以足衣食。五曰:尚节俭以惜财用。六曰:隆学校以端士习。七曰:黜异端以崇正学。八曰:讲法律以儆愚顽。九曰:明礼让以厚民俗。十曰:务本业以定民志。十一曰:训子弟以禁非为。十二曰:息诬告以全善良。十三曰:诫匿逃以免株连。十四曰:完钱粮以省催科十五曰:联保甲以弭盗贼。十六曰:解仇忿以重身命。见印鸾章著:《清鉴纲目》,长沙:岳麓出版社,1987年,第172页),以示尚德缓刑,化民成俗至意”(《清圣宗实录》卷三四,康熙九年十一月己卯。见《清实录》第四册,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年,第466页)。雍正帝将“‘上谕十六条’寻译其意,推衍成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清世宗实录》卷一六,雍正二年二月丙午。见《清实录》第七册,中华书局影印版,1985年,第266页),于雍正二年颁行天下,其后的清帝继位,都严格要求全国各地“切实遵行”,甚至官吏提拔首看落实《圣谕广训》的成绩,直至清末。有清一代,《圣谕广训》以中央政令的方式不仅在内地得到大力推广,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亦是如此。现存于(此碑立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沙溪镇石龙村的《乡规碑》,便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接受《圣谕广训》的例证④笔者2010年在该村做田野调查时,录得此碑碑文。后完成《普适伦理:清代云南大理石龙乡规碑文化诠释》一文,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4)。。清帝高度重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圣谕广训》,是以文化认同来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这实际上是清王朝一项重要的治边政策。如前所述,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演进中,藏族文化长期受儒家文化的浸润,然而,在张荫棠劝导藏俗改良之前,尽管有孙筠等驻藏大臣注重“文教治边”,但是一直没有形成专门的宣教文本,在张撰译的《藏俗改良》《训俗浅言》首次把这种浸润的内容条理化、系统化和书面化。联豫继续推行张荫棠所开启的藏事改革期间,才有在西藏撰译刊发《圣谕广训》之举。
张荫棠劝导藏俗改良的思想是他个人行政的智慧和勇气,亦是时代思潮和现实需求的产物。20世纪初,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维新变法成为历史潮流,在传统文化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发生剧烈变迁重构之际,对“近乎于死水一潭”[35]的西藏民俗文化进行改良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再者,1904年,英国发动第二次武装侵藏战争,导致西藏危机空前,西藏边疆治理成为当时朝野共同关心的重要国事。在此情势之下,临危奉命“查办藏事”的张荫棠在其倡言革新、筹划新政的整体运思中,结合中国历代“为政必先究其俗”的传统社会治理理念,经与西藏地方筹议酝酿而成《藏俗改良》、《训俗浅言》两本小册子,刊发民间,“冀荡涤其龌龊窳惰之积习,而振其日新自强之气”[36],这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张荫棠身处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他在西藏边疆治理中劝导藏俗改良的思想无疑受到民族国家建设的影响。救亡图存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在化解西藏边疆危机迫切的20世纪初,张荫棠以创新的儒家文化为向导劝导的藏俗改良,对西藏社会的旧风陋俗是一次空前的洗礼,这在当时不仅具有引领西藏文化走出“困境”的现实意义,在中央在藏主权面临严峻挑战的历史紧要关头,更有以文化认同来增强国家认同的深层意义。
文化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尽管张荫棠劝导的藏俗改良在当时并没有取得他所预期的效果,但在其后的西藏社会发展中大部分被认同、接受,藏俗改良所释放出文化认同的能量正是寓于此过程之中。如今,在西藏仍然面临严峻的反分裂斗争的形势下,加强“四个认同”成为新时期的一项重要命题。虽然张荫棠所处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但其以劝导藏俗改良加强藏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边疆治理方略,是当代和未来边疆治理中无法绕过的思想与逻辑环节。因此,在新时代,重新审视历史的过程和意义,将有助于我们在西藏更好地开展加强“四个认同”,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
[1]王辅仁,索文清.藏族史要[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61-165.
[2]伍昆明.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M].厦门:鹭江出版社,2006.249-258.
[3]郭卫平.张荫棠治藏政策失败原因初探[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8,(1).
[4]曾国庆.论清季驻藏大臣张荫棠[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5).
[5]苏发祥.清代治藏政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126-132.
[6]许广智.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J].西藏研究,1988,(2).
[7]冯丽霞.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的性质[J].西藏研究,1987,(4).
[8]牙含章.达赖喇嘛传[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148-154.
[9]恰白·次旦平措等.西藏通史—松石宝串[M].陈庆英等译.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909-912.
[10]多杰才旦主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下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791-799.
[11][33]顾祖成.明清治藏史要[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齐鲁书社,2000.290-304,299
[12]康欣平.“大民族主义”抑或“普适主义”——张荫棠〈藏俗改良〉、〈训俗浅言〉析论[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13]扎洛.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张荫棠西藏新政[J].民族研究,2011,(3).
[14]顾祖成.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总体演进与西藏主权归属的历史形成——兼批达赖集团篡改历史、鼓吹“西藏独立”[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15]张云.丝绸文化·吐蕃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87.
[16]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148.
[17][18][19][25][26][32]余仕麟,刘俊哲,李元光,魏新春.儒家伦理思想与藏族传统社会[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15,206,217,206-218,41,4.
[20](北宋)王钦若,杨仁等.册府元龟·卷九六二·外部臣·和亲二[Z].北京:中华书局,1960.
[21]拔塞囊.拔协[M].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4.
[22]赵永红.神奇的藏族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93.
[23](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吐蕃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74.
[24]李清凌.藏传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J].中国藏学,2001,(3).
[27][31]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46,139.
[28]万俊人.现代性的伦理话语[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124.
[29]任剑涛.伦理王国的构造——现代性视野中的儒家伦理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82.
[30](北齐)魏收.魏书·卷七·帝纪七[Z].北京:中华书局,1984.
[34]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J].清史研究,2010,(4).
[35]仁真洛色.正确认识和对待藏族传统文化[J].中国藏学,2001,(3).
[36]张荫棠.使藏纪事自序[A].清代藏事奏牍[Z].吴丰培.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1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