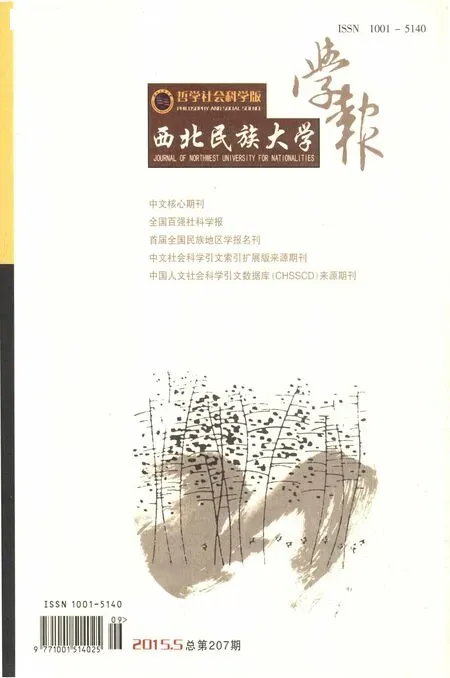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理性交流——以中国近代佛学复兴为线索
顾 毳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200241)
理性精神,是佛学的显著特点。佛学的发展不是宗教热情的燃续,而是理性精神的深耕。宋明以来的佛学式微,实为禅宗顿悟精神跃迁、理性精神坍塌所致。汉传佛学,正是以理性复兴为旗帜,通过对唯识学的复兴、日本佛学的借鉴与藏传佛教的引入,开启了其近代复兴之路。虽然中国近代佛学界对佛学复兴的史料研究、学理研究不少,但一直缺少对其开展理性维度的历时审视。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近代汉传佛学复兴为线索,以其理性精神的发展为视角,以汉藏佛教交流为焦点,试图以历时态方法,探索近代中国汉传佛学是如何开启其近代复兴之路的内在历程。
清末,清朝统治的坍塌造成中国政治体系的瓦解与中国人现实世界的崩溃。严复所译《天演论》撕碎了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梦,“理一万殊”的静态画面切换为“变动不居”的进化论视角,“诸行无常”比以往显得更为深刻。现实世界的崩溃,不仅影响到近代知识分子生存处境,更给他们带来思想和心灵上的震撼。他们“上下求索”苦思救国之道。在“西学东渐”的同时,许多士大夫在回眸的一瞬,看见“灯火阑珊处”以往“西天取经”之所得,从佛教典籍中重新发现了佛学的价值,纷纷从佛学中吸取思想养分,或安顿乱世心灵,或振臂改革佛教,或经世治世。佛学在沉寂数个世纪之后,重新焕发生机,并形成持续的佛学研究热潮。这股热潮首先由居士引发,继而寺僧响应,学者推波助澜,居士、寺僧、学者共同成为三支主力军。然而空穴不能来风,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大门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的。坚船利炮是那位西方近代“赛先生”,即科学思想的产物。近代科学从根本上说是从西方近代认识论之树结出的果。与其说近代中国的大门是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的,不如说是西方理性思维的结果。随着国门的打开,自负的国人开始警醒,将狭隘和偏见暂置一处,向西方的“赛先生”、“德先生”学习。在西方理性思维的影响下,近代佛学重新拾回佛教理性,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进行了一次理性交流。
一、《大乘起信论》以理性的姿态开启近代佛学复兴
近代佛学兴起可以追溯至近代思想家龚自珍(1792年-1841年)和魏源(1794年-1857年)①龚自珍与魏源是否归依有争论。。龚自珍于佛学以天台为宗,持咒念佛,助印经书,其信仰大于理性。“不过由于他未能把理性的目的和非理性的手段完美地统一在一起,所以在一些宗教活动中,表现了信仰主义多于理性主义……”[1]魏源初入于禅宗,晚年归于净土,主张“禅净双修”。他重视《佛说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佛说阿弥陀经》《净土论》和华严宗所尊的《普贤行愿品》。魏源信佛有自幼家族熏陶的因素,也有援佛入儒以补救世衰的企图。总观其佛教信仰有迷信的成分,亦有理性的成分。杨仁山评价曰:“魏公经世之学,人所共知,而不知其本源心地,净业圆成,乃由体以起用也。”[2]龚魏二人对佛教总体是信仰多于理性。从他们所关注的佛典可以看出,他二人总体倾向是重经轻论,这与汉传佛教重《经》传统相吻合。由重《经》转向重《论》是由杨仁山开始的。
佛教典籍由《经》《律》《论》组成。其中《经》为佛语,多为宣说,对佛教徒来说具有不可怀疑的神圣性,因明学出现后,佛经更成为不证自明的“圣言量”。佛在灭度前,阿难问佛“佛灭后以何为师”,佛说了四依法,即“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识”。其中前三依的指向是所依,第四依指向能依。前三依中的“法”和“义”等以经为物质载体,成为佛弟子的所依。能依的智的载体则是具有能动性的“补特伽罗”,即佛弟子。佛弟子依经造论,阐明佛理。因此论可以看做是经的诠释系统,是佛弟子通过理性思维所作的对经的诠释。《俱舍论光记》中说:
“西方造论皆释佛经,经教虽多,略有三种,谓三法印:一诸行无常,二诸法无我,三涅槃寂静。此印诸法故名法印,若順此印即是佛经,若违此印即非佛說,故后作论者皆释法印,于中意乐广略不同。或有偏释一法印,或有兴一以明三。如《五蕴论》等唯解諸行无常,如《涅槃论》等唯释涅槃寂静,此即偏释一法印。如《俱舍论》等解諸法无我,此即是举一以明三。”(大正新脩大藏经第41冊No.1821俱舍论记,CBETA电子佛典)
与《经》相比,《论》则更多思辨色彩,表现出逻辑严谨、论证细密的特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出一套格式规范。通常是由概念辨析,概念逻辑推衍层层展开,内含理性的精神,与现代西方学术规范有相近之处。
近代佛学学者,第一个从论典悟入佛理者,是杨仁山。杨仁山(名杨文会,字仁山,1937年-1911年)是居士佛教中的“实干派”。据载杨仁山在其父亡故后,大病一场。病中“再取《大乘起信论》读之,手不释卷,钻研五遍,乃归心向佛”[3]。CBETA电子佛典中所收录的《大乘起信论》有两个版本,皆为马鸣所造。一为陈真谛所译《大乘起信论》,一卷。另一为实叉难陀所译《大乘起信论》,二卷。杨仁山所见为真谛本《大乘起信论》。两个版本《大乘起信论》篇幅实际相差无几。《大乘起信论》,篇幅短小,但内容涵盖极广。《起信论》采用从概念到概念,以表诠的方式层层演绎,此与西方学术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其中主要探讨了体相用三者的关系、阿赖耶识的定义、六度、止观双运以及后世争论较多的本觉、始觉等的论述。正如杨仁山所说“有马鸣菩萨所作《起信论》,文仅一卷,字仅万言,精微奥妙,贯彻群经……”[4]
杨仁山尝言:“随人根器各有不同耳!利根上智之士,直下断知解,彻见本源性地,体用全彰,不涉修证,生死涅槃,平等一如。此种根器,唐宋时有之,近世罕见矣!其次者从解路入,先读《大乘起信论》,研究明了再阅《楞严》《圆觉》《楞伽》《维摩》等经,渐及《金刚》《法华》《华严》《涅槃》诸部,以至《瑜伽》《智度》等论。然后依解起行,行起解绝,证入一真法界……”[5]
杨仁山认为禅宗“利根上智”是“近世罕见”,也即否定禅宗的“不涉修证”的方法,提出“从解路入”。“从解路入”四字极为重要,代表了近代佛学的转向和开端。“信、解、行、证”和“解、信、行、证”是趋入佛教两条不同的路径,二者不同之处在于“信”和“解”何者为先。先“信”而后“解”,是因信称义,易流于盲信、迷信。先“解”而后“信”,是通过理性分析而后的信仰,是理性的信仰。杨仁山一扫禅宗“不立文字”、“直悟本心”的流弊,一改净土只诵一句佛号,只读净土三经便往生极乐的简易信仰。从经到论的转向,可以看做是佛教信仰从因信称义到理性信仰的转向,而这一向度是由杨仁山所开出的,杨仁山是当之无愧的近代佛学复兴第一人。
在这里,提出“从解路入”之后,杨仁山给出了“先读……,再……,渐及……”等修学次第。虽然这一次第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开了次第修学的先声。众所周知,道次第思想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标志性思想,在之后的汉藏佛教显宗方面的沟通上,宗喀巴大师的道次第思想对汉传佛教影响最大。
虽然杨仁山之后,《大乘起信论》真伪判定引起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然而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孰是孰非的判定上移开,我们会发现争论本身即代表理性信仰的觉醒,正是争论把众多注意力吸引到此论的解读上,使得佛学义理得以开显,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开始进行理性思考。同时,争论也为近代佛学复兴注入的活力,在一潭死水中击起千层浪,唯识学振兴正是这千层浪花中最亮丽的一朵。
二、迟到千年的唯识学研究兴起
唯识学的兴起跟《大乘起信论》有着内在的联系。“《大乘起信论》争论的背景是在唯识学发展的前提下进行的……”[6]唯识学开创于公元4世纪的印度,由无著、世亲所开创,曾在印度佛教史上称霸一时,盛行数个世纪。公元7世纪时,玄奘去印度学习,在唯识学祖庭那烂陀寺学得唯识学说。回国后,听从弟子窥基的建议,将数家唯识学说糅译成为《成唯识论》,开创法相宗。然而,时人并未接纳唯识学说,传至三代,前后不过百年便消亡。近代唯识学兴起得益于杨仁山居士对佛教典籍的搜集。他于1878年随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以参赞的身份出使欧洲,在英国伦敦结识日本近代佛学大师南条文雄。此后在南条文雄的帮助下,搜求得到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所传的唯识学文献,从而使得唯识学回归。法相唯识经典的再现为后来持续百年的唯识研究热开了先河。
为何以玄奘印度求学为蓝本的小说《西游记》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他辛苦所求得的唯识学说在中国盛唐以后的一千三百多年间成为绝学?在一千三百多年后的20世纪唯识学又突然成为僧俗学各界研究百年而至今不衰的学说?这些问题很多学者都进行过思考,如张曼涛、霍韬晦、黄夏年等人,他们共同的看法是唯识学的体系化特征以及它与西方学术的相通性。“理性”是西方近代思想的基本特征之一。西方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以来,“高举理性主义大旗”,探索“确定性”、“明晰性”的客观知识。他们普遍认为感性是不可靠的,唯有理性才可以作为认识主体,从而获得确实可靠的客观知识。他们通过运用概念演绎的论证方法,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环环相扣,形成体系。那么唯识学与西方学术的内在联系到底如何呢?
杨仁山认为:“《起信论》虽专诠性宗,然亦兼唯识法相,盖相非性不融,性非相不显……”[7]。那么何为法相?法相一词梵文是,由dharma“法”与“相”构成的依主释,藏文与之对应的是,也即法之性相,法之相法,法之特征。《佛光大辞典》对此词给出了三个条目:
(一)诸法所具本质之相状(体相),或指其意义内容(义相)。唯识宗之特质在于分析或分类说明法相,故又称法相宗。
(二)指教义上之分齐、区别、纲要。
(三)指真如、实相。与‘法性’同义。(《佛光大辞典》第三版)
唯识学遂成为20世纪的显学,造就了“南欧北韩东范西王”①即欧阳竟无、韩清静、范古农、王恩洋四人。四大唯识家,此外尚有新儒家代表熊十力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唯识学经典有一部分是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这些文献由法尊翻译而进入汉语研究范围。
三、“道次第”思想的译介和影响
如果说中国近代祸起“闭关”,那么,自唐之后汉传佛教就在“闭关”。唐玄奘、义净之后绝少有人再向“西天取经”。与此不同,藏传佛教正是在玄奘、义净之后以开放的心态或迎请印度高僧进藏传法,或历经艰辛、九死一生去印度求取佛法,获得印度佛教中后期的佛法传承。从时间上推算,藏传佛教所得正是汉传佛教所缺。唐以后,汉传佛教由于各种原因日趋衰落,而藏传佛教却一直讲、辩、著兴盛。自近代理性为信仰注入生机后,汉传佛教亦开始“出关”,有去国外主动弘法者,如太虚法师。有去日本学密法者,如大勇。但是最华丽的“出关”是“留藏学法团”,这可以看作理性思维的延续。“西藏佛教为现代世界学界所重视,是当代佛学研究史上一大进步,一大成绩。”[8]近代藏传佛教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是藏密。当代学者索南才让认为“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藏密是一种生命科学,它集光学、声学、思维学、语音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知识于其中。不仅是佛教文化的精华,而且也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注重师徒传承,修习次第分明,仪轨齐备,制度完善,组织健全,具有深邃的哲理和修持规范等特点。然而,作为一种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藏密作为藏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有积极性,也有消极性,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态度,认真加以分析,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部吸取。”[9]大勇法师是近代佛教史上精研密法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日本学密归来后,在一次与藏传佛教高僧白普仁的切磋后,发现藏密比东密更为高深殊胜,于是起意去西藏学法。这是“留藏学法团”之缘起。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据学者统计成功进藏的学僧、居士有54人,大多在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学习。由于藏密本身的保守性、秘密性,以及对学者的佛学素养、身心素质等都有非常高的要求。尤其是格鲁派对密法的传授极为严格。据刑肃芝②刑肃芝是上世纪解放前进入拉萨学习的获得拉然巴格西学位的两个汉僧之一。回忆“学完了五部大论,拿到了格西,只能证明你在密宗的理论部分或者说是显教部分过了关,具备了修持密法的资格。黄教对于喇嘛学习密法有很严格的规定,要先显后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佛学经典能够融会贯通了,有了对佛法的正知正见,才能去学密法,这时你才能在修持中得到受用,而不会生出邪知邪见,堕入邪魔外道。这时你才有资格进入上下密院,去专修密法”。[10]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当时去西藏求法的汉僧尚无一人去上下密院学习密法。③但这并非说除了上下密院,就学不到密法。《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提到:“密法却并非一定要在密院里才能学到,如果有机缘能够得遇好的金刚上师,一样也可以求到。”参见第188页。因此有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内地密教的传布几乎停留于‘摇铃振鼓’的灌顶仪式”[11]。进入哲蚌寺学习的汉僧主要学习的是格鲁派的教学次第,即五部大论④即《现观庄严论》《入中论》《量释论》《戒律本论》《俱舍论》,由此也可以看出,格鲁派对论典的重视程度。,接触到的主要是格鲁派思想,尤以宗喀巴(1357年-1419年)的“道次第”思想影响最大。
前文已经述及,近代有关修学次第的思想,可以追溯到杨仁山居士,他曾提出过简单的修学次第,但是并未产生影响。真正修学次第对汉传佛教产生影响的是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思想。太虚受宗喀巴道次第思想的影响提出“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12]。从时间上看,最早注意到宗喀巴“道次第”思想的是大勇法师。他在1925年进藏受阻于甘孜时,仍然精进不怠,约于1927后译出《菩提道次第略论》。之后,有留藏学法团成员恒演写出《略述西藏之佛教》(1930年6月),简要介绍了格鲁修学次第。吕澂不久之后也关注到了宗喀巴,在他的《西藏佛学原论》(1933年2月)的别录、附录中,除印度学者著作和相关目录书籍之外,西藏佛教学者的著作进入其视野的主要有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布顿的《善逝教法史》、罗桑崔吉尼玛的《一切宗义明镜》、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大本》、隆亲喇嘛的《隆亲喇嘛全书》。其中《菩提道次第大本》就是后来法尊所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吕澂对此书评价道:“此书是宗喀巴最要之著述,后半别明止观,详述各家学说抉择是非,尤为精粹。”[13]此书藏文为,其中意为“菩提”意为“道路”意为“次第”,意为“大,广大”。法尊曾随大勇一同译《菩提道次第略论》,所以以“广”对“略”译之。
真正发现宗喀巴思想魅力的人是法尊。法尊说:“这一年所求的学非常满意,对于藏文方面也大有进境;对于西藏的佛法产生了一种特别不共的信仰。因为见到《苾刍戒释》《菩萨戒释》的组织和理论,是在内地所见不到的事。尤其那部《菩提道次第论》的组织和建立,更是我从未梦见过的一个奇宝。我觉着发心求法的志愿,总算得到了一点小结果,哪怕就是死在西康,我也是不会生悔恨心和遗憾的了。”[14]比较系统地译介宗喀巴论著的人正是法尊。他于1926年与大勇、朗禅在西康试译宗喀巴的《缘起赞》,摘译《宗喀巴大师传》和《阿底峡尊者传》,在《海潮音》上发表。进藏后,于1931年依止安东格什学法,开始译《密宗道次第广论》。1934年法尊再次入藏,依止绛则法王学法,并译出宗喀巴的《辨了义不了义论》及《释》《菩提道次第广论》《密示道略论》,后来于1936年在武昌出版。1939年译完宗喀巴的《密宗道次第广论》,由北京菩提学会印刷发行。
同一时期,尚有超一法师等翻译出版《菩提道次第论颂掇》、《菩提道次论极略颂》、《菩提道次第论掇科判》。能海法师1936年译出《菩提道次第科颂》,1938年译成《生起次第津要》等。
随后,在汉传佛教界陆续有法师宣讲宗喀巴的道次第思想。1936年4月,上海佛教界发起丙子息灾法会,能海(1886年-1967年)宣讲了《菩提道次第论》,在上海佛教界影响很大。1936年,喜饶嘉措(1884年-1968年)受国民政府聘请,赴京讲学,在北京、清华、中央、武汉和中山等大学开设西藏文化讲座,主要讲了宗喀巴大师的传略、菩提道次第、格鲁派发展史和汉藏文化交流等相关内容的报告,场面很是热烈。1946年左右,密悟①密悟为留藏学僧中另一位获得格鲁派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学僧。法师离开拉萨返回成都,受到四川各大寺院如文殊院、宝光寺、尧光寺与宝慈佛学社、成都佛学社等佛教组织的邀请,在这些寺院和佛教组织曾讲说《菩提道次第广论》。1947年底,能海弟子清定在上海讲《菩提道次第科颂》。
至此,在宗喀巴圆寂五百多年后,其思想正式传入并开始持续影响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学者的著述在汉传佛教界得以流传且至今不衰,这在汉传佛教史上非常罕见,究其原因,实需深思。现援引太虚为《菩提道次第广论》所作之序略备一说:
“然中国尚禅宗者,斥除一切经律论义。虽若《宗镜录》遍录经论,亦但扬厥宗,鄙余法为中、下。尚净土者,亦劝人不参禅学教,专守一句弥陀。贤、台虽可以小始终顿、藏通别圆位摄所余佛言,然既为劣机而设,非胜根所必须,纵曰圆人无不可用为圆法,亦惟俟不获已时一援之,而学者又谁肯劣根自居,于是亦皆被弃。……中国至清季,除参话头、念弥陀外,时一讲习者,亦禅之《楞严》,净之《弥陀疏钞》,及天台《法华》与《四教仪》,或贤首《五教仪》,附《相宗八要》而已。经律论古疏早多散失,保之大藏者亦徒资供奉,或翻阅以种善根耳。空疏媕陋之既极,惟仗沿习风俗以支持。学校兴而一呼迷信,几溃颓无以复存。迄今欲扶掖以经论律仪,亦尚无以树立其基础,而借观西藏四五百年来之黄衣士风教,独能卓然安住,内充外弘,遐被康青蒙满而不匮。为之胜缘者虽非一,而此论力阐上士道必经中、下士道,俾趣密之士,亦须取一切经律论所诠戒定慧遍为教授,实为最主要原因……”[15]
宗喀巴素有宗教改革家的称号,他于15世纪对藏传佛教进行的宗教整顿,一扫藏传佛教乱象。他的“道次第”思想给佛教徒一套切实可行的“阶梯”,通过它学僧可以由浅入深一窥佛学之堂奥,而不会剑走偏锋。由此可以看出,宗喀巴的“道次第”思想对于近代佛教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还具有现实意义。
四、结语
由此,近代汉传佛学与藏传佛学在理性的引导下,汉藏佛教实现了历史性的交流。这一交流是在汉传佛教复兴的诉求,以及藏传佛教东传的诉求之下进行的。就汉传佛教而言,需要进行振兴及改革。杨仁山等人以理性为主轴,发起汉传佛教复兴运动。太虚大师几乎尽其一生都在为汉传佛教改革而奔波。他提出“教理改革”、“教制改革”、“教产改革”三项改革,以及“人间佛教”的构想,至今影响巨大。就藏传佛教而言,九世班禅、白普仁、喜饶嘉措等活佛高僧迫于西藏政治形势,怀着爱国心愿来到内地,为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交流提供了历史契机。大勇、法尊等人为代表的西藏留法团在汉藏佛教两种诉求下,使得汉藏佛教实现了更为深层次的接触和交流,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1]麻天祥.龚自珍佛教文化研究特征[J].晋阳学刊,1991,(2):94.
[2][3][4][5][7]杨仁山.杨仁山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84,1,29,27,66.
[6]黄夏年.百年的唯识学研究[J].社会科学动态,2000,(1):25.
[8]张曼涛主编.现代佛学丛刊·西藏佛教教义论集(一)[M].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1.
[9]索南才让(许得存).西藏密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
[10]刑肃芝[洛桑珍珠]口述,张健飞杨念群笔述.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修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185-186.
[11]梅静轩.民国以来的汉藏佛教关系(1912-1949)——以汉藏教理院为中心的探讨[J].中华佛学研究,1998,(2).
[12]太虚.太虚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76.
[13]吕澂.西藏佛学原论[M].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149.
[14]法尊.现代西藏[J].成都:汉藏教理院,1937.14.
[15]宗喀巴,宗喀巴大师集[M].法尊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