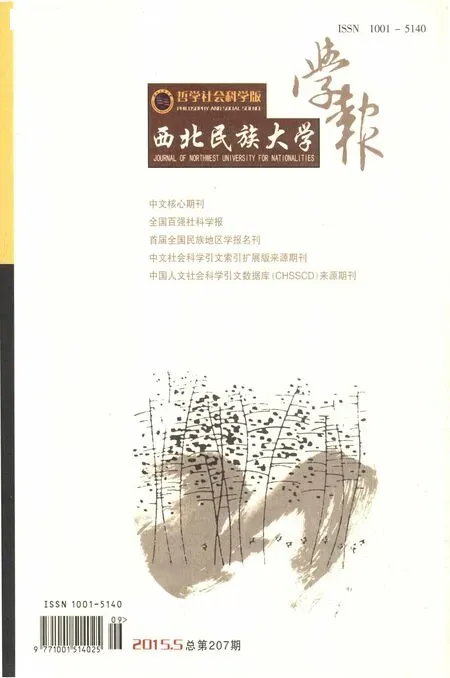苏毗人的历史演化进程研究——对人类文明演化路径及影响因素的思考
李淮东,裴 蕾
(1.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710062;2.河北省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北 张家口075000)
研究苏毗人的历史演化问题,先要明确两个概念。本文讨论的苏毗人,是指古代在青藏高原生存和发展的一支族群,他们主要分布在唐古拉山南北一带广大地区,是以游牧和狩猎生产方式为主的游牧人群。吐蕃人,是指7世纪前未完成统一时的吐蕃人,即生活在雅鲁藏布江南部雅隆地区的吐蕃人部落联盟。苏毗人的历史演化进程,主要体现在两者之间的历史联系中,促成苏毗人历史演化的条件和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苏毗人自身的历史发展轨迹,也包括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影响,更重要的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人、象雄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对苏毗人的巨大影响。古代吐蕃人正是由吐蕃、苏毗、象雄三大族系以及古羌人、突厥蒙古人甚至可能还包括中亚地区的印欧人的一些分支演化而来,并共同创造了西藏文明,可以说苏毗人是现代西藏人的祖先之重要一脉。
苏毗人的历史演化及苏毗与吐蕃的关系问题已有学者进行过深入探讨,①杨正刚的《苏毗初探》和《苏毗初探(续)》,分别载于《中国藏学》1989年第3期,第35-43页,以及第4期,第136-144页;《苏毗与吐蕃及其他邻近政权的关系》,载于《西藏研究》1992年第3期,第49-55页;周伟洲的《苏毗与女国》,引自《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页;林冠群的《苏毗与森波杰考辨》,引自《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317页;[法]石泰安著、耿昇译的《西藏的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1页。杨铭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所见苏毗与吐蕃关系史事》,载于《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第26-32页。另见杨铭的《唐代的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55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本文以考古学资料、藏史传说、汉藏史籍等史料中提取的苏毗人历史演变的信息,对苏毗人与吐蕃人的关系进行分析,讨论苏毗人的历史演变,并对西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多元化因素进行总结。
一、高原人的游牧性特征——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中的苏毗人
在传世的汉藏文献以及佉卢文书中对苏毗人有许多描述,传世文献中最早对苏毗人的记载当属佉卢文书。继续探究佉卢文书的来源,可以发现这种文字最早流行于古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公元前2世纪传入中亚希腊化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此后,传入到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这批佉卢文书是公元2世纪末至4或5世纪时,西域城郭国鄯善王国统治下的精绝(中心在今雅尼遗址)等地的遗物[1]。因此,这批文书所记关于苏毗人之事迹最迟也在4或5世纪。我们可以推测,西域诸国完全有可能与苏毗人在很早的时期就有所联系。在这批文书中,有15件涉及到苏毗(Supiya)这个族群,大多记载了有关苏毗人劫掠西域诸国人口、牲畜等事,试举其中两例。
如国王敕谕编号272号文书记:“……去年,汝因来自苏毗人的严重威胁将州邦之百姓安置于城内。现在苏毗人已经全部撤离,以前彼等居住在何处,现仍应住在何处。”
722号信函亦说:“据且末方面的消息,苏毗人要带来威胁。谕令书已再次下达,军队须开赴。”[2]
从这两件文书看,当时苏毗人的经济方式以游牧为主,且发展的水平不高,至少低于当时西域诸国的发展水平。游牧民族常与农业民族进行物质交换,这种物质交换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劫掠,这两条文献即为明证。这里提到的苏毗人很可能是藏北、青海南部一带的苏毗人,通过青藏高原与西域之间高大山脉的隘口进入到当时的西域绿洲,他们逐水草而居的特点又决定了劫掠之后即行离去。
另外,汉文文献最早记载苏毗的《新唐书》中一段关于苏毗人的记载:“苏毗,本西羌族……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峡,户三万。”[3]这条史料是关于7世纪以后苏毗人种属与居住地的记载。据周伟洲先生考证,苏毗人的居住地在今金沙江上游通天河以西,跨唐古拉山之地,西至今青海索曲北源上流。其北与吐谷浑相邻,河(黄河)北吐谷浑,河南即苏毗[4]。汉文史料与佉卢文书所记的苏毗人居住地是略有差异的。西藏古史传说中,对苏毗的族属与居住地也有一些记载,法国汉学家石泰安(R.A.Stein)对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苏毗一族,在藏文典籍一般认为是属于东(Stong,tong)部族。他通过对西藏神话、古史传说、汉藏文献的研究,认为“该民族居住在西藏的东北部,从8世纪起逐渐被吐蕃人所同化了”,“吐蕃的苏毗人肯定属于汉文史料中的羌人”[5]。
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新石器时代西藏地区至少存在三种与外来文化发生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土著文化在主要吸收从黄河上游南下的氐羌系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属典型土著系统的曲贡文化以及源自华北的细石器文化传统经北方草原地区南下进入藏北高原的藏北细石器文化。而这三种文化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则各有差异,卡若文化主要是从事定居农耕经济并兼有狩猎畜牧经济的居民群体;曲贡文化则主要是从事定居农业和渔业经济为主的曲贡居民群体;藏北高原细石器文化则是从事游牧和狩猎经济的藏北游牧居民群体[6]。藏北高原细石器文化的居民群体在居住地上与汉文史料所提供的证据相吻合,这些居民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特点则与佉卢文书中所记载的苏毗人经济方式相一致。
因此,至少可以给我们提供出一个简单清晰的苏毗人早期历史发展的脉络——苏毗人应该生活在藏北高原地区,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7]。在其后的若干世纪,经过不断的迁徙,其中的一部分苏毗人北面越过昆仑山即与西域的于阗相联系[8]。另外,在汉文史料中记载,唐古拉山南北居住的苏毗人更易从西北越阿尔金山,至且末、鄯善(今新疆若羌),这条道路即后所称之的“吐谷浑道”或“青海路”[9]。这就更能说明苏毗人的大致活动地域。
这样一支青藏高原上的人群,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藏东南的雅隆河谷地带所形成的吐蕃人,大约在公元前350年,由吐蕃第一代聂赤赞普(鹘提悉补野)统辖“吐蕃六牦牛部”组成了吐蕃人部落联盟[10]。吐蕃人很早就已经与其周边邻近的政权有了联系[11]。从地理上看,苏毗人与吐蕃人两者的生存环境并不相同,苏毗人生活在藏北高原,吐蕃人生活在雅鲁藏布江的河谷地区。经济形态上看,苏毗人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要形式,吐蕃人则以农业、狩猎为主要经济形态。石泰安先生的《西藏的文明》中也提到“雅隆是吐蕃最肥沃的地区,吐蕃的王家政权就是在那里形成的”[12]。考古学的证据还提示我们,雅隆河谷地带的吐蕃人无法归属到任何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具有本地土著化的特点。两者之间的联系很早就已经开始,那么苏毗人与吐蕃人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联系的呢?
二、共同的文化纽带——汉藏史籍所载上古、中古时期苏毗人与吐蕃人的联系
苏毗人与吐蕃人,两者之间在上古时期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文化因素的作用呈现在历史记录之中。在文化上,苏毗人和吐蕃人都受到了象雄文明的影响。藏文史籍《五部遗教》《四洲之源》和《贤者喜宴》中,叙述了西藏王政统治之前的“小邦时代”。《贤者喜宴》中记述的象雄(Zhang-zhung)、森波(苏毗人,Sum-Pa)①周伟洲先生认为此为苏毗的一部。参见周伟洲的《苏毗与女国》,引自《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和亚松(苏毗人)[13]、藏(吐蕃人,bod)即是这些小邦中的三支。象雄是这三支部落联盟中最早发展起来的一支,据藏族苯教学者格桑丹贝见参(skal-bzang-bstan-Pavi-rgyal-mtshan)所著《世界地理概说》的记载,象雄地域有三大部分,即今天的阿里、拉达克等地为“内象雄”,卫藏等地为“中象雄”,多康等地为“外象雄”[14]。从象雄联盟这个地域分布来看,已经与雅隆部落的吐蕃人和藏北高原地带的苏毗人有了联系(比照前文所述苏毗人与吐蕃人的居住地域)。据苯教传说,象雄曾一度拥有西藏北部和西部为中心的广大疆域,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字——象雄文,而且还成为西藏传统的宗教——苯教的发源地。正是象雄文明在地域、文化上对苏毗人和吐蕃人的影响,才使得这两大族群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据杨正刚的研究,这时的苏毗已经为象雄所统治[15]。笔者亦认为早期西藏各部落、族群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互相控驭的关系,就如同商、周早期邦国时代一样,周部落即商王朝的一个属邦。这一时期,苏毗人最早接受了象雄文明的苯教。据苯教经典《集经》(mdo-vdus)记载,最早将苯教传入苏毗的是苯教前弘期“世界六庄严”之一的苏毗人苛呼里巴勒(sum-gu-hu-li-spar-legs)[16]。此后,有大批苏毗人热心致力于在苏毗传播和发展苯教,使苏毗成为当时除象雄以外的苯教又一大中心。
《贤者喜宴》则记载,雅隆吐蕃部落联盟的第一代赞普号“鹘提悉补野”大力提倡和宣传苯教,在雅隆建立了第一座苯教寺院——雍仲拉孜寺(gyung-drung-lha-rtsevi-gsas-ma)。其子木赤赞普也笃信苯教,曾从象雄请来苯教大师传教。据《嘉言宝藏》载,当时雅隆悉补野部苯教的若干仪轨就是经苏毗而介绍过去的[17]。因此,象雄文明中的苯教从文化上把苏毗人和吐蕃人联系在一起,三大部族之间共同的文化因素逐渐形成。
公元6世纪以后,象雄、苏毗两大部族日益势微,吐蕃则欲发强盛。政治上,吐蕃王权与苯教教权的结合使得吐蕃社会形成政教双轨运行的社会,相较象雄、苏毗比较单一的社会体制而言,吐蕃的部族社会发展很快,势力越来越大。在吐蕃王权与教权发生尖锐矛盾时,吐蕃第七代止贡赞普意识到苯教势力已经严重威胁到吐蕃王权的地位,终于兴起灭苯之历史事件。这次历史事件并没有影响吐蕃王政,反而使吐蕃社会在王权体制下,更加迅速的发展。率先求变的吐蕃人无疑在与苏毗、象雄的抗衡中占得了先机,并利用政治合作、政治联姻的手段使象雄与苏毗的势力不断削弱。这一历史演变的表现为苏毗豪族娘氏、韦氏、农氏三姓秘密与吐蕃郎日松赞结盟,又取得了苏毗蔡邦氏的归附,到7世纪初期,吐蕃迫使苏毗归附。苏毗人大致被固定在藏北高原东部一带以及甘青地区,成为吐蕃王朝对抗唐王朝的主力之一。到松赞干布统治时期,松赞干布通过政治联姻灭象雄,最终完成了统一青藏高原的大业,建立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吐蕃王朝。
苏毗人与吐蕃人联系的桥梁是象雄文明,而象雄文明所创造的文化因素,又为这两大部落联盟所吸收,并最终由松赞干布在政治上统一青藏高原。从上所述,可以发现文明早期发展的状态基本上应该是遵循着地域上各地人群的迁徙与交流——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融——政治上的逐渐统一的发展脉胳所演进的。
三、苏毗与吐蕃——征服亦或融合?
吐蕃王朝建立之后,并不意味着吐蕃王朝即刻就进入到鼎盛阶段。苏毗人与吐蕃人在融合的过程中,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与反复。与此相反,象雄人则很快地融合到吐蕃人之中,这里带给我们的思考就是苏毗人为什么如此顽强的使汉藏史籍中一直保留着对它的记载?
我们可以继续循着文明早期的发展路径去研究这个问题。目前,学界对苏毗人渊源的基本看法是认为苏毗人即羌人,代表人物为法国著名汉学家石泰安先生和国内的周伟洲先生。而笔者认为羌人即苏毗人的说法还存在问题,有待更加坚实的证据去证明。这里我们来梳理一下羌人的历史发展轨迹,亦可推测苏毗人非羌人,而是羌人中一支融入了苏毗人。《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中记载:“苏毗,本西羌族……”[18]此条史料似乎说明苏毗人即羌人。从考古资料和藏汉文献中也不难发现羌人所居地正是汉藏走廊一带以西地区。《诗·商颂·殷武》记载的“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最有可能说明在商灭夏之后,西方与西北各部落方国随之臣服,但商代中晚期,武丁以来的甲骨卜辞却反映出商代主要边患与征伐方向都比较集中在西方和西北方,主要方国有土方、羌方、鬼方与周方等。《说文解字·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这里基本确定了古羌族是游牧民族。羌人主要活动的地区是今甘青地区,而甘青地区在上古时代环境良好,是适合农耕发展的地区,我们从考古实物资料中可以推测,羌人把农业经济作为其辅助经济形式。孔颖达疏:“氐羌之种,汉世仍存,其居在秦陇之西。”我们可以推测出羌人与上古的周部落有接壤的可能性,并与周部落有一定的联系亦未可知。
《后汉书·西羌传》中还记载:“王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兵临渭首,来狄獂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嶲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羌为之盛,从此起矣。”[19]
此段史料提供给我们很多信息:1.羌人的一支由于不堪为秦所灭而移其种于西数千里。从甘青地区往西千里,当为现今藏北高原地区——唐古拉山南北一带。2.羌人中的另一支没有远徙,他们仍然留在湟中地区——即甘青地区,继续生存、发展。3.羌人的一支通过汉藏走廊一带向西迁徙到苏毗人生活的藏北高原地区,可能是因为受到外部政治势力的压迫与进攻,羌人也因此可能与苏毗人在汉藏走廊一带有所接触。
考察《后汉书》的史料之后,我们可以推论出,至少在地域上,苏毗人与羌人联系并不紧密。而《新唐书》说羌人即苏毗人之祖先的说法,可能是因为苏毗人与羌人都是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体的人群,而汉地史家并不了解两族之不同源,仅以羌人曾西奔于汉藏走廊而错以西羌为苏毗之祖先,而古人亦未见考古发现之遗迹,故出现此误。关于藏族族源“西羌说”不成立早为石硕先生论证,①石硕的《藏族族源“西羌说”的缘起及其不成立性》,载于《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另见石硕的《青藏高原的历史与文明》,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0页。本文考虑到苏毗人与早期吐蕃人的区别,另在此处加以论证。
从世界上现存的各民族的发展情况上看,没有哪一个民族是纯粹的单一民族。各民族基本上都是由不同种族的人群相互整合所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是历史演进过程中各种人群融合的产物。这种融合包括了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上的融合,是民族融合中最重要的因素。
石泰安先生在《西藏的文明》中阐述了关于苏毗人可能是由于政治的原因,被吐蕃人派驻在东部的边防地区,所以与汉地发生了联系[20]。在汉文史籍中,苏毗人已经从藏北高原转移至汉藏走廊一带与唐朝河西陇右地区发生了联系。苏毗人极有可能吸收了隋唐先进文化的许多成果,因此经济文化发展很快。《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中记载:“东与多弥接,西距鹘莽峡,户三万。”[21]对于一个游牧经济形态为主体的游牧部落,三万户的人口已经不少。在政治上,苏毗人可以依靠唐王朝的支持与吐蕃对抗。唐王朝也非常了解苏毗人与吐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在积极扶持苏毗人。
如《新唐书》中记载:“天宝中,王没陵赞欲举国内附,为吐蕃所杀。子悉诺率首领奔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护送阙下,玄宗厚礼之。”[22]
又《册府元龟》记有天宝十四载(755年)正月;内引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上奏云:“苏毗一番,最近河北吐泽(应为“吐谷浑”或“吐浑”之讹)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兵马,半出其中。”[23]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亦可知苏毗虽为吐蕃所并,但苏毗人仍然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当时吐蕃王朝对汉地的袭扰恐多出自于苏毗人。由此,可略见苏毗人虽然归附吐蕃,但没有为吐蕃真正掌控,仍然是吐蕃王朝中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24]。这也从反面说明吐蕃帝国的政治统一是不稳定的,特别是在军事、经济的控制上缺乏稳定的统治基础。吐蕃帝国的政治环境也异常险恶,松赞干布即位之初,苏毗人与象雄等部落就时常叛乱。
《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载:“松赞干布赞普之时,父王所属民庶心怀怨望,母后所属民庶公开叛离,外戚如象雄(羊同)、犛牛苏毗、聂尼达布、工布、娘布等均公开叛变。……其后,叛离之民庶复归辖治之下。又后,娘·芒布杰尚囊对苏毗一切部落不用发兵征讨,有如种羊领群之方法,以舌剑唇枪服之。”[25]
从上面的史料来看,苏毗被吐蕃吞并以后经常叛乱。吐蕃对于他们的叛乱采取的是攻心战术,即吐蕃对苏毗的一切部落不用兵征讨,仅以舌剑唇枪服之,其中的含义颇有意味。第一,苏毗人在唐王朝和吐蕃人之间进行着艰难的选择,他们摇摆不定,因此吐蕃以攻心战术扰乱、打击苏毗。第二,苏毗人的社会组织内部很可能出现了问题,对待唐王朝和吐蕃的态度上出现了意见的分歧。第三,这是吐蕃对苏毗人进行威慑的一种表现。因为吐蕃对各小帮的统治是十分严酷的,经常在各小邦内进行“大料集”,即征集粮草、兵丁[26]。在唐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大举进犯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地区,其中又征调了包括苏毗在内的各个茹的军队,分别驻守于今青海北部、河陇及西域等地,时间长约百年之久。这样,苏毗人有一部分就驻迁到了上述地区,从敦煌发现的P.T.1080、1083、1089号卷子中,经常提到了所谓的“吐蕃·苏毗”(bod sum)部落或“吐蕃·苏毗小千户”(bod sum gyi stong chung)。至今在青海一些地方还保留有以“苏毗”命名的村落[27]。苏毗人与吐蕃人一直在汉藏走廊一带进行着不断的碰撞与融合,这一过程直到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瓦解,苏毗人仍保持着其族群的特征和生存方式。
据《新唐书》记载:“乞离胡的大论尚与思罗(尚思罗)与吐蕃洛门川讨击使尚恐热在河陇一带征战,尚恐热略地至渭州与宰相尚思罗战薄寒山。思罗败走松州,合苏毗、吐浑、羊同兵八万保洮河自守。恐热谓苏毗等曰:‘宰相兄弟杀赞普,天神使我举义兵诛不道,尔属乃助逆背国耶?’苏毗等疑面不战,恐热麾轻骑涉河,诸部先降,并其众至十余万,禽思罗缢杀之。”[28]
从上可知,至吐蕃帝国灭亡时,苏毗仍然有十余万部众,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定居在今天的甘青藏区,厌倦了战争的苏毗人在历史的演进中,逐渐与吐蕃融合,形成了今天的甘青藏族。另据杨铭研究,9世纪中叶吐蕃河陇统治结束之后,苏毗人还继续在于阗活动,而且其势力与影响尚存。①杨铭的《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所见苏毗与吐蕃关系史事》,载于《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第32页。另见杨铭的《唐代的吐蕃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苏毗人的部族大体仍然分布在藏北高原地带、甘青地区,另有一部分活动到西域地区。活动在甘青地区和藏北高原地带的苏毗人就成为现代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活动在西域地区的苏毗人未见史籍的记载。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政治上的统一并不能迅速的迫使一个族群融入到另一个族群,使族群融合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文化、经济上的认同与融合。吐蕃王朝建立后,印度佛教与中原佛教由两个方向传入西藏,逐渐取代了苯教的教权地位,佛教使居住在藏地的众多部众在心理上有了更加紧密的联系;人种学上羌人、吐谷浑人、吐蕃人、苏毗人、象雄人基本上融合到了一起;经济上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及与汉地、西域诸国的联系,已经使得青藏高原内部区域经济结构的差异性变得不是那么明显;再加上吐蕃王朝的建立,政治上已经使得各部落寻求到了统一的归宿,并最终在藏地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个性的藏传佛教,成为藏民族的精神纽带;青藏高原居民与其生存、发展所居住的自然环境也是其最终融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西藏文明的形成。
今天,我们仍然缺乏对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关系的认识,本文认为人地关系是西藏文明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西藏地区,在上古时代可能是比较封闭的,较少有与外部的交流和活动,但是不可否认仍然存在着与中亚、南亚、中国内地的联系[29]。历史并不是由我们想象而发出的,法国汉学家石泰安先生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深思:“西藏地区表面上看是隔离于其他地区,但是它从相当古老的时代起就向四方开放。只是我们的古代地图中,那里尚为一个空白点。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那里也似乎是个置身于世界历史发展之外的地区。”[30]而苏毗人与吐蕃人内部的联系则更加富有历史的曲折性,汉藏史料、佉卢文书、敦煌文献中所记载的大量与此有关的历史信息,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西藏地区内部各部落之间的碰撞与融合的景象。特别是有关汉藏关系方面的历史文献,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了汉藏走廊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苏毗人与吐蕃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不断碰撞和交融,特别是汉藏走廊在地理上所起到的联结作用,使得苏毗人与吐蕃人共同完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蜕变。这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并没有昭示苏毗人的再次崛起,而是把苏毗人融入到吐蕃人中的这一历史过程演绎得更加富有戏剧性。历史犹如一场戏,苏毗人和吐蕃人是这场精彩大戏的重要演员。
余 论
苏毗人的游牧性特征,使得他们很早就与吐蕃人之间存在地理环境上的联系,之后象雄文明苯教文化因素的联结作用,使得苏毗人与吐蕃人在文化上有共同的信仰成分。在长时段的上古中古时代的时间维度中,汉藏走廊成为西藏文明历史发展进程的空间平台,又使得吐蕃与苏毗拥有了共同的历史舞台。中古时期,苏毗人与吐蕃人的关系中又掺杂进了中原王朝和西域诸国的联系作用,这些因素使苏毗人最终融入到藏族当中,成为西藏文明中重要的文化因子。苏毗人的历史演变过程基本遵循着地域上的迁徙与交流——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融——政治上的逐渐统一的发展脉胳而演进的,当中经历反复与曲折的政治、军事斗争,并由此融入西藏文明。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谈到历史学的研究应该借助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借以开拓历史学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并中肯地表达了“用新的研究方法和态度去解决历史学遇到的问题和处理历史资料的时代已经到来”[31]的思想。沿着前人的研究理路,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本文通过分析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的资料,对西藏地区的苏毗人的历史演化阐述一点不成熟看法,重构上古与中古时期苏毗人的历史演化进程。本文有论述不当之处敬请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1][2][4]周伟洲.苏毗与女国[A].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史论稿[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8,9,4.
[3][18][21][22]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下[Z].北京:中华书局,1975.6257.
[5][法]石泰安.川甘青藏走廊古部族[M].耿昇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71-77.
[6][10][14][16][17]石硕.西藏文明东向发展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35,51-53,47-49,53,52-53.
[7]林冠群.苏毗与森波杰考辨[A].唐代吐蕃历史与文化论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291-317.
[8]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5-27.
[9]周伟洲.古青海路考[J].西北大学学报,1982,(1):65-72.
[11][12][20][29][30][法]石泰安.西藏的文明[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15-21,13,16,11-21,21.
[13]杨正刚.苏毗初探(续)[J].中国藏学,1989,(4):136.
[15][24]宗喀·杨正刚布.苏毗与吐蕃及其他邻近政权的关系[J].西藏研究,1992,(3):49-55.
[19]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Z].北京:中华书局,1975.2875-2876.
[23][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九七七·外臣部[Z].北京:中华书局,1989.3895.
[25]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增订本)[M].王尧,陈践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165.
[26]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诏传上[Z].北京:中华书局,1975.6278.
[27]杨正刚.苏毗初探(一)[J].中国藏学,1989,(3):35-43.
[28]新唐书·卷二一六·吐蕃传下[Z].北京:中华书局,1975.6105.
[31][英]杰弗里·巴拉克勒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