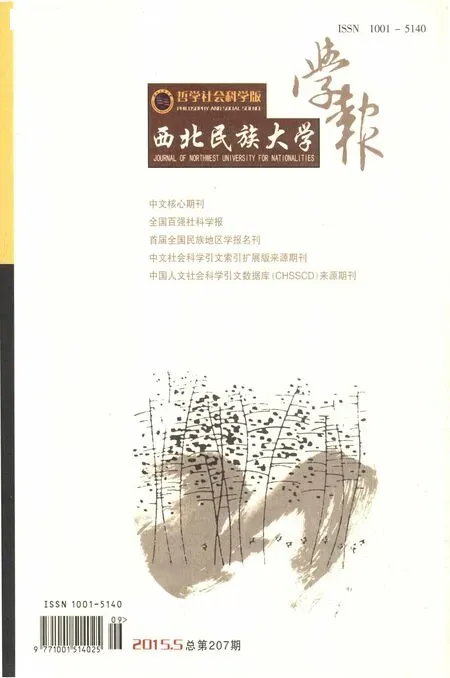“习惯法”中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探析
李中和
(惠州学院 思政部,广东 惠州516007)
习惯法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调整本民族内部的社会关系,维护本民族的社会秩序,体现本民族群众的意志和利益,具有行为约束力的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行为规范体系。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习惯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逐渐积淀下来的,对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影响很大的行为规范体系。习惯法在调整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方面有着国家制定法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为“这种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它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的法律衰老或消亡的时候,它可以复活那些法律或代替那些法律,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的创新精神,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以习惯的力量代替权威的力量”[1]。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民族群众智慧的结晶及民族意识、民族心理的重要体现,在民族群众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强大的思维定势,成为民族群众评价社会关系及衡量行为价值的特殊标准。
一、习惯法、习惯及国家制定法
习惯法普遍存在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其内容丰富,类型多样,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生产分配、债权债务及纠纷处理等方面的习惯法,对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影响很大。但对于什么是习惯法,学界看法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习惯法就是习惯,或者传统习惯。如冉继周,罗之基在《西盟佤族社会形态》中说:“佤族社会仍然依靠长期的历史形成的习惯和传统,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各种关系,维持社会的秩序。佤族没有文字,这些传统习惯和道德规范,没有用文字固定或记录下来,所以也可称为习惯法。”[2]也有学者将习惯法等同于国家制定法,认为习惯法是国家制定法的组成部分。孙国华在《法学基础理论》中说:“习惯法是经国家认可并赋予国家强制力的完全意义上的法。”[3]还有学者认为,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法之外、依靠特定的社会权威或社会组织实施并赋予其强制力的行为规范体系。如田有成,阮凤斌在《中国农村习惯法初探》一文中说:“习惯法是指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的,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根据事实和经验,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4]
事实上,习惯与习惯法及国家制定法是不同的概念。习惯是模式化的日常行为,“通常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自然形成,或由于重复和练习而巩固下来的某种行为方式和生活准则。”[5]既可以是个人生活习惯,也可以是生产习惯,其范围较广且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其遵守也不具有强制性;习惯法则是群体性的行为规范,其内容稳定,其遵守具有强制性。习惯法也不同于国家制定法。习惯法是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自然形成,或依据特定民族社会组织的权威约定而成的,体现本民族群众的共同意志和利益,为本民族群众共同遵守,依靠本民族群众所认可的权威力量来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国家制定法则是由特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体系。习惯法体现特定地域群众的共同利益和意志,有着明显的地域性、群体性及民族性特征。习惯法虽具有强制力,但这种强制力不是源自国家政权,而是源自民间权威。而“这种权威既可以是得到民间社会成员信任、认同的权威人物,也可以是人们所认同、尊奉的民间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等。……但无论哪一种权威,它都必须得到民间社会成员的认同、信服甚至是崇拜”[6]。习惯法与国家也没有必然联系,法国学者亨利·莱维·布津尔曾指出:“还未产生文字的原始社会必然生活在习惯法的制度下。在原始社会中,习惯法数不胜数,多种多样。”[7]
综上所述,我们既不能把习惯法等同于习惯,也不能把习惯法等同于国家制定法。那种将习惯法视为习惯的看法,混淆了习惯与习惯法的区别,扩大了习惯法的范围。美国学者霍贝尔曾就这种观点提出批评,他说:“照字义解释,这意味着陶器制造术、钻木取火术、训练小孩子大小便的方法以及另外的人们的全部习惯都是法律,这岂不是一个荒唐的主张!”[8]而那种将习惯法等同于国家制定法的观点,又混淆了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区别,缩小了习惯法的范围。此种观点将习惯法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认为习惯法是由国家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它否认那些未被国家认可却普遍存在于民族地区并对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调整及社会秩序的维护发挥重要作用的行为规范的存在。在习惯法概念方面,高其才教授认为:“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9]这种观点明确界定了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范畴,指出了习惯法的基本特征,是符合习惯法客观事实的正确观点。
二、环境习惯法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与基本要求,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保障则是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首先依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一个平衡、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是人类生产、生活的资源保障。如果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就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就不可能得到保障,社会和谐就无法实现。“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10]事实证明,社会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如果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破坏,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就会受到影响,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就难以建立起长久的和谐关系。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也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我国各民族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及维护生态平衡的环保意识。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各民族先民以“万物有灵”为特征的自然崇拜就体现了人类早期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而这种“万物有灵”观念又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演变为人与代表自然物的“神”之间的关系。为了趋福避祸,祈求神灵保护,人们对神灵化身的自然物敬而崇之,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种种威严神圣的宗教禁忌。“禁忌成为原始社会唯一的社会约束力,是人类以后社会中家族、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所有规范性质的禁制的总源头。”[11]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禁忌逐渐演变为世代共信共行的行为模式,它扮演着法律的角色,起到与法律相似的引导、教育、保护、遏制、威慑、惩罚以及协调社会关系的作用。在今天广大的民族地区,禁忌仍是习惯法的重要内容。民族群众以宗教禁律、行为禁忌等方式规定了各种保护“神山”“神树”的习惯法。例如,拉祜族群众奉养“神山”“神树”,其习惯法严禁砍伐“神树”,严禁破坏森林资源。“广西田林县的壮族村落,几乎村村屯屯有大榕树或龙眼树,少则一棵,多则满村都是,郁郁葱葱,碧绿掩映。原来这里的壮族群众崇敬大树,认为它们富有灵性,特别是大榕树和龙眼树,它们年代古久,高大如巨盖,四季常青,便视之为生命的神树和村屯的保护神树。当然,对于一些高大古怪的树,他们也加以崇拜。认为有了大树,村屯人畜的生命才能得到保障,才能保证全村的兴旺和富裕。”[12]由于畏惧“神”的威力,没有人敢去砍伐树木。在这里,禁忌控制着人们的精神意识,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体现着法律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
今天藏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与藏族先民的苯教信仰密不可分。苯教是藏族先民们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万物有灵”为特征的一种原始宗教。“在苯教看来,自然万物本来是人类生命的组成,人与万物共享基本的生存方式。人类敬畏天地万物,实质就是敬畏生命。敬畏自然和生命的外在方式是看护生命,看护自然,做自然和生命的奴隶。”[13]藏族先民对神灵化身的山水等自然物敬而崇之,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世代传承的保护环境的宗教禁忌。杨士宏教授在谈及藏族习惯法时说:“藏族习惯法的形成,最初不外乎其先民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出于‘万物有灵’的观念而产生了信仰与禁忌,久而久之成为人们敬天、敬地、敬人的行为规范,并形成人们在群体生活中所共同遵守的习惯和风俗。”[14]在藏区,高山林立,湖泊众多,到处可见藏族民众所崇敬的“神山”“圣湖”。藏族民众借助种种禁忌保护着这里的动植物。例如,四川德格藏区习惯法规定:“不准开垦‘神山’,不准在‘神山’打猎、采药。”若违反这些禁忌,则会受到神的惩罚。“关于这些思想,在甘、青一带藏区生活中反映得更为突出和广泛……出于对山神的尊崇,还有在山神周围捕猎动物和砍伐林木花草的禁忌,倘若在山神区捕杀飞禽走兽,认为那将会祸难临头,也是对山神的侮辱。”[15]藏族民众的神山圣湖禁忌“已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或公约,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坚定信念。”[16]对藏族群众而言,无论植物还是动物,已不再是单纯的生物,它们已被赋予神性而不能任意亵渎。由于这些禁忌习惯法的存在,藏区的神山圣湖因人为性破坏活动的避免而成为草木茂盛、动植物繁多的自然保护区。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以资源环境为中介的利益关系。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日趋明显,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有些人为了个人利益、眼前利益肆意攫取自然资源,破坏了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大量涌现,这不仅会影响到民族群众之间的团结和睦,而且会危及到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存在于我国广大民族地区的环境习惯法,不仅使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观念,而且有效地约束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减少了人们在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与冲突,在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群众之间的团结和睦。
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互帮互助习惯法,有利于促进民族群众之间的团结和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涉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的诸多问题。然而,当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都发生着深刻变革,人们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发展,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来自社会、人际和文明等多方面的挑战。人们往往在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忽略了对于道德伦理的重视,致使社会道德衰颓,社会矛盾突出,人际关系日趋复杂尖锐。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以正确处理而任其积累和发展,势必会带来更多的不安定因素。而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很多规定在促进民族群众之间的团结,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大多规定有尊老爱幼、赡养老人、救助孤寡、扶贫济困、互帮互助等内容。例如,贵州各少数民族习惯法几乎都有孝敬父母、尊敬老人、互帮互助等规定。在他们传统的社会组织中,“寨老”“款首”“族老”等村寨头人通常由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侗族习惯法“侗款”,提倡团结和睦,强调家族内部要团结,村寨群众要友善,要团结互助,要维护村寨安宁,如“不许拆散家庭”“睦家族”“和邻里”“见人落水要扯,见人倒地要扶”等内容。鄂温克族习惯法要求尊敬老人和长辈,遇见老人和长辈时须屈膝请安。土家族自古就有以孝为上、生产生活互帮互助习惯法,他们的族谱家规中都规定有“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内容。土家族习惯法严惩子女的不孝行为,若成年子女成家立业须分家,应先留下父母的“养老田”及其他财产。布依族习惯法称:“帮苦济贫,天下太平”“富不要忘贫,饱不要忘饥。”苗族村寨习惯法“榔规”,提倡大公无私、热心公益事业、团结友爱、助人为乐、尊老爱幼等。在苗寨,如果有人因病或灾祸不能完成生产任务时,寨人就会帮其完成。
这些关于尊老爱幼、以邻为友、救助贫困、生产生活互助习惯法巩固和增强了民族群众之间的认同感和亲切感,有效维护和促进了民族群众家庭成员之间及民族群众之间关系的和谐,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民族地区村风寨风的改善、村民之间的和睦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都起着积极的作用。“在今天,广大的彝族农村基层的社会秩序也主要是依赖于习惯法,在自然村一级的社会单位中习惯法充当了微观秩序实现的主要依赖。”[17]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对这类习惯法加以引导、提升,进一步挖掘其中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其在促进民族地区和谐新农村建设,协调民族地区社会关系及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习惯法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体现了在解决纠纷问题上的和谐理念
纠纷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和重要表现,任何社会都难免有纠纷和矛盾。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说:“纠纷意味着失范,代表了社会秩序紊乱和道德规范失衡的反动倾向。”[18]纠纷的产生意味着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并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纠纷的解决则是为了恢复、保障社会和谐。社会秩序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延续、社会发展的推进,都离不开纠纷的有效解决。任何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都是以恢复社会和谐为目标的。由于纠纷具有类型多样性特征,其解决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而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进而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如果一个纠纷根本得不到解决,那么社会机体上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如果此纠纷是以不适当的和不公平的方式解决的,那么社会机体上就会留下一个创伤,而且这种创伤的增多,又可能严重危及人们对令人满意的社会秩序的维护。”[19]尤其是在民族地区,纠纷能否得以正确解决,直接影响到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奋斗目标的实现。
习惯法在处理民族群众纠纷方面,通常采取以调解为主,避免事态扩大的调处息讼机制。调解纠纷通常由在本民族或本家族、社区威望较高的寨老、族长、宗教人士或其他德高望重者出面主持,寨老、族长和宗教人士等不仅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较强的办事能力,而且要具备办事公道、能言善辩、有胆识、处事沉稳等品质,还要熟悉本民族习惯法及各种礼俗。寨老、族长等调处纠纷、解决矛盾,以民族群众团结和睦及社会稳定为出发点,以民族礼俗和习惯法规则为依据,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上进行沟通、调解,并达成双方当事人都较为满意且日后不得反悔的协议。例如,壮族习惯法处理群众纠纷,大多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由寨老、都老或者乡老主持调解。如果问题较为复杂,则由长老会议或村民大会来讨论解决。根据独龙族习惯法,群众纠纷不能自行解决时,由家族长出面主持调解,家族长本着息事宁人、邻里和睦的态度,根据案情及群众意见来判断是非,化解矛盾。瑶族群众纠纷通常请石碑头人或瑶老来处理,石碑头人或瑶老以和解为原则进行处理。侗族习惯法规定,遇到群众纠纷不能自行解决时,由各村寨头人进行斡旋调解,最终结果是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可见,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纠纷,没有社会矛盾,而是需要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对社会矛盾和纠纷迅速地加以化解,使社会恢复到有序的和谐状态。但这不意味着纠纷的有效解决都是借助国家强制力实现的。“国家法律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似乎容易得以有效贯彻;其实,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其再公正,也肯定会失败。”[20]这是因为,“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结构明确的行为规则和正式的强制程序所起到的作用都很有限”。而且,“许多冲突和争议并不涉及法律问题,完全能够通过某种非正式的方式,在不危及社会和平的情况下得到解决”[21]。习惯法以调解方式解决群众纠纷,不仅能迅速地化解矛盾,有利于促进民族群众之间的团结及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而且能够丰富、完善民族地区的纠纷解决方式,有利于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调解机制。
当然,在肯定习惯法在维护民族地区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下,不应忽视其也存在着一些阻碍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消极因素,这主要表现为某些习惯法存在着与现代法制及民主精神相违背的内容,如“赔命价”“赔血价”及“神判”习惯法等。所谓“赔命价”,就是加害人或其亲属在宗教人士、部落头人等的调解下向受害人亲属赔偿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财物,以此补偿受害人家属所遭受的损失而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习惯法。“赔命价”“赔血价”不问案件事由、罪与非罪,只要致人伤亡,就要赔偿命价、血价。虽然“赔命价”及“赔血价”习惯法在解决群众纠纷、惩罚犯罪、稳定藏区社会秩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以这种习惯法来处理刑事案件,不仅破坏国家法制的统一,损害国家法制的尊严,阻碍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而且还会给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同样,“神判”习惯法在解决群众纠纷和冲突,保障家庭和村寨安宁,维护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等方面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神判”毕竟是唯心的,它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而是依靠“神”的意志论争讼、断是非。“有罪或无罪的证据常求之于超人的权力。定谳的权委于神灵,而以占卜及神断的方法探神之意。问神的话是一句率直的问题,要求‘是’或‘非’的一句答案。”[22]“神判”这种违背理性的原始陋习,经常造成冤假错案,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的法制进步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此外,民族地区还存在着影响社会和谐的械斗、血亲复仇等习惯法以及有害、落后的陈规陋习等消极因素。例如,瑶族尤其是广东连南瑶族的“搞是非”,就是械斗习惯法。白族家庭,或者村寨之间发生纠纷难以和解时,则以械斗来解决。但械斗习惯法禁止危害妇女和儿童。珞巴族、高山族等民族地区还存在着血亲复仇习惯法。珞巴族的血亲复仇主要是由盗窃、劫掠、债务、婚姻等原因引起的。高山族一些地区存在以两造的父系家族直系血亲为中心而临时纠集起来的复仇团体来解决通奸、杀人等问题的复仇习惯法[23]。这些落后、有害的旧习惯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破坏了民族地区和谐的社会关系,阻碍了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
五、结语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的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完善,已经形成了包括社会组织习惯法、婚姻习惯法、刑事习惯法、所有权习惯法等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行为规范体系。对各民族群众而言,从其出生就受到本民族习惯法的强烈熏陶和影响,思想上深深地打上习惯法观念的烙印。这也是习惯法至今仍在民族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所在。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保护民族地区的生态坏境,调解民族群众之间的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习惯法中也存在着阻碍民族地区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消极因素。因此,对待少数民族习惯法,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全面肯定,也不能全面否定。
对于习惯法中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关系和谐发展的优秀成分,如劝善惩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水源、禁止滥砍滥伐、处理相邻关系、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维护民族团结等习惯法,应当与时俱进,赋予其时代精神,使其向开放化、规范化、科学化方向发展。这部分习惯法代表着民族群众的整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相符合,也与国家制定法的基本精神相一致,能够与国家法律法规形成良性互动,起到共同维护和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和谐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条件成熟时,对这部分习惯法进行总结、提炼,吸收其精华,并通过民族自治立法将其逐步纳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那些与我国民主法治精神相违背的内容及其他影响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的消极因素,如与国家刑事法律相冲突的“赔命价”“赔血价”习惯法,复仇、械斗习惯法及其他有害、落后的陈规陋习等,这些消极因素严重桎梏了人们的思想,妨害了人们的生产、生活,阻碍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对此,应根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民族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采取循循善诱、科学渗透等办法进行改造或摒弃。
总之,对待少数民族习惯法,应采取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在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民族生活习惯、民族文化心理、民族审美观念和民族感情等因素,运用正确的民族理论并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对其现实状况及价值进行科学地分析、鉴别、取舍、改造,批判地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分,并加以创新,增加符合时代要求、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新内容,使其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发挥在保护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加强民族群众之间的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加大民族地区经济及教育的发展力度,努力提高民族群众的政治文化素质,逐步改变落后的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群众的法制观念,从根本上消除习惯法在构建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和民族地区法制建设中的消极影响。
[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73.
[2]冉继周,罗之基.西盟佤族社会形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
[3]孙国华.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41.
[4]田成有,阮凤斌.中国农村习惯法初探[J].民俗研究,1994,(4).
[5]刘艺工.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特点[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6]李可.习惯法——一个正在发生的制度性事实[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
[7][法]亨利·莱维·布津尔.法律社会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49.
[8][美]霍贝尔.原始人的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18.
[9]高其才.论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文化[J].中国法学,1996,(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任聘.中国民间禁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14.
[12]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壮族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520.
[13]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
[14]杨士宏.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2.
[15]谢热.藏族习俗中的本教遗迹[J].青海社会科学,1988,(2).
[16]南文渊.论藏区自然禁忌及其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作用[J].西北民族研究,2001,(3).
[17]张小辉,方慧.彝族法律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336.
[18]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4.
[19][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0]苏力.变法、法治建设及其本土资源[J].中外法学,1995,(5).
[21][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22]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08.
[23]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