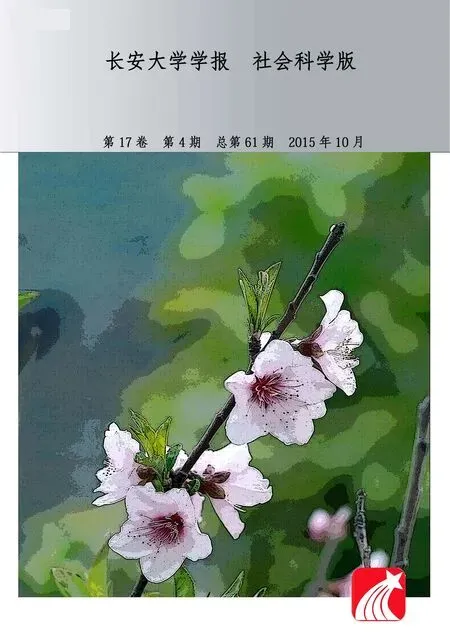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苏礼和
(1.闽江学院法律系,福建福州 350121;2.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 350117)
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苏礼和1,2
(1.闽江学院法律系,福建福州350121;2.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福州350117)
摘要: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和经济为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强烈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经济观,认为必须把社会公平引入公共行政中去,并作为其基石和核心,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的现代启示,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维度,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关键词:效率;经济;社会公平;公共行政道德化;公共行政
传统公共行政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效率与经济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指导着公共行政的发展与前进,基于此,公共行政呈现出一番令人惊讶的图景:它一味推崇效率至上的理念,坚持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崇尚价值中立,却使公平正义、民主等公共性意涵备受冷落和忽视,使公共行政缺失了“公共”,凸显出“行政”的管理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新公共行政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批判了这种效率至上的发展范式,认为在效率和经济之上,公共行政必须植入社会公平观,只有这样,公共行政才能获致合法性和公共性。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观的现代性启示,它要求价值和道德因素必须渗透于公共行政之中,具体言之,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内容,而道德化的公共行政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一、以效率为核心的传统公共行政
政党分肥制是西方各国一项重大的政治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包括领导者和下属在内的政府官员与政党共进退,行政职位成为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奖励给成员的一种犒劳品。显然,带有奖励性质的政党分肥制有着明显的弊端。第一,行政人员缺乏与职位相适应的专业化知识和技能,他们无法进行专业化、科学化、技术化的操作,无法熟悉行政所特有的运作程序和规则,而且政府行政人员处于周期性的大规模更迭中,政局不稳、人心不定致使当时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第二,政党分肥制是一种竞争的政治制度,在竞争的状态下政党间互相攻击和诋毁,使政党矛盾愈加激烈,这种矛盾进而扩大到社会,社会容易分裂成对立的阶级、阶层和群体,促成了不同利益对立情绪的增长,而这种对立情绪一旦被煽动起来,那么公共利益就成了无人看守的空门,极易遭到践踏和侵犯。第三,政党的活动受利益集团的赞助,那么基于对利益集团的回报和馈赠,上台执政的政党极有可能制定有利于自身以及偏向于自身利益集团的政策,而忽视了公共利益的表达和守护。由于行政职位成为获胜政党对成员的奖励品,行政人员由此掌握大量的权力,这容易导致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之风盛行。第四,由于是分肥制,行政职位掌握巨大权力,权力的稀缺性和自利性促使更多的人为了能够进入政府,发生相互勾结、金钱交易、营私舞弊等各种社会丑陋现象。总而言之,政党分肥制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公共利益无人看守。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弊端出现呢?这成为西方近代学者不断探索的问题。
威尔逊通过理论与实践的探究,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他认为,政治与行政有明显的区别,它们之间有自身特殊的领域,不能相互混淆:“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1]“行政管理是置身于政治所特有的范围之外的。行政管理的问题并不是政治问题,虽然行政管理的任务是由政治加以确定的,但政治却无需自找麻烦地去操纵行政管理机构。”[1]“政治是在重大而且带有普遍性的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政策如果没有行政管理的帮助就将一事无成,但行政管理并不因此就是政治。”[1]可见,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试图将政治与行政相区别,赋予行政一块属于自身的领域而免受侵犯,把社会秩序、公共利益的实现等功能交给了行政来承担,为行政效率的提高提供了一种可能和保证。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理论的提出,使行政管理从政治的裹挟之中挣脱出来,行政管理开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如果说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为行政的高效率和经济目标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那么如何实现公共行政的高效率,如何以最少的资源提供最优质和最大化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通过什么方法和手段来实现效率和经济目标?马克斯·韦伯所精心构建的官僚制理论为实现这两大目标提供了答案。官僚制强调行政人员需恪守价值中立原则,在执行政策时必须不偏不倚,它崇尚工具理性,强调合理的组织分工、等级森严、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严格依照规章制度和程序办事的运行机制。可以说,韦伯所创立的官僚制学说,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科学化、技术化、专业化、理性化的进程,是一个不断提高行政效率最大化、谋求公共行政合法性和合理化的历程:“对于政治而言,行政是以属于工具理性原则的,是政治工具,只有当它毫不包含任何价值因素的时候,它才有了对政治而言最充分的价值。也就是说,行政作为政治的工具,它的唯一追求就是效率。它多大程度上是高效率的,它就多大程度上是实现了它对于政治的价值。”[2]
总而言之,无论在实践还是理论上,追求效率占据了传统公共行政的主流地位,这一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家和实践者都将精力和目光投向于如何使效率更高这一问题上。实际上,追求效率是公共行政的应有之义,但问题是它只追求效率,将效率奉为自身的唯一目标。这显然忽视了公共行政领域的特殊性,公共行政有自身的价值偏向,不能将其与市场相提并论。效率至上观所呈现出的管理主义思维模式只会使公共行政“公共性”的丧失和被遗忘,“功利主义的思考和行动逐渐占据了优势的地位。功利主义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对个人欢乐的诉求,对经济成本和利益的斤斤计较,取代了为公共利益而思考及其行为。社会似乎成为人们角逐个体利益的战场,‘公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3]。“公共性”的丧失客观上使政府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为“对经济效率的崇拜,对个人、部门、地方以及短期利益的追逐,无视公民和社会的合法期待,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贪污、腐化以及对公共资源的公开掠夺等等”[3]。
二、新公共行政之社会公平观解读
新公共行政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在强烈批判传统公共行政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同时,把社会公平的价值引入到公共行政中,认为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和基石,这为公共行政学注入了一种新鲜的血液和活力。对公共行政学的历程来说,这无疑是公共行政价值体系的一次重大突破。
新公共行政学强烈批判了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学,认为传统公共行政学只把焦点聚焦在财政预算、人事管理、组织机构内部运行上,忽视了对社会、文化、政治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也忽视公共行政与民众的互动和联系,很少关注公共行政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使公共行政远离社会危机处理的需要。它认为“政治”和“行政”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公共管理者并非是价值中立和冷漠无情的,公共管理者必须有其价值取向,必须信奉并致力于实现良好管理的价值。新公共行政学还对当时流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提出了质疑。它认为,民众是“顾客”而并非“公民”的观点必将摧毁公民神圣的观念,政府不是简单的企业,而是有其内在的公共性,采用市场机制、竞争机制和工商管理技术、坚持顾客导向和市场导向改造的所谓“竞争型”、“企业化”政府办法并不可取,民营化、市场化和放松管制会导致更大的腐败,认为政府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更多的政府,而不是更少的政府。
接着,新公共行政学提出了社会公平理论。社会公平理论是新公共行政学最核心的表达和诉求。弗雷德里克森并不否认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强调的经济和效率两大支柱:“效率——尽可能地利用已有的金钱实现更大的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实践的理论基础。经济——尽可能少地使用纳税人的金钱去实现某一公共目标——同样是一个诱人的目标。”[4]但仅仅有效率和经济作为支柱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要。”[4]因为某些政策在某些人看来也许是有效率和经济的,但在某些人眼中它也许是低效和昂贵的。这样很有可能造成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将会导致非正义。他强调,公共行政人员必须致力于实践社会公平,这是公共行政这个特殊领域所决定的:“公共管理者解决和改善问题,对服务分配问题进行判断,在执行政策时使用自由裁量权。公正、平等一直是指导行动的共识。”[4]他认为,公平应该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的指导理念:“建立一种成熟的社会公平和公共行政复合理论是我们构建理论和研究的目标。这种理论必须在政策领域得到检验;必须用联邦主义意旨来指导;如果不能预测也至少必须能够界定代替性政策、组织结构、管理风格等对公共行政计划的平等性的影响。”[4]
社会心理学家亚当斯认为公平应该是人们不仅关心个人努力所得到的绝对报酬量,而且关心自己的相对报酬率。公平就是付出与所得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责权利相结合。弗雷德里克森对公共行政中的公正与社会公平进行阐释和解读,他认为,社会公平应该作为民主公正社会的基础,作为分配公共服务的法律基础和实践基础,作为理解复合联邦制的知识来源,以及作为研究和分析的一种挑战[4]。同时他建立和阐述了一套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认为这一理论应包含单纯的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公平、公平的领域、机会公平和公平的价值等6个方面,最终他得出结论:“社会公平原则指导着我们对公共行政精神的理解,它要求我们既要高效,又要公平。”[4]这一理论包含了新公共行政学派,还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概括了公平的含义,并赋予了其社会意义。社会的公平有助于加强社会凝聚力,是社会群体团结的黏合剂,而不公平会加剧社会的不信任,会导致政体合法性的下降。为了进一步阐述公平的意义和概念,弗雷德里克森还从美国著名政治自由主义学家罗尔斯那里获得了“公平”的坚实基础,即公平不仅是法律上的公平,更应该是事实、结果的公平。罗尔斯假设在原始状态下人们处在一个“无知之幕”中,人们不知道关于他们自身的某些特殊事实,如他在社会中的地位、阶级出身、天生资质、自然天赋等,因此为避免将来可能造成对自己的不利,人们便通过订立契约以“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将是正义的。基于“无知之幕”的假定,罗尔斯提出了“正义论”的两个基本原则,即“自由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弗里德里克森还论述了罗尔斯的代际公平和正义理论,认为“无知之幕”在运用代际正义时,就是各方都不知道属于哪一代人,不知道自身是富裕还是穷困,更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人与其他代人相比,是富裕还是穷困,也不知道自己属于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每一代人需考虑到下一代人的生存状态和条件,承担一定的义务和责任。可见,公平、平等地享有自由权利,是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新公共行政学所追求的目标。
三、公共行政道德化:社会公平观的现代性启发
新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公平观强烈呼唤公平与正义,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公平与正义呢?毫无疑问,人们把目光聚焦在行政部门以及行政人员身上,因为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秩序的提供者,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增进公民幸福生活和实现公平与正义方面起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另一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现有的公共行政体制在公平与正义方面显得苍白无力,总是在追求效率时冷落了公平正义,忽视了伦理性和道德化的取向,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激发公共行政的应有精神和价值追求回归呢?我们觉得只有使公共行政道德化,使公共行政体制和制度道德化,才能实现公平与正义,重拾对那些亘古不变信条的信仰。传统公共行政在追求科学化、技术化和专业化的道路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它企图通过制定大量的法律和制度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以为有了规章制度就可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了。但法律与制度总是滞后于现实生活,所提供的仅仅是一个规范空间和制度框架,它无法预测未来发生的情况,无法囊括社会的方方面面,总存在一些真空地带和漏洞,而且政策、法律与制度都是由人制定和执行的,如果制定的人是不道德的,或者内容缺乏价值合理性,那么法律极有可能成为恶法。或者在执行过程中,法律或制度的价值合理性得不到有效遵守,缺乏现实性和手段而陷于瘫痪,这些弊端要求公共行政道德化,要求行政人员在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注入道德的因素,弥补制度设计和运行中的不足,使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获得实现的可能。单单靠宣传和教育是远远不能实现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它要求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
具体言之,公共行政道德化包含两个维度:
第一,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行政体制的道德化是指行政的制度法规、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内含着伦理道德的因素,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安排中有着道德化的合理规范,包含着道德实现的保障机制;二是已经确立的制度是应当有利于道德因素的生长和成长,能够对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的提高起鼓励作用。”[2]为什么要体制道德化:“因为只有制度的和体制的道德才是深刻和广泛的,才是具有稳定的引导功能的行为规范。”[2]制度和体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相对于个体,具有稳定性和确定性特点:“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道德化的制度和体制,不为个体的偏爱所左右,无需通过个体的认同为中介即可产生作用。罗尔斯也强调: “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 只要它们不正义, 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6]我们从制度伦理建设的视角来考察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发展, 就是要跳出制度设计纯科学化和技术化的认知偏误, 坚持“一切技术,一切规划以及一切实践和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7]。
第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如上所述,制度、体制的安排和设计由于具有相对性、滞后性等缺陷,无法对社会现实做出及时回应,并不能全部解决社会的所有问题,即使能解决,也因为它自身缺乏价值判断和选择而使结果缺乏正当性。同时,公共行政面临的环境是不确定、变幻莫测的。人类所有的活动都依赖于人,依赖于它的主观能动性,即使是制度、体制的设计和安排,也是因为人的存在才得以形成。人具有主观性,任何一次行政活动的开展和实施,都是行政人员价值的选择和取向的结果,因取向和选择的不同而导致的结果也会有所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而行政人员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即是赋予他取向和选择的权力,在此过程中,他们是否拥有美德、是否肩负崇高使命、道德是否高尚同样对结果产生巨大差异。可见,公共行政所涉及的领域和活动不但依赖于体制和规章的合理安排,使体制和规章拥有道德化的因素和倾向,同时,它还要借助于“人”,通过提升行政人员的美德、道德化水平和崇高使命来实现公共行政的道德化。有学者大胆提出,行政人员在公共领域中必须拒绝权利[2],因为行政人员一旦在公共领域中享有权利,那么行政人员就必然会运用公共权力去为他的个人权利的实现和扩张开辟道路,且行政人员的个人权利不可能或很少受到侵害,没有理由念念不忘自己的权利。
四、公共行政道德化的基本内容
(一)从行政人到公共人
行政人假设是政府和行政人员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他们不偏不倚,注重规则和程序,相信人类理性能够解决公共行政中存在的问题:“行政理论所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方面和非理性方面的界线,行政理论,是关于意向理性和有限理性的一种独特理论,是关于那些因缺乏寻求最优的才智而转向满意的人类行为的理论。”[8]行政人假设固然有一定合理之处,但它将公共行政内外部环境做简单化处理和分析,忽视了公共行政面临环境的变化性和复杂性,总以为依凭规章制度就能控制一切,忽视了对外部的重视,造成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回应性差、机构臃肿等弊端。公共人是公共领域中政府和行政人员应然的角色定位,是公共行政体现“公共”性质的内在表现。“公共管理者以公共利益为行动动机,摒弃个人狭隘的私利,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这就是‘公共人’假设。”[9]“公共人的基本行为宗旨就是维护公共利益,并通过对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增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性内涵。”[10]第一,它是非人格化的。“公共人”并非依据具体的人而设定,它是由特殊的职位及其权力、责任所决定的,不是人的特性而是职位决定了它的角色定位。它要求不管行政人员在私域中有多少私利和欲望,只要进入公共行政领域后,就应该抑制甚至抛弃私域,应该将“公共人”作为自身的角色定位。第二,它是利他的。“公共人”追求的是他人的利益,它不追求也不允许追求自身的私利,它为他人利益的维护和增进提供帮助和服务,是一种完全的利他主义者。第三,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政府是公共利益和公众个体利益的守护人和看守者,“公共人”的各种活动的实施和开展,都是围绕如何保护公众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地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要求政府和工作人员转变对自身角色认识,进行合理、科学的定位,只有认清了自身的角色定位,才会有与角色相适应的行动和价值取向。无疑,公共人为政府和工作人员找到了合理的定位,进一步促使政府和行政人员富有崇高的使命、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二)从顾客到公民
新公共管理运动追求以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将政府提供服务的对象称之为顾客,认为政府应积极满足顾客的需求,对顾客的需求做出积极、及时的回应:“为顾客提供与企业的最佳服务相同的服务。”[11]“民众是政府的‘所有者’,而非顾客,‘所有者’概念具有主动性,它可以决定政府的议程,更符合人民的地位。”[12]这种将经济领域中消费者的身份引入到公共领域中,强调成本—收益的理念,无疑忽视了公共领域的特殊性。“在公共部门,我们很难确定谁是顾客,因为政府服务的对象不只是直接的当事人,而且,政府有些顾客凭借其所拥有的更多资源和更多技能可以使其自己的需求优先于别人的需求。”[11]同时,顾客身份忽视了政府服务对象是政府的主人、所有者、监督者和授权者的身份。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要求政府将服务对象视为公民,公民不仅单指拥有一国国籍的人,它还特指一种特殊的理念、价值观、认同感和情感。“公民权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包含着对社区及其成员的承诺,包含着对公共事务的一种重要参与水平,并且包含着一种将个人自己的利益置于更广泛的社会利益之下的临时意愿。”[11]特里·库伯认为:“公民角色是认识公务员角色的基础,更明确地说,公民角色是认识公共行政官员角色的基础。”[11]“公共行政官员的道德身份于是就应该是被雇佣来作为我们中的一员为我们工作的公民;他们是一种职业公民,他们所委以从事的工作是我们在一个复杂的大型政治共同体中所不能亲自干的工作。行政官员应该是那些‘特别负责任的’公民,他们是公民这个整体的受托人。”[11]因此,公共行政道德化应将公众视之公民,从公民的视角履行公共行政的职责、满足公民的需求,建构一种和谐、活力、畅通的政府与公民关系。
(三)从管理到服务
长期以来,公共行政是一种管理行政,它强调政府在与公民之间的优越性,政府是作为一种管理者而存在的,公民是被管理者,需接受政府的管理,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一种统御与被统御关系。同时,它突出了技术主义、管理主义、实证主义的逻辑思维和价值取向,这种思维和取向带来的是政府与公民关系的失衡和冷漠,忽视了公共行政本真、崇高、神圣的使命。公共行政的道德化要求政府从理念深处实现釜底抽薪式的转变,即从管理走向服务。从政府产生的来源来看,社会契约论认为,政府是公众让渡自身绝大部分权力而形成的,是人类理性、妥协的产物,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的成立是为了能更好地为人类带来福祉和利益,为人类提供秩序、自由、民主、安全等公共性“产品”。因此,道德化的公共行政必须还原和重归它的原初之样,即突出它的服务意识和观念。具体言之,这种服务表现为:第一,从理念上树立起服务的意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认识到,他们存在的理由是为了服务于民众,服务是他们的应有之义,需摒弃官本位、权力本位等落后思维,将公民视为国家的主人,而不是统治、管理的对象,主动设计各种体制、机制和渠道接受公众的监督;第二,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利益是关乎全体公民的一种切身利益,政府的所有行为和理念都必须服从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不能有自身膨胀的利益倾向,更不能有任何有悖于“公共性”目标的行为。
(四)追求公共性
公共性是政府的第一属性和本质属性,追求公共性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公共行政道德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努力维护和增进政府的公共性。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人民能自主、平等地参与国家权力的运转和公共政策的形成,人民能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地监督和控制,人民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13]而公民向政府纳税,税收为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提供了物质支撑,为政府工作人员提供了物质来源:“不征收和开支金钱任何政府都无法存在。”[14]“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它任何东西的经济的基础。”[14]可以说,社会契约论和公民纳税从理论和现实层面确立了政府公共性。政府公共性有多重涵义:它是作为一种衡量、分析和评判政府及工作人员活动的工具;它是作为一种理念和精神规范和引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利益取向上,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供的是公共的、而非私人的产品和服务;它还意味着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维护政府的公共性,是道德化、正义性、伦理性政府的应有之义。具体言之,政府公共性包括:第一,权力的公共性。政府权力的来源决定了权力的公共性。权力来源于每个个体的让渡和授权,它所指向的是公共利益和个体的合法利益。既然权力是公共的,那么政府又有何权利凭借手中的权力去谋私利呢?它应该时刻铭记自身的职责,在权力使用的每个过程、每个结果都应深深地烙上“公共”的痕迹,它不是某些人的私权力,不是谋求私利的权力,而是谋求社会福祉的工具。此外,它还意味着公民对权力有监督权。监督权力是否出现异化,是否成为某些个体的专属品,是否偏离它的轨道。第二,责任的公共性。享有权力即意味着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公共的权力决定责任的公共性。“只有责任才是行政人员的全部行政行为的基本内容。”[2]这意味着:第一,对公共利益的责任。政府向社会输出的公共政策、公共物品和服务,是追求公共利益的具体表现,而不应是为了某些利益集团和群体。第二,对公平正义的责任。公平和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政府是公平正义的实现者和看守人,对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公共行政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说明,单纯追求效率和经济并不可行,因为它忽视了公共行政领域的特殊性和价值取向,冷落了公平与正义这一公共行政极其重要的价值。因此,公共行政必须引入社会公平观,必须彰显其伦理性和道德化的倾向,使其回归公共行政的应有精神和价值取向。具体言之,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包含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做到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只有这样,公共选择才能恢复其应有面貌,重拾公众的信任。
参考文献:
[1]彭和平,竹立家.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2]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张成福.重建公共行政的公共理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4):1-7.
[4]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刘霞,张璋,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苗力田. 亚里斯多德全集:第8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社,1994.
[8]西蒙. 行政行为:对行政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佚名,译.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9]陈庆云,曾军荣,鄞益奋.比较利益人:公共管理研究的一种人性假设[J].中国行政管理,2005(6):40-45.
[10]张康之.公共行政:经济人假设的适应性问题[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2):12-17.
[11]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方兴,丁煌,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2]张成福.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反思与批判[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15-21.
[13]肖君拥.人民主权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Publicadministrationmoralization:modernvalueofsocial
equalityinthenewpublicadministration
SULi-he1,2
(1.DepartmentofLaw,MinjiangUniversity,Fuzhou350121,Fujian,China;
2.SchoolofMarxism,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50117,Fujian,China)
Abstract:The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takes the efficiency and economy as its the core value based on the dichotomy of polit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 bureaucracy. The new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rongly criticizes the theory of efficiency and economy in the tradit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troducing the social equality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akes social equality as its cornerstone and core, Only then it can reflect the spiri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ralization is 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of social equality, includ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system moraliz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moralization with its four basic contents containing from administration person to the public person, from the customer to the citizen, from management to service, the pursuit of publicity.
Key words:efficiency; economy; social equality; public administration moralizati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ZW059) 陕西省中德文物保护科技合作项目(2010(201))
收稿日期:2014-12-09 2015-06-02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4-0095-06
作者简介:苏礼和(1985-),男,福建闽清人,讲师,法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