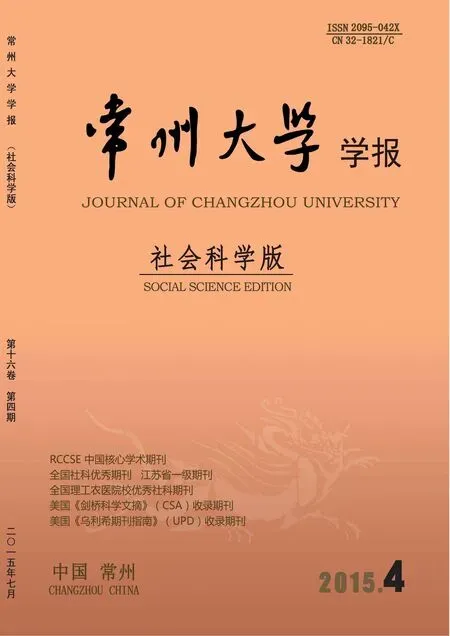1946―1949国统区新闻界“整肃运动”探析
李时新,陶喜红
(1.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广西南宁530004;2.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统治区,记者敲诈索贿时有发生,民众视记者为特殊人物,“敬鬼神而远之”[1]。1946年,新闻界自动发起了一场以“建立职业道德”为主旨的“整肃运动”。这场运动因其广泛影响被上海《前线日报》以“报界整肃运动之展开”评为1947年新闻界“十大国内新闻”。对于这一历时三年,“在我国报业史上还是空前的举动”[2]的新闻道德运动,除了偶有文章提及其中的个别事件,学界少有论及。为什么这一时期记者的不端行为如此突出?为什么矫正记者行为的“整肃运动”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本文拟对此进行一番探讨。
一、记者的不端行为
在当时的新闻界,大多数记者都能清白自爱,忠贞自持,但“少数记者的堕落行径,全体新闻界已蒙受其害”[3]。这些行为主要表现为强行推销报纸或广告,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等。以汕头为例,因报纸销路滞阻,为维持营业,各报馆不是着力改善报纸的内容和形式,而是强迫商户订阅报纸。尽管各商户在商铺门口贴上“各报上涨,不负报费”的声明,但报馆报差依旧每晨丢下一份报纸,月终便登门催讨报费,不容诿卸。否则,报馆必定百般恫吓,务使缴款。而在长沙,许多报社不按定价收费,也不经商家同意迳自刊登广告,尔后索要费用,“市民深以为苦”[4]。
此外,常有记者以刊发负面新闻敲诈当事人。1947年8月,某市市长挟妓开房,一些报社的记者得悉,立即前往包围,威胁见报。结果,每人当场领到二十六万元“遣散费”[5]。有的记者还无中生有,虚构事实,勒索对方。然而,并非每个当事人都如此轻易就范,这种情况下记者便直接刊登不实报道向对方施压。1947年9月,南京一名六旬老翁因纠纷在蓝姓仇家门口自杀,此案即将由法院审理。五名记者以各报所载不符合事实,影响法院判决,须由蓝家出面招待新闻界为由,索要费用一千二百万元。蓝家之子蓝华堂认为数额巨大,置之不理,以后“各小报上,散见各种不正确的歪曲报导”[6]。对此,南京《中央日报》社长马星野指出:“在新闻界的人,都知此种事情为经常发生之事。受过此种毒害的人,都知道这是无可告诉之受苦。每天有不少的冒牌记者,在做同样的勾当。每天也有不少的‘蓝华堂’,在受同样的敲诈。南京如此,上海更甚;京沪如此,内地更甚。”[7]
受贿或变相受贿在新闻界也很常见。这些记者笃行“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游戏规则,或隐匿不报,或文过饰非,或歌功颂德,拿报道权作交易。1946年12月,长沙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面粉事件”,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分署和市政府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用于建造本市平民住宅所需的一千五百吨面粉,划拨给各报馆,通讯社,记者公会以及六家外地报纸 (包括:上海《申报》《新闻报》 《大公报》 《东南日报》、南京《中央日报》、汉口《武汉日报》)驻长沙特派员。为掩人耳目,由他们以建筑商的名义领取。当总署执行长刘鸿生到长沙视察工作时,各报都大登社论,以整版的篇幅刊发分署的“工作报告”,卖力地吹捧。《大公报》驻长沙特派员王伯恭还发出总署执行长“甚为满意”的专电[8]。对于长沙报界的行径,《中央日报》斥为“中国报业的大污点”,指出救济分署不过是借贿赂报纸掩盖其平日的渎职行为而已[9]。
这种“官” “报”勾结甚至演化为“报”对“官”的挟持。如汉口食盐短缺,而盐务管理局却常常以低廉的官价大量配给各报,各报转而在黑市销售,获利甚厚。对此,盐务管理局谓有“难言之苦”[10]。汕头的几名记者到侨务处索要“人情船票”未遂,竟将该处捣毁。报馆前往调查肇事记者的姓名,侨务处“反坚不吐实,似有无限隐痛者”[11]。显然是记者掌握了这些部门的不法行为,这些部门不得不一再隐忍,受其驱策。
另外,还有名为采访实为选举拉票,诋毁银行信誉,籍以贷借资金,过年过节向政府或商家索取赏钱,强行募款招股或兜售书刊等情况存在。
记者的失检行为之所以如此严重,除了整个社会风气堕落,还与记者的生存环境恶化,记者队伍鱼龙混杂以及一些记者缺乏正确的职业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1946至1949年,国内经济动荡,各报经济窘迫,减薪和欠薪严重,记者生活十分清苦。以1947年初的广州报纸为例,总编辑月薪二十万元左右,编辑为十五万至十七万元,有的仅七万元,辛苦三十个日夜还不够买一石米。随着物价日增夜涨,这种状况更加突出。
记者生活困窘,除了报纸经济惨淡,报纸老板侵害记者利益,记者公会组织不健全也是主要原因。以1948年为例,长沙各报老板多不顾员工生活,且中饱其平价米,以致有《商情导报》编辑李天舜为生活所迫,偷窃铅字,流为盗贼。当各报员工发动“清算 (报老板)运动”,要求“员工薪给应照中央分区调整办法支给”时,一些素恃剥削员工为生的报纸立即采取统一行动,进行抵制[12]。在上海,《小日报》老板刘德铭一面将政府廉价配纸转售黑市非法获利,一面又克扣员工工资。其报馆记者每月仅百万余元,常以稀饭充饥。
记者公会本来是维护记者权益的组织,但多由报纸老板一手掌控,要想让记者公会改善记者待遇无异于缘木求鱼。由于报管倒闭,不少记者失业,记者公会不但不施以援手,反而规定记者离开报社即失去会员资格,任其自生自灭。1947年“九一”记者节,姚苏凤等二百零二名记者在《东南日报》发表文章,批评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未能履行职责,“对于记者福利、进修等项,几于没有一件提起或办到”,“根本就不把记者当作‘同业’”,呼吁“争取记者合法权益”,“清算记者公会工作”,声明“脱会”[13]。有的地方的记者公会负责人不仅不为记者办事,反而肆意侵占其利益。例如,何冰如身为济南市报业公会和市新闻记者公会的理事长,却凭借职权侵占记者公会的平价面粉,引发同业声讨,后虽经中央社济南分社出面调解,也只是退还部分面粉分给各通讯社。
面对生存危机,意志薄弱,不耐清贫的记者于是借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正如一位报人所言:“若干记者的‘行为下流’,做出坏事,可说是环境的迫使,自有物质的背景在!”[3]
另外,记者队伍急骤膨胀,良莠不齐,也是造成记者行为失检频发的重要原因。1947年下半年,各地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选举在即。按照规定,记者属于自由职业团体,其候选人选票系综合全国的票数计算。如果某地的记者越多,所提出的候选人也越多。这样,一些报纸老板或记者公会负责人为了在选举中胜出,便不加审查,大量扩充记者,“将记者头衔,制就无数‘纸帽’,逢人便送,异常冗滥”[1],不少嗜利之徒乘机混入记者队伍。1948年,在上海“九一”纪念会上,一位记者质问:“记者公会究竟是为办选举的还是做事的?”引起全国同业的共鸣[14]。此外,一些报纸或通讯社为了谋利还大量出售记者证,也使会员成分庞杂。如杭州一家通讯社每年售出记者证四五十本之多。这些所谓记者有的是商店老板,有的是戏院女伶,有的是地痞流氓,有的是漏网的小汉奸。他们凭借记者身份胡作非为,危害一方。市警察局就曾向记者公会发函,称有“记者”数人出入娱乐场所,以吃白食,看白戏为能事,且有捣毁茶室物件的事情发生。
在记者队伍中,不乏持正不阿之人。1946年8月,湖北汉寿县《汉寿民报》总编辑黄少文和《正义日报》副总编辑李仲篪同时收到要求着重报道某新闻的钱款,二人均拒收,并联合发表启事:“(吾人)向以维持正义为职志,倘再有行贿行为,决依法诉请法办。”[15]然而,也有一群记者从业动机不纯,把新闻工作当作进入仕途或聚敛钱财的终南捷径。1947年7月,粤汉铁路列车在广东英德坠江,伤亡八百余人。8月,为了掩盖过失,粤汉铁路局局长杜福汉在长沙举办盛大的记者招待会,并邀请各报记者参观粤汉铁路全线。二十日后,这批记者由港穗倦游归来,衣着均已焕然一新。为投桃报李,这些记者发表了许多歪曲事实的报道。汕头的几个税务机关每月都负担着各报数万至十余万元的“津贴费”。一些洁身自好的报人为维护报格,不受收买,拒领津贴,反被同业视为“傻子”和 “眼中钉”[16]。
总之,这些背弃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激化了新闻界与民众的矛盾,也激起了新闻界的危机意识,一场由新闻界发起的“整肃运动铺展开来。
二、“整肃运动”的开展
“整肃运动”最早于1946年上半年由长沙报界发动,其他地方报纸或记者公会亦陆续起而倡导, “整肃运动”在多个城市零星开展。1947年秋,首都新闻记者公会呼吁从严规定记者资格并及时惩处五名实施敲诈的记者,形成了整肃声势。之后,各地报业公会或记者公会开始广泛地推动这一运动。
当记者的不轨行为刚刚萌生时就引起了新闻界人士的警觉,他们不惮自揭“家丑”,痛陈这些记者不仅自坠人格,自招轻侮,抑且玷污了整个新闻界的声誉,遭到社会的轻视。他们斥责这些记者为“败类”或“害群之马”,号召新闻界为了自己的职业和使命,拿出勇气,进行自我整肃。《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记者的职务,在倡导公论,分别正邪,辨白是非,倘若我们自己立身不正,如何能够正人?自己自私自利,如何能够主张公道?自己为非作歹,如何能够彰明善恶?”提出“整肃职业风气,建立职业道德,实为当前的急务”[17]。正是这些报人或报纸的不懈呼吁使“整肃运动”逐渐成为新闻界和社会的共识。为了形成整肃的舆论声势,当一起事件被检举时,众多报刊都及时披露,指名道姓,同声谴责。如长沙“面粉事件”发生后,上海《评论报》在1946年12月第9期和第10期分别发文《“面粉事件”余波》和《长沙“面粉事件”高潮》,揭露长沙报纸与救济分署沆瀣一气,由“民众喉舌”沦为“民众喉塞”。《中央日报》在1947年1月6日发表评论《长沙的“面粉事件”》批评长沙报纸屈服于贿赂之下,希望长沙同业“解全国新闻界之惑”。上海《新闻天地》在同年9月第27期撰文《整肃新闻记者的队伍》,指责分署公开行贿,记者甘受收买。此外,上海《社会评论》和香港《光明报》还分别在1948年第73期和1949年第9期刊载《报界的一些黑幕》和《长沙报界的怪现象》,抨击长沙报界触目惊心的腐败黑幕。北平《华北日报》还举办征文活动,利用其新闻学专刊《现代报学》于1947年10月12日和26日刊登了两期“报人道德问题特辑”。其“编者的话”指出,整饬新闻记者道德极为重要,“特辑”的目的就是集思广益,研讨记者应该遵守哪些新闻道德,最终形成“记者守则”之类的文件。其他报纸,如《申报》、天津《益世报》、重庆《大公报》等也都陆续发表文章,呼吁整肃记者风纪。总之,新闻界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开启了“整肃运动”,也助推了“整肃运动”。
记者行为不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制定的记者资格标准宽严各殊,致使记者队伍滥竽充数,因而,规范源头成为问题的关键。1947年7月27日,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分呈市民政局、社会局及内政部、社会部、选举总事务所,并通电全国同业,请求从严规定记者任职条件。8月中旬,汉口、济南和天津三市的记者公会都先后表示支持。17日,首都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全国,就记者资格提出“必须严格规定”,“应限于以新闻事业为其专业者”和“全国务求一致,不可稍有轩轾”三项主张[18]。成都、桂林、开封和北平四市的记者公会也迅速响应,呼吁政府尽快颁布“记者法”。22日,首都新闻记者公会还推派理事刘启瑞、许君武、邓季惺三人赶赴社会部,请政府从速确定记者资格标准。23日,马星野撰文《整肃新闻记者的队伍》,希望政府负责部门切实制定确立新闻记者的身份标准[19]。在记者公会的呼吁和敦促下,内政部会同社会部最终于10月底颁布了记者任职资格,即“凡在报社或通讯社担任发行人、经理、撰述、编辑、漫画编辑、采访、广播、广播评论员、摄影,及以新闻为专业之特约通讯记者,或主办发行广告之人,均应视为新闻记者”,为各地记者公会登记和审查会员提供了标准。尽管记者公会的呼吁和敦促更多着眼于即将举行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但在客观上加速了“整肃运动”的开展。
当记者资格标准尚在酝酿时,一些记者公会或报业公会已经开始筹组机构,制定措施,配合“整肃运动”。1947年7月,天津市新闻记者公会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整饬记者风纪,决议“以后如有假藉记者名义招摇撞骗,请各界随时向本会举发,以便查究”,同时组建“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9月,首都新闻记者公会召开第二届理监事联席会议,通过了由马星野、张友鸾、邓季惺等人的联名提案[20]:(1)由理事会通知各理监事及各单位负责人于七日内自动清查本单位会员;(2)由本会推定理监事五人、其他会员三人,合组会员审查委员会,调查各会员身份。凡属会员均可公开或秘密向审查委员会检举。审查会限于十日内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并将整肃后之名单公布。不久,记者公会又组织“整肃委员会”,并制定了“奖励检举办法”[21],包括:(1)凡本会会员,为爱护团体名誉负责检举不肖记者,经本会调查属实者,得于事后由本会授予荣誉奖状,并以公开仪式授予之;(2)凡社会各界人士负责检举不肖记者,经本会调查属实者,得于事后由本会赠予奖金,其数额为检举人服务单位,全部薪津三个月至六个月之和,视其情节之轻重而定,由被检举人所服务之单位,自被检举人扣缴送会转发;(3)前条所谓“负责”字样,指检举人必须列具真实姓名、住址及职务,并签名盖章,详列所检举事实而言,如有挟嫌诬告,一经查实,检举人亦当负法律上之责任;(4)凡检举函件,一律请寄送记者公会组织组,本会绝对代检举人保守秘密。同月,开封市新闻界整肃运动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常务会议,通过:(1)登报公告取缔各同业,以任何名义或方式在外募捐,并通告各界检举;(2)久悬空招牌未出版或未发稿之报社通讯社,函请省府依法取缔[22]。10月,无锡新闻界成立“风纪整饬委员会”,整肃记者阵容。同月,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第二届年会通过了汪松年、成舍我、张明炜等四十四人提出的“为请大会一致主张新闻从业员应恪守新闻记者道德案”,提议新闻界同仁“共同维护新闻职业神圣庄严之不可侵犯性”[23]。12月,南昌市报业公会规定,对未出版而利用各种名义进行募捐等活动的报社,商请地方军警当局取缔。1948年11月,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审查会议,决议:(1)函催未填报会员登记表之报社,迅即填报,以便汇齐审查;(2)小型报、通讯社先送请小型报联谊会及作者协会作初步审查,再由会核定[24]。会员资格审查委员会和整肃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各项措施的颁行,为打击腐败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
在整肃过程中,一些地方的记者组织工作主动,不护短,不迁就。杭州市新闻记者公会原有会员五百三十三名,1948年7月经审查通过者四百三十四名。8月初,鉴于有记者行为不轨,市外勤记者协会发表宣言,列举其种种劣迹,请社会人士检举,肃清这些败类。记者公会当即重启审查,清除不合格会员二百二十余人。亚细亚通讯社记者沈国钧和陈秉权“图谋非利”被人检举,也被开除会籍①。
在前文所述五名记者敲诈事件中,共有社会新闻通讯社、《首都晚报》《社会日报》《和平日报》和《建设日报》五家单位的记者涉入。首都新闻记者公会、首都通讯业协会和各报社、通讯社负责人对此极为重视,指派七家报纸的记者进行调查,其中就有《社会日报》 《和平日报》和《建设日报》。这三家报纸不因自己的记者涉嫌而有所偏袒,而是严肃认真地追究事件真相,并将事件经过公正客观地披露出来。 《中央日报》对此颇为赞赏,指出:“新闻界自动自发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实为新闻界树立一种良好的楷模。”[25]而这几名记者也被所在的报社停职,并被记者公会开除会籍。事实上,五名记者的敲诈行为也是由一位同业向首都新闻记者公会整肃委员会检举而揭发的。
只要牵涉新闻道德问题,不管是普通记者还是报社负责人,记者公会等组织都能够及时予以处置。如汉口《大华晚报》社长常奥定招摇敛财,汉口市报纸联合会和新闻记者公会都给予其开除会籍的处罚,而《大华晚报》不久亦自动停刊。
三、“整肃运动”无果而终
然而总体看来,“整肃运动”并未有效提高记者的职业道德水准。根据掌握的材料,在这三年中,记者的不端行为并无减少。究其原因,有如下数端:
自1946至1949年,全国物价持续攀升,员工收入每况愈下。以贪贿求生存仍是许多记者的选择。改善记者待遇无疑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有人就指出,“记者待遇的改善,应该是‘整肃运动’中的积极工作”,因此“政府应该扶植和保障新闻业”。问题是,受制于动荡的政局和自身体制,政府难以有大的作为。以1947年为例,公教人员 (即公务员和教师)可以享受实物配给,而报人却没有,“单以京沪两地来说,大部分新闻记者还及不上京沪的小学教员的待遇”[3]。1948年6月,上海市民食调配委员会呈请粮食部核准,决定为本市新闻从业人员配给特价米,但由于上海市报业工会 (会员为从事铸字、排版、印刷和杂务的工友)提出同样的要求,因牵涉甚广,易生枝节,又即刻悬置。这姗姗来迟的待遇都无法兑现,又如何遏止记者铤而走险?同时,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也牵扯了报馆的视线。面对随时可能倒闭的危险,“很少有报纸不是在斤斤于赚一点钱来苟延残喘地维持下去,至于如何将报纸办得好,能真正教育启导民众,倒成了其次的问题,甚或不能顾及了”[26],当然也没有更多的精力关注非关眼前存续的记者职业道德问题了。
“整肃运动”由新闻界自动发起,在首都新闻记者公会通电全国后,得到多地记者公会的呼应。然而,由于缺少统合各地新闻记者公会的全国性记者组织,全国新闻界对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肃并没有形成一个纲领性文件。因此,各地记者公会多各行其是,断续开展,整肃并不彻底,这样就出现了一面整饬一面贪腐的怪象。而具有一定号召力的首都新闻记者公会并没有勇挑重担,负起领导之责,只是强调自我整肃,发挥示范作用,以期带动全国新闻界(“以为全国倡导”)。没有制度的约束,感召的效果可想而知。
惩治记者的贪污行为,除了由报社和记者公会共同实施,还需要司法部门的紧密合作,但后者常常疲沓拖延,削弱了惩处成效。汉口中央分社主任徐怨宇因贪污被撤职,后又被提起公诉。1946年10月,法院一再传讯徐怨宇,但徐避不到庭。鄂高法院呈准司法行政部明令通缉。两个月后,尽管徐仍寓居武汉,迄未缉获。1948年4月,汉口地方法院检察处决定不予起诉,理由是司法院解释中央分社主任并非公务员,不能按贪污论。“各界对此案发展,均惊奇不置”[27]。曾经在国内激起轩然大波,引起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严重抗议的长沙“面粉事件”,终因牵涉大多数报纸发行人,亦不了了之。
“整肃运动”也没有获得政府主管机关的及时支持。“整肃运动”的关键是确定记者的任职标准,内政部和社会部本应主动配合,及早研究并出台相关规定,但两个部门多少表现拖沓。在首都新闻记者公会通电提出“三项主张”后,各地记者公会纷纷呈请中央确定记者身份,颁布“记者法”。首都新闻记者公会还派专人向社会部反映意见,督促跟进。社会部总是答复还在洽谈。在此期间,社会部称“新闻记者身份……在《新闻记者法》第一条已有具体规定……自仍可参照办理”,而中央宣传部则称“记者公会之会员资格,可由各省市公会自行决定”,政出多门,令人无所适从。经过数月的洽商,内政部和社会部最终公布了记者任职资格。两个部门行动迟缓导致各地记者公会会员审查的滞后和混乱,予一些心术不正的记者以可乘之机。
最后,政府管理的漏洞也影响了惩治的力度。根据有关规定,创办一家通讯社只须在银行存入一亿五千万元基金,内政部即可核准成立②;而通讯社可以不受限制地招聘记者。一些既无专业技能又无职业观念的人混入记者队伍之后,往往凭借合法的身份招摇撞骗,更具隐蔽性。有报人认为“内政部对滥发执照一事应负责任”③。
综上,某些记者的贪腐行为激起了民众的怨恨,也损害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声誉,国统区新闻界乃以刮骨去毒的勇气发起了这场“整肃运动”。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动荡不安,记者待遇未见改善;新闻界组织多为报社老板掌控,偏离组织宗旨和员工利益;政府忙于应付紧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无暇顾及新闻界,而一些部门行政执法不力,又牵制整治,这场运动未能有效阻遏记者的贪贿行为,未能达到其“建立职业道德”的目标。
注释:
①《清除新闻界败类杭展开整肃运动》,载《报学杂志》,1948年试刊号,第23页。
②此规定见彭河清: 《买空卖空也领执照》,载《报学杂志》,1948年创刊号,第12页。
③彭河清:《买空卖空也领执照》,载《报学杂志》,1948年创刊号,第12页。
[1]三十六年记者节 [N].前线日报,1947-09-01(02).
[2]蒋荫恩.谈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 [N].华北日报 (北平),1947-10-26(06).
[3]茅锦泉.新闻界整肃运动应着重积极工作 [N].前线日报,1947-09-01(05).
[4]新闻的新闻 [N].前线日报,1948-02-16(05).
[5]伍修麟.整肃新闻记者的队伍 [J].新闻天地,1947(27):8.
[6]新闻界整肃运动第一炮[N].申报,1947-09-23(05).
[7]马星野.新闻界二三事[N].中央日报 (南京),1947-09-25(02).
[8]龙福高.“面粉事件”余波 [J].评论报,1946(9):14.
[9]长沙的“面粉事件”[N].中央日报 (南京),1947-01-06(12).
[10]新闻的新闻 [N].前线日报,1947-04-07(05).
[11]新闻的新闻 [N].前线日报,1948-06-07(03).
[12]新闻的新闻 [N].前线日报,1948-05-31(03).
[13]慷慨陈家丑 [N].前线日报,1947-09-08(05).
[14]珞.记者公会应该做点事了! [J].报学杂志,1948(2):2.
[15]新闻的新闻 [N].前线日报,1946-08-23(11).
[16]李白虹.华南报业的逆流 [N].前线日报,1947-03-10(05).
[17]我们当前的课题——祝九一记者节 [N].中央日报 (南京),1947-09-01(02).
[18]新闻记者资格必须严格规定 首都记者公会通电提供意见[N].申报,1947-08-18(02).
[19]《周末观察》刊文论记者身份问题[N].中央日报 (南京),1947-08-24(04).
[20]首都记者公会倡导整肃 设委员会严格审查会员 [N].中央日报 (南京),1947-09-09(02).
[21]新闻界整肃运动奖励检举办法 [N].申报,1947-09-23(05).
[22]汴垣新闻界组织整肃委员会[N].前线日报,1947-09-23(02).
[23]平市记者公会二届年会通过之恪守新闻记者道德案 [N].华北日报 (北平),1947-10-12(02).
[24]记者公会举行审查会员资格 [N].申报,1948-11-11(02).
[25]树立良好的楷模 [N].中央日报 (南京),1947-09-22(04).
[26]穆加恒.物价与报价——一部十五月来的报价上涨史 (上)[N].前线日报,1948-04-26(03).
[27]新闻的新闻 [N].前线日报,1948-05-17(03).
——基于FPS游戏《穿越火线》战队公会的网络诈骗行为研究
——以FPS游戏《穿越火线》战队公会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