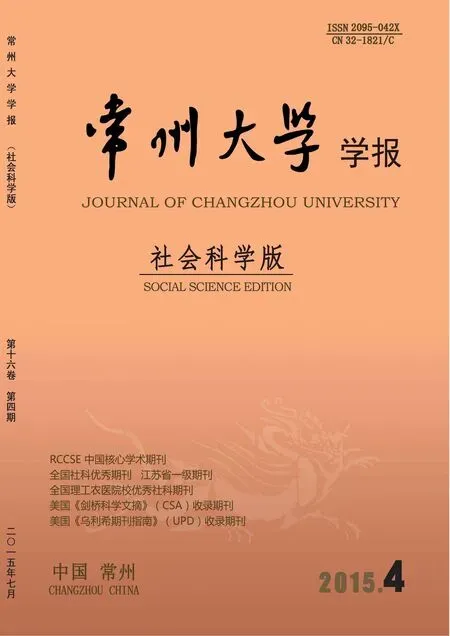孔子“仁”学体系的基础与提升——以 《论语》为中心
郭院林
(扬州大学文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一、孔子之前“仁”的意思
关于“仁”的起源,有学者依据《说文》“古文仁或从尸”的说法,进而结合社会学推论“仁”就是古老的东夷的风俗习惯逐渐孕育出类似行为准则的思想意识,这些意识正是“仁”的最初萌芽。[1]仁的本源脱胎于尸礼中的仪规“设尸”,就是以活着的死人后代,比如长孙,来扮装鬼神。“仁”本来是对祖灵的一种极端虔诚和敬拜的自然心性,从而认为仁的原始内涵不是横向的人偶相爱,而是悼亡哀死的纵深的内在心性。仁不因横向关系而立,本源在于自发的、纵深的、内在超越的心性。[2]
“仁”字在可靠的古书中, “其在成康以后乎”①。《尚书·金縢》中也有提到一个仁字:“若尔三王,是有不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这里“仁”相当于人。《诗经·郑风·叔于田》:“叔于田,巷无居人。岂无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齐风·卢令》说:“卢令令,其人美且仁。”联系上下文,可以认为此处“仁”为外貌英俊威武的意思。“仁”字意义的发展经历了由崇拜容貌、气质、力量,进一步发展到道德的自觉和反省,这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灵走向成熟的反映。
春秋时人相偶爱的仁是推己及人。《说文》在解释“仁”时说: “仁,亲也。”段玉裁特别对“相人耦”进行关注,认为“人耦犹言尔我亲密之词。独则无耦,耦则相亲,故其字从人二。”[3]365实际上,纯粹从文字字形上难以得出“仁”即“亲”之意。或者认为“仁”右边部分为“心”省文,仁为上人下心的形声字,或者郭店简中“仁”字写作“身心”,这些“仁”很难从字形进行解释,抽象义理难以从文字训诂考据得出。②无论“仁”为会意字,或者认为“二”是重文符号,“仁”为象形字 (人人)[4]219,“仁”是“尔我”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仁”是“独则无耦”的话,其一是表示自己,其二是表示与自己面对面的他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代表集体,或者就是整个人类社会。[5]90语言的意义往往是约定成俗和在生活中改变并适应现实生活需要而产生新意的。也就是说,仁可能是由人分化出来的一个字,郑玄注《中庸》中“仁者,人也”即此意。 “仁”与“人”的联系与区分:由“人”字发展衍化而产生抽象的哲学的意义,当这个意义足够重要时, “仁”字出现,意义内涵仍属“人”,另加两点,以区别“人”字。
本文不准备探讨孔子之前是否有“仁”字或“仁”什么意思,因为“从古文字来看,仁字有几种写法,造字时取义都是什么”难以确定。[5]90文献不详,所论犹如射覆。我们认为,孔子“仁”学体系的阐述必须从与之最密切最可靠的文献《论语》文本出发 (而不是文字学),分析“仁”的语境,才有可能揭示其丰富意义。
二、孔子“仁”意义基本价值
“仁”字在《论语》中先后出现109次,其中,他人讲仁25次,孔子自己讲仁84次。孔子与弟子在“仁”的应用和所指意义上应该说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笼统地将《论语》中所有“仁”看作孔子思想的表达。“仁”成为贯穿孔子思想的主线。孔子是第一个系统论述“仁”的思想家。《吕氏春秋》说:“孔子贵仁。”[6]15前贤近哲大都认定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③《论语》对孔子“仁”学体系一以贯之的思想有明确的表述:
子曰: “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孔子曰: “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也就是说,孔子在追求博学的同时有一个约束的东西,亦即《述而》篇所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
子曰: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
《说文》心部“恕”字下解释说: “仁也。”段玉裁注认为“恕”和“仁”“析言之则有别,浑言之则不别也。”段玉裁注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孟子曰: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则为仁不外于恕。”他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些注释都是外延,没有内涵式定义。[3]504
然而这固然可以看出孔子对于“仁”的重视,然而仁具有多重意蕴,是孔子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性格、志趣、学识、根器的学生和人物,随机作答。而这些“仁”没有明确内涵与外延,亦即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从而为我们研究带来了困难,同时也是考验与机会。这些“仁”在表达或叙述时意义模糊,逻辑层次上似有可商。单就问仁包括问仁人、仁行等总计达20次,而有些是正面界定“仁”的外延,例如:
有子曰: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
……
同时,有些反面界定也在一定程度规范了“仁”的边界,如: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子曰: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里仁》)
……
我们可以从逻辑起点来看《论语》中“仁”的本初意义及其意义如何扩大。
《说文》“仁,亲也”的解释与其说是词义真实,不如说是许慎或汉代人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取向,而这也就是《论语》“仁”的德性起点。有子所谓“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④《学而》)以往多解释为“根本”。如果说孝悌是仁的根本,似乎与孔子和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并不一致。《说文》对“本”解释为“木下”,抽象意义多为后来学者所赋予。《贾子·道术》篇解释道:“子爱利亲谓之孝,反孝为孽。弟敬爱兄谓之悌,反悌为敖。”而《管子·戒》篇“孝弟者,仁之祖也”中“祖”与“本”似乎可通。《说文》“祖”训为“始庙”[7]3,段玉裁引 《释诂》曰: “祖,始也。”[3]4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孝悌”本为自然情感,作为家庭关系的人伦道德,它是处理社会所有关系的起点和开始。这样与生俱来的自然情感为孔子建立“仁”学体系提供了基础。
正如上文所论证,“仁”从客观上来说是个人之“我”和外界的关系,亦即一己和他人相处之道。当人对社会认识达到一定高度,知道如果放纵自己必然会伤害到对方,因此提出约束自己。仁是每一个人能够进入社会关系存在的标志。原始人不能孤立生活,必须依靠群体。同时西方哲人说人和人相处就像刺猬相处,太近就会伤害到对方,因此主张“keep your distance”(保持距离)。而孔子对此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则是剪除自己身上的刺,以便于相处,也就是“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就是通过个人自觉的行动努力消除个人的外在殊异而进入普遍的平等社会关系中。如果人能达到自我规定的自觉自律,维护尊重人的原则,便达到了“仁”的境界,由此“仁”成为“我”和外界相处的道德原则,从而带有伦理道德评价与倾向。这一原则当然并非自然情感,它是在孝的基础上推恩 (推己及人)的结果,是人类自觉维护团体意识使然。为了“仁”有时甚至需要退缩或牺牲自我。
我们从《论语》中对伯夷、叔齐的评价,进一步分析孔子“仁”的基本价值。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 “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
子曰: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长》)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论语·季氏》)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从孔子的评价看,伯夷、叔齐的道德品质,罗列出来有不念旧恶、无怨、求仁得仁、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在孔子的信念中,能让是君子或贤者的美德,尤其是让国让天下的行为。所以孔子称赞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杨树达认为:“《论语》称至德者二,一赞泰伯,一赞文王,皆以其能让天下也。此孔子赞和平,非武力之义也。”[7]179《春秋谷梁传·定公元年》谓: “人之所以为人者,让也。”这一观念可以看作孔子观念的继承与表达。人和外界相处的原则在每个人退让,而不在于不停地向外获取。“让”与“克己复礼,为仁”精神也是一致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才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与佛教“普度众生”以及基督教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殊途同归之旨趣。
“仁”作为道德的要求,它的基本内涵与最初情感基础一定是对他人的爱,否则不会为他人而“克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大戴礼记·王言》篇说得很清楚:“是故仁者莫大于爱人”[7]298。董仲舒说得更清楚:“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仁者,爱人之名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7]297-298当然,仁者固然无所不爱,但还要有先后主次之分,所以“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急亲贤之为务,亲仁也”[7]17。
正是由于“仁”非本能,所以需要后天培养与规范。“仁”如何进行规范呢?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做到“仁”呢?“为仁由己”。(《论语·颜渊》)“己”为仁的动力,我 (己)是一个道德的发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我欲仁斯仁即至,仁表现为生活中的道德要求。主体首先需要有“仁”的主观意愿,有了这个意愿才有可能开始“仁”的炼成。而这个过程则需要遵循一定行为规范与限制。颜渊向孔子请教礼的具体内容与做法时,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这其实谈到了个体自己对外界的态度——约束自己,诚如《礼记·中庸》所谓“斋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8]787。孔子所谈“四不”内容即修身内容,而礼则是行为规范,相当于后世的养成教育,而目标则是“仁”。为了提炼纯粹的“仁”,孔子认为: “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孔子对学生特别强调自身修养,有时甚至将修身直接等同于“仁”。这其实是以外延代概念。在这种意义上,孔子才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久处约”,“长处乐”,乃是仁者气象,仁者会自守仁德,智者会做有利于自身德性发展的行为。在回答樊迟对于“仁”的疑问时,他就说: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这些内容都与修身相关,与子张问行相一致。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论语·卫灵公》)所以《荀子·修身》篇就说: “体恭敬而行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9]28人们经过系列的训练,“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一套有关“絜矩之道”礼的行为内化为自觉,那么也就可以逐渐由内而外化为“仁”了。所以在子张问仁时,孔子论“仁”则逐渐由内 (个人修养)转为外 (对外影响):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 “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也正是由于内在修养的完备,所以才可以施诸于外:“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论语·宪问》)结合《老子》“慈故能勇”,可以看出仁爱的力量才产生巨大勇气。《荀子·荣辱》篇的例子最有说服力:“乳彘触虎,乳狗不远游,不忘其亲也。”[9]55正是对他者 (双亲)的爱,才产生弥天大勇。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仁”是处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的理想境界。孔子设计了对自我加强内在修养的规范,由于这些规范强化为内在的意识,从而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一个消极层面,而积极层面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仁”是自我美德对外界的辐射,由此“仁”成为生命的目标,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是人作为人在理智状态下而非自然本能的行为结果,是为了他者牺牲自我的艰难选择,也是“仁”难能可贵之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仁”为重器,为远途,提举的人没有谁能胜任,行走的人很少到头的,因此“取数多者,仁也”[8]807,只能取数量多的算作仁。也就是说“仁”不仅是独善其身,而应该能兼济天下,也就是在这样的观念支持下,孔子才为阳货所说服: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 “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三、孔子对“仁”意义的提升
论及知识与“仁”的关系时,孔子认为:知识是才知,知人即为很重要的才能之一;“仁”是人伦,知识与伦理究竟是正比例还是反比例关系?在孔子看来,知识有助于加强“仁”。如:“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子夏在孔子学生中,属于文学才能类,对于后世继承传播六经具有很大贡献。而他所说的几方面,恰与《礼记·中庸》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8]789相一致,也就是说学习礼乐规范能够更好地行仁,“仁在其中”,亦即那些学习行为是“仁”的表现之一。人生在世,患之所在,非徒在智的欠缺,还在于仁的不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
如果一味关注仁而对知识不够重视,那么也就为人愚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论语·阳货》)当樊迟问仁问知时,子夏代替孔子将仁、知二者关系显示出来: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 “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淮南子·泰族训》说得更明白:
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谓仁者,爱人也;所谓知者,知人也。爱人则无虐刑矣;知人则无乱政矣。治由文理,则无悸谬之事矣;刑不侵滥,则无暴虐之行矣。上无烦乱之治,下无怨望之心,则百残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书》曰:“能哲且惠,黎民怀之。何忧讙兜,何迁有苗。”智伯有五过人之材,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不爱人也。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而身虏于秦者,不知贤也。故仁莫大于爱人,知莫大于知人。二者不立,虽察慧捷巧,劬禄疾力,不免于乱也。[10]1434
然而孔子并不将具体能力等同于“仁”,所以在孟武伯问及自己的学生哪一个“仁”时,孔子指出他们具体的才干,而否定了“仁”的定位: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 “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 “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
这里孔子对三位学生才干的评价与《论语·先进》篇《侍坐章》三人自我评定是一致的。在孔子观念中,能力与伦理价值不能等同,“仁”作为伦理价值是人作为类别的根本价值,当然超越工具理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孔子才提倡:“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有人认为做好本职工作就算是“仁”,而孔子则持反对意见:
子张问曰: “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恨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
孔子认为,令尹子文和陈文子,一个忠于职守,一个不与逆臣共事,但他们两人都还算不上仁。“忠”应该是份内之事,“清”是保持一己清高,而“仁”应该是超越本职工作的。
当子路、子贡质疑“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时,言下之意是说管仲对公子纠不够忠,那么一个不“忠”的人如何成为“仁”呢?这不仅代表了当时的意见,也是对当时道德的质疑。孔子对此很明确回答: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管仲在小节方面有欠缺,但在保存华夏,维护华夷之辩的名分方面有大贡献,后世徐干作了详细分析:
管仲背君事仇,奢而失礼,使桓公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功。仲尼称之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召忽伏节死难,人臣之美义也。仲尼比为匹夫匹妇之为谅矣。是故圣人贵才智之特能立事益于世矣。[7]353
恰如前文所论,“仁”是对他者的关爱,如果所做事情涉及对象有矛盾时,那么就看涉及对象的众寡,因为召忽不过忠于一姓一家,而管仲的功业则事关整个民族。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仁”的意义在社会事功前进行扩展的努力。也正是这个原因,孔子极力肯定对广大人民有益的事功: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孔子很明确自己的定位,所以不敢以圣人自我期许:“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而》)治学与教育是孔子一生的形迹所在,而后世却已在拔高其地位。《孟子·公孙丑上》指出这是孔子应对子贡的回答,并且指出恰是子贡他们意欲将孔子圣化:“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学不厌是加强自我,而教不倦是施予他人,也就如前所论证,只有将自己的爱施诸外界才是仁。
四、结论
孔子对于人的要求是逐步提升的。 “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8]784。也就是说,孝敬双亲是“仁”学体系的基础与起点,在此情感基础上推及他人,推衍出更广泛的爱。仁是人之为人的根据,它是基于保全类的考虑而生发出来的,为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理想原则。在孔子看来,一方面节制一己私欲,谦让他者;一方面将爱施予他人。 《吕氏春秋·爱类》说:“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6]202这是这种对大类的爱使得人能超越小我,实现“仁”德。“仁”不是先天的情感,而且人类理智的选择。为了让人达于“仁”,孔子设计了很多规范进行人格塑造,通过日常行为规范训练从而产生收敛个性,包容他人,这是较低的层次。克己复礼直接影响到国民的性格,不张扬个性,为集体牺牲个性。更高的层次则是帮助他人成功。孔子在“仁”意义上,否认才能等同于仁,同时认为“仁”超越本职工作,它不是对一姓一家的忠诚,而是看能否救助更多的人,救助的人越多,则“仁”的价值也就彰显。正如《中庸》所说:“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8]780。从整个结构系统来,孔子的“仁”学可概括为“孝—忠—仁—圣”这样一个从个体向外推衍的模式,孝悌是家庭范围,而忠恕则是事业层面,而仁与圣则是对社会影响层面。由此也可以看出,孔子积极入世的态度恰是“仁”学思想的实践。
注释:
①阮元.揅经室集[M].《揅经室集一集》卷九“论语论仁论”,邓经元点校,中华书局,1993:206。而侯外庐认为“仁”不但不见于西周,而且不见于孔子以前的书中。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56:614。此处取阮元说。
②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这一点十年后为翁方纲所批评,他认为象《三礼》、《尔雅》等典制名物固然可以考据得知,但是《周易》卦爻彖象,乘承比应之义、《春秋》比事属辞之旨以及《尚书》、《诗》、《论语》、《孟子》、《孝经》等内容则不能用考据方法探求。 《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复初斋文集》卷七《理说驳戴震作》附录。钱穆先生也认为“《论语》‘仁’字只能直接以义理求之,而阮元用考据方法来写《论语论仁篇》,到底得不到结论”。见钱穆.孔子与论语[M].九州出版社,2011:106.
③阮元曾经系统研究孔子的“仁”,并得出践行论。阮元:《揅经室集》上,《揅经室集一集》卷九“论语论仁论”。匡亚明认为,仁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根本,从最通常的“仁者爱人”到“克己复礼为仁”对道德准则的遵从,最后提升为“仁者人也”这一人本哲学核心概念。“在《国语》中仁凡二十四见,基本意义是爱人,《左传》中仁凡三十三见,除爱人之外,其他几种德行也被称作仁,然而这些材料中反映的有关仁的思想,都是零散的,无系统的,思想内涵也是比较肤浅的,孔子在形成自己的思想时,抓住当时在意识形态中已经出现的仁的观念,明确它,充实它,提高它,使它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深的人本哲学。”(匡亚明.孔子评传 [M].齐鲁书社,1985:181-183)。徐复观认为:“在孔子,仁是功夫,是一切学问行为的总动力,又是本体,是一切学问行为的总归宿。”以蔡尚思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在于“礼”,见蔡尚思.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论[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另外如上引金景芳也持此观点。
④黄怀信认为此句“仁”为“人”之误。参见黄怀信.《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J].齐鲁学刊,2007(1):5。但黄氏讨论仁其实没有在一个层次上进行,而是将其分为“仁德”、“仁人”、“仁行”、“仁声”,这并不能理清仁的体系。
[1]武树臣.寻找最初的“仁”——对先秦“仁”观念形成过程的文化考察[J].中外法学,2014(1):139.
[2]谢阳举.“仁”的起源探本 [J].管子学刊,2001(1):46.
[3][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王献唐.山东古国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3:219.
[5]金景芳.论孔子仁说及其相关问题[J].中国哲学史,1996(1-2).
[6][秦]吕不韦.吕氏春秋·淮南子[M].杨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9:15.
[7]杨树达.论语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清]王先谦.荀子集解 [M].沈啸寰,王兴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