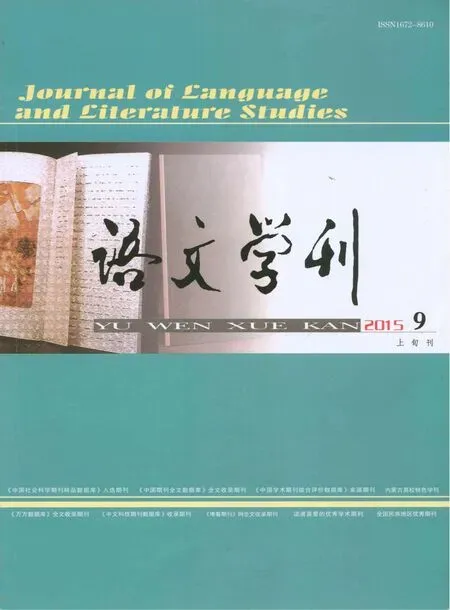行吟的诗魂:论西尔维娅·普拉斯诗歌对哥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
○赵蔚榕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西尔维娅·普拉斯的诗歌自出版至今一直受到众多读者的追捧,也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普拉斯将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包括自杀经历和她与英国诗人泰德·休斯的情感纠葛等融入诗歌创作中,用诗歌表达强烈的个人情感与人生体验。同时,普拉斯也关注社会、历史、政治问题,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书写被压抑的女性自我。在她的诗歌中,不可忽视的是以女性自白话语描绘的在黑暗、紧张、恐怖的世界中痛苦挣扎的社会边缘人。普拉斯的哥特式书写体现了诗歌强烈的暗恐性(the Uncanny)。继承了传统哥特文学的特点,在哥特式自白中,普拉斯用其独特的诗歌艺术表达了被压抑的自我,激发他者的反抗。
一、西尔维娅·普拉斯的创作与哥特文学传统
哥特文学起源于18 世纪的英国,其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惊险悬疑,常以幽森的古堡、神秘的荒野为背景,借助凶杀、复仇、幽灵、疯癫等一系列哥特元素,营造恐怖气氛,带给读者以审美体验。根植于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语境中,哥特文学通过描写暴力与恐怖,揭露社会政治、文化意识等问题。从最初因通俗文学而畅销,到之后被大批作家盲目追随,而导致哥特作品的语言粗糙、情节固化,哥特文学曾一度不被批评界认可。随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对哥特风格的借鉴,到维多利亚时期哥特文学走过低潮,产生了《呼啸山庄》《白衣女人》等名篇。自19 世纪之后,哥特文学在新大陆的美国发芽,詹姆斯·库柏、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威廉·福克纳等一大批作家先后创作了一系列经典的哥特文学。
虽然普拉斯的诗才在她8 岁时就已显现,她也靠写作赚得不菲稿费,但是其诗歌在英美诗界并未引起较大波澜。直至在她自杀后,由泰德·休斯整理出版她的诗集《爱丽尔》问世,普拉斯的诗歌才在英美诗界轰动一时,并受到了女权主义者的追捧。早期学者将普拉斯归为自白派诗人,事实上普拉斯的早期诗歌的确受到以罗伯特·洛厄尔为代表的自白派诗歌的影响,她在诗歌中真实地书写生活以宣泄敏感的个人情感。后来,她借鉴了休斯诗歌中的神秘主义风格,在诗歌创作中融入超现实主义元素,塑造了众多神话原型。“(埃伦·莫尔斯)将她的创作实践视为以‘幻想超越现实,怪异战胜寻常,超自然取代自然’的女性哥特主义传统的延续。”[1]99普拉斯的哥特式写作方式与同时代诗人的影响不无关系,同时,普拉斯也受前辈诗人及国外诗歌的影响。克里斯蒂娜·布里茨拉基丝对比了普拉斯诗歌与爱伦坡、波德莱尔等人作品中哥特元素,认为普拉斯借鉴了小说、诗歌、电影文学中的哥特元素,为其诗歌创作带来了戏剧化的特点。[2]129抛弃诗歌形式上的束缚,普拉斯在内容上寻求创新。她利用其独特的女性感悟,用恐怖元素编织情节,以自白的形式,强有力地为被压迫的他者呼吁。
二、西尔维娅·普拉斯诗歌中的哥特元素
在传统哥特文学中,人物形象多为邪恶的暴君、骇人的幽灵、不幸的女性等。作家通过塑造对柔弱形象摧毁的邪恶形象,形成富有张力的恐怖情节。批评家将哥特文学分为男性哥特文学与女性哥特文学。相比于男性哥特文学中着重描写的男性主人公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具体的血腥、死亡情节,女性哥特往往围绕女性自身经历展开,聚焦于女性在与社会、家庭中的男性暴力抗争中的恐惧与焦虑。
普拉斯的诗歌明显继承了女性哥特文学传统,书写女性自我在家庭中男性暴力阴影下的抗争,同时,普拉斯在其大屠杀诗歌中也继承了男性哥特文学宏大的历史叙事。在普拉斯诗歌中,恐怖的主体往往不是邪恶的魔鬼,而是家庭生活中的男性强权者,和社会政治中的屠杀者。在“爹爹”中,父亲是“吸血鬼”,是纳粹军官,是残暴的男性形象。普拉斯以第一人称的“我”向父亲审问,使父亲沉默、失语,同时建构了女性的主体地位。“你不行了,再也/不行了”[3]269“爹爹,我必须杀了你”[3]269。在战争中,普拉斯将自己看作犹太人,痛斥带给犹太人苦难的纳粹军官。在这里,父亲成为父权社会的一个符号,被置于社会、家庭边缘的女性通过自白话语跨越了符号的边缘。
为保持其神秘性,哥特文学常在时间上选取遥远的中世纪、超现实的时空,地点选取幽闭的城堡、荒凉的野外等。在传统哥特文学中,社会公共场所由男性主宰,属于女性的场所是家庭。在诗歌创作中,普拉斯常常借助空间意象,表现身份危机。在“巨像”中,女儿怀念亡父,却无法疏通巨像喉咙的泥污,与巨像交流。为了躲避父亲的猥琐话语与喉间噪声,女儿藏进了巨像的左耳,成为“嫁给了阴影”[3]148的巨像清扫者。女性因而成为父权压制下失语的他者。在“玛丽之歌”中,集中营的焚尸炉“熔化异教徒的油脂,/逐走犹太人”[3]316。普拉斯还原了大屠杀的历史,表现纳粹暴力下陷入社会身份危机的犹太人。
死亡与复仇是哥特文学永恒的主题,在黑暗与死亡的阴霾下,恐怖应运而生。普拉斯一生迷恋死亡,认为“死亡/是一种艺术”[3]301。在“拉撒路夫人”一诗中,普拉斯完美地诠释死亡,使拉撒路夫人成为跨越生死边界的幽灵。身体被肢解,面目全非,而“人们嚼着花生/挤进来看/他们扒开我的手脚——/好一场脱衣舞”[3]300。虽然女性成为男性凝视下的他者,但是她的肉体可以回归,“我披着红发/从灰烬中复活/像吃空气一样吃人”[3]302。拉撒路夫人的复仇是对男性逻各斯的反抗,对不平等的两性政治的挑战。吉娜·威斯克认为死亡是女体的再生,普拉斯将女性的家庭角色陌生化,将女性从家庭角色中分离。[4]115普拉斯在诗歌创作中塑造了哥特式邪恶人物,借助空间意象,通过死亡与复仇的叙事,展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受压迫的他者形象,揭露现实,为他者言说。
三、创伤与暗恐:他者身份的建立
在普拉斯一生中,家庭和社会都给她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少年时代父亲病逝,紧张的母女关系另她内心异常孤寂、焦虑,与休斯婚后生活不幸更是另她一度崩溃。同时,身处战后社会动荡的年代,深刻的家庭和社会创伤折磨着敏感的诗人,诗歌成为普拉斯言说女性自我的途径。然而普拉斯又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诗人,她“强调创作应对历史事件作出严肃的回应和书写。”[5]143哥特文学根植于特点的历史时代,其暴力、恐怖往往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在内容上追求创新的普拉斯正是借鉴了哥特文学强烈的感染力,以自白的形式书写创伤。通过女性独白,借助哥特元素,她审视黑暗的社会现实,回视凝视的主体。
“文明的基础是压抑,但压抑会造成精神的焦虑和不满。哥特小说中的鬼魂、噩梦、幽灵,其实都是这种焦虑和不满的外化。”[6]102弗洛伊德在对哥特文学的研究中提出了“暗恐(the Uncanny)”的概念,认为暗恐是受压抑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现象。[7]148在诗歌中,普拉斯塑造了许多他者形象,有在家庭生活中被父权压迫的女儿、妻子,还有在社会中被凝视的女性,战争中的受害者等等。这些他者在普拉斯营造的恐怖的哥特氛围中,他们的意识开始觉醒。恐怖的受害、死亡威胁激发他们反抗、逃离禁锢自身的囚笼,表达内心的声音。如“面部整容”中女性,将皮肤“像纸一样容易剥离”衰老的自己“封存于某个化验室的罐子。/任她在那里死去”,而“我是自己的母亲,我裹着纱布醒来,/粉红光滑如婴儿”[3]183。在强烈的暗恐感受中,他者接受了手术,建立了新的自我。
普拉斯受前人诗人的影响,形成了自白式、神秘的诗歌艺术,然而她的诗歌关注的不是自白式呐喊,不是无情地揭露,也不是恐怖本身,而是对于时代问题的关注,对家庭爱与伤害的思考,对个人自我意识的表达。通过一系列的哥特书写,普拉斯在诗歌中营造了焦虑、恐怖的氛围,表达了自身的精神焦虑。作为有深刻的性别意识和政治意识的女诗人,普拉斯通过对传统哥特文学的借鉴与改写,达到超越,向禁锢女性和战争受害者的父权社会和残暴的社会政治表达无法言说的自我,给予他者以言说的权利,向读者展示了一条探讨创伤经历、追求话语权利、建构主体身份的有效途径。
[1]杨国静.西尔维娅·普拉斯诗歌中的暗恐[J].国外文学,2014(1).
[2]Britzolakis,Christina. 1999. Sylvia Plath and the Theatre of Mourning[M].Oxford:Oxford UP.
[3]西尔维娅·普拉斯.西尔维娅·普拉斯诗全集——未来是一只灰色的海鸥[M]. 冯冬,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Wisker,Gina. 2004. Viciousness in the Kitchen:Sylvia Plath's Gothic[J].Gothic Studies. vol. 6,No.1.
[5]朱新福.普拉斯作品张的大屠杀描写及其政治历史意蕴[J].外国文学研究,2013(3).
[6]陈榕.哥特小说[J].外国文学,2012(4).
[7]Freud,Sigmund. 2003. The Uncanny. Trans. David Mclintock[M].New York:Pengu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