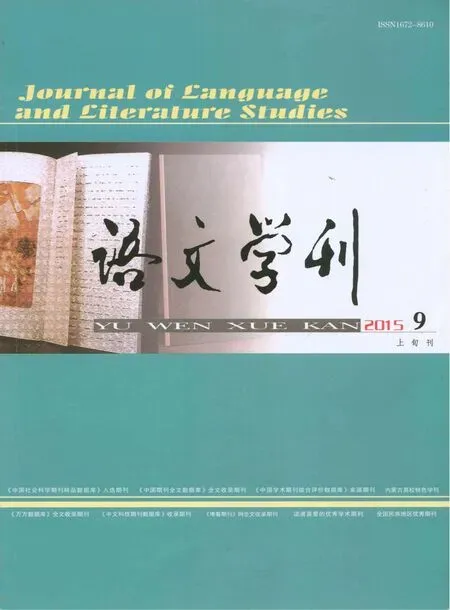胡适眼中的晚清与民初文学——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 王铎
(西南交通大学 艺术与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胡适眼中的晚清与民初文学——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 王铎
(西南交通大学 艺术与传播学院,四川成都611756)
[摘要]胡适于1922年所著《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论述了1872年~1922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其中许多观点颇有独到见地,但也不乏检讨和修正之处。文章以细读的方法对《五十年》进行评析,对其中错讹之处加以检讨和反思。
[关键词]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学史观
1922年3月,为纪念上海《申报》创办五十周年,胡适作了长文《中国五十年来之文学》,此文一出,即在当时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五十年”指的是1872年至1922年,时间的划分并无特殊含义。胡适在前九节论述了晚清、民初的文坛概况,最后一节写到新文学,对“这五六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进行其存在合理性和演变必然性的论证,得出新文学势不可挡,必定取代旧文学的结论。
此文为新文学的根基起到巩固作用,亦为后世的晚清民初文学研究打下基石。《五十年》作为评述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之作和晚清民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可谓意义重大。但,我们不能忘记胡适这篇文学简史是他戴着有色眼镜书写的——至少,此论文有两种性质:一曰学术性,二曰功利性。
《五十年》体现了胡适的“双线文学观”。所谓“双线”,是指胡适对中国文学分类的结果,共分作两类,一类是“活文学”,一类是“死文学”。活文学即从民间兴起的、生动活泼、语言浅易近于白话的“平民文学”,死文学即为古代统治阶级服务的、正统僵硬的“贵族文学”。这“双线文学”古已有之,数千年来,此两条线索并行不悖地向前推进,其结果是,前者衰落灭亡,后者兴起壮大。1872年以来到现今的文学发展史,亦是如此:一边是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的少数人的“贵族文学”、“死文学”或“半死文学”,另一边是由北方平话小说和南方讽刺小说构成的多数人的“活文学”。
在胡适看来,只有白话文学才可以称得上活文学。胡适以科学方法,以“白话文学正统论”重构中国文学史,也重新发现了白话文学的价值,此为胡适之历史功绩。为了重建文学正统而刻意抹杀掉数千年的古文传统,则使理论本身摇摇欲坠。胡适认为,只有白话文学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学主流,却不知中国的文学流变一直处于官方和民间的交互之中。显然,胡适的二元对立模式是站不住脚的。以胡适观点推论,既然白话已为主流,何必文学革命——例如,之所以才有“小说界革命”和“新小说”,恰恰是因为近代中国的白话小说处于边缘地位。
胡适在《五十年》中,尽力发掘白话文学的优点,给予高度评价和褒扬。相反,对于古文作家和文学作品,胡适尽力忽视或排斥——即便胡适看到了近期四派古文的成绩,却只是在一番赞扬后得出即使这些古文作的优秀,但免不了走向死亡的结论。与“白话文学正统论”相对应,胡适赞赏平民文学,建立了“平民文学正统论”。而《五十年》中所述的民间文学只有“白话小说”一项。作为胡适所构建的“正统文学在民间”的理论体系,难免站不住脚。
何为平民文学?以《五十年》中的例子看,是《老残游记》、《恨海》等一些白话小说,“平民文学”——该词的发明者周作人——原意指可以表达平民之真情实感,体现普遍情感与事实,人人平等之观念的文学,并非简单的指向通俗小说。但是,“平民文学”这一概念在胡适这里发生了置换:民间文学,这五十年来的优秀的白话小说即为代表。胡适扭曲了或者说误会了“平民文学”的概念,这是非常不妥的。
那么,胡适所谓的“白话”到底何指呢?他把“白话”的定义范围放得很大,就算是“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1]171,也可算作白话文学,这样便可以称得上“活文学”的称号了。但是他自己也没有确切地把“活”与“死”区分开来:《<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胡将《史记》里的大部分篇章归入活文学,而在1918年7月写给朱经农的信中,胡将《史记》归入了死文学。这样的矛盾,能不能算作是作者自己在理论构建上的漏洞呢?且,文学可真有“死”与“活”之分?以今观古,胡适不能把“一时代之文学”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既然胡适承认“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却要为所谓的“民间文学”造反正名,岂不自相矛盾?
贯穿《五十年》全文的是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思想。胡适认为,两千年中国文学从未有过退步或停滞不前的状态,而是始终发展,不断进步,从古文到文学革命,期间的这五十年的变迁自然成为从古文到白话的过渡历史。因此,胡适对这五十年作出了新旧文学过渡史的定位。以“过渡史”定位这段文学历史,的确抓住了其基本特征,胡适认为这五十年只能分作三个部分(不求变通的古文的“末路史”、变革中的古文的“失败史”、生机勃勃的白话文的“进化史”),却使得这段过渡史显得颇为孤寂。
既然胡适已经看到这五十年间的古文并非因循守旧,但胡适不认为这是古文的“进化”,而是古文的“挣扎”。何为历史之真实?至少,晚晴和民国的这段文学史的解读方法不止一种,在王德威看来,这段历史热闹纷呈,各种新旧矛盾和文学资源化为一体。这样的理论框架必然要求胡适不得埋没掉许多古文大家和优秀的文言作品,具有无限丰富可能性的文学史料被单因论取代,种种文学作品众声喧哗的丰富性被进化论掩盖。否则便不能够自圆其说了。 同时,胡适认为对这段时期的白话文学的使用仍旧是无意和随便的,却在文中对梁启超等前辈们所作的努力——“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避而少谈,胡适声称直到文学革命,才有人“有意的主张白话”,这样的论述便是对前辈们的不负责任了。
再者,值得注意的是,在胡适声称的这段“过渡史”当中,胡对鸳鸯蝴蝶派亦无只字片语的提及。从胡适所列举的《恨海》《广陵潮》《儿女英雄传》等白话文代表作,和他所列举的作家吴趼人、李涵秋等作家来看,似乎鸳鸯蝴蝶派更有理由承接白话文学的传统(与新文学相较而言——然而,鸳鸯蝴蝶派却是新文学的劲敌),这一点,是否可也算作胡适在理论构建过程中的漏洞呢? 到现在,文言和白话、死文学和活文学、平民文学和贵族文学等种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所造成的影响,依然体现在文学史教科书里:比如,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角度、研究方法难以融合;诸多现当代文学大家的古体诗歌难以进入文学史等等。我们不能不为古今文学史的断裂感到悲哀和遗憾。
我们不应该忘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的开创之功,更不应该遗忘摇旗呐喊、开一代风气的胡适,但若只是简单否认胡适的历史功绩,或者只是将其作为偶像顶礼膜拜,皆不可取。如今,距离文学革命已近百年,当年一些反对者们的声音却在近百年后掷地有声,胡先骕说:“中国文言与白话之别,非古今之别,而雅俗之别也,夫雅俗之辨,何国文字蔑有……即在英法德诸国,文人学士文章,岂贩夫走卒之口语可比耶?”[2]25文学毕竟不是日常里的“大白话”。也许,文学史可以这样被解释:中国文学的传承并未断裂,古今传承,实为一脉。
【 参 考 文 献 】
[1]胡适.胡适说文学变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2]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C]//申报五十年纪念册.
[3]胡适.胡适文集(3)[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胡全章.白话文运动:既有晚清,何必“五四”?[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5)09-0056-02
[作者简介]王铎,男,陕西汉中人,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