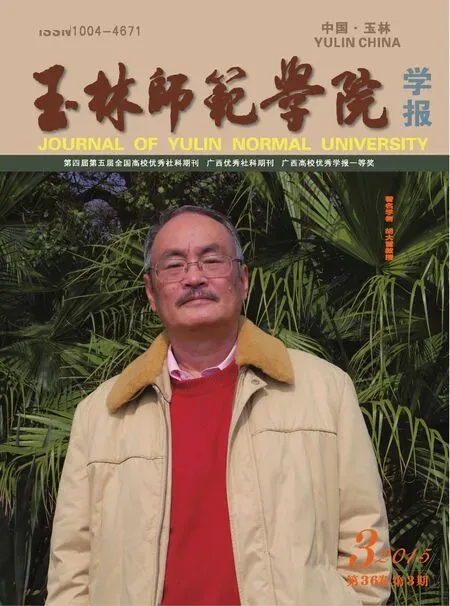六朝韵律建构与诗的文化自觉
——兼论对当代诗歌韵律建构的启示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六朝韵律建构与诗的文化自觉
——兼论对当代诗歌韵律建构的启示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人类生活之初,诗追随音乐、舞蹈的韵律并与其共同构成人类的艺术活动,诗作为“以声为用”的一份子为文学奠立了在文明社会中的地位;自汉代起,以语言文字的“言志”、“缘情”高度凝练、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虽然诗以其韵律保持着与音乐的关系,但已使文学脱离附庸于音乐、舞蹈的地位而“以义为用”,成为独立的文化门类。其三,“以义为用”的诗寻求韵律之路,自汉魏至“永明体”、至唐初,经历数百年,格律诗定型,完成了以严格的韵律完善自身,以韵律这一与其他文学样式不同的形式特征而独立。其四,自中唐开始历经宋、元、明、清,不断有反韵律倾向,乃至颠覆韵律,白话诗出现,旧诗的韵律系统被打破,诗处在要不要韵律、怎样进行韵律建构的重要关口,新时代下诗的韵律重新建构,也是文学将要接受的磨难或磨练之一。
以声为用;以义为用;韵律;白话诗
诗的文化自觉,是指诗对于文化发展的某种责任与担当;古代社会论诗,绝不就事论事、就诗论诗,而往往是联系诗的文化身份而论的,如《毛诗序》曰: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
从《毛诗序》所说可知,诗的文化身份有二:一是由诗的产生而促发其他艺术形式如歌、舞的产生,三者共同构成文化形态;二是由诗为主导的文化形态发生社会作用而具有应用价值。上述二者的连接点为“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诗由此而促发歌、舞的产生;诗也由此发挥社会作用。这“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诗的韵律。因此我们说,韵律与诗的文化自觉关系极大:一是诗的“以声为用”,诗的自身韵律建构,诗从自身情感抒发的需要出发,不断地探求就是不断地破坏旧有形式包括破坏旧有韵律形式的过程。建构与破坏及其相互间的纠缠,使得诗始终如一对韵律有着某种焦虑或亢奋,诗就在这种焦虑或亢奋中继续前行。二是诗怎样把生命的律动、节奏结合进入文化之中,其“以声为用”——韵律建构怎样带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以下探讨这两个问题
一、诗追随韵律而兴起与“以声为用”
我们先来探讨诗的产生。
第一,诗与音乐、舞蹈三位一体。音乐、舞蹈,二者都是以身体为语言、以声音为语言作“心智交流”。内心有所需求,肢体响应有所行动,发出声音,行动、声音的节奏的第一个模拟对象就是人自身内部的律动、节奏,如心跳、步伐、连续的发声等。音乐、舞蹈的节奏乃至韵律最早出自人自身。《吕氏春秋•古乐》讲音乐、舞蹈、诗的三位一体: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2]
当我们讲三位一体时,诗显然是最后起者,诗是追随音乐、舞蹈的节奏与韵律而形成的。音乐、舞蹈是在人的有节奏、韵律意味的劳动、发声相配合下的生成的,诗追随音乐、舞蹈而生成,当然更是在人的有节奏、韵律意味的动作、发声相配合下生成的。
第二,歌是伴随劳动、娱乐、仪式等身体的肢体行动节奏、韵律产生。如:
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3]
歌与节奏的关系,古书上多有记载,如:歌与“舂”(舂杵),《汉书•外戚传》:
戚夫人舂且歌曰:“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幕,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4]
歌(讴)与“筑”(夯土),《左传•宣公二年》:
宋城,华元为植,巡功。城者讴曰:“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5]
歌与“挽”(走步),崔豹《古今注》曰:
《薤露》《蒿里》,泣丧歌也。本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伤之,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于蒿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谓之挽歌。[6]
歌与“澣(浣)”,《乐府诗集》卷六十:
《风俗通》曰:“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乐作,所赁澣妇自言知音,因援琴抚弦而歌。问之,乃其故妻,还为夫妇也。”[7]
第三,歌的音乐是经过节制的。刘师培从另一个角度谈诗歌的后起,其云:
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观《列子》所载,有尧时谣,孟子之告齐王,首引夏谣,而《韩非子》《六反篇》或引古谣,或引先圣谣,足徵谣谚之作先于诗歌。[8]
他称是先有谣谚后有诗歌的,前者是口说,后者是歌唱;那么,这个歌唱是经过“声成文,谓之音”的阶段的。刘永济曰:
郑玄《诗谱序》:“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大庭轩辕,逮于高辛,其时有亡载籍,亦蔑云焉。”孔颖达《正义》曰:“大庭,神农之别号,大庭轩辕疑其有诗者。大庭以还,渐有乐器。乐器之音,逐人为辞。则是为诗之渐,故疑有之也。”又曰:“然则上古之时,徒有讴歌吟呼。纵令士鼓苇蘥,必无文字雅颂之声。故伏羲作瑟,女娲笙簧及蒉桴士鼓,必不因诗咏。”如此则时虽有乐,容或无诗。郑疑大庭有诗者,正据后世渐文,故疑有尔,未必以士鼓苇蘥遂为有诗。若然,《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叹。声成文,谓之音。”是由诗乃为乐者。此据后代之诗,因诗为乐。其上古之乐,必不如此。郑说既疑大庭有诗,则书契之前已有诗矣。[9]
“书契之前已有诗”者,为“讴歌吟呼”;“乐器之音,逐人为辞”者,为诗,即所谓诗之合乐。诗之诞生,由乐器的节制,其韵律应该是较为固定的;而歌的韵律,则有较多的随意性,然亦延续。
第四,一来当我们说歌或诗的起源有追随音乐、舞蹈的节奏与韵律而生成时,那么讨论此三者表达的意义,就应该是音乐、舞蹈的意义在前,而歌或诗的意义在后。二来“乐”是明确经过节制的。因此,诗一开始“以声为用”。历史上确实是这样,如著名的季札观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以下都是为季札“歌”而季札称“美哉”等,[10]杜预《注》曰:“美其声。”孔颖达《正义》曰:“先儒以为季札所言,观其诗辞而知,故杜显而异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声也。”[11]称季札是“美其声”,是以“听声”为主的,当然也要“听歌辞”,即刘勰所说“季札观乐,不直听声而已”[12]。在这种“以声为用”的阶段,诗依附于音乐,也就是诗作为文体来说并未独立;而乐是独立的、自主的,所以季札是“美其声”。其他如《荀子•乐论》“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13],《周礼•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14]应该都是就“声”而言的。非但诗作为文体来说并未独立,而且诗依附于“乐”,其韵律也是依附于“乐”的。
二、诗的文体独立与韵律
当我们说“文学的自觉”时,往往提到曹丕的时代,即文学就是文学,“不必寓教训”[15];当说音乐、舞蹈、诗三位一体,诗是依附于前二者时,诗作为文体并未独立。《毛诗序》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的情况,只有在文体独立后才能出现,而确实在《毛诗序》的时代,诗正在脱离“乐”而实现文体独立,这就是诗脱离“乐”的进程。
其表现之一,即由“以声为用”到“以义为用”。春秋时代外交流行赋诗言志,诸侯士大夫常在各种社交场合,请乐工或自己朗诵、配乐吟唱《诗经》,借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主要是“以义为用”,或不用“声”,即便是用“声”,“声”也是配角。到战国时代著述引诗,《诗经》被引之诗已脱离“声”,完全是“以义为用”;著述引诗,完全是供阅读的诗。
当诗“以义为用”时,诗就在观念走出了独立的第一步。汉时诸类文章中所述的“歌”,完全是供阅读的诗,就完全是“以义为用”的,如杨恽曰:
家本秦也,能为秦声。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卬,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16]
本是“拊缶而呼乌乌”的“歌”,写在书中则称为“诗”,因为读者读到的是文字,而没有提到歌曲。又如“不歌而诵”的赋,其中之诗,也是只供“诵”而不入乐的。班固《两都赋》载:
主人之辞未终,西都宾矍然失容,逡巡降阶,惵然意下,捧手欲辞。主人曰:复位。今将子以五篇之诗。宾既卒业,乃称曰:美哉乎斯诗!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学,盖乃遭遇乎斯时也。小子狂简,不知所裁,既闻正道,请终身而诵之。”(诗略)[17]
这样的作品才可以称“诵之”。而到汉末,赋末所系有号称“歌”,也是不入乐的,如赵壹《刺世疾邪赋》的末尾: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脏倚门边。”鲁生闻此辞,系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18]
又如先作诗,再配乐,就是诗的“以义为用”才予以入乐的。具体的例子如: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9]
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20]
(汉武帝)为作诗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21]
这些都是先有独立的诗,后再配乐。
以后的乐府诗作,也有不依乐曲而作者,如刘勰《文心雕龙•乐府》所说“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22]
诗歌脱离音乐而独立,但诗歌还是有韵律的,如陆机《文赋》所云:
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23]
所谓“音韵天成”阶段,此即沈约《谢灵运传论》所说: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而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24]
称优秀诗歌“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刘勰《文心雕龙•声律》:
又诗人综韵,率多清切,《楚辞》辞楚,故讹韵实繁。及张华论韵,谓士衡多楚,《文赋》亦称取足不易,可谓衔灵均之声馀,失黄钟之正响也。凡切韵之动,势若转圜;讹音之作,甚于枘方。免乎枘方,则无大过矣。练才洞鉴,剖字钻响,识疏阔略,随音所遇,若长风之过籁,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宫右徵,以节其步,声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忽哉![25]
也谈到诗歌声律的运用。
诗歌的这些声律的运用,非取自音乐,钟嵘《诗品序》即说:
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26]
他认为乐府诗要以乐曲的韵律,诗“不被管弦”,不用乐曲的韵律;虽然这是从反对诗歌的人工音韵而言,但说出了一个事实。
三、诗完善自身的历程:人为格律的制定
格律诗至唐代定型,但经过了整个六朝的奠定基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格律原理、原则的确立。诗在脱离乐曲后,诗人与诗歌理论家认为,是仅有自然韵律是不够的,诗应该制定出自己的韵律。陆机《文赋》所说的“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成为制定韵律的基本点,这个理论表述表明其韵律建构的路径是:第一,诗的韵律是由各种(若五色)“音声”组成的,非单一化的;第二,所谓“迭代”,其韵律是循环往复的。注意到陆机是当时有名的诗人,《诗品》称其曰:
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气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叹其大才,信矣![27]
他的创作对对其提出理论应该有重大影响,所谓“举体华美”、“咀嚼英华,厌饫膏泽”、“大才”就含有其追求韵律是意味,而“尚规矩”则有指定规则的意味。魏晋南北朝诗人在韵律方面的努力,不脱上述二者。
其次,美好传说与接收外来影响。在魏晋时多有对韵律美好的吟诵的企羡的故事流传,如《异苑》载:
陈思王曹植字子建,尝登鱼山,临东阿,忽闻岩岫有诵经声,清通深亮,连谷流响,肃然有灵气,不觉敛衽祗敬,便有终焉之志,即效而则之。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一云:陈思王游山,忽闻空里诵经声,清远遒亮,解音者则而写之,为神仙声。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28]
又如《世说新语•言语》载“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29]于是就有称说韵律是接受外来的影响、效仿“诵经声”而形成的。假如说曹植时代对诵经声的“效而则之”及“道士效之,作步虚声也”只是传说而已,那么,《高僧传•释僧辩传》所载就是历史的真实:
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维摩一契,同声发而觉,即起至佛堂中,还如梦中法,更咏古维摩一契,便觉声韵流好,有工恒日。明旦即集京师善声沙门龙光、普知、新安、道兴、多宝、慧忍、天保、超胜及僧辩等,集第作声。[30]
南齐竟陵王萧子良就因为梦中的梵音吟咏,便召集审音定声,想让这种“声韵流好”有法可依。本来,佛法由音声而宣说,故称“声教”,所谓“声教开合,化道可知”,[31]即教由声说,故云声教。对“声韵流好”的企羡进化为有法可依的审音定声。于是或有认为,从佛教转读梵文拼音,而到沈约四声说的创立,是合乎逻辑的过程。。陈寅恪《四声三问》,则认为平、上、去“实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归纳得来。
其三,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天生的对声律有着特殊的感觉,对韵律有天赋,如范晔就自称“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32]钟嵘所称声律创始那些人,“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33],那是一批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的人。
其四,诗人与理论家有意识的总结规律,制定创作规则,团体的、集体的力量。“永明体”的构成:
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34]
“以气类相推毂”者以沈约为著,他提倡声律,他官居显贵,是文坛实际的核心人物,他每每奖掖诗人,这既是做文坛领袖为推进文坛繁荣所应尽的职责,又是他有意识地推行“永明体”的努力。他说谢朓的诗是“二百年来无此诗也”,[35]他对何逊说:“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36]刘显“尝为《上朝诗》,沈约见而美之,命工书人题之于郊居宅壁”,[37]谢举“尝赠沈约诗,为约称赏”,[38]“沈约每见(王)筠文咨磋”,称之“晚来名家无先筠者”,称之“后来独步”,[39]何思澄“为《游庐山》,沈约见之,大相称赏,自以为弗逮。约郊居宅新构阁斋,因命工书人题此诗于壁”,[40]“沈约尝见(吴)均文,颇相称赏”,[41]刘孺“恒与游宴赋诗,大为(沈)约所嗟赏”,[42]王籍,“尝于沈约坐赋得《咏烛》,甚为约赏”,[43]这些人都可能成为声律说的响应者。又如沈约对刘勰的赏识,刘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取读,大重之,谓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44]这样,《文心雕龙》才推赏开来。而《文心雕龙》有《声律》曰:
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迭韵杂句而必睽;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飏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45]
其六,学术讨论的影响。古代音韵之学,孙炎《尔雅音义》创立反切;李登《声类》以宫、商、角、徵、羽分韵,为日后“永明体”诗的四声运用与律诗奠立了基础。而在“永明体”后与律诗定格前,多有韵律的学术讨论。如关于声律对偶的著作大量出现,日本和尚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序》称:“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缃帙满车”;又称自己“阅诸家格式等,勘彼同异,卷轴虽多,要枢则少,名异义同,繁秽尤甚。余癖难疗,即事刀笔,削其重复,存其单号,总有一十五种类:谓《声谱》,《调声》,《八种韵》,《四声论》,《十七势》,《十四例》,《六义》,《十体》,《八阶》,《六志》,《二十九种对》,《文三十种病累》,《十种疾》,《论文意》,《论对属》等是也。”[46]又一大型类书成批刊行,虞世南《北堂书钞》、欧阳询《艺文类聚》、徐坚《初学记》等,载有大量的韵律与对仗的例子。
其七,在争论中生成,钟嵘《诗品序》批评声律论说:
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贰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尝试言之:古曰诗颂,皆被之金竹,故非调五音,无以谐会。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为韵之首。故三祖之词,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义也,与世之言宫商异矣。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邪?[47]
又称其“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48]陆厥也有书给沈约讨韵音律,对其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称其“近于诬乎”,结论就是不必追求统一,所谓“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49]沈约回答,称为什么前人对韵律不那么关心时,有“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立言之所急也”云云,[50]于是又回到当诗脱离“以声为用”回到“以义为用”,回到诗的独立所产生的影响力。
其八,社会风气。刘师培论“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也”时曰:
自晋代人士均擅清言,用是言语、文章虽分为二途,而口出成章,悉饶词藻。晋、宋之际,宗炳之伦,承其流风,兼以施以讲学。宋则谢灵运、瞻之属,并以才辩辞义相高,王惠精言清理。齐承宋绪,华辩益昌。《齐书》称张绪言精理奥,见宗一时,吐纳风流,听者皆忘饥疲;又称周颙音辞辨丽,辞韵如流,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辨;又谓张融言辞辩捷,周颙弥为清绮,刘绘音采不赡,丽雅有风则。迄于梁代,世主尤崇讲学,国学诸生,惟以辨论儒玄为务,或发题申难,往复循环,具详《南史》各传。用是讲论之词,自成条贯。[51]
那时已经在社会形成了讲求声律的风气。
其九,规则的形成。沈约《谢灵运传论》就称,此种规则是: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52]
其韵律建构的道路,在陆机“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基础上更明确“尽殊”、“悉异”,这是讲词语、句子韵律的相反、相对;又加上词语、句子韵律的相反、相对是为了“八音协畅”。至唐代,《新唐书•文艺传》载: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53]
这就是律诗。
我们看到,“永明体”、律诗的形成,动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即:音乐、外语、佛教诵经、语言学研究成果、诗人创作实践、个性天赋、文学集团支持、哲学理论(一正一反)、类书、理论专著,等。上述关于“永明体”、律诗形成的历史逻辑的论述,实际上说的就是其形成的合理、合法、合情的问题。
首先,为诗制定韵律规则的合法性问题。钟嵘认为“今既不被管弦,亦何取于声律”,即为诗制定韵律规则不具合法性;而沈约认为汉魏以来诗歌“音律调韵,取高前式”是有规律可寻的。
其次,为诗所制定的规则,其本身合不合理?这就是以四声来协调自陆机《文赋》以来就提倡的“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
第三,为诗所制定的规则,是否合情?即人们喜欢不喜好?能不能遵不遵守规则?所谓平、上、去、入,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史通•杂说》所谓“自梁室云季,雕虫道长。平头上尾,尤忌于时;对语丽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54]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开来。
四、反韵律倾向与当代诗歌韵律的构建
中国古代格律诗定型以来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及其应对,对现当代新诗的韵律构建提供着某些借鉴、有着某些启示。
其一,自唐以来,新诗体的诞生往往要有韵律建构。如词,盛唐文人所写的曲子词基本上都是整齐的五言、七言形式,个别为长短句。到中唐,文人开始认真地倚声填词。元和年间后,文人填词逐渐增多,词正式成为一体。 苏轼之前,音乐是词的生命,音乐的特性重于文学的特性,因此协律合乐是填词的首要条件。苏轼第一次使词从重乐的框框中摆脱出来,使词与音乐初步分离,使词首先成为一种文学体裁,而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庸,从而使词在文学史上有了独立存在的地位。韵律的不同运用促进新的文学形式的出现,词、曲等。
其二,但自唐以来,诗歌又面临着反韵律或破坏韵律的挑战。如韩愈,就刻意破坏诗的外在形式的规范整齐、节奏和谐、句式工稳,他常常把散文、骈赋的句法引进诗歌,使诗句可长可短、跌宕跳跃、变化多端,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或”和“若”,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妥若弭伏,或竦若惊雊”,《忽忽》、《寄卢仝》、《谁氏子》等,大量运用散文的虚词,使诗的节奏发生了曲折变化,或有人称它“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55]
此后以白话文挑战文言文的韵律,渐成主流。如元曲以口语式的白话文为衬字,在曲牌所规定的格式之外另外加字,以补充正字的语意,使内容更加完整充实,语言更加周密丰富或生动,或者使字句与音乐旋律更加贴合。曲于是在遵守格律的前提下,有更大的灵活性,行文造字更为自由,不受格律的束缚;如关汉卿的南吕《黄钟尾》“我正是个蒸不熟煮不烂炒不爆锤不碎打不破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之类,“响”字前的部分即为衬字。
其三,唐时王梵志作白话诗,但清人编《全唐诗》,就把它排除在外,不视其为诗。事隔千馀年,黄遵宪又积极提倡白话诗体,他在诗创作上引俗话入诗,其1868年(同治7年)写的新诗,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56]
白话时代迫使诗歌做出回应,旧诗的韵律已完全不适应历史转折形成的巨大冲动下产生的新诗。由提倡白话诗的创作实践,到胡适虽说要充分采用白话的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但他提出废除旧诗韵律问题,所谓“不拘格律”。以后诗人们认为,以白话文、口语化为诗歌的语言载体,还是要有格式,要有韵律。闻一多开创了现代格律诗的新诗流派,提出了更甚于古代格律诗的要求,就是著名的“三美”音乐美是指诗歌从听觉方面来说表现的美,绘画美是指诗歌的词汇应该尽力去表现颜色,表现一幅幅色彩浓郁的画面,建筑美指诗歌每节之间应该有外形的匀称。何其芳《关于写诗和读诗》、《关于现代格律诗》主张建立现代格律诗,对诗的顿和押韵提出自己的见解。
自胡适1920年出版《尝试集》,至今已近百年,新诗的韵律还没有一个定位。心灵表达,需要一个独立的、自足自律的韵律体系,因为这是生命对韵律的需求、文学对韵律的需求。社会需要规则,诗歌作为一种与声韵相辅相成的艺术作品,也需要声韵规则,诗歌创作遵守规则成为诗人的内在需要。虽然诗人更看重的是个体的主体性、语言的独创性,但这一切需要一个平台、一个地平线、一个秩序,让人们可以明白地衡量出诗人的主体性、独创性到底是什么!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云:
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然,文亦犹之。惟是 欲通曝,纮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轾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迹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57]
此所谓“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当代诗歌的韵律构建,当然应该汲取中国的文字特点,当然也应该奠基在吟诵的基础上。从古代看,韵律构建本来就在反韵律的争辩中形成,而且在定位后又不断受到反韵律的挑战,但新的诗体就是在如此的挑战、应战中形成期格律的。新诗可以走散文诗的路子,但不是惟一;但新诗选择韵律,构建韵律,所要走过的路会更加漫长,与永明体调动大量的资源比照,现在可以调动哪些资源?与永明体比照佛教梵语的特点,现在也有西方诗的借鉴,如人们已经借鉴过的欧洲十四行诗;也有“当代艺术”的比照,在摒弃写实性的同时制立韵律规则?新型传播媒体,比如网络对诗的韵律会有什么影响?等。
当我们看到,从汉魏诗到永明体有数百年,从永明体到律诗又经历了二百年,那么对新诗韵律的形成就不必多有焦虑,让新诗去自然而然的发展吧!让诗人们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吧!让读者们以各种各样的腔调去吟诵诗歌把!而有一条是肯定的,即新诗韵律规则的形成,是建立在汲取社会多方面的资源基础上,也是要靠诗人、理论家、读者孜孜不倦的实践的。 ■
[1]萧统撰,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637下.
[2]吕不韦.吕氏春秋,诸子百家丛书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3上.
[3]刘安.淮南子•道应训[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414.
[4]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37.
[5]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866下.
[6]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七引[M].北京:中华书局,1979:396.
[7]郭茂倩.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880.
[8]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27.
[9]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37.
[10]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6—2007.
[11]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006中.
[12]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51.
[13]章诗同.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24.
[14]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787下
[15]鲁迅语,鲁迅撰,吴中杰导读.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87.
[16]班固.汉书•杨恽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2896.
[17]萧统撰,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35上.
[18]范晔.后汉书•文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5:2631.
[19]班固.汉书•礼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2:1045.
[20]班固.汉书•佞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725.
[21]班固.汉书•外戚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3952.
[22]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59—260.
[23]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241下.
[24]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1779.
[25]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37—1242.
[26]钟嵘撰,曹旭集解.诗品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32.
[27]钟嵘撰,曹旭集解.诗品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32.
[28]刘敬叔撰,范宁校点.异苑[M].北京:中华书局,1996:48.
[29]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173.
[30]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503.
[31]隋释智顗.摩诃止观卷七下[M].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32]沈约.宋书•范晔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30.
[33]钟嵘撰,曹旭集解.诗品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40.
[34]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898.
[35]李延寿.南史•谢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3.
[36]李延寿.南史•何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871.
[37]李延寿.南史•刘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240.
[38]姚思廉.梁书•谢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529.
[39]李延寿.南史•王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9.
[40]李延寿.南史•何思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82.
[41]李延寿.南史•吴均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80.
[42]李延寿.南史•刘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1006.
[43]姚思廉.梁书•王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713.
[44]李延寿.南史•刘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1782.
[45]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18.
[46][日]弘法大师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9—10、15—16.
[47]钟嵘撰,曹旭集解.诗品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29、332.
[48]钟嵘撰,曹旭集解.诗品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340.
[49]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898-899.
[50]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899.
[51]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1.
[5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79.
[53]欧阳修等.新唐书•文艺•宋之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51.
[54]刘知几、章学诚.史通 文史通义[M].长沙:岳麓书社,1993:173.
[55]冷斋夜话引沈括语,欧阳修、释惠洪著,黄敬德批注.六一诗话 冷斋夜话[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49.
[56]杂感其二,.黄遵宪集上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90.
[57]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
【责任编辑 吴庆丰】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oems’ Rhythm in Feudal Dynasties and Poem’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lso on the Enlightenment for Rhythm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Poetry
HU Da-l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In the early life of human beings, affected by the rhythm of music and dance, poetry, together with music and dance, constitutes the art of human activities. As a member of rhythm’s family, poems contribute to literature’s status in civilized society. Since Han dynasty, although poems still had relations with music because of its rhythm, as language’s function of conveying aspirations and expressing emotions were highly compacted to reflect social life centrally, literature had been breaking away from the class of music or dance; it relies on the usages of meaning and became an independent category of culture. Poems which rely on the usages of meaning seek to obey the rule of using rhythm. From Han’s “Yong Ming Style” period to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shape of metrical poetry has been finalized; it perfected itself by with strict rhythm and differed from other literary stylesthrough its special form of rhythm. Since mid-Tang Dynasty, going through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there had been constant anti-rhythm tendencies. At that time, free verse poem appeared and the rhythm system of old style poems was broken. It came to a critical time to decide whether to abandon poems’ rhythm or not and how to carry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rhythm. In the new era,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em’s rhythm will be one of the difficulties for literature to face.
relying on voices; relying on meanings; rhythm; free verse poem
I207.227
A
1004-4671(2015)03-0002-08
2015-02-26
胡大雷(1950~),浙江宁海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古文学研究、文体学研究、桂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