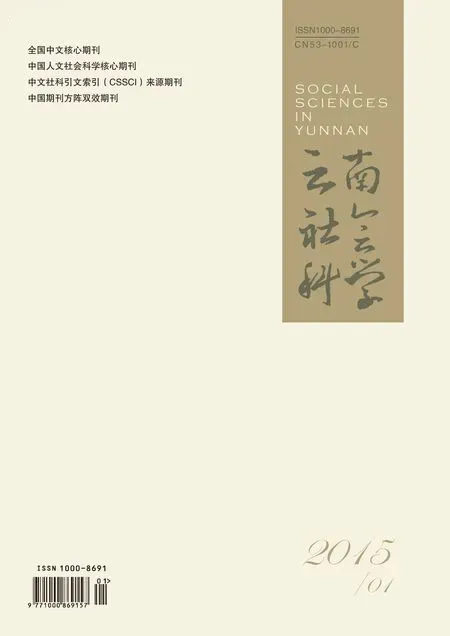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左康华
一、“礼义”的发现与礼学的开端
从《三礼》(即《仪礼》《礼记》《周礼》)的部分篇章所反映的宗周的典章制度来看,周代的礼乐文明,已经发展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周礼的系统,以《仪礼》所言,有冠、婚、丧、祭、朝、聘、乡、射等礼;以《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言,礼有吉、凶、宾、军、嘉,五礼名下又细分为三十六目,内容繁复、巨细无遗,形成了一整套按着一定社会秩序和规范来进行生产和生活、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的具有极大强制性和约束力的典章、制度、仪节。
如果说典籍的记载尚有后人美化、造伪的可能,那么出土的文物无疑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忠实见证者。从西周礼制建筑遗迹,到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成批礼器,再到各类金文、甲骨文的记载*参见杨向奎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无不反映着周礼的普遍性、实践性与强制性。
考察礼的起源,自古至今影响最大的假说是祭祀说*这一观点认为礼起源于祭祀活动,最初是指将祭品(玉石或酒)装在礼器中献给所祭神祇,随后推衍出人所需要尊奉的举止规范的含义。最早出自《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徐灏笺:“礼之言履,谓履而行之也。”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礼”字最早指以器皿盛两串玉献祭神灵,后来也兼指以酒献祭神灵,又推而广之为奉神人之事。这一说法应当是有关礼的起源诸说中影响最为深远、为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一种。;此外,古人尚有人情说*该说认为礼起源于对人的情欲的顺应与节制。郭店楚简《语丛一》:“礼因人情而为之”,《性自命出》篇则载“礼作于情”。《礼记·丧服四则》:“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史记·礼书》:“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风俗说*该说认为礼起源于风俗习惯。《慎子·轶文》:“礼从俗。”《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也。”近人刘师培、吕思勉也持此说。参见刘师培著,《刘师培全集》(第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吕思勉著,《经子解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乃至天道说、圣王说*该说认为,礼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种种礼仪。最早由杨宽提出,李泽厚也持此说。参见杨宽著,《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4页;李泽厚著,《中国古代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近代学者则有礼仪说*这种说法认为礼起源于天道秩序,而为圣人所制。《礼记·礼运》:“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夫礼必本于太一”。、交换说*此说认为礼起源于人类原始的交往活动,遵循“礼尚往来”的原则;后来逐渐演变为带有强迫性的礼品交换。参见杨堃著,《西周命册制度研究·序》,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古人论礼,多临事取义,各根据礼的某一方面立说,今人论礼,虽不乏创见,但更是各据一端,难发全面之论。然而,无论哪种假说,都承认礼起源于实践,形成的是一套行为规范与共尊仪式,且具有一定程度的强制性。曾有学者概括周礼的各项功能,认为其具有政治功能、道德功能、节制情感功能、社会功能,并且是贯穿一切道德观念的核心范畴[1](P264~270)。我们并不否认周礼或许在事实上起着这样那样的作用,但归根结底,这些功能的发挥都还处于自然自在状态,并没有上升到理论的思考层面。而礼的实践层面的丰富,并不能代替哲学的思考。因此,这一时期有“礼”而无“学”;礼学尚处于孕育期。
发生于春秋末期的“礼崩乐坏”的现实危机说明,“日用而不知”的单纯实践,已经不能适应变动的社会现实。面对周礼的价值危机,思想家们必须从理论上对礼的本质及功能进行思考与探索,以图从日益崩溃的礼仪典制中拯救出礼的价值内核。用理性的目光审视礼本身,审视礼的本质、功能及意义。
这种思考首先表现为“仪”与“礼”的区分。春秋时期,开始有人意识到礼的形式与内容的不同。学者们普遍注意到了《左传》的如下记载:“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凌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左传·昭公五年》)[1](P667~668)关于“仪”与“礼”的另一次讨论则出现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2](P765)。可以看出,此时“仪”不但被区别于“礼”,甚至隐隐与“礼”对立;对“揖让、周旋”的细枝末节的追求、行礼如仪已经不会被赞为“善于礼”,反而可能因为某种价值原则的缺失而被嘲笑为“焉知礼”。
需要注意的是,《左传》的其他记载则说明“仪”在当时依然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可见对于礼仪的强调依然存在。参见(清)洪亮吉撰、李解民点校,《春秋左传诂》,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0页。。在“揖让、周旋之礼”的强约束力并未消散的同时,对于“礼”的格外强调就显得引人注目。究其内涵,人们已经开始注意礼的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并做出了礼义高于礼仪、内容高于形式的价值判断:“揖让、周旋之礼”是为礼仪,是礼之末;“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是为礼义,是礼之本。若不知礼以其义为本,而“屑屑焉习仪以亟”,不过是徒有其表而无其实,或者虽有礼仪而失其大用,舍本逐末,不可赞为知礼。
如果将礼义与礼仪的分离视为内在精神与外在形式的区分,那么在礼仪之外,礼义也从同属于形式的礼器乃至礼数上剥离,礼的精神彻底摆脱了形式的束缚而得以彰显。
礼器或称礼具,是礼典中所使用的、体现差别的器物;礼数则是礼器、礼仪的具体的数量,“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2](P248),是等级地位之差的最直观的表现。就前者而言,“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3](P1216)的追问;就后者而言,“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礼记·郊特牲》)[4](P706)的轻视:二者所反映的,都是礼的内在精神——礼义,对于礼的外在形式——礼仪、礼器、礼数的全面超越,最终确立了“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郊特牲》)[4](P706)的最高原则。
礼义的产生,是对仪式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总结,又使礼摆脱了礼仪的躯壳的束缚而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首先,礼义的存在使礼制的构建更具灵活性。“礼者在于所处”,礼义可以用于指导礼制的建设,礼制可以在礼义的指导下因时而变、有所损益,不致再次面对先秦时的危机;其次,礼义的抽离促使人们从思想学术层面而不再是制度典章层面研究礼、认识礼,换言之,从形而下的器物、行为层提炼出形而上的意义,是“礼”向礼学进化的起点;对于礼的现实层面的反思,促使人们意识到礼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二、以礼文为价值追求的儒家礼论
如果将礼仪与礼义近似等同于礼的外在表现与内在精神的话,礼文与礼质之别则更为复杂。孔子及其弟子有关“文质彬彬”以及“绘事后素”的有关讨论,将“文”“质”这一对概念范畴引入了礼学研究的视野。
从字源学角度看,“文”与“礼”似乎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说文》释“文”:“错画也。象交文。”段玉裁注:“错画者,交错之画也。《考工记》曰:‘青与赤谓之文,错画之一耑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依类象形,故谓之文。”[5](P425)《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6](P319)可见“文”的原始意义当是指条纹、纹彩交错的具有美感的样态。这种有规律的具有美感的样态,在天表现为“刚柔交错”,在人则表现为“文明以止”*《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参见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5页。。《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宫、羽,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4](P820)其所描述的行礼的程式、复杂的装饰,乃至配合着乐曲的节拍,无不与“文”所代表的丰富的纹理和合理的秩序相合。这使得“文”与“礼”在内涵上有了相通之处,继而能够互用。《论语》中,无论是夫子“郁郁乎文哉”的赞叹,还是“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的自我期许,其中对于“文”的定义,无不与“礼”的概念尽相吻合。
“质”是作为与“文”相对的概念进入研究视野的。《说文》训“质”为“以物相赘”,又训“赘”为“以物质钱”;段玉裁注“质赘双声。以物相赘,如春秋交质子是也。引申其义为朴也、地也,如有质有文是。”[5](P281)可见“质”的本义是以物交易,引申开来,“质”首先具有实体性:相较于“文”的工巧形式,“质”更侧重内容,因而引申出“实质”“本质”之义。其次,“质”作为未经加工的素材、质地,又往往与朴实、自然等特征相关联。无论是本质义,还是质朴义,“质”都与“文”的文采、文饰紧密联系而又构成矛盾;因此,“质”作为与“文”相对的概念范畴被引入礼学的研究,就显得顺理成章。
从《论语》的记载来看,孔子及其弟子坚持“文质彬彬”,也即是人的行为举止与自然本性协调共济的原则:“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3](P400)在棘子成与子贡的讨论中,子贡反驳了棘子成“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的观点,认为文、质就犹如动物与其皮革的关系,“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文、质相辅相成,去彼无此、去此无彼[3](P840~842)。以孔子为首的儒家认为“文”表现于外,构筑起了进退揖让的礼仪形式系统,“质”隐含于内,内化成为人心的道德规范;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文质彬彬”为原则,即外在的礼仪必须与仁义的内在品德协调相配、不偏不倚,才能共同构成礼的理想状态;奢、易则文饰有余而其质不足,失于虚华,俭、戚则其诚有余而文饰不足,失于粗鄙,任何一方的偏胜都会导致礼的缺陷。
多有学者用内容与形式这对范畴来概括“质”与“文”之间的关系,认为“礼的文质关系反映的是礼的形式与内容、意蕴,或礼呈现的式样与其本质、精神、功能的关系。”[7](P1)然而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文/质”说是对“仪/义”说的继承与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之外,“质”与“文”更是指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儒者所追求的“质”,更多地存在于道德范畴,是一种天性追求仁义的、乐于接受礼乐教化的本性,正如《礼记·礼器》所言,“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4](P333)。这里,“质”与“文”超越了单纯的内容与形式,而是构成一种正向关联,共同指向更为完善的道德境界。《国语·晋语》中,胥臣答晋文公:“胡为文,益其质”[8](P387),以及前引“文犹质也,质犹文也”,无不是这一观点的反映。
从儒家追求的另一项“质在文先”的原则中,可以更明显地看出这种继承关系。在“文质彬彬”的合乎中庸的理想境界难以达到时,孔子认为应当坚持“质在文先”“仁在礼先”。《论语·八佾》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3](P157~159)就像礼仪的外壳不能束缚礼义的价值,与文采焕然的礼乐制度相比,质朴的本性更为可贵,因为“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9](P71)。
然而,当礼学的研究从“仪/义”论进入“文/质”论,儒家所无法割舍的对于“文”的价值追求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儒者的立场。以完整的“文”“质”内涵来审视儒家的文质论,可以看出儒家有意回避了“质”的全部内涵,而更多地停留在道德范畴,认为只有易于接受礼乐教化的本性才可称之为“质”;其所追求的是文化了的“质”,而与“质”的本义有所偏离。无论孔子怎样表示出对于“巧言令色”“便辟”“善柔”的深恶痛绝,都不可能真正反对英华发外、焕然成章的文象;无论怎样强调“质”的先在性,都不可能真正以质之朴代替文之华*儒家所追求的“质之朴”,也往往是符合“文”的审美的“大圭不琢”的美玉,而并非真正的质朴甚至简陋的质料。。换句话说,对于华丽之形式的追求、对于价值生命的向往,是深刻在每个儒者灵魂中的本能。这种对于核心概念的含混与避重就轻无疑使儒家“文质彬彬”的原则最终屈服于“礼文”的价值追求。
三、诸子的攻讦与礼意的复归
从礼义到礼文,儒家文质之说超越了此前礼学研究中形式/内容的简单划分,使礼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极大地丰富了先秦礼学的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儒家重礼文而轻礼质的实际立场也招致了诸子的批判。
批判的焦点之一是儒家质论的偏颇。老子并不认同儒家对于“质”的定义,而是以纯乎天然的、未经雕琢的本性为“质”,认为任何外在文饰的赘附都是对“质”的戕害:“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第三十八章》)[10](P151~152)在老子看来,既然宇宙万物皆归本于自然,这未经雕琢的自然便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一切人为的加工与文饰都只会损害其本来面目。所以他要发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第十二章》)[10](P45)这样的警告,并提倡“见素抱朴”和“复归于朴”。
韩非持相近的立场,并进而认为文盛即是质衰:“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11](P133)韩非子认为,“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11](P133),如果事物的本质足够美好,那么没有任何礼文能够修饰;反过来,需要礼文来装饰的事物,正说明了本质的枯萎。
对此,庄子更为尖锐地提出了“文灭质”的主张:“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12](P136)在道、法诸家的思想家们看来,文、质无法共存,对一方的强调必然会损及另一方,因此权衡之下取“质”而轻“文”乃至弃“文”。
批判的焦点之二则是儒家的文繁之弊。《墨子·非儒下》中批判的“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13](P291),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时人(特别是社会中下阶层的民众)心目中儒者的形象。墨子认为耗心力于文采修饰无益于国计民生,故而反对礼的繁文缛节。《墨子·非乐》篇中对于乐的批评是这一观念的集中反映:“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13](P251)即便在后世,学者对于儒家虽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然而对于其流弊之所在,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司马谈“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论六家要旨》)[14](P3290),刘子“流广文繁,难可穷究”(《刘子·九流》)[15](P520)的批判,皆可为证。
就诸子对儒家文质论的攻讦而言,前者补充完善了礼质的内涵,指出了礼文所具有的掩饰功能对自然本性的戕害;后者更是鲜明地指出了儒家坚持的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可能带来的奢靡之弊。然而,诸子尚文轻质的立场不可避免地割裂了礼的文质,其对礼文的激烈否定则更不可取。礼的发展程度,可以作为文化是否发达的一个标准,甚至可以作为文明成熟程度的标志。礼萌生于先殷,至夏、殷而稍具规模*陈戍国通过对先秦史料的研究,参考现代考古成果,认为多种礼萌生于有虞时期,到夏代,礼的门类多已具备而初具规模;殷礼已代表了相当高度的文明,五礼齐备而仪节渐趋繁缛。参见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69-176页。。周代继承前代文明积累,又经周公制礼作乐*有关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所载季文子之言,更广为人知的出处则是《礼记·明堂位》:“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在经古文学者口中,《周礼》更是周公所建官政之法。近代以来,疑古之风盛行,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乃至三礼的可靠性受到极大质疑,甚至被认为全部出自汉儒的伪造,影响甚大。建国来,陆续有学者对这一观点做出修正,认为三礼中某些篇章可以与先秦古籍互证,若以三礼为全伪,则中国将无信史可言。有持中之论认为,今存三礼,虽然羼杂了不少战国时代的礼制,又经过汉朝人的篡改,但大体为先秦礼书;周公不一定是三礼的作者,但礼的设计及实施肯定是周初统治者所为,而主要是周公。,文物制度已灿然可观。我们可以批评文明的发展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抑制乃至戕害,却绝无可能抛弃历代的积累而真的重返自然。
对此,庄子重提礼意*本文之所以先用“礼义”而后用“礼意”,是出自对《庄子》原文的尊重,对二者可能有的差异不多分析。,试图以此消解文质之争议。与老子反礼的主张不同,庄子从根本上是认同礼文所代表的尊卑秩序的,认为其代表了天地之间固有的规律。《庄子·人间世》认为命与义是“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根本原则,《天道》篇则载“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庄子·天道》)[12](P116),其中透露出的无可辩驳的尊卑之意与道家另一支派的杨朱学说一味“贵生”“全生”的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段文字而常被人们怀疑并非庄子学说。现代学者李镜池、陈鼓应等先生从《易传》与道家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系辞》在自然观方面所受到道家的影响。在这里,它从天道有尊卑先后之序而推及人道的秩序,正体现了道家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与内篇《人间世》中,对“子之爱亲”与“臣之事君”这两大宿命的认同,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庄子所激烈反对的,就是痛恨俗世之人“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庄子·大宗师》)[12](P65),认为这反而是对真正的礼意的遮掩。《庄子·大宗师》所载“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一段,子贡认为临尸而歌不合礼,反被孟子反、子琴张二人嘲笑为“恶知礼意”,这里的情景与对话正透露了庄子与儒者对待礼仪的不同态度。儒者认为临尸而歌是对丧礼的漠视、对友人的漠视,是一种非礼的行为;庄子则认为人有生有死,这是天道秩序之所在,因此人应当顺从天道的安排,就像幼子顺从父母的安排那样*《庄子·大宗师》载:“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参见(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4页。,这才符合与大化同流的更高层次的礼意。
四、“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
面对“文质彬彬”的理论设计与“文多质少”*这句话是喜好黄老的窦太后给予儒者的评价。《汉书·万石卫直周张传》载:“郎中令王臧以文学获罪皇太后。太后以为儒者文多质少”,参见(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七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95页。的现实评价的南辕北辙,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儒者选择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试图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用于指导汉代礼制的实践。有学者认为,“文质说是一种东方独特的文化思想,它经历了一个由伦理哲学、历史哲学到文化哲学的历史发展,最后才进入文学领域。”[16](P9~13)而在礼学的视域下,文质论从伦理哲学向历史哲学的发展,正是文质论从礼论向礼制论的发展。
汉代儒家认为,夏、商、周三代礼之大体相因而不能变,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各有所侧重,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董仲舒提出的三代改制质文说,通过对上古礼乐制度细节的构建,主张一种文胜则救以质、质胜则救以文、文质更迭循环的“文质互救”说。《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载:“王者以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17](P204)“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故立嗣予子,笃母弟,妾以子贵。昏冠之礼,字子以父。别眇夫妇,对坐而食,丧礼别葬,祭礼先臊,夫妻昭穆别位。制爵三等,禄士二品。制郊宫明堂员,其屋高严侈员,惟祭器员。玉厚九分,白藻五丝,衣制大上,首服严员。銮舆尊盖,法天列象,垂四鸾。乐载鼓,用锡舞,舞溢员。先毛血而后用声。正刑多隐,亲戚多讳。封禅于尚位。”[17](P205~208)在后文中,董仲舒不厌其烦地描述了夏礼、质礼和文礼,并将一质一文、一商一夏的礼乐系统与有虞、夏、商、周四代的礼乐实践相联系,这种礼乐系统的追述与《礼记·表记》的记载相比,其中不乏冲突之处*《礼记·表记》以为夏属质,亲而不尊,《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则认为夏属文,尊尊而多义节;《礼记·表记》以为商属文,尊而不亲,《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则认为商属质,亲亲而多质爱。,联系董仲舒所描述的四代礼乐制度如此丰富的细节,大致可以断定,孔子时文献就已“不足征”的有虞、夏、商礼,基本不可能在董仲舒时全盘重现,那么很难将其所描述的上古礼乐制度视为历史的真实。
因此,这里对于礼乐制度的“描述”(或者说是“构建”),最大的亮点在于“文”“质”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外在文饰”与“内在品德”,而是被当作了上古礼制所表现的风貌的代称:“文”是因尊尊的特质而表现出的文胜于质的礼乐系统,“质”是因亲亲的特质而表现出的质胜于文的礼乐系统;两套系统文质同存,并因文质各有侧重而得以命名。礼在历史的发展中,往往会出现偏文或者偏质的弊端,这时就需要以质救文或者以文救质,从而加以补救损益。
这种以文、质为两种礼制、往复互救的主张,在两汉学者那里,成为一种共识。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赞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14](P393~394)《盐铁论·救匮》载:“桡枉者以直,救文者以质。”[18](P400)《汉书·杜周传》载杜钦给成帝的上书:“殷因于夏尚质,周因于殷尚文,今汉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质,废奢长俭,表实去伪。”[19](P2674)甚至直到东汉时期也无出其右,何休在《春秋公羊传注》中认为:“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皆所以防爱争。”[20](P13)乃至《春秋纬》《白虎通》等概莫能外,使得两汉文质论在整体上表现为“文质相救”、往复循环。
以董仲舒为首的西汉儒者继承了先秦儒家所使用的文质论的概念范畴,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试图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是理论上的创见,也从另一个角度弥补了先秦儒家礼论的不足。然而,前面提到,“文家”与“质家”的区别,多是体现于对坐而食与同坐而食、制爵三等与制爵五等、封坛上位与下位等具体而微的细节,从董仲舒对“质家”的描述中,很难看出有虞礼、商礼之质朴,反而对其繁复的礼制印象深刻。汉代学者多埋首于文质礼制论的构建,使礼学研究从礼论转入礼制论,促进了礼在制度上的落实,却在客观上加重了儒家礼学的“文繁”之弊,有待后来者的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