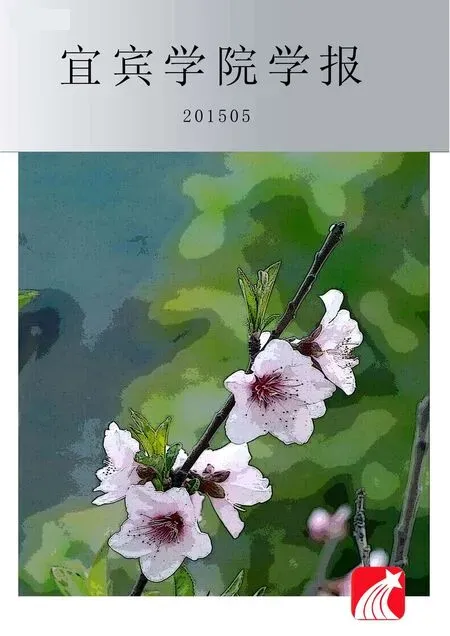书写理念、文本形态及多重性价值
——对《史记》的几点理论思考
梁新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200083)
书写理念、文本形态及多重性价值
——对《史记》的几点理论思考
梁新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上海200083)
摘要:《史记》有着双重性的书写理念,即实录与修饰。这两种书写理念从表面上看是相悖的,实则是同一的,二者在深层次上殊途同归。《史记》这种二元同一的书写理念,根源于作为史家的司马迁的独特人性观。《史记》在文本存在形态上是多元同构的,它不单是一部优秀史学著作,更是一部兼容并包的文化经典。《史记》这种多元同构性决定其具有多重性价值指向,它的价值呈现模式是“以美启真,以真启善”。
关键词:《史记》;实录;修饰;多元同构;多重性价值
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其不仅堪为中国最早的包罗万象的文化经典,而且开启了后世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模式,为后世千百年的历史书写创造了典范。关于《史记》,古往今来的研究者可谓恒河之沙,研究性的著作也汗牛充栋,从书写理念、文本形态、价值取向可以看出《史记》的史学价值和超时代的意义。《史记》以其复杂同构的书写理念、多元交织的文本形态、丰富多重的价值指向,真实细腻地揭示了历史的多样化的真相,以及此多重真相背后的复杂的人性图景。司马迁以其深刻的人性洞察力、超然的伦理关怀立场,呈现出上古中国博大的历史景观和人性悲歌。
一《史记》书写实录与修饰的同构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宣称其《史记》乃是“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1]546。司马迁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史记》的书写理念乃是“述而不作”。这一“述而不作”的写作原则,后来被班固命名为“实录”——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引刘向、扬雄之言,赞扬《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2738。可以说“实录”作为《史记》文本书写的核心理念当是确凿无疑的。我们通观整部《史记》,也确能发现其处处体现出来的“实录”精神。这种精神不仅在《史记》的十个大事年表中体现着,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及众多人物列传中也都清晰地呈现着。可以说,“实录”精神在《史记》文本中的强有力贯彻也是确凿无疑的。司马迁在其《史记》书写中可谓真正做到了“秉笔直书”,“如实地”记录下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事实。
但在《史记》人物纪传的书写过程中,“实录”精神却是很难完全贯彻的。如实地记录下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容易(只需要按年次细致地编排历史事件即可),而如实地“记录”历史人物却难。因为历史人物总是复杂多面的,要想在简短的文字编排中生动地“还原”出他的真实形象并不容易。因此,“实录”精神虽然对具体的传纪书写而言非常重要,但其实是很难完全贯彻的。事实上,对人物繁多的生平史料和逸闻轶事的选择性取舍,也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实录”原则在人物书写中的不可能。而在根本上,重大历史场景中人物的微观言行细节其实也是不大可能被还原的。这些微观的细节(包括动作、表情、私密性言语、甚至微妙的心理动向)一般很难在正式的史料文献中找到,而各种道听途说的逸闻轶事又多不可信。因而对于《史记》作者而言,其自己的取舍和判断就显得无比重要。也因此在具体的人物传记书写中,《史记》作者的主体意识必定会有意无意地介入其中。而这种“介入”意识使得“实录”的客观性和纯粹性开始消解。
事实上,除了“实录”理念,《史记》在其具体的人物传记书写中同样存在着一个潜在的理念——“修饰”。“修饰”的本意是装扮、美化,也就是借用细节性的东西点缀、粉饰事物本身。在《史记》诸多人物传记中,我们能发现大量的这类细节性“修饰”。它主要体现为具体的人物刻画中的细节性点缀之笔,如微观动作、微观表情、细微的心理动向、私密的言语表述等。司马迁的人物传记中的人物是非常饱满的,可谓复杂多面、生动真实,充满着人性的本色。这些复杂形象的建构就得益于其精彩的细节刻画。而这些传神的、生动的细节刻画,其实很多是基于一种合理想象下的“臆造”、一种人性规律下的推测与揣摩,也即装扮性的“修饰”。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曾说过一段话,他虽然是在论述《左传》的人物特点的,但其实同样适用于说明《史记》的人物构造规律。
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室之谈,或乃心腹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
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3]164-166
如钱钟书先生所言,我们也能在《史记》的人物纪传中发现这种“臆造”和“虚构”的诸多蛛丝马迹。如很多缺乏史料根据的人物的一些微观言行、细微表情、隐秘的心理活动等。从《史记》的传记文本中我们能发现大量这类的细节。
总之,归结来看,《史记》中这种“修饰”——人物书写中的细节性刻画,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人情事理下的合理想象,但不能不说它已然踏进了文学书写的疆界之内。司马迁的这种体现在文本中有意无意的“修饰”,虽然未必是一种刻意的编造,但其实已然可以算作一种“虚构”。这种“虚构”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完全凭空捏造的,而是建立在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上的。它是一种合乎人情事理的想象性描述,它之于建构一个生动饱满的人物而言是极为必要的。我们把这种人物书写方式称之为“有限虚构”。事实上,这种“有限虚构”,构成了《史记》文本的“文学性”的核心特征。
二实录与修饰的同一与司马迁的人性观
《史记》文本书写中的“修饰”,表面上看似乎与其所宣称的“实录”是相背离的,但事实上,如若我们对此进行深入思考的话,便能发现其在深层次上是不违背“实录精神”的,甚至可以说,二者是一种表面矛盾实则同一的关系。
《史记》人物书写中的“修饰”,其意图显然是为了凸显历史人物的复杂真实的性格。《史记》正是想借这种合理想象之下的“有限虚构”,来实现其“实录”历史人物真实性格的史学追求。也就是说,“实录”绝不仅仅意味着“如实地记录”文献资料中人物的言行事迹、趣闻轶事,而且还意味着要在此基础上,还原复现出人物复杂真实的性格。司马迁的“述而不作”的“实录”理念其实是有着多重内涵的。其“实录”绝不只是机械地搜集、整理、筛选、编排历史人物的生平资料,还需作者有一种强烈的主体参与意识,即试图透过人物的言行事迹确切地把握人物复杂真实的内在灵魂。这一“再现”人物真实灵魂的诉求,也正是“实录”理念的内涵之一。所以,从这一角度上看,“修饰”其实是通往更高层次“实录”的一种手段,它是为了“实录”历史人物的复杂真实的性格。也就是说在这一维度上,所谓的“修饰”其实就是一种“实录”,它就是要“再现”复杂社会处境下的人的丰富真实的性格本相。
而为何要“再现”这种复杂社会处境下人的性格本相呢?在《太史公自序》中,我们也许能找到些许答案。这就是司马迁特别的人性观念——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这种欲“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抱负,其实映射了其内心的一种宏大诉求。考察《太史公自序》,我们能发现司马迁企图在归纳六家之旨要的基础上,提出对历史、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核心是人性)。如张新科所言,“他始终把‘人’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由人的变化而去推究社会的变化,去探讨古今之变的规律”[4]6。司马迁的史学追求暗含了这点:要在儒家“人性向善”、法家“人性本恶”以及其他各家各派人性学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史家”的独特人性观。通过《史记》中大量的纪传性文本,也通过司马迁自己的阐述,我们可以认为司马迁所谓史家的人性观即是:人性是复杂的、动态演变的,它既不是先天确定的(或善或恶),也不是后天环境下一旦生成就持久不移的,它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后天实践过程。司马迁借助于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正试图表达这样的人性立场。他不认为人性是“向善”或者“本恶”的,而是以其深刻对历史人物的洞察和体悟,超越了形而下的实用伦理立场,发现了人性是在后天的各种生存境遇下不断生成流变的。人性更多的是一种动态性过程,而不是刻板的印象式脸谱。
司马迁也许认为这种“人性”生成的根本动力是自发的“生命力”。在整个《史记》的人物纪传中(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我们都能发现一股浓郁的对“生命力”的礼赞意识,这种“礼赞”意识即对昂扬恣肆的奋斗精神的讴歌,对放诞无畏英雄情怀的认同。司马迁叙写历史上的人物,无论褒贬,无论爱憎,都始终对其基于“生命力”昂扬恣肆的奋斗精神充满敬畏。通过对大量历史人物生平史料的研读,通过实地查访历史大事的发生地,通过游历天下结交各方人士的生命体验,司马迁可谓看透了社会历史的兴衰规律、人性的复杂存在,才立志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即便是在身废受辱的痛苦境遇下,也要矢志不移地完成其史学志业。从这一角度上看,司马迁本人也可谓一个英雄——《〈史记〉美学论》便雄辩地论证了这一点[5]1-22。可以说,司马迁艰难书写的《史记》正是其作为英雄的奋斗结晶。
三《史记》多元同构的文本存在形态
《史记》作为一部复杂的文化经典,绝不只是一本权威的史学著作。从我们现代学科的视角出发,我们可认为《史记》作为一典型的文化文本,其存在形态必然是多学科性复杂同构的。通过上文对《史记》文本中“文学性”因素的一些阐发,我们可认为《史记》的这种存在形态至少可体现为历史性、文学性因素的同构。
而实际上,《史记》也包含着确凿的哲学(思想)性因素。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认为自己的“史家”是继往开来的第七家思想流派,他在梳理“六家之旨要”的基础上,批判性地吸取借鉴各家各派观点,自谓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这种宏大抱负,体现在文本中就是其哲学(思想)性因素。这种因素在每篇本纪、世家,或纪传的结尾处的太史公评语中能明显看出,在“八书”中的许多章节段落中也能发现,而在《太史公自序》这篇提纲挈领的总序性文字中也确凿无疑地体现着。
除了哲学(思想)性因素外,其文学性因素也当是确凿的。杨树增甚至认为,文学性是《史记》艺术价值的根本所在[6]3。如上文稍微梳理的那样,《史记》中的文学性因素主要体现为一些细节性的描述,如人物的微观动作、表情、私密的言语表述和心理动向等。这些人物言行的细微之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定观念下的合理想象,而这种观念即是史传作者本人对人物的理解。虽然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历史人物的生平资料和逸闻轶事的综合研判之上的,但其客观性仍有问题,因为作者本人一定程度的想象性、其受制于自身观念的倾向性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也因此,《史记》人物传记中的文学性因素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再加上为了塑造出饱满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必须使用的细节性虚构,文学性因素出现在史传中就更是不可避免的了。
除文学性因素之外,《史记》作为历史著作的经典性文本,当然有其巨大的“历史性因素”,如历史学家翦伯赞所言,《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历史著作”[7]230。梁启超也说,“《史记》为正史之祖,为有组织有宗旨之第一部古史书”[8]30。事实上,《史记》中的全部文章也几乎都确凿无疑地体现着一种客观求实的“历史性”。我们不仅能在十表八书中确凿地发现此点,而且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中,也能毫无疑问地发现这种确凿的“历史性”。此外,除了“历史性”之外,我们也发现《史记》比以往的历史文本如《春秋》《左传》《国语》等在“文本性”的建构上变得更加精密严谨。也就是说,《史记》在文本性上的(因果)逻辑性、(时空)有序性、结构性、内在节奏感等方面都变得比以往更加严谨,更加体大精深和富于条理。这也是《史记》作为继往开来的集大成之作的一大特点。
综上所述,《史记》作为一皇皇巨著,其绝不只是一部体大精深的史学著作,更是一部集历史性、文学性、哲理性于一体的文化经典。其文本存在形态是复杂同构的,它体现为严谨的文本性、富有感染力的文学性、确凿的历史性以及深刻的哲学思辨性的多元统一。
四《史记》的多元价值指向及价值呈现模式
《史记》作为一多元同构的复杂性文化文本,其必然有着多元的价值指向。第一,最根本的,其价值自当是巨大的史料文献价值。第二,其体现着丰富的文学性价值。通观整部《史记》,我们能发现《史记》的文字表述始终充溢着一股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司马迁骚赋式的人文情怀、强烈的英雄礼赞意识、对昂扬恣肆奋斗精神的讴歌以及字里行间所透露出的历史使命感,无疑都彰显着《史记》巨大的文学性价值。第三,其以深刻的历史和人性洞见以及丰富深邃的思辨意识,体现出深刻的思想性价值。第四,司马迁在既客观又有强烈主体意识地书写历史人物时,显然也有着深刻的思考,其对人性的考量与洞见也有着深刻的伦理价值导向。总之,《史记》的价值是丰富多元的。
此外,《史记》这种多元的价值的呈现模式,有着一定的规律性。简单来说,即“以美启真,以真启善”。《史记》首先以其优美凝练的文字,以其丰富多样的文学性魅力吸引着我们走进历史的纷繁复杂的本相之中,让我们得以获得对历史真相的经验性体认。《史记》这种精彩的叙事艺术和生动的人物刻画,都引导着我们进入历史的真实之域。这就是“以美启真”。
其次,《史记》在以其文学性魅力吸引我们走进真实复杂的历史本相之中时,也必然会把我们引入一个深度思考的空间。这种空间即是伦理思考的空间。我们在对历史人物有了全面深入的把握之后,必然会对其所作所为做出自己的思考,进而做出自己的道德性判断。历史的复杂存在图景,历史人物的丰富的性格,都使得我们无法避开对历史和人性做出深刻的思考。这种思考引导我们关注善恶问题,关注善恶的相对性、历史性、时代性问题。通过这种思考,我们也许能获得一种对人性的启悟,能对“善”产生一种超然的理解。这就是“以真启善”。
〔责任编辑:王露〕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易行,孙嘉镇校订.北京:线状书局, 2006.
[2]班固.汉书:司马迁传[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4.
[3]钱钟书.管锥编[M].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张新科.《史记》与中国文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5]何世华.《史记》美学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6]杨树增.《史记》艺术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
[7]翦伯赞.中国史纲要: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长沙:岳麓书社,2010.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on the Writing Philosophy, Text Form, and Multiplicity of Value
LIANG Xinjun
(InstituteofLiteraryStudies,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Shanghai200083,China)
Abstract:TheHistoryofChinahad been written by a writing philosophy that contains record and fiction, which seem to be contrary on the surface, but is concordant in essence. This writing philosophy ofTheHistoryofChinais rooted in the independent view of human nature of the writer. The text form of it is diverse but isomorphic, which means it is not only an excellent history record, but also an all-inclusive culture canon. The diverse isomorphism of the book determines its multiplicity of value orientation, which takes the form of “showing the truth by beauty, and showing the goodness by truth.”
Key words:TheHistoryofChina; record; fiction; multivariate isomorphic; multiplicity of value
中图分类号:I206.2;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05-0065-05
作者简介:梁新军(1988-),男,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