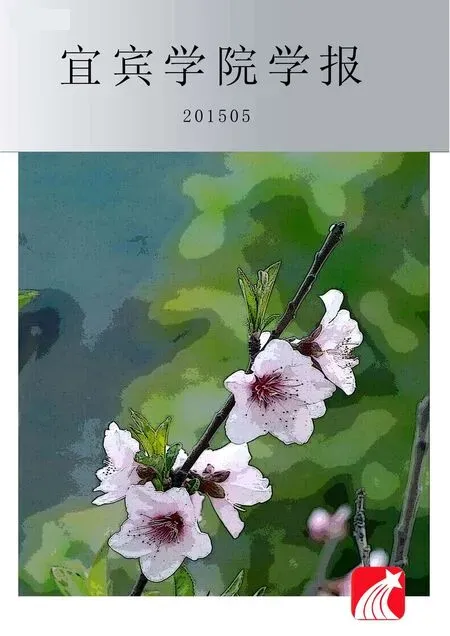娜夜现代女性诗探索:女性抒情短诗的新纬度
周建军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娜夜现代女性诗探索:女性抒情短诗的新纬度
周建军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满族女诗人娜夜,以日常琐屑体验入诗,营构了一种篇幅短小、精致丰满、细腻温婉、含蓄直接的诗歌境界。在长达20多年的诗歌创作中,她不断探索女性抒情短诗的表达方式与诗意技巧。其诗在隐藏与直达中,以清澈纯净的语言,跳脱克制的感情;在空灵与简洁的抒情中,展示现代女性短诗的智慧与厚重,悲悯与苍茫。
关键词:娜夜;现代女性;抒情短诗
娜夜,1964年生于祖籍地辽宁兴城,隶满族镶黄旗,在西北长大。1985年底开始真正意义的诗歌创作,1986年结识诗人老乡,深受其影响,并通过老乡认识诗人阳飏、人邻,在《星星》诗刊发表处女作《会讲故事的朋友》,1989年,《飞天》发表其组诗《远梦》,获甘肃省“飞天文学奖”,1991年与诗人阳飏、人邻、古马等人在兰州创办《敦煌诗报》,1996年11月,参加诗刊社第十四届“青春诗会”,后入南京大学作家班和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进修,2005年,《娜夜诗选》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6年获“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2007年,获《人民文学》诗歌奖,2011年,获“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兰州一家报社工作,现移居西安。在二十多年诗歌创作中,她以智性、沉稳、持守的女性抒情诗短诗见长,先后在《飞天》《绿风》《诗刊》《诗歌月刊》《大家》《民族文学》《广西文学》《江南》等刊发表大量诗作,出版诗集《回味爱情》(1991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冰唇》(199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娜夜诗选》(2003年,甘肃文艺出版社)《娜夜的诗》(2009年,敦煌文艺出版社)等。
不同于一般西部作家对地域题材的倚重和风物描写的依赖,也有别于民族诗人对民族风物的礼赞、族属的认同及习俗的浸炙,其诗民族性相对淡薄,地域描写稀疏,纯属现代女性抒情诗,“在创作中,她崇尚体验,追求真实的爱情,但不放纵感情”[1],开辟了一条以女性意识为主,兼顾智性、抒情、妙悟、哲思、隽永的短诗境界,其诗追求日常生活诗意美发掘,探索出人意表的抒情表达方式。
一《回味爱情》与《冰唇》:娜夜诗作型式与抒情风格的确立
1991年10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娜夜第一部诗集《回味爱情——娜夜爱情诗99首》,内收1985年12月至1991年6月间诗作99首,包括最早的《鹿》和近作《猛然感悟》,多数为其追寻爱情体验和生活写照近作。整部诗集,以抒情主人公日常琐屑工作、生活、爱情为题材,通过细腻情绪抒发及体验,对人生、命运、情感细致玩味、体察和追问,具备其后诗歌创作常见因子、质素,如感性与知性,精致与留白,白描与省略,简约直接的力度与含蓄深邃的隽永,体现出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常见的一些特点:敏感的爱情渴慕、初遇时的惊喜、离去时的黯然,既娇羞、萦怀,又无奈、自怜,不乏精致的景物描绘与情感抒发,如《三峡情》写美丽的邂逅所激荡起的涟漪和绮梦;《必须出门》将大龄女无奈的待嫁与母亲殷殷的目光道出;《远梦》在其早期诗作中算长诗,由10部分组成,构成一组情节单元与抒情空间,1989年发表于《飞天》后,获甘肃省“飞天文学优秀奖”,诗中吟道,“我怎么能够忘记/我以整个青春体验过的震颤/以及月光的压力/门前的红玫瑰 摇曳着/红彤彤的芬芳/红彤彤的荡漾/我抱紧双臂/将头颅低垂贴近心的姿态/是多么的可怜可爱”(5),将伊人临近爱情时的颤栗与不安情态活脱出,再如“我说过:我就是那个/创造了你就得不到你的女人/创造你。在我独特的思维深处/你终于诞生。光芒照耀/完美无缺//在这个欢天喜地的日子里/我却不敢相信地捂起双眼/你便顺着我的指缝/悄然溜走”(10),这些诗句已具备其诗注重的表达方式与情感力度、婉曲、迂回的特点。这种抒情方式在西部女诗人中非常扎眼,不同于民间女子的直接与洒脱,其诗作一开始就具备城市女子抒情的试探性、暗示性、隐喻性。尽管身居西部,又不同于一般西部诗人,其诗中西部风物、意象是稀少的,除《古阳关印象》外,几难觅影踪,其诗是女性的、生活的、日常的,是书斋茶水泡出的。此时的娜夜,在创作中多从日常情节中捕捉灵感,展现一种深挚的倾诉方式和久长的灵感获取方式,从日常入手、生活入诗,正如诗人档案所说:“倾听内心,面对生活”①,其诗也作如是观。
1995年10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娜夜第二部诗集《冰唇》,收诗145首,与《回味爱情》同题旧作约40首,另收新作百余首。据诗作标注时间可分两段:1986年1月至1991年6月为第一阶段,有56首诗作,与《回味爱情》同题篇名旧作约40首,新收10多首;1991年9月至1995年10月为第二阶段,收新作约90首。在诗集编排中,诗人有意“迷踪”,不按时间排,也不按主题类别绾结,给读者、研究者制造了一定的阅读障碍,有“删略”(《回味爱情》一诗题)的感觉,若套用其诗作标题归纳,可视为“多思季节”“深藏的语言”与“带色的思维”。《冰唇》与《回味爱情》呈交叉、承续关系,近40首诗作在《回味爱情》集中已出现,如《感觉》《小蚂蚁》《写诗的女孩》(《回味爱情》集中为《写诗的少女》)《多思季节》《会讲故事的朋友》《捉迷藏》《夜的忧虑》《召唤》《我从未抚摸过你》《远梦》《对不起母亲》《这样的雨天》《无法戒掉什么》《一位少女的悼辞》《回味爱情》《枯木的唯一之花》《必须出门》《今年春天》《我还能说些什么》《带色的思维》《告丫丫》《楼上琴声》《猛然感悟》等。这些诗作除《感觉》《写诗的女孩》两诗稍异外,其余均相同。《感觉》一诗在《回味爱情》中写作时间为1986年12月2日,在《冰唇》集中时间提至1986年1月,诗尾建行稍异,在《冰唇》为:“谁的梦/向我偷偷游来/穿过凤尾草掩映的幽径/在似浪的云中/将一朵含苞的红莲/轻轻启开/记得那雪青的翅膀/每一次的扇动/记得那花瓣上的露珠/每一滴的滴落/梦 在窗内退色//摇醒我的晨光只管摇醒”;《回味爱情》集中《感觉》一诗结尾为:“摇醒我的晨光/只管摇醒//”;《回味爱情》集中《写诗的少女》在《冰唇》集中标题为《写诗的女孩》,流露出斟酌改动痕迹,“似一首深蓝色的阶梯诗/怕你站到最后一行/回过头的推敲/所以我总想把它写得/长一点 陡一点/让你的心跳动得再剧烈一点/眼神再专注一点/那么 你会改变主意/乘坐电梯——/翻阅一针见血的形象吗?/我有些担心/并不是诗的太长太短 忧虑/稚嫩的笔下/冗长了画龙点睛的/尾声”。
这一阶段(1986.1-1991.6)新作诗10多首,如《共伞》《一曲烟径》《误入》《隔墙有耳》《最新鲜的植物》《阳光哗哗》《黑暗》《我的爱该押什么韵》《为爱而老去》《所谓情人》《我突然害怕撞响他们的呐喊》《在这秋天的边上》《独一无二的早晨》等,以“躲闪”形式散见诗集,构成其诗幽深、玄奥、谐趣、重生活感的特点。诗总体上可分三类:
(一)情感体验与日常生活叙述,充满爱的浓情与谐趣。诗如《共伞》《误入》《隔墙有耳》《最新鲜的植物》《我的爱该押什么韵》《所谓情人》《在这秋天的边上》,等等。《共伞》一诗取远譬,以神奇想象夸张“闪电”与“小路”在弯曲性上的相似,由“你也不来/与我共伞”到“你却不来/与我共伞”,抒写女主人公浪漫、绮丽的遐思,从渴慕到幽怨的心态。《误入》《方式》《最新鲜的植物》《我的爱该押什么韵》等留下诗人情感脉络,或述误入歧途的倾慕与欲罢不能,“你见多识广/我必须拐弯抹角走进你/而我早已体无完肤/眼睛 这永不结痂的伤口/向你疼着”(《误入》);或记交往时的沉醉,“我们结交的方式其实很简单/说说话/做做伴/相爱的时候/互相暖暖彼此的梦/说说连自己都没想过的话”(《方式》);再或直陈爱的甜蜜与陶醉,“你的胡子越发扎人了/我当然知道/这是为什么//原来自己走不出的/就是这春风吹又生的意境”(《我的爱该押什么韵》)。进而写日常琐事与婚后角色转换,《收割之后》一诗表面写农人收割,实喻女主人公婚后生活的甜美与辛苦,“像农人在庄稼里除草的心情/我挥舞着抹布/认真对待周围的每一个死角/我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在阳光下看去/没有一点污浊的痕迹/所有的果实/都透露出本质的光泽和香味”。娜夜有的诗是幽默、智性、谐趣的,如《告丫丫》一诗,如此写道:“丫丫/谁教你的/把瓜皮整个套在头上/只露出眼睛/浑身挂满了瓜秧/好孩子/男娃娃爱干的/你别干//丫丫/你可要小心呀/妈妈就是这样爬进瓜地/装成成熟的瓜/被人摘去的”。诗纯以口语写成,从日常情节入手,妙趣横生将人生体验嵌入,微妙传达生活况味,由瓜皮联想到瓜秧,由瓜秧想到瓜果,再由瓜熟蒂落、摘瓜、破瓜等风俗演进,潜意识快速闪现,在电光火石瞬间,达到民俗与世相、人生与日常的诗意洽契。诗是胡适开创的白话口语诗的继承与发展,不同于胡适等白话诗派的有白话无诗意,也不似90年代后女性“口水诗”的寡淡、无聊,诗纯以场景出之,但由于众所周知的隐喻作用,诗作较好地表达了场景内外互文与譬喻,抵达了言近旨远妙趣横生的诗艺效果,这种效果是场景的、情节的,也是诗意的。
(二)对历史事件与现实黑暗的婉曲影射与批评。不同于女诗人对历史与现实的躲闪与回避,娜夜少数诗作对刚发生的史事与现实黑暗进行了婉曲的批评,这些吉光片羽诗句,宛如暗夜中的闪电,划破夜空,曳出惊艳光芒,《黑暗》《鬼节》《我害怕突然撞响他们的呐喊》《独一无二的早晨》等诗,或以玄奥诗句表达深邃哲理,或以佯狂直率表达信念执著,或以暴风雪隐喻纯洁与死亡、呐喊及惊悚,抒发对历史事件的思索,如“一种语言/宣泄完了/就是黑暗//我注视过黑暗了/并与它脸贴脸/划着伸手不见五指的拳/喝着和平酒//黑暗即将过去/天亮了最终怎样/太阳会淡泊我们/这多像我们的创造啊/和所有的创造者一样”(《黑暗》)。诗作以曲折,甚至不知所云的“捉迷藏”形式,隐喻现实“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种时代语境下,除了喝“和平酒”,就只能以诗躲闪反思;再如《冬酒》:“烧一壶老酒/暖冬天/喝不喝 都是幸福//随便说些什么都很暖和/谈谈雪 雪白不了鹰的翅膀/说说鱼 鱼在冰层下/仍然活得很健康/像那个黑衣人 和头顶的太阳/聊着天 走得很悲壮//揣一壶老酒/闯冬天/醉不醉 都说真话”,诗中“喝不喝 都是幸福”与结尾“醉不醉 都说真话”形成一种封闭圆环结构,既有内心感觉,也有信念表达,其“黑衣人”“走得很悲壮”的形象尤为警策,耐人思索;而“这雪下湮埋着不少的生命/以及植物的根/我害怕突然撞响他们的呐喊/惊醒一窝的梦//我想 这场最后的暴风雪/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害怕突然撞响他们的呐喊》)有对雪(洁白、纯洁、消亡意象)下生命根突然死亡的凭吊和梦魇般感觉,做出判断“这场最后的暴风雪/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些“删略”诗作散落各处,构成奇崛、峭拔的诗风,对刚发生史事与现实构成婉曲影射与批评。
(三)简约山水描摹与人物素描映衬,激发自然与人的情感呼应关联。娜夜早期诗作还存在一些简约与深挚并存诗作,如《一曲烟径》《阳光哗哗》《在这秋天的边上》。《一曲烟径》似写情人幽会,又似写风景画后人物心绪,“人影远小/脚步凝重/悠悠踏响一曲烟径/蓝烟/紫雾/油脂般的乳光/潺潺流去/无风//小巷尽头/一轮黄昏的美日/等待久违的脚步/惊跳如心”;《阳光哗哗》以神奇想象、夸张,将阳光比作“太阳雨”,赋予超常神思与乐感,“太阳雨/太阳雨/雨滴石穿/一种声音石破天惊/瀑布从岩缝跌落/阳光哗哗”;《在秋天的边上》,反复咏叹“想我 却不是你的情人”,抒情者与抒情对象充满弹性,到底是你想我,还是我自己思忖“在这秋天的边上/小草青青/我青青 想我/却不是你的情人/我必须坐在你的梦之外/一个人/一个黄昏/一杯茶/想我 却不是你的情人”,在落寞与无奈中,以景结情,平添孤独幽怨之美。
第二阶段(1991.9-1995.10)诗作约90首,多数“以情纬文”,如“草蛇灰线”留下诗人日常生活脉络与轨迹。这种诗主要有《英雄乐章》《幸福的时候》《天机》《棉衣外的暖风》《卧室与徒步之间》《各自有岸》等,是诗人日常经验情感肌肤的自然涟漪,表现了现代女性情感的丰富复杂性,或抒萍水相逢的艳遇与好感(《各自有岸》),或叙床第间女人的情感方式(《卧室与徒步之间》),或发春日之感伤(《棉衣外的暖风》),或忆梦魇中的恩怨(《天机》),或状豪饮时的佯狂与恣肆(《幸福的时候》),林林总总,不独构成其日常诗的异彩,也构成其诗的细腻与热烈。这些诗分散排列,梳理其情感脉络非常费劲,要完整分析其情感空间异常困难。但“以情纬文”,顺其自然,巧构卯榫,勾连不刻意。
二诗风转折:简约与直接,含蓄与留白间的跳跃之美
娜夜早期诗以短诗为主,坚持抒情化方向,但如何深化短诗艺术魅力,是件棘手之事。她除了陆续在《星星》《飞天》《诗刊》《绿风》发表诗作,也借机深造,观摩学习,赢得在诗歌界交往发表良机。1995年,她出版诗集《冰唇》,1997年,参加诗刊社组织的“十四届青春诗会”,到南京大学作家班学习,后进鲁迅文学院深造,增长了才识,对诗歌艺术的理解和感悟也日渐得法,于朴素、自然、纯净外,另增简约一格,但简约不是简单,更不是简陋,是以题材丰富性弥补短诗之纤巧,改以独特构思,简约凝练诗行组接,增加短诗的厚重感,获得书斋型读者的喜爱。
这种艺术自觉与探索,主要体现在其第三部诗集《娜夜诗集》和零星发表的诗作中。
2003年,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娜夜诗集》,汇集诗人140余首诗作,其中,旧题诗作仅10首,如《会讲故事的朋友》《丫丫》《好马》《开累的花》《漂亮的女人晴朗的天》《往好处想》《我用口红吻你》《纸里包火》等,其余均为1995年后的诗作,体现新的诗歌写作趣味与风尚。鲁迅文学奖评语评《娜夜诗选》说:“这些诗有着浓郁的个性生命体验,并由此折射相互开阔的生存现实。诗人以女性的细腻感受,写出了日常生活中本真的人性、情感的欣悦和纠葛,吟述了生命和生存的挚爱。在诗歌语言上,娜夜采用了异质融会的方式。她的一些诗,在轻逸中含有内在的沉实。既有口语的自然腴润,也不乏精敏的深层意象或隐喻。诗人将不同的语型和谐地融为一体以保持诗歌语境恰当的张力,体现了她较高的综合创造力”②。其中,《起风了》,是首最能体现简约、柔美、空旷、淡远诗美的诗作,“起风了 我爱你 芦苇/野茫茫的一片/顺着风//在这遥远的地方 不需要/思想/只需要芦苇/顺着风//野茫茫的一片/像我们的爱 没有内容”。沈奇评论此诗时,以简、淡、空三字来评其诗境之美,“此诗之妙,可用简、淡、空三个字概括。简:用笔简括,着墨简净,形式简约,题旨简明,简到极致,却生丰富;淡:淡淡的语词,淡淡的意绪,淡淡的一缕清愁,淡淡的一声叹咏,淡影疏雾,细雨微风,不着张扬,却得至味;空:语境空疏,意蕴空漠,以空计实,大音希声,留白之外,有烟云生,有风情在,有精神浸漫而言外之意弥散矣!”[2]作者有意轻描淡写,形成以简求丰,至味则淡,言近旨远的艺趣。陈仲义在《百年新诗百种解读》一书中,通过文本细读指出,“起风了”,是自然界的,又是内心的,“野茫茫”——秘而不宣、含而不露,“诗人就这么用起风、芦苇和野茫茫这三个简洁的词组,装载小诗的重量。九行二十五个字,比七律还少四个字。简淡、简约、简隽,一片清空,乃如‘风行水上茧抽丝’”[3]。她深谙省略、转折与沉默在短诗中的作用和效果。
这种含蓄温婉,充满想象空间和多义性的诗句,为其诗作赢得了跳跃性,形成跌宕、错综的浮雕感,有效拓展了诗歌的蕴涵。如在《绿风》诗刊2000年第1期中所载她的《在一起》,“从纸上下来/在椅子上坐了很久/太阳剩下半张脸时/我的眼睛确实看见了/你的身体/和我 在一起/可我又是多么容易感到/你在事情之外的 荒凉/我反复抚摸的/只是你一件衣服上/一根多余的线头//”也体现其诗歌语言的“重入轻出”特点,是一种“双重结构”:“‘从纸上下来’,可以是刚刚写完了信,也可以是从‘纸上谈兵’退出来。但这并不是诗的深意,深层次的语意则暗示出诗的题旨。爱情只是‘纸’糊的。她还特别用了一句‘你在事情之外的 荒凉’,一种不屑的鄙弃的语调淡出,已经鄙薄到了极点,爱情是没有指望了,因为那‘爱’徒有一具僵的躯壳”,“这就是‘在一起’:躯壳在一起,灵魂不在一起”,“‘在一起’的只是你我的‘身体’。”所以诗人以“只是你一件衣服上/一根多余的线头”形容这种虚设的爱情。这种不言之言,“以不说出来为方法,达到说不出来的境界”[4]。这种“双重结构”主要体现在入诗语言的惊奇与寓意的深沉,既开辟诗句的抒写方式,也重视不言之言的留白效果,此外,则惜墨如金,很多论者都指认其诗的洁净、干净、没有毛边,没有多余语言瑕疵,如有论者指出, “娜夜对语言的使用,直截了当,即使有暗示的需要,也不刻意求繁”“这正是娜夜的魅力所在,符合她写作诗歌的一个基础性思想——将繁复淡化为简洁,将晦涩消解为明了,以小见大,言简意赅”[5]。
三丰富性写作探索:《娜夜诗选》及后期诗歌创作
应该承认,从《回味爱情》《冰唇》到《娜夜诗选》,娜夜诗作范围尽管多于80年代中后期女性诗表达范围,但题旨还较狭窄,多从女性琐屑日常生活和情感体验中寻诗,偶尔穿插一些宗教背景、哲学思考或现代意识,在都市高楼的飘窗后凝思疑虑,辗转反侧,较符合一些知性女性柔靡诗风的阅读期待。2005年《娜夜诗选》获奖,为其诗不仅赢得声誉,更让她赢来其后诗歌表现的丰富性与写作自信,一个厚积薄发,创作力与创造性旺盛的娜夜涌现。她大量风格各异,题材日新的诗作刊发于《诗刊》《星星》《《诗歌月刊》等,带来诗风与写作的一些新变化,主要体现在:
(一)旅程、宗教氛围、民俗风情等西北与西藏等新体验诗进入其诗表现领域
我们曾说过,这种西部意象,在其早期诗中是稀疏的,只有《古阳关印象》,她似乎并不想借助西部意象,或以历史文化为表达对象;至《娜夜诗选》时,则陆续出现《从西藏回来的朋友》《甘南碎片》这样的诗作。或许是对人精神层面的关注,其诗借友人之口谈“灵魂”:“从西藏回来的朋友/都谈到了那里的蓝天和雪/谈到灵魂的事儿/仿佛一卷经书就足够了//大大小小的寺/仿佛一盏酥油灯就足够了/大红喇嘛 小红喇嘛 白白的牙/仿佛一碗圣水就足够了/牛的神 羊的神 藏红花的神/鹰的身体替他们飞翔/一句阿嘛呢叭咪哞/就足够了//”。诗有效避免了谈宗教问题可能招致的麻烦,只以“灵魂的事儿”所关联的高原意象反复吟咏绝非那么容易“就足够了”,探究宗教氛围与海拔氧气高度等;《甘南碎片》是诗人行旅与自然妙趣的碎片,由连续性行旅来抒发异域的发现之美。
《娜夜诗选》后,诗人开始关注这种诗歌写作,不刻意回避也不有意写作这种诗歌,陆续写些旅次、宗教氛围和民俗风情的诗作,如《那不楞寺短歌》《在甘南草原》《大悲咒》《青海》《西夏王陵》,这些诗类似速写,但有风俗与时代风貌入诗的味道与痕迹,“街上的藏人少了 集市散了/汉家的格桑花顺着大夏河的流水走远了”,“天堂寺以西/她的小卓玛已经上学/牧区的春风温暖/教室明亮/鹰 在黑板上飞得很高”(《那不楞寺短歌》),旅游擦亮了她善于发现的双眼,在不经意的民俗勾勒中,暗示一种新的民生图;《在甘南草原》写宗教禁忌,“不要随手取走玛呢堆上的石头/或者用相机对准那个为神像点灯的人”“不要试图靠近:一条朝圣路上的鱼/昏暗中苦修的僧人/和他裸露的半个肩膀”(《在甘南草原》)。这些诗弥补了她作为少数民族诗人诗作中民族生活与题材的匮乏,在其诗歌版图中的意义自不待言。娜夜诗作中并不是没有民族意识,其早期诗作《鹿》《鹿恋》等就有这种心理的暗示,“鹿”是作为其神话原型的集体无意识在诗中的遗存。无论早期,还是中后期,“鹿”这一伴随满族人的灵兽,从善良、跳脱、灵性到躲避伤害聪慧的少女,成长为能干的少妇,完成其对世界知性的感悟,一路伴随其诗歌创作。
(二)日常琐屑生活的随意点染与感悟
从《回味爱情》《冰唇》到《娜夜诗选》,娜夜诗作有一特点可说是一以贯之的,即以日常碎屑生活点染入诗,在简短篇幅里有效传达诗人对人生的感悟与思索。如《回味爱情》集的《收割之后》《旧居》《楼上琴声》,《冰唇》集的《英雄乐章》《棉衣外的暖风》,《娜夜诗选》集的《飞雪下的教堂》《沿河散步》《墓园的雪》等,都是诗人从日常琐屑小事寻诗,随意皴染,传达诗人对人生世态的感悟。通过三部诗集,诗人从总体勾勒出从少女到少妇的洁癖、追求完美爱情的过程,其笔下抒情女主人公既聪慧又犀利,狡黠又淑娴,现代又古典。诗人眼光敏锐、洞悉力强,善选裁,知道什么可入诗,什么应舍弃。近年她的一些诗作,似乎有意突破写作范式与藩篱,将大量看起并不具备诗歌抒写题材拟诸笔端,随意性和亲和力有所增强,“句式逐渐由陡峭趋向平缓,语气由跳跃转向娓娓如私语,境界也从品味向更为开阔的感悟展开”[6]。
娜夜以现代女性短诗探索,为满族文学在新世纪赢得了赞誉,获取了尊重,但也应看到,其诗进步缓慢,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逐渐形成特色。她的诗歌既不同于巴音博罗痴守白山黑水,以颂扬努尔哈赤血统的豪迈与阳刚为创作纬度与旨归;也有别于匡文留以西部女性诗游侠祁连沙漠,热烈奔走于灵山秀水间,找寻远古的足迹,在岩画与砂砾中叩寻历史的回音壁,从容袒露女性情感世界。其诗以建构短小精致篇什为趣,细腻温婉,含蓄直接,在“隐藏”与直达中,以清澈纯净的语言,跳脱克制的感情,在空灵与简洁的抒情中,展示现代女性短诗的智慧与厚重,悲悯与苍茫。
参考文献:
[1] 王珂.民族性:浓、淡、无多元相存:论20世纪末期少数民族女诗人现代汉诗的抒情倾向[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2]沈奇.一份简、一份淡、一份空[J]//娜夜的诗.诗选刊,2005(9):61.
[3] 陈仲义.百年新诗百种解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256.
[4]刘强.大入世的爱:读娜夜的诗[J].绿风,2000(5):119.
[5]杨森君.一切往好处想[J].大家,2008(3):54.
[6]唐欣.娜夜诗歌及点评[J].诗选刊,2005:39.
〔责任编辑:王露〕
注释:
①见《诗刊》2009年1期下半月刊《诗人档案》。
②见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授奖评语。
Na Ye’s Poems of the Modern Woman: A New Perspective
of Woman Short Lyrics
ZHOU Jianjun
(SchoolofChineseLiterature,Guizhou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Guiyang550025,Guizhou,China)
Abstract:Na Ye, a Manchu woman poet, bases her lyrics on her daily trivial affairs, constructing a short but delicate and rich, implicit but direct lyric mode. In her 20 years’ career of poetry composition, she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ploring expressional means and techniques of woman short lyrics. In her lyrics, she makes use of limpid and clear words, tripping but restrained feelings to present the wisdom, richness, mercy and boundlessness of modern woman lyrics.
Key words:Na Ye; modern woman; short lyrics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15)05-0047-07
作者简介:周建军(1965-),男,重庆石柱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与现代诗学研究。
基金项目: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校科研2014(09)号)
收稿日期:2015-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