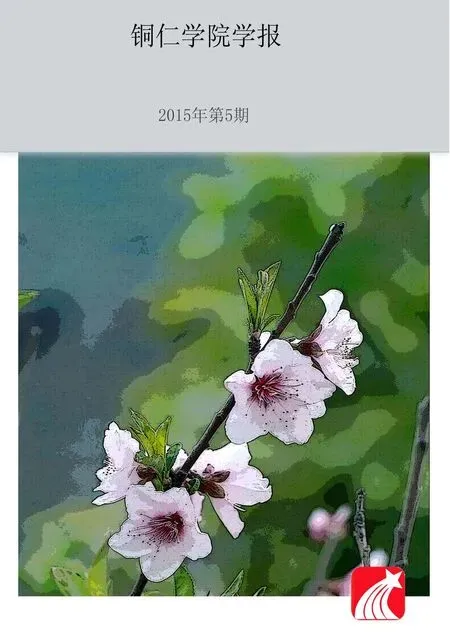透视刘庆邦小说中的底层世界
透视刘庆邦小说中的底层世界
刘庆邦书写的底层世界有残酷的一面,也有充满诗意的一面。作为“底层书写”的代表作家之一,刘庆邦始终将目光对准农村、对准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煤矿,把农民和矿工作为作品的主角,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底层人民生存环境的恶劣,注重抒写他们精神上的困顿,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在苦难重压下导致的人性异化,同时彰显了底层人民在苦难中展现出的人性光辉。
刘庆邦; 底层; 人性
近年来,出身农村的小说家刘庆邦凭借其作品的独特魅力逐渐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其作品主要有小说集《走窑汉》、《家园何处》、《红煤》、《神木》等。出身农民,做过矿工的他,凭借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始终将笔触延伸到农村、矿区等民间底层,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对底层人民表现出深切持久的关怀,奏响了民间底层的人民的乐章。林斤澜曾戏称刘庆邦是不跟潮流的“稀缺动物”。[1]1这一评价使刘庆邦为底层代言的民间立场得到了印证。
一、刘庆邦的民间立场
民间立场,就是到底层世界中去,从民间内部发现民间的意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为人民说话。莫言就直接申明自己的写作是为老百姓的写作,因而“在写作时,没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而是怀有平等的心。”[2]16作家和作品中的人物是在同样的角度和高度,没有高高在上,将自己置身事外,作家本人也没有比读者和故事中的人物优越。以民间作为叙事的对象,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自古以来就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就我国的文学史而言,从《诗经》开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体裁中都有与底层叙事相关的作品。五四时期,鲁迅、沈从文等作家的文学创作更是将这种着眼于民间底层的写作精神推向顶峰。而后的赵树理、莫言、余华也在不同的时代以自己的创作丰富着民间创作领域。由古至今,着眼于民间故事、以底层人民的生活作为创作视角的作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由一股弱小的暗流形成为一股强大的底层文学潮流。一部分当代的作家,在看到弱势群体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所遭遇的苦难后,将其作为自己的写作方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刘庆邦的《神木》、《鞋》,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陈应松的《马斯岭血案》等。“底层书写”,正如南帆所说:“并不是一种异质性的叙述”[3]135,它一直作为一个潜在的传统存在于中国文学的发展长河之中。现如今,以富人形象作为中心的作品不在少数,文学创作底层意识不够深刻。而在这样的潮流之下,有一批作家,能够以底层平凡的生活,宁静质朴的乡村为着眼点,着重社会底层的书写,也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欲望化、庸常化的文坛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之获得了鲜活的生命力,开辟出一番新文学天地,为沉闷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刘庆邦作为底层书写的代表作家之一,其底层写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作为底层书写的作家之一,刘庆邦自觉地把他的注意投向平凡的民间世界,始终关注底层人民生存的尴尬处境和人性的异化,并且擅长体察人物的心理世界,凭其写作让我们感到其中真实。与作家同样生活在大平原的读者,更能够理解小说的语言、人物的情感。什么样的世界才算是“底层世界”?有人说:“‘底层’隐喻着身份卑微、生存空间艰难和生活贫困。”[4]115这一关于底层的定义,是符合社会现实的。“底层”这个词本身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意味着它保有城市所没有的淳朴、善良;而另一方面,与城市的现代化相比较,农村又的确是愚昧落后藏污纳垢的场所。刘庆邦近些年的作品,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写作始终没有超出底层人民的生活范围。作家写作的独特视角和写作立场决定了这样的选材意图和特殊的审美形态,寻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但在爱的环境中成长以及作家自己特殊的人生经历是刘庆邦选取民间立场进行写作的决定性因素。
(一)弥漫在成长记忆中的爱
刘庆邦出生在饥荒年代下的一个农村,常常食不果腹,在他中学辍学后,为了应对生存压力,和乡亲们一起在田间劳作,春种秋收。早年的生活经历对他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曾多次提到:“那块平原,用粮食、用水、也用野菜、树皮和杂草养我到十九岁”[5]2。那里朴实的父老乡亲、河流山川也像血液一样流动在作家的身体里,让他时常记忆起那片土地。正是农村生活,让他饱尝生活的艰辛、让他感动于人间的温暖与爱,这种情感体验让他将笔触延伸到那块让他魂牵梦萦的土地。
(二)特殊的人生经历——矿工生涯
在农村成长的刘庆邦长大之后,走出生养他的故乡,转而成为一名煤矿工人。他工作的场所是一个国营煤矿,九年的煤矿工作经历,不仅积累了他的人生厚度,也让他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农村的世界,这个用煤包裹着的黑暗世界就是中国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刘庆邦以其敏感的内心、敏锐的视角洞察煤矿中矿工的生存状态,借助神来之笔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个中国式的煤矿。在创作的过程中,刘庆邦忠实于内心的声音,所写即所思所见,他的小说质朴而凸显生活的本色,彰显了其创作的底层视角与民间立场。
二、刘庆邦小说文本中民间世界的具体形态
刘庆邦的民间世界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它既包括贫穷落后而又静谧的农村,也涵盖了煤矿这一底层世界。正是容纳万千的民间世界呈现了人间生活的百态,如大观园一般,呈现给我们真实的乡村图景、复杂的人性。
(一)农村
在某些人眼中,农村被认为是藏污纳垢的地方。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也常常被视为愚昧、无知、保守的代名词。农村虽有其不好的一面,而农村的环境又是干净纯洁的,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有着淳朴善良、踏实辛劳的一面。作家刘庆邦既着重对民间人民生存艰辛的书写又兼具对民间纯真感情的显现。刘庆邦对底层生存艰辛的写实是他的一种直面现实、承认现实、再现历史的人生态度。鲁迅曾说:“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6]34刘庆邦无疑是一位真正的勇士。以小说《平原上的歌谣》为例,这部小说描写了20世纪60年代三年饥荒时期,人民与饥饿抗争的故事。在那个公社社员吃大锅饭的年代,文凤楼村的村民们每天的食物由两顿红薯菜汤一顿黑红薯馍减少到两顿清可见底的菜汤,眼见乡村人面临生存的威胁,村里养的一头牛又病死了,村民们围绕着牛的处理问题,各有不同的想法。最后这头牛被埋掉了,饥饿的农民半夜挖出病牛,哄抢牛肉,谁料还没来得及入口,就被公社干部强行要走。为了生存,饥饿难耐的村民们什么都吃,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他们挖野菜、捞水草、啃树皮、吃锅底的糊土渣,拔火罐儿用剩下的有毒面皮在饿极了的孩子眼中也成了天下最好的美味。在饿殍遍野、饥荒成灾的年代,能够生存是每个人最迫切的需要。但是活下去又是极其艰难的,红满的亲娘为了一个红薯馍而让自己的女儿用身体去交换,即使如此,最终也难逃生活的厄运。这让我想到老舍《月牙儿》中的主人公在年纪还小,尚未踏入社会的时候不懂得生存的艰辛,对母亲依靠男人生活的方式极为反感。而当她开始真正为了生存四处奔波,发现生活着实不易,渐渐地理解了母亲,走了母亲的老路。她最终也明白:肚子不饿对底层人来说才是最大的真理。这两部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处,都向我们展现了底层人民生存过程的艰难挣扎,人民生活的窘境。
刘庆邦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既有残酷的一面,又有诗意的一面。谈到这种诗意描写,他在论文随笔《超越现实》中说道,“小说所传达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诗,关注的是人类心灵的历史”[7]12。小说希望通过诗意乡村的描写,再造一个慰藉人们心灵的世界,作家希望通过诗意的呈现进而能影响到现实。以《小呀小姐姐》为例,平路是一个“才坏人”(残疾),“身上背了一座拱桥,只能用细胳膊支撑着尖屁股在院子里走来走去”[8]499,八岁的小姐姐心疼弟弟,背着弟弟去田间感受生命,享受自然的美妙,在弟弟病入膏肓的时候,为了给弟弟捉鱼吃,不幸掉进池塘,淹死在池塘中。而在这短暂的生命中却流露出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和小姐姐对生命的敬畏。当然,这里的诗意乡村也是饱含悲情的。
(二)矿井
刘庆邦不仅善于发现并展现底层的真善美,而且也对人性的假丑恶进行无情的鞭挞。如果说以乡土为题材的小说是柔美小说,那么以煤矿为着眼点的小说堪称是酷烈小说。刘庆邦的矿工生涯为他打开了另一番生存世界的大门。煤矿使他感受到的是炼狱般的世界,因而作家所写的煤矿也是炼狱般的生活场景。煤矿就像鬼门关,漠视着矿工的生命,一旦下井就有死亡的可能,这些都震撼了作家刘庆邦的灵魂。谈起酷烈小说的写作,刘庆邦说过:“我想写生命的状态和人性的丰富、复杂性,所以才写酷烈小说。”[9]357对矿井的分析,笔者将从矿井上的生活和矿井下的生命两方面作论述。
1.无处安放的生命
矿井世界被刘庆邦用“炼狱”一词形容,是十分生动形象的,无论是从它的地域深度还是从煤井环境来看,都是生动形象的。黑暗属于煤矿的矿井世界。这里暗无天日,没有阳光。“窑下到处都是黑的,水是黑的,空气是黑的,空气是死滞的。”[10]16然而矿工工作环境的恶劣与矿下的危险相较就微不足道了。“煤矿井下没有风暴雨雪,呼雷闪电,井下的瓦斯爆炸就是雷电。”[11]125人在自然面前并不是绝对的强者,在不见天日的地底深处采煤,人对未来不可把握,生命随时都有陨落的危险。作家在无数矿难的描写中,在对一个个被煤矿吞噬的生命的描写中,表达了生命价值被漠视的痛苦。
《神木》中,宋金明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故意制造矿难的发生,以死难家属的身份对矿主进行敲诈,这种草菅人命的行径令人发指,也让我们看到生命的不可捉摸和把握。刘庆邦还对矿工的死亡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在《离婚申请》中,“钢丝绳往矿工的脖子抹了过去,他的人头已经落在脚边的煤窝”。[12]1作家将矿难的发生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让我们感到生命是如此易逝,如此脆弱。刘庆邦虽没有对矿难的描写渲染,平淡朴实的矿难描写就足以让人对生命价值的卑微感到痛心。矿难的发生,不仅无情地掠夺了矿工的生命,更是带给矿工家属一生都难以抚平的痛。“它影响和波及着后来者,使后来者心灵和生活变得残缺不全。”[11]3矿工作为家中的顶梁柱,生命的陨落不仅让家庭瞬间陷入困顿,更给家人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晚上十点,一切正常》中,李顺和是国营煤矿的矿工,因国营煤矿经营困难,为了挣钱去小煤窑工作,而在国营煤矿的安全检查笔记上敷衍了事。一次突发的瓦斯爆炸事故,使得很多矿工葬身其中,他的儿子也未能幸免。悲痛之余,儿媳对他由冷漠到断绝来往,小孙子也渐渐地疏远了他,整个家庭气氛也变得不再和睦。老人丧子、女人丧夫、儿子丧父,让死亡的意义更加重大,这是家属无法承受的生命之痛,这种以生命为代价支撑的生活沉重得令人窒息。
2.家园何处的迷惘
较之于矿井之下生命的脆弱,矿井之上的身份认同更加压抑着矿工的内心。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乡差异明显。城市和乡村之间是分割的,差别是巨大的。城市是欲望、权力、金钱、富贵的象征,农村是封闭、愚昧的象征,城乡之间几乎没有交集。改革的春风打开了城市的大门,乡村农民开始背井离乡,奔向城市,或成为矿工,为城市的建设贡献自己力量。“中国矿工是中国农民的另一种形态,矿区多是城乡结合部”[13]76,掺杂着农村和城市的生活习惯。很多矿工都是离开土地、离开田间耕作的农民,有着农民的心态,残留着农民的文化传统。刘庆邦通过塑造这一想进城而又被城市排斥的边缘角色,对生活在城乡交叉地带的矿区里的矿工给予了深情的关注。
刘庆邦的小说中关于身份认同的主题在《月光依旧》、《红煤》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月光依旧》中,叶新荣因丈夫在煤矿工作、是工人的身份感到骄傲,期待着带着孩子来到城里生活,摆脱农村的户口。当她真正来到矿区之后却发现生活的苦处,女儿的就业问题、儿子的上学问题、住所安排等等都成了眼下最基本的困难。没有办法,只好去租住临近村庄的房子。叶新荣认为“她一转就变成城市户口,到附近村里租磨坊住算什么”[14]373,但为了维持生活,她最终重操旧业,在异乡的土地上种植小麦,找到了曾经的感觉。“他们站在两难的位置,只能向农村寻找精神皈依,但又羞于回到农村。”[15]68文本以“我这是在哪里呢?”[14]354结束全文,发人深思。
《红煤》叙述了一个农民出身的临时矿工宋长玉,为了能够转成正式工,处心积虑地追求矿长的女儿,矿长识破他的计划,借故将其开除,而后他复仇的故事。“轮换工和正式工区别是,轮换工不迁户口,不改变原来的户籍。”[16]10宋长玉为了转正,追求矿长女儿,开始给唐丽华写信,他想通过追求唐丽华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设想着一旦成功,“他将彻底告别农村、农民,摇身一变,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宋长玉。”[16]15他是如此地渴望改变自己的身份,摆脱农民身份的束缚。即使后来他获得了金钱和地位,可依然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自卑情结。刘庆邦的小说细致地描绘了社会变革对农民生存方式的冲击,真实地表现了矿工的痛苦与无奈。
3.权力挤压下的人性异变
对于权力的过分迷恋是一种病态的心理,而即使如此,人类还是乐此不疲地追求着权力。与官本位紧密相连的是对权力的尊崇和膜拜。有权就有一切,权力甚至还改变着自己的命运或者他人的命运。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渴望权力,希望用权力保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而当权者总是利用权力对弱势群体施压。矿工生存的窘迫和精神的困境归根到底是没有权力所造成的。
作家首先塑造了一系列滥用权力者的形象。《家属房》中,工会冯主席贪恋矿工家属小艾的美色,以给小艾安排工作为诱饵,满足自己的私欲;《走窑汉》中,矿区书记张清诱奸马海州的妻子小娥;等等。同时,底层人民对权力的觊觎也是作家的着眼点。权力情结使人们费尽心机去获得、争取,在权力的角逐之中,只有少数人是胜者,这一残酷的过程必定有失败者。在权力争夺中败下来的那些人,心理上会经历从希望到绝望的变化,这种极大的心理落差极易导致人性的异化。《红煤》中的孔令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渴望权力,但最终未能实现,他也因此精神错乱而发疯了。与孔令安不同的是,宋长玉在对权力的追逐失败之后,转移方向,离开煤矿,去红煤厂开发一个新的煤矿,自己当老板,实现了名利双收。官本位思想已经扎根于中国人的思想中,宋长玉和孔令安等人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当权者利用权力对矿工进行的精神迫害,也使我们痛心于追逐权力的矿工在追名逐利的过程中的人格异化。
三、刘庆邦底层叙事中的女性世界
刘庆邦小说中有一个底层女性形象系列,其特点更能体现底层世界的另一个层面:诗意乡村。刘庆邦所塑造的底层乡村是诗意的,是脱离生存层面的另外一面。
细读刘庆邦的小说,不难发现,底层女性世界是其小说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无论是单纯美丽的少女还是充满朝气的少妇,抑或是含辛茹苦的母亲,乡村女性的一生几乎被完整地勾勒出来。
刘庆邦笔下的少女形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十岁到十五岁之间的女孩子,因她们长期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笔者把她们称为自然的女儿,主要代表作有《梅妞放羊》;另一类是待嫁闺中的女儿家,她们怀着对爱情的憧憬,用中国式的矜持表达自己的爱情,主要代表作有《鞋》。
《梅妞放羊》是一部农村少女的心灵成长小说,梅妞从小生活在农村,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和小羊在一起,当她看到小羊吃奶的情景,就试想着自己是母亲的模样,模仿母亲的样子给小羊喂奶。“一只手把驸马托抱着,一只手捏着奶往驸马嘴里送奶头。”
[17]2通过这些细节描写,梅妞的母性意识展露得一览无余,一个散发着母性美的女孩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乡村少女的天真无邪在这一片宁静和谐中得到了充分的烘托和渲染。随着女孩的成长,终于到了出嫁的年龄,在对怀春少女的描写过程中,作家为我们呈现了传统的乡村古典爱情。《鞋》中的守明与“那个人”订亲之后,遵循乡间民俗为未婚夫做鞋,从纳鞋底、选花型、做鞋帮儿到最终缝合整个鞋,守明把自己对爱情的美好幻想寄托在一双用心缝制的鞋子里,作家细致地描写了闺中少女爱情的心路历程。
随着时间的流逝,少女渐渐蜕变成少妇。《嫂子和处子》可谓是作家对自设禁地的一次小规模突破,对女性约束的一种松动。这里的规矩,弟媳不能跟大伯子开玩笑,但嫂子可以随便跟弟弟们开玩笑,玩笑开到什么程度都不算过分。民儿与会嫂、二嫂便是这样的关系。嫂子们虽已为人妇,但还没有孩子,这时的女性角色没有冠以“母亲”的沉重头衔,她们便多了份女性的生动和活力,展现了人性中自然的一面。
时光荏苒,乡村的少女也渐渐地转向母亲的角色,对乡村母亲形象的描写,饱含着刘庆邦对母亲的感恩。《平原上的歌谣》是作家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献给母亲的一首赞歌。作家为我们塑造了一位坚韧、勇敢的母亲形象——魏明月失去了丈夫,一个人带着六个孩子在饥饿的年代坚强地活下去,虽然生活贫困,却依然乐观向上;对弱者乐善好施,在某种程度上,她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象征,也是人类真善美的象征。
纵观刘庆邦的女儿国,这些女性形象无论年龄大小,她们身上都有着未被城市文明浸染的朴素自然之美;面对生活的苦难,超然乐观,不向命运屈服。她们是刘庆邦乡间回忆不可缺失的角色,是乡村自然风景的诗意写照。
四、结语
刘庆邦所描绘的底层世界不是单一面孔,有柔软的一面,也有粗劣的一面。简言之:一种是柔美之风,另一种是酷烈之风。以柔美之风为例的作品大多是写农村的,乡村是作家在感受了城市的快节奏、冷漠无情及压力之后开始将自己的灵魂寄托在自己建构的理想化的田园牧歌式的农村,第二种酷烈风格的小说则是对现实的写照,多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的创作。无论是田园牧歌式的农村,抑或是残酷的现实,刘庆邦的每一篇小说都是值得深读的,读他的小说,会让读者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有相似体验的读者会因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而汹涌澎湃着自己的内心,同时又会通过那些逝去年代的往事追忆自己的童年以及曾经难忘的岁月。
刘庆邦的小说一直围绕着人性的主题来展开书写,他的每一篇作品都着重对人性进行思考和探究,既写人性之美,又写人性之丑,通过证美来感受人间的温暖,通过审丑来唤醒人性,达到救赎。无论是人性之美还是人性之丑,都是人性复杂性、多元性的体现,都是真实的社会及现实世界的写照。我们常常说,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这句话已然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最好诠释。文学作品会以生活中的故事作为选材的内容,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呼唤人性之美。
刘庆邦自踏上写作的道路以来,就一直坚持着文学为生活服务的理念。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呼吁有良知的人们关注社会底层,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超越苦难。正如他自己说,“好的小说是一种载体,它轻柔小心地把读者的灵魂引出来。”[18]3的确,刘庆邦的底层写作使人的心灵净化并给人以温暖,让人即使面对苦难也有前行的力量。
[1]林斤澜.吹响自己的唢呐(代序)[M]//民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2]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J].当代作家评论,2002,(1).
[3]南帆.民间的意义[C]//90年代批评文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刘庆邦.老老实实地写[M]//走窑汉.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6]鲁迅.纪念刘和珍君[M]//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7]刘庆邦.超越现实[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8]刘庆邦.小呀小姐姐姐[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
[9]赛妮亚,梁祝.刘庆邦访谈录(代跋)[M]//民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10]刘庆邦.逃不过自己[J].啄木鸟,2004,(8).
[11]刘庆邦.得地独厚[M]//从写恋爱信开始.北京:国际出版社公司,2004.
[12]刘庆邦.离婚申请[M]//河南故事.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13]刘庆邦,夏榆.得地独厚的刘庆邦[J].作家杂志,2000,(11).
[14]刘庆邦.月光依旧[M]//刘庆邦短篇小说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2.
[15]刘伟厚.躲不开的悲剧——试论刘庆邦的矿井小说[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4).
[16]刘庆邦.红煤[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17]刘庆邦.梅妞放羊[M]//响器.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18]刘庆邦.刘庆邦中短篇小说精选[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2.
李继林
(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 )
Perspective Liu Qing Bang’s Bottom World
LI Jilin
( Xi hua Normal University, Literature College, Nan chong, Sichuan 637002, China )
Liu Qing-bang’s bottom world not only has cruel aspect, but also has ideal aspect. As on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of "bottom writing", he always concent rated on the rural areas, the mines between cities and villages. He made the farmer sand miners as the protagonist in his works with delicate style of writing, and depicted the poor living environment of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He focused on describing their mental frustrations, and sharply criticized the alienation of humanity in the cause of their suffering stress, mean while high lighting the people at the bottom in the suffering to show of human glory.
LIU Qing bang, the bottom world, humanity
I207.42
A
1673-9639 (2015) 05-0074-06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田兴斌)
2014-12-03
李继林(1990-),男,河南洛阳人,在读研究生,教育学(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研究方向:中学语文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