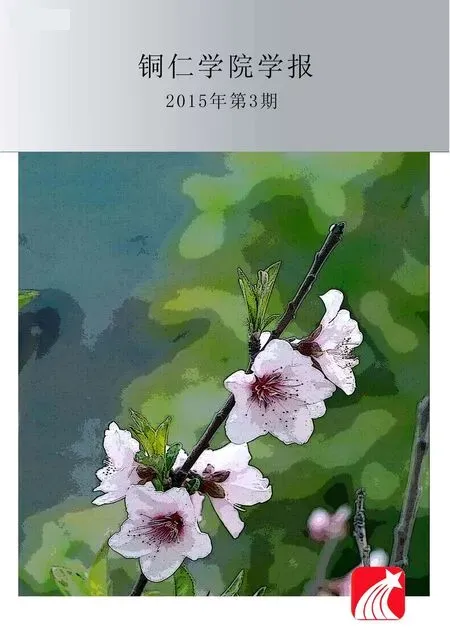读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札记
姜红霞
(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
读陈寅恪《韦庄〈秦妇吟〉校笺》札记
姜红霞
(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
《韦庄〈秦妇吟〉校笺》是陈寅恪先生“以史证诗”释诗方法的代表名篇之一,文章一经问世就在学界掀起了《秦妇吟》研究之风潮。其中不乏学者对陈先生“颇疑‘杨震关’实为‘杨仆关’之讹写”的猜测提出质疑,认为这一猜测与实际地望和行程相矛盾。鉴于此,笔者试图回归《秦妇吟》长诗文本本身,并结合史料,从“秦妇”东奔的时间节点和路线行程两个角度出发来佐证陈寅恪先生猜测的合理性。另外,笔者通过反复吟读《秦妇吟》一诗,较深地感受到这首长诗音韵之和谐、旋律之优美,而诗作诞生的当时,民间就广有流传,并被制为幛子悬挂,作者则被呼为“秦妇吟秀才”,与被称为“长恨歌主”的白居易并称佳话。一首诗歌竟能够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笔者大胆猜测《秦妇吟》或作为歌诗被歌者广为传唱,遂逐渐风靡于民间。
秦妇吟; 杨震关; 地望行程; 歌诗
一、“杨震关”地望考辩兼论“秦妇”东奔之路线
陈寅恪先生在《韦庄〈秦妇吟〉校笺》中颇疑“杨震关”实为“杨仆关”之讹写,他广征史料典籍来佐证自己的这一猜测。对于陈氏的说法,学人颇多涉论,其中不乏质疑者。笔者以为,陈寅恪先生所提供的史料虽然丰赡,但稍嫌不够具体清晰,且陈氏在最后也是以“耶”这一疑问词作结,并非确凿语气。鉴于此,笔者试图回归《秦妇吟》长诗文本本身,从“秦妇”东奔的时间节点和行程路线两个角度来佐证陈寅恪先生猜测的合理性。
陈先生在《韦庄〈秦妇吟〉校笺》论释“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二句曰:
然则杨仆关正在新安之地,与下文‘明朝又过新安东’之句行程地望皆相符合。颇疑‘杨震关’乃‘杨仆关’之讹写,殆由传写者习闻东京之‘关西孔子杨伯起’,而不知有西京之楼船将军,遂少致误耶?[1]122
陈寅恪先生怀疑“杨震关”为“杨仆关”的讹写,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并征引了《汉书·武帝纪》《水经注·洛水篇》《水经注·谷水》《元和郡县图志》几种相关史料,例举了函谷关与新安县的历史沿革与地理位置关系。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函谷关在历史上的地理位置变迁。据《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可知:汉武帝以前,函谷关本汉旧县,属弘农郡,故址在今天河南省灵宝市东北。①①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函谷故关,在县东一里,汉武帝元鼎三年,为杨仆徙关于新安。按:秦函谷关在今陕州灵宝县西南十二里……今县城之东有南北塞垣,杨仆所筑。”卷5,中华书局,1983年,第143页。汉武帝应楼船将军杨仆的请求,徙潼关以东本属弘农郡的函谷关于新安县,距离弘农郡三百里。可见函谷关曾一度被杨仆迁徙于新安县。[2]《元和郡县图志》卷二还记载:
至后汉献帝初平二年,董卓胁帝西幸长安,出函谷关,自此以前,其关并在新安。其后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马超于潼关,则是中间徙于今所。[2]35
这里的“徙于今所”确切位置未有交代,但可以明确的是函谷关被迁徙到了原本所在的潼关附近。自曹魏建安直至韦庄所处的晚唐,函谷关就地处于陕西潼关而非河南新安。根据笔者检索到的相关资料,并未发现有关于徙于新安的函谷关曾被称为“杨仆关”的记载,也不存在其它如“杨仆关”这样的专属名词。至于“杨震关”这一说法也是间接取源于《后汉书·杨震传》中:“关西孔子杨伯起”的故事[3]667。由此看来,“杨仆关”与“杨震关”虽然只是一字之别,却不能就此证明《秦妇吟》之“杨震关”就是“杨仆关”的讹写。当然,在这里,陈寅恪先生也只是据相关史料做出的猜测。
若如陈氏所言,“杨震关”是“杨仆关”的讹写,秦妇于前年“又出杨震关”,即新安县的函谷关(杨仆关),她举头曾在云际间远望“荆山”,此处的荆山(今河南省灵宝县阌乡南)位于距新安近 200公里以外的湖城县,那么秦妇过杨仆关(新安),是不可能看到往西200里之遥的荆山的。
关于这一点,邓小军先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前年又出杨震关’可理解为先总说出关,‘举头云际见荆山’以下再说出关之前经过。此种写法,史籍和唐诗之中,证例甚多。”[4]基于此观点,邓小军先生援引了《史记》《水经注》以及别集中的诸多诗篇来予以说明,得出结论曰:“由上可见,先总说出关,再说出关之前经过,或先说到某地,再说到某地之前经过,这是史籍和唐诗习见写法。”在此,邓老师为“杨震关”为“杨仆关”之讹提供了一个力证。
对于陈寅恪先生猜测“杨震关”为“杨仆关”之讹的第一个理由笔者虽然持有怀疑的态度,然而他提出的第二个理由却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陈氏在文中说:“‘前年又出杨震关’与下文‘明朝又过新安东’之句行程地望皆相符合。”按夏承焘《韦庄年谱》[5]1中和三年癸卯为883年,此年韦庄在洛阳,与“秦妇”偶见。陈先生亦认为“秦妇”从长安东奔洛阳,其行程即端己所亲历,“秦妇”或即为“端己本身之假托”。而据《年谱》和陈氏言,在黄巢血洗长安城的前年(当理解为 882年方可)韦庄就已经离开长安来到了洛阳,即“前年又出杨震关”。又据《年谱》,883年的四月以后,韦庄客游江南,“明朝又过新安东”,新安在洛阳以西,为何在883年三月的“明朝”还要从洛阳折返向西到新安东?
要解释这个困惑,我们首先假定“杨震关”为“杨仆关”的讹写这一猜测成立。秦妇于前年(882年)出关(新安之杨仆关),出关前她一路途径陕州、蒲州,并描述了沿途所见所感,并在“前年”的“明朝”,也就是前年(882年)的翌日她从新安的杨仆关继续向东奔往洛阳,在新安往东行进的路上她偶遇家本东畿县的老翁。笔者认为,这就是陈氏所说的二句之“行程地望皆相符合”的话中之义。这种叙述方式类似于记叙文的倒叙,回溯性的记事手法,由于诗句语言的高度凝练,省略了部分说明性的词语,容易给我们的理解带来困扰。这种用法在《秦妇吟》中不只此处,如诗文前面的“前年庚子腊月五”与后面的“昨日良媒新纳聘”和“昨日官军收赤水”[6]155,此处的“昨日”就是“前年”的昨日,而并非“今年”883年的某个昨日。此外,我们说“杨震关”只有地处新安,秦妇才能在“前年”的“明朝”就到达新安东,如果“杨震关”地处潼关,潼关据新安 200里之遥,秦妇是不可能于一夜之间就抵达新安东的。至此,我们从秦妇东奔洛阳的时间节点的角度亦佐证了“杨震关”确实如陈氏所说的为“杨仆关”之讹。
有必要根据《秦妇吟》全诗的内容来梳理一下“秦妇”的逃亡路线,其在广明元年(880年)至中和癸卯年(883年)的大致行程当为:
长安——含元殿(大明宫丹凤门)——花萼楼(兴庆宫)——城东陌——坡下(霸陵)——霸陵东——骊山——三峰路——金天神(庙前、殿上)——荆山——陕州——蒲津——杨仆关(前年)——新安东(明朝)——更欲东奔——汴路——彭门——宿野——河津——金陵——江南。
可以看出,秦妇的整个东奔路线都是按时间和空间有序展开铺叔的,只有在“杨仆关”一处打乱顺序,回溯倒叙其经历。其中缘由,邓小军先生这样理解:
“前年又出杨震关”,如果是言杨仆关,此下一节便是过渡、是一笔带过,意在引出洛阳。如果是言潼关,则此下一节便成流水帐铺开,效果是似乎京洛两大灾区之间,陕虢新安一带安宁,可以鼎足而三。实际上,此地岌岌可危,哪能安身立命?“见说江南风景异”,“愿君举棹东复东”,只有江南,才是《秦妇吟》安身立命的希望所在。[4]
邓小军先生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笔者还想补充一点:“前年又出杨震关”的前两句诗是“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这里的“东诸侯”可以猜测就是暗指接下来五句所描述的“陕州主帅”和“蒲津主帅”。前面“路旁试问金天神”②这几句诗在《秦妇吟》中的大致位置是:“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前年又出杨震关,举头云际见荆山…明朝又过新安东,路上乞浆逢一翁。”出自马茂元、刘初棠:《〈秦妇吟〉注》。这一部分虽是作者的想象之语,但并非泛泛而谈,而是隐含着深刻寓意的,也就是为下面的暗讽“东诸侯”的苟且偏安的行径作铺垫。这是诗人含而不露的“以微言刺时事”之笔法。他表面上是赞扬陕蒲二州主帅的偃兵守城,实际上是批判和控诉他们逃避现实、置百姓生死而不顾的恶行。所谓“何须责望东诸侯”,借金天神之口讽刺和斥责陕蒲二主帅,而不是“破口而出”式地发泄出来,这也体现出韦庄诗歌继承了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特点。可见,诗人独于此处打乱行程的有序性,实在是有意为之。从这个角度也可以验证陈先生对于“杨震关”乃“杨仆关”讹写的猜测。
至此,笔者以为陈寅恪先生的猜测成立,即“杨震关”确为“杨仆关”之讹写。
二、韦庄自禁《秦妇吟》原因浅析
《秦妇吟》自问世以来即风靡一世,盛况空前,这首长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艺术特色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为中国古代叙事诗树立了一座丰碑。然而这首“不仅超出韦庄《浣花集》中所有的诗,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之作”[7]的佳篇,却厄运难逃。由于政治缘故,韦庄本人晚年即讳言此诗,“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8]51。后来此诗不载于《浣花集》,显然出于作者割爱。致使宋元明清历代徒知其名,不见其诗。至近代,《秦妇吟》写本复出于敦煌石窟。
自陈寅恪先生对韦庄讳言《秦妇吟》的原因作了考证以后,这个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终止,出现了不少关于此问题的相关论述,其范围不出对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适触新朝宫阃之隐情,所以讳莫如深,志希免祸”这一推论的质疑,或者是在陈寅恪先生立论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增损。关于这一点,俞平伯和黄广生两位先生的观点具有普遍代表性,总结如下:
1.兵戈扰攘间,侵凌弱者,惯常之事,军阀尤甚。杨部诸将后蜀新贵,览斯篇一妇人之踪迹,不足惊怪。
2.通篇之严重惨淡气氛,诚恐不为时人所喜,尤其当权者。
3.当日官军之恶甚于黄巢,端己晚节身事伪朝,与王建君臣晤对,其“讳莫如深,志希免祸”。
4.陈氏所论,多取外证,没有从诗的原文中去分析,故前面的“推原”确为不刊之论;后面的“结论”似乎有商榷的地方。[7]9
除了《北梦琐言》这一孤证外,我们还能够依赖的就是《秦妇吟》诗歌文本,其他论据的提出只能是仅供参考的旁证。笔者通过对《秦妇吟》的学习和相关资料的查阅,也在此提出自己关于韦庄自禁《秦妇吟》原因的几点猜测:
其一,韦庄或许认识到了自己对于黄巢农民军起义的偏见。或许是由于当局者迷,韦庄把自己“一从陷贼经三载”的惨痛经历完全归罪于黄巢起义,他借《秦妇吟》历数黄巢“贼军”的罪行,对起义军的暴力作了较为恶毒的歪曲和夸张。然而,自己年轻时看待世事的眼光和评判标准难保到了年老以后有所转变,或许在多年以后重新掌握了史实并经过成熟思考,想弥补自己在诗文中的言语过失,这也可能是他自禁《秦妇吟》的原因之一。
其二,人在经历过残酷的社会灾难、身心受到巨大的创伤以后,性格往往会发生大的改变,特别是随之进入老年,更容易变得畏祸且谨小慎微。更何况这段史实对于亲历过它的韦庄来说就像是一枚被空投下来“导弹”,它虽未致命,却令闻者生畏、生痛。《秦妇吟》所触及的史事涉及到了当时的许多阶层,包括皇权统治阶层、士大夫官僚阶层、农民阶层等等,更令人后怕的是它已经广布于街陌闾巷,即使没有来自于他人的诽谤,韦庄也不会安心。可见,“志希免祸”的韦庄自禁《秦妇吟》以弥谤,此处之“谤”即使不是来自于外界施加的压力,也是来自于韦庄煎熬的内心深处。
三、《秦妇吟》作为歌诗传唱的可能性的探讨
笔者通过反复吟读《秦妇吟》一诗,较深地感受到这首长诗音韵之和谐、旋律之优美,而诗作诞生的当时,民间就广有流传,并被制为幛子悬挂,作者则被呼为“秦妇吟秀才”,与被称为“长恨歌主”的白居易并称佳话。一首诗歌竟能够产生如此深广的影响,笔者以为或许还有其他原因有待挖掘,例如《秦妇吟》作为歌诗被歌者广为传唱,遂风靡于民间。
《秦妇吟》是唐末五代诗人韦庄创作的长诗。这是一首七言歌行。胡应麟谓:“‘五言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赡,极于《木兰》’,使胡氏而获见《秦妇吟》,吾知其必继之曰:‘七言之赡,极于《秦妇吟》。’”这是从古体诗的角度给予《秦妇吟》以高度的评价。有鉴于此,笔者就从晚唐歌诗角度对《秦妇吟》试作分析,或许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把握。
关于《秦妇吟》是否披歌入乐或者是无乐徒歌,这个也较难确定,还是可以从以下两点出发试做探讨。一是《北梦琐言》记载:
尔后公卿颇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为“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诫》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8]51
这里的“幛子”指古代的步障或屏风。一般用来遮蔽风尘或视线。如唐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障子松林静杳冥,凭轩忽若无丹青”。[10]459其中的“障子”是上面题有文字或画有图画的整幅绸布。也有如王维诗《题友人云母障子》[11]2中的“障子”则是美丽的石材制成的屏风。《北梦琐言》中韦庄所深讳的“幛子”很有可能就是前者。据前人记载和今人发掘可证,此诗曾广流民间,人们不但制为“秦妇吟幛子”,甚至是边陲的寺僧、文人们手抄笔录,藏之石室千年留存后世。正如王国维题诗曰:
劫后衣冠感慨深,新词字字动人心。
贵家障子僧家壁,写遍韦郎《秦妇吟》。[12]
《秦妇吟》全诗238句,1666字。白居易的《长恨歌》也不过 840字。这样一篇洋洋洒洒的千言长诗,经一出世就风靡不衰,甚至被制成屏风悬挂于民间屋室内,仅凭诗歌在题材、语言等文学艺术上的魅力就能获此殊荣似乎有些说不通。况且,《秦妇吟》与一般的民歌不同,它的文辞非常典雅优美,虽然是叙事的长诗却不乏诗意文采,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未必能完全消化整篇诗作。我们可以猜测,《秦妇吟》或因受到了当时歌者的传唱,才能够如此深入人心、广播边陲。
吴相洲师曾在《唐诗繁荣原因重述》一文中说到:
将诗歌传播到社会各阶层,除了诗人们直接赠送题写以外,主要得力于三部分人的作用:教师向生徒直接传授,书商抄写贩卖,歌者以歌传诗。其中歌者传播作用最为有效,也最为重要。[13]
这段文字给我们的启示是,《秦妇吟》能够传播于民间,其中最便捷快速的方式莫过于歌者的“以歌传诗”。另外,我们从分析《秦妇吟》的声韵特点来看:“《秦妇吟》是一首七言古诗,这种古体诗的韵律,不像近体诗那样受平仄的限制,比较适合用流水调来读,又加上它是一首有 238句的长诗,所以作者多用收音短促的仄声字来押韵以适应流水调速读的规律,使整首诗读起来琅琅上口,有一唱三叹之妙。在这一点上韦庄完全继承了‘长庆体’的转韵特点,如描写长安城的混乱情况时,从‘扶羸携幼竞相呼’到‘婴儿稚女皆生弃’二十句就换了五次韵,不仅造成了一种流利舒畅的旋律美,并且配合着诗歌内容,还营造出一种扣人心弦的紧张气氛。”[14]28可见,《秦妇吟》音韵和谐、旋律优美的特点也是非常适合入乐的。
前面我们提到,韦庄的《秦妇吟》继承了元白二人的“长庆体”,而“长庆体”就是以《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为代表的叙事风情婉转、语言摇荡多姿、平仄转韵的七言长篇歌行之专用名词。“长庆体”相对固定的题材类型有二:一是通过铺陈某一人的遭遇,以见朝廷政治的得失;二是通过描写某一宫廷苑囿的变迁,以见国运的兴衰,从中寄托对于朝廷的殷忧。《秦妇吟》的题材内容当类于前者。既然与《长恨歌》《琵琶行》《连昌宫词》同为“长庆体”,如果能证明三者都曾“播于坊间”,那么《秦妇吟》的入乐可能性也比较大。唐宣宗《吊白居易》诗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15]160《旧唐书·元稹传》有载:“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16]4333关于元白歌行长诗的入乐情况,吴相洲师曾撰文有专门论述[17]。由此看来,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秦妇吟》入乐的可能性。
回归到《秦妇吟》诗的本身,韦庄在诗歌的最后说:“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关于“歌”的释义,先秦时期典籍不乏载录,如:
《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马融曰:“歌,所以长言诗之意也。”[18]70
《毛诗》释“歌”:“曲合乐曰歌。”[19]365
《礼记·乐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20]1148
以“歌”合乐,歌以长言,“长言”即引长或拉长声音唱。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歌”可以分为两类情况:“无伴奏的人声和有伴奏的配乐均可称之为歌”。当然,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断定《秦妇吟》中的“长歌”就必然是拉长了声音唱,但是综合前面对此诗入乐可能性的分析,或许从侧面可以作为一个佐证。
四、小结
综上,是笔者在研读过《秦妇吟》本诗以及陈寅恪先生的《秦妇吟》校笺后的几点体会。自 1912年王国维先生从敦煌遗书中发现这首长诗至今已有百余年时间了,这期间学界从未间断过对《秦妇吟》的研究,无论是从文献还是文学角度,都收获颇丰。笔者虽怀揣浅陋,也还是斗胆在此把自己的不同见解表达出来。但是由于史料的阙失,有些立论尚停留在猜测和设想的层面,姑且撰文于此,以备就教于方家。
[1] 陈美延,编.寒柳堂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杨震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 邓小军.关于陈寅恪解释《秦妇吟》“前年又出杨震关答问”[EB/OL].http://dxiaojun.blog.sohu.com/172896637. html,2011-5-16
[5] 夏承焘.夏承焘集·第一册·韦端己年谱[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6] 马茂元,刘初棠,校注.《秦妇吟》注[M]//中华活页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 俞平伯.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C]//文史(第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黄广生.韦庄自禁《秦妇吟》原因再析[J].吉林大学学报,1979,(4).
[10] (清)仇兆鳌.杜诗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1] 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2] (清)王国维.王国维诗词笺校[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3] 吴相洲.唐诗繁荣原因重述[J].北京大学学报,2009,(6).
[14] 韦秀芳.韦庄诗歌研究[M].合肥:安徽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3.
[15] (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15)[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6]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66)[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7] 吴相洲.论元白新乐府的创作与歌诗传唱的关系[M]//中国诗歌研究(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
[18] (清)孙星衍,著.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注疏(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 (汉)毛享,撰.(汉)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卷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39)[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Notes on Chen Yinge's “Notes and Proof of Qinfuyin Written by Wei Zhuang”
JIANG Hongxia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
“The notes and proof of Qinfuyin written by Wei Zhuang” is one of Chen Yinge's masterpieces that interprect poems by applying the approach of “Interprecting Poetry by History”. The article had aroused a upsurge in academia since it was published. Some scholars questioned that — Mr. Chen was in much doubt and believed that “Yangpuguan” was mistakenly written to “Yangzhenguan”.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walking direction, they thought there was a contradiction. For this reason, I'm going to get back to the content of the poem itself, to prove its rationality about Chen's guess with the historical records, from the point in time and route which Qin Fu ran to the east. Besides, I read “Qinfuyin” again and again and feel deeply that the rhythm is harmonious and the melody is exquisite. However, the long poem was widely circulated among people when it was born. I'll venture to guess that maybe “Qinfuyin” was widely sung among many singers as a poem, 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and then it had gradually swept over the fork.
Qinfuyin, Yangzhenguan, geographic position and walking direction, song-poem
I207.22
A
1673-9639 (2015) 03-0120-06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白俊骞)(英文编辑 宋志勤)
2014-11-24
姜红霞(1987-),女,汉族,吉林长春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唐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