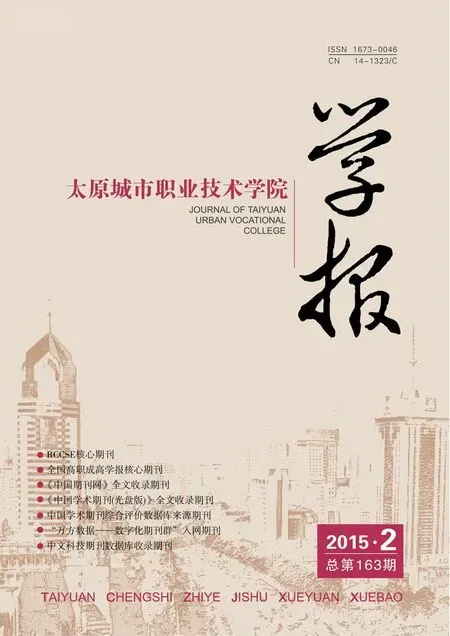试论《柠檬》的无意识自我
汪艳
(广州私立华联大学,广东广州510660)
试论《柠檬》的无意识自我
汪艳
(广州私立华联大学,广东广州510660)
井文学堪称以病人为视角的文学,代表作《柠檬》描写了一个宿疾缠身的青年形象,表现主人翁的一些心境变化,因此文章一直被认为是心境小说或是具有自传性质的私小说。本文运用精神分析批评理论,对作品中主人翁的矛盾行为进行分析,厘清文本中主人翁的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行为,准确把握作者的心理结构和创作历程,最终得出《柠檬》表面上看是一篇传记性质的心境小说,实际上却是通过作品设定人物的矛盾纠结的神经质行为,表达作者对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抵触排斥以及对于回归日本传统社会和文化的肯定和期望。
柠檬;意识;无意识;潜意识
一、先行研究
二、本论
(一)意识层面的“自我”
小说中这样写到:“我”被“莫名的不祥之感”所累,如整日宿醉,说不清是焦躁还是厌烦,总的感觉是“空虚”“难耐”,让“我”坐卧不安,好像某种东西在“驱赶”,使“我”不得不终日徘徊于大街小巷。喜好的东西也发生了改变。现在的“我”喜欢上了破旧凌乱的街市,喜欢上了廉价不值钱的烟花以及充满童年回忆的玻璃弹珠。因为“我需要一点奢侈的东西,挑动我那死气沉沉的触角”,“这种东西能在无形中安抚我的灵魂”。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破旧的街市,廉价的烟花以及玻璃弹珠对于“我”来说,为什么具有安抚灵魂的作用?“我”内心深处究竟需求些什么?它们与“我”喜欢的破旧的街市、廉价的烟花、玻璃弹珠有什么关系?
(二)冲动的无意识
为了摆脱长期积压在“我”体内的空虚、焦灼之感,“我”做了一件有悖于常理的“不可思议”的事情——把柠檬放置于丸善的书店里,幻想这颗“柠檬炸弹”能把“令人喘不过气来的丸善”炸得粉碎。这一有悖常理的出格行为与“我”一贯崇尚的奢侈作风非常不符,表明了“我”的无意识心理在某个瞬间一定程度上挣脱了理性意识的禁锢,不受意识层面的“自我”约束,表现出一种不合常理的诡异状态。当然,这种不合常理的行为表现与“我”日思夜想的一种潜意识活动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无意识本身是一种本能冲动,它毫无理性,一团混沌。“我”把柠檬幻想成一颗金灿灿的炸弹,想借此来粉粹丸善,这本身就属于一种匪夷所思的冲动行为,与“我”一贯崇尚追求的以“丸善”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非常不符。因此,从表面看来,这种借“柠檬”来粉粹丸善的冲动行为完全是无理解、无理性的。然而事实上可以说,无意识又是我们每个人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暗中支配着我们的意志行为,是决定人的行为和愿望的内在动力。“我”的一种长期的空虚、焦灼之感,偶然间通过“柠檬”一下子得以纾解。“在我握着柠檬的时候,我感到那一直积压在我心中的不祥之兆,竟松弛下来”。柠檬的芳香使“我”的热血朝上奔腾,让“我”体内的元气复苏。那样执拗的忧郁,竟然会一下子被这么一个小东西所化解。“我”不禁感叹:人的心灵,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精神分析理论,如果说意识是处于大脑表层的“我”所直接感知到的“焦躁”“厌烦”“无奈”之感,而无意识是处于大脑底层的我们平时所无法感知的一种本能冲动。譬如“我”把柠檬幻想成炸弹,想借此来粉粹丸善的匪夷所思的冲动行为,那么潜意识就可以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可以通过集中注意力或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回忆起来的一种过去的经验感受。过去的经验,感受是什么?“我”的内心真正追求的是什么?在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我”所直接感知并表现出来的意识心理层面状态以及冲动出格的行为心理的内在成因,分析总结文中“我”的潜意识心理状态和真实的内心追求,以便达到解析文本的最终目的。
(三)寻觅潜意识
“我”作为一个宿疾缠身、穷困潦倒,且终日无所事事的青年,看到周围人忙于工作学习而感到格外“空虚”“难耐”,又因生活落魄穷困使“我”焦灼,坐卧不安,这些都是文中描写出的“我”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心理层面状态。这种“空虚”“焦灼”“难耐”的心理状态,有一天偶然间通过一颗柠檬得以纾解。“我”幻想着柠檬是一颗金灿灿的炸弹,希望它能把自己一直以来自以为中意追求的西方文明的代表——丸善炸得粉粹,呈现给我们读者一种无理解、无理性的本能冲动。在此,我们借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重点分析文中“我”的这种冲动出格的无意识行为是由于怎样的潜意识心理活动而促成的。
应该说,作为一个宿疾缠身、穷困潦倒的青年患者,经历了经济落魄前后的生活状况的巨大反差对比,更容易引起对于之前无暇顾及的过去美好生活的回忆,看待问题也更加理性、客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更需要借助于一些回忆,幻想和错觉来消解这种“空虚”、迷茫。事实也确实如此。现在的“我”,感觉更喜欢那些破旧的街市,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之前的那种对于西方文物的喜好与追求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已经算是一种豪华与奢侈,跟“我”现在的经济窘迫的状况不符。在“我”看来,现在的“我”反而是跟那些破旧的街市更加吻合贴切,从中“我”可以“找到一丝亲近感”,相比“冷漠的繁华大道”,这种常年被风雨腐蚀的土墙裂瓦更能让“我”感到亲切,寻找到一种归属感。
事实上,“我”并没有因为这种寒酸破旧的场景而完全迷失与自弃,它们也并没有完全给“我”颓废荒凉的感觉。相反,“我”总能在其背后发现令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残垣断瓦之后能发现长得气势蓬勃的向日葵或是美人蕉。它们固然不是那么高贵美丽,却能在任何恶劣环境中努力生长,这正是切合了现实中的“我”潜意识中一直孜孜以求的东西——宿疾缠身但从不放弃,穷困潦倒仍有所追求。并且“我”总是陶醉于这种错觉当中,希望能够逃离京都,去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城镇,能有“空旷的旅馆、干净的坐垫、香味扑鼻的蚊帐以及浆的笔挺的浴衣”,这种似曾相识的画面描写,真正表达出“我”在潜意识当中对于过去传统生活方式的怀念与向往。
廉价的烟花与玻璃弹珠同样是此时“我”所喜欢的,喜欢玻璃珠那“幽幽的,清爽的,诗情画意”的味道,它能轻易地把“我”带回到“小时候偷偷含在嘴里而遭父母责骂”的充满甜美回忆的童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父母健在,生活无忧,更是“我”潜意识中最珍视,也最希望保留的东西。“我”的这种喜好与感悟的变化,正是得益于生病以后由于经济落魄所带来的生活的巨大反差,能够让“我”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待之前一直追求崇尚的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代表——丸善。现在的丸善在“我”眼中已变成“一个沉重郁闷的场所”,“书籍,学生,收款处,在我眼中都像是一群讨债鬼”,令“我”“焦灼,难耐,唯恐避之不及”,最终致使“我”幻想藉由一颗金灿灿的柠檬炸弹来摧毁它。
综上所述,通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分析《柠檬》文本,最终我们得出:文本中的“我”从不同层面呈现给读者三种不同形象:一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意识层面的“我”:焦灼,难耐,空虚,郁闷,终日坐立不安;二是无意识的冲动所表现出来的“本我”状态:希望通过柠檬炸弹摧毁丸善,摆脱西方工业文明的束缚,实现自我;三是文中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潜意识的自我追求。通过分析意识和无意识层面“我”的种种心态和行为,最终我们得出:实际生活中“我”的宿疾缠身的病体和经济窘迫的现实变化,致使“我”在潜意识中对于西方工业文明和日本传统文明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估,表现出对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排斥和对于日本传统文明社会的向往与眷念。可以说,《柠檬》在追求“生”的能量以及自我认同的同时,也明确体现出了作者的价值取向,即希望回归日本传统文明社会,实现自我。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王先霈.文艺心理学读本[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I106
A
1673-0046(2015)2-019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