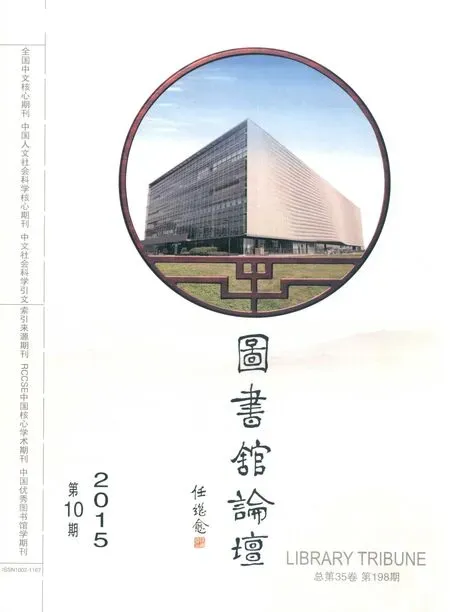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到《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
徐雁
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到《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
徐雁
文章依据有关史料,梳理了缪荃孙学识结构的来源及其师承,其助编张之洞《书目答问》以及获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学术机缘,指出柳诒徵继承了缪荃孙的目录之学,并鼓励和成全了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的编写,对于深化缪荃孙学术生平和《书目答问》的读者接受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迪性。
缪荃孙 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补正
关于《书目答问》的编撰者,历来有缪荃孙(1844-1919年)助理张之洞(1837-1909年)成书之说,但孰为主,孰为次,由于当事人先后在20世纪初过世,而历史记事又语焉不详,遂成扑朔迷离之势,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谜案。
比较典型的说法,如冯天瑜、何晓明在《张之洞评传》第八章中所说:
《书目答问》(不分卷),完成于光绪元年(1875)四川学政任上,光绪二年(1876)初刻本即广为流行。光绪三年(1877)重加勘定,在京师为诸生授读。光绪五年(1879)贵阳王秉恩刊刻本增补二百多处,为较善之本。《书目答问》究竟是张之洞自撰,还是由目录学家缪荃孙执笔,素有争议。民初学者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范在跋中称:“张氏《书目答问》,出缪筱珊先生手,见《艺风堂自订年谱》。”柳诒徵为《书目答问补正》作序,亦称:“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这类说法的根据是缪荃孙本人,他在《艺风老人年谱》中说:“光绪元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但缪氏《丰岩厂所见书目序》却别有讲论:“同治甲戊,南皮师相督四川学,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棠)督署,随同助理。”若依此说,则张为《书目答问》著者,缪为协助者[1]。
本文将通过梳理缪荃孙学问结构的基本来路,以见他何以能够襄助张之洞编纂《书目答问》,以及《书目答问》一书的目录学授受源流。
1 缪荃孙学识结构的奠基及其师承
缪荃孙出生于江阴申港镇缪家村祖居西宅,这是一个家有四橱藏书的官宦之家。他幼沐书香,庭承家学,发蒙后获读经、史、子部书籍。他的曾祖父、祖父均为知县、知州级的清廷命官,其父在获得举人学衔后,入过幕,做过贵州候补道。纵观缪荃孙的一生,在其求学之路上,除了个人勤奋努力外,名师的教导,名宦的提携,都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以官宦为价值本位的封建专制社会中,他对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似不甚满意。他晚年在《艺风老人年谱》的“引言”中曾表示:“荃孙幼罹兵燹,长守冷官,蕉萃邅迍,无可纪录。惟是身历十六省,著书二百卷。一生踪迹,略志雪鸿,不足质诸大雅。”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才5岁的缪荃孙在母亲的教导下,已识字数千,能诵其母口授的唐人小诗。次年入私塾,先后从其族祖、岁贡生缪以康先生及族兄缪墀先生,接受启蒙教育。次年,即缪氏七岁时,他随母归宁省亲,得到掌教山东兖州书院的外祖父瞿绍邦先生的好评:“是子口齿清,记性好,或能绍书香也。”8岁时,读毕《四书》,然后开读经书。次年,学作诗。至11岁,《五经》读毕,开始诵读《周礼》《仪礼》。12岁时,从族叔缪重熙先生,学习科举应试诗文。两年后,又从吴表兄学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及“唐宋八大家”文章。从这年岁起,开始喜欢随意翻阅家藏四橱旧书。十五六岁阶段,先后读《文选》《说文解字》。
咸丰十年(1860年),也即缪荃孙17岁时,为躲避太平军蹂躏江阴的战火,他侍继母渡江逃难到淮安,就学于丽正书院,师从“气平心细,识见明确”(汪廷珍语)的清代校勘学家丁晏先生(1794-1875年),学习文字、训诂和音韵知识。21岁时,缪荃孙奉继母到四川华阳依其父,得以师从“常州派”骈文家汤成彦先生(1811-1868年)、双流宋玉棫先生研习经史之学,考订古文字。
据《艺风老人年谱》的记述,长他10岁的知名学者、藏书家李文田先生(1834-1895年),是缪荃孙24岁时以“寄籍生”身份参加四川乡试的“座师”(主考官)之一,时为同治六年(1867年)。次年,他进京参加会试,还在京师循例拜谒了李先生。大概正是此行获得指点,他对古书收藏和目录版本学发生了兴趣,“始收书为目录之学,是时书直尚贱也”。田柳在提交给中国图书馆学会、江苏省图书馆学会与江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缪荃孙学术研讨会(1997年11月8-9日,江苏江阴)”的论文《缪荃孙对故乡江阴的情愫》中指出:“特别是李文田,既是藏书家,又是版本目录学家,对舆地学也极有研究。李启发他从事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缪荃孙在一批学有专长的名流引导下,博览群籍,研究文史,开始踏入学问这个殿堂的大门。经过几年努力,缪荃孙学业大进……纵观缪荃孙的一生,实际上他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和成就而名垂青史的。”[2]
李文田,字畲光、仲约,号若农、芍农,广东顺德均安上村人,卒谥“文诚”。咸丰九年(1859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武英殿撰修,官至礼部右侍郎。工书,善画。在公务之余,治学不倦,学问渊博。精通经、史、兵法、天文、地理,对蒙古史、地及明季野史尤其关注,旁及西政书籍。1874年乞归,主讲于广州凤山、应元书院。在广州城西多宝坊筑两层书楼,以所藏秦代泰山石刻旧拓及汉华岳庙碑宋拓本,命名为“泰华楼”。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西游录注》《塞北路程考》《和林金石录》《双溪醉隐集笺》《四朝书刻纸版考》等。据曾造访其位于京师北半截胡同官邸的叶昌炽(1849-1917年)说:“几榻之外惟图籍,列椟数十,皆启其钥。手题书签,长至尺许,下垂如帘,甲乙纵横,密于栉比。”[3]徐绍棨(1879-1948年)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其“精于目录学”的治学特点,说他任职京师时,备有一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简端即分录孙星衍廉石居所记、邵懿辰所标注、缪荃孙所校订诸语,颇为详备,原著今犹可见”[4]。李渊源在《李文诚公行状》中说:“凡《四库》所未收而有关考据者,亦莫不藏焉。”伦明(1875-1944年)则是在1929年始得观其所遗藏书的。他发现:“每书衣皆有题识,辨证书中得失无不精切,不似他藏书家但记得书岁月、板刻源流也。”[5]
同治七年(1868年)夏,吴棠任四川总督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惠民政策。除了招收10余名苏州昆曲艺人到成都江南会馆建立“舒颐班”外,他还创办了四川官书局,25岁的缪氏因而被分派入局。据《艺风老人自订年谱》记载:“(同治)七年,戊辰……八月,吴勤惠公师(即吴棠——引用者注)到川督任,派书局,校刻《朱子全书》。与刻书人作缘始于此。……八年,己巳,年廿六岁。在成都书局,刻《八家文》、《方望溪文选》,刻殿版《汉书》。与嘉兴钱徐山年丈宝生、张道生同年同事。”也正是从这两年开始,他与刻书业结上了缘。
在四川期间,缪荃孙还做过目录学家、藏书家,时任川东道的姚觐元(?—约1902年)幕僚,得以游历川东北各地,搜拓石刻。姚氏字彦侍,又作念慈,浙江归安(吴兴)人。幼承家学,博览古书,“尤精于声训诂,故搜采独多,皆世间不传之本。勇于流布古籍,又虚怀博访,往往从故家藏本及通人写本辗转録好古之士,有终身求之不得者”。
2 助编《书目答问》的学术机缘与获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
同治十三年(1874年),督学四川才一年的张之洞鉴于蜀中士风颓废,便大力整治科举积弊,牅启后进。他认为:“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为此专门创办了尊经书院,延请宿儒名家担任主讲教师,讲习经世致用的“实学”,及训诂、考据、古文、诗词等[6]。
鉴于院中有好学者请教他“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张之洞产生了编撰一部推荐导读书目的想法,以期为生童们指明读书的范畴和进学的方向。吴总督听说后,便把在书目之学上有一技之长的缪荃孙推荐给张学政做其学术助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缪氏在《半岩厂所见书目序》的开篇中,记述了当年张之洞给予他的一次重要学术指点:
同治甲戌(1874年),南皮师相督四川学,诸生好古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者为善?谋所以嘉惠蜀士,并以普及天下学人,于是有《书目答问》之编。荃孙时馆吴勤惠公(棠)督署,随同助理。谈次,偶及位西先生是书,师相推为淹雅闳通,如数家珍,当时惜未传录,否则出诸箧中。按图索骥,数日事耳,不似如今考及两月,尚未惬新贵当也。
光绪丙子(1876年),赴计车,见诸黄再同同年所,大喜捧归,觅人录副,小小讹脱,见即订正,并就所见书目,添注眉头。藏诸箧中,以作枕秘[7]。
据缪氏《艺风老人自订年谱》云:“光绪元年(1875年),年三十二,八月,执贽张孝达先生门下,命撰《书目答问》四卷。”可见缪氏在接受《书目答问》编纂助理后,张之洞曾与他进行过多次讨论。
当年9月,《书目答问略例》定稿。张之洞在其中提出:“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为分别条流,慎择约举,视其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于其中详分子目,以便类求。一类之中,复以义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时代,令其门径秩然,缓急易见。凡所著录,并是要典雅记,各适其用。总期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惘眩惑而已。”
《书目答问略例》定稿后,缪氏开始赴富顺,游览苏东坡早年曾前往读书的中岩千佛洞。12月到重庆,入住姚觐元川东道官舍。12月29日,张之洞在致潘祖荫(1830-1890年)的信中推荐缪氏道:“缪筱珊孝廉……今秋回省城,数相过从。其人警敏非常,淹博好古,目前江东之秀,殆罕其匹,充其所造,殊未可量。”
光绪二年(1876年)二月廿一日,缪荃孙至京师参加进士试,四月榜发得中第31名,再参殿试获二甲第125名。以庶吉士留京。在此期间,他终于借得其举人同年黄再同(1849—1891年)所藏的邵氏《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传抄本,录得一部,从此“寝馈其中”四十年。
邵懿辰(1810-1861年),字位西,清仁和(今杭州)人。道光十一年(1831年)举人,历授内阁中书、户部主事,迁刑部员外郎。咸丰三年(1853年)被贬山东济宁,次年革职后返乡,家居著述。在居官京师期间,他购书极多,命名藏书处为“半岩庐”。于书斋案头置备有一部乾隆间四库馆臣编刊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遇所见宋、元旧刊本,抄本,珍秘之本,以及少许认为足资参考而《四库全书》未予收录之书,即注记于各条书名之下,以备校勘之助。该书稿后被其友人借阅录副,嗜书者相互传抄,遂以抄本形式流传士林。
宣统三年(1911年),邵章以胡念修抄清本校正付刊,始定书名为《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附录有《善本书跋及其他》《四库未传本书目》《东国(日本、朝鲜)书目》。缪荃孙称誉并推荐之道:“此书通行后,何啻得千百导师于家塾,而保全旧学,不致湮没于尘埃,流失于外域。旧学绝续之交,岂非绝大关系之事哉!”
《书目答问》于光绪二年(1876年)完成初稿。张之洞特别说明,此编为告语生童而设,“非是著述”,“此编所录,其原书为修《四库》书时所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八”。由此可知,《书目答问》特别重视版本的优劣善否,基于张氏当年所见邵懿辰标注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传抄本,显然,邵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对于《书目答问》的编纂主旨和体例产生了一定影响。
《书目答问》以经、史、子、集、丛书五部为大类,部下又分小类、子目若干,突破了我国长期沿用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系。也就是说,重点收录了乾嘉以来问世的约2200种新著,又于各书下注明卷数、作者、通行易得本等,间有简明按语,指示读书门径,体现了与时俱进、不断革新的学术观,显然,这一基本指导思想应该来自远较缪氏见多识广的张之洞高屋建瓴的要求。
综上所述,缪荃孙的人生,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家学滋养、名师指点、贵人提携的成才特点。终其一生,缪氏获得了藏书家、校勘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教育家及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等尊贵的社会地位,而这些成就的取得,又与他能够凭借聪颖天资,孜孜不倦地不断努力分不开。但成才、成名后的缪荃孙,在目录学界又发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 柳诒徵继承了缪荃孙的目录学,并成全了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
光绪二十年(1894年),缪荃孙担任南京钟山书院山长,兼掌常州龙城书院。1901年任江楚编译局总纂。正是在此年秋,他在镇江接见了柳诒徵(1880-1956年),并把他推荐给了张之洞。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钟山书院改为江南高等学堂,缪氏担任学堂监督。“癸卯学制”实施后,两江总督府拟在江宁筹办一所师范大学堂,以掌学务全局,缪氏被任命为学堂总稽查,负责筹建具有江南最高学府性质的“三江师范学堂”。两年后,受张之洞派遣,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七位教员组团赴日本东京、京都等地考察教育,参观学校。回国后,仿日本东京大学规制,在南京国子监旧址建筑校舍,并将“三江师范学堂”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至1915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成为南京大学近代校史之开端)。
柳诒徵在南京江楚编译局从事编译工作期间,以及在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时获缪翁的指导。据柳曾符教授说,在日本参访期间,缪氏一行听了许多日本专家的报告,加以记录后编印了《日游汇编》一书。“此书虽由缪先生具名,但缪先生不掠先祖著作之美”,特命其祖父在扉页上题写书名“日游汇编”四字,下署“柳诒徵”[8]。由此细节可知,缪翁意在昭示自己仅是基于“职务行为”而挂名为“编者”,这体现了对该书“实际编撰人”柳诒徵的承认和尊重。此时,距缪荃孙当年受命于张之洞编撰《书目答问》已有27年。
柳氏于1927年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当他得知范希曾(1899—1930年)“广勼公、私书目,时时札劄记于《书目答问》上、下方,朱墨狼藉,盖以之为问学之基”时,便邀他入馆编修《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同时鼓励并支持他从事《书目答问》的补正工作。1931年初夏,他在《书目答问补正》的序言中说:
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叶郋园氏亟称之。第其书断自乙亥,阅五十余年,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概未获载,故在光绪初足为学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则病其漏略矣。郋园批校增辑之三、四本未印行,江氏笺补亦不广。希曾所辑最后而较备,虽亦有限于见闻,或浏览虽及而未暇胪写者,要已可备俭学之检阅。艺风之传,倘赖以益广乎!
《书目答问补正》纠正了《书目答问》旧存的“四误”(书名之误、卷数之误、作者之误、版本之误);增补了原著漏记的书籍版本,添加了光绪二年(1876年)至1930年的新刊本;补收了一些和原书性质相近的书,其中大多数是后出的书。经过这一番学术条理,其内容更为充实、完善,成为一部适应于时代需求的学术要籍书目。
4 结语
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到《书目答问》再到《书目答问补正》,为学术界提供了中国目录学史上的一个生动案例,让我们得以具体而微地看到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术源流关系。
最后需要补充的一条史料,是柳诒徵(1880-1956年)之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柳曾符(1932 -2005年)的回忆。他说:
人传《书目答问》是缪荃孙代张之洞所作,从来研究的人很多。祖父当然更注意。1955年2月,缪先生的族人缪子彬来上海南昌路356号家中,给祖父看缪先生的手札,其中有一封与盛宣怀的信,提及编《书目答问》事,证明此书确系缪先生完全代作。那时缪正在上海帮盛宣怀编《愚斋藏书目》,中有一段说:“荃孙自同治甲戌(1874年,此年缪先生年四十一,张之洞年四十八)为张文襄《书目答问》一手经理,近南阳学部图书馆均有同志帮忙,荃孙止总大纲,专注善本,现在无一书不过目,无一字不自撰,直与办《书目答问》一样。”先祖急将此札摘录[9]。
若按缪氏“一手经理”之说,则也即柳氏所谓“完全代作”之意也。难怪他在《书目答问补正》的序言中要言之凿凿地说:“文襄之书,故缪艺风师代撰也。”录此存照,以供方家再研讨。
[1]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214.
[2]田柳.缪荃孙对故乡江阴的情愫[C]//缪荃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江苏省图书馆学会,1998:205-206.
[3]叶昌炽.藏书纪事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07.
[4][5]徐雁,谭华军.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230.
[6]周询.蜀海丛谈[M].成都:巴蜀书社,1986:187-191.
[7]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M].邵章,续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首.
[8][9]柳曾符.君子之道——我所知道的缪荃孙先生[C]//缪荃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江苏省图书馆学会,1998:191-192.
From Simplified Annotated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 to Q&A about Book List and the Supplement and Correction of Q&A about Book List
XU Yan
Based on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this paper tells the origi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MIAO Quansun’s knowledge structure,his academic opportunities to assist ZHANG Zhi-dong in editing Q&A about Book List(Shu Mu Da Wen)and to transcribe Simplified Annotated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Si Ku Jian Ming Mu Lu Biao Zhu).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LIU Yi-zheng inherits MIAO Quan-sun’s bibliographical theory and encourages FAN Xi zeng to fulfill the Supplement and Correction of Q&A about Book List(Shu Mu Da Wen Bu Zheng),which gives some enlightenment on the deep study of Miao MIAO Quan-sun’s academic life and the acceptance history of Q&A about Book List(Shu Mu Da Wen).
MIAO Quan-sun;Simplified Annotated Catalogue of Complete Library in the Four Branches of Literature;Q&A about Book List;Supplement and Correction of Q&A about Book List
格式 徐雁.从《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到《书目答问》《书目答问补正》[J].图书馆论坛,2015(10):102-106.
徐雁,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
2015-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