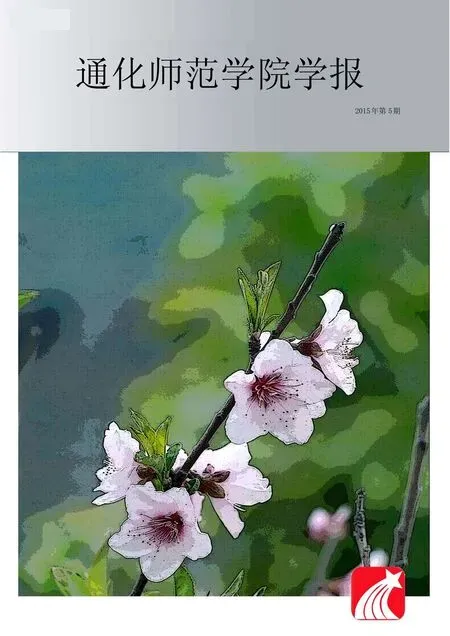选择性执法存在的必然性、弊病及其规制路径
胡晓玲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选择性执法存在的必然性、弊病及其规制路径
胡晓玲
(西北政法大学 行政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3)
选择性执法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执法方式,源于法律规范的先天不足以及执法资源有限性的约束,其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不法平等”的抗辩是不能成为拒绝选择性执法的理由的,出于不当动机被异化掉的选择性执法存在着诸多弊病,亟需从遵循程序规则,制定裁量基准,合理配置执法资源,塑造法治行政观,培育行政伦理观等层面予以综合规制。
选择性执法;不法平等;裁量基准;规制
近年来,“选择性执法”一词屡见各类媒体报端,如在城管执法、污染治理、食品安全、酒后查驾、制止行人“中国式”过马路等事例上常可窥见该词,并且其在报道中多为被批评的对象,坊间对其给予的也多是否定性评价。毋庸置疑,情绪的宣泄是必要的,但如果只限于感性而不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仍不免陷入浅薄的窠臼,理论亟需对此给予必要的关注,且提供一定层次的智识支持。
事实上,“选择性执法”一词,最开始出现在美国法律中,其多被用于警察执法及相关业务事项上,英文名为“Selective law Enforcement”,某些地方也用“Discriminative enforcement”加以指称。就其内涵而言,其并不属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或者说,它是归属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之列,就学界研究现状来看,其也尚未被给予一个广泛采纳的定义。就形成的共识来看,一般而言,它多指执法主体在执法中具有高度的主观性,发挥有极大的裁量能动性,可以选择不同的对象进行执法,或者对不同的执法对象在执法过程中采取不同的标准加以区别对待,如执行时间、执行空间、执行手段、执行强度以及认定哪些行为属于执法的范围,甚至包括是否要采取执法行动等等,其根本特性就是基于一定的因素或者现实需求,而在具体执法中对执法的有关指标加以取舍,对执法对象给予差别对待,概念中冠以的“选择”,恰是一种并不一视同仁,而对之采用不同判断机制的精准描述。从该词观之,“选择性执法”应是一“中性”概念,而绝非贬义用语。实务中,舆论以及媒体一边倒的批判,可能是和“discriminative”一词的翻译有关,该词有“差异化”和“歧视”两种含义,对其只理解为歧视是有失公允的。
作为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并被广泛运用的一种典型执法现象,选择性执法有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基于篇幅以及笔者的关注兴趣点,下文集中于其存在的必然性及其内在弊病及消解策略,因为这属于实务中迫切需要给予理论关注的问题,而对“不法平等”抗辩理由的拒绝也为现实中的执法困境提供了理论依据。无疑,本文的写作具有充分的现实针对性,而这或许也体现出本文写作的价值。
一、选择性执法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选择性执法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根源于某些不可消弭的客观因素的制约,而这必然导致选择性执法一定会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能做的只能是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在个案执法过程中将选择性执法的一些弊病和问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笔者以为,影响选择性执法存在的客观因素至少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法律规范的盲区及其模糊性涵义的存在
我国属于典型性的大陆法系国家,而大陆法系一般主要是借助于成文法来规制社会关系,协调解决各种现实矛盾。可以说,白纸黑字表述出来的成文法条款可以刚性调整诸多社会关系。然而社会生活并不是整齐划一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不能被法条所完全囊括;更为重要的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字面上的法律从其制定之初就内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比如其注重适用对象的普遍性而往往忽视个案的特殊性,制定出来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有未被规定的漏洞和法治盲区。比如法律自制定后没有被及时修改而带来的僵化滞后的存在,而且就制定出来的法律而言,其语言本身也存在着模糊性及被多种解释的可能。此外,立法上还有大量的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及空白条款的普遍存在,这些都导致成文法并不能够完全适应社会生活衍生的各种需求,只能依靠执法者依据一定的因素进行自由裁量,这必然会催生选择性执法的出现。可以说,法律规范的先天不足为选择性执法的诞生留下了生长的空间和土壤。
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在当下正处于一种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各种矛盾纷纷涌现,风险社会带来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在需要迅捷灵活处理的同时,也导致了行政权的普遍扩张。法律之稳固性和行政事务之多变性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使得自由裁量不可避免地在执法实践中被大量运用,现实需要执法者根据个案之需求做出更富于人文情怀的决策。那么,究竟何为自由裁量权呢?德国的毛雷尔先生对此有言曰,“自由裁量权是法律赋予行政主体可以选择的权力,是指行政机关处理同一事实或事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1]125从以上表述可以看出,自由裁量权具有高度的主观性,而其内在的“选择的权力”,与选择性执法的内在意蕴不谋而合。
可以说,正是基于刚性条文所受之辖制,加上纷繁复杂变动不羁社会关系之需求,作为一种运作在法治规则真空地带,并能很好解决现实具体情势困境的依势而定的执法方式,选择性执法的存在是有其深刻必然性的。
(二)执法资源有限性的约束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资源的总量是恒定的。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盘活这些资源,将其有机整合并使得最终效益最大化,换言之,实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化”配置,是一个非常有探讨价值的话题。对选择性执法而言,将执法成本和执法收益通盘考虑,统筹兼顾各种利益因素,并将资源整合到最需要的执法领域,是在执法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必须考虑面对的现实问题。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违法行为是层出不穷的,加之转型社会的背景,各种利益的彼此交织和冲突表现更为明显,这只会导致现实生活的执法需要付出更为高昂的成本,并使得执法资源愈发显得捉襟见肘、左支右绌。有限的执法资源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必然要求在一定规则下进行一定的分配,甚至于“抓大放小”、“全面执法”只能是理想愿望而遥不可及,有些事项注定是会被拖延处理甚至根本得不到处理。现实中也常可看到主观上有所倾向的、有意识的选择性执法,如实践中的抽查和抽检等,通过这种灵活性的以点带面的执法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产生广泛的威慑效应,使得社会秩序在一定层面上得到维护。
另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下,百分之百执法要求的执法成本无穷大,远远超过了违法本身所带来的损害而得不偿失。因此,现实中的执法概率必然小于百分之百,只有部分违法者得到了惩罚”[2]。可见,“全面执法”是不划算的,经济的执法方式必然是要针对不同的执法对象,根据具体情况的差异做出相机选择的区别对待。Becker和Stigler在研究后认为,选择性执法是执法成本和违法损害之间边际平衡的结果,最优执法应当寻求达到执法减少的损害与因此增加的执法成本之间尽可能合适的比例关系,那种认为一切违法行为都应得到执法者的关注,并采取实际行动的观念实际上是不经济的[3]。最优执法理论为选择性执法奠定了经济学上的理论支撑。
由上可见,“选择性执法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4]162-165。
二、能否以“不法平等”抗辩选择性执法
上文论证了基于法律自身的原因以及一定时期内执法资源有限性的约束,选择性执法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然而,遵照上述缘由开展的选择性执法,在实践中却常常会遭遇到一种抗辩。比如在人行道上停放了多辆机动车,职能部门只对其中几辆车的车主给予处罚,受处罚的车主辩称“他能停,为什么我不能停?”,“别人不交罚款,为什么只要我交?”,申言之,行为人虽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并且也承认自己是违法的,但是却以该种违法行为别人也存在,却因违法仅招致对己而并不是也施加于他人的处罚,而主张自己的豁免或者要求对他人也一律给予处罚的一种申辩,我们将其谓之——“不法平等”抗辩。
那么上述事例下的抗辩到底能否成立呢?其基于平等原则提出的申辩理由到底要不要支持呢?源自欧洲人权公约中的平等原则,其涵义何谓,我们是耳熟能详的,受不利处分的当事人到底能否援用平等原则来请求撤销或变更特定处理呢?相对人能否以前人的违法行为未被处理,而要求基于信赖利益保护之精神主张自己也免责呢?在行政法的视野下,一般认为,平等原则可以被细化为两项子规则,即“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和“禁止恣意原则”。所谓行政自我拘束原则,即行政主体要受其前已形成的合法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惯例的拘束;所谓禁止恣意原则,即禁止任何违反宪法基本精神及事物本质的行为,禁止对弹性法律用语任意作扩大或缩小性解释,不允许持有不当偏见,不允许不适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导致结果的畸轻畸重。从上述细化的子规则来看,行政机关是不能出尔反尔的,其执法应受先例的约束,并应在执法中自我克制,动机纯良。那么,不法的先例到底有无拘束力?在不法的状态下,相对人能否主张不法的平等?类似的争执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普遍存在的。从目前德国以及台湾地区的相关判例来看,不法平等是并不被承认的,如台最高行政法院1992年度判字第275号判决指出,“行政行为,非有正当理由,不得为差别待遇,……然行政机关若怠于行使权限,致使公民因个案违法状态未排除而获得利益时,该利益并非法律所应保护之利益,因此其他公民不能要求行政机关比照该违法案例授予其利益,亦即公民不得主张不法之平等。”虽然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判例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在法无明文规定或者法治储备不足的前提下,现实运作的事实是,相关情况常会受类似判例精神的潜在影响,实务进行执法时,对不法平等的抗辩理由常常并不理睬。实务部门这样去做的原因,多是源于潜意识本能而为,甚至出于执法会获取经济上的巨大利益而率性作为,其并不会深入探究这种执法的根源所在。而理论上对此的探究就显得很有必要,这主要源于理论研究之使命就在于为其现实执法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笔者以为,不法平等的抗辩理由之所以不被支持,是源于不法的先例是不具有合法先例所具有的约束力的,不法先例的不法状态原本就是应该被纠正的,不法前例对事后事例不具有约束力,也不需要被事后类似行为所遵循,以平等原则主张不法状态被维护是站不住脚的。
由上可见,是不能以不法平等的理由,主张抗辩对之施以选择性执法的。
三、被异化的选择性执法及其弊病
出于公心,迫于执法资源有限性而进行的选择性执法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实践中却存在大量被异化掉的选择性执法,成为人们所诟病的对象,并客观说明选择性执法为什么在坊间臭名昭著的缘由所在。
正是基于选择性执法有其自我“选择”的空间,执法者在选择之初,常常就会目的失纯,甚至会夹杂一些见不得光的内幕,出现权力寻租、利益勾兑等腐败交易行为,在这种场景下,“最神圣的法律在选择性执法下变成了执法者或者权力享有者谋取私利的魔杖”[5]。现实中常见的一种现象是,执法者“因钱执法”——从狭隘的部门利益甚或个人利益出发,以缴纳“赞助费”等名义要挟其所辖对象,对于缴纳者给予一定的保护,而对于未缴纳者却百般刁难,因其“不识相”或“不懂规矩”动则上门执法,甚至施以报复性执法。这种相机执法的方式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对社会公平机制产生了直接致命性的破坏,引发出的逆向选择倒逼机制,导致社会上投机心理和机会主义的普遍蔓生,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逼良为娼的结果,只能是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民众对法律的敬畏心理不再,整个社会法治观念迷失甚至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
被异化的选择性执法,还表现为对被执法对象背景因素的考虑。如果出身显贵或者背景深厚,执法者对其就会“呵护备至”;而如果出身卑微或者属于弱势群体,执法者对其更显凌厉凶狠。如在某年,在武汉一个日本人丢了一辆自行车,武汉动用全市警察力量帮助寻找,这种做法使国人不解甚至愤闷,本质上源于执法者对有特殊背景人的特殊待遇已明显超出了法定自由裁量的范围。而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现实中常见对“软柿子”表现强硬甚至手段蛮横的执法,君不见城管暴力执法现象比比皆是。欺软怕硬,见了老虎作揖,逮住兔子猛踹,这样的选择性执法让人实在是唏嘘不已。
不单是对象,选择性执法还表现为对执法时间上的选择。这一方面表现为推迟执法甚至不了了之,现实中基于无利益可图的执法常常是会被拖沓延宕甚至落个根本不执行的结果;而另一方面,现实中还有大量择时而定的执法,比如基于情势发生了变更,政治意志或政策运作上有特殊需要,都会出现特定时间上的浓墨执法。现实中还会发生一种运动式执法,主要是源于被强势群体利益俘获而发生,这种间隙性进行的执法,因其发生时间的高度不确定性,加重打破了大众对社会生活正常运作秩序的合理预期。而且,在运动式执法中,违法行为的发生在运动式执法前就已大量存在,只是在遭遇运动式执法时才可能有所纠正。对于违法行为的不及时制止会导致“破窗效应”的产生,即窗子被打破了,但没有被批评,会有更多的人也会去打破窗户,从而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状态。而即便是迎来了运动式执法,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是所有的违法行为都会被查处,违法者仍会滋生侥幸心理。退而言之,即便被查处了,机会主义心理的存在导致其仍有可能选择卷土重来,重操旧业。此外,在执法时间的影响因素上,还有一种基于民众态度以及舆论导向而发生的执法,如对于重大社会公共事件或者群体性事件,社会热点或媒体焦点等,常会根据“民意”而对执法事项发生放大效果,如一定时间段对酒后驾驶的集中查处和重点整治等,再比如在山西黑砖窑事件后对所有砖窑的集中清理整顿等,这种执法多具有应景特征,一般是为了平衡各方利益冲突,基于社会客观需求而做出,是一种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治理策略。
上述的选择性执法,滥用了裁量权,异化了“选择”权,秉持的是权为上,利为大,在不当动机或目的驱动下的选择性执法,必会侵蚀到苦心营造的有序社会格局的根基。被异化掉的选择性执法,会通过层层发酵的过程,形成一种危险的锁链效应,最终可能将公平正义引向不可逆的泥沼之中。
四、对异化的选择性执法的规制路径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6]264,《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至理名言,深刻说明着控制的必要性。基于此,对选择性执法予以规制是必须的。笔者以为,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一)遵循必要的程序规则
在尽力抵达实体正义彼端的途中,必要的程序规则的遵循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程序类似于一种必要的事前规制,而“防火要比灭火更有效率”[7]161-165;而且“程序正义不仅可以模塑和生成实体法规范,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人们愿意容忍那些虽然存在瑕疵,但是经过公正程序检验的执法行为。”[8]所以,在进行选择性执法之际,遵循必要的程序规则是意义重大的,如要尽可能做到信息公开;在进行执法时表明身份;在作不利处理时要听取对方陈述,并给予申辩甚至举行听证的权利;在执法时要遵守执法的时效要求;在被合理怀疑时要进行回避;不“单方面接触”任何一方当事人;在作处理决定时,要严格依据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案卷笔录,遵从“案卷排他性”规则等等。此外,结合十八届三中及四中全会的精神,笔者以为,对于执法过程中产生的争议,还可考虑引入第三人评价机制,即通过第三方的客观评价结果,秉持公正心来妥善处理执法分歧。虽然在目前的执法实践中,有执法监督员制度,但其存在着过于稳定,被选任渠道单一,甚或被利益者“俘获”的可能。在这种背景下,引入选任机制流动,趋于灵活性的,由没有利害关系的社会第三人广泛参与的评价机制,可以起到更好的保证实体正义的功能。
(二)制定必要的选择裁量基准
行政执法中拥有自由裁量权是必须的,然而执法运作的实践情况表明,裁量权的行使是应该有边界的,裁量权的随心所欲或宽泛化行使,只会导致执法的公平和正义被专断或恣意执法所取代。裁量权应该有其运作的轨迹路径或者说运作空间和范围;裁量权的行使需要遵循必要的运作规则,缺乏监督的运作只会导致裁量的结果变得面目可憎,而这便催生出了裁量基准——一种对裁量进行控制的规则的出台。所谓的裁量基准,简单说,就是一种为如何进行裁量而设计的尺度规则,或者说,是一种规制裁量权如何行使才更为规范的规则的集合体。裁量基准,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行政机关的自我解释,通过这种规则,可以对裁量的范围予以限定,对裁量的空间加以限缩,从而保证法在适用上的尺度整齐划一,最终实现公平统一的社会效果。在国外,类似的制度也是存在的,如“在德国,除法规命令外,行政规则中的解释基准、裁量基准也是以法解释的方法、条文规范的方式将行政机关对法规范的解释定型化,意在拘束裁量,以确保法律的统一适用。”[9]594在我国的法律实务中,也曾推出过类似的裁量规则,如早在2004年时,浙江省金华市就率先推出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制度》;在2009年底,湖南省还出台了《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都是意图通过给予标尺而避免裁量乱象,规制选择性执法出现不公的积极举措,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的借鉴和推广。
(三)合理配置执法资源
如前所述,执法资源的不足,是导致选择性执法出现的重要原因。在资源总量一定的前提下,如何盘活资源,使其最终效用最大化,涉及到执法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对此,笔者以为,资源首先应被用于最为需要的时间和空间,要将资源集中到某时某处最为需要的场合中,这是合理配置资源时应考虑的第一要义。如在交通运行高峰期,可以调配较多的执法人员参与执法,甚至动用一定的协警力量。此外,在平时分配执法资源时,要充分考虑所设岗位所要解决事务的多少、事务的复杂程度、处理起来的难易程度等,根据上述因素综合决定一定岗位上到底要配置多少兵马,坚决避免只拿“俸禄”而不干活人员的出现,人浮于事、闲职堆聚的现象应从源头上予以制止;另一方面,对于繁杂事务要保证配备有充足的人手,发现出现资源稀缺甚至严重不足的混乱局面时应及时加以纠正。可以说,选择性执法是在资源总量不足背景下的无奈之举,也正因如此,对执法资源加以合理配置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如果对资源没有做到合理配置,不仅会导致选择性执法运作不规范,更可能导致执法系统运转困难甚至面临重重危机。
(四)塑造法治行政观,培育行政伦理感
在构建和谐社会之时,物质或技术层面的 “硬件”是必须的,但是,社会整体的良性运转却不是仅仅只依靠“硬件”即可,因为在经济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构建或引进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10]351基于此,软件系统的配套是必须的工作。具体而言,要切实加强对执法人员法治精神的日常教育,注重对其法治意识的点滴熏陶,通过对行政人员执法伦理精神的培育,有效提高执法者的人文素质。当然,执法素养的提升是一缓慢渐进的过程,这种人文情怀的培育与其原有的个人品质和文化修养相关,而不断的法治教育也可使其得以进一步升华。在执法者素质得以充分提升的前提下,执法中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现象将会被有效控制,执法目的或动机上的不纯粹性将会被显著消减,最终达到选择性执法制度原初设置的美好初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法律和制度规范的盲区,恰恰是行政伦理的功能与价值生成的根据。”[11]在这一领域,作为良善美好结晶体的行政伦理大有其用武之地。
结语
从某种夸张的角度而言,选择性执法的运作,关涉到行政法治图景构建的半壁江山,探究对其予以规制的合理路径,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以一管之见,谈些浅薄意见,希望能抛砖引玉,引发学界更多的讨论,以对该问题的有效解决有所裨益。
[1]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戴治勇.选择性执法[J].法学研究,2008(4):28-35.
[3]See Gary Becker,Crime and Punishment:An Economic Approach,76 J.Polit.Econ.169-217(1968);Gary Becker&George J. Stigler,Law Enforcement,Malfeasance and Compensation of Enforcement,3J.Leg.Stud.1-18 (1974);George J.Stigler.The Optimum Enforcement of Law,78J.Polit.Econ.526-536(1970).
[4]K·C.Davis.Discretionary Justice:A Preliminary Inquiry[M].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6.
[5]何立慧.选择性执法的成本、收益和激励效应的经济分析[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5(2):68-73.
[6][美]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7][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M].杨伟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8]胡智强.论选择性执法的法律规制——兼及“钓鱼式执法”的法律约束[J].学海,2011(2):199-205.
[9][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0]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11]曾盛聪.论行政伦理的价值生成[J].人文杂志,2007(3):59-66.
(责任编辑:吕增艳)
D905.2
A
1008—7974(2015)03—0059—05
2015-01-2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制性征收研究”(13BFX049)和“选择性执法研究”(09CFX023)
胡晓玲,女,山西大同人,法学博士,讲师。
10.13877/j.cnki.cn22-1284.2015.05.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