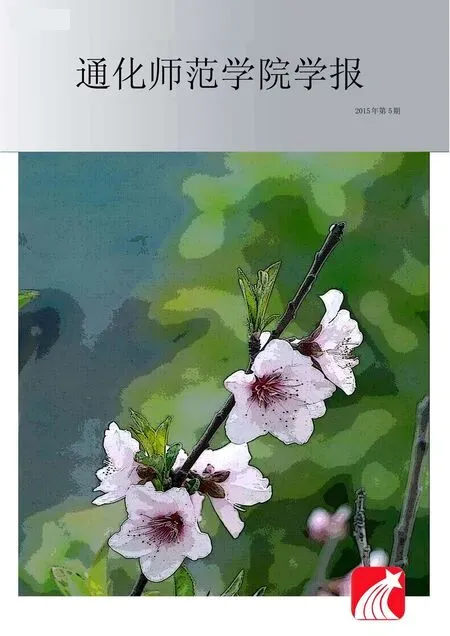探寻满族民间剪纸的造型美
宫丽慧,黄 千
(1.渤海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辽宁 沈阳 210000;2.通化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
探寻满族民间剪纸的造型美
宫丽慧1,黄 千2
(1.渤海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辽宁 沈阳 210000;2.通化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吉林 通化 134002)
不同的地域与民族都会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创造出相应的本土文化。生存在东北的满族先民们,在其繁衍、生息、劳作的过程中创造了深邃、纷繁、朴真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满族民间剪纸便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满族民间剪纸可谓历史久远,它不仅有着独特的适用价值与审美价值,而且有着鲜明独特的造型美感。满族民间剪纸的发生与传承发展,有其内在的文化成因以及艺术特色;满族民间剪纸的造型美对当代造型艺术的审美意识与审美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满族民间剪纸;造型美;审美意识;审美行为
鲁迅先生说:“艺术越有地方性,就越有民族性,就越有世界性。”换言之,越是乡土的就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满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民族民间文化积淀深厚,满族民间剪纸就是这种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承载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散发出一种强烈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有着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尤其在剪刻的造型上,无不流露出简约、粗放、随意、贯通、自然的美。
一、满族民间剪纸的产生与传承发展
满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肃慎和勿吉、挹娄、靺鞨、女真——满族的先民在东北地区繁衍生息了三千余年,在这漫长的演变历程中,创造了独特鲜明的民族民间文化,满族民间剪纸便是这种民族民间文化的代表。经专家考证,满族民间剪纸始于明代,那时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满族先民们多以狩猎采集为生,有很强的宗教信仰——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不但对天、地崇敬膜拜,并且把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动物及祖先都奉为神。先人们将这种生活情景和信仰经常用剪纸的形式加以表现,来求得精神与情感上的慰藉。剪纸所选用的材料多是桦树皮、树叶、布帛、动物的皮等,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先民们能够制造粗糙的纸或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贸易市场中换取纸张,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剪纸创作。随着各色纸张的出现,剪纸艺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剪纸的题材也从单一的宗教信仰逐渐转入现实生活,拓展了剪纸的实用功能。剪纸已成为满族劳动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活动,并得到广泛的普及。
时至今日,满族民间剪纸在满族的集居地依然被保护与传承。许多关于满族民族民间文化研究院所的创建,满族民间剪纸选修课开设,这些保护与传承措施,无疑对这个古老的民族民间艺术的存在与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满族民间剪纸的艺术特色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满族劳动人民在东北地区特有的环境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下,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思想情感、朴实无华的性格用剪纸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这些剪纸简约、粗犷、朴素,却能满足满族劳动人民对生活中的幻想、渴望、追求及宗教信仰等精神需求。正因如此,满族民间剪纸才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
(一)题材朴素凝练
满族民间剪纸的题材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宗教信仰——萨满教;其二是现实生活。宗教信仰是满族先民们主要的精神支撑,而剪纸则是这种信仰的重要宣泄方式,其选材多是生活中常见的动植物。比如,剪纸《蛙》《龟》《人参梦》等作品,造型是十分简约、夸张的,没有细腻繁琐的雕琢。这种表现手法是对客观物象高度的概括与凝练,是宗教信仰的需要,也是这个民族情感表达的慰藉。倘若满族没有宗教,也就不会有朴素凝练、浑然天成的宗教题材剪纸作品的存在。满族民间剪纸的题材可谓是宽泛的,又是凝练与抽象的。生活化的题材是剪纸表现的主流,体现了民间艺术家“大俗”即为“大美”的朴素审美思想,不受客观理法的约束,它的理法可谓是活态的、流动的,是装在民间艺术家心中的,以非物质的形态存在着的。正因如此,剪纸的题材既是宗教的又是生活的,也是朴素抽象凝练的。
(二)造型随意自由
满族民间剪纸在造型上是自由随意、粗野、奔放的,富有超凡的创造力。造型行为取决于审美意识,审美意识要先于造型行为。满族民间艺术家审美的主体意识为“好看就中”,也就是说他们在剪刻中不受具体的客观物象和理法的约束,它是以感情和信仰为理念的,造型不以追求客观物象的相似程度为目的,更多的是情感的投入,创作行为具有极强的随意自由性。比如,剪纸作品《人参梦》,作者打破常规理法的束缚,自由随意地将人参剪成人形,并且参大于人,这样的造型手法明显不受客观物象(人参、人)比例、结构等理法的约束,造型自由随意。这种自由随意的造型意识与行为成就了满族民间剪纸的鲜明特色。
(三)材料朴实多样
东北地区作为满族剪纸的发源地,白山黑水的丰富自然资源,不仅养育了这个民族,也铸就了他们的灵魂,智慧的他们充分利用自然所赐的各种材料剪刻出充满神秘色彩和情感宣泄的剪纸作品。这些剪纸作品除了用各色纸张之外,还会用桦树皮、树叶、玉米叶、辣椒皮等天然物质剪刻成剪纸。许多剪纸作品在内容与材质的结合上浑然天成、完美无瑕。
三、满族民间剪纸的造型美
满族民间剪纸应归属于造型艺术,若想认知造型艺术,首先要弄清语言与造型艺术语言的内涵。以往人们对语言的认识可能过于狭窄,认为文字、符号、言语等是语言的范畴,其实不然,语言应是传达和交流人们思想的一切方式,这些都应归属语言范畴,只是它的存在方式不同而已。造型艺术语言是美术家通过造型艺术行为表达思想情感和宣泄对事物内心感受的手段,它通过造型媒介和语言手法展示出来。这里以石器的打造为例,阐明造型艺术语言的形成过程。在旧石器时代,古老的石器大都是将砾石(鹅卵石)敲打一头,打造磨制成较规则的石器。笔者认为打制的过程即为造型行为,打制意识即为审美意识。比如,规则、对称、光滑等造型意识即是人类祖先的审美意识,审美意识与造型行为的融合便形成了早期的石器艺术,这可谓是造型艺术的初始,也是造型艺术语言萌生的表现。
满族及其先人在宗教信仰、万物有灵、生活向往的审美理念支配下,产生相应的民间造型艺术行为,创造了独特的、丰富的民间造型艺术语言,从而形成鲜明的、灿烂的、乡土的民间剪纸形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简约的造型美
纵观满族民间剪纸,一般无具体入微的客观再现,而是以简约、概括、鲜活、明了的表现手法来剪刻客观物象,传达情感和信仰,求得多数人的认同。这种以少胜多,以简代繁的民间审美诉求,正是其生存至今的关键,也是人们一直青睐它的原因。满族民间剪纸简约的几乎没有复杂情节和内容的表现,可以说它是在简约的造型中求得文化寓意和一种朴素的美感,在凝练中求得造型上的含蓄美。比如,表现鹿图腾的剪纸——“回勃鹿”,鹿的造型实在简约的不能再简约。剪纸也十分的粗放、朴拙。图像虽然省略了很多客观物象本身真实的细节,但鹿的根本特征却表现的淋漓尽致。人们通过图像能够感受到一只姿态生动的鹿。这种简约的造型美能够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空间,赋予作品超现实的色彩,也是简约造型美的魅力。
(二)夸张、随意的造型美
从客观上讲,满族民间剪纸艺术家在剪刻作品时,从来不受具体客观物象的约束,他们是以情感和信仰为理念,依照生活感受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比如,剪纸作品《蛙》与《龟》,他们的造型是十分简约、夸张的,没有细腻繁琐的雕琢,仅是夸张、随意地剪出了蛙和龟的边廓,但其中的霸气、浑圆的造型美感就应韵而生,这是民间艺术家的情感与夸张、随意的造型手法交融的结果,这种夸张、随意的造型美极具感染力。
(三)不求“形似”求“神似”的造型美
关于“形似”与“神似”的问题,中国画论中多有论述。诸如,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论;谢赫的“气韵生动”说;郭若虚的“神是赋予生命的灵魂,神无形不存”等等。诸多关于“形”与“神”的论述,似乎“形似”与“神似”的造型观是中国画的专利。其实不然,满族民间剪纸艺术家在剪刻过程中,就有意无意的追求各种物象“神似”的造型美。比如,剪纸作品《打核桃》,核桃树是东北地区常见的大型乔木,其上结有黄色的果实,每逢秋季,满族山民进山小秋收,遇到核桃树,以长杆击打树梢,成熟的核桃就会落地。此幅剪纸表现的就是打核桃的情景,作品人物剪刻的虽说简约,但头部的神态和身体的姿态表现的却很是生动“传神”,叶子与核桃的造型更是动感十足,神态贻人。这种不求物象的表层相似,只求“神似”的剪纸造型观,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也吻合满族及其先人的审美习俗,实为造型行为中的大美。
(四)“一线”的造型美
任何种类的造型艺术都有自己特定的存在方式和造型手段,满族民间剪纸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剪纸是用剪刀铰出来的艺术,从表层上看,剪刻是剪纸的造型手段,其实在剪纸作品中形象的塑造是靠剪痕来表现的。剪痕即是线条,线条是剪纸主要的构成元素。这种剪刻的线条不仅有粗细、长短、刚柔、方圆等不同品格,也有疏密、聚散的各种变化,而且在剪刻中线条具有极强的贯通性,即“一线”感,每根线条都是缺一不可的造型元素,否则形象就无法贯穿。“一线”的造型形式决定了剪纸具有鲜明的装饰性美感,原因是剪纸多以剪刻客观物象的边廓为主,不去剪刻客观物象的内部构造。比如萨满树刺绣(它的底稿是剪纸),图像中鸟、兽、树的连贯性极强,似乎用一根线就能表现出来,作品充分地显示了“一线”的造型美。由此可见,线条是满族民间剪纸造型的命脉,“一线”的造型更是满族民间剪纸美的根源所在。
四、满族民间剪纸造型美的当代审视
当我们审视那些弥足珍贵的满族民间剪纸作品时,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满族民间剪纸应是在特定的民间民俗文化语境中产生与形成的,倘若离开这种特定的文化语境,其剪纸风格与造型特色以及所产生的造型美就会变味。这就好比宋代的绘画,人们都很青睐其写真的造型表现,但今天谁都无法完全复制那一时期的作品一样。满族民间剪纸已有的剪刻形态尽管已成为过去,但它的那种粗拙、简约、夸张、随意的造型特点,以及其潜藏的“大俗”的审美意识,依然让我们激动不已,难以忘却,并引发出许许多多的思考。
(一)“大俗”的造型审美意识,能够提升造型艺术的审美品位
“俗”应有二层含义:一是大的、通俗的、被多数人认同的;二是没有主观思想意识的,面面俱到地显现事物的外表。“大俗”是通俗到了极致,作品不仅融入主观思想情感,而且是朴素的、真我的情感,故有人以事物发展两极的思维方法认为:“大俗”即为“大雅”。满族民间剪纸造型的审美意识似乎简单通俗,如“好看就中”“中用就可”等审美意识,着实没有什么深奥的哲理,可以说通俗的不能再通俗了,然而其中道明一理:民间艺术家们已将自己的思想情感放在作品创作的首位,进入自由创作的王国,是为“大俗”。在这种“大俗”的造型审美思想的驱动下,艺术家经常用几条简约的不能再简约的剪刻线条来表现生活中意象鲜活的生命,来实现自己的剪刻目的,可以说剪纸作品在表层上看是平淡的,其实不然。当我们凝心静气的品读时,会发现满族民间剪纸作品不仅陈述了这个民族的历史、信仰与民俗生活,更重要的是其背后隐藏了“大俗”造型的审美取向。这种“大俗”即为“大雅”的审美意识正是当代造型艺术审美领域中所缺失的东西。就中国画艺术而言,许多作品没有明确的审美取向,不去感悟生活,不倾入自己的感情,一味地强调制作,脱离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只求所谓的现代,舍弃中国画的大传统与民族性,强调西化混乱的审美取向与艺术行为,致使中国画艺术家乱了方寸,出现了一种浮躁不安的现象。中国画是不可丢失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中国画。倘若中国画艺术家能够持有民间艺术家那种安定的、不浮不躁的心绪,再接纳一些地域的民族民间“大俗”的造型审美意识,那么中国画创作的造型审美品格将会有新的生机。
(二)本我、超我的心理素质,会觉醒当代造型艺术家的本真境界
艺术家的心理素质对其艺术创作思维的建立起着直接的作用,具体表现在艺术家对本我、超我的选择与表述上。
本我,儒学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画论有“人品即画品”之论。这种对本我的强调体现了中国画的精髓实质,其中也道明了画家的本性与心态直接与其作品挂钩。画家若能操控本我,即可达到超常的境界,这种境界实际就是超我的境界。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满族民间剪纸艺术家在本我与超我的心理素质发挥上是极为卓越的。他们在剪刻的过程中不受任何外界因素影响,没有板结的法度,没有任何思想的束缚,一切全由心生,致使其作品达到无私无欲、无我无为的超我境界。如此的心理素质,艺思广博,下剪如神助,意境自然得,哪里还存在创造之难的问题。然而,当代的造型艺术家在创作时由于思想与技术负担过重,画什么?师承谁?如何用笔用墨等等负重不健康的心理素质,造成作品没有自信没有本我,更谈不上超我表现的艺术境界。基于此种现象,艺术家应该回归本我,寻求本我的思维意识与健康的心态,才能达成实属自我的艺术创新目的。
(三)随意自由的造型行为可以改变当代造型艺术的“板结”
造型艺术贵在获取鲜活的艺术形态,即艺术作品的生命感,这种生命感的获得,需要诸多鲜活造型语言的汇集与构成。这就好比自然界中生命体的构成一样,如人体由头、颈、躯干及四肢构成,这些部件都需要鲜活灵活的,否则不能构成完整统一的生命体。倘若造型语言 “板结”,就很难获取有生命感的艺术作品。满族民间剪纸造型手段虽说单一,但其追求情感至真,往往不注重形象的客观真实,致使其在剪刻时随意自由,常常是烂熟于心,不加思索,信手拈来,剪刻的线条语言自由、生动自然,往往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笔者曾目睹了满族剪纸大师候玉梅的创作过程,她的剪纸造型充满了随意自由性,她剪刀下的人物形态常常是歪歪扭扭,举手投足不拘一格。最让人关注的是人物脸的塑造,或是木木然有几分愣气,或是苦涩中带有几分惨然,更有趣的是那种不能在同一视点上看到的脸,或者说,人物的脸在不停的转动。这种造型表现犹如毕加索立体主义时期的绘画。这些鲜活形象的获得是艺术家的情感与剪纸语言所致,她那欲行欲止的运剪方法增加了线条的力度,“漫不经心”的情感表达平添了剪纸作品的几分生气。然而在当下的造型艺术作品中,确很难见到造型行为随意自由,艺术形态生动鲜活的内涵深邃的上乘之作。这种“板结”的艺术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点,其一是多数当代造型艺术偏离了对艺术生命的追求,即“活”的表现。“活”不仅是艺术作品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哲学的主题。以当代中国画表现为例,许多作品缺少对生命气息的认知与追求,画面中的艺术形态僵硬,艺术语言表现的不够随意自由,没有情感的融入,一味的追求所谓的笔墨传统与制作,作品不能给人以“活”的气息,丢失了其存在的价值。其二是当代艺术家不能深明其理,认真探寻“随意自由”的造型行为。深明其理是艺术家经过千锤百炼得到的艺术体现,也是其对社会、人生、自然与绘画美学的综合感悟,在此基础上会产生有理智有修养的随意自由的造型行为以及鲜活的造型语言。从现象上看,民间艺术家似乎没有什么文化修养,其创作现象是偶然的,其实不然。他们不仅有深厚的民俗文化的综合修养,还有至真至纯的人生体悟,因此产生随意自由的生动鲜活的艺术作品,也就顺理成章了。
综上所述,满族民间剪纸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劳动人民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不仅创造了许多鲜活的剪纸作品,而且也为其它姐妹造型艺术提供了间接或直接的创造思路。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些质朴、无华、简约、率真的剪纸作品时,无论对其简约的造型行为,还是对那种随意的审美意识所产生的艺术价值,都不容轻视,尤其满族民间剪纸的那种“土”与“俗”的民族独特性,更是弥足珍贵,这种造型的独特性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与时代所需要的养分。
[1]周积寅.关于中国画传统与创新的思考——兼与赵绪成先生商榷[J].文艺研究,2001(3).
[2]泰华.论中国人物画的“形”与“神”[J].美术界,2012(6).
[3]王纪,王纯信.萨满剪纸考释[M].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
[4]黄千.长白山花卉线描研究[M].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2005.
[5]范瑞华.中国画向何处去[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6]左汉中.中国民间美术造型[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品风)
G112
A
1008—7974(2015)03—0038—04
2014-04-26
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辽西佛教艺术与民间美术遗产研究”阶段性成果(L13dwj024)
宫丽慧,女,副教授;黄千,吉林辉南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10.13877/j.cnki.cn22-1284.2015.0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