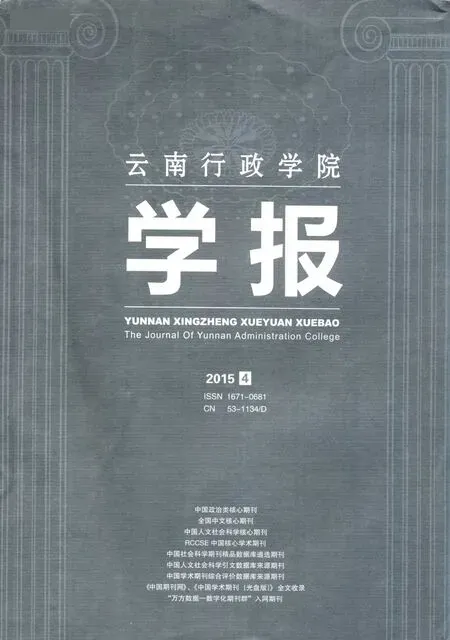密尔与协商民主:契合与悖离*
张继亮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天津,300387)
密尔与协商民主:契合与悖离*
张继亮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天津,300387)
当代许多协商民主理论家将约翰·密尔视为协商民主理论的先驱人物,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指出在何种意义上,密尔是这样一个先驱人物。而且,他们也未明确指出作为协商民主理论先驱的密尔的民主思想中包含着反协商的要素。本文从协商民主的角度出发,通过梳理密尔的相关著作来明确他的民主思想中所包含的与协商民主一致的地方以及与协商民主相悖的地方,从而廓清人们对密尔民主思想的认识。
约翰·密尔;协商民主;民主思想
当前许多协商民主理论家将约翰·密尔看作是协商民主理论先驱人物,例如,约翰·S.德雷泽克(JohnS.Dryzek)[1](P2)、埃米·古特曼(AmyGutmann)和丹尼斯·汤普森(DennisThompson)[2](P8)以及约·埃尔斯特(JonElster)[3](P5)都将密尔看作是在19世纪协商民主理论“最早的提倡者”。虽然如此,但他们都没有详细地论述他为什么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先驱,而且他们也没有阐明他在何种程度上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先驱人物。本文结合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及其相关文献试图说明,从一方面来看,他的民主理论中包含着很多协商性要素,但从另一面来看,他的民主理论又与协商民主理论的基本要求相冲突,换言之,密尔的民主理论与协商民主理论相悖离。
在详细分析密尔民主思想中蕴涵的协商要素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协商民主这一概念的内涵以明确密尔民主理论中的协商性要素与反协商性要素。通过梳理德雷泽克[1]、赛拉·本哈比(SeylaBenhabib)[1](P190-213)、詹姆斯·博曼(James-Bohman)[4]、艾丽斯·M.杨(IrisMarionYong)[5]、古特曼和汤普森[1](3-47)以及乔舒亚·科恩(JoshuaCohen)[1](P173-189)等协商民主理论家对协商民主的看法,本文认为,协商民主意味着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通过理性论证等各种方式进行沟通,在沟通过程中尽量提出互惠性、公共性的理由来说明自己的主张或政策的合理性,从而最终达到以下目标——减少冲突、增进理解、维持合作,甚至在理想的条件下达成共识。
一、密尔与协商民主之契合
密尔虽然没有提出完整的协商民主理论,但他的民主思想中包含非常多的协商性要素,这些要素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单个公民的内在民主协商、公民之间展开的协商、公民与代表之间展开的协商以及代表与代表之间展开的协商。
(一)单个公民内在的民主协商
内在的民主协商是由罗伯特·古丁(Robert-Goodin)提出的、一种独特的民主协商形式。在古丁看来,由于协商民主需要公民或代表在场,并花费时间进行协商,因此,协商民主受制于“时间、人数和距离”,即全体公民无法同时在同一个场所开展协商。在这样前提下,古丁认为人们需要将关注点从“外在集体”转到“内在思考”——“将协商民主的大量工作转换至每个个体的头脑中”,更确切地说,“协商并不是使人们‘通过对话在场’,而是使人们以协商者的思想‘通过想象在场’”[6](P59)。
基于相似原因,密尔反对秘密投票制度,他提出了两点原因。首先,基于对人性的分析,密尔反对秘密投票制度。密尔认为一个人有两种利益“自私的”利益和“高尚的”的利益,或者说,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在秘密投票的情况下,人们更多地是去追求“自私的”或个人的利益而不是“高尚的”或公共的利益:“一个人对公共利益具有自己特定的份额,即使他不拥有使自己处在相反方向的私人利益,也不能保证他不需要其他外在的刺激就能充分地履行公共职责,这是一条不变规则”[7](P249-250)。
其次,密尔认为投票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项权利,它更是一项义务,秘密投票无法保证选民履行选举权所附带的义务。密尔认为,在道德上,人们并没有一种对他人行使权力的权利,“选举权就是这种权力”,其原因在于,选举所赋予的权力不仅仅是针对个人自己,它还是针对他人的权力[7](P235)。基于此,密尔认为公民应将投票看作是一种责任,并且,在进行投票时应当从公共利益出发进行投票[8](P152)。但是,密尔认为,在现实当中,由于实行秘密投票,选民多出自“自私自利或自私的偏好”进行投票,完全没有将投票看作是一项责任[7](P245)。
基于此,密尔认为需要实行公开投票制度,因为,公开投票制度迫使选民进行内在协商。在他看来,在众人的目光之下,选民意识到或想象到自己要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进行投票(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性原则),否则,在投票结束之后,其他投票者会“要求对自己的行为给予解释”[7](P249),解释他为什么没有与其他人一样从公共利益角度出发进行投票,这些解释必须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并接受(协商民主中的互惠性原则),否则,他就会遭受“社会非难”(socialstigma)[9](P34)或“饱受訾议”[7](P248)。事实上,在密尔看来,公开投票制度的确能保证选民在经过内在协商之后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很多的选民有两套选择,其一是根据个人理由的选择,另一是根据公共理由的选择。只是后者是选民愿意直认不讳的。人们急于想显示的是他们性格的最好的方面,哪怕是对他们自己更好的人显示也好”[8](P170)。
(二)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协商
密尔认为,在代议制政府之下,公民在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特别是地方公共事务管理(例如担任陪审员与教区职务)可就如何管理好公共事务进行有效地协商。密尔指出,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过程当中,“文化低的人”可与“文化高的人”“发生极为有益的经常的接触(contact)”,通过这种“极为有益的经常的接触”,“文化低的人”可以从“文化高的人”那里获得有关地方和职业的知识,甚至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从“文化高的人”那里获得“更广阔的思想和更高、更开明的目的”的启发[8](P54)。
这里需要分析的是密尔所说的“接触”,因为,正是“接触”体现了“文化低的人”与“文化高的人”之间进行的协商,“接触”意味着协商,意味着“文化低的人”与“文化高的人”。因为,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特别是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时,无论“文化低的人”与“文化高的人”都会发表关于他们关于某项公共事务的主张、建议或政策及其理由,在这一过程中,“文化高的人”可能会通过自己的研究或思考提出一些基于公共利益的主张或政策,当“文化低的人”对这些主张或政策提出疑问时,他们就会向他们解释这些主张或政策的原因,通过这一解释,很多“文化低的人”可能就会接受这些基于公共利益的主张或政策,并在理想的情况下趋向于达成共识:接受这些主张或政策。随着这一协商过程的不断重复,“文化低的人”通过与“文化高的人”的讨论获得了很多“有关地方和职业的知识”,而且,他们会获得感情上的“升华”———逐渐获得了“公共精神”:“只有通过政治讨论,一个从事日常工作、其生活方式又使他接触不到各种意见、情况想法的体力劳动者,才懂得甚至很远的原因和发生在很远地方的事件,对他的个人利益都有极明显的影响。只有通过政治讨论和集体的政治行动,一个被日常职业将兴趣局限在他周围的小圈子的人,才会同情他的同胞,和他们有同感,并自觉地变成伟大社会的一个成员……”[8](P127-128)。在这种情况下,当“文化低的人”想就某项公共事务提出自己的主张或政策时,他们很可能也会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来进行思考并向他人提出基于公用利益的主张或政策。所以,正是通过“接触”,通过“文化高的人”与“文化低的人”通过讨论,“文化低的人”理解了基于“公共性”与“互惠性”的主张或政策,并且,在理想情况下,人们就某项公共事务可能达成“共识”。
(三)公民与代表之间的协商
密尔认为,公民不仅要积极与代表展开协商,而且,代表也要与其代表的选民积极展开协商。首先,公民要与其代表积极开展协商。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曾指出,议会是表达意见的舞台,而代表或议员代表公民表达意见:议会“既是国民的诉苦委员会,又是他们表达意见的大会。它是这样一个舞台,在这舞台上不仅国民的一般意见,而且每一部分国民的意见,以及尽可能做到国民中每个杰出个人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出来并要求讨论。在那里,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可以指望有某个人把他想要说的话说出来……”[8](P80)。密尔既然认为议会有如此功能,代表或议员有如此作用,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合理地推断:每一个公民都有权也需要与其代表之间进行不断地协商,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于捍卫它们时,才可免于被忽视……在没有天然的保卫者的情况下,被排除的阶级的利益总是处在被忽视的危险中……”[8](P44-45)。每个公民与代表展开的协商可使议员不仅知晓公民们的需求或主张,同时需要尽可能地使议员明确这些需求或主张背后的原因,而且,这些原因需要立基于公共利益之上或者它们建立在从这些公民的角度出发所理解的公共利益的基础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仅保证“不仅国民的一般意见,而且每一部分国民的意见,以及尽可能做到国民中每个杰出个人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出来”。
其次,代表需要与其代表的选民开展协商。在密尔看来,“一个有良心和公认有才能的人应该坚持按照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认为是最好的那样去行动的充分自由,而不应该同意按照任何其他条件服务。但是选民有权知道他打算怎样做,在所有关系到他的公职的事情上他打算用什么意见指导他的行动。如果有些意见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他就要使他们确信他仍然值得当他们的代表……”[8](P179)。毕竟代表是由他所代表的公民选举出来,他最终要对他们负责。虽然,代表并不需要在每件事情上都要征得他所代表的公民的同意[8](178-179),但是,当公民向其代表提出疑问时,代表仍然有义务向其所代表的选民说明其做出某个决定的理由,并且,当公民与其代表之间意见不一致时,代表需要提出有效的理由来说服其代表的公民。
(四)代表们之间的协商
密尔认为一个代议制团体的适当职能并不在于管理国家事务,国家事务应当交给有一个人统辖的组织去管理,“一个团体能比任何个人做得好的是协商”[11](P424),特别地,“当听取或考虑许多相冲突的意见成为必要的或重要的事情时,一个进行协商的团体就是不可缺少的。”[8](P71)
基于此,密尔认为,在代议制团体当中,“这个国家的每一种利益和每一种意见都能在政府面前以及其他一切利益和意见面前对自身的理由进行甚至热烈的辩护,能强迫它们听取,或者同意,或者说明不同意的理由……”[8](P81)。这表明,在密尔看来,通过代表,“不仅国民的一般意见,而且每一部分国民的意见,以及尽可能做到国民中每个杰出个人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出来”,代表们彼此就对方的意见进行辩论:或为自己的意见提出理由进行辩护,或者说明其他代表的理由之不充分。在这一协商过程中,即使有些代表自己意见被其他代表否定,他们也并不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意见和相关的理由表达出来,其他代表已经知晓他们的观点或主张及其理由,他们的观点及理由之所以被“压倒”是因为其他代表的观点更合理,他们的理由更充分,或者说,其他代表提出了“更佳的理由”,并且,代表们基于“更佳的理由”基本上都接受建立在这些理由基础上的意见[8](P81)。
总体而言,密尔民主理论中协商性要素体现在每个公民个体进行的内在民主协商、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代表之间以及代表之间展开的协商,在这些协商过程中体现的主导性要素是,无论是公民还是代表都要针对其观点提出互惠性或公共性或既有互惠性又有公共性的理由,并且,无论是公民还是代表都会倾向于达成一致见解。
二、密尔对协商民主之悖离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明确了为何当代如此之多的协商民主理论家将密尔视为协商民主理论先驱。然而,密尔的民主思想中不仅包含着协商性要素,而且它也包含着反协商性要素。这些反协商性要素包括:选举权的资格要求、复数投票权以及对力量对抗的强调。
(一)选举权的资格要求
密尔认为每个公民都需要有选举权以保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而且,他还认为,如果人们不给一个人以选举权是“对他这个人的不公平”:“无论哪个人,当别人不征询他的意见,擅自掌握限制他的命运的无限权力的时候,他的地位就降低了,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即使在人类思想不曾达到过的进步得多的国家里,遭到这种处置的人也不会受到和有投票权的人同样的公平对待”[8](P128)。即使如此,密尔仍然认为不能将选举权赋予所有人,尤其不能赋予那些不会读、写、计算的人,不交税的人以及领取教区救济的人。
密尔认为,在一个人很容易获得受教育的机会的前提下,不能将选举权赋予那些不能读、写、计算的人。因为,在他看来,那些人由于不能充分发展并运用他们自己的理性去思考公共事务,不能承担起公共责任,所以,将选举权赋予那些人相当于“把选举权给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一样”[8](P129-130)。另外,密尔认为需要那些不交税的人没有选举权的资格。如果将选举权赋予这些人,那就等同于“允许他们为了他们认为适合于称之为公共目的而把他们的手伸进他人的口袋”,这势必会造成浪费,“不交税的人,通过他们的投票处置他人的财产,就很有可能造成浪费而不会想到节省”[8](P130-131)。最后,对于领取教区救济的人而言,密尔认为他们并没有获得选举权的资格。密尔给出的理由是,靠别人养活的人没有决定公共事务的权利[8](P131)。
密尔对那些不会读、写、计算的人、不交税的人以及领取教区救济的人的排斥在选举权之外不仅违反了密尔自己所提出的“自保准则”[8](P44),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违反了协商民主所体现的包容原则———所有自由、平等的公民都有参与协商的权利:上述三类人由于没有选举权,他们就不会与代表们进行协商,因为他们知道,由于他们没有选举权,代表们可以不理睬他们的意见或主张,即使他们的意见或主张的理由非常充分[8](P128)。
(二)复数投票制
密尔不仅将一些人排除在选举权或协商之外,他还主张实行复数投票制,即有些选民拥有两张以上的选票,这一制度与协商民主中公民平等相悖。密尔认为,对于公共事务而言,那些在道德或智力比较卓越的人的意见比其他人的意见要重要,[8](P133)因此,他们需要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选票以保证他们的意见能影响多数人的决定,尤其是在大众民主兴起的状况之下更要赋予道德或智力比较卓越的人更多的选票,因为,大众民主的兴起带来的是“政治知识水平太低的危险和阶级立法的危险”[8](P132)。
假设我们接受他的这一观点,然而问题是如何确定某些人在“道德”或“才智”比较突出呢?密尔认识到人们缺乏测量“道德”的标准[7](P235),所以,在此情况下,“唯一能证明把一个人的意见计算为不止一个是正当的做法的事情,乃是个人的智力上的优越性”[8](P135)。但是,问题仍然是如何测量一个人“智力上的优越性”?密尔认为,在缺乏普通考试制度的情况下,只能诉诸“个人职业的性质”来判定一个人智力情况的高低:一般而言,雇主相对于工人来说更有才能,工头相对于工人更有才能,技术性行业工人比非技术性行业工人更有才能,银行家、商人以及制造业者多半比小商人更有能力,这些更有才能的人,在密尔看来大都是在智力上具有“优越性”,因而可以拥有复数投票权;同样,从事自由职业者、大学毕业生、“持有讲授各种较高级学科的学校的合格证件的人”以及通过像牛津和剑桥大学等具有认证资格团体认证的人都有复数投票权[8](P135)。
密尔主张复数投票权实际上是为了应对民主社会存在的危险,但是,这一措施与协商民主中的公民平等原则相悖。复数投票权违背了公民拥有平等的民主协商权利:借助于复数投票权,在“道德”或“才智”上具有优势的公民比普通公民在程序上拥有更多的影响协商的权利,因为他们拥有复数选票,他们可以选择多个人来表达他们相同的观点或意见,这样,在代表之间进行协商或讨论时,他们的观点由于许多议员的倡导而最后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增大。
(三)从理性协商到力量对抗
密尔认为公民之间的协商能够促进公民在治理与道德方面的增长,而智力与道德方面的增长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特别是智力方面的进步对社会进步尤为重要。在《代议制政府》当中,密尔也提到,能够促进进步的人类属性包括“智力活动、进取心和勇气”[8](P20),而且他特别指出,“似乎专属于进步并且是导致进步的各种倾向的集中表现的智力属性是创造力或发明才能。”[9](P386)
但是,密尔并没有一直坚持他的这一逻辑,即协商促进人们在智力、道德方面的发展,智力、道德方面的发展促进社会进步,他有时从理性言说或协商、讨论转向力量对抗,并认为力量之间的对抗才是促进社会进步的要素:“只是当社会最强大力量和某个对抗力量之间,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之间,军人阶级或地主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国王和人民之间,正统教会和宗教改革者之间进行着斗争的时候,社会才有过长期继续的进步。”[8](P115)但是到了19世纪,密尔认为,在民主成为唯一的力量之后,社会有陷入停滞的危险,因为作为“社会最强大力量”的民主缺乏“对抗力量”:“到目前为止民主制政府的一项巨大困难似乎是如何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为个人抵抗统治权力提供一种社会支持,即一种支点。这种社会支持是迄今保持先进的一切社会情况所提供过的。它是为受到占优势的公众舆论轻视的那些意见和利益提供的一种保护,一种集合点。因为缺乏这样一种支点,较古老的社会,以及除少数几个以外的所有现代社会,通过只有享受社会和精神福利的那部分人的独揽大权,或者逐渐解体,或者变得停滞(也就是缓慢地退化)”[8](P115)。为了提供对抗民主力量的“支点”、“集合点”,密尔提出了上文提及的复数投票权制以及比例代表制,他希望借此,那些智力和道德上优越的少数人能起到对抗民主力量的作用,以此来推进社会进步。
从强调协商、讨论来促进社会进步到强调社会力量对抗来促进社会进步,密尔似乎并没有对协商民主性要素抱有百分之百的希望,他似乎从一种理想主义的观点跃到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他似乎认为力量而不是理想言说或民主协商才是政治真正的底色。
三、结语
如果从协商民主的角度来看,密尔既可以说是一个协商民主理论的先驱——强调公民进行内在协商、公民之间进行协商、公民与代表之间进行协商以及代表与代表之间进行协商,他又可以说是一个反协商民主论者——并非所有的公民都能参与到协商之中,公民并不具有同等的协商权以及强调力量对抗的作用而非理性言说或理性协商的作用。如何看待这一矛盾性现象?密尔究竟是协商民主论者还是反协商民主论者?或许,我们不从协商民主的角度而是从发展的角度出发来看密尔的民主思想,我们可能就不会对他是否是一个协商民主先驱感到困惑:密尔一生的目标在于致力于“人类的改善”[11],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他既在“文明社会”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又在“非文明社会”强调“文明社会”对它的专制或殖民统治;同样,在民主政府之下,为促进文明社会的进步,他一方面强调人们之间要展开协商,通过协商来促进社会进步,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民主社会存在智力低下与阶级立法的危险,因此,他主张通过一些反协商式的制度或方法来抵消这些危险。总之,只要我们从发展的视角出发去理解密尔,我们就会明确他为什么既是一个协商民主先驱又是一个反协商民主论者。
[1][澳]约翰·S·德雷泽克.协商民主及其超越:自由与批判的视角[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2][美]埃米·古特曼,丹尼斯·汤普森.审议民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3][美]约·埃尔斯特.协商民主:挑战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4][美]詹姆斯·博曼.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5][美]艾丽斯·M·杨.包容与民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6][美]詹姆斯·费什金,彼得·拉斯莱特.协商民主论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7][英]约翰·密尔.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
[8][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9][英]约翰·穆勒.论自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John Stuart Mill,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VolumeXIX[M].Routledge and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7.
[11]JohnM.Robson.The Improvement of Mankind[M].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1968.
(责任编辑马光选)
D802
A
1671-0681(2015)04-0078-05
张继亮(1983-),男,山东日照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讲师,博士。
2015-02-23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国别政治思想史”(批准号:13&ZD149)子课题“英国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当代中国问题研究院基本科研项目(编号:NKDDZGYJI3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