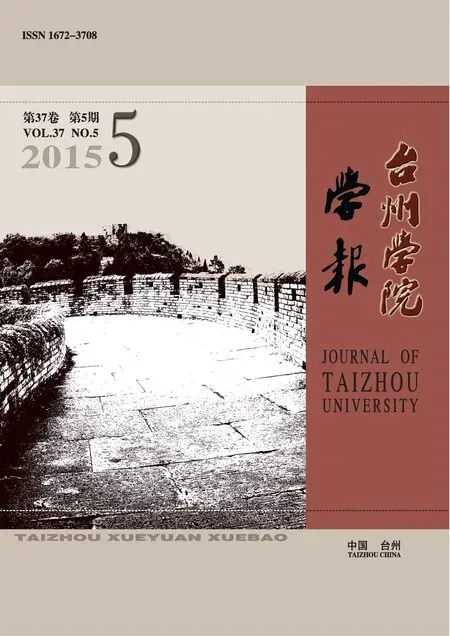论徐志摩对十四行体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许 霆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215500)
论徐志摩对十四行体中国化的历史性贡献
许霆
(常熟理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熟215500)
在新诗建立了连续形自由诗体、建立了诗节形格律诗体之后,徐志摩适时提出移植十四行体以建立固定形新诗体;在1930年代初新诗大众化运动兴起时,徐志摩直面新诗语言存在的问题,正面提出以十四行体等欧美诗为向导改善诗语;这是徐志摩对中国新诗作出的重要贡献,更是徐志摩对十四行体中国化作出的重要贡献。徐志摩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建立新诗体、改善新诗语,而且身体力行通过创作来移植十四行体,取得重要成果。
新诗;十四行体;徐志摩;新诗语
经过数代人的持续努力,中国诗人已经初步完成了十四行体由欧洲向中国的转徙,这一转徙也就是十四行体中国化进程,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卓越成果。在十四行体中国化进程中,徐志摩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对这一进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1931年11月18日,徐志摩罹难,随后《诗刊》第4期(1932.7)出刊“徐志摩纪念号”,朱湘和饶孟侃同时发表悼徐志摩的诗,而这两诗恰巧都是十四行诗;由友人编辑的徐志摩第四本诗集同时出版,书名借用徐志摩的诗《云游》,而这诗恰巧是徐志摩最珍爱的十四行诗;李唯建写于1929年后在徐志摩逝世后出版的《祈祷》,包括千行的十四行组诗,其序诗是《赠志摩》,把诗集题献给徐志摩。这种种似乎都是巧合,但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同人们正是以此来纪念徐志摩在推动十四行体移植中国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一
在新诗发生期,我国诗人输入十四行诗的意图,即李思纯所说的“多译欧诗输入范本”[1]23,给诗体解放后无体的新诗提供借鉴,这就有了如郭沫若所译雪莱《西风颂》等。翻译的同时是模仿创作,早期汉语十四行诗作者有郑伯奇、浦薛凤、闻一多、郭沫若等,稍后有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韵律运动兴起,诗人集合起来为新诗创格,陆志韦、徐志摩、孙大雨、闻一多、张鸣树、刘梦苇等都有汉语十四行诗创作。但令人费解的是,孙大雨在1926年发表了较为成熟的汉语十四行诗,却并未引起人们讨论的兴趣,理论和创作都没呼应;新月诗人推动新格律诗创作,但《诗镌》11期上仅有个别匿名十四行诗,没有诗论提及十四行体;部分新月诗人虽有十四行诗发表,但不约而同不去标示十四行诗。这看似意外现象,其实有迹可循。首先是新月诗人在理论和创作上为新诗创格,主要是在探索新诗韵律体系,即使孙大雨恰巧写出的是十四行诗,但其意不在十四行体本身,而是着眼于整个新诗体建设;其次是新月诗人提倡新格律诗是主张创造诗节形诗体,强调的是“相体裁衣”[2]85,并非如十四行体的固定形。这时李金发的《食客与凶年》(1927)中虽有《sonnet二首》,王独清的《死前》(1927)中虽有《SONNET》五首,但那只是用此诗体来写作象征主义自由诗。总之,那时的诗坛尚未真正把移植十四行诗体的课题提上议程。
历史的转机出现在1928年3月10日,徐志摩等主编的《新月》创刊号发表了闻一多翻译的一组白朗宁夫人十四行情诗,同时发表的还有徐志摩的长文《白朗宁夫人的情诗》,在新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闻一多的译诗尽量地保留原诗格律,有时不免牺牲了意义的明白,但朱自清认为“这个试验是值得的;现在商籁体(即十四行)可算是成立了,闻先生是有他的贡献的”[3]373。而徐志摩的长文则是借题发挥,提出了移植十四行体并使之中国化的重大课题。他说自己自告奋勇地写作此文,一是来宣传白夫人的情诗,二来引起我们文学界对于新诗体的注意。这里正面提出了“对于新诗体的注意”的问题。徐文主要内容是:
第一,具体剖析白朗宁夫人情诗的审美价值。
徐志摩介绍白朗宁夫人情诗的思想内容,又介绍白朗宁情诗的写作和发表情况,阐明其社会意义和审美价值,认为“在这四十四首情诗里白夫人的天才凝成了最透明的纯晶”[4]。同时,他选出其中10首进行了具体作品分析,并在《新月》第二期继续发表闻一多译诗。这样就把白朗宁夫人情诗之美较为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创体中的新诗人提供了一个十四行诗较为成熟的文本。
第二,由衷肯定十四行体的艺术魅力。徐志摩在新诗史上首次具体地介绍十四行体发展史,突出地介绍了意大利的彼特拉克和英国的莎士比亚体。他赞赏地说:“商籁体是西洋诗式中格律最谨严的,最适宜于表现深沉的盘旋的情绪,像是山风,像是海潮,它的是圆浑的有回响的音声。在能收中它是一只完全的琴弦,它有最激昂的高音,也有最呜咽的幽声。”[4]这种介绍是完全准确的,对于后来诗人把握十四行诗体特征起着提示作用。
第三,充分肯定闻一多译诗的重要意义。徐志摩认为“一多这次试验也不是轻率的,他那耐心先就不易”,自己介绍文章仅是“在一多已经锻炼的译作的后面加上这一篇多少不免蛇足的散文”。[4]他认为闻一多翻译“是一件可纪念的工作”,“因为‘商籁体’(一多译)那诗格是抒情诗体例中最美最庄严、最严密亦最有弹性的一格”。[4]
第四,主张在移植基础上创建汉语十四行体。
徐志摩明确地说:“当初槐哀德与石垒伯爵既然能把这原种从意大利移植到英国,后来果然开结成异样的花果,我们现在,在解放与建设我们文字的大运动中,为什么就没有希望再把它从英国移植到我们这边来?”这种理由是充分的。徐志摩希望人们在移植中保持耐心,即“开端都是至微细的,什么事都得人们一半凭纯粹的耐心去做”[4]。希望年轻诗人学些商籁体以锻炼自己的文字控制能力。
总归起来说,徐志摩介绍十四行体,意在提倡移植十四行体创作汉语十四行诗。这里的介绍超越了个别模仿创作,也超越了新诗创格要求,而是主张把它作为一种诗体加以移植,在此基础上建设我国的新诗体。这种倡导实现了从输入十四行体无意创体到有意创体的转变,从移植为新诗创律到为新诗创体的转变。它标志着十四行体中国化的大幕正式拉开,而开启者是当时诗坛闻、徐两员大将的联袂,其场面有声有色。这是新诗发展中的重要篇章,更是十四行体中国化进程中的伟大事件。一种世界性诗体由它的本土移植到别国,想要保持其形式的纯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每个国度的诗人必然会根据自己的文化对之进行相应改造。因此,诗体移植就是本土化过程,移植十四行体创造新诗体本身就是中国化的课题。徐志摩在新诗发展的特定阶段提出这一课题意义重大,它体现着一种思想解放。美国学者劳·坡林归纳出世界现代诗体包括连续形、诗节形和固定形三类。连续形没有固定的外在结构,图案的格律成分较少,按其性质说是自由诗体;诗节形以诗节作为重复单位,而诗节可以借用传统旧的或自创新的,按其性质即新月诗人创造的新格律诗;固定形指的是“应用在整首诗中的传统体式”[5]175-179。我国律诗与西方十四行体均属固定形诗体。新诗发生是以打破传统固定形而创连续形自由体为标志的,前期新月诗人探索的是诗节形诗体。在此期间诗人无法正面提出新建固定形诗体这一敏感话题,是人们不愿打破律绝体后再受固定格律束缚。但新诗还要有自己的固定形诗体,因为它是新诗体成熟的标志。本来不合时宜无法提出的敏感话题,在新诗格律体普遍为人接受的情形下,则已经具备条件正面提出来了。正是在此关键点,闻一多所译白朗宁夫人十四行情诗发表,徐志摩顺应历史趋势,借题发挥提出了建立新诗固定形的课题,这是历史的必然。新诗探索固定形诗体主要是输入和自创两途,既然十四行体是一种世界性抒情诗体,所以在移植基础上创造新诗固定形诗体就是一个必然选择了。
徐志摩提出移植十四行体创建新诗固定形诗体,得到了诗坛共鸣。闻一多在徐志摩编的《新月》第三卷第五、六期(1930.5-6)发表给陈梦家的信,在评论陈的《太湖之夜》时专论十四行体特征。罗念生在《文艺杂志》第1卷第2期(1931.7)发表长文《十四行体》,专论十四行体形式规范和发展历史,并认为孙大雨的汉语十四行诗是典范之作。尤其是梁实秋发表《谈十四行诗》,精细地介绍了十四行体审美特征。梁文认为:“中国诗里,律诗最像十四行体。现在做新诗的人不再做律诗,并非是因为律诗太多束缚,而是由于白话不适宜于律诗的体裁。所以中国白话文学运动之后,新诗人绝不做律诗。”[6]270梁实秋分析了中外语言差异,认为英国的白话与古文相差不多,所以伊丽莎白时代诗人惯用的十四行诗,到了华兹华斯手中仍然适用。而律诗到了我们白话诗人手中绝不适用,这就导致了新诗人不做律诗而肯做十四行诗,这绝不是“才解放的三寸金莲又穿西洋高跟鞋”[6]272。其结论是:“律诗尽可不作,不过律诗的原则并不怎样错误。十四行诗尽管作,不过用中文作得好与不好,那另是一个问题。”[6]272这种论证为诗人创作汉语十四行诗找到了理论根据,这就是十四行体这种固定形式可以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之上,它同建立在古代汉语基础之上的旧律诗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论证对于十四行体中国化进程具有指导意义。
理论共鸣的同时是汉语十四行诗创作丰收。1928年以后到30年代初,《诗刊》《现代》《文艺杂志》《人间世》《文学》《青年界》《申报自由谈》等都发表汉语十四行诗,着实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热闹局面。如1931年7月出版的《文艺杂志》第2期,发表了罗念生《十四行体》论文,发表汉语十四行诗如朱湘《女鬼》、柳无忌《春梦(连锁十四行体)》九首、曹葆华《你叫我》、罗念生《十四行》九首、啸霞《十四行》五首,还有柳无忌《译十四行》四首。柳无忌后收入《抛砖集》中的21首十四行诗,基本都发表在这个年代。曹葆华《寄诗魂》在1930年出版,《灵焰》和《落日颂》于1932年出版,总计有近50首十四行诗,不少曾在刊物发表。这时的卞之琳也有多首十四行诗发表。朱湘在1934年出版《石门集》,其中70来首十四行诗大多写于1930年至1933年间。李唯建在1933年出版《祈祷》,包括70首十四行诗,诗人自述写于1929年初。以上初步罗列,就可以看到这确实是个汉语十四行诗创作的丰收期,是一次集体亮相的十四行创体行动。
柳无忌《为新诗辩护》中说到十四行体中国化线索,“我们最先感觉到传统文学的陈腐,我们有意要革新它而创造新的有生命的文学,于是我们第一步应做的是破坏,第二步应做的是模仿,经过了破坏和模仿后我们达到了最后一步,真正的建设与创造”[12]。如果说十四行体早期输入处在破坏期,新诗创格期则是模仿期,那么1920年代末开始进入建设与创造期。到1930年代后期始,诗人在民族形式讨论中进入中国十四行体全面建设期,基本特征是在规范基础上大量创作变体,经过数十年努力初步完成了十四行体从欧洲向中国的转徙。梳理十四行体中国化连续推进的历史进程,我们看到徐志摩提倡借鉴十四行体建设新诗体,正处在第二期向第三期转变的关节点,其历史意义就充分得到了体现。
二
进入1930年代后,后期新月和京派诗人共同推动新形式运动,徐志摩创办《诗刊》,更多地关注十四行体移植。《诗刊》总共出版四期,其中第4期是纪念徐志摩专辑,前三期情况如下:第1期(1931.1)发表梁实秋《新诗格调及其他》,论及十四行体;发表孙大雨、李唯建、饶孟侃等十四行诗,另有徐志摩推介言论。第2期(1931.4)发表徐志摩“前言”论及十四行诗,发表梁宗岱论诗信,论及十四行体,发表陈梦家、林徽音、曹葆华等十四行诗。第3期(1931.10)发表卞之琳、方玮德、徐志摩等十四行诗。这时的徐志摩继续关注移植十四行体创建新诗体,如他在《诗刊》创刊号序言中说:“大雨的三首商籁是一个重要的贡献!这竟许从此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李唯建的两首‘商籁’是他的《祈祷》全部七十首里选录的。”[8]这就明确了孙大雨创建“新的诗体”的贡献。在新诗史上,孙大雨最早按照对应移植方法创作汉语十四行诗,这就是发表在1926年的《爱》。该诗无论用韵、音步、建行、分段和结构等都使用意体正式;诗采用音组排列节奏创格。《诗刊》创刊号又发表孙大雨的《诀绝》《回答》《老话》,同样采用意体正式和音组排列写成,因此徐志摩认为它“奠定了一种新的诗体”,可见他对移植十四行体创建新诗固定形诗体的殷切期望。
这里需要说的是,《诗刊》期徐志摩除持续期愿建立汉语十四行体外,同时期愿通过十四行体移植的扩展功能来推动整个新诗建设。这是徐志摩对十四行体中国化的又一历史性贡献。创作汉语十四行诗,即把对象作为固定形予以整体移植,然后在改造中使之契合“今日”和“此地”,以此来丰富我国新诗体,这种移植是必要的。但还有一种移植,即只从对象中分解出为我所用的因素,以此来发展自己的东西,这是移植中的功能扩展。朱自清对译诗功能有精彩阐述:“不但意境,它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3]374。“闻、徐两位先生虽然似乎只是输入外国诗体和外国诗的格律说,可是同时在创造中国新诗体,指示中国诗的新道路”[9]397。朱自清认为输入域外诗体有着两个功能,一是输入一种固定诗体,二是输入一种诗美要素。后者内涵更为丰富,可概括为语言形式(语言表达和语音声音)。朱自清认为它“将融化在中国诗里。这是摹仿,同时是创造,到了头都会变成我们自己的”[9]398。事实上,从我国翻译和模仿创作十四行诗开始,其审美要素始终潜在地影响着新诗创作,但真正把此功能提出并使之成为自觉的则是《诗刊》期的徐志摩。
徐志摩正面提出十四行体移植功能扩展的背景是新诗语言的改善。五四期最终成形的现代汉语是相对于文言的白话语言,这种语言以口语化、精确性、界定性为基本特征,传统文学语言所具有的模糊性、多义性、意象性、声韵特征等诗性功能有所消弱。尤其是现代汉语多音节词增加、语法复杂和成分结合紧密,造成了诗歌音律建构困难。所以新诗发生初期,人们一方面倡导白话写诗,为白话诗争取生存空间,另一方面要说“现行白话,不是做诗的绝对适宜的工具”[10]21。新诗发生后存在的非诗化都同白话质素有关。所以,新诗始终在改善着白话诗语,重点解决的是形象加工和声音加工。这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大而复杂课题。完善诗语需要广阔的空间,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寻求资源。现代汉语本就包含欧化因素,充分发挥十四行体移植的扩展功能去改善新诗语言就是历史提出的必然要求。正是在此背景和要求下,徐志摩在《诗刊》第2期“前言”中正面提出了移植十四行体改善诗语的课题:
大雨的商籁体的比较的成功已然引起了不少响应的尝试。梁实秋先生虽则说‘用中文写Sonnte永远写不像’,我却以为这种以及别种同性质的尝试,在不是仅学皮毛的手里,正是我们钩寻中国语言的柔韧性乃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以及别一种单纯‘字的音乐’(Word-music)的可能性的较为方便的一条路:方便,因为我们有欧美诗作我们的向导和准则。[11]272
这里提出的是一个新诗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即新诗语言的现代化问题。推动新诗语言现代化,较为“方便”的路是把“欧美诗作我们的向导和准则”,而联系上下文表述,我们可以认为这里的欧美诗虽然是个广义概念,但首先是指十四行体。这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思想的充分体现。稍后的朱自清认为“语言的‘欧化’实在该称为语言的现代化”[12]294,徐志摩主张借鉴欧美诗来改善诗语同样体现着新诗现代化取向。
对徐志摩以上“前言”的理解分为相互关联的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于孙大雨商籁体和梁实秋诗论的评价。孙大雨的诗不仅采用意体正式和音组节奏形成诗语格律美,而且在语言表达的细密和浑成方面取得成功。孙曾说到自己诗语的追求,即“要挣脱文言文的句法结构及惯用的辞采,而且还应当博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思维、快意、感受、悬念、企盼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凝练成一个个语辞单位,加以广泛运用,以充实我们的表现力。并且应该,也完全可以借鉴外国诗歌文学的格律机构,作为参考,以创建我国的白话新诗的格律”[13]173。梁宗岱在《诗刊》第2期发表给徐志摩的论诗信,肯定孙大雨《诀绝》“把简约的中国文字造成绵延不绝的十四行诗,作者底手腕已有不可及之处”[14]27。孙大雨的十四行诗语言的这一特点成为徐志摩立论的依据。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载《诗刊》创刊号,也是写给徐志摩的信。梁实秋认为新月诗人创格是模仿外国诗的,而自己则“以为我们现在要明目张胆的模仿外国诗”。在此基础上,他对于“音节”能否采取外国诗的存在怀疑,然后说:“我不主张模仿外国诗的格调,因为中文和外国文的构造太不同,用中文写Sonnet永远写不像”[15]144。这种观点在常理上说并没有错,因为梁并不否定移植十四行体,只是希望写诗的人自己创造格调,“创造新的合于中文的诗的格调”。但其过分看重中外语言构造差异,对于移植十四行体诗语改善新诗语言的意义认识存在偏差,尤其是没有认识到朱自清所说的欧化因素融合后会变成我们的东西。对此,徐志摩倒是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他的“前言”一方面肯定了孙大雨的探索,另一方面用“我却以为”否定了梁实秋的观点。这种肯定或否定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实际上是巧妙地正面回应了当时对移植十四行体改善诗语的不同看法,导引十四行体中国化进程的推进。
在“前言”第二层次里,徐志摩正面提出移植十四行体扩展功能的内涵:一是钩寻中国语言的柔韧性乃至探检语体文的浑成,致密;二是寻求别种单纯“字的音乐”。前者关涉诗语表达素质问题。新诗采用现代汉语写作,而现代汉语天然缺乏古代汉语那种含蓄性、音乐性和精炼性,即诗性。欧诗语言采用日常散文结构,细密富有弹性,情意表达曲折。后者关涉诗语韵律节奏问题。新旧诗在节奏建行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旧诗之音组成行成句是以文言句法或者说韵文句法为准的,新诗的音组成行成句是以口语或散文的句法为准的!”[16]10既然新诗采用存在欧化因素的现代汉语创作,所以其诗语向域外诗语借鉴就是一种“方便”的选择。新诗语无论在表达或音律方面的完善,向外借鉴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但徐志摩在“前言”中又强调“在不是仅学皮毛的手里”,这是善意的提醒,也是真诚的要求。
事实上,十四行体移植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作为模仿创作新诗固定形诗确实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局部借鉴和功能扩展所产生的影响却更为重要。实践证明,徐志摩关于在十四行体中国化过程中改善新诗语的内涵概括是完全正确的。就改善诗语表达素质说,移植十四行体时化句为行,通过自由地分行、跨行和并行延展了诗行结构;移植十四行体超越形式文法组织诗语,增加语言的朦胧性和暗示性,移植十四行体在打破传统诗词粘对的同时,采用对等原则组织诗语,借鉴诗体持续进展构思,形成“层层上升而又下降,渐渐集中而又解开,以及它的错综而又整齐”的诗语美[17]270。以上移植成果增加了新诗语言的柔韧性、浑成性和致密性。就探寻诗语音乐性说,新诗节奏基础是“音组”,新诗创格遵循“均齐”“匀称”原则,新诗的韵式丰富多变,这些新诗格律探索虽然受惠于多种途径,但接受十四行体的重要影响却是不容置疑的。
三
创建新诗体,改善新诗语,这是徐志摩关于移植十四行体的两大期愿,它对于新诗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在新诗建立了连续形自由诗体、建立了诗节形格律诗体之后,正面适时地提出还要建立固定形的新诗体,这是一种顺势而为的思想解放。在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新诗大众化运动兴起时,直面新诗语言存在的问题,不合时宜地提出以欧美诗为向导和准则改善诗语,更是一种高瞻远瞩的思想解放。新诗大众化运动兴起自有其合理性,但片面提倡大众俗语、指责散语探索的极端倾向却是早有历史定评。正是在此背景下,当时的周作人明确地说,五四白话不是太欧化,而是太大众化,“其缺点乃是在于还未完善,还欠高深复杂,而并非过于高深复杂”[18]773。因此,在徐志摩之后的艾青提出“诗的散文美”、废名提出新诗形式是散文的理论,强调新诗语言现代化的探索方向。这就是徐志摩对十四行体中国化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难能可贵的是,徐志摩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两大期愿,而且身体力行创作汉语十四行诗实践期愿。因为徐志摩新诗优秀之作很多,数量很少的十四行诗常遭忽视。但人们并没把他忘记,江弱水在论现代汉诗十四行体中,重点提出了四位诗人,认为“闻一多善于守法,徐志摩敏于变法,卞之琳精于用法,冯至敢于破法”,并认为“还有不少诗人写过十四行诗体,但影响并不十分突出,因为这与他们诗歌创作的整体成绩的高低是有关系的”[19]164。徐志摩是百年中国最优秀的十四行诗人,其创作特征是“变法”的追求,这是符合事实的。“守法”“变法”“用法”“破法”其实都是十四行体中国化的探索。
徐志摩最早的十四行诗发表于《小说月报》第14卷第9期(1923.9.10),题为《幻想》,这是新诗史上最早的连缀体十四行诗,两首十四行诗28行连贯而下。早期创作这种连缀体的还有闻一多如《静夜》《天安门》等,但时间则在1926年以后。这诗表现出诗人对现实人生的关注和对光明的追求。前后两个十四行的首行都以天空中长虹出之,均用“幻”字点题,形成复沓呼应。诗的语言特点是重视旋律美,并不遵循十四行格律,音步、音数并不整齐,但字句和诗行对等组织,形成回环往复、相关亦相间的旋律,自有其诱人的趣味。荷兰汉学家汉乐逸认为,前期徐志摩的《天国的消息》也可算十四行诗,因为该诗遵守了十四行体的总体框架,但采用了3344诗节模式,诗行长度不一,韵式为abb abb ccdd bbee。在1925到1926年间,徐志摩翻译了沙孟士(阿瑟·西蒙斯)的十四行诗Amoris victima两首,译诗通篇采用偶韵,江弱水认为西洋十四行这样押韵不是没有,但毕竟出格。这一翻译影响着徐志摩随后的十四行诗创作,而随后的创作就是发表在《诗刊》第3期上的《你去》《在病中》和《云游》。其中《你去》《在病中》还是两首28行的连缀体,《云游》则是意体十四行诗。这三首诗写于同一时间段,在完善新诗语探索方面也有共同追求,从本文论题出发,我们选择其中的《云游》进行解剖分析,重点分析其诗语探索成果。
《云游》无论以什么标准来看,都可算是徐志摩最好的新诗作品。《云游》也是徐志摩珍爱的十四行诗,写于1931年7月,后易名《献词》收入这年出版的《猛虎集》,后又以《云游》为题载10月出版的《诗刊》。而诗人又恰在11月因飞机失事去世,因此诗也算是一种心灵感应的产物,“云游”遂成为他的新诗集名。诗抒写情绪的矛盾冲突和生命的真实体验,特征是意象的象征和意蕴的多义。读《云游》的关键是把握“你”“我”相对性。“你”的形象是自在、轻盈、逍遥,永不停留的云游,诗人以“美”去赞美;而“他”则是想抱紧“云游”,结果只是绵密的忧愁,诗中流露着追求和失落交织的情绪。在诗中,“你”和“他”并非对等,落笔始终在“你”即“云游”,由此我们才能把握诗的主体形象,把握诗的意象关联,把握诗的抒情脉络,把握贯穿在诗中对爱、对自由的不渝追求。下面来读《云游》: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只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我们从创建新诗体、改善新诗语的角度对诗作如下剖析。
一是诗句组织结构的延展。诗打破了行句统一的诗行结构,采用了跨行、并行等多种技巧,实现了诗行组织由传统的“句”向现代的“行”的转变。诗中第二行的诗句跨入第三行,第六行的诗句跨入第七行;同时,第二行由两个半短句组成,第八、十一、第十三、第十四行由两个短语(分句)组成;诗行并非以诗句而是以字数组织。全诗采用了经过提纯的诗语,但这种诗语不同于传统的“诗之文字”,而是包含着较多的散文成分(句式、连接词甚至逻辑复句),写来自由灵活,读来亲切自然。优秀的十四行诗要求表现一个思想感情的转变过程,或者发展过程,首句与结句不应处于一个思想感情平面,这样诗就有深度,耐人咀嚼,因此屠岸认为诗行或诗节对称不是十四行体规则。《云游》诗语采用的是纵直绵延而下的诗语进展组织结构,诗情起承转合带来了诗语的对等盘旋进展。这种种探索都使得诗句组织结构获得自由,行的结构、行间结构、段的结构、全诗结构都在传统诗基础上获得延展,增加了诗语的柔韧性、浑成性和细密性。这种语言是存在“欧化”因素的,却又是在借鉴基础上的中国化,借用朱自清评周作人译笔的话说就是:“虽然‘中不像中,西不像西’,可是能够表达现代人的感情思想,而又不超出中国语言的消化力或容受度。”朱自清甚至认为周作人“欧化”我们的语言“是第一个该推荐的人”[12]293-294。
二是声韵优美的语言经营。《云游》的韵式是:AABBCCDD AEAEFF。前八行运用了四组偶韵,较为倾向于中国传统诗歌,而这在西方十四行诗中属于变格特例,但我们得承认,偶韵较好地配合了“云游”风姿,诗情在两行一转中盘旋进展,诗语自然流畅,节奏轻盈聚散。结末两行同出用了偶行,也属意体写作中的出格之举,但它同前八行呼应,从导引诗情诗语持续进展,形成圆满整体。在前八行与末两行前穿插交韵,这本是意体前八行的韵式,放在这里当然是变格,但诗人正是通过变格一方面增加韵式复杂性,一方面改变诗的进展节奏。《云游》的韵式既有整体一致性又有局部变化性,这种变格韵式是同诗情进展契合的。江弱水认为《云游》还有三个因素值得注意。一是前八行三度跨行,使得行断句不断,句法腾挪灵动之至,与诗中所写的自由云游吻合无间;二是频繁地使用了双声叠韵技巧。双声如“自在”“绵密”等,叠韵如“轻盈”“逍遥”“卑微”“点染”“空灵”“忧愁”“湖海”等;三是前八行与后六行之间的“转”,用了“顶真”的修辞手法,首尾蝉联,重复述说,造成声音上的小停顿,激起意义上的大落差。末行再次叠用“盼望”两字,生出最后一个波澜而至于平复[19]158。这种分析,揭示了徐志摩新诗声韵优美的语言经营特点。
三是建行方式的大胆创新。徐志摩新诗建行方式不是音组而是诗行本身,是以诗行的匀整构成诗节诗篇。他认为“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他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行数的长短,字句的整齐或不整齐的决定,全得凭你体会到得音节的波动性;这种先后主从的关系在初学的最应得认清楚”[19]。即外在语言的音节要依据内在情调的节律,而外在的语言节奏关键是诗行的长短,新诗节奏的审美就是内含的音节的匀整与流动。这种诗律论表现在十四行诗创作中,就是诗行不以音组而是以诗行为基本单位,《云游》中各行基本整齐的匀整,14行中有12行是11音,其中2行是10音,这种诗行从外在语言形式看呈现着整齐中的变化,从内在情调看是通过自然语调来呈现诗的情调,自有其独特审美特征。这种节奏形式同样基于我国汉语特征,它是继孙大雨诗行限音组数而不限音数的节奏模式、闻一多诗行既限音数又限音数的音组节奏模式外的第三种模式,由徐志摩、朱湘、柳无忌等人在创作十四行诗中建立起来。历来人们对这种限音建行模式非议颇多,其实,为了凑足诗行音节,不顾文法与语气的通顺,任意地增削,这是不足取的,但这并非写作均行诗的过错,事实上朱湘、李唯建、冯至、曹辛之的十四行诗都写得语调自然。柳无忌认为,在这类诗中,“诗人可以自由地界定每行的字数,依照着诗中的情感或思想而变化着。同时,作者不一定一行内写着一句,他可以在一行内写着几短句,或者可把一长句带到另一行内结束。在这里面尽有很多的自由,可以免去拘束,有很多的变化,可以免去单调与生硬。”[7]102这就是徐志摩等人探索诗行节奏的创新意义,很多汉语十四行诗正是藉此获得成功的。
[1]李思纯.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J].少年中国,1920,2(6):16-24.
[2]闻一多.闻一多论新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3]朱自清.译诗[M]//朱乔森.朱自清全集(2).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4]徐志摩.白朗宁夫人的情诗[J].新月,1928,1(1):151-173.
[5]劳·坡林.怎样欣赏英美诗歌[M].殷宝书,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
[6]梁宗岱.谈十四行诗[M]//梁宗岱.偏见集.南京:正中书局,1934.
[7]柳无忌.为新诗辩护[J].文艺杂志,1932,1(4):101.
[8]徐志摩.《诗刊》序语[J].诗刊,1931,1(1):2.
[9]朱自清.诗的形式[M]//朱乔森.朱自清全集(2).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10]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的各种心理观[M]//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11]徐志摩.《诗刊》前言[M]//王亚民.徐志摩散文全集(2).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12]朱自清.新语言[M]//朱自清全集(8).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
[13]孙大雨.格律体新诗的起源[M]//孙大雨.《诗·诗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14]梁宗岱.论诗[M]//梁宗岱.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15]梁实秋.新诗格调及其他[M]//杨匡汉,刘福春.中国现代诗论(上).广州:花城出版社,1985.
[16]解志熙.《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序言:精心结算新诗律[M]//刘涛.百年汉诗形式的理论探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7]李广田.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M]//李广田.李广田全集(4).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18]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M]//钟叔河.夜读的境界.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19]江弱水.商籁新声——论现代汉诗的十四行体[M]//江弱水.中西同步与位移——现代诗人丛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On the Xu Zhimo’s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ization of Sonnet
Xu Ting
(School of Humanities,Changsh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hangshu,Jiangsu 215500)
After the New Poetry had built unified form and strophic form,Xu Zhimo suggested transplanting sonnet to establish regular form of New Poetry.When the Movement of New Poetry’s popularization was in vogue in 1930s,Xu Zhimo,confronting with the language problem of the New Poetry,expressed his opinion of improving poetic language by reference to western sonnet,which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hinization of sonnet as well as to the Chinese New Poetry.Xu Zhimo not only theorized Chinese sonnet in form and language,but also composed sonnets for the sake of a successful transplantation.
New Poetry;sonnet;Xu Zhimo;New Poetic language
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5.05.011
2015-08-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诗发生论稿”(11FZW 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新诗韵律节奏论”(13FZW07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十四行诗史稿”(15FZW021)
许霆(1951-),男,江苏太仓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