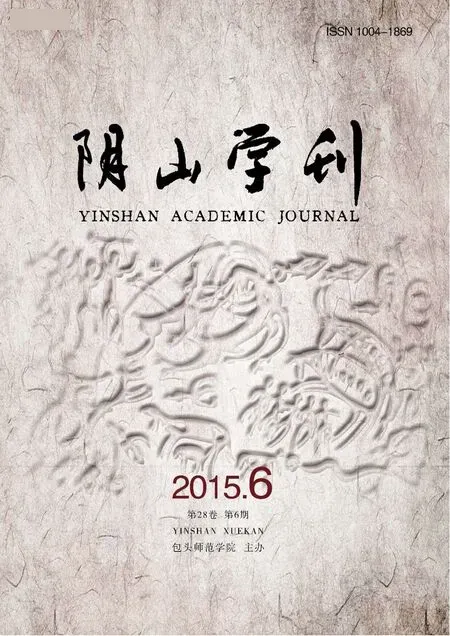臆想造就“权力人物”——《逃离巫师》中的权力人物存在原因及实质分析
许 媛 媛,吴 炳 月
(1.皖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2.六安市第二中学,安徽 六安 237005)
臆想造就“权力人物”
——《逃离巫师》中的权力人物存在原因及实质分析
许 媛 媛1,吴 炳 月2
(1.皖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六安 237012;2.六安市第二中学,安徽 六安 237005)
摘要:艾丽丝·默多克的作品《逃离巫师》中,各人物间存在着一种逃离与控制的关系,权力人物既是权力的控制者又是其受害者。权力人物最主要是由周围人物的心理需求创造的,是他们精神生活臆想的产物。
关键词:《逃离巫师》;权力人物;双重特性;存在实质;臆想
艾丽丝·默多克深受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故其作品《逃离巫师》中,核心探讨的问题便是人的存在,她所研究的是身处与他人、与世界的各种联系中的人,即是说,将人物置于与他人及世界的关系中加以考察。基于艾丽丝·默多克对小说情节的设置,读者可以清晰地整理出小说的各人物间主要存在着一种逃离与控制的关系。
不同于传统小说,默多克在《逃离巫师》中设置了四条并行情节线,主要围绕《艾格尼丝》杂志的收购与反收购展开,借由女主人公罗莎,将其他三条副线穿插于情节主线中,四条线同时进行,且每条线都有对应的“巫师”与受害者(控制者与逃离者)。同时,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关系均是围绕“巫师”密斯恰·福克斯而展开,那密斯恰·福克斯又何以为权力人物呢?
作为其他人物围绕的中心,密斯恰代表着权力的破坏性,他极力控制他人却从不感知他们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依据自己的理念来建构与他人的情感。作为核心性的权力人物,他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结合艾利亚斯·卡纳蒂的权力理论和小说细节,可得知“巫师”的首要特点是其神秘性,“神秘性是权力的中心”[1](P292)。因此,密斯恰利用其神秘性吸引他人并操纵他们的想象力,使人臣服于他,就如同陷入“符咒”中无力逃离。而他最大的神秘性集中于他扑朔迷离的双重性,他是邪恶的控制者,他人臆想的来源,也是被动的无辜受难者,在这个男人的体内“流淌着残忍和同情的源泉”[2](P208)。出于同情,他如上帝般爱一切生物,却又认为要想拯救这些脆弱的生灵,首先要摧毁它们;他将这种同情等同于爱,事实上,他的同情只是一种爱的戏仿。如此这般的核心人物,也同样深陷逃离-控制的矛盾体中,过度关注自己遭遇的痛苦,并被这种机制束缚其中。那权力人物又为何存在呢?
如上所述,权力人物自身也是被动的无辜受难者,他的受难经历造就他喜于控制他人,以此来平衡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大多数人物将自己的处境视为“迷惑”,自愿被置于迷惑中,以便让自己在面对困境时显得软弱无力,从而无须直面无序的社会现实,逃脱自己需承担的责任。他们的迷惑状态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精神上的无根性和虚无性密切相关,他们急切需求一个如神般强大的人物来控制他们,为他们思考、行动,他们则从中获取一种莫名的安全感,密斯恰正好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密斯恰的存在事实上是由周围人物的精神需求决定的。正如阮伟所言,“他(密斯恰)的权力是由他的‘造物’赋予的,是他们的受虐需求的产物”[3]。对权力的追逐与依附,除以上两种原因,小说中还存在另一种如安格尼斯·凯思蒙特小姐和波兰兄弟那般渴望握有权力,利用权力来立足社会扎实地位,以及如妮娜和卡尔文·布莱克这般无国界、无身份归属的影子人物,膜拜权力而甘愿成为它的精神奴隶,完全的精神堕落。
一、 追逐权力,以此平衡自我受难经历
密斯恰的个性特点如同他的名字(Mischa Fox)般充满矛盾,一方面,“fox”是种狩猎型动物,静候在隐蔽处等待它的猎物;另一方面,“fox”又是种被人类追逐的动物,想从人类的狩猎中逃离。所以,默多克并非简单地将密斯恰塑造成一个控制者、狩猎者,她同时赋予密斯恰一定的受难经历,使其成为大背景下权力的受害者。遭受了这个世界政治权力的滥用,相应地从精神上他渴求逃离这个纷乱无序的世界。
从小说的部分细节,读者可以发现无论是密斯恰还是波兰兄弟,其周围都环绕着一层东欧的神秘光环,他们均是东欧移民,因为战争而丧失家园。小说中的东欧是默多克想象中集中营的标志,所以,这些控制者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正由于沉浸于自己的苦难,他们将手中的权力看成一种保护,韦伊认为:“恶以受难的形式由一人传播给另一人”[4](P18),因为这是转移他们所受苦难最有效的方法。
密斯恰便是此类型的典型,即便手握权力,仍无法使自己从所受中解脱。小说第二十六章,在大海前,默多克将密斯恰内心面对世界的恐惧展露无遗。这里,大海场景有着特殊的意义,当密斯恰站在海边,安妮特从他的脸上读到的是恐惧与迷惑。“他盯着波浪,如同是被陌生动物逼到角落的人。恐惧与迷惑爬上他的眉间……”[2](P201)。这里的大海并不是平静、慈祥的,而是危险的,试图吞没人们,这个在密斯恰身后欲图吞噬人类的大海如同是我们这个充斥着苦难与斗争的暴力世界,因为权力而肆意杀戮,在这样的世界里,爱正在死亡或已死,让密斯恰恐惧又欲求逃离的正是这个满是诱惑却又凶残的世界。
默多克认为,在施展权力的过程中,控制者同受难者一样遭受着苦难,他们极力地追逐权力,却永远得不到他所渴求的对他人的完全掌握。正是他们的受难经历,使他们欲求在追求控制他人的权力过程中,来平衡或转移自己的苦难。
二、 渴望权力,以此扎实社会地位
小说中,逃离与控制主题见于人物关系中,权力人物并非天生,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工作来夺得相应的社会权力、性权力、毁灭权力等,以致最后将他们的“猎物”连根拔起。这些人物起初并不是控制者,只是无所依附的流浪者,懂得如何利用工作来猎取他人而使自己从流浪者的身份中解放出来,安格尼斯·凯思蒙特和波兰兄弟便是此类人物的典型。
同为东欧移民,不同于密斯恰,波兰兄弟对于权力的追逐却是为了使自己在陌生国度立足。起初,波兰兄弟刚到伦敦时,依附于罗莎,被其魅力所掌控。但是,随着他们在伦敦取得一定的社会肯定后,他们也就相应地掌控了性权力和掌控他人的权力,他们的身上具有一种危险的、无根的自由。通过对罗莎及其家人、朋友的一系列行为,波兰兄弟迫使他们的猎物丧失自己的本原而陷入麻木的无意识状态,从而将权力的主控权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再是依附者。
虽然安格尼斯·凯思蒙特猎取猎物的方式显得文明得多,但同波兰兄弟一样,她会有效地利用自己的工作来猎取权力,使她的受难者失去“根”,她代表着那种投机的小资产阶级,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机智,为自己铺平走向权力的道路。安格尼斯·凯思蒙特不知使用何种手段而经常被神秘地提拔,而后又通过从女性杂志上学到的粗俗性技巧,在工作上逐渐取代了雷博洛夫,并几乎诱使其成为她的丈夫。通过对工作这个工具的利用,安格尼斯·凯思蒙特除了获取相应的社会权力外,也夺得了性权力以及毁灭权力。
三、视权力为逃避方式,
以此沉浸于自己的臆想世界
第三类人物则将权力视为逃避偶然无序的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从而完全沉浸于自己的臆想世界,安妮特和雷博罗夫便是其中的典型。
从小说第一章安妮特辍学的细节描写和她的思维方式,可推断出安妮特对外界世界有着浪漫的幻想,有一种自我迷惑的奇特潜质,她的这种特质使她能够自我催眠,最终无法逃离自己的臆想世界。小说第五章中的“火车”的意象,是安妮特一生的主要意象,“这是一部控制着她的过去,也即将掌控着她的未来的机器”[5](P29)。旅途中,安妮特为窗外的现实世界所着迷,但她“从未踏出火车,躺在草地上,她甚至从未离开过车厢”[2](P58),无论火车驶向何处,她都被束缚在这个她臆想的火车上。她辍学后以为自己踏入的是现实世界,事实上,“她进入的世界虽然被视为‘生活的大学堂’,却是出奇的空洞,引领她经历一个压缩自我的循环之后,把她恰恰放回小说开始前她出发的地方”[5](P25),这个她臆想的世界一直跟随着她。
对于密斯恰的权力,安妮特毫无招架之力。她完全被其吸引,幻想着怎样“帮助孤独的密斯恰,带着一种深深的愉快,她感受到一种要拥抱他、安慰他、挽救他的强烈愿望和力量”[2](P199)。事实上,这不过是她的幻想,“一个人能把另一个人的灵魂从受缚状态解放出来,这只不过是一个年轻人太过天真的想法”[6](P80)。她对密斯恰权力的这种脆弱性很大程度上是她国际游民身份的产物。作为外交官的孩子,安妮特是在忙乱世界里成长的,不断地穿梭于不同国家,造就了她没有固定的国家意识。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她的家,但同时又不是,这个情感上的流浪者自此成为了爱做白日梦的女孩。她习惯性地依据自己对他人的认知来将他们与己关联,将人物置于自己臆想的戏剧情境中。事实上,她对密斯恰一无所知,围绕在密斯恰身上的神秘性吸引着她将自己与密斯恰联系在一起。小说第七章,在妮娜的裁缝店,密斯恰与安妮特初次相遇,但她对密斯恰的初次沉迷,却主要是通过镜子这个意象来完成的,这预示着安妮特如同是奇幻记中的爱丽丝。她从镜子中所获得的密斯恰的形象,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对密斯恰臆想的反射。从而,她对密斯恰的沉迷,事实上是对自己臆想的沉迷。如凯恩所言,“到底是密斯恰迷惑了安妮特,还是安妮特允许被自己对于这名神秘男子的众多臆想所迷惑”[7](P23)。
同安妮特一样,雷博洛夫极力逃避外部世界,想要躲进自我的臆想世界。一方面,他的住所是他的避难所,但这个自我世界却常常被人侵扰。他家附近的医院要扩建一个X光线透视室,计划推倒雷博洛夫花园的围墙,连根拔掉那棵古老的紫藤树,紫藤树“在英国传统文化中是温和和忠诚的象征,而医院是功利和实用的象征”[8](P74),从而安逸有序的过去被摧毁,混乱的未来正在眼前展开;另一方面,雷博洛夫与凯思蒙特的情感交错也反映了他对现实的逃避,对自我臆想世界的沉迷。他无法理性地正视与凯思蒙特小姐的情感,他的爱是“空洞抽象的,缺少对爱的对象的真正认识和真情实感”[6](P81),此人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符合他心底对浪漫的爱的臆想。起初,雷博洛夫“佩服她的细致”[2](P89),被其出色的勤奋所吸引,并开始找寻与其相关的任何事情,甚至是一些细小的东西,如她的教名,他幻想她的容貌,幻想与她接触的每个场景,但他的这些观察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凯思蒙特利用自己的神秘性主宰着雷博洛夫的情感世界,而雷博洛夫过分沉浸于自己臆想的世界,按照他的幻想在生活中接纳她。由于真实的凯思蒙特小姐完全不像他臆想的那样,而是“以一个独立于他的真实个体身份凸显在他的生活中”[6](P81),这让他无法接受,他别无选择只好逃离。事实上,令雷博洛夫着迷的并不是凯思蒙特这个肉体存在,而是她的香水,她抽完的香烟,她的红色奔驰跑车等一些外在的东西。他将女人视为一个个分离的部分而非完整的生物体。他活在自己的价值观世界里,为了逃避从凯思蒙特的臆想中惊醒,借由另一强大的巫师(安妮特的母亲)来试图逃避“真实世界”(凯思蒙特)对其的摧毁和冲击,但他的逃离确是“从偶然无序现实逃向虚无的未来”[5](P35)。
四、 视权力为庇护,权力的精神奴隶
面对权力,有人渴望拥有它,有人利用它的力量充当逃避方式,而有些人则视权力为庇护,仰视它,甘愿成为它的奴隶。妮娜和卡尔文是密斯恰的侍从,一个是他的笼中鸟,另一个则是他黑暗的一部分,作为其代理人来干一些肮脏的勾当。他们都是密斯恰彻头彻尾的奴隶,是其精神麻痹的受害者,陷入完全的精神堕落。
卡尔文自身便是灵魂完全被巫师控制的典型。小说中卡尔文被塑造成那种丧失家园及文化根后相应地使他人失去一切的人物,“卡尔文如同弥诺陶洛斯一样”[7](P29),是个由密斯恰创造的,来替他进行肮脏勾当的可怕怪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密斯恰多年以前就杀死了我”[2](P280)。卡尔文和密斯恰的关系一直是多数评论家困惑的问题。如苏利文所言,如若卡尔文同密斯恰是一体的,那这两种讽喻式的角色则代表着权力的双重特性,卡尔文如同是邪恶的弥诺陶洛斯,通过毁灭自我来强化密斯恰,他放弃自己本质的根,而变成黑暗的密斯恰的一部分,像他的影子般存在着。
起初,妮娜同安妮特一样迷恋着密斯恰,妮娜是个丧失家园、丧失国籍、丧失文化根一样的存在,无任何官方的存在证明,贫穷地生活着。密斯恰为其租了一间房,将她打造成小有名气的裁缝,让她有了存在感,从而使她陷入了对其痛苦的迷恋中。密斯恰曾送给妮娜一台缝纫机,如今早已陈旧、笨重,虽然她另有一台新的,却怎么也用不习惯。这台陈旧的缝纫机是妮娜与密斯恰控制关系的外在载体,妮娜无法适应新的机器,预示着她无力逃脱密斯恰的影响。妮娜在临死前,对自己的受难经历有过短暂的感悟,她是“奴隶、难民、丧失家园的人,是被人鄙视的人”[6](P86)。她在自杀前所做的噩梦,象征着她是权力的受害者。她发现自己被缝纫机的针齿里吐出的布匹绊倒,紧接着针齿开始狼吞虎咽,最初被吞食的是布,继而是妮娜。她发现布原来就是一幅“有着所有国家的世界地图”,而在所有的国家中她是无国籍者。妮娜是默多克刻画的“丧失家园的极端典型”[4](P44),“作者通过妮娜刻画了受难概念的社会效果”[6](P87)。
通过卡尔文和妮娜,读者可以认知到,丧失家园是最为可怕的社会疾病,它与权力人物的产生既互为因果,又相辅相成。
《逃离巫师》中密斯恰·福克斯这个如“巫师”般的权力人物总是试图去控制他人。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沉浸于自己的臆想世界,从而难以打破符咒逃离“巫师”的控制,所以,神秘的“巫师”在小说的整个框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类权力人物创造的根源与艾丽丝·默多克自身的二战经历息息相关,她在小说中对权力及权力人物问题的探讨,反映了她对希特勒集权政策的思考,映射了当今世界的政治局势。虽然默多克一再强调她书写的并非政治,但她自身对政治问题的思考,以及埃利亚斯·卡内蒂权力理论和西蒙·韦伊的受难观点,对其创作均有一定的影响。在小说中,她并非强调对权力的追逐是造成灾难的根源,而是展示人们在看清偶然无序的社会现实方面多么的软弱无力。她不断地在后续作品中转世、变体权力人物,主要为了反映现实社会中热衷于权力的人们及其依附者的共同状况。事实上,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巫师”,这个“巫师”是自己的心理需求创造的,是自己精神世界臆想的产物,唯有从关注自我走向关注他人,认清自我与现实,方可净化内心“恶”的存在。
参考文献〔〕
[1]Canetti, Elias. Crowds and Power [M]. London: The Viking Press, 1968.
[2]Murdoch, Iris.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M]. London: Vintage, 1984.
[3]阮炜.评《逃离巫师》[J].外国文学研究,1995,(2).
[4]Byatt, Antonia Susan. Degrees of Freedom: the Novels of Iris Murdoch [M]. London: Vintage, 1994.
[5]Sullivan, Zohreh Tawakuli. Enchantment and the Demonic in Iris Murdoch: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J]. The Midwest Quarterly. Kansas State College of Pittsburg, 1971.
[6]何伟文.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7]Kane, Richard Charles. Iris Murdoch, Muriel Spark, and John Fowles: Didactic Demons in Modern Fiction [M].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88.
[8]Wolfe, Peter. The Disciplined Heart: Iris Murdoch and Her Novels [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6.
〔责任编辑常芳芳〕
A Study on the Existent Essence of Power Figure in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XU Yuan-yuan1, WU Bing-yue2
(1.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237012;
(2. The Second Senior School of Lu’an, Lu’an 237005)
Abstract:In 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there exists common relationship among each characters, control and flight. But all characters center around power figure who has dual quality-controller and victim. Thus it tries to induce the reason of the existence of power figure and its essence, that is: It is the other characters that create enchanter. Their psychological needs make the enchanter. Power figure is the outcome of their fantasy.
Key words:“The Flight from the Enchanter”; power figure; dual quality; existent essence; fantasy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869(2015)06-0042-04
作者简介:许媛媛(1987-),女,安徽巢湖人,硕士,皖西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皖西学院2014年青年项目“《逃离巫师》中的权力人物问题研究”(WXSQ1409)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