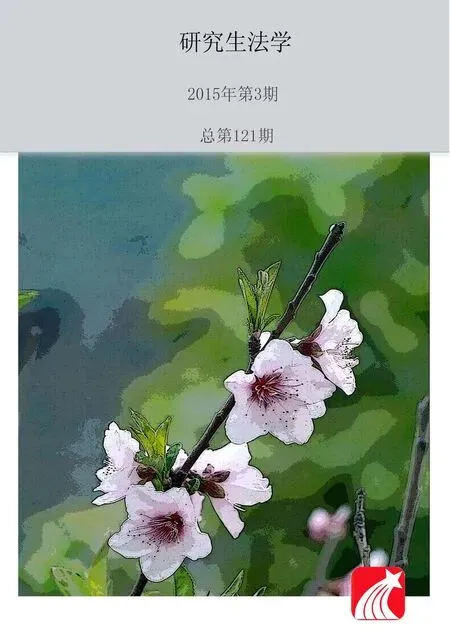《德国民法典》侵权编立法“实物中心化”研究——以SNS网络著作权侵权为出发点谈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著作权特殊保护
李 亨
*李亨,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比较法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100088)。
《德国民法典》侵权编立法“实物中心化”研究——以SNS网络著作权侵权为出发点谈我国民法典编纂中的著作权特殊保护
李亨*
*李亨,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比较法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100088)。
[摘要]作为中国民法典编纂之重要参考的《德国民法典》(BGB),在其侵权编立法中长期盲目坚持老旧、过时的“实物中心化”立场,难以对著作权形成全面有效的保护,甚至对其后德国著作权单行法的制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民法典在编纂的过程中,理应避免《德国民法典》就“实物中心化”对中国立法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将知识产权作为关注的重点,并根据其性质加以特殊保护,或以“标注原则”、“法定赔偿精确化”、“诉讼成本开支保留”核心,为知识产权保护之特殊立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德国民法典》侵权编“实物中心论”恢复原状法定赔偿诉讼费用
引言
近代历史上的民法典编纂运动最早在19世纪初发端,有些重要国家甚至在20世纪初乃至20世纪中期才完成了现代民法典的编纂工作,而作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胜利产物”,*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并且是为获得财产之重要保证的著作权,其相关立法的出现甚至还要早于民法典的诞生——例如法国“早在1785年即民法典诞生的近二十年前便制定了《关于使用原则和不审查原则为内容的制造标记和商标的法律》”作为知识产权立法的开端,其后更是“于1791年制定了表演权法和艺术产权法”明令保护著作权。*本段关于法国知识产权立法的两段知识性资料,见刘晓军:“知识产权法立法的典范——《法国知识产权法法典》”,http://bjgy.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3/10/id/82201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5月25日。
或许正因为知识产权法这种早于民法诞生的独立性,作为“巩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法律上奠定基础”*《拿破仑法典》,李浩培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译者序部分第1页。的根本,欧洲各国民法典似乎很少将著作权这种财产性质的权利纳入其框架内,即使在近代法律生活中,“民法曾长期规范着全部的个人私生活以及私人关系”,*[法]雅克·盖斯坦等:《法国民法总论》,谢汉琪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8页。著作权也难以在这种无所不包的规范中找到其应有地位,相应的则是民法典中无论是财产法还是侵权救济法,多以有实体或者可以实物化的财产,及有形财产所衍生的权利(如物权、债权)作为主要的乃至是唯一的保护对象,相应的法律条文亦以实体财产的存在形式或其可能的被侵害方式为基础制定。这一现象便是本文论述的核心——民法典救济法中的“实物中心论”。
一、 《德国民法典》诞生前的“实物中心化”
(一) 罗马法中的“物”论原则
“西欧绝大多数大陆国家——水泽遍地的低洼地国家荷兰,干旱的山区国家西班牙,还有昔日田园式的普鲁士,今日工业发达的德国,它们现在的法律制度皆以罗马法为基础。”作为欧洲诸国民法典编纂的最重要的参考之一,罗马法富有时代性的“物”论对欧洲各国民法影响极其深远,而罗马法中的“物”化正是其中之一。“恰如经验所证明的那样,罗马法的规范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法律体系不能比拟的,但它们可以运用于完全不同形态的社会里。”*本段引号内的两段内容,出自[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姚新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1页。
罗马法自订立伊始“就需要确定这样一个一般问题:将哪些外部世界的标的置于人的主宰和经济处置之下”,*[意]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而罗马法立法者指出,与此问题最相契合的首先是“物(res)”的概念——所谓的“物”,指的是“在具体的和特定的意义上是指外部世界的某一有限部分,它在社会意识中是孤立的并被视为一个自在的经济实体”——更重要的是,所谓的“物”“只能是这种意义上的物,即实体的物”。*[意]彼得罗·彭梵德:《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除此以外,为了就“物”及与其关涉的权利进行明确,罗马法发展了“财产”的范围,指出:“一个人的财产既可以表现为财物,也可以表现为债。对财物和债之间的区别是拥有和应当拥有之间的区别。”*[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然而,在罗马财产法中,无论是“物”(包括以物为基础的各类“物权”在内)还是“债”,其内核针对的都是实体意义的“财产”,与如著作权一样不以纯粹的物为基础的特殊权利全然没有关系,具有“实体”属性的“物”无需赘述,而针对罗马法中的“债”,尚不论其属于相对权的根本性质与著作权相差甚远,甚至连其产生的根源都无法不涉及任何和著作权相关的内容——“每个债或者产生于契约,或者产生于私犯”。*[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应注意的是,罗马法的契约以“实物”作为产生基础,剩下的三种产生方式均为程序性内容,出处见同页。值得一提的是,罗马法中堪称现代侵权法鼻祖的“私犯”所保护的权利,亦只针对人身权/父权/夫权及实体财产设立,这一现象直到优士丁尼时期仍未改变。*优士丁尼《法学总论》中所列明的侵权行为仅有四种,分别为盗窃、抢劫、非法损害和侵辱,其出发点只有两项即人身权及其附属的父权、夫权,以及以“物”为基础的财产权。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190~205页。故称罗马法为民法“实物中心化”的鼻祖及代表,并无不妥。而在涉及与著作权有关的问题时,罗马法这一能“解答最多的疑问,蕴藏着最多与迅速接触问题实质能力的思想财富”*[德]莱布尼茨:《著述与书信集》(第2组,第1册),柏林科学院出版1926年版,第50页。转引自江平、米健:《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的历史遗产亦不能为今人提供什么有效的意见与参考。
然而,将“实物中心化”归为罗马法的“错误”或“弊端”,对于罗马法的立法者来说并不公平,毕竟在罗马法产生的特殊历史时期,连著作权的物质载体——纸质出版物都寥寥无几,更遑论对其进行侵权。故罗马法的“实物中心化”有其合理的历史原因,不应对其过度苛责。毕竟,罗马的法学家只是对“我的财产-你的财产-每个人自己的财产”勾画出一个边界,*[法]菲利普·内莫:《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张竝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引言部分第1页。而这个“边界”内的国土该如何建设,本应当是各国法学家大书特书的问题。然而在此问题上,诸国仍然近乎于盲从地沿袭了罗马法的态度,将罗马法中的“实物中心化”承袭之甚至是放大化。
(二) 法国法及其承袭者民法典中的伪“实物中心论”
作为欧洲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对罗马法“物”化在民法典上的承袭贡献良多,在其第2编开头规定:“财产或为动产,或为不动产。”而作为法国民法典主要继承者的意大利法律及法国殖民地法律亦做了与法国相近的规定,如《意大利民法典》第810条规定,“所有能够成为权利客体的物品都是财产”,并按法国法的方式在第812条将财产分为动产和不动产。前法国殖民地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民法典在其第899条复制了法国法的规定:“财产,无论是有体的或物体的,均分为动产或不动产。”荷兰民法典则对法国法的具体规定进行了一定的补正,具体方法论是直接在民法典中规定“资产包括一切物和一切财产权利”(第3-1-1-1条),同时在立法中为“财产权利”增加“获得财产性有型权利”之来源的定义(第3-1-1-6条),而不仅仅将其如罗马法或法国法一样作为实体财产的附随,这样就明文确定了拥有同样性质的权利(如著作权)在民法典中的地位。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法国法及其继承国家民法典中规定了“实物中心化”,但这种趋同只能视为所谓的“伪实物中心化”,其并没有对著作权的保护产生不利影响。原因在于:1.虽然法国民法典并未直接将著作权列为“财产”的一种,但同时其也未明确地将著作权纳入民法典的调整范围中,因为在法国的立法史上,知识产权类法律的产生甚至要早于《法国民法典》,其在《法国民法典》诞生时已经独立地产生并存在;2.法国民法典采用了一般性条款的侵权法立法对侵权行为进行规制,其侵权法部门的中心条文即第1382条强调的侵权起于“使他人受损害”,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损害”必须出自民法典的具体规定(如“财产”)。正因为该法国法的救济体系相对而言范围较广,比较灵活,也未将针对实物财产的规定强行加于著作权保护中,故未对著作权被侵权人寻求救济造成太多不利的影响。当然,正因为此类规定是如此的灵活乃至于到了“空泛”的地步,故其亦未能就如何在民法典中建立著作权特殊保护制度提供必要的参考。
二、 《德国民法典》中实质意义的“实物中心化”
将“实物中心化”的消极作用扩展到极致的,恰恰是“现代民法采之立法例者十之六七”*改编自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初版序言部分内容。原文为:“现代民法采德国立法例者十之六七。”、“中国民法从中吸收的营养,也远较从法国民法得到的多”*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续)”,载《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4期;转引自中国法学网: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id=234,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5月30日。的《德国民法典》(以下简称BGB),这种消极影响不仅仅体现在BGB自身的法律规定中,甚至还波及到了德国其他特殊领域立法的法典(特别是《著作权法与邻接法》)。
(一) BGB侵权法总则性条文将著作权作为保护内容的纳入
关于哪些利益应受到侵权法保护并将其扩张到侵权法保护范围内,“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西班牙,即那些对侵权行为责任有一个一般条款的国家,不需要此等扩张,而是需要对责任加以限制。……但是,德国的情况则相反。”*[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上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不同于法国及其民法承袭国法典,《德国民法典》及其后的判例对于包括著作权在内的“权利”是否应被纳入其中的并由民法典进行保护的态度是明确的——“《德国民法典》中的所有权,仅指在物上的支配权。物,只包括有体物。……但权利都是财产,因此当人们在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意义上使用所有权概念时,通常也将它们包括在所有权之中。”*[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而“第903条规定的物之所有权作为一种全面的支配权和归属权只能存在于作为所有权人支配对象的有体悟之中。不过,绝对的支配权和归属权也可以以无形物作为对象,如专利权、著作权和商标权等……由于这些权利的无形支配对象主要是精神思想和观念,所以人们称之为精神所有权”。*[德]曼弗雷克·沃尔夫:《物权法》,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这大概是由于著作权法作为“特别私法”,“没有自成一体的规则。毋宁说,其以民法的存在为前提,本身仅仅规定了一些纯补充性规范”,同时其“与民法的划界”亦“缺少一种必要的、体系上的理由”。*[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而在侵权法总则条文(BGB第823条)中,著作权法作为受保护的“权利”的性质体现得更为明显,甚至称其去除了“实物中心化”的影响也不为过——“对于第823条第1款,尚可以考虑某些至少与物权类似的法律地位……另外,属于该项规定的范围的肯定还有著作权”。*[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债法分论》,杜景林、卢谌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0页。对于著作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是以存在对受保护权利的某种有过错的、违法的侵权行为为前提的,这其中不但包括《著作权法》的内容,还包括《民法典》第823条。*[德]曼弗雷德·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0页。
(二) BGB侵权界定与损失赔偿部分的“实物中心化”保留——兼析其对德国《著作权法》的影响
然而,虽然BGB第823条选择将著作权纳入其保护范围,但其在侵权法其他部分并未作出适应这种保护的改革,换言之,BGB侵权法除总则条款外的部分就权利保护问题所做的立法,仍然围绕着实物财产的具体特征进行,而这些立法不仅独立存在于BGB中,甚至还对德国《著作权法》(UHBR)立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些内容表现在:
1.侵权界定与所有权人同意的关系
德国民法典侵权编中关于财产侵权的规定,最早可追溯至整个德国私法体系“思想的基础”*参见[德]米夏埃尔·马丁内克:《德国民法典与中国对它的继受》,转引自《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对《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的康德主义法哲学中。在康德看来,依托人格为基础,一切事物均可以被划分为典型的人格和独立于人格的事物——“没有理性的东西只具有一种相对的价值,只能作为手段,因此叫做‘物’”,*[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德文版),第2章;转引自[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中文文献表述不一。这是“一种在我之外的物,并且可以在别的空间或时间中找到它”。*[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9页。这种“物”并不绝对等同于物权法上的“物”,而是一个广泛得多的包括所有财产及财产性权利在内的大集合,黑格尔将之解释为“跟自由精神直接不同的东西,无论对精神说来或者在其自身中,一般都是外在的东西”,即“某种不自由的、无人格的以及无权的东西”。*[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0页。
关于“物”,康德对其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分类:“我的”或“非我的”,其中“我的”是可以直接通过原始占有而取得、确定不属于任何人的“物”,“非我的”则不能通过占有而原始取得。对于“我的”与“非我的”,康德给出了极其明确的界限,即每个人只能处分“我的”,而不能对他人的“我的”进行处分,否则即构成侵犯。“这种互不侵犯属于别人的东西的保证,并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条文来使其生效,而是已经包含在一种权利的外在责任的概念之中,因为这种普遍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相互间的责任,是从普遍法则产生出来的。”*[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68页。而当事人若想要处分“非我的”,或将“非我的”变为“我的”,最常见的方式则是契约的方式,而“契约”最重要的构成便是“同意”。*[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9页。
康德的观点可被总结为:未经同意即处分他人之物即构成侵权,或按克尼佩尔语总结为:“没有人可以侵犯一个物,除非所有人就此同意。”*[德]罗尔夫·克尼佩尔:《法律与历史——论〈德国民法典〉的形成与变迁》,朱岩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页。这一观点被德国侵权法全盘接收:“财产所有人地位的特征在于,他可以对物任意进行处置,并排除他人的一切干涉(第903条)。对所有权人的各种支配行为的任何侵扰即构成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侵害财产所有权。”*[德]马克西米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齐晓琨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而著作权法则照搬了这一规定,特别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领域。原《著作权法》第15条第2款第2项规定作者享有“公共传播权”,其是指将作品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提供给公众,而使个人可以在自己选定的时间与地点接触作品的权利。“这一规定沿用了欧盟信息指令的规定,并明确规定在数字化网络中使用作品的财产权权能由作者本人享有。”*[德]曼弗雷德·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3页。新修订的德国《著作权法与邻接法》强化了这点,其明确规定:“在网络传播作品,须经权利人同意。否则,构成侵权。”*韩赤风:《德国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经典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
2.损害赔偿部分
由于知识产权本身属于“所有权”的一种(见上文论述),故对其保护原则适用BGB关于“侵犯所有权”的救济手段。BGB关于“侵犯所有权”的结果表述为“物的恶化、物的消灭或其他导致无法返还的情况”,*[德]曼弗雷克·沃尔夫:《物权法》,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对其中最常见的“物的恶化”(“物的损失”)的赔偿主要基于BGB第249条“必须恢复到假如没有发生赔偿义务存在的状态”的规定,并常常以支付“恢复原状为必要的金额”作为偿付手段。而非属于“物的恶化”的侵权则适用BGB第251条“只要恢复原状为不可能或不足以赔偿债权人,赔偿义务人就必须用金钱赔偿债权人”,这种赔偿方式不仅包括上述的“物的消灭”或“其他导致无法返还的情况”,还包括“未经同意的使用”——虽然在表面上看,对他人之物未经同意的使用不一定会直接减少物的市场价值,而“物的损害如果丝毫不导致其市场价值的减少就不存在赔偿”,但“一个物随时之使用可能性是有市场价值的……在确定可赔偿性损害时,应将这一点考虑进去。”*[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张新宝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7页。显然,未经允许的使用干扰了所有权人的正常使用并在实质上减少了物的价值,因此侵权人应当对此予以赔偿。但这种赔偿的范围“仅限于属于第989、990条的保护范围内的损害”,“因追索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原则上不应当计算在内”。*[德]曼弗雷克·沃尔夫:《物权法》,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BGB中的损害赔偿模式在德国《著作权法》中得到了完全的继承,即侵犯著作权行为发生时,主要以援引上述的BGB相应条款(N249-N251)作为赔偿方式,*[德]曼弗雷德·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页。而针对“未经允许的使用”这一特殊情况情况下则“特别可以要求非法使用作品的人支付正常的许可费用”,*《联邦法院民事裁判集》,第77卷,第16页及25页以下:Tolbutamid案;转引自[德]曼弗雷德·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83页。或者要求侵权人“返还通过使用他人利益所获得的收益”。*这一系列规定参见最新德国《著作权法与邻接法》第97条第2款规定。
三、 新媒体时代BGB“实物中心化”的弊端——以SNS网络侵权救济为核心
BGB诞生于一百多年前,无法否认的是,其立法的时代背景在信息爆炸的今日,其秉承的“实物中心化”原则对于发挥保护著作权这一传递信息并获得利益的主要载体的功用来说,实在显得有些太老旧了。BGB侵权编将著作权纳入其保护范围,却以完全围绕着实物财产所制定的立法对其提供保护,堪称是“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的表里不一。在SNS网络并不发达的过去,这一手段尚可以勉强应付著作权的保护问题,而在新媒体时代的今日,这种保护在愈发复杂的事实状态下愈发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 侵权认定的弊端——“同意”原则的过时
“实物中心化”以“未经允许的使用”作为认定侵权的主要要件,这其中也包括著作权在内。针对当事人通过传统媒介行使的著作权,这一要件对著作权的保护有着诸多的裨益,其最大的功用便在于同时可以打击来自于“剽窃者”和“其他侵权人”的多种模式*“剽窃者和著作权的侵权人都是仿制者;他们的区别在于,剽窃者试图将所复制的作品冒充为自己的作品,而侵权人之为侵权人,则只是因为试图侵占由属于他人的财产所产生的价值。”参见[美]威廉·兰德斯、理查德·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的侵权行为,而避免了以往只注重对剽窃者的打击,忽略了其他侵权行为的不足。*美国法采用了同样的立场,即:“就追究责任(不同于损害赔偿)而言,该法没有区分下列不同的复制者:明知侵权却用他人作品的故意复制者,自以为他人作品不受保护或者其复制行为可依法抗辩的人,以及不知道自己是在复制他人作品的人。简言之,侵权意图不是责任的必要条件。”参见[美]谢尔登·W.哈尔彭等:《美国知识产权法原理》,宋慧献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68页。
但在新媒体时代,这一认定要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原因在于新媒体时代的信息传递速率相对以往已经以几何级别在递增,为了让每个作为信息传递者的个人与这种速率适应,当代媒介法允许“一个人可以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放在网上,通常在标题下注明作者署名和版权标记……不久,数千或数以百万计的人就已经收到这个信息了”,*[美]韦恩·奥弗贝克:《媒介法原理》,周庆山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0页。而并不一定需要严格的著作权人同意,而当信息交流出现在Twitter或新浪微博*以新浪微博为例,如果在自身微博中使用了他人微博上的原创内容,但标注了规范的出处的,则不作侵权处理。参见黄洁:“独创性微博可享著作权不注明出处擅自使用易侵权”,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13-04/18/content_4383172.htm?node=5955,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5月30日。这样的SNS网络(“社会交往网络”)平台上时则更是如此。而就此问题,德国法的规定显然已经严重不合时宜,其规定甚至与新的欧盟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核心相悖。*欧盟法律已经对知识产权“唯有允许方可使用,否则构成侵权”的规定做了一定的改革,原因在于“如不这样,种种保护就将转化为只在保护普及作品的原来技术型的媒体的既得利益的手段,因复制技术和收发信息技术的普及给社会带来的便利全体私人却不得享有”。即为了公众享受信息普及的成果,不应局限于过去的老旧立法。参见李明德等著:《欧盟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9页。
更重要的是,这种“未经允许则不得公开传播”的规定在新媒体时代甚至并非著作权人自身所愿,盖在新媒体时代,以出版等传统媒介行使著作权本身带来的利益,可能已经远远比不上通过直接将原创内容放在个人网络平台账号上,以此来吸引“粉丝”,并在吸引粉丝之后通过广告营销等方式获利,从而让自身的著作权传播得更广、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著作权人所期望的。而未经允许但在发布的过程中标注了具体的出处,使得“粉丝”可以通过标注的信息关注著作权人,对于著作权人的利益来说有益无害。*这种利用SNS网络获益的方法被称为“职业用户”或“段子手”体制,参见曾鸣:“独家报道:段子手军团的崛起”,载《智族GQ》杂志2015年5月刊,转引自GQ官网:http://www.gq.com.cn/celebrity/news_1513315cd4428db8.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5年5月30日。故不加区分地将所有“不经允许的使用”作为侵权行为,实际上并不利于著作权人自身的利益。
(二) 损害赔偿问题的弊端——从赔偿额与追索权两方面谈起
BGB和德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赔偿额主要采用了三种计量方式,除了基本的“赔偿损失”外,针对著作权侵权最常见的赔偿方式为“合理的使用费”和“返还侵权所获利润”。这三种赔偿计量方法在传统知识产权领域基本可以覆盖损害赔偿的全部内容,但在新媒体时代针对著作权侵权的救济则显得有心无力,这主要由于:
1.许可费用难以计量
以“合理的许可费用”作为著作权侵权的赔偿方式,存在着难以计量的问题,这一点即使在传统媒介时代也早已有体现。“合理的许可费用”(或“使用价值法”)主要通过“考量一个意愿买家为获得版权作品所需支付的数额来确定”。*该原则使用的典范源自美国的DELTAK CORP v. Advanced System Corp.案,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确定了“使用价值法”,即通过严格分析过去许可使用费数额来计算损害赔偿额。延伸到很多过去的案子,它们都是以交易双方对相同或相似产品在过去协商中的价格为基准确定许可使用费数额的。审理DELTAK案的法院认为,合理使用市场价值可以通过考量一个意愿买家为获得版权作品所需支付的数额来确定。参见[美]凯文·本迪克斯:“版权损害赔偿:引入专利法中的合理许可使用费制度”,林小慧、仇沐慈译,载万勇、刘永沛主编:《伯克利科技与法律评论:美国知识产权经典案例年度评论(2012)》,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德国法的规定与之类似,但相对而言更为拘谨,参见下文注释47。但作品不同于实际存在的“物”,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作品的著作权都可以获得以许可费用为表现形式的直接金钱利益,换言之,并非所有的作品都能如“物”一样,拥有愿意为其支付许可费用的“买家”,例如学术论文便是如此——“在学术和科技论文这一独特的领域中,出版商支付使用费的唯一方式常常就是出版。因为,对于作者来说,论文得以出版,是专业进步和声望的关键。在学术领域,收益不是用美元衡量的。最有价值的收益是获得承认,因为,它常常影响专业的发展和教员的任期”。*[美]罗伯特·摩杰斯等:《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齐筠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0页。而在新媒体时代特别是直接发布于SNS网络上的作品,其依托著作权的获利方式与“许可费用”的“脱钩”更加常见,著作权人从一开始创作作品开始,便不再以直接的金钱利益为根本目的。其通过作品的获得的“利益”,早已经从传统的“许可费用”或“稿酬”之类,转化为影响力、粉丝数量等“间接收益”,这就导致了很多著作权被侵权人在寻求赔偿时,没有相应的“许可费用标准”作为参考,从而导致赔偿金难以计量。
值得一提的是,德国法对于“许可费用”的计量,还使用了一个有些莫名其妙的“比例计算”原则,这就进一步削减了被侵权人获得赔偿的可能。就此问题,德国柏林夏洛滕堡初级法院在其2003年第236C 105/03判决中,对“使用许可费用”的计算使用了所谓的“比例计算”主张,该案指出,“使用许可费用”的计算,应当综合合法使用人的使用数据与侵权人的使用数据比较进行,如在该案中,合法取得著作权使用的网站支付的使用费用为一百多欧元,浏览人次约为三十万人次,而侵权网站的浏览人次只有三千人,故赔偿金应按照合理使用费用乘以侵权浏览人次与合法浏览人次的比例得出。以此方法,该法院最终得出相关的侵权赔偿金只有1欧元多一点,同时又根据“微利不计”原则,直接驳回了当事人的起诉。*AMTSGERICHT BERLIN-CHARLOTTENBURG URTEIL. Aktenzeichen:236C 105/03. Entscheidung vom 17. November 2003;转引自韩赤风:《德国知识产权与竞争法经典案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3页。但笔者对这一判决完全持否定态度,理由在于合理的“许可费用”归根到底取决于双方的合意,而非其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利用该许可能达到多大的收益,并非著作权人需要考虑的因素。正如在合理许可的情况下,著作权人不需要为不同被许可人使用同一作品产生了不同效果,向结果相对不好者退还价金一样,侵权发生中法院亦不能因为侵权者的无权使用行为未达到合理使用人达到的结果而减少甚至免除侵权人的赔偿义务。
2.侵权获利方式非金钱化与“损失赔偿”“利益返还”操作难度的提升
使用“许可费用”进行补偿有着较高的难度,其他两种“实物中心化”体系下的赔偿方式亦是如此。如上文所述,由于新媒体时代,著作权人进行创作的目的本身不限于获得直接的金钱收益,而同理,SNS网络中的侵权人进行著作权侵权的目的亦不在于此,而同样在于粉丝数、影响力等“间接利益”,而这样的“间接利益”,是无法通过“弥补损失”或“返还利益”之类的传统补偿模式进行弥补的:首先,粉丝、影响力等“间接利益”无法构成著作权人的直接损失,毕竟这部分收益不同于金钱利益,不是通过著作权的授权使用可以直接获得的(其极大程度上取决于粉丝本人的主观心态),故不能直接断言侵权者无权使用了作品,就“剥夺”了著作权人获得粉丝、影响力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弥补”间接利益的损失也就显得难以操作;其次,以“返还利益”的方法进行赔偿也不太现实,即使这种以影响力为基础的“利益”可能确实存在,*美国法院在著名的“Napster案”中已经指出:“商业使用不需要显示出直接的经济利益……通过网络对于作品的免费共享显然使相关音乐作品的销售市场受到了很大影响。”美国联邦第九巡回法院:A & M Records, Inc. v. Napster, Inc., 239 F.3d 1004,(9th Cir.2001);转引自陈剑玲编译:《美国版权法案例选评》,对外济经贸易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0页。但将这种间接利益进行“返还”实在太难操作:首先,法院包括网站自身均没有足够的证据来判断哪些“粉丝”是因为被侵权人无权使用的作品才关注侵权人的——即使有相关证据可以确定无疑地判断一些“粉丝”的确是因为喜欢被侵权作品才关注侵权人,如果将这部分粉丝的“关注”作为“所获利益”“返还”给被侵权人的话,除了技术上难以操作外,更重要的是可能产生伦理及道德的风险——“粉丝”数量能产生间接的利益不假,但“粉丝”账号之后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人,不顾这些人的意愿(有的人甚至本身就更爱关注内容繁多但合法性不强的“营销号”而非原作者),肆意将他们的关注作为“利益”在不同群体间分割(哪怕这种分割是出于侵权赔偿这种法定理由),恐怕不符合民法典编纂中有关“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
3.维权难度加大与“追索权”自身范围的受限
除了以上原因,新媒体时代侵权难度的减小、侵权频率的增加,这一系列因素都导致了被侵权人维权难度的增加。不同于对“物”的侵权多发生在物的所在地即侵权人及被侵权人的共同所在地,SNS网络中对于著作权的侵权,对于很多被侵权人来说是“异地侵权”,高昂的车马费和律师费往往使其对维权的主张望而却步,而“实物中心化”对于“追索权”的限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被侵权人维权的困难。“实物中心化”将对于所有权的赔偿限制在“所有权”自身的法律范围内,而“因追索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原则上不应当计算在内”(见上文注释34)。这就从根本上断绝了著作权人要求侵权人支付其因为异地起诉所需的交通费、旅费以及律师费等费用的可能,从而在大大增加了维权人维权成本的同时大大地降低了侵权人的侵权成本,使得侵权人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侵权而不用担心支付高昂的赔偿金。
(三) 德国学界对“实物中心化”的改革和中国现行法与BGB“实物中心化”的引入
对于侵权法“实物中心化”存在的诸多问题,德国法学界的有识之士早已声明了对其进行全面改革的基本立场。如在2009年问世的《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DCFR中),主编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教授便极力避免以往的BGB中的“实物中心化”对著作权的保护不力,明确表示该民法典草案针对损害赔偿的内容“不适用于著作权法”,*欧洲民法典研究组、欧盟现行私法研究组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5~7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72页。并指出著作权法应当由各国针对知识产权的特殊立法进行保护。
然而,我国现行法在制定的过程中,似乎并未考虑德国学者的合理建议。201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在第2条明确地将“著作权”列入侵权法保护的权利体系中,而对其的救济仍然是老旧的“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偿损失”(第15条,《著作权法》就侵权赔偿的规定采用了同样的立法,见《著作权法》第49条)等,全然不考虑著作权作为无形财产权的特殊性。而在2003年左右出台的我国第一批民法典草案中,对于侵权认定和损害赔偿的内容同样照搬自BGB的“实物中心化”条款,*参见王利明、杨立新:《中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侵权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页起;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24页起。这不得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
但上述内容不表示我国法律没有任何优于德国法之处,就追索权的问题,我国现行法有着明显优于德国法律的规定。德国法原则上不允许将“因追索权利而发生的费用”作为侵权赔偿,但我国在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修正了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6条规定:“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这是我国立法与前人相比可喜的进步,在未来的民法典立法中应予以保留。
四、 以BGB为鉴谈未来民法典编纂中对“实物中心化”的改革
由上描述可以得知,以BGB为代表的侵权法“实物中心化”理论,对于著作权的保护特别是新媒体时代的著作权保护弊多而利少,其老旧过时的观点已经无法对现代社会的著作权提供全面的保护,而沿袭了这种立法的我国现行法律某种程度上存在着相同的问题。故在未来的民法典编纂中,应对“实物中心化”原则从“侵权认定”到“损害赔偿”的全部内容做出系统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
(一) 对SNS网络中的侵权责任的认定应以“不标注”为原则
“实物中心化”就信息网络传播权所制定的“未经同意,不得使用”原则并不符合在保护著作人权利基础上提高信息传递速率、保障公众利益的原则,也未从真正意义上符合著作权人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对这部分内容进行改革。具体的改革手段为将“不标注”作为SNS网络著作权侵权的认定要件,即不标注原作者身份,或将原作者身份标注为“佚名”、“来自网络”等方式,以及标注了原作者身份,但未能以“@”*SNS网络一种特殊的信息交流形式。标注“@”后,被“@”的著作权人可以得知自己作品被转载的信息,其他用户也可以通过点击“@”的内容直接跳转至著作权人的个人页面并予以关注。方式链接至著作权人本人页面的,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但标注了原作者身份,并以“@”方式注明原作者个人主页所在的,不构成侵权。
应注意,这种认定标准应仅限于已经在SNS网络上公开的作品,对于其他未公开的作品,应当立场坚定地坚持“公开使用作品即构成侵权的原则”,*对此可参考《日本著作权法》第30条“为私人使用的复制”。即使以“帮助向公众进行传播”这样的提供行为为理由,也构成对“传播可能化”的侵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日]田村善之:《日本知识产权法》,张玉敏等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455页。此外,民法典在改革“实物中心化”在侵权认定方面的弊端的同时,不应连同其有效用之处一起“改革”,而应予以保留。例如“实物中心化”原则在认定侵权过程中不区分侵权人主观心态的理论就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使得被告不能因为他不是有意复制或者他用的是第三人的作品而他不知道该作品是第三人非法复制而来的,作为借口来逃避法律责任。*[美]乔纳森·罗森诺:《网络法——关于因特网的法律》,张皋彤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对于“违反版权所有人之排他性权利的任何人”,都要追就其侵权责任。
(二) 数额更为精确的“法定赔偿”制的引入
BGB“实物中心论”就损害赔偿的三项主要方法:“弥补损失”、“许可费用”和“返还收益”在新媒体侵权中难以操作,因此需要引入一种替代性的方法方便当事人弥补损失,这便是针对著作权保护设定的“法定赔偿”。为了确保版权主体遭受侵权后,能够得到赔偿,以美国版权法为代表的多国法律确立了法定损害原则。这一原则旨在用法定损害代替其他难以估量的损害。*[美]阿诺德·卢茨克:《创意产业中的知识产权——数字时代的版权和商标》,王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就此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已经走在了德国之前,其第49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但这一规定只有上限,没有下限,不利于著作权人利益的维护,因此我国应就“法定赔偿”效仿美国设置一个数额不低的下限,*美国法规定:“就涉及任何一部作品的所有侵权行为而言,著作权人可以选择法定赔偿金,而不是实际损害赔偿金和利润的赔偿方式……法院应当在不少于750美元但不高于3万美元的范围内裁定合理的法定赔偿金。”参见《美国著作权法》第504条C款。这样在保护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侵权人的违法成本,从而使法律可以对其侵权行为产生一定的遏制力。
(三) 诉讼开支支付的保留
版权补救措施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胜诉方可以要求败诉方支付相关诉讼费用和开支。*[美]阿诺德·卢茨克:《创意产业中的知识产权——数字时代的版权和商标》,王娟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页。在新媒体网络侵权中,即使有了“法定赔偿”的保护,被侵权人获得的侵权赔偿总额,相对于高昂的律师费、异地旅费、诉讼费来说,仍然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我国应当在未来的民法典立法中,继续保留现有司法解释中有关被告方承担原告方“合理开支”支付的要求,从而在以“法定赔偿”保护被侵权人侵权所得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被侵权人的不当损失,并提高侵权人的侵权成本。从而使得民法典可以真正意义上抑制此类新型侵权的出现。
结语
朱子有云:“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朱子语类·朱子五》卷一百八。法律是一种实践的艺术,必须紧密追随时代的发展,作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有力改革。对此,笔者并不妄言自己提出的立法意见能够万无一失地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毕竟“法立于上则俗成于下”*(宋)苏辙:《河南府进士策问三首》之一。,它不可能给每个人以方便,“但如果它有益于全体和大多数人,我们就该满足了”(李维语)。
(实习编辑:冯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