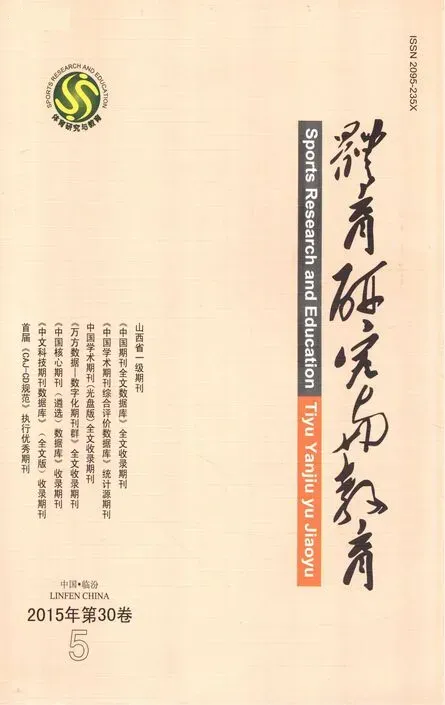具有中国特色的振兴“三大球”之路
——回应刘建和教授的问题
黄 璐
1 问题意识的重要性
评价一名优秀学者的重要标尺,不仅要看其专业知识和方法学习的多寡和深浅,更要看其批判性、创新性和思想性所能达到的高度。小到学者个人,大到国家层面都是如此。一穷二白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思想和理想。在现有学术评审体制与僵化思维中,一篇独立的学术成果必须要有结论或建议,或者说,没有解决问题哪能算作研究成果。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提问题”不能作为一篇独立的学术成果?“提问题”不是随便抛出“问题”,而是提得出“像样的问题”,必须具有超强的学术敏感和问题意识,要沉寂在学术的海洋中不能自拔,失眠销魂,痛苦难堪,坠入到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这一“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沉状态,同时,必须建立在海量的学术阅读和多年的实践工作的基础之上,在大量冒出来的问题中甄别出“真问题”“好问题”并针对问题提供知识、经验和思想储备。
张力为教授的观点“研究方法总是使我们处于科学研究的十字路口”[1],笔者深表认同,更无反驳之意。如果有学者提出“问题意识总是使我们处于科学研究的十字路口”或许相得益彰,更为完美。笛卡尔有句名言:“方法学的知识是最有用的知识。”爱因斯坦则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体育研究中好的想法、好的问题能否获得应有的尊重,避免出现体育论文“Idea”事件[2],挽救这些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好观念”“好点子”“好想法”不“岁月无声”地被一些“不劳而获”“别有用心”的专家们“拿去”发表。
刘建和教授的《综述与诘问:具有中国特色的振兴“三大球”之路》一文(下简称《诘问》)即是一篇专门提问题且独立成章的学术成果,值得作为案例进一步学习讨论。刘建和教授在文中谦逊的呼吁,“限于笔者的能力,本文只能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相关情况进行诘问,至于对这些问题的求解,就全赖读者诸公了”[3]。引不起后续讨论的学术成果是苍白乏力的。笔者才疏学浅,斗胆以学术争鸣的形式,对刘建和教授的诘问进行评论性回应,期待学友们后续的批评与评论。
2 振兴三大球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诘问》中追问“人们所说的‘振兴三大球’究竟要振兴三大球的什么?”列出四个选项,即健身功能、娱乐功能、产业功能、“为国争光”功能,其中“为国争光”功能为笔者根据《诘问》中对于“振兴三大球”内涵的所指得出的,即“特指怎样在奥运会、世界杯(世界锦标赛)、亚运会等重大国际赛事中争金夺银”,这里将“振兴三大球”的“争金夺银”效应表述为“为国争光”功能似乎更符合国民的认识。随即,《诘问》明确了竞技体育概念的讨论范畴,“意即在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范畴内进行探讨”。目前学界一般认为,竞技体育分为高水平竞技体育和“人人参与竞技”,这点毋庸讳言,但问题是以商业利益为追求的职业体育也属于“高水平竞技体育”的范畴。如果不做必要的区分,在竞技体育的价值认识和主题讨论中就很容易产生分歧,尤其是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上随意定义“体育”概念的所指,以“偷换概念”的写作手法达到论证的目的。
高水平竞争性体育分为职业体育(Professional Sports)和精英体育(Elite Sports)。现代奥运会秉持更快、更高、更强的精英体育精神、国际足联世界杯则以一贯之商业逻辑,这两个概念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对立关系,二者之间的重叠部分、联系与互通性较大。(详见拙文《大型运动会真的太多了?》,发表于《体育学刊》2012年第1期)令人欣慰的是,更多的媒体和学界同仁将二者区分开来,犹如“身体教育”(Physical Education)和“竞技”(Sports)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不能简单地称为“体育”。陈玉忠教授认为,“职业足球和国家足球的整体水平属于两个层面的问题。两者有联系,更具备相对的独立性。‘恒大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软实力,激发了社会正能量,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4]。
《诘问》认为“竞技体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比赛中争金夺银,这是竞技体育的本质规定”。可以说,《诘问》中的竞技体育概念是指精英体育,也就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理念,侧重于在高水平国际或区域性比赛中争金夺银,赢得“升国旗、奏国歌”的“为国争光”与“国家认同”效应。竞技体育当然要继续搞下去,要向“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一“顶层设计”和人民期待的总体目标坚定前进。不仅要继续推动发展精英体育,加强国家认同与意识形态领域建设,更要大力发展职业体育,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实现经济增长与精神生活双丰收。具体到精英体育领域,不仅要保持目前中国精英体育优势项目的竞争力,即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举重、射击等“软金牌”项目,更要挑战自我,勇攀高峰,向田径、游泳基础大项和团体项目金牌发起猛烈冲击,扩展奥运会金牌大项的覆盖率,在保证“软金牌”的前提下,拿更多的国际高竞争力项目金牌。
这里的“软金牌”是指跳水、乒乓球、举重等这类国际上普遍不受重视,业余性比较强,市场价值比较低,国际整体竞争偏弱的项目。中国凭借“举国体制”优势和专业运动员后备力量保障,去攻关这种“软金牌”项目,在短时期内可以拿到更多的奥运金牌。抄近路,走捷径,符合中国讲实用的传统,在意识形态宣传上达到为国争光的社会效应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效果。体制内学者将这条通向成功和荣耀的捷径视为中国特殊历史背景下制度设计、智慧和努力的结果,或者换一种说法“扬长补短是我国奥运争光战略的必然选择”[5]。在万分艰苦的国家成长年代和特殊的历史背景环境中,凭借有限资源堆砌逐一攻克“软金牌”项目,建立中国奥运金牌伟业,这本身就是新中国发展史上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里无意否认中国精英体育取得的突出成绩,而是提醒学友们以及“自我感觉良好”的相关人士,这个整体“金牌”业绩的结构和成分,在国家大力倡导结构化转型的今天,看清局势,明辨是非,为“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推动工作”[6]提供认识基础。
《诘问》中借用搜狐网的观点来解释自己对金牌观的理解,对“需不需要金牌”问题的诘问,如果向前推进一步,“需要什么样的金牌”或许更能发挥“诘问”的社会反思效果。“国民不需要金牌?”这是一个伪命题。有金牌总比没有金牌要好,51枚金牌总比38枚金牌要好,至少这是一种生活常识。关键是这些金牌的“含金量”是否得到国民的认可。拿19枚奥运“软金牌”换一个世界杯足球赛冠军,国民会不会答应这种“以多换少”的亏本买卖,相信大部分国民会同意。这是一个“天马行空”想象的“情形”,在现实中不会存在。举这个例子是要形象说明,国际高竞争力项目金牌“含金量”和影响力的重要性。
如何理解国民“需要什么样的金牌”的真实诉求,必须从新媒体舆论生产机制谈起。在新媒体冲击传统媒介生态的大变革背景下,“街头巷议”的人际传播模式早已失去舆论市场,传统媒体逐渐丧失舆论主阵地,取而代之的是新媒体舆论生产机制。新媒体技术力量和传统媒介势力激烈碰撞;媒体从业者的知识结构和职业素养良莠不齐;“新闻叙事”难以客观反映社会舆论的事实诉求;媒介改变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力日趋提升。这些已成为新媒体舆论生产机制的特性。
笔者曾在“北京奥运会国际媒体政治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研究中发现,在北京奥运会比赛周期时间里,伴随比赛进程以及中国金牌榜第一的事实,中国主流媒体全面飘红,好评如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国际媒体出现了大量妖魔化中国和嘲讽中国竞技体育的言论。一些国际媒体运用新闻议程设置(时间轴)和整体宣传战略(空间轴)对中国国际形象和对外舆论环境展开了别有用心的舆论“攻势”。在人权、西藏问题、开幕式“假唱门”、何可欣年龄争议、刘翔退赛事件、中国唯金牌论等事件上发表了大量负面言论[7]。与此同时,自由放任的新媒体舆论系统炮制出大量负面言论,新媒体传播平台建构的公共生活形态逐渐形成。这些悲观消极的言论极大消解了主流媒体舆论场的正能量,模糊了“真”问题与“假”问题、真实诉求与“别有用心”的舆论攻势之间的边界(这一时期相应提出了“两个舆论场”概念)。近年来,党和政府加大了对互联网传播领域的整治力度,以期开创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新局面,伦敦奥运会周期中国精英体育面临的新媒体舆论环境由此获得改观。应该看到的局面是,不仅中国奥运金牌成为网民“吐槽”泄愤的话题,成为国内外某些媒体“捕风捉影”制造“标题党”的工具,成为西方媒体“羡慕嫉妒恨”炮制负面言论的来源,延申到中国的教育体制、医疗环境、文化艺术生活、突发性公共事件等问题也成为了无控制言论的攻击对象。体育界应该看到这一点,并要适应这样一个认知与体验的过程。这是从事体育行业的人锻造“强大的内心世界”和自信心成长的必经之路。这里有理由相信在里约奥运会期间,体育界再次面对诸如刘翔退赛事件中“网络推手”策动的“别有用心”言论,就会自信并坦然面对了。
诚然,为中国奥运“软金牌”辩护不能过于狂热,体制内人士更不能陷入“自我鼓吹、自我陶醉”的境地,关注一些合理中肯的批评,避免被沾沾自喜的情绪遮住双眸,羁绊前进的脚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面对网络世界如潮的批评,也并非毫无根据,空穴来风。在国家体育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坊间主要针对“为什么国际主流的职业体育项目我们都不行”这一问题发出诘问,国家队比赛成绩遭人诟病,职业市场培育也没能做得更好。伴随中国应对发展国际高竞争力项目的持续萎靡状况,觉醒的中国人民在网络世界表达了尖锐的批判观点。中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世界接轨步伐加快,互联网服务迅猛发展,在今后国家边界逐渐开放过程中,这种参透玄机的全民认知和维权意愿将越来越强烈,将对体育“举国体制”的绩效结果形成更广泛、更深刻的诘难和冲击。凭借“软金牌”项目的积累,寻求“举国体制”继续存在的社会合法性这一固定套路,来搪塞国民日渐拔高的体育赛事观赏和精神文化诉求,今后是行不通的。中国竞技体育“金牌”结构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因而转向足球、篮球、排球、网球、田径、游泳等国际高竞争力项目来谋求重大突破。
精英体育的主要目的是尽全力获取优胜,这点毋庸置疑,这是由精英体育的本质决定的。《诘问》中认为,“竞技体育作为人们有目的的活动,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比赛中争金夺银,这是竞技体育的本质规定……在高水平运动竞赛中获取优异成绩,是振兴三大球的主要目的,追求金牌,是我们永久的梦想,对此不必羞羞答答。”笔者认同这一观点的前提条件是,《诘问》中所指的竞技体育概念是“精英体育”,而非“精英体育”和“职业体育”二者的混合体。虽然说尽全力获取优胜,并保障比赛的精彩程度是“职业体育”赢得收视率和商业价值的前提条件,但凭此就将“职业体育”的主要目的定义为“争金夺银”,就勉为其难了。在思维认知和具体工作中区分“精英体育”和“职业体育”的关系,不仅是体育理论研究是否严谨的客观要求,也是体育实践活动中自觉谋划推动工作的必然要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就是有力的证明,其中第三章“改革完善职业足球俱乐部建设和运营模式”主要针对“职业足球”发展的具体部署,改革任务设计为“促进俱乐部健康稳定发展;优化俱乐部股权结构;推动俱乐部形成合理的人才结构”。第八章“推进国家足球队改革发展”主要针对“精英足球”发展的具体部署,改革任务设计为“精心打造国家队;完善队员选拔机制;提高服务保障能力;加强教练团队建设;统筹国家队与俱乐部需求”[8]。此外还有“校园足球”和“社会足球”领域的具体改革发展部署。如果将精英足球即“精心打造国家队”层面的“争金夺银”价值取向,渗透到职业足球、社会足球、校园足球发展的价值定位中,就是一种价值与功能的错位,也是一种社会功利观念的突出反映。竞技体育不仅仅是“争金夺银”,还蕴涵着更丰富的意义生成和价值追求。这就要求体育界和学界别耍“偷换概念”的把戏,抛开“部门利益”和私利杂念,把不同概念对应的价值和目标说清楚,正确引导社会和国民看待体育及其多元目标价值,“宣传引导群众客观认识足球(三大球)现状,建立合理预期,理性看待输赢”[8]。
《诘问》中“增强人民健康”这个提法有待商榷。毛泽东同志提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中的“体质”可以“增强”,“健康”问题似乎无法“增强”。健康作为一种机体内平衡的状况(身体、心理、社会适应三维),说“促进”或“保持”或许更贴切。比如医学研究和高质量医疗服务能够促进人民健康,合理饮食能够促进人民健康,良好睡眠能够促进人民健康,心理调适能够促进人民健康,休闲、旅游、养生活动能够促进人民健康,保持正确与适量体育活动同样能够促进人民健康。健康问题是一个涉及到社会全方位的系统性问题,正如《诘问》所言:“不仅仅是由体育事业可以单独解决的……不要有意无意放大体育的功能。”这一问题可以归结为上述“竞技体育”概念的认识分歧问题上,也可以扩展为对“大体育观”的概念理解上。“大体育观”属于一个“口袋”概念,体育界将家族相似的概念或者需要扩大业务范畴的现象均可纳入“大体育观”的发展轨道。《诘问》中认为,“把人民健康的重担全部押在体育(更不要说竞技体育)身上,是很不公道的。‘增强人民健康’固然是体育的最重要目的”,这里的“体育”可能所指“大体育观”这个无所不包的“口袋”概念,也可能专指“全民健身”。全民健身对促进人民健康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发展精英体育、职业体育的最主要目的是“促进人民健康”就值得商榷了。有效讨论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清楚概念,对于长期奉行大尺度“体育”概念理解的体育界来说,做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3 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体制
将体育“举国体制”置于特定历史背景与资源约束环境中考虑,进而获得国人的宽容和理解,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力避“休克疗法”,慎重选择渐进式改革伟大道路的必然选择。“举国体制”是计划经济的特有产物,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举国体制”的“举国”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如果当下集中体育部门的力量侧重发展精英体育是一种“举国”形态,如果凭借国家财政投入和彩票公益金的支持是一种“举国”形态,那么正如一些“似是而非”的辩护,欧美发达国家实行的也是“举国体制”。例如,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The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是澳大利亚政府的法定主管部门,依据1989年颁布的澳大利亚体委法案运行,负责澳大利亚体育发展事务,并提供政府资金支持与分配事宜[9]。难道澳大利亚实行的体育制度也是“举国体制”?站在体育人的立场,为体育“举国体制”取得的功绩辩护的急切心情可以理解,这样“盲人摸象”式的理解问题却无助于论证观点,也无法产生更强的说服力。再如,《诘问》中提醒我们,“请大家不要忘记,三大球的辉煌较多的都是在举国体制支持下造就的。”按照这一推理逻辑,李娜的单飞、丁俊晖的社会成长所取得的体育成就,是否能够说明失去举国体制的力量支持,中国竞技体育也能发展得更好。《诘问》中列举高考制度这个案例不合时宜,比如医疗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生育制度同样也实行了几十年,套用任何社会改革领域都能说得通,但不具有可比性。
《诘问》暂且搁置“举国体制”的历史评价,将目光聚焦于当下局势和未来发展,是一个很好的思路。《诘问》中指出,“更重要的似乎是考虑举国体制是否还有延续的价值及价值有多大;举国体制究竟还能为三大球的振兴发挥什么作用?”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精英体育和职业体育制度,具体行不行得通暂且放一边,至少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伟大实践的内在要求。至于《诘问》中提到的“在中国三大球职业化进程中存在的‘市场、政府双失灵’的现象”,体育界扪心自问,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轰轰烈烈搞了20年的职业体育联赛,乃至发展至今的职业联赛市场形态,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化、市场化吗?恐怕“贼喊捉贼”的成分更多一些!卢元镇教授的一席话切中肯綮。“在体育行政垄断向协会制改革的实体化进程中,始料未及的是,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既可以行使行政职权,又可以经商,从而导致它原来能做的继续都能做,而原来不能做的如今也都能做了。[10]”
《诘问》中提出“联赛水平的提高与国家队水平的提高何以同步”,这是古代蹴鞠发源地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同样也是现代足球发源地英格兰面对的忧愁烦恼。这种现象反映了职业体育和精英体育两个概念体系的不同价值取向。以足球运动为例,就存在职业足球和精英足球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践形态。世界最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聚集在欧洲足球五大联赛中,由此形成了世界职业足球的核心市场,而英超、西甲、意甲联赛无疑是世界职业足球的领头羊。吊诡的是,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国家队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中惨遭淘汰。传统足球强国英格兰、西班牙、意大利队的意外出局并非偶然事件,伴随运动员跨国流动的全球大趋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球员赴海外高水平联赛踢球。这些球员在海外联赛锤炼出过硬技能之后回国效力,有效提升了本国精英足球的整体竞技水平。例如,巴西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英格兰对阵乌拉圭的比赛,英格兰首发球员全部在英超联赛踢球,而乌拉圭首发球员全部在国外高水平联赛踢球,球星对球星,整体竞技实力比较接近,英格兰队输球自在情理之中。这一例证说明,职业足球以追求商业利益为发展目标,而精英足球除了顾及商业利益,主要还是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炮制出的国家对抗氛围和虚拟战争神话。如果说,英超、西甲、意甲联赛等职业足球是以商业利益为核心,那么世界杯足球赛、亚洲杯足球赛等精英足球则是以国家荣誉为核心。应该说,一个国家职业联赛发展水平与这个国家足球队竞技水平之间不能简单划等号。如果简单一点来理解,“联赛水平的提高与国家队水平的提高何以同步”的问题,是在国家地域开放和全球化移民时代如何处理好运动员跨国流动中本土球员与外籍球员培养及贡献(联赛经济发展方面和国家队比赛成绩方面)的关系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研究者撰写的《英格兰为何失败》一文[11]或许揭开了谜团。该文谦逊地认为是对James Walvin《足球和英国的衰落》一文观点的扩展与更新,无法承诺提供一些全面和明确的解释,而是为英格兰国家队的失败提供了一些社会学解释。文中强调影响英格兰国家队成绩的五大因素是足协、教练员、本土球员、媒体、球迷。更详细一点来说就是,英国足协以及英国足球的制度结构和随之而来的英国足协聘请优秀国家队教练的困境、英国本土教练员的整体素质、选手的地域性特点(本土球员问题)、无规矩的英国媒体以及球迷群体的作为。笔者认为中国足球目前的处境也类似。中国足协从“举国体制”合法性衍生出的理直气壮的“管办不分”,到打着体制改革和“顶层设计”旗号且变相实行的“管办不分”,离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2];历届中国男足主教练绝大部分聘请外籍教练;高水平本土球员和后备球员培养捉襟见肘;媒体和球迷以嘲讽谩骂中国男足作为一种情绪发泄和消遣方式。
《诘问》针对联赛和国家队水平的同步提高方面归纳了若干问题,“现在的联赛体制存在先天性缺陷?训练不够、国家队和俱乐部利益平衡不够、政府放开规制仍不够?”方方面面的诘问,与《英格兰为何失败》一文的观点和全面深化足球改革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一致的,是涉及到整体性的问题。同时,《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对于全面深化足球领域改革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把握,符合足球改革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体现出足改方案具有的较高政策水准。《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针对全面深化足球改革发展的不同方面,具体划分为职业足球、校园足球、精英足球、社会足球等改革工作领域。对每个改革发展领域应该达到什么层次水平,也指明了具体的目标方向和改革思路。足改方案提纲挈领式的主要目标即实行“三步走”战略能够充分显现。“形成足球事业与足球产业协调发展的格局……女足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足球成为群众普遍参与的体育运动,全社会形成健康的足球文化;职业联赛组织和竞赛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国家男足进入世界强队行列。[8]”这是对足球改革发展的一种“全面部署”,也是一种“全面工作”。置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中,对足改方案“全面布局”的国家战略思想便能理解[13]。《诘问》中所言,“《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说的是足球,对篮球、排球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笔者将理解范畴扩展为整个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生态,同样也能说得通。
在“四个全面”精神引领下,针对全面深化体育领域改革的发展问题,党中央和相关部委配置了一揽子政策文件,冀望达到综合治理和整体推进改革目标的良好效果;针对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42条“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中指出:“强化体育课和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体魄强健。[14]”;针对体育产业与消费领域的改革治理问题,国务院制定下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针对足球运动这一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体育项目,全力推出“校园足球计划”和《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足改方案“顶层设计”与中央“四个全面”改革精神一脉相承,中国体育步入全面协调发展的“新常态”[13]。
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针对不同工作领域建立的多元发展目标可以看出:不仅精英足球和职业足球要发展好,学校足球和社会足球同样不能掉队。放到“大体育观”的层面来说,就是“新常态”下体育改革发展的整体推进问题,不仅要推进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的协调发展,更要推进体制改革、学校体育、职业体育、体育产业与体育消费、体育场地建设的全面发展。凡是“大体育观”能够涵盖的内容,或者能够联想到的内容,都应该设置具体目标,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至于社会资本和市场活力能否顺利激发出来,与“举国体制”的力量交汇推进“大体育观”多元目标的改革蓝图,开创全面深化体育领域改革发展的新局面,我们拭目以待。至于这是不是一种社会进化的资源配置,乃至一种发展目标的“顶层配置”,是不是“上层建筑”为扮演好自己的引领者角色所做出的努力,或者沦为“喊口号”“放卫星”的独特景观,那就留给实践和历史来评判了,也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畴。
《诘问》借用吉登斯“第三条道路”这个概念来形象表达问题,“第三条路”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依据《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顶层设计”部署的路线图,是举国体制与市场体制相结合的道路,或者说是“加强党的领导”与激发市场活力二者齐抓共治、功能互补的道路。“举国体制”在经济“新常态”周期里不会消亡,拿了这么多奥运“软金牌”,在体制优越性和合法性层面上没有“废除”的理由。即便为“举国体制”退出历史舞台做最坏的打算,按照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14]”这替代了此前使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为充分释放市场活力迈出了一大步,但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定位与改革实践上可能出现的状况,仍重点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按照党中央推进体制与社会改革的精神指引,至少在经济“新常态”周期中,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不会废除,而是强调“完善”与“改革”,至于“废除”的具体时间表,就要由时势发展和顶层布局决定了。
可以预见,在经济“新常态”周期里,体育“举国体制”的存废问题,仍然处于一种向完全市场化主导的新型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与过渡阶段。“举国体制”有可能在某些体育利益固化领域得以强化,极有可能肩负平稳过渡的历史使命而走向弱化,最不可能的结果是“扔进历史的垃圾桶里”。具体反映到体育领域改革问题上,笔者认为体育“举国体制”的改革处于“被国家化”“被现代化”的新常态[15]。孙科博士具体指出:“国家统领性的改革文件势必与社会各领域的突出问题遥相呼应,通过全局带动局部是国家政策性文件的重要特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政策精神的延续,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具体体现。[16]”我们要提前适应体育举国体制与市场体制这种交错混搭的局面,由党中央高屋建瓴、顶层设计、改革部署的总体指导精神,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某些学者的呼吁而改变。至少在未来10年时间里,是各方力量坚定不移贯彻推进发展的目标方向。《诘问》中有关中国特色的新型体制的未来判断,符合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诘问》中认为,“三大球也许正处于令人担忧的‘转型阵痛期’,即旧有体制失灵,新体制又没有建立起来。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转型阵痛期’是历史的必然。”笔者深感认同,借用《诘问》中的话说,“我们的责任,则是尽可能缩短这段时间。”
4 三大球回归学校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诘问》中认为,“客观地看,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所取得的成效离国家、社会的预期还有不小的差距。据了解,在三大球项目中,高校学生运动员能够进入国家队的少之又少,更遑论成为‘明星’级选手的例子。”毋庸置疑,高水平学生运动员凤毛麟角,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学生”比较常见。但是,藉此现象就否定精英体育回归学校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就值得商榷了。基于传统三级训练网的体工队后备力量输送模式,挤占了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职业俱乐部)应有的生存空间,或者说这是一种功能的替代。因为体工队模式的垄断力量和路径依赖的现实存在,让学校体育和职业俱乐部无法发挥输送国家精英体育人才的功能。通俗一点来说,你没有给我充分条件和平台去做这件事,却说我这事没干好,这是蛮横不讲理的态度。
值得庆幸的是,体制内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研究者鲍明晓、李元伟认为[17],政府一家在体育系统内办竞技体育的格局60多年来一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局部赶超、争光为先”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副作用,就是对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办竞技体育产生挤出效应,致使社会和市场有能力、有意愿也很难办竞技体育。换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如果废除体工队人才培养模式,而由学校体育独立承担,或学校体育和职业俱乐部共同承担人才培养功能,中国精英体育人才同样会不断涌现。这里大胆假设,取消跳水项目三级训练网体制,将国家跳水队交给清华大学去办,也就是完全由学校体育机制替代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功能,笔者坚信清华大学有这个能力办好,学友们你们怎么看?
《诘问》将“学、训矛盾”归结为竞技体育和高等教育两种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不相容性,进而推出“运动员的职业目标定位决定了这种牺牲主要集中在学业领域,国家、社会以一定的形式对前述‘牺牲’予以补偿是合乎情理且完全必要的”观点。这种观点类同于为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越性和合法性的辩护,以及在国家与社会改革大潮中寻找继续扎根生存的意义,沦为拒绝或延缓体制改革的遁词。这种观点重在强调“举国体制”取得的奥运业绩,所谓“一俊遮百丑”。选择性忽视或“别有用心”的贬斥学校体育和职业俱乐部在培养与输送国家队体育人才中的作用和效果,更是对竞技体育的世界潮流视而不见。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
青训系统有两种主要模式:一种是由普通教育系统负责完成;一种是由职业体育俱乐部或地方、国家级别的职业体育机构直接负责。北美国家主要使用的模式是前者,而欧洲绝大多数国家普遍使用的是后者[18]。科比·布莱恩特、勒布朗·詹姆斯这类跳过大学教育,直接进入美职篮联盟的球员毕竟是极少数。欧洲职业俱乐部青训体系完全是建立在青少年接受文化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基础上,注重打造职业俱乐部所在城市与社区的课余训练网络。张尚武事件、冠军搓澡工事件从一个侧面说明,体工队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长期以来,凭借体育系统的力量,体工队模式很难优化配置文化教育资源,加之功利思想作祟,直接以放弃专业运动员文化与人文教育(作为一种摆设)为代价,“举国体制”人才炼炉的“高能耗”特征显露无疑,体育人才培养“金字塔”中“塔中”“塔基”的就业安置缺乏基本保障,留下不可逆转的社会后遗症。在社会资本不断积累和市场力量迅速崛起的“新常态”下,体育系统的力量日渐式微,“举国体制”与文化教育间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缺失了运动员接受良好的文化与人文教育的必要环节,加之常年封闭式训练与管理以及运动员社会适应能力培养环节的缺位,使得体育“工具”与“玩具”间的价值认知与目标错位。在人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时代要求中,这种“身体征用”[19]的发展模式将愈发面临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和道德伦理的拷问。
破除专业运动员“全面发展”的体制魔咒和“身体征用”的道德枷锁,让运动员的一生享有尊严,有更多获得感,更加幸福,或许才是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价值旨归和最终目标。这是时代与世界发展潮流,是国家经济与社会改革发展的目标方向,也是既得利益集团不可阻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组成部分。
体制内担心体制改革与转型可能造成的混乱局面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业绩基础产生强力冲击,进而导致我国奥运优势项目的成绩下滑,使得奥运“软金牌”失去体制保障。鲍明晓、李元伟不无担心的指出:“竞技体育自身发展战略的调整,需要把更多的资源投放到以三大球为代表的集体球类项目和以田径、游泳为代表的基础大项上,优势项目原有的绝对优先保障的优势地位将很难维持。在转变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初期,出现我国在奥运会上金牌总数下滑的可能性极大。[17]”《诘问》中担忧“三大球回归学校”面临的诸多问题,以及体制内学者担忧“奥运金牌的暂时下滑”,实是杞人忧天。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作为一个不断进化的行业系统,在适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生存环境过程中不断进行要素结构的调整与提升,已经具备“内循环”系统的特征。至于可见的具体效果,也就是笔者所说的,“凭借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力和行业内部资源的高效配置,完全有能力实现优势项目体育人才的‘垂直培养’”[13]。当然,中国竞技体育优势项目绝大部分是奥运“软金牌”项目。
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的体育部门连“软金牌”都保证不了,还奢谈什么改革,还妄想发展“高精尖”的三大球项目?坊间关于“撤销体育总局”这一“无中生有”的话题,真有可能列入“上层建筑”的议事议程。况且,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非常清楚一个逻辑与事实:“举国体制”合法性的根基源自“软金牌”,失去“软金牌”这个业绩的表征,“举国体制”离退出历史舞台就不远了。这个讲究“实利”的“举国体制”金牌生产机制,是不会放弃自己的“主业”,并全身心投入到新的国家体育战略领域(全民健身、体育产业与体育消费、足球改革)。最大的可能性是,在确保奥运“软金牌”数量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调动体制内资源和力量,或者更为明智地创造一套符合中国现实的利益协调机制,激发资本与社会力量携手去做更多的事情。
《诘问》涉及到“三大球回归学校”操作性层面上的问题:诸如“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为高校运动队参加国内外高水平运动竞赛创造条件;大幅度提升教练员水平;提高运动队生源质量;尽快形成训练传统和环境-竞技文化氛围;加大经费投入和场馆建设”等方面内容,这里深表认同。有没有必要做,怎么做,如何具体做,是截然不同的思考层面。或许不能急于着手操作性问题。操作层面的问题属于“不懈地追求”的范畴。如果前进的目标方向不正确,再多的资源、努力和汗水也只会白费。关键是“舵手”要准确把握改革潮流,勇于“破局”,敢于做“动作”,站在崭新的历史高度,赋予更大的政治魄力,完成大尺度的“顶层设计”,为“三大球回归学校”创造充分解决各类问题的制度条件,这也是基本条件和必要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积极与全球治理接轨的同时,也带有强烈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民族烙印,这让中国更多地在形式上、实利上追逐全球化的成果,而国家内部也形成了独立的且相对稳定的体制机制运行结构。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民族崛起战略,在西方社会指责中国市场经济名存实亡的同时,也让中国避过多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改革步入关键时期,利益主体分化趋势造就了盘根错节的改革局面,亟待进一步释放社会活力推动经济与社会平稳、持续发展。《决定》中“治理”概念出现了24次,可以预见,“第五个现代化”概念、方向和思路的提出将引领未来中国各领域改革发展的进程。在经历改革开放30年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探索及参与全球治理互动的过程中,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竞争中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真正意义上迈进全球治理的时代道路。
体育全球化变革的结构性力量,改变了民族国家体育发展的内部环境,既有伊朗、卡塔尔等西亚体育崛起的案例,也有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体育发展环境变迁的启示。这种当下面临的民族国家的普遍状况,让大国体育治理无处逃遁。以马来西亚体育市场发展为例[20],植根本地化的传统体育消费形式已经由高度商品化的英超足球联赛、美职篮联赛等西方职业联盟赛事取代。公众对2007年亚洲杯足球赛和2009年“曼联俱乐部马来行”商业比赛的态度存在巨大差异,填满了马来西亚国内体育市场的消费空间,催生出西方体育诱惑和国家建设需要之间的调和性文化消费产物,成为全球化与民族性、地方性之间价值冲突与社会调适的象征。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完善与改革,以及伴随“校园足球计划”《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涉及校园足球的战略部署、教育部将“三大球”、田径、游泳等列为七大重点项目等一揽子配套政策的出台,这些有关“三大球回归学校”的行动战略,与其说是体育界主动谋求体制转型与转变发展方式,不如说是在行业局势和国际环境的“倒逼”形势下,不得不进行的政策调整与应对结果。
一些专家学者预判后北京奥运时期的体育体制机制改革“分水岭”并未如期而至[21—22]。而事实上是,在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北京奥运会之后、伦敦奥运会之后,乃至当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四个关键的时间点,一直在坚持和完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日常工作改革程序及部门调整,而不是进入“分水岭”意义上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这不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走向更为开放、包容、协商、均衡的改革问题,而是现有体制机制的强化固化问题。吊诡的是,体育问题的整体性和跨界性超越了既有的条块分割体制的承载能力和作用范围,导致中国体育出现发展瓶颈,三大球社会基础薄弱问题不是体育系统、教育系统或任何一个单一的系统所能独立解决的[23]。也就是说,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一以贯之“强政府”模式,但在缺乏社会、市场、个人力量参与共赢和深度合作的情况下,问题治理和综合治理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建构“举国体制”合法性的基础,在于迫切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压力,而“倒逼”体制内萌发全面深化改革的愿望和决心,以避免陷入更为尴尬的境地。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存废、建制与改革问题,是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运行机制的集中反映。当既有体制机制不能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和协调发展时,就必然走向存废之争和革新之路。我们坚信崭新的局面迟早会到来,只是我们期待早点到来。
5 结语:请关注陌生
感谢刘建和教授的诘问,促使我把多年来压抑心里的想法和观点痛痛快快地表达出来。学术期刊在保护“新观点”上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支持发表来自体育基层一线和研究生群体非常有创意观点的文章,尤其是针对学生弱势群体和年轻学者“新点子”的知识产权保护。借此呼吁期刊办刊和学界同仁能够给予承载“问题意识”的“新点子”更大的空间和支持。“新点子”“新想法”“新观点”代表了一种“陌生”。我们应该“关注陌生[24],因为“陌生”使学术生活变得有趣,让人“惊疑”,让人眷恋。学术生活中的“陌生”是稀缺的,需要加倍珍惜呵护。有了“惊疑”,才有寻找方法解决问题的根本动力。不时听见学人扼腕叹息,斯人已去,后浪在哪?试问,有了“陌生”,有了“惊疑”,何愁没有学术追随者。
[1] 张力为.研究方法总是使我们处于科学研究的十字路口[J].体育科学,2004,24(6):1~6.
[2] 薛原.体育论文IDEA的知识产权保护[J].体育科研,2011,32(2):101~103.
[3] 刘建和.综述与诘问:具有中国特色的振兴“三大球”之路[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5,38(4):118~120,135.
[4] 陈玉忠.“恒大现象”的社会学解析[J].体育科研,2014,35(2):6~11.
[5] 罗超毅.扬长补短是我国奥运争光战略的必然选择[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11):11~13.
[6] 新华社北京.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地位 自觉运用改革精神谋划推动工作[N].人民日报,2015-04-02(1).
[7] 黄璐.盘点美国 回顾北京 遥望伦敦——媒体政治建构奥运神话的宏观作用机制[J].体育科研,2010,31(6):78~82.
[8]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N].人民日报,2015-03-17(6).
[9] Department of Sport and Recreation. Australian Sports Commission Sports Governance Principles[EB/OL].[2015-06-08].http://www.dsr.wa.gov.au/support-and-advice/organisational-development/governance.
[10] 王庆军.把脉中国体育:当下问题与对策诉求——卢元镇教授学术访谈录[J].体育与科学,2013,34(3):5.
[11] Anthony King. Why England fails[J].Sport in Society:Cultures,Commerce,Media,Politics,2014,17(2):233~253.
[12] 谭建湘,邱雪,金宗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管办分离”的研究[J].体育学刊,2015,22(3):42~47.
[13] 黄璐.《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的国家战略思想[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5,31(2):34~37.
[14] 人民出版社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5] 黄璐.国家体育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和广泛涵义[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5,31(1):14~17.
[16] 孙科.中国足球改革诠释——对《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思考[J].体育科研,2015,36(3):16~19.
[17] 鲍明晓,李元伟.转变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1):9~23.
[18] 华金·盖林,沙培培.教育·体育·人文:西班牙“拉马西亚模式”的启示[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2,24(5):415~421.
[19] 孙睿诒,陶双宾.身体的征用——一项关于体育与现代性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2(6):125~145.
[20] Callum Gilmour, David Rowe.Sport in Malaysia: National Imperatives and Western Seductions[J].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2012,29(4):485~505.
[21] 卢元镇,张新萍,周传志.2008年后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准备[J].体育学刊,2008,15(2):1~6.
[22] 李卞婴.2008 年奥运后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之路[J].体育学刊,2008,15(2):7~13.
[23] 杨桦,任海.我国体育发展新视野:整体思维下的跨界整合[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7(1):1~8.
[24] 任火.关注陌生[J].编辑之友,201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