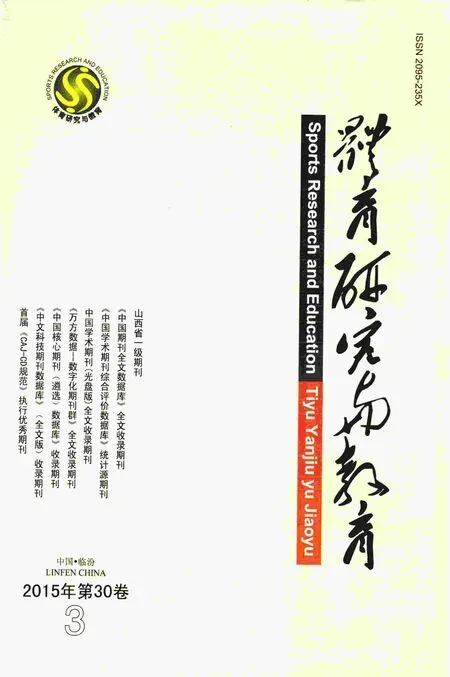浅议黔东南苗族传统村落体育中的伦理意蕴
刘礼国,徐 烨
所谓伦理,就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1]“伦理”强调社会性,是侧重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理论。[2]注重伦理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最为和谐的状态,使人性得到完美健康的发展,从而形成和谐的社会状况。苗族村落体育的功利目的并非强身健体,而是满足生存需要、传承民族文化、进行伦理教化等。苗族村落体育承载的伦理文化是苗族人民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创造的生存哲学和生存智慧,独具特色的伦理文化使得黔东南苗族村落体育具有友善和谐的文化魅力。
1 黔东南苗族传统体育的伦理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前,黔东南苗族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仍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痕迹。苗族传统伦理产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原始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前,黔东南苗族地区保留着原始公有制经济形态,如苗族的毽塘、秋千堂、摔跤场、跑马场、铜鼓坪、跳月场、斗牛场等体育场地是房族、宗族或村寨的公共财产,当地人享有平等的使用权,不允许据为私有,更不准进行买卖;二是原始公社的社会结构。新中国成立以前,黔东南苗族地区的封建政治组织流于形式,而带有氏族性质的鼓社组织则发挥着实质性的自治作用。寨老、鼓头是鼓社的自然领袖,没有特权,不取俸禄,乐于奉献,并利用具有伦理色彩的“榔规”影响和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使苗族社会形成“无政府的有序状态”。寨老、鼓头在苗族村落体育活动中发挥着组织和指挥作用,利用苗族传统伦理保障村落体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亲近自然、重血缘、重人伦、重家庭、重族群的伦理观。这些传统伦理意识至今仍影响着苗族村落体育,使苗族传统村落体育带有鲜明的伦理色彩。
苗族传统伦理具有如下基本特征:(1)原始公有的伦理观念突出。苗族生产力水平低下,从事集体采集和狩猎活动,社会分化不明显,没有等级秩序和特权意识,形成了人人平等、和衷共济的良风美俗;(2)原始集体观念强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苗族个体成员生存能力不强,必须依靠集体或族群,因此形成了强烈的集体意识;(3)平等意识原始而朴素。苗族相信万物有灵,认为人与自然地位平等,他们甚至将某些自然物视为自己的血缘亲族,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拟制性亲属关系。恶劣的生存环境、频繁的灾异等使他们敬畏自然。此外,苗族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中很多内容都是由原始宗教、巫术、禁忌所构成的并借助其神秘力量来维持和传播。
2 黔东南苗族村落体育的伦理观
苗族传统伦理渗透到传统村落体育中。传统村落体育折射出苗族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伦理观、亲善和睦的人际伦理观、群体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伦理观;苗族村落体育反映了其和谐伦理关系,是苗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人与族群关系的生存哲学与生存智慧。
2.1 和谐共生的自然生态伦理观
苗族村落体育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伦理关系。苗族崇拜自然,把某些自然物视为图腾(即亲族),与之形成了亲缘伦理关系。苗族村落体育体现了人类的生态伦理理念,在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过程中形成了尊重自然生态、“寡欲节用”的伦理规范。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也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体价值所在。[3]“天人合一”的朴素思想规制着苗族的体育行为。如台江县施洞苗族制造独木龙舟的过程就体现了苗族人民对树神敬畏的伦理态度。由于适合造船的大树常常是靠近寨边的风景树,因此被苗族视为树神。施洞苗族采取“平等协商”的祈求巫术方式,用祭品祭祀山神和树神,肯请他们允许砍树造船。从选树、砍树和运树的程序、仪式和禁忌来看,苗族对树木存有浓厚的伦理情怀,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力求做到人与自然平等和谐。而从江县岜沙苗族荡秋千则体现的是岜沙人崇拜自然、与树同乐及以类相感的生物伦理观。岜沙苗族信守植物生命观,相信自己的灵魂能寄予草木,自己的生命与草木的生命能神秘交感地联系在一起,二者荣枯与共。岜沙人有敬树习俗,寨里的重大活动和民俗节日都在树林中举行,岜沙荡秋千所选择的树要有吉祥的传说,秋千荡得越高越久就说明男女双方越是情投意合,从而形成人与树同乐的伦理氛围。苗族村落体育具有仿生性,“道法自然”体现了以动物为师为尊的伦理态度。角抵、摔跤、武术、舞蹈等许多体育项目是对图腾动物的模拟巫术而形成。例如,苗族斗牛舞与秦汉间的角抵戏同源,而苗族斗牛舞和角抵戏又都源于黄帝与蚩尤之战的“火牛”。[4]苗族村落体育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平等互惠与互渗感应的伦理关系。施洞苗族《龙舟飞歌》中“你们给龙一头猪,龙给大家子孙”的唱词即体现了这种关系。其伦理目的不仅是为了拯救族人,也是为了拯救自然万物,体现了“我向大自然索取,我也要回报大自然”的伦理理念。[5]
苗族村落体育的主旨常是祈年与求子,他们希冀通过祈求巫术的伦理途径达成祈愿。如苗族村落的宗教祭祀活动的目的就在于取悦各种神灵,求其赐助保持与自然的沟通,达到满足人类需要的伦理目的;而苗族的斗牛、划龙舟、玩龙灯、舞狮、爬坡、跳月等传统村落体育项目更是祈年、求子意蕴浓厚;台江县施洞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目的是祈雨。其间有一系列仪式和禁忌,其伦理目的就是避免冒犯自然神灵,否则人间就会五谷不丰、六畜不旺。爬坡节的主旨则是祭祀土地神,通过爬山、对歌等途径来达到土地增殖和人口繁衍的伦理目的。
受制于“天文”,苗族村落体育在时间安排上张弛有度,体现了人类尊重自然节律的伦理态度。苗族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为单一的农耕狩猎经济,形成了特定的生活节律。大家约定生产季节不得进行娱乐交往,节日期间不得进行农业生产。所以苗族村落体育活动时间往往是被固定在节日或节气,主要在农闲、苗年和春节等。
2.2 亲善和睦的人际伦理观
苗族村落体育暗含着苗族社会的交往礼仪规范。它约束着人际间的交往行为,形成了亲善和睦、美美与共的伦理关系。
(1)苗族村落体育表达人际伦理。苗族村落体育是苗族人生礼仪的组成部分。如刀、枪、剑、弓箭等利器就是男婴诞生礼的主要符号,是勇力型“英雄”的伦理意象*《清水江畔龙舟节》、《子、午“爬坡节”》、《香炉山爬坡节的由来》等体育起源神话传说也渗透着崇尚力量与勇敢的伦理意蕴。,以此塑造男儿的勇敢品格,赋予其保家护寨的伦理义务。与中国传统村落体育“尚德不尚力”不同的是,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往往将力量和勇敢作为美德。正如拉法格所说:“力量和勇敢是处于经常不断地彼此斗争和同自然作斗争的原始人的首要的最必要的美德”。[6]刘红认为,“勇”是英雄最外显的伦理特征。关注英雄的勇敢品质透视出人们对自身主体精神和本质力量的肯定与称颂。[7]苗族诞生礼中锻造“双环刀”、配枪等习俗即是对氏族成员力量和勇敢伦理品质的塑造。《贵州通志》记载:“九股苗*旧时代的反动统治者不尊重少数民族的意愿,以服饰、头饰、地域等因素为界限来区别某些少数民族的支系,某些旧志书、旧文献对少数民族的认识有偏见,常以“某某苗”记载,如“红苗”、“白苗”、“黑苗”、“高坡苗”、“九股苗”等,这是对少数民族情感的伤害。“某某苗”的称呼不符合国家的民族政策,应当摒弃。所用之利刃名曰‘双环刀’……造刃之法,子初生时,亲戚家各送铁一把,由匠人造成粗样,埋入泥沟,每年取出冶炼一次,至16岁方成刃口……”[8]火枪是从江县岜沙男人成年礼的主要物象。据说,岜沙苗寨是我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在这里,不配枪的男人不受尊重。男孩满15虚岁时,父母要请鬼师为其举行“入堂”仪式。鬼师用镰刀为其剃头后,把火枪交给男孩,男孩即被接纳为村寨集体的正式成员,之后就要遵循“用手中的枪捍卫家族利益”的伦理义务。
苗族节日体育强化血缘伦理认同。民族伦理认同就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血脉传承、生活方式、节日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的承认与归属感。黔东南民族节日众多。它积淀着世居民族的古风古俗,是民族伦理的载体。许多节日具有献祭祖先的目的,通过对共同祖先的认同达到维系家族和睦、社会和谐的伦理秩序。如苗族鼓藏节上斗牛、跳舞、射箭等活动即是为了娱祖媚神,以身体活动形式来表达对祖先的祭祀和血缘认同。苗族生死观认为活着的人是由逝去的先祖投胎转世而来,因此春耕前的耍狮节、踩亲节、花炮节、芦笙节、斗牛节、爬坡节等都是希望以迎接生命之神的复活而达到惠及在世生人的伦理目的。
苗族村落体育还常以限制体育参与人员以强化伦理禁忌。禁忌是宗教、法律和伦理的前身。在社会规范体系中,禁忌属于外在的控制机制,伦理属于内在的控制机制。以婚姻为例,苗族村落体育具有婚姻伦理教化的目的,男女双方结婚时,要由寨老或父母向成婚者进行婚姻伦理教育,使其了解和认识本民族婚姻禁忌。讨花带是雷山县西江苗寨及其周围地区苗族芦笙舞会的内容,由于有求爱的情节,讨花带禁忌规定只允许本村男子向外来女客讨花带,禁止外村男子向本村女子讨花带。为此,活动主持者鼓藏头会反复强调,还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并且赠送给每一位跳舞的未婚女客一张洁白手巾,系在胸前作为区分的标志。为什么形成如此法约?其一是遵守西江外婚传统,西江男子不能向西江女子讨花带示爱;其二是遵守苗族不能在女子的村寨当着女子父兄的面向女子求婚示爱的传统公共场域伦理观念。[9]
(2)苗族村落体育活动体现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伦理的最高原则是敬畏生命。以生育信仰和生育崇拜为表征的生命意识和生生不息意识,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精神。[10]苗族崇拜生殖,祈求生育,苗族传统村落体育即体现了苗族对以万物繁衍和人类生存为最高伦理追求的特征。如苗族春节舞龙舞狮除了具有祈年求丰稔的涵义外,还有求子求育的意蕴。因为“灯”与“丁”谐音,根据巫术的相似律,迎灯有祝愿人丁兴旺之意。在巫术接触律的无意识支配下,台江县舞龙嘘花时有些人家会讨要龙头上的绫子捆在小孩身上以避灾痛。而苗族跳花节通常是由无子嗣的人家抢着承办。如果没有承办机会就祭祀花杆以祈求赐子;有子女的人家则讨要花杆上的布带系在子女的脖子或手上以达到护生的伦理目的。
(3)苗族村落体育提供了自由婚配的伦理平台。伦理是关于人类关系尤其以姻亲关系为重心的自然法则。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苗族传统伦理的基本内容。苗族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尤其注重通过姻亲关系来巩固或扩大交往范围。他们利用血缘或拟制的亲属关系,建立广泛的亲缘关系,因此,苗族特别重视男女婚姻。自由婚是苗族婚姻的主要形式,苗族集团性交往保留着对偶婚集团交往的遗迹,青年男女交往采取集体形式,通过歌舞、体育娱乐等伦理途径示爱。清代陆次云《洞溪行志》云:“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即春日跳舞求偶也。”丹寨县锦鸡舞动作中就有模仿锦鸡求偶步态的动作,实际就是男女青年跳舞交心,以乐示爱的舞蹈。苗族村落体育对自由婚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①直接促成男女的婚配。镇远龙舟节、鸡毛毽、岜沙荡秋千、舟溪甘囊香芦笙会、爬坡节、跳花节的主题就是男女婚配,凯里市舟溪甘囊香要求恢复被清朝统治者禁止的芦笙会而在芦笙场边刻碑勒石立下《永垂不朽》碑,碑文严正声明:“窃维吹笙跳月……更为我苗族自由择配佳期。”即是一证;②为男女择偶求婚提供平台。龙舟节、斗牛节、花炮节、芦笙节等既有体育竞赛,也有男女对歌、跳舞,节日的晚上更是苗族男女游方的好机会。
苗族以祖先崇拜为核心构建社会伦理秩序,以血亲和姻亲构建社会网络结构,加强伦理认同和社会秩序整合。施洞苗族在独木龙舟节推选龙主时就特别看重姻亲关系,要求龙主当选者必须各方面完美,家里女儿多并都已出嫁的人容易当选,因为女儿多,女婿就多,收到的礼物就比别人家多,挂在船上就能炫耀身份,获得好的声誉,提高本宗支的社会地位,对儿女的婚姻前程也有裨益。[11]儿女婚姻是宗族的大事,不同村寨男女联姻结成姻亲关系对于苗族拓展和改善生存环境至关重要。
(4)苗族节日体育活动促进礼尚往来。苗族是传统的伦理型社会,人情伦理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特别注重礼尚往来。由于苗族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单一(为水稻农耕经济),农闲时间较长,因而为对外交往提高了条件,而苗族节日的创制也为礼尚往来打下了基础。苗族集体性的做客方式是:错开时间过节,轮流做客。例如,雷山苗族苗年跳芦笙从蜂糖寨开始,经甘益等地,最后集中到公统。丹寨县跳芦笙始于九门村,经番江、番娘、笔通、番扛,最后集中到南臬。此外,苗族村寨之间或村寨内部几个房族之间也常进行互访式的集体做客,斗牛、秋千等活动是这种互访做客礼俗的组成部分。斗牛场上,牛主的亲友均要带着鞭炮、礼品来贺牛。轮到下一个斗牛节时,牛主人则又必须以重于或相当于客人的贺礼去回贺客人。
苗族注重礼尚往来,收礼以后要还礼,参与斗牛、独木龙舟、舞龙嘘花成为这种交往礼俗的借口。台江县施洞举办独木龙舟节时,每条船上有记礼一人,登记亲戚朋友所送礼物,以便日后还礼。施洞独木龙舟原来只在平兆、塘龙、旧州三处划,由于总是这三处的人当“嘎牛”(即龙主),亲友每年都向他们送礼,可是送礼的没有机会当“嘎牛”,这三处受礼的人无法还礼,于是又分别在廖洞、小河、平寨三处划龙船。[12]这促使划龙船更加兴盛。台江县元宵节举行舞龙嘘花,两个关系好的寨子可以提前嘘花和相约抬猪。抬猪礼俗是在有亲戚关系的寨子之间或事先邀请的寨子之间进行。某村寨元月二月欲与他寨联络感情,遂约由甲寨至乙寨抬猪。约定后,甲寨每家派一人至乙寨吃酒,乙寨还要预备一、两只猪给甲寨抬回去。来年乙寨回访甲寨,抬猪饮酒如故,意在通达感情,消遣农闲。
(5)苗族村落体育展示了互助互济的美德。和衷共济、患难相恤就是要求同约者在别人遭遇灾难时互助互济,用集体的力量帮助遭灾家庭渡过难关。苗族个体家庭经济力量单薄,常需依赖集体力量和互助合作机制渡过难关。互助救济机制使苗族社会的总体力量不会减弱,能够以集体力量应对外来威胁。
苗族村落体育活动中的互助合作关系是苗族互助合作关系的缩影。以苗族独木龙舟为例,主办人龙头开支很大,要招待划手和房族(苗族是同姓同族聚居,所以要宴请全寨成年男性)。虽然当龙头要收礼,但以后也要还礼。据说有人当了龙头而债务缠身,只得典当田地,如果田地被汉族地主购买就会使苗族整体经济实力削弱,为此,苗族通过互助机制解决活动资金问题。此机制包括三种互助形式:(1)台江县施洞苗族的龙船属于全寨共有,或属于一个家族、几个家族共有。每条龙船都有田土、山林、稻谷或现金作为互助基金,称为“众田(用于资助龙舟活动的耕田被称为“龙船田”)”“众山”或“众谷”等。到土地改革时,有两条龙船已积累到一千二百余元大洋,稻谷三千二百多斤;(2)接受亲戚的礼物可以贴补龙舟节开支;(3)如果轮流到家境较差的人家当龙头且他不愿意放弃时,其他家庭在经济或饮食上给予帮助。
(6)苗族村落体育活动特别注重礼节。热情好客、讲礼节、说吉利话是伦理秩序的应有之义,在传统农耕社会显得特别突出。苗族为了迎接斗牛节、秋千节等节日,在节前要邀请客人,主寨要安排客人的食宿,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客人都会受到热情接待。接待的方式有“分客”与“抢客”两种。客人要体现对主寨的敬重,否则就会受到冷遇。说唱吉语贺词要符合苗族的审美伦理和求吉心理。说吉利话能促进人际和谐,玩龙舞狮队伍中都有会说吉利话的专职“吉利手”,他们也是玩龙舞狮队中受欢迎的核心人物。
苗族村落体育强调尊重主寨的礼俗。苗族不忘祖恩、恪守古俗古礼、尊重主寨。雷山县西江举行的苗族芦笙舞会上,不管哪支芦笙队,只要带上礼物祭祀主场,表示尊重主寨,就可以自由地在场内表演,这是当地苗族公共场域传统的伦理规范。1998年由政府组织的西江鼓藏节在西江小学球场举行,当主持人宣布击鼓跳笙后,寨众没有听从调动而冷场半个小时。原因是主会场所在的场地不是鼓场,鼓藏头及村民们坚持“只有在鼓场才能跳铜鼓舞”。于是政府主办的仪式只好宣布结束,村民挪到鼓场才跳起了铜鼓舞。[9]
(7)苗族村落体育调适人伦秩序。“伦理”一词中的“伦”是次序、秩序的意思。黄建中认为:“伦谓人群相待相倚之生活关系,此伦之涵义也。”[13]在汉语中,“伦”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引申为秩序、规律和位差。[14]秩序是重要的社会规范,确定的人伦秩序有利于社会运行的稳定。“森严的等级观念深深植入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之中。”[15]而苗族社会等级色彩不明显,其平等观念却十分原始而朴素。苗族社会关系主要是平权型的关系,即使寨老、理老等权威也没有特权。苗族村落体育在调适人际关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整合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姻亲关系和联盟关系发挥着重要的伦理秩序价值。苗族村落体育的参与者要按古规约定的顺序出场,以体现对人伦的尊重,这不仅利于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稳定,也能保障活动“清吉平安”。斗牛节时踩塘或打斗顺序都有规矩,打鸡毛毽时姑娘、小伙子要遵守“守塘”与“踩塘”的规则,舞场上姑娘、小伙子、中老年人的位置秩序要依从古规。而且,苗族村落体育秩序由自然权威来维护。苗族村寨的寨老、理老、鼓藏头是自然权威,斗牛、赛马、划龙舟等体育活动都离不开他们维护秩序。苗族社会男女平等的秩序在秋千节、姊妹节、板凳舞、铜鼓舞、木鼓舞等节日体育活动都能得到体现。由于早期的部落或民族战争,男子事武功与女子事农耕的社会分工决定了苗族男女的地位大体平等,又由于苗族长期处于“有族长无君长,有贫富无贵贱”的状况,这种平等的悠久传统,又为当代的男女平等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8]
2.3 苗族村落体育折射出集体利益至上的伦理观
(1)苗族村落体育活动强化集体认同。由于苗族传统社会生存能力较低,必须依靠集体才能生存和发展,致使其各种活动皆带有集团性特点。对外交往强化了集体伦理认同,苗族村落体育活动以村寨、宗族、房族或村寨地段为单位的特征呈现出其集团性、公共性特点。
“鼓社共财”是苗族社会宗族伦理的基本内容。苗族村落体育活动场地为集体公共财产,由村寨、宗族、房族等集体提供,不得买卖或改变用途。从江县加鸠苗族吃牯脏是以共有“牛堂”,即以公共斗牛场的一个或几个村寨为一个单位来进行的;从江县加勉苗寨妇女跳舞的场地称为“秧堂”。每逢吃牯脏的时候要踩歌堂。每年二月间开始撒秧之前也要踩秧堂。全寨共有四处秧堂,该寨规定秧堂不得作屋基或其他用途。
苗族村落体育活动充分展示了集体的凝聚力。苗族的民族性很强。它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以社会血缘为根基的氏族血亲集团。这使得它有一种极强的内聚力。[16]苗族独木龙舟的制作从砍树到制作完成需要五百多人协作,体现了集体团结的协作精神;台江县元宵节舞龙嘘花有舞龙表演和竞赛。获得优胜是整个寨子的荣耀。该寨子所有出嫁的姑娘都会买来礼物和鞭炮前来祝贺。传统节日中一个寨子或家族能不能组织参与斗牛、摔跤、划船、舞龙嘘花、玩龙舞狮等活动是村寨凝聚力大小的体现。苗族村寨对内以血缘关系或拟制性血缘关系为纽带构建内部人际关系,对外有明显的排他性。所以,体育竞争在形式上是为了个人的荣誉,而实质上是为了村寨、家族的集体荣誉。所以有些村寨对不到场助威的缺席者会给予约法制裁。
苗族通过传统的村落体育强化集体伦理认同。苗族跳花、鸡毛毽、划龙舟、芦笙会等节会开始前要举行巫术祭祀,既祈求平安,又祭奠先祖;苗族独木龙舟节期间,龙舟下水前要举行巫术祭祀,由鬼师讲述祖先迁徙史。通过祭祖活动能厘清血缘关系,加强身份辨识,强化集体认同。苗族龙舟节、舞龙嘘花等体育活动在事前先要向寨民发布告示,筹集款物,如果不凑钱就会脱离集体。活动结束还要会餐、斗歌、斗酒,这是集体情感表达和集体认同的过程。
(2)苗族村落体育活动倡导集体利益至上。历史上苗族社会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他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存下去,由此形成了集体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伦理观。苗族村落体育即体现了这种集体利益至上的伦理倾向。当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每个人牺牲个人利益以保全集体利益。中华民国时期《台江边胞生活概述》描述施洞独木龙舟“竞渡以胜者为荣,往往有为争胜利曾坠河而死,亦不以为意。且俗以为坠河者多,则年岁愈益丰稔太平,若坠死独子,尤为大吉大利,故往往竞争至死。”[17]这是活人献祭的巫术遗存,苗族人认为以祭品取悦于祖先,祖先会给予回报;祭品越高贵(美貌、年轻或尊贵),祖先给予的回报也越多越大(如年景丰稔、人丁兴旺)。因此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是值得倡导的伦理行为。这种自我牺牲的做法在今天看来许是不道德的,但在当时的苗族人看来却是十分值得推崇的美德。
[1] 《现代汉语辞海》编委会.现代汉语辞海[M].太原:山西出版社,2002.
[2] 赵炎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基本特征透析[J]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30(6)29~34.
[3] 龚坚,蒋至兰.论古代体育伦理思想的基本文化精神[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29(12):1611~1613.
[4] 李国章.雷公山苗族传统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
[5] 张少华.方旎苗俗[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
[6] 拉法格著,王子野译.思想起源论[M].北京:三联书店,1963.
[7] 刘红.云南民族民间艺术的伦理观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8] 李国章,文锡美,文远荣.报德苗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9] 杨鬃,王良苑.苗侗文坛(49)[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10] 陆景川,吴军.原生态的魅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9.
[11] 李文明.贵州黔东南[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
[12]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6.
[13] 黄建中.比较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14] 王仕杰.“伦理”与“道德”辨析[J].伦理学研究,2007(6):42~46.
[15] 张新,夏思永.管窥中国传统村落体育伦理思想[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27(1):28~30.
[16] 罗义群.苗族牛崇拜文化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17] 李瑞岐,杨培春.中华龙舟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