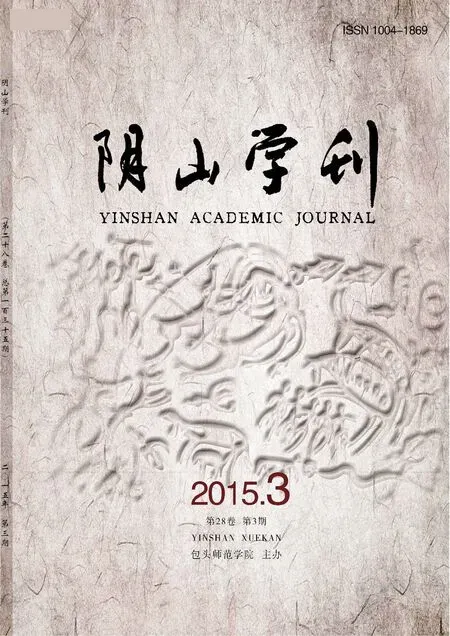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思维
——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
魏 明 康,万 高 潮
(1.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2.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思维
——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
魏 明 康1,万 高 潮2
(1.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2.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自早年在长沙求学,经杨昌济五年耳提面命,青年毛泽东接受了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所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尽管青年毛泽东在经验形下具体的层面上重实践、重实用,但由于以“宇宙真理”为先验存在的形上本体,又以政治过程为对此真理的认识与实现,他混淆了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与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因而使得为其本人所主张并以“宇宙真理”自命的“大同圣域”政治理念,必然失去为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妥协性;使得民主政治领域中的人人平等关系,必然为认识领域中的“圣贤凡愚”关系所颠覆。
毛泽东;政治思维;政治文化;先验形上本体;经验形下具体
本文旨在从政治文化角度讨论青年毛泽东的政治思维。通常学界多依价值取向不同而析政治文化为以经验理性为基础的宽容型的政治文化和以先验理性为基础的专制型的政治文化:前者指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任何先验形上的社会本体,无论其叫做柏拉图的世界理念,或叫做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抑或叫做斯大林的历史规律,所以任何人就都必须宽容其他人在政治实践中作选择的权利,只要其选择不伤害他人的同样权利;后者则主张某个人或某些人即使不是某种先验形上的社会本体的化身,也是其唯一的掌握者,所以他或他们就有权力强制他人服从他或他们所作的选择。而因杨昌济等师长的五年耳提面命,与以上两类泾渭分明的政治思维模式有别,毛泽东自早年在长沙求学,所接受的却是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所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
一、从朱熹经曾国藩到杨昌济
众所周知,依庄子见解,圣人之学是为“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形下学,故《论语》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后《孟子》固然谈天命,但谈的其实是人心,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至北宋以降,面对西来佛学“崇本息末”所带来的挑战,程朱理学才不得不也将汉儒董仲舒鼓吹的三纲推崇为“天理”,亦即先验形上的社会本体。如此即朱熹《答黄道夫》云:“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至于理气关系,则《朱子语类》称,若从时空层面来看,盖天地民物都是由同一个理与不同的气相聚而成,“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故“理气本无先后之可言”;然若从逻辑层面来看,则“理在事先”,所谓“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缘由是:“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不过自觉为新儒家,理学家们“崇本”不崇“无”,故斥佛家指“色”为“空”。在他们看来,天地民物不仅都实际存在,而且都是同一个天理的不同表现,不过因禀气相异而有人的贤愚之分、物的木石之别。如此即所谓“理一分殊”,所谓“理同气异”,所谓“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且正是因为“理一分殊”、“理同气异”、“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若果然要把握“总天地万物之理”,人就不能脱离天地民物去苦思冥想,而是要把功夫下在“即物穷理”、“格物致知”上,“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以于“异”之中求“同”、“殊”之中求“一”、人人物物之中求“太极”,“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那么“方知理本一贯”又如何呢?朱熹有云:“知行常相须。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即谓知了后是一定要行的。如此即其《观心说》之所谓:“圣人之学,本心以穷理,而顺理以应物。”即指“穷理”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是要依经格致所得的一以贯之的天理,转回来再去应对纷至沓来的万事万物,所谓“稽考实理,以待事物之来;存此理之体,以应无穷之用”。倘若果然,也就实现了天理与民物之间,亦即理先与气后、形上与形下、本体与具体、道与器、体与用、知与行之间的结合与统一。
经明至清,朱熹的政治思维为曾国藩所继承。首先,曾国藩极认同朱熹之“崇”儒家伦理为天理。其《遗嘱》云:“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其次,曾国藩极认同朱熹之“知行常相须”的务实主张。所谓“即物穷理”,他一反训诂学家“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而指“实事求是”非纸上考据:“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1](P166)又“即物穷理”何以为必须,其《答刘孟容书》亦云:“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故“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至于格致何益、穷理何为,作为理学中人而兼湘军统帅,他强调:“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在他看来,晚清之所以天下大乱,根源就在理学式微、人心不定,所以凡主张“为务实之学”的学问中人,就切切不可坐视,而必须以格物所致之良知、即物所穷之天理,挺身而出,“顺理应物”,收拾天下人心。如此即其《讨粤匪檄》之所谓:“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及至民初,朱熹和曾国藩的政治思维方式的真心服膺者,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号为“湘中大儒”的杨昌济。一方面,杨昌济完全认同朱熹的“总天地万物之理”和曾国藩的“大本大源”,并美其名为“宇宙大原则”:“宇宙间所有一切之表现悉自此大原则而生。吾人当深思默会,洞晓此大原则,所谓贯通大原也。”[2](P85)另方面,他又反复告诫自己的学生:“宋儒之学都是切实的”,故义理之学同时是“练达世情”之“学”、“应世接物之道”;为学者当秉此义理之“真精神”,“实意做事,真心求学”,“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世所宜。”据毛泽东《讲堂录》记载,当年在修身课上,其老师就要求自己的学生“高尚其理想”且“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他还向学生推介“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尤其是时他即以曾国藩为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所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的人格化身,来对自己最喜爱的学生作有意识引导。1915年4月5日与毛泽东长谈后,他曾留下一段日记:“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至于他何以视曾国藩为所谓“异材”并堪为青年毛泽东模范,日记中无明细。不过据毛泽东《讲堂录》记载,其老师在课堂上对此倒曾有详解:“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前如诸葛武侯范希文,后如孔孟朱陆王阳明等是也。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不言而喻,此段议论直指曾国藩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就确实抓住了曾氏一生事业的最大特点。而曾国藩以“秀才肩半壁东南”,其之剿灭“粤匪”,既能率千军万马攻城略地,又能举“大本大源”收拾人心,如此“办事而兼传教”,也的确让以天下国家自命的杨昌济的学生们从此刻骨铭心,以致数年之后谈起来,毛泽东依然百般感叹:“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有如彼之完满乎?”[3](P85)即使此后四十余年,毛泽东已为中共领袖,他之口口声声“我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语气间“办事而兼传教”的痕迹依然清晰,无非“之人”已由臣子级晋为帝王级,是为所谓君师合一。
二、“向大本大源处探讨”与“切于实际生活”
对曾国藩这个人格化身的心悦诚服,即是对为这个化身所体现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的心悦诚服。而体察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的初步政治思维,他亦确实是在自觉追求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的结合与统一。首先,他直接师承杨昌济之“宇宙大原则”,提出了一个与朱熹的“天理”和曾国藩的“本源”相当的概念:“宇宙真理”,以为先验存在的形上本体。他明言:“世界之外有本体”,且其“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即不仅在天地民物之先,而且在天地民物之上。具体到人类社会,则其表现为“绳束古今为一贯”的“历史公理”,所谓“古今制度不同而理则不易”:“有一时之正义,如君臣奴隶之类;有万世之通义,如仁义礼智信以及天心民意之类”。至于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的关系,他亦认同朱熹的“理一分殊”和曾国藩的“万物一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既如此,他强调,那么“临民制治”的政治家们就当明白:“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例“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然此三位政治家之所以并无大成就,不就是因为其眼中只有“枝节”而于“大本大源”或者“胸中茫然无有”,或者“似略有本源”而“徒为华言炫听”吗?惟其如此,倘若反其道而行,“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所以为政者果然“欲动天下”,就当从“动天下之心”入手:“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4](P25)
那么要如何才能“探讨既得”呢?毛泽东称:“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天达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故“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关于“倡学”,面对民初之“天下纷纷”,他提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所以称“宜”,在哲学主人思想,伦理学范人道德,而“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故“思想道德必真必实”;然而回顾历史、环顾现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斯言!”那么“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又是否仅具“切于实际”之经验理性层面的意义呢?当然不。他接着称,他之所谓“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固包括思想道德当在经验理性层面“切于实际”,然而究其根本,此命题的主旨却不在经验理性层面的务实,而在先验理性层面的求真;且即使是经验理性层面的务实,亦不过是服从、服务于先验理性层面的求真。故“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所以“真欲立志,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4](P84~89)
在面向社会“倡学”的同时,毛泽东尤重个人“倡学”。所谓个人“倡学”,他提出,固然是要读圣贤之书,但绝非所有的儒家典籍都要读,而是要读其中“实事而有用之书”。例“宋元两代人尚实学”,宋儒之书就当读。尤其朱熹的“即物穷理”之作,“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而“乾嘉之代,士人趋于考据,一字一义动累数万言而不休”,则其书就不读也罢。除了读纸上书,他强调,所谓“倡学”还另有指,就是要读无字书。在他看来,从孔孟之道到义理之学,其所言说固然都是天经地义,但圣人亦非“生而知之”之人,所谓“‘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之不可信也”。个中道理,就是因为“理未尝离乎气”,即先验形上本体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实存于天下每一事物之中的。所以即使是孔夫子这样的圣人,他要把握先验形上本体,也只能从经验形下具体入手,“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和常人一样走格物致知的路子。如此即朱熹之所谓“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亦即曾国藩之所谓“研乎至殊之分,洞乎至一之理”。进而,既然圣人尚且需要“即物”方能“穷理”,那么不言而喻,任何人只要不是经自己于事事物物之中格致所得,那么即使他可以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也不过是习得一些空洞的词章而已,绝不能说此人就已经把握了天经地义。就如同某人虽熟读“《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但只要其不曾亲历亲为,他就依然是一个“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的书呆子。由是毛泽东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即谓“行事”比较“学文”甚至是“为学”之更重要的一面。同时他自我宣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于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为难能的是,毛泽东言出必行:顾虑“学生在学校学习,与社会之实际不相一致,结果则学生不熟谙社会内情,社会亦嫌恶学生”,在长沙求学时期,他曾多次利用假期徒步三湘,以接触民间、增广见识;顾虑“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任湖南一师学友会总务一职后,他又特为该会增设交际部,“所以谋内外之联络,通新故之情愫,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意甚盛也。”尤其饶有兴味的,是其时他作的一篇寓言体日记:“客告予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萲,缠牵成蔓,不能自伸。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矞皇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客曰:虽然,吾观于子,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虽强其外,实干其中,日学牡丹之所为,猥用自诡曰:吾惟匏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予无以答,逡巡而退,涊然汗出,戚然气沮。”[4](P19)值得一提的是,该篇日记题《自讼》,作者以文中“客”“予”问答,形象地表达了自己志在实而不华的匏瓜,而非华而不实的牡丹的务实品格。
三、“宇宙真理”与“圣贤凡愚”
尽管青年毛泽东在经验形下具体的层面上确实重实践、重实用,但因其受制于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所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故其之重实践,不过相当于朱熹的“即物穷理”和曾国藩的“实事求是”,即其行为固然是“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而其目的却只是为了求得在“世界之外有本体”并因此“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的“宇宙真理”;其之重实用,亦不过相当于朱熹的“顺理应物”和曾国藩的“学自此兴”,即其目标固然是“欲动天下”,而其方法却只是“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所以若不只从经验形下具体的层面上看,尤其从先验形上本体的层面上看,其在根本上就仍然是一个先验理性主义者。而如此所导致的政治理论后果相当消极, 概其大要者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由于青年毛泽东以“宇宙真理”为先验存在的形上本体,又以政治过程为对此真理的认识与实现,他就不仅从根本上混淆了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与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而且也使得为其本人所主张并以“宇宙真理”自命的“大同圣域”政治理念,必然失去为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妥协性。众所周知,政治之为谋利是政治学的一条公理;政治与经济的不同,在经济是通过市场体系的运行而谋利,政治则是通过国家制度的运行而谋利。一般而言,政治之为谋利,其主导过程是在国家制度的框架内,由公权力出而协调人与人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由于利益诉求之为主观表达,政治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就都不可能以自己一方的利益诉求,来充当整个社会利益格局所由以确立的客观标准而为冲突各方所心悦诚服。继而,由于客观标准的付之阙如,政治冲突各方的不同利益诉求之间,也就并无认识论意义上亦即主客观相符意义上的所谓对错可言。惟其如此,各方之间的利益分歧就只能在公权力的协调下,经市场式的讨价还价来解决。若经讨价还价而利益分歧仍在,就只好诉诸投票机制: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而如此即意味着,至少在自由民主的制度条件下,政治过程本质上具有妥协性而非零和游戏。然而认识过程不同。认识过程关涉的并非主观和主观的关系,而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此即是说,凡主观认识符合于客观对象的就为对,也就是真理;凡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对象的就为错,也就是谬误。惟其非对即错,非真理即谬误,认识对立的各相关方之间就确实只能是相互否定的零和关系,因而根本上不具相互妥协的可能性,而确实只能如青年毛泽东所描述:“真理流行,群妄退匿。”问题是尽管他本人亦称“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但他同时又坚持,“价值”与“真理”、“人为”与“天然”之间的这种分野,并不适于作为天地民物之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本身:“宇宙真理”既在“世界之外”,又在“人人之心”,“发显”虽然不同,“本质”依然同一,因而大可以集“价值”与“真理”、“人为”与“天然”之二者为“一体”。所以他就既以事实陈述的言说方式,界定“宇宙真理”的性质为先验存在的形上本体,所谓“世界之外有本体”,即于人而言为客观存在;又以价值判断的言说方式,界定“宇宙真理”的内容为“大同圣域”,所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即于人而言为主观诉求。而经将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混而为一,将客观存在与主观诉求混而为一,将认识“宇宙事理之真”与谋求“大同圣域”之“善”混而为一,他也就顺理成章地赋予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以一种客观真理意义上的不可动摇与不可妥协性。虽然在上杨昌济伦理学课程时研读德国学者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他对中国传统义理之学的“大同圣域”理念亦曾有过某种怀疑(“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然而那不过是因为受激于作者的善恶相对论(“苟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而生发出来的一时之感慨,而并非对先秦儒学所倡扬的“和而不同”果然有所体贴。相反,由于坚持“宇宙真理”的实现即“大同圣域”的实现,“大同圣域”的实现即“宇宙真理”的实现,他在张扬自己的理想时就完全不知妥协为何物。如此即其之所谓:“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4](P88)
另方面,由于以“宇宙真理”为先验存在的形上本体,又以政治过程为对此真理的认识与实现,青年毛泽东就不仅从根本上混淆了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与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而且也使得民主政治领域中的人人平等关系,必然为认识领域中的“圣贤凡愚”关系所颠覆。众所周知,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完全平等的。而在认识领域,由于先天遗传差异与后天环境差异的永远存在,人与人之间在智力水平和知识水平上的差异亦永远存在。此种差异用青年毛泽东所习用的术语来描述,就大致相当于所谓“圣贤凡愚”之辨,或“智者愚者”之辨,或“君子小人”之辨。问题是他确实混淆了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与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1912年就读湖南省立高中时,他就曾试图用认识论概念来解答政治学问题,如指中国之“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是因为“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纵有商鞅等少数几个“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亦无济于事。入读湖南第一师范后,在提出以“宇宙真理”为“临民制治之具”的同时,他又主张以真理的有无为区分圣贤凡愚与君子小人的“确实之标准”。在他看来,凡愚小人之所以为凡愚小人,是因为他们“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不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稊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而圣贤君子之所以为圣贤君子,则因为“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至于君子之智德何以得称为“高尚”,他强调,就是因为其体现了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的结合与统一。关于此,一如前述,由于先验形上本体是与经验形下具体结合在一起,实存于天下每一事物之中的,所以即使是孔夫子这样的圣人,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经“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务实路径来认识“宇宙真理”的。惟其如此,用毛泽东后来的政治话语来说,圣人就把自己与那种只知道从书本到书本的“教条主义者”区别开来了。二是经从“发显”深入到“本质”、从具体上升到本体的格致过程,圣人又确实掌握了“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的“宇宙真理”。青年毛泽东称:“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其坚持执“一”应“百”,用毛泽东后来的政治话语来说,圣人就又把自己与那种无视大本大源的“经验主义者”区别开来了。既然圣人左右逢源而高明若此,他强调,人类社会常态就确实是并且只能是“愚者多而智者少”,如此亦“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之大意耳。进而他断言:“人有贤愚,因之而有贵贱。”当然,值五四前后,他之有此言倒也未必是在主张什么贵族政治。问题是倘若谋利之政治过程即求真之认识过程,而人类认识活动又确实是“愚者多而智者少”,那么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政治原则,岂不就真的要为多数服从少数的贵族政治原则所颠覆吗?毕竟,人类认识活动的游戏规则总还得是“愚者”追随“智者”而不是相反吧?惟其如此,毛泽东才坦然称,即使“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竟不能遂愿,既然政治过程即认识过程,掌握了“宇宙真理”的少数就不仅仍然可以,而且应该“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而大可不必转过来服从执迷不悟的多数:“圣人之所为,人不知之,曲弥高和弥寡也,人恒毁之也,不合乎众也。然而圣人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与乎无愧于己而已。并不怕人毁,故曰举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毁之也愈益甚,则其守之也愈益笃,所谓守死善道是也。”[4](P172、593、639)
四、“唯物史观”与“现实主义”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经五四运动至中共成立,本着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所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他在自己最初的政治实践中就表现出既在本体层面重求真,又在具体层面重务实的思想品格。所谓在本体层面重求真,其时他依然视政治为追求真理,视真理为无可妥协。1918年组织新民学会时他即称,他“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5](P38)。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时他又称,其办刊宗旨在“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并称政治的“基础”是“主义”,“主义之争”是“真妄”之争而非“私人之争”,私人之争“大概是可以相让的”,而“真理只有一个,不容谁捣乱,也不容谁调和”。当然,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毕竟是巨大的。虽然其时他依然把“要寻着什么是真理”视为“彻底解决”种种社会问题的“拔本塞源的方法”,不过与在长沙求学时期相比较,对于真理究竟为何物,其认知已经有了根本变化。在他的笔下,不仅过去的“孔圣人”变成了“孔老爹”,就连康梁等过去为他所极佩服的维新派人物,也都被其指为“一味的‘耗矣哀哉’,刺激他人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4] (P293、363、497)倘若传统旧学已经不算真理,改良维新也已经不算真理,所谓真理又当为何物呢?经五四新文化左倾思潮的影响,毛泽东选择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从俄国送来的马列主义。在他看来,马列主义既已证明人类之走向“世界大同”是为历史必然因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就当然是实至名归的宇宙真理。如此即其之所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5](P15)更何况马列主义在揭示此一真理的同时,还以十月革命的成功给出了实现此一真理的可行途径,这就是经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走向世界大同。
毛泽东之认定马列主义为宇宙真理,其过程并非一蹴而就。1919年下半年,他即曾关注因“美博士杜威东来”而在国内盛极一时的实用主义,并参加了“问题与主义”的大讨论。不过经一番琢磨他表示,实用主义之注重实际问题固然可取,但“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本体层面缺乏“主义”却成了实用主义的致命缺陷。1920年下半年,在放弃对实用主义的兴趣后,他又把目光转向了继杜威之后来华的罗素所宣传的费边社会主义。他首先承认费边社会主义在本体层面有真理在。因为该主义既认可“世界大同”,就大与孔孟康梁的政治意趣相同一。然而该主义同孔孟康梁一样,也没有找到通往大同的可行之道。因为该主义旨在“用教育的方法”和平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的奴隶,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故于该主义他只能说:“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当然,即使中国事实上可以和平渐进地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亦不会选择费边社会主义。之所以不会,理论上的原因,在此前杨昌济曾告诫自己的学生:“为学之道”当“重现在。重现在有两要义,一贵我,二通今”,他并且将此“道”与为圣贤当为“三不朽”的旧学传统相联系:“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而毛泽东对此心领神会。他于是称:“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一曰现实主义。乃指吾之一生所团结之精神、物质在宇宙中之经历,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继而称:“小人者,吾同胞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孔子知其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五四前后与新民学会会友交流时,他的态度益发显得急迫:“我们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而正是基于此种务必于“人生百年”及身成功的强烈欲望,1920年12月,当有会友“主张温和的革命”时,他才会不顾自己此前之憎“法兰西恐怖”,相反称:“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至于他不会选择费边社会主义,实践上的原因,在与接触费边社会主义同时,以宣传鼓动兼上书请愿为手段,毛泽东操作了一场颇具声势的湖南自治运动而终于一无所获。于是大失所望之余,他不再主张“呼声革命”,相反称:“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4](P45、89)所谓“另辟”,他表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6](P4~7)时过境迁,抚今追昔,区区“几个月”的改良之成效不尽人意,就以为从此“绝无希望”,从此“山穷水尽”,政治上之急功近利如此,除了年轻人所特有的青春政治品格,就真的只能用务必于“人生百年”及身成功的“现实主义”来解释了。
五、“吾侪的主张”与“吾侪的下手处”
至迟至1920年底,在毛泽东看来,他已经在本体层面“寻着什么是真理”,余事是如何在具体层面予此真理以落实。为此他强调,即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也不能取代中国革命者对本国实际的调查研究。回顾当年,当他指“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时,他的新民学会会友、后来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李维汉曾表示:“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然而毛泽东不以为然。因为依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所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本体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与具体相结合,实存于天下每一事物之中的。而他之认定“走俄国人的路”,其本意就并非要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诸如城市暴动、工人起义、苏维埃政权等等,而是要吸取俄国革命的本体,诸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所以只要认同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那么从具体层面来看,就不存在“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的问题。而如果从本体层面来看,由于本体本身具有“万物一源”的性质,所谓“质天地而无疑,放四海而皆准,俟百世而不惑”,所以又确实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当然,也正是由于中国革命者于俄国革命所吸取的还只是其本体,这个本体在客观上是如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而存在,在主观上当如何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而应用,这两个大问题的答案都还在未定之天,所以在认定马列主义为宇宙真理的同时,毛泽东就仍然注重对中国实际的调查研究,就如同中国传统义理之学之注重“即物穷理”、注重“实事求是”。例1920年7月,经蔡和森提议,新民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变更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毛泽东当然热衷此议,同时他警惕各会友视“改造”为夸夸其谈:“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标)?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于是他要求学会将会友们组织起来:“讨论共同的目的;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怎样实践。”[4](P464~465)同年底他还给蔡和森写信:“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就可以知道了。”不过尽管和会友们一样“鄙弃爱国”,毛泽东强调,所谓“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6](P1);“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该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6](P2~10)而正是因为视中国为世界“先”,当有会友向他呼吁:“润之兄啊!你是一个有志的人,你如何带一个头,权且努力于研究学问的事呢?弟近来想及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学,异日回国,各抒所学以问世,发为言论作社会之唤醒提倡者。”[5](P44)他当即表示:“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既如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好处: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2.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4](P474~476)
除了强调即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也不能取代中国革命者对本国实际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还强调,即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其在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时,也仍然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当然他肯定,马列主义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宇宙真理,那么即使这个主义是被俄国人从万里之遥送到中国来的,它就不仅仍然可以,而且还确实应该被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如此即中国传统义理之学之所谓“万物一源”、所谓“顺理应物”的道理。然而本体毕竟不能脱离具体而存在,所以中国革命者果然要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就仍然必须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1941年在延安他曾回忆:“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7](P378~379)所谓“老老实实”,通过比较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毛泽东意识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所以从无产阶级在全国四万万人口中只占区区二百万而资产阶级更是人数少得可怜的现实出发,他就并没有把力气花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上,而是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口号。所谓“民众大联合”,其政治目标“纯然为对付国内外强权者”,其社会构成则“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全国最大多数人民”都在内。那么该如何政治行为才能把“全国最大多数人民”动员起来呢?同样通过比较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和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毛泽东在与新民学会会友通信时终于承认:政治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政治行为必须建立在实际利益的基础上,“所以要有群,要有社会,要有联合,是因为想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然而,就如同他其时不把力气花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上,不等于他从此就放弃了这个斗争一样,毛泽东之以利益为民众大联合的政治基础,也不等于他从此就划分了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与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相反他提出,利益固然是民众大联合的政治基础,但民众大联合并非只有一个政治基础;由于只有与“主义”之“真”相吻合的利益诉求,才能最终经得起人类历史的“末日审判”,所以“主义”之“真”同样是甚至因此而更加是民众大联合的政治基础。惟其如此,他强调,为了迁就多数民众不觉悟的现实,少数政治精英固不能不以现实利益为动员民众的号召与旗帜,但精英本身的结合当仍为“主义的结合”。虽然值五四前后,他“根本反对”在政治上“把少数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但由于他仍然同在长沙求学时期一样,从根本上混淆了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与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而真理的获得在客观上又的确如他本人所说,“大半为个人的独到所创获”,所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日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故只要把个中逻辑贯彻到底,青年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所得出的政治判断:“人有贤愚,因之而有贵贱”,就是在此时也还是不难被推理出来的。[4](P368、373、392、520、523、554、557)
六、余 论
1921年7月中共成立。此后通过融会贯通自柏拉图经黑格尔至马克思的一整套欧陆唯理论哲学范式,诸如普遍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本质与现象、抽象与具象、感性与理性、理论与实践等,经与王明等不仅在本体层面,而且在具体层面为一以贯之的教条主义者作斗争,毛泽东成功地将中国传统义理之学所倡扬的先验形上本体与经验形下具体相结合的政治思维模式,改造成为了中共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思维模式,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早在1927年大革命中,他就一面把“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马列主义理论当作“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一面“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在1930年代“井冈山的斗争”中,他又一面“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一面“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之后在赣南,据他本人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回忆:“中央苏区整我,整我狭隘经验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给我很大刺激,因而读了几本书。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8](P190、293)至1937年七七事变,他的《实践论》已经明确:“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尤其1941年在延安,他如此解析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毋庸置疑,倘若与不仅在本体层面,而且在具体层面均为一以贯之的教条主义者的王明相比较,毛泽东之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至少在政治策略上远为高明。关于此,1945年4月他曾在中共“七大”上称:虽然依马列主义普遍真理,无产阶级革命当以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但由于中国社会十分落后,所以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出发,就只能把革命分成两阶段来做。即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这个阶段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为革命的同盟军和主力军。只有在这个阶段完结后,才能进行以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为革命对象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此这般,就叫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时过境迁,抚今追昔,应该承认,在国民成分的绝大多数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人们的国情下,毛泽东依具体层面之经验理性提出来的以上主张,至少在策略上“是和中国人口中的最大多数相一致的”[9](P994、956)。相形之下,“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10](P79)而正是由于在政治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如此差异,虽然其主张未必尽合王明所拘泥的意识形态教条,但是与后者曾将中国革命引向绝境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距“七大”召开仅四年,毛泽东的主张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胜利。
然而,就如同在长沙求学时期其心目中的“宇宙真理”,在五四运动前后其心目中的“天下大本”一样,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心目中的普遍真理本身亦是先验存在的形上本体。之所以称先验,固然在马列主义是经“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被俄国人从万里之遥送到中国来的,其在时空意义上本来就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之先。更重要的是,尽管马列主义是由马列本人从其具体经验中“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不过这个主义绝非因此就是具体经验。相反,经一番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从具象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实践到理论的“改造制作工夫”,这个主义所反映的已经是不以任何人其中包括不以马列本人的意志为转移,因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真理,亦即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既如此,那么不言而喻,此种超越于任何人其中包括马列本人的具体经验而存在,同时又在时空上具有绝对普适性的客观真理,亦即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逻辑上就是并且就只能是一种先验存在的形上本体。进而,正是由于坚持其政治主张的实现即历史规律的实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如同在长沙求学时期及五四运动前后一样,毛泽东依然混淆了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与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因而其主张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为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妥协性。其时他曾反复称:“真理只有一个。”[11](P623)那么是哪一个呢?就是马克思主义。原因在于:“地球是在发展的,太阳是在发展的,整个宇宙不晓得经过多少万万年,地球上出了生物,出了人类,出了文明社会,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宇宙观教给我们,要懂得将来还要进步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10](P299)可是资产阶级的人们却无人“教”给他们这样一个宇宙观,所以“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12](P1357)。既如此,共产党就是真理的化身,“把真理打烂就是把共产党打烂。”[10](P254)不过共产党既然已经真理在握,所以不难想象,“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12](P240)继而,还是由于坚持其政治主张的实现即客观规律的实现,坚持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即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依然未能准确把握民主政治领域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虽然他始终称:“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他同时又坚持,谋求利益的政治过程同时是追求真理的认识过程,而“真理常常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他又常常在政治精英的内部纷争中取以多数服从少数的强硬立场:“真理要坚持,有时真理不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和了解,我们也要反潮流。”[13](P28)而如此以真理化身自居并坚持反潮流也就是反多数,其极端案例,即1930年在赣西南因反AB团而激起富田事变,个中原因,就是他本人的政治主张与当地干部奉行的“立三路线”相冲突。至于政治精英与群众的关系,类似在长沙求学时期及五四运动前后之所谓“圣贤凡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依然视二者为政治上的“师生”关系。在他看来,由于缺乏从感性到理性、从现象到本质、从具象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从实践到理论的理性思维能力,群众从来只能看见“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而不可能认识需要通过理性思维才能够把握的“将来利益”。如此就给了真理在握的共产党人一个兼具政治学与认识论双重意义的任务:作为“人民的教师”,“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13](P1029、1217)可是果然到了社会主义“将来”,人民中的“落后”分子比如民族资产阶级和城乡小资产阶级的人们,偏偏就是不肯“认识真理”,不肯“去掉脑子中的错误思想”,不肯接受“我们”的思想“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呢?倘若果然(后亦实然),从来自认真理在握因而也就是历史在握的毛泽东,也就不惜对这些非无产阶级的人们实施政治强制了。关于此,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他的《实践论》就已经讲得明白:“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包括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1]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6.
[2]杨昌济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3]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
[4]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5]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6]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李锐.庐山会议实录[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9]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2]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13]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责任编辑 韩 芳〕
On the Political Thinking Mode of Mao Zedong in his Youth Age
WEI Ming-kang1, WAN Gao-chao2
(1.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2.School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s a student of Yang Changji, young Mao Zedong accepted the political thinking mode to combine the transcendental metaphysical ontology and the experience physical specific from Chinese traditional argumentative philosophy. Although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ractice and pragmatic in the aspect of the experience physical specific, because of taking “universal truth” as the transcendental metaphysical ontology, and tak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as the process to know and realize the “universal truth”, he confused the political process for benefit and the cognitional process for truth. So it is inevitable for his “Datong world” political idea, as an “universal truth” , to lose the compromise tha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the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more, the 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man in the filed of democratic politics must be subverted by the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wise man and fool man”.
Mao Zedong; political thinking mode; political culture; transcendental metaphysical ontology; experience physical specific
2015-03-09
魏明康(1958-),男,江苏南京人,硕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A753
A
1004-1869(2015)03-007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