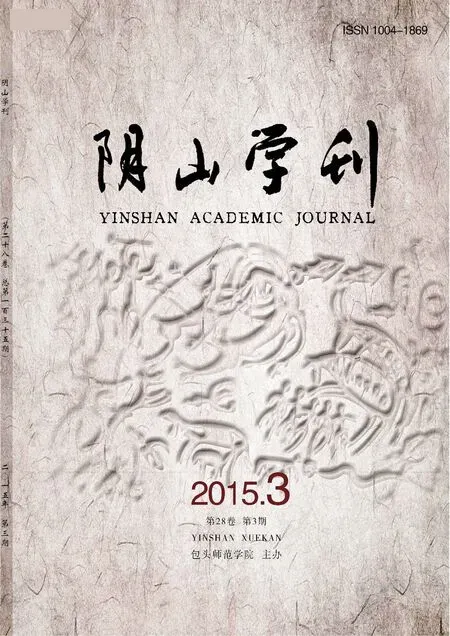文脉交织中的信仰重申
——《约伯记》的互文性探析*
王 晴 阳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文脉交织中的信仰重申
——《约伯记》的互文性探析*
王 晴 阳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475001)
《约伯记》是希伯来圣经智慧文学最重要的篇章之一,也是最具争议性的圣经文本之一。在互文性理论的引导下,拟从语词象征和主题复现中解读其深厚意蕴,并根据历史背景和宗教文化脉络的延续,对《约伯记》的主旨思想进行探讨性解读。
《约伯记》;互文性;圣经
作为圣经*圣经(和合本)[Z].南京:中国基督教两会,2002.文中所引《圣经》皆出此本,《约伯记》篇名不再标注,其余引文均表注篇名。智慧文学的扛鼎之作,《约伯记》叙述了义人约伯遭到上帝考验而探寻苦难原因的故事,是古希伯来民族“为探索人生意义而进行的强烈挣扎”[1](P1)。该书更为深湛雄伟的象征意义在于透析犹太民族的深重苦难,尤其重申一神论信仰。
互文性理论(Intertextuality)亦译作“文本间性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此起彼伏的浪潮中,涉及文本意义生成、阅读、阐释与文化表意之间的关系等西方文学的诸多理论问题。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和罗兰·巴尔特为代表的理论家提出广义互文性,指任何文本都与其意义传统、符码和表意实践相互牵连、彼此照应,构成一张具有解读之无限可能性的意义生成网络。一如罗伯特·阿尔特对读者意味深长的提醒:“希伯来圣经是一个内在诸元素紧密联系的统一体,而非互不相干的拼凑物。”[2](P17)对《约伯记》的解读不可孤立,不仅要关注文本形式之间的相互牵连与对话,还要注重它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最重要的是,须结合其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站在纵观希伯来圣经宗教使命和历史意图的高度,对其做出全面的负责任的解读。本文拟将该书置于希伯来圣经的浩瀚文化海洋中,分析其语言元素与其他正典经卷的高密度交织,进而展开探讨性解读。
一、语词象征:多神论的挑战
克里斯蒂娃认为,“文字语词之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文本空间的交汇,是若干文字的对话,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人物的,现在或先前的文化语境中诸多文本的对话”[3](P36)。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从词语之间的反射与交织,读到跨越文本的遥远回应。其中提到的地名应该引起高度警觉,约伯所住的“乌斯地”(1∶1)隐晦表明主人公的身份,“乌斯”是亚伯拉罕兄弟拿鹤的长子(《创世记》22∶21);在《耶利米哀歌》中,读者得知“乌斯地”也是以东人的住地(《耶利米哀歌》4∶21),由此推断约伯是他拉家族及以扫家族的后裔。这一推断对认定本卷书的核心意义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表明约伯既非以色列人,更非以色列人的祖先。那么,希伯来圣经何以设专篇且以诸多笔墨记载一个质疑耶和华的非誓约之民呢?仅仅意在探讨“义人为何受苦”这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哲学议题吗?由此,其意义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再来分析书中具有强烈指涉意义的人名。对于主人公“约伯”的词源,有两种说法:一是源自其希伯来词根,取“敌对、抗议”之义,申明约伯无辜罹难后提出的抗辩;二是源于阿拉伯文,意为“回转”和“悔改”,重在强调约伯质疑上帝后的幡然悔悟。他的三个朋友之名亦非偶然设置,依据先知书所论“提幔人再没有智慧吗”(《耶利米书》49∶20),可以判定“提幔人以利法”来自以东人的智慧中心,是以利法家族的长者和以东地区德高望重的智者。据《创世记》所载,书亚是亚伯拉罕的庶子,在父亲临终前被打发前往东方(《创世纪》25∶2),书亚人在以色列王国时期与巴比伦和亚述帝国一起军事入侵耶路撒冷(《以西结书》23∶23)。在希伯来语中,“比勒达”是“巴力”和雷神“阿大达”这两个别神的合称(8∶1)[4](P129),《约伯记》在此婉转提示了约伯的这个朋友其实是迦勒底的多神崇拜者。“拿玛人琐法”的籍贯亦表明他是以东人,因为“拿玛”是被约书亚所征服的“与以东交界相近的”城市。最后出场的不速之客是“布西人兰族巴拉迦的儿子以利户”,该族人出自亚伯拉罕兄弟拿鹤的儿子“布斯和亚兰”的家族,他们虽与以色列人通婚、知晓耶和华之名却不信奉耶和华。“撒旦”一词的希伯来原义是“指控者”,这篇故事肇始于其挑衅“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1∶9),他被神话叙事列入“神的众子”(1∶6)。联系圣经其他文本,“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诗篇》82∶1),“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诗篇》95∶3),所用语词都借助多神论言语烘托耶和华至高无上的权柄,以否定其他“神的众子”“万神”等的偶像崇拜。
综上分析,《约伯记》的人物名称和象征“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焦点——多神论与耶和华一神论的论战。这种有意为之的姓名设置表明了圣经含蓄、简约的叙事艺术,如同俄尔巴赫所论,这类叙述留下极大的解读空间,需要挖掘和阐释后才能还原历史语境,进而完整理解该卷书的用意。
二、主题互文:亚伯拉罕的遥远回应
克里斯蒂娃将文本分为现象文本(pheno-text)和生殖文本(geno-text)两种类型。文体学者把前者关注的语法、语义等文本表层结构视为其最终意义之所在;实则不然,因为现象文本只是在心理和历史活动中较完满地形成一种文本残余。生殖文本则能修正叙述主体因他人价值观念导入而引起的错位,在无形中影响并规定主体特有思维逻辑的表达,是现象文本意义生成的场所。由此观之,互文性产生于现象文本和生殖文本对话的“零度时刻”(zero moment),叙述主体能利用叙述把自我中心的欲望转化为历史性的客观法则。
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影响下,不少学者主张用宏观视野对圣经进行整体性考察,罗伯特·阿尔特开风气之先,认为“圣经故事不但在细微之处铺排得精致巧妙,甚具创意,而且也被精心连结成一个整体”[5](P188)。希伯来圣经全书都记载着耶和华一神论反对偶像崇拜和多神崇拜的过程,该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逐步展开并演绎着。在综合性解读的视阈中,《约伯记》与《创世记》第22章所载“亚伯拉罕献祭以撒”事件具有显在的相似性,尽管描述的语言和方式不同,二者却共同证明了信奉唯一真神耶和华的义人,能应对比多神崇拜者更严酷的试探,承担更巨大的牺牲。两部书的中心思想一脉相承,《约伯记》以再现的超越性情节,对信仰问题达到更辩证也更深入的思考。
在《创世记》中,亚伯拉罕被上帝呼召,携家前往以色列民族的应许之地迦南,开启了整个民族对耶和华的信仰之旅。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的虔诚与忠信,要他将爱子以撒作为祭物来奉献,亚伯拉罕无言服从上帝的意愿,让儿子背负着幡柴一道上山。在筑好祭坛、捆绑以撒、挥刀将砍的一发千钧之际,上帝派来天使拦住他,使他用一只公羊代替爱子献祭。这次试探使上帝证实了亚伯拉罕的忠诚,遂赐予他更多恩典;叙述过程中展示了亚伯拉罕在最决绝境况下的心灵冲突——信仰与伦理的抉择;在这桩神学创立时期的初始性事件中,他以因信称义成为后世瞻仰的信仰典范。圣经接连用“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创2∶22)道明以撒的可贵之处,烘衬出亚伯拉罕在关键时刻悬置了伦理的艰难抉择。
《约伯记》讲述了一个同样惊心动魄的试探故事。耶和华受魔鬼撒旦的挑衅,决意降下天灾人祸来考验义人约伯,使他丧失财产和家庭,肉体也备受折磨,于无辜罹难中饱受极端的颤栗与恐惧;其多神教朋友发出种种误解和指责,更使他身心俱疲,开始口出怨言,质疑信仰。终于上帝在旋风中显现,以造物之奇妙反诘约伯,用禽兽之天性拷问约伯,最终使之领悟神意,悔过自新。《约伯记》的叙述者把维护一神论的言辞巧妙地转化成一个试探信仰的故事,借以肯定了约伯胜于亚伯拉罕之处——“敢于独立思考的勇气和才能;从怀疑中生出了最坚定的信念”[6](P84)。
犹太拉比的解释有助于我们认清上帝为何要用亲子献祭这一不合常理的方式试探义人。迦南习俗之一是把亲子献祭给所崇拜的神灵以表达忠心,因此可以大胆设想,犹太教一神论在创立之初必然面临异族的挑战和质疑,耶和华则用“献祭以撒”向世人标榜亚伯拉罕矢志不移的信仰,间接证明唯有真神耶和华值得敬畏,异神只不过是偶像。
《约伯记》是一部关乎神义的辩护之作,它借约伯之口无所畏惧地激烈挑战并质疑了神的正义,可谓畅快淋漓:“我只要在我一切争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到来。”(14∶14)“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17∶3)“你们若说,我们逼迫他,要何等地重呢?惹事的根乃在乎他。”(19∶28)神的辩护同样有理有节:“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7∶12)“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晨监察他,时刻试验他。”(7∶17-18)约伯被辩得哑口无言,只得承认自己无知妄言,且忏悔自新。约伯的形象历来为学者瞩目,安德森给予极高评价:“在圣经全书中,约伯应该说是仅次于耶稣的最伟大的信仰者。”[7](P271)他在反抗与辩驳中对神意作出更具思辨性的探索,表现出无视传统、怀疑权威的精神,这岂非比沉默无语的亚伯拉罕更可贵吗?在坚韧不拔地求索中,读者得以同约伯一道领略耶和华创造宇宙的雄奇能力和无比威严,意识到世人即使是义人,也无法洞察上帝的无穷意向,更遑论对其神秘意志妄加揣测了。
三、互文性的历史缘由:重申一神信仰
众所周知,由39卷书汇纂而成的希伯来圣经系统地收录了自公元前11世纪末期形成的古犹太律法、史册、典籍,全书于公元前6至前2世纪逐渐编峻,从结构上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和圣卷三大部类,亦反映了犹太经卷相继成书的三个阶段。《约伯记》和《箴言》《传道书》一并被归入诉诸文艺体裁的哲理书,所属的圣卷是成书最晚的部分,较之于其他经典更加晦涩难懂,对早期基督教著作如《启示录》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考察《约伯记》的文体、语法、术语和写作技巧,可以肯定,约伯的故事定型于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之后。其早期素材与公元前15世纪的苏美尔语和乌加列语文献有着密切关系,首尾的散文体叙事是全书最早的雏形;约伯的故事或许成书之前就在希伯来人或其邻近民族广为流传;诗体部分则有极大可能是在社会矛盾不断尖锐的分国时期逐渐充实并完善的。[8](P482~485)分国时期社会矛盾不断加深,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弱肉强食、善恶不分的对立冲突愈演愈烈;亡国事件对希伯来人更是一次沉重打击,以致耶和华似乎不再是那个保护雅各子孙逃出埃及、前往迦南、继而赐福大卫王朝的正直公义之神,而变得性情怪癖,甚至暴躁多疑。亡国被掳的灾难动摇了希伯来人对上帝公义的信心,致使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等异端思潮暗流涌动。希伯来思想家艰难地思考并试图解释现实的灾难,第二以赛亚等犹太先知便以彻底的一神论对亡国悲剧予以释读,称之为宇宙唯一主宰耶和华以巴比伦人入侵对犯罪子民实施了合理惩罚。然而诸多民众显然无法接受其说,《约伯记》的创作、整理和正典化过程很可能就是此一思潮的文学化呈现。
根据巴尔特对互文性理论的理解,写作是“一种冲动的移位、推进、释放性能的辩证法在象征秩序中的记录,它作用着并构成能指,但也超越能指;它将通过运用意指过程(移位、压缩、重复、逆反)的最基本法则使自己并入语言的直线秩序中去;它将指派其他辅助网络并产生一种超意义。”[9](P108)在此视阈下,互文使《约伯记》浸润在希伯来圣经的政治、历史、文化和宗教中,利用这些已经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的正典化文本的精神内涵,形成交织和叠映,广阔吸纳此前经卷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技巧之精华,形成丰赡厚重的一卷经书。
在该卷书中,约伯的身心痛苦不仅来源于现实性灾难的打击,也来自多神教友人的污蔑和指责,甚至泯灭其希望的企图。约伯拒绝了来自多神论者的“安慰”,表现出虽然前路漫漫仍旧上下求索的坚定信念。他强烈渴望独一真神耶和华的裁决,指示其厄运的出路。值得注意的是,耶和华的最终显现与回答并非答疑,而是从根本上否决了约伯上诉和质疑的合法性!这是对上帝权能的终极维护,“神圣的谋划无非就是那个他以其预见一切并在该预见中提供一切的神意”[10](P190~216)。犹太民族的王国灾难本来就无须解释,乃是神之雄浑博大旨意的一部分。与“献祭以撒”、试探约伯一样,耶和华自始至终都知晓苦难的全部,参与了整个考验的过程。
那么,希伯来圣经为何记载这个质疑、反抗神意的非誓约之民约伯呢?这需要结合犹太民族的历史背景做出解释: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兴旺大族的400年间,亚伯拉罕的庶出后裔及以扫的后代同样堪称人丁兴旺,而圣经遗漏了耶和华对该时期该后代显现的记载,《约伯记》的成书则圆满填补了这一空白。另有一处经文值得注意,约伯曾直言:“惟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6∶2, 3)语中充满了内在冲突和自相矛盾。约伯的天平最后不但衡量出无私的信仰和虔诚的美德,而且衡量出一种未经誓约的个体性信仰的艰辛。上帝的亲自显现抵消了约伯前期忍受的全部苦难,他以一句“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42∶5)道出了自己全部的喜悦之情。就“罪与罚”的审问而言,我们可以窥见,“犹太思想的出发点,不是恶的真实性或者人的罪恶本性,而是创世的奇迹和人所具有的遵行上帝意志的能力。”[11](P353)因着质疑之后更加坚定的信仰,约伯顺理成章地与众多族长一样,得到上帝加倍的赐福。在圣经记载的拯救史中,上帝赐予恩典是契约的实现,这将激励着上帝拣选的子民超越人类苦难的深渊。
结 语
借助于互文性理论指导,《约伯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愈加丰富多彩,在多重象征和复现的主题中更显意蕴深厚;同时,历史背景和宗教文化脉络的延续亦赋予其驳杂的观念和意识。对《约伯记》的解读表明,希伯来圣经各经卷之间都密切联系着,相互印证和解释着,全书是一个前后呼应的博大的精神性文本,需要读者去融会贯通地分析研究。圣经正如千万条彩线织就的一匹五光十色的锦缎,依据纷繁复杂的历史内容而裁剪得体,亦因裁剪技术之高超而显得天衣无缝。巨锦之上笼罩着来自至高一神上帝的亦真亦幻的神秘气息,其间贯注着多样性的语词和主旨,处处光彩夺目。
[1]H. C. Habel, The Book of Job. Lexington[M], Mass: Lexington Books Company, 1979.
[2]罗伯特·阿尔特.圣经的叙事艺术[M].章智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3]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M]. Toril Moi e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4]赵敦华.圣经历史哲学·上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5]Robert Alter,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M].New York: Basic Books, 1981.
[6]金亚娜.充盈的虚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F. I. Anderon, Job: A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M].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1976.
[8]梁工.圣经指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9]Julia Kristeva, The Bounded Text,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Leon S. Roudiezed[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10]张缨:上帝的权能与智慧——《约伯记》中审议主题的展开[A].梁工主编.圣经文学研究第二辑[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11]亚伯拉罕·海舍尔.觅人的上帝:犹太教哲学[M].郭鹏,吴正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韩 芳〕
Reaffirming the Belief in the Biblical Context:An Interpretation onTheBookofJobUnder the Intertextuality Theory
WANG Qing-ya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TheBookofJobisoneofthemostimportantyetthemostcontroversialchaptersofthewisdomliteratureintheHebrewBible.Undertheguideofintertextualitytheory,thispaperaimstointerpretitsdeepconnotationfromthewordssymbolandsubjectretrieval.Italsointerpretsthethemeinapioneeringwayaccordingtothehistoricalbackgroundandthecontinuationofreligiousculturecontext.
TheBookofJob;Intertextuality;theBible
2015-03-02
王晴阳(1990-),女,河南新乡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圣经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I106.99
A
1004-1869(2015)03-004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