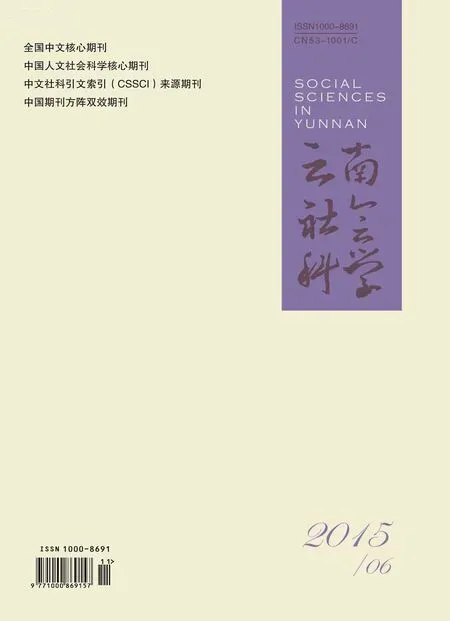张载与福斯特之自然观比较及其生态启示
陈 云
张载(1020—1077年),北宋著名哲学家,他主张“气”本论的宇宙哲学观,认为天地宇宙之间都充满着“气”,虚而无形是“气”之体,聚散变化是“气”之用,宇宙万物都是由“气”而成,从而形成了以“气”为核心的自然观体系。张载的“气”本论自然哲学体系对后世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产生着重要影响,张岱年先生指出:“气之本体,即谓空时非纯然无有,而乃物质之本原。空时凝结而成最细微的物质,最细微的物质聚合而成通常的物质。所以张子的本根论,实可以说是一种唯物论。”*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73页。陈俊民先生也指出:“这标志着中国哲学在探索‘世界的真正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这个宇宙论问题上的最新阶段,也表明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已初步获得了完全的意义。”*陈俊民:《张载哲学思想及关学学派》,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7页。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基于张载及其自然观的重要地位,对其进行“现代性”关注也即为一种应有之义。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性”关注并不是专门对张载的自然观进行系统阐述和现代建构,而是立足于现时代,以当今世界最活跃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1953— )的自然观为比较视界,具体探讨张载和福斯特关于自然观及其生态哲学意涵的同构契合和异质分歧,并从中获得相互融合和借鉴的启发,以期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整体视角和辩证方法。
一、张载与福斯特之自然观的同构契合
张载与福斯特尽管属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差异甚大,但是在他们各自的自然哲学体系中,二者关于自然的看法和观点仍然具有某种同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笔者主要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点。
1.“凡象皆气”与“直接地自然存在物”
张载的自然观是建立在“气”本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世界万象都是由“气”而成的,换言之,人与自然万物从本原上看都是一体的,不存在人与自然万物的异质性区分。张载曰:“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舍气,有象否?”《正蒙·乾称篇》就说明凡是可以形容的客观事物都是存在的,这种客观存在都彰显着一定的表象,而所有表象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式,“人”与“自然万物”都是作为可描述的客观存在,他们必然因“气”而同原。因此,在张载“气”本论的整个自然哲学体系中,人也是自然化生的,人也与万物同原。张载还用“太虚即气”的观点进一步阐明,人与自然万物都是出于“太虚”,都是太虚之气聚而成,其曰:“万物取足于太虚,人亦取足于太虚,”(《张子语录中》)“游气纷扰,合而成质者,生人物质万殊。”(《正蒙·太和篇》)同时,张载弟子吕大临继承其师观点,也认为:“天生人物,流行虽异,同一气耳。人者,合一气以为本,本无物我之别。”*吕大临:《蓝田吕氏遗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49页。后来,朱熹对此以更加形象的比喻阐释曰:“游是散殊,比如一个水车……一上一下,只管滚转,中间带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万殊’。天地之间,(阴阳)二气只管运转,不知不觉生出一个人,不知不觉又生出一个物。”*黎靖德:《朱子语类(七)卷九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08页。因此,从中可以得知,在天地之间,人与自然万物是同原性的,此原即气,此物即因气而成。
同样,在福斯特的自然哲学体系中也突显着类似的观点,认为人直接的就是自然存在物。福斯特作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其自然哲学观主要是建立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上的,他首先强调:“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的唯物主义——的总体责任……唯物主义都是必不可少的。”*J.B.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页。福斯特站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立场之上具体阐述其自然观主要是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异》以及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这两重向度进行展开的,其主要目的是试图通过肯定伊壁鸠鲁对宗教目的论和机械决定论的批判,吸收继承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精神哲学批判和决裂的理论成果,从而形成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所以,福斯特后来总结说:“他(指马克思)同伊壁鸠鲁主义和英法唯物主义者们的相遇,使他们和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了面对面的关系,”*J.B.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p.63.以及“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使自己完全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J.B.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p.78.因此,在这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形成的前提之下,福斯特则明确指出:“马克思继费尔巴哈之后认为,重要的是把客观世界以及人类的存在作为客观存在,也就是,真正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J.B.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7页。所以,福斯特顺理成章认为自然从本原意义上是唯物的,这种唯物既有外在的自然也有内在的自然,而所谓内在的自然也就是人自身,包括形体、肉、血以及头脑等等,这些都属于自然界,福斯特因而明确肯定了马克思所言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J.B.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p.71.,“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J.B.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p.73.等观点。
因此,从以上张载和福斯特关于人与自然的本原意义上来看,事实上二者的论调已然体现出了一定的同构契合性。张载从“气”本原的立场阐释人与自然万物都是因气聚而成,不存在人与自然质料方面的差异,因为二者都是同原的,并且都是唯物的,正如张岱年先生说:“张子注重物质(气),讲物质与空间(太虚)之统一,以内涵对立而能变为物质之本性,实甚精湛。”*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第73页。同样,福斯特站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立场考察人,认为“人”也是唯物的,人直接就是自然之物,所以从本原意义上来说,人与自然万物并无实质差别,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甚至也可以视为人类真正的自然史。所以,关于张载和福斯特自然观的其中一个契合点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同原性和唯物性。
2.“物无孤立之理及万物相感”与“依赖自然及‘征服’自然”
张载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相互关联、互为感通的,正是因为有了感通才有了异质性事物的形成,世间万物才得以成物。张载曰:“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异、有无相感,则不见其成,不见其成则虽物非物,故一屈一伸相感而利生焉。”(《正蒙·动物篇》)从中可以看出,张载一方面强调自然万物的普遍关联性,另一方面又突出了这种普遍关联是建立在“同异”“屈伸”“终始”和“有无”的相互对应和感通基础之上的,如果没有这些相感之存在,那么自然万物也不成物。张载接着提出了万物相感的主要方式,例如有“以同而感”“以异而应”“以相悦而感”“以相畏而感”等等,并指出:“感如影响,无复先后,有动必感,咸感而应,故曰咸速也。”(《横渠易说·下经》)那么,万物何以相感呢?张载仍然认为这是因“气”之阴阳而效用,也就是说,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感应最终还是通过阴阳之气来实现,其曰:“气有阴阳,屈伸相感之无穷,故神之应也无穷。”(《正蒙·乾称篇》)实际上,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都是互相关联而互为感通的,例如,人与自然的关联是因二者之间的同原异象,人与自然的相感是因二者之间的阴阳化生,然而,当且仅当人的外在行为与自然的内在属性存在不协调时,那么就必然产生张载所言的“有动必感,咸感而应”。张载对此还特别指出:“感而生则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篇》)应当说,张载的这一自然观对于当代人如何审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和谐相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
同样,福斯特站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强调包括人在内的自然万物都是客观联系的,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互为依赖而向前发展的。特别是以“人”为主题指出,人与自然万物无异,人也是自然,人的发展要依赖自然,人的生活离不开自然界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问题。福斯特认为,在马克思那里,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从而两者原本非但不冲突,而且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类对自然的关系是一种自然历史现象”,“人类与地球在整个物质进化过程中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这既是伊壁鸠鲁、费尔巴哈,更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J.B.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p.15.人类对自然的关系依赖主要源于“人”作为自然存在物的“生命力”,人是“能动性”存在物,其生命力的延续必然依靠自然界的物质基础。福斯特已经注意到了马克思把客观自然界和人的存在作为一种真正的实在论和自然主义来看,其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饥饿是自然的需要;因此,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得到温饱,他需要在他之外的自然界、在他之外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8页。既然如此,这就涉及人类为求得“生命力”而“征服”自然的必要可能,其实马克思本人也不否定对大自然的“统治”或“征服”,但是这个过程并非恣意妄为,而是要在尊重大自然的客观性和有限性的前提上进行,福斯特特别重申和澄清了马克思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福斯特一方面指出,“‘占有’和‘再生产’自然不等于人可以充当自然的‘所有者’,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人不仅来源于自然界,而且也‘靠自然界生活。’”*J.B.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p.72.另一方面也强调,“在马克思看来,‘统治自然’的观念,‘并不必然是指对自然或者自然规律的极端漠视。’”*J.B.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p.2.由此可见,人类依赖于自然,但这重依赖绝非完全“征服”意义上的,而是尊重意义上的。
因此,不论是张载还是福斯特,他们都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张载主要从“同异”“屈伸”“终始”和“有无”的矛盾论范畴说明了自然万物并无孤立之理,并且以“万物相感”的方式阐释了“有动必感,有反斯有仇”的道理。如果从生态哲学意义上来看,这揭示了人与大自然应当和谐相处,因为二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阴阳协调,才能和谐相感,否则必然遭到大自然报复。同样,福斯特主要站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了人类与自然万物在进化过程中都是相互依存的,人本身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又区别于机械的自然,因为人具有生命力和能动性,这就使得人类为获得自身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与自然万物发生实践性关系,但这种实践不是绝对性的征服大自然,而是要先在性地尊重自然,这样才能使得人与大自然和谐发展。应当说,张载与福斯特在这个论调上也是同构契合的。
3.“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
在上述关于张载与福斯特的自然观阐述中,主要从自然与人的同原性与唯物性,自然万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赖性两重维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表达了人类与大自然的整体统一性,人类进行物质实践活动应当遵循客观规律和尊重大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哲学内涵。然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特别是基于人性的复杂性与生产力的发展,何以呈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社会形态则往往成了一个难题。当然,不论是张载还是福斯特,他们并未因此而放弃这一追求,二者把希望分别寄托于“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认同和建构上。应当说,这种思考路向共同表达了张载与福斯特对自然万物的终极关怀。
张载立足于“气”本论的哲学根基提出了“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其主要见之于张载《西铭》之著。《西铭》构建了一副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表达了张载关爱自然、关爱人、关爱世间万物的人文情怀。《西铭》载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也就是说,既然“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由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聚合而成,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同胞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就是朋友关系。有了这重友好关系,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则自然而然形成了具有伦理情怀与生态内涵的理想共同体。《西铭》再曰:“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巅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正蒙·乾称篇》)也就是说,尊敬长辈就是尊敬天地之长,慈爱幼弱就是慈爱天地之幼,圣人是与天地合德的,贤人也是与天地之秀者,凡是天下之病苦残疾等弱势群体,都应像我等颠沛流离而有苦无告的同胞兄弟一样能给予抚育和关怀等等,这是张载所描述的何等美妙的民胞物与之大同社会啊!“气”化生自然万物,人也属于自然万物之一部分,人是我的同胞,物是我的朋友,自然万物之间就应是和谐之共同体的建构,这也是张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追求。
那么,对于福斯特来说,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自然容易发生异化,而异化的根源就是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他以马克思的土地异化为例认为:“它既意味着那些垄断地产从而也相应垄断了自然基本力量的人对土地的统治,也意味着土地和死的事物对大多数人的统治。”*J.B.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p.74.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垄断者为了获利而不得不加深对土地的占有和无限开发,从而破坏了土地的自然属性,使土地发生异化,而同时这种异化又反过来影响着统治者甚至所有人类,因为土地(或自然)的异化将引发大地污染、资源短缺,环境破坏等等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的问题。因此,为了消除异化,必须消除私有制,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对此,福斯特特别重视马克思对“联合”和“联合生产者”等概念的探讨,认为只有通过“联合”,联合所有无产者,才能消除私有制,消灭雇佣劳动,消除物质变换的裂缝,从而消除自然异化,而这个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其不仅仅是人道主义社会,而且也是自然主义社会,福斯特引马克思语:“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页。福斯特对此阐释到:“人的这种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联合体(完全社会性的)而存在。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不再因为把私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推动力而被异化。”*J.B.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第89页。无独有偶,这是一种积极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都不会因为土地、财产、工业、利润而存在私有制和剥削,更不会因此而成为影响人们生存家园的威胁力量。这种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一种终极关怀型的社会,其不仅从人道主义关怀“人”,也从自然主义关怀“自然”,“人”与“自然”和谐共同体及其理想社会的建构是包括福斯特在内的所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探讨和追求的。
因此,不论张载还是福斯特,二者分别所言的“民胞物与的大同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事实上,他们只是站在不同的视角和立场阐释了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生命安顿和终极关怀的问题。面对现实残酷性和社会发展的某些可能性悖论,寻求并努力建构一种类似乌托邦的社会发展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是必要的,因为它给人予精神信仰和行动力量。在这一点上,张载和福斯特在分别对待自然的终极问题上已然有一定的默契。
二、张载与福斯特之自然观的异质分歧
在某种程度上,张载和福斯特之自然观的契合性比较对于当今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共识具有一定的哲学基础意义。当然,再做细究,他们关于自然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异质分歧,厘清这些分歧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二者的自然观具有一定的辩证意义。
1.“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抑或“自然界是没有等级秩序的”
事实上,从现实层面考量,张载所建构的“民胞物与”大同社会具有一定的宗法等级意涵,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封建社会的政治模式所决定的。张载尽管主张“长其长,幼其幼”,但他仍然强调“大宗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的宗法等级观念。张载认为宗法等级都是天理之所在,有尊卑才有秩序,其曰:“天子建国,诸侯建宗,亦天理也,”(《经学理窟·宗法》) “生有先后,所以为天下序;小大、高下相并而相形焉,是谓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后经正,知秩然后礼行。”(《正蒙·动物篇》)从中可知,在张载看来,宗法序格之存在是必要的,这就为自然万物之间的层级关系之建构做好了理论铺垫。那么,在自然万物之中,何为最高呢?张载认为是“人”,他曾说:“得天地之最灵为人,故人亦参为性,两为体,推其次序,数当八九。”(《易说·系辞上》)而后来朱熹因而进一步解释说:“惟人也,得其形气之正,是以其心最灵,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体于并生之中,又为同类最贵焉……物则得夫形气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与我不同类,而不若人之贵。”*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41页。因此,从人与自然这个层面来看,一方面,基于封建宗法社会的特性,“等级”序格的基础性事实无以否认,另一方面基于“性命之全”的通达,“灵贵”身份的人为性表征得以显示。所以,当人们如何以人性之“爱”去对待自然之物时,往往就存在一个亲亲推演的问题,张载明确宣称:“施爱固由亲始矣 。”(《张子语录·上》)可见,天生万物必然有亲疏远近之别,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才是最切实际的情感表达。一言以蔽之,从广义层面审视张载的自然观,包含人在内的自然万物之间确实是存在等级性的,然而这并不代表其对自然(狭隘)的漠视,而是以一种阔达的“民胞物与”情怀去捋顺人与自然之间的层级关系,张载曰:“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顺之而已。”(《经学理窟·礼乐》)
然而,福斯特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层级关系层面却表现了不同的观点,他不认为人与自然或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等级性,而是认为自然界是没有等级秩序的,是平等的。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争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唯有人的利益才是最高的,而生态中心主义则认为人也属于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自然万物都有其存在价值和权利。也即,人类中心主义唯“人”为最高地位,生态中心主义唯“自然”为最高价值。对此,福斯特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双方只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看,而没有看到它们相互依存和统一的方面。沿着这一问题,福斯特坚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人类也不再被假设地完全占有统治性地位,自然界也不是“最高天使”,而是认为人与自然是伙伴关系,它们之间是平等的,福斯特说:“自然界是没有等级秩序的,在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并没有截然的不可逾越的鸿沟。”*J.B.福斯特:《历史视野中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第2期。因此,福斯特认为必须超越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二元对立模式,还原人与自然的平等地位,“把自身的命运与地球的命运结合在一起”*J.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66页。,否则必然陷入或“控制自然”或“崇拜自然”的困顿和迷途,他说:“关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差异就被解释为空洞的抽象概念——仅仅是对诸如人类征服自然和自然崇拜之间的对立这样古老的二元论的重新阐述。”*J.B.Foster,“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2000,p.21.
因此,在对待人与自然层级关系这一问题上,张载与福斯特明显表现出不一样的观点。张载站在封建社会“宗法等级”的范式下进行阐释,认为人与人之间都存在尊卑关系,何况人与自然呢!福斯特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模式下进行辩证的,认为唯“人”或唯“自然”为最高地位都是不够合理的,只有填平二者之间的鸿沟,以“平等”言二者关系才能实现辩证统一。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张载和福斯特的分析角度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无法达到所谓的视域融合之比较意义,但是关于“人与自然”到底是“等级”关系还是“平等”关系之分析结论却是分歧明显的。
2.“阴阳两端循环不已”抑或“有限不可能变成无限”
自然(亦指自然万物)的存在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张载和福斯特对此做出了不同的阐释。张载从循环论的视角出发,认为自然万物因气化而成并受阴阳二气的作用而变化无穷,“气”聚而生,气“散”而死。当然,生与死并不是决然对立的,而是统一于“气”之循环往复之理的。这就是说,自然万物的存在是生于“气”而又归于“气”的,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过程。例如,张载指出:“阴阳之精互藏其宅,则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万古不变。若阴阳之气,则循环迭至,聚散相荡,升降相求,絪缊相揉,盖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正蒙·参两篇》)这里主要说明了自然万物循环往复之理在于阴阳二气之消长变化。此外,张载还以动物和植物为例来说明阴阳二气促使动植物聚散生死的循环过程,其曰:“动物本诸天,以呼吸为聚散之渐;植物本诸地,以阴阳升降为聚散之渐。物之初生,气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气日反而游散。”(《正蒙·动物篇》)这就是说动植物从生到死的过程都是受阴阳二气聚散变化之主导,并且也特别指明了物之成熟(或其他原因)而“气日反而游散”的循环路径。在此,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自然万物的聚散循环过程隐含着对立面的斗争,张载将其界定为“仇”(有反斯有仇),这就涉及这种斗争到底会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呢?张载认为其最终将“和而解”(《正蒙·太和篇》)且“形溃反源”(《正蒙·乾称篇》)。这就进一步说明,自然万物之间即便存在着冲突、矛盾以致生死之斗,但无以超越原有的自然本性,其最终还是要回到“太和”之气,因为“气”乃自然万物之始,阴阳两端而循环不已。所以,自然万物不论经过怎样的变化或斗争,其仍然是自然万物,其可以通过“气化”循环往复而呈现其面貌。
然而,福斯特却认为自然或自然万物是有限的,甚至已经濒临枯竭,其不可能是无限循环的。福斯特仍然站在生态马克思的立场指出,自然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有限存在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在对伊壁鸠鲁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扬弃之基础上形成的。例如,伊壁鸠鲁强调一切生命和存在的暂时性,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可能从‘无’中产生出‘有’来。再如,费尔巴哈也指出,真正的世界是有限的,有限不可能变成无限等。*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页。因而,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进行吸收,特别强调和突出大自然的有限性和短暂性,因而福斯特认为面对自然界应该给予有限性的审视。福斯特在其《脆弱的星球》一书中阐释得很清楚,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森林面积的减少、湿地的破坏、地表水的减少和污染、珊瑚礁的毁灭以及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等等已经充分表明了自然万物正发生着质的变化,这种残酷的现实也进一步说明了原生态的自然界及其生存万物是有限的。福斯特还说:“受土地和劳动力等工业的基本要素不断商业化的内在逻辑驱使,资本主义必然要破坏自然和人类的生存基础,必然使自己越来越陷入与自然的战争中。”*J.B.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99,pp.51-52.“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J.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第74页。这就更加可以说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介入,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愈加明显,但这种矛盾及其引发的激烈斗争并没有像张载所言的“仇和而解”且“形溃反源”,而是整个自然界正发生着恐怖的生态危机,宇宙社会已经呈现出了“不可持续”的发展态势,这种福斯特所言的“500年来的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正是大自然存在限度的有限性体现。所以,应当说,张载和福斯特在对于自然的存在限度这一层面的描述,是存在“无限循环”和“有限存在”的差异的。
3.“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抑或“反对道德革命”
不论自然是无限循环还是有限存在的,张载与福斯特认为都应该给予充分维护。当然,关于如何维护,在张载与福斯特那里明显呈现出了柔与刚的不同方式。张载首先明确提出了“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的柔性维护方式,其实质是道德关怀。
尽管张载认为自然万物秩存有着宗法等级性,但是仍然主张要以“大其心”来“体天下物”,这样才能达到宇宙万物阴阳感通而和谐的“太和”状态。张载指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正蒙·大心篇》)所谓“大其心”就是要扩充人的道德情感,发扬人的善性,打破主客二分的内在之别,视自然万物为我心之物,这样世界就不再与我对立,人与自然就“仇和而解”了。所谓“体天下物”就是在“大其心”的基础之上,以仁德之爱去体验和体恤自然万物。张载曰:“天体物不遗,犹仁体事无不在也。”(《正蒙·天道篇》)也就是说上天以生生之德体恤自然万物而无一遗漏,这正如人以仁德之心去体恤万事万物一样而无所不在,这主要突出人们应该以仁德之心“统天下之善”,从而做到“安所遇而敦仁,故其爱有常心,有常心则物被常爱也。”(《正蒙·至当篇》)那么,如何做到“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呢?张载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为天地立心”,只有“心”立好了,才能所谓的“体万物”。需要指出的是,“为天地立心”并不是在天地之间树立一个心来,天地本无心,关键是要从人的主体性出发,以“人心”来认识天地自然万物及其发展规律。例如,天地无心,其不会思考亦无忧患意识,所以作为主体的人就应该对自然万物要有忧患意识,要道济天下之物。对此,张载曰:“天则无心,神可以不诎,圣人则岂忘思虑忧患?……圣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横渠易说·系辞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为天地立心,就是要充分认识自然,存有忧患意识,发扬仁爱之德,这样才能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然而,在福斯特那里却表现出了明显不一样的态度,他反对将道德素养的提高或生态伦理的建立来维护大自然,换言之,他反对道德革命。福斯特明确指出:“在大多数生态道德呼吁的背后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臆断,即认为在我们的社会中个人的道德才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关键,倘若人们作为个体能够转变自己的道德立场,尊重自然,对自己的在诸如繁衍、消费以及商业领域的各种行为来一番变革,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种道德改革的呼吁对于我们社会的核心体制,即所谓的全球‘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treadmill of production)’常常视而不见。”*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2,p.44.也就是说,福斯特认为从表面上看,自然界的破坏是由于人的贪欲及其对自然的无限统治而造成的,而本质上却是因为常常被人所忽视的“踏轮磨坊的生产方式”,即以资本增值为本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们的需求、道德观念以及行为准则已经被自身所处的生存环境和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甚至强迫。例如,福斯特指出消费者消费需求并不是不道德的,也不是破坏自然的原因,最不道德的就是“生产的不道德”。只有减少投资,限制“踏轮磨坊”生产方式的继续扩大才能使自然界得以被拯救。再如,福斯特也指出公司企业的赚钱营利也不是不道德的,他们的赚钱营利并不是其自有意志所决定的,而是这个特权社会背后的体制决定了他们必须得这么干。福斯特说:“过多地把责任与非难强加到了作为个体的公司经理的身上,而他或她其实不过是体制巨轮上的一个齿轮而已。”*J.B.Foster,“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2002,p.48.所以,归根结底,从一般人的道德层面去呼吁维护大自然和拯救地球其实并不是根本出路,所以福斯特反对盲目的道德革命,而主张进行以消除资本积累和增值为任务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革命,这才是根本出路。
那么,相对张载所提倡的“大其心以体天下之物”的道德关怀使命来说,福斯特则更加从形而下的立场面对现实,把握问题并进行社会体制和生产方式的思考,以此来找到维护大自然和谐的有效路径。立足现时代,张载的道德体恤和关怀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言的道德革命或者说生态伦理的呼吁,显然这与福斯特的核心观点是不一致的。
三、张载与福斯特之自然观比较的生态启示
立足当代社会,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而透过张载与福斯特关于自然观及其生态意涵的比较性阐述,总体上可以获得以下两方面启示。
1.自然万物的“一体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合作
从张载与福斯特之自然观比较的同构契合层面来看,不论是“凡象皆气”与“直接地自然存在物”“物无孤立之理及万物相感”与“依赖自然及‘征服’自然”还是“民胞物与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都体现了一个“一体性”的理念。尽管说张载与福斯特处于不同的文明发展时代,他们关于自然观的契合性阐述也可能基于不同的文化语境甚至异样的问题而做出的某种表达,但是二者所隐含着的全人类都属于自然万物中的一员,全人类都要依赖自然万物而共生共长,全人类都应追求健康美好的理想生存家园这一“一体性”理念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为推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寻求全球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保护大自然也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全人类都承担着保护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寻求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合作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体性动力。当前,全球正面临着自然危机的残酷现实,固体废弃物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动植物的灭绝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等已经不再陌生。然而,生态帝国主义的出现更是加重了自然危机的严重程度,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寻求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合作中遇到了阻力。例如,全球变暖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但美国却拒绝在《京都协议》上签字,理由是一旦签字则意味着美国要减少碳排放量,这必将牵制美国的经济增长。显然,美国政府不想因此而付出高昂的代价。福斯特指出,美国已经因全球气候变暖而遭遇着北极冰块融化所带来的威胁甚至灾难,但是美国政府却仍然无动于衷,这就是“生态帝国主义的一个极端的例子”*J.B.Foster & B.Clark,“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Curse of Capit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2004 ed.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London: Merlin press, 2003,p.197.。此外,美国政府曾经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发射了大量贫铀穿甲弹,贫铀火箭炮和导弹,炸毁了当地诸多化工厂、生物工厂、核电站等,致使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大面积扩散,严重影响着人类的生存,据官方报告对此描述:“留在沙漠中的放射性残余高达40吨,可能导致50万人死亡。由于铀-238的放射性能够持续几百万年,整个科威特和伊拉克可能不再适合人类居住。”*J.B.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p.106.当然,生态帝国主义在自然资源掠夺、污染性工业的国外转移等方面也是表现得十分明显。不言而喻,自然万物的“一体性”及其所遭遇的自然危机以及生态帝国主义的漠视和干预使得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合作更显得必要。因此,努力寻求全球合作,培育全球公民生态意识,加强全球环境正义制度建设,构建合理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才能真正树立人类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才能确保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万物的“一体性”安全和完美。
2.自然万物的“差异性”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性推进
从张载与福斯特之自然观比较的异质分歧层面来看,其实体现了自然万物的差异性问题。人与自然到底是否存在尊卑大小或等级之别,自然万物的存在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保护大自然究竟是靠道德革命还是社会革命?这些问题整合起来看,实质上就是追问如何在自然万物的“一体性”中审视其“差异性”,因为自然万物的地位高低、有限无限,如何保护事实上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正如英国物理学家金斯(J.H.Jeans)所言:“自然的过程不可能适当地表示于空间和时间的构架内。”*参见孙显元:《现代国外自然科学家哲学思想》,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第42页。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所谓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一种不可知论,而是试图告知人们在认识自然万物的过程中应该要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视角。一言以蔽之,从自然万物的“差异性”出发,如何从中获得启示,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固然需要辩证而理性的审视。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承认人的主体性地位,又要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性,抹杀任何一个方面都无助于真正理解自然万物的整体面貌。人的主体性表明人具有区别于自然的意识能动性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如果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地位,就否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陷入了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相等同的认识误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成了无源之水,推进建设生态文明既要依靠人类集体智慧和实践能力,又要做到以全人类的普遍利益实现为根本。然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并不等于说人类可以高高在上而忽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基本权益,大自然本身也有生生之意,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和利用应该充分尊重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性,否则,人类将自取其咎,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3页。因此,与其将人类与自然放在谁为最高性的争论中,不如要求人类自我真正履行一名理性生态人的角色。此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看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一面,张载所谓的“气”化万物循环论本质上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诠释,其能给我们提供的也就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价值观念,却无法真正引导我们把握宇宙世界中的自然危机问题。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应该超越自然万物的有机循环论,深入自然万物的生态系统,认清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球承载能力的脆弱性等现实问题,以便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最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要有根本问题的变革出路,又要有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法。福斯特认为自然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并非人类的道德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则应该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这才是有效出路。然而抛给我们的难题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或者“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建设”如果没有“资本”的支撑,那么何以“现代化”?资本的增值和贪婪确实可怕,我们也无法真正改变资本的本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限制资本的扩张,通过健全的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去改造人性和规范人行,使人类对资本的利用和扩张能够将损害大自然的程度降到最低。应当说,生态文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而应当从广义上充分认识到自然万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既要看到其一体性,又要把握其差异性,循序渐进,理性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