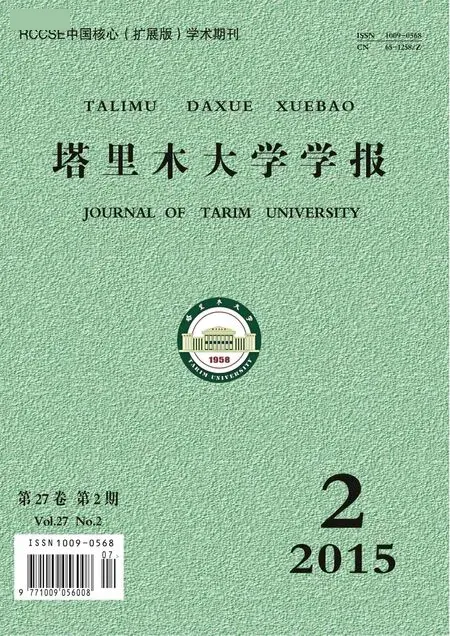古代龟兹乞寒舞研究
连殿冬 于 力 拓万亮
(塔里木大学体育工作部,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古代龟兹乞寒舞研究
连殿冬 于 力 拓万亮
(塔里木大学体育工作部, 新疆 阿拉尔 843300)
通过民族学、历史学、体育学和考古学等多种学科原理,结合背景分析、综合分析和文献资料法等,对古代龟兹乞寒舞的产生、内容、性质、表现形式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结果表明:乞寒舞产生于生产、生活实践与战事之中,具有祭祀性、集体性和武舞的舞蹈特征,其内容完整地反映了古代龟兹民众祭祀、祈福、征战等过程,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西域民族体育风格;并对中原和日本等地的民俗体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乞寒舞; 内容; 性质; 表现形式; 东渐
我国著名的东方学家季羡林先生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1]古代龟兹地区位于今天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北沿,是丝绸之路中道必经之地,它处于中原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四大文化交汇之处,多种异质文化在此汇聚、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逐渐形成了兼容并包而又自成体系的璀璨的龟兹文化式样。多元文化生态也催生出了花开别样的龟兹民俗体育。以乞寒舞为代表的古代龟兹民俗体育曾经大放异彩,并对中原和日本等地的民俗体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纵观学术界对乞寒舞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对乞寒舞源流的考察,如赵世骞的《西域乞寒舞》一文和王嵘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苏莫遮>》一文;二是对乞寒舞的东渐和流变过程的研究,如柏红秀等的《泼寒胡戏之入华与流变》一文和王凤霞的《从泼寒胡到苏幕遮——泼寒胡戏在中原地区流变的几个阶段》一文;三是对乞寒舞在中原地区被禁断原因的考察,如丁淑梅的《唐代禁断泼寒胡戏的戏剧学考察》一文和赵望秦的《泼寒胡戏被禁原因发微》一文;四是从考古文物角度对乞寒舞活动内容的研究,如王嵘的《龟兹舍利盒乐舞图文化解读》一文。通过对乞寒舞文献资料的考察,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从体育学的视角出发对乞寒舞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从体育学视角出发研究古代龟兹乞寒舞对于丰富乞寒舞的研究视角亦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古代龟兹乞寒舞的源流
龟兹,又名“丘兹”、“屈支”、“拘夷”、“苦叉”等,它位于中亚腹地的塔里木盆地。在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山脉与雀尔达格山、库鲁克达格山、塔里木河之间形成了一个从南到北宽约300多公里的富庶地带,这就是古代龟兹之地。《汉书·西域传》中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2]古代龟兹国的疆域,据《大唐西域记·屈支国》记载:“屈支国,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3]龟兹古国的物产也极其丰富。据《册府元龟·外臣传》载:“(龟兹国)能铸冶,有铅。……婚姻、丧葬、风俗、物产与焉耆略同。唯气候少温为异。又出细毡、獐皮、氍毹、铙沙盐、绿雄、雌黄、胡粉及良马、封牛等。……土多稻、粟、菽、麦、饶铜、铁、铅、安息香、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4]古代龟兹也是“丝绸之路”西域段中道的必经之地。东行七千余里可达中原,北越天山隘口可低乌孙草原故地,西行可达中亚、西亚诸地。独特的丝路区位促进了龟兹商品贸易的高度发达,东汉时,“丝绸之路”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5];而且,“丝绸之路”的开通也诱发了不同类型的文化在此汇聚、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季羡林先生认为“龟兹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和汉唐文明唯一的交汇处”[6],可见,古代龟兹文化是多种异质文化相互撞击、交流与融合下的结晶。总之,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为古代龟兹乞寒舞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乞寒舞作为古代龟兹民俗体育的典型代表,关于它的起源,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其主要有三种起源说:波斯说、康国说和龟兹说。
岑仲勉先生认为“乞寒舞”起源于波斯。他曾在《唐代戏乐之波斯语》中引用波斯萨珊王朝民间节日的泼水故事,故事云:“Farvardin月之六日,供奉不死圣神Hanr vatat 举行大新年节。是日,谓之谋望日。相传命运神于本日支配快乐也。人民互用水相洒。有谓此日系供奉水之保护神者;有谓神话中Jamahid王因缺水乏雨,特令开凿运川,以图救济,故纪念其乐时者;更有谓此王颁定用水传祓之制,因而留此纪念者。”而供奉不死之神用的不死之酒是用“苏摩”草酿制的,因此,岑仲勉先生认为“苏幕(摩)遮”即乞寒舞起源于波斯[7]。
据史籍记载,乞寒舞源自西域康国。《文献通考》中记载:“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其乐大抵以十一月,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8]《旧唐书》亦云:“(康国)以十二月为岁首……至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泼,盛为戏乐。”[9]以此看来,乞寒舞应该出自西域康国。
另据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中又表明“乞寒舞”是古代龟兹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形式。据唐代僧人慧琳所著的《一切经音义》记载:“苏幕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达。此戏本出自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状,以泥土沾洒行人,或持绢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灾,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10]而且,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亦云:“龟兹国,元日斗牛、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婆罗遮(即乞寒舞),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为戏。”[11]此外,在龟兹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有关于乞寒舞生动的描绘。二十世纪初,日本探险家在今新疆库车县城以北20多公里处的昭怙厘佛寺遗址中挖掘出一个绘有精美乐舞图像的舍利盒。其盒身上绘有由21人组成的演出团队,其队员依次为手持舞旄的女舞者,将舞旄斜插身后的男舞者,六位手牵手相连的头戴各式假面具的舞蹈者,一位头戴颇似猴面的假面具并且手持一根舞棍的独舞者,紧接着是由八人组成的一组乐队,最后又是一位头戴假面具的、手持一根舞棍的独舞者,并有三个孩童围绕其身。整幅乐舞图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形式恰如文献记载所描述:“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其应为“乞寒舞”演出内容的一部分,也应是其最具有艺术魅力的一部分。可见,乞寒舞应是古代新疆龟兹地区的一种民俗体育活动。
以上三种起源说可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本文认为流行于古代龟兹地区的“乞寒舞”是多种文化撞击、交流、融合下的产物,它一经产生就受到古代龟兹和西域诸国人民的普遍接受和喜爱。
2 古代龟兹乞寒舞的概说
乞寒舞,又称为苏幕遮、婆罗遮、泼寒胡戏。从史籍记载和出土文物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乞寒舞的全貌。此舞表演者分作三队,一队头戴各式面具,载歌载舞;一队舞蹈者或以水相泼,或以绳索套人取乐;一队为持各种乐器进行伴奏。表演过程中,伴随着“腾逐喧噪”的人声和各种乐器齐奏的相和,声振百里,惊天动地。这充分显示出西域少数民族粗犷豪放的性格特点和及时行乐的狂欢情绪。而从乞寒舞盛大的仪式、舞者头戴各式面具的舞蹈内容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舞蹈者把乞寒舞作为一种媒介,作为人神沟通的载体,把自己全部的信仰与情感都倾注到表演动作中,用以娱神、媚神和祭神。从中不难看出是原始宗教祭祀和各种图腾崇拜所遗留下来的痕迹;另一方面,捉人为戏的“人”应指罗刹的扮演者,而“罗刹”应是印度佛教中的人物,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驱魔活动;泼水沾洒行人,是古代波斯、印度供奉不死之神的活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外来的宗教文化也被龟兹人吸纳进来成为乞寒舞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文献通考》中记述“乞寒舞”的本源是西域康国,那么以此推测,龟兹本地的“乞寒舞”可能由康国传入,或者至少是吸收与借鉴了康国“乞寒舞”的一些宗教或艺术内容。因此,可以说乞寒舞是古代龟兹艺术家吸纳融合百家之长而推陈出新的,具有龟兹地方特色和审美形态的艺术形式。
3 古代龟兹乞寒舞的性质
乞寒舞作为古代龟兹地区的一种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西域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其性质有如下几个方面:
3.1 一种祭祀性舞蹈
对于乞寒舞的这一性质,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首先,从乞寒舞的舞蹈名称来看,它是一种祭祀性舞蹈。乞寒舞,顾名思义就是乞寒求水,冻灭害虫,多降瑞雪,祈求来年身体安康、人丁兴旺、雨水充沛、农牧业丰收。谷苞先生指出:“乞寒舞的主观愿望是为了乞寒,同时也是为了乞水,乞求有大量的水从山区滚滚流出灌溉农田。”[12]在古代新疆南部地区的农业灌溉主要靠天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等山区的积雪融水,于是民间自发地跳起“乞寒舞”祈祷山中多降水积雪,以利于来年农牧业的丰收;其次,乞寒舞中还包含以泥土沾洒行人的活动内容。佛雷泽在谈到世界不少地方的居民普遍存在的定期驱邪仪式时指出:“人们逐渐觉得需要定期地普遍地消除邪恶,一般是一年一次,为的是使人们能够重新开始生活,摆脱他们周围长期积累起来的邪恶影响。”[13]因此,龟兹本地民众在每年的七月初公行乞寒活动,在活动中以泥土沾洒行人,用以祛除人们生活中的各路妖魔鬼怪,使人们能够摆脱他们周围长期积累起来的邪恶影响,并能够开始新的生活。简言之,乞寒舞中以泥土沾洒行人的活动内容,也表明乞寒舞是一种祭祀性舞蹈;再次,由乞寒舞活动中一部分表演者的装束来看,即“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状”[14],乞寒舞具有宗教祭祀性。乞寒舞中戴上假面的表演者就具有了宗教意味,表达出某种祈愿与禁忌行为的神圣之举,象征无言的警示和声明作用,从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用以为人们祈福与禳灾。
3.2 一种集体性舞蹈
根据出土文物和史籍记载,乞寒舞为一种集体性舞蹈。乞寒舞是盛行于龟兹等西域各地的祭祀性和群众性的街头假面歌舞戏,活动过程中旗鼓开路,声势震天,气氛热烈,人物众多,边行边舞,边舞边歌,表演者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既有身披铠甲者,也有形体裸露之人;有人手捧盛水油囊或容器,有人手持套人绳索,或以相互沾洒泥土为戏,或以搭钩捉人作耍;演员与观众融为一体,乐舞气氛威武雄壮,场面甚为壮观。乞寒舞演出之际,成为一场全民狂欢盛宴,“男女无昼夜歌舞”;乞寒舞不仅仅限于一城一地,活动之际整个西域地区都为之动容。般若三藏译著的《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中记载:“老苏幕遮,亦复如是,从一城邑至一城邑,一切众生披衰老帽,见皆戏弄。”[15]凡此种种皆表明乞寒舞是一种流行于西域地区的,表演人数极其众多的集体性舞蹈。
3.3 一种武舞
乞寒舞也是一种武舞。《新唐书·宋务光传》载:“……此见坊邑,相率为浑脱队,骏马胡服,名苏幕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相也……”[16]。这里的“军阵势和战争相”表明了乞寒舞是一种武舞。而且乞寒舞中所用的乐器之一“铜角”是军队鼓吹乐器之一;此外武士和一部分舞蹈者身上穿着甲胄服饰。“甲”是古时战士的护身衣,用皮革或金属做成;“胄”即头盔,是古代战士所带的帽子。这些乐器与服饰也表明了乞寒舞是一种武舞。总之,当古代龟兹地区处于和平时期,在乞寒舞举行期间,也将军队仪仗仪表的检阅纳入其中,久而久之,“军阵势”也成为乞寒舞活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古代龟兹乞寒舞的表现形式
4.1 穿戴装饰方面
因乞寒舞流行于西域地区,所以表演者最基本的服饰为胡服。胡服的服饰大体为身穿翻领紧袖花边长袍,腰扎联珠纹饰腰带,下穿长裤,足登高筒皮靴,腰上佩带有一把短剑。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也记载了龟兹地区的服饰:“服饰锦褐,断发巾帽。”[17]佩带面具的舞蹈者是乞寒舞表演形式中的灵魂人物,他们往往占据着表演队伍中的核心位置。他们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做种种面具形状,而面具的形式主要以狗头猴面为主。这些假面舞者身穿甲胄般的彩色服饰,上身内穿贴身紧袖服,外穿圆领花边短袖紧腰外套,底襟为弧形,腰下扎有方形小裙,腰间系扎着两片尾部开叉的下甲,足蹬软靴。这些别具一格的装饰与服饰,充分表现出了乞寒舞独特的艺术形式和魅力。
4.2 演奏乐器方面
乞寒舞中的演奏乐器比较多。《文献通考》记载:“其乐器有大鼓、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18]大鼓是中原先秦时期流行的乐器,很早以前就传入西域。因此,大鼓在西域是一种比较普及的乐器;鼗鼓与鸡娄鼓是一种独特的乐器组合,两种乐器由一人演奏。鼗鼓是中原周朝就有的乐器,其形制多为一根柄上串连一至三个小鼓。鸡娄鼓源于西亚,因形似鸡娄而得名。《文献通考》记载:“鸡娄鼓,其形正而圆,首尾所击之处平,可数寸。龟兹、疏勒、高昌之器也。后世教坊奏龟兹曲用鸡娄鼓,左手持鼗牢,腋挟此鼓,右手击之以为节焉。其形如瓮,腰有环,以绶带系之腋下。”[19]琵琶和箜篌由波斯传入。箜篌又分为竖箜篌和弓形箜篌两种。竖箜篌是龟兹地区的主要乐器,它的共鸣箱头部为尖形,整个乐器呈流线形体;弓形箜篌源于古印度,印度人称其为“维那”,中原汉族人称其为凤首箜篌,而且它也是龟兹石窟壁画里出现频率最多的乐器之一;铜角是一种声响很大的,用来营造气氛的乐器。角本是游牧民族惊马之器,后来多用于军队鼓吹乐中。《通典》云:“西戎有吹金者,铜角是也,长二尺,形如牛角。”[20]上述即为乞寒舞中主要的演奏乐器。从中我们也能看出龟兹地区的乐器既有古代波斯、印度的乐器身影,也有中原地区的乐器元素。可见,多元化的乐器组合也反映出古代龟兹乞寒舞的多元融合性特征。
4.3 表演内容方面
乞寒舞的表演内容丰富多彩。既有骑马武士排列成的纵队,也有头戴各式假面具的舞蹈内容,还有乐队伴奏。在整个舞蹈过程中舞者并非独自“寒江垂钓”,还有行人和观众被席卷其中,也即包含以泥土沾洒行人和套勾行人的活动内容。因此,乞寒舞更像是一场规模盛大的巡游活动和全民参与的狂欢节。
5 古代龟兹乞寒舞的东渐
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汉代以来历届中央王朝对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和控制,西域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日趋紧密,双方的文化交流与经贸往来也渐趋频繁。因此,自汉代以降,以乞寒舞为代表的古代龟兹民俗体育逐渐传入中原地区。并且随着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与联系,古代龟兹乞寒舞又远传日本,并对当地的民俗体育文化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古代龟兹乞寒舞至晚在西魏或北周时就已经传入中原地区。最早记载乞寒舞在中原演出盛况的是唐人令狐德棻等人撰写的《周书》,据其记载,北周宣帝宇文赟于“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十二月甲子,还宫,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伎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泼为戏乐”[21]。可见,北周时的“乞寒舞”是在皇宫中演出,而到了唐朝,“乞寒舞”已经成为京城长安醴泉坊一带龟兹人聚居区一年一度的盛大节日,不仅皇帝登御楼观赏,还动员诸司长官观看。对此,史籍中多有记载。据《旧唐书》记载:“(神龙元年即公元705年)十一月乙丑,御洛阳城南门楼观泼寒胡。”[22]另有《旧唐书·张说传》记载:“自则天末年,季冬为泼寒胡戏,中宗尝御楼以观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戏。”[23]可见,至唐朝中晚期,源自龟兹的“乞寒舞”不仅是西域胡人娱人娱己、思念故土的民俗体育活动,它也成为唐朝宫廷礼仪中的重要活动内容。
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继位。而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呈现出种种盛极而衰的迹象,例如在文化政策上由开明、开放而趋于禁锢、保守,由龟兹传入的乞寒舞正是在唐玄宗为政时期而遭到禁止的。 《唐大诏令集》记载了乞寒舞被废止的前因后果。其诏令云:“腊月乞寒,外蕃所出;渐渍成俗,因循已久。致使乘肥衣轻,俱非法服,阗城隘陌,深点华风。联思革颓弊,返于淳朴。《书》不云乎:‘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况妨于政要,取紊礼经。习而行之,将何以训?自今以后,即宜禁断。开元元年十二月七日。”[24]自此,泼寒胡戏即“乞寒舞”在唐代市民社会中销声匿迹。而乞寒舞中艺术化的乐舞部分,即“苏莫遮”“曲”被保留下来,依然作为宫廷乐舞的一部分。但却对其作了艺术化的处理,例如将金凤调《苏莫遮》改名为《感皇恩》,沙陀调《苏莫遮》改名为《万宇清》,而水调《苏莫遮》仍保持原名。自此以后,艺术化的《苏莫遮》成为君主显示皇威、增福添寿的宫廷乐舞。
“乞寒舞”中艺术化的部分即“苏莫遮”随着中原唐王朝与日本的交流与往来也流播到日本,并成为日本舞蹈艺术最具魅力的一部分。“苏莫遮”传到日本后成为日本天王寺的秘传舞蹈。并且由集体舞变成了独舞,舞者披着蓑衣,戴着面具,左手执桴,右手剑指。这里的“戴面具”同古代文献中关于“乞寒舞”的记述“或作兽面,或象鬼神,假作种种面具状”、“并服狗头猴面”[25]是相一致的。然而,该舞的内容已完全不同于唐代的“乞寒舞”了。该舞表现的是:日本古代英明的圣德太子迁往片冈的宫殿,途中遇到一条大河,圣德太子立在河边,吹起了悠扬的洞箫乐曲,使山神忍不住跳出来,随着乐曲声翩翩起舞。这已完全日本化了,不过在形式上还保留着唐舞的某些特色,如戴面具、弓箭步、剑指、圆场等[26]。
总之,古代龟兹民俗体育活动“乞寒舞”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互动与融合背景下的产物,它经由丝绸之路东传到中原地区,并经由中原王朝又流播到日本等地区,从而丰富了上述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内容,并经历了交流、撞击、冲突、互动和融合等诸种历程,最终成为当地民俗体育文化的一部分。
6 结语
古代龟兹乞寒舞是多种异质文化汇聚、碰撞、冲突、交流与融合下的产物,它源于民间,最初为一种祭祀性舞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不断地融进了一些军事和日常生活等内容,具有武舞和集体性舞蹈的特点。而且,不论是在穿戴服饰方面,还是演奏乐器方面,或是表演内容方面,乞寒舞的表现形式极其丰富多彩,在实践过程中它具有锻炼身体、愉悦身心和沟通情感等诸多价值。随着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古代龟兹乞寒舞又远传中原地区和日本等地,从而丰富了上述地区的民俗体育活动内容。总之,古代龟兹乞寒舞是在多元文化互动背景下吸纳、融合多种异质文化而形成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这种民俗体育艺术形式为现代民俗体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一是现代民俗体育在发展中要具有开放的心态,即以积极的心态接纳异质文化的传播,采纳与借鉴异质文化中的精华,从而丰富、发展、壮大自身;二是通过文化交流,使民俗体育走出“家门”,为异域它乡的民众所接触、了解、欣赏、认同和接受,从而提升本地民俗体育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简言之,在“文化强国”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引下,对古代新疆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繁荣新疆文化的多样性,这对于正确阐明新疆历史,实现新疆多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构筑多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目标,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季羡林.朗润琐言:季羡林学术思想精粹[C].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119.
[2] (东汉)班固撰.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2007:1456.
[3] (唐)玄奘撰,章巽点校.大唐西域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3.
[4] (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11299.
[5] (南朝宋)范晔,(晋)司马彪撰.后汉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4:1299.
[6] 刘阳、曾玉华. 龟兹文化对唐代长安体育的影响[J].体育文化导刊,2013(1):128-130.
[7] 霍旭初.龟兹艺术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266~267.
[8]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4.
[9] (后晋)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310.
[10] (唐)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M].台北:大通书局,1985:868.
[11] (唐)段成式撰,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5:37.
[12] 贾应逸,霍旭初.龟兹学研究(第一辑)[G].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348.
[13] 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金枝(下)[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788
[14] (唐)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M].台北:大通书局,1985:868.
[15] 王昆吾,何剑平.汉文佛经中的音乐史料[G].成都:巴蜀书社,2001:203.
[16]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77.
[17] (唐)玄奘撰,章巽点校.大唐西域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3.
[18]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4.
[19]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08.
[20]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3674.
[21] (唐)令狐德棻等撰.周书[M].长春:吉林出版社,1995:58.
[22] (后晋)刘昫.旧唐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87.
[23] (后晋)刘昫.旧唐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936.
[24] (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G].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517.
[25] (唐)释慧琳撰.一切经音义[M].台北:大通书局,1985:868.
[26] 金秋著.丝绸之路乐舞艺术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259.
Research on Ancient Qihan Dance in Qiuci
Lian Diandong Yu Li Tuo Wanlia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rim University, Alar, Xinjiang 843300)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ethnology, history, sports and archaeology and with the methods of background analysi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literature review,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birth ,contents, nature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of sports involved by ancient Qihan dance in Qiuci. The Qihan Dance were born in agriculture work, life and warfare. With the characters of military dancing, sacrifice and group dancing, it reflected the whole process of fighting , returning successfully and sacrifice of the local people. The sports contain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minority style of sports in the ancient Qiuci; it produced improtant influence on the folk sports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Japan.
Qihan Dance; contents;nature; form of expression; eastward transmission
2014-06-2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CTY033)
连殿冬(1978-),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文化。 E-mail: liandiandong@163.com
1009-0568(2015)02-0073-06
G85
A
10.3969/j.issn.1009-0568.2015.02.014
- 塔里木大学学报的其它文章
- 新疆杂话中的民间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