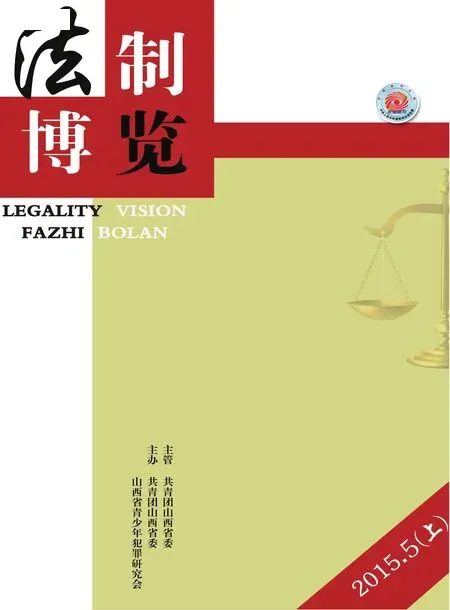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变迁轨迹
——以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为视角
李阳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变迁轨迹
——以盗窃罪的犯罪构成为视角
李阳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经历多次大修小改,其修改呈现出一定的特征。盗窃罪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数次修改,理论上盗窃罪客观方面从秘密窃取说到平和窃取说、客体的所有权说到占有说的转变,由此不难看出我国刑法修改轨迹的变迁,得出我国刑法发展变迁中关于刑法罪名的覆盖范围逐步与社会发展情况相符合、调控范围不断扩大、应对型以及法定刑幅度不断提高的变迁特征。
刑法修改;盗窃罪;调控范围;规制
自我国1979年刑法实施以来,我国刑法以平均每年一次的频率修改。在这三十多年的刑法修改中,我国刑法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理论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文以盗窃罪为切入点,从盗窃罪的立法发展变迁和其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出发,分析盗窃罪这三十多年以来的发展变迁,进而对我国刑法发展变迁的轨迹作出分析。
一、我国盗窃罪在立法上的发展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以1979年刑法为开端,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修改和完善。我国79年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规定集中在一百五十一条到一百五十三条,主要是对盗窃罪的数额、对象、量刑标准和转化抢劫做出了规定。在这些规定中,盗窃罪只是作为一种财产犯罪被笼统的与诈骗、抢夺规定在一起,其量刑标准和法律适用标准也没有作出相应的区分,与诈骗与抢夺适用同一量刑标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盗窃罪的发生频率有所升高,盗窃方式也逐渐多元化,这对有关盗窃罪的立法提出了新的要求。1997年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适应了这一要求,相关规定更加详尽和完备,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79刑法中惯窃的规定在97刑法中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加严谨的关于“多次盗窃”的规定。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对于1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自此,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包括盗窃财物数额较大和多次盗窃两种,而对于入户盗窃或扒窃行为,即使不符合数额较大的要求,也可以根据行为次数的多少予以惩治[1]。第二,在对盗窃犯适用主刑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适用附加刑的规定,明确了盗窃罪死刑的适用条件。第三,盗窃罪的对象增加了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通讯线路、电信码号是无形财物,其经济价值不仅反映在电话初装费,手机入网费,还表现在用户因这些无形财物被窃取而可能支付的电话费,[2]所以97刑法规定了这种无形财物的窃取方式包括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促使出现很多新的有价值的无形财物,司法实践中盗窃这些无形财物的案件屡见不鲜,97刑法的规定无疑是对无形财产保护的一个良好开端。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盗窃罪又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重新取消了盗窃罪死刑的适用,将盗窃罪的最高刑确定为无期徒刑;将《刑法》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多次盗窃的”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对盗窃罪的客观方面做出了修改,增加了三种新的盗窃类型,即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扩大了盗窃罪的刑罚范围,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关于盗窃罪规定的新进展。
二、盗窃罪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变迁
我国关于盗窃罪的法律规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变迁,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与进展,与此同时,关于盗窃罪构成要件方面传统的理论在实践应用中也备受质疑,学术界不断出现新的关于构成要件方面的理论。下面就盗窃罪构成要件方面的理论发展展开讨论。
(一)关于盗窃罪客观方面的发展变迁
我国理论界通说认为“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3]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将盗窃罪客观方面界定为“以秘密窃取的方法,将公私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并非法占有的行为”。但是随着很多以公开窃取方式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的出现,“秘密窃取说”的缺陷日益显露,通说观点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有所下降。我国刑法学界就此展开争论,对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是否仅仅局限于秘密窃取很多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张明楷教授所倡导的平和窃取说。
平和窃取说认为“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意志,采取平和手段,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盗窃行为既可以具有秘密性,也可以具有公开性”[4]。“他们认为,窃取这个用语并不只限于秘密地取得,在公开地侵害占有的场合也是窃取,至于窃取的手段和方法没有限制。”[5]《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将扒窃行为纳入盗窃罪的范围之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平和窃取说的赞同。扒窃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一般理解为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秘密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的财物的行为,扒窃行为在公共场所实行,并不符合传统理论中关于秘密窃取的条件,是一种公开的平和的获取他人财物的方式,将其纳入盗窃罪范围,是一种理论和实践上的进步。但传统理论认为,这里所谈的秘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秘密”,“所谓秘密并不是对任何人的秘密,而仅仅是针对窃取当时财物控制人而言,如果窃取行为人窃取财物时被财物控制人以外的第三人发觉,只要还没有被财物控制人发觉,则不影响窃取财物行为的秘密性。”[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秘密窃取说”和“平和窃取说”其区别的关键在于对于秘密窃取中“秘密”的含义所产生的不同的认识,秘密窃取中“秘密”在满足犯罪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同时是否需要满足“秘密”的客观条件,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二)关于盗窃罪客体方面的发展变迁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也就是所谓的所有权说。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财物所有权与其使用权、占有权等各项权能逐渐分离,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逐渐复杂化。只强调保护财物所有权势必导致权利人其他财产权益受到损害而无法得到刑法上有效救济,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
由于传统的所有权说理论的缺陷日益显露,有学者提出学习借鉴日本刑法理论中的占有权说。占有权说主张的是对财产的占有状态予以保护,保护的法益是财产的持有,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事实上的占有本身,不仅包括合法的占有,而且包括非法的占有”[7]。但有学者认为,占有权说主张对财物的占有权进行保护,虽然能够有效的打击犯罪,但同时会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基于此,理论界提出混合说,认为“财产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及其他本权,其次是需要通过法定程序改变现状(恢复应有状态)的占有;但在非法占有的情况下,相对于本权这恢复权利的行为而言,该占有不是财产犯的法益。”[8]这种观点以占有说为基础,在对占有权说作出限制的同时对所有权说予以扩张,将占有纳入到盗窃罪的客体之内,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三、我国刑法发展变迁总趋势
盗窃罪在立法和理论的不断变迁都是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所呈现出的新情况,使刑法能更加有效的规范人们的行为,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前文对盗窃罪的立法和理论的发展变迁的总结,我们大致可以由此分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发展变迁的总趋势。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刑法关于罪名的覆盖范围逐步与社会发展情况相符合。79刑法诞生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立法经验不足,当时的刑法还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阶段,相关规定也呈现出“宜粗不宜细”的特点。当时我国经济发展程度尚较低,盗窃罪的发生频率也相对现在而言比较低,这也导致盗窃罪没有引起当时立法者的足够重视。到97年,社会经济有所发展,盗窃罪发生频率有所提高、方式逐渐多样化,79刑法的相关规定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97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积极应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的盗窃方式,将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纳入到盗窃罪的对象之中。无形财物作为一种具有经济价值属性、能够被人力所控制、占有的财物,具有盗窃罪对象的一般特征,将其纳入盗窃罪对象中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刑法修正案(八)》将盗窃罪的入罪范围扩大,也是由于近年来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等行为增多,在尚未达到97刑法规定的入罪标准时,仅仅依靠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来进行处罚无法有效的控制这种盗窃行为的发生。对刑法某些条文的修改以及增加,很大程度上都是积极适应社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的需要。
第二,刑法调控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刑法的历次修改,大多以入罪条款及新设罪名的增加为特点。例如,97刑法相对于79刑法而言,刑法所规定的罪名由一百多种增加到四百多种,入罪条款和罪名的增加,势必导致刑法调控范围不断的扩大。《刑法修正案(八)》将盗窃罪的入罪条款新增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盗窃形式,实际上扩大了刑法对盗窃罪的调控范围;另外《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危险驾驶罪,将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的行为纳入到刑法规制的范围内,也是刑法调控范围扩大的典型变现。在盗窃罪的构成要件新的理论中,将盗窃罪的客观方面界定为以平和方式窃取他人财物,在司法实践中可以将一些非以传统的秘密方式窃取财物的行为纳入到盗窃行为之中,以及占有说的出现将盗窃罪的保护范围扩大为占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有扩大刑法调控范围的趋势。
刑法的效益主要是以刑法对犯罪的控制为重点,将刑法调控范围不断扩大,无疑可以达到犯罪控制的效果,在短期内实现刑法的效益,但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关注这样的刑法运行是否会带来较大的代价,无限扩大刑法调控范围势必导致刑法威慑力的降低。刑法不但有控制犯罪的有利后果,同时也对犯罪人和社会造成不利后果。我们在考虑刑法效益的同时,必须关注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这就要求在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中,必须把握必要限度,在追求犯罪控制的积极效果的同时,确保新的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的积极效果大于消极效果。
第三,我国刑法的修改具有“应对型”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迅猛发展造成司法实践中新型犯罪行为与行为方式的出现,79刑法依据当时的国情所制定出的刑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无法有效规制新出现的犯罪行为。例如,97刑法纳入盗窃罪范围的通讯线路、电信码号等无形财物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这种无形财物的出现,实践中出现盗窃这种无形财物的行为,对于盗窃这种无形财物是否能够以盗窃罪论处,根据79年刑法无法做出有效判断,97刑法将其纳入盗窃罪的对象范围,就是刑法“应对型”特征的体现。
我国刑法的“应对型”特征,是由成文法国家法律所固有的滞后性所决定的。成文法的这种天然滞后性要求立法机关顺应社会发展,迅速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反应,以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法律的稳定性决定了刑法不可能朝令夕改,这就造成了刑法的滞后性。我国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当司法实践中出现新的犯罪行为的时候,现有法律无法对其做出有效规制,大量司法解释应运而生,对司法实践进行指导,这是我国刑法应对性的一个典型表现。
第四,附加刑被广泛适用,法定刑幅度有所升高。我国刑法修改中法定刑的提升主要以97刑法为分水岭,97刑法以前的相关单行刑法呈现出严重的重刑思想,而在97刑法后的修改中虽然刑罚幅度有所降低,但总体上仍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以盗窃罪为例,97刑法将盗窃罪的法定刑的最高刑提高为死刑,并在对盗窃罪适用主刑的基础上增加附加刑的适用,虽然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重新取消了死刑对于盗窃罪的适用,但是与79刑法中关于盗窃罪的规定相比,附加刑的适用导致盗窃罪的法定刑幅度总体升高。目前的刑法规定中,附加刑与经济犯罪形影不离,几乎所有的经济犯罪都在主刑的基础上规定了处罚金或没收财产的附加刑,这无疑是加重了刑罚法定刑。另外,关于死刑的适用,在79刑法中只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97刑法颁布以前,《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等多个单行刑法的出台使死刑罪名增加到了71个。死刑罪名在经过97刑法及《刑法修正案(八)》的削减减少到55个,但不可否认,总体上我国刑法关于死刑的适用明显增加,法定刑幅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我国刑法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与完善,已经初步摆脱了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发展的落后状态,从最初照搬苏联刑法逐步改变为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借鉴国外立法经验,我国刑法体系逐步科学化,对社会的调控力度也逐渐增强。但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的刑法立法和理论都存在着需要完善的部分,我国刑法的发展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
[1]王瑞祥.浅论盗窃罪的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第39条的理解与适用[J].天津法学,2012(1).
[2]赵秉志.刑法分则要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89.
[3]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504.
[4]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J].法学家,2006(2).
[5]高格.比较刑法学[M].长春:长春出版社,1991:563.
[6]赵秉志.刑法分则要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384.
[7]陈洪兵.财产罪法益上的所有权批判[J].金陵法律评论,2008.
[8]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02.
D924.3
A
2095-4379-(2015)13-0018-03
李阳(1991-),女,山东威海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2013级刑法学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