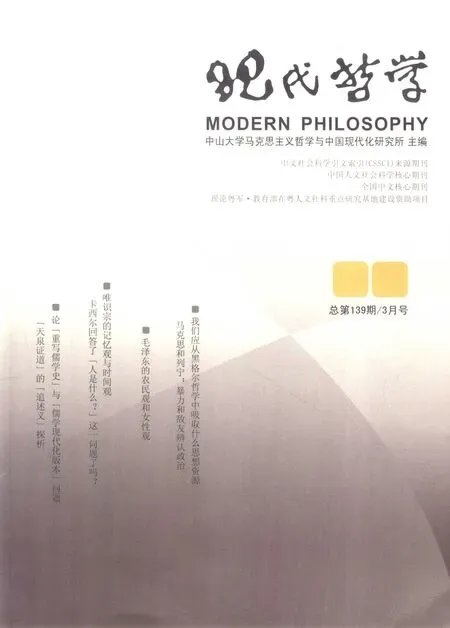谁之正义?何种自然?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的自然正义
高健康
谁之正义?何种自然?
——《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五卷第七章的自然正义
高健康*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本文试图探讨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到底是何种自然。本文认为,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更进一步,自然正义作为公民的正义的一种,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再经过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论述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进行对比,笔者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因为它是人生而具有的、并且是由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完善而来的。
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自然;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以下简称《尼伦》)的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著名的自然正义①“自然”一词的希腊文为“phusis”,英文为“nature”,汉语则有多种翻译,比如“本性”,本文试图全部用“自然”一词来翻译,包括人的自然。而“正义”一词的希腊文为“dikaiosunē”,英文为“justice”,汉语又译为“公正”或“公道”,本文试图全部用“正义”一词来翻译。据此所发生的译文改动,下文不再说明。本文中涉及《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的引文主要来自廖申白先生的商务印书馆译本。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历来学者主要关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正义与自然法的关系,并且一般把亚里士多德视为自然法的真正奠基者。②但也有学者如施特劳斯(LeoStrauss)和亚科(BernardYack)等不同意这一看法。以亚科为例,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正确不是指一套更高的正义标准,而是指一种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然发展着的关于正义的判断。参见[美]亚科:《自然正确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城邦与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刘小枫编,柯常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54页。亚科对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思想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有论文两篇:1、《自然正确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2、“CommunityandConflictin Aristotle'sPoliticalPhilosophy”,TheReviewofPolitics,vol.47,No.1;还有论著一本:ProblemsofaPoliticalAnimal,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但本文主要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谈的自然正义究竟是谁之正义、何种自然?在研究进路上,笔者主要采取《尼伦》书中各处相关论述的对比阅读的方式进行。本文的第一部分讨论“谁之正义”的问题,结论是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而且自然正义作为属人的正义,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是对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也就是说,自然正义是公民的正义的一种。第二部分探讨“何种自然”的问题。
一、谁之正义?
“谁之正义?”这个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自然正义所指的“正义”到底是属于谁的?与神和其他低等动物有关吗?在人类之中自然正义关涉的是所有人吗?抑或只是人类中的某些部分?
(一)“正义是属人的”,神和其他低等动物与正义无关
在《尼伦》第五卷第七章中,亚里士多德就提到了神的正义:“在神的世界这个说法也许就完全不对。”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49页,1134b27。引文中强调为笔者所加,以下不再注明。他用了“也许”这样的字样,这说明他对神的正义(在神的世界中的正义)并不是明确的肯定。考虑到古希腊是有神论的时代,不敬神是个严重的罪名,苏格拉底就是因为渎神和败坏青年而被处死,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含混其词已经是很大胆了。而亚氏在《尼伦》一书的另外两处对神的说明则更进一步指出正义不是属于神的。一处是在紧接着的第五卷第九章,也就是在讨论政治正义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正义之后,亚氏明确提到“正义是属人的”。他写道:
正义存在于能够享得自身即善的事物,并且能享得的多一点或少一点的人们之间。有些存在者,比如神,不能再享得更多的这类善。还有些存在者,即那些不可救治的恶的存在者,哪怕是享得最少的一点这类善都于它们有害。另一些则在一定限度内可以分享这类善。所以正义是属人的。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59页,1137b25—30。D.Ross的脚注本也注意到这里的论述与《尼伦》第十卷第八章的联系,并称之为“奇怪的”:“essentiallysomethinghuman:thispavesthewayforthesurprising claiminX.8thatjusticeisnotaqualitythegodspossessoract from”。参见Aristotle,NicomacheanEthics,trans.D.Ros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p.235.
这里亚氏明确指出,正义不是属于神的,神享有最充分的善,若能增加就不是最充分的了;“那些不可救治的恶的存在者”即其他低等动物,则与之相反。②有学者认为,这里叙述的人也含有神似的人之意,其他低等动物也包含兽似的人,多数的或一般的人处于神和兽之间,或处于兽似的人与神似的人之间。这种看法并不妥当,因为亚里士多德这里的结论是“正义是属人的”,他并没有明确排除神似的人和兽似的人。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59页脚注③和④。而在另一处,在《尼伦》的最后一卷的论述可以确认“正义不是属于神的”这种看法。在那里谈论到沉思与神的关系时,亚氏说:只有沉思活动才是神应有的活动,不能把正义归于神。“我们可以把哪种行为归于它们呢?正义的行为?但是,说众神也互相交易、还钱等等岂不荒唐?”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309页,1178b10。
这样在对正义与神的关系的讨论中,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有着正义与神无关、正义不属于神的这样一个在当时极为大胆的结论。除了正义不属于神之外,正义也同样不属于其他低等动物。根据亚氏,正义既不属于神,也不属于其他低等动物,而是属于人。
(二)政治正义只存在于公民之间
现在的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正义是属人的”这一论断中的“正义”与他所说的自然正义是什么关系。《尼伦》第五卷通篇是对正义这一德性的讨论,其中对自然正义的探讨出现在比较靠后的第七章。他在讨论了作为合法的普遍正义与作为公平的特殊正义之后,突然转向了对政治正义的探讨。④关于前两种正义和政治正义的关系,学者有不同看法。我这里把普遍正义和特殊正义理解为政治正义的两种类型,而把政治正义划分为自然正义和约定正义是根据另一种标准的划分。在他看来,自然正义和约定正义一起就属于政治正义(即城邦正义)。⑤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49页,1134b19。“约定”,希腊文为“nomos”,该词在希腊文中有多重含义;汉语翻译起来比较困难,汉语学界有“法律”、“律法”、“礼法”、“习俗”等诸多翻译。本文根据情况,译为“约定”、“法律”或“人为”,据此所发生的译文改动,下文不再说明。既然自然正义属于政治正义,所以在讨论“正义是属人的”这一看法与自然正义的关系之前,首先我们要谈的是“正义是属人的”这种看法与政治正义的关系。关于政治正义,亚氏在谈论自然正义前面的一章来谈这个问题。他在第六章的中间和结尾部分两次谈到政治正义的界定:
政治的正义是共享追求自足地共同生活这一观念的、自由且在通过比例达到平等或在数量上平等的人们之间的正义。在不自足的以及在比例上、数量上都不平等的人们之间,不存在政治的正义,而只存在着某种类比意义上的正义。正义只存在于其相互关系可由法律来调节的人们之间。⑥[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47—148页,1134a26—30。译文有改动。
而在同一章的结尾处:
因此,各公民的正义与不正义并不是在这些关系中所表明的;因为它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根据法律的,是在自然地服从法律的人们之间,还有,这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拥有平等的机会去统治与被统治的人们之间。所以,正义在丈夫同妻子的关系中比在父亲同子女或主人同奴隶的关系中表现得充分些。这种正义是家室的正义。不过这种正义也还是不同于政治的正义。⑦同上,第148—149页,1134b13—18。译文有改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正义并不是属于所有人的之间的,而是指那种在自由和相对平等的公民中发展出来的正义,这些公民个体借助法律统治彼此。既然政治正义如此,那么作为政治正义之一的自然正义也应是如此,自然正义也只对一个城邦中的公民有效力。亚氏自己不惜笔墨反复强调,政治正义不是对所有人有效力,而仅仅对城邦中的一部分人有效力,这部分人是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这样,亚氏在《尼伦》第五卷第九章提到的“正义是属于人的”比这里所说的“政治正义是仅仅属于公民的”这一表述要广。也就是说,政治正义只是正义的一种,政治正义是严格意义上的,而不是同家室正义那样类比意义上的正义。
(三)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有效力
上面已经论述,自然正义作为政治正义的一部分,只是对公民才有效力,不同于那些类比意义上的正义即家室的正义(主人与奴隶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父母与未成年的子女之间),更不用说用于神和其他低等动物了。现在我们转向亚里士多德对自然正义的界定,看亚氏在自然正义只能用于公民这一观点上有没有添加。
在《尼伦》第五卷第七章,亚里士多德说:“自然的正义在任何地方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认或不承认。”①同上,第149页,1134b19—20。译文有改动。这句话中的“pantachou”一词,由“pan”和“tachou”两部分组成,前一个词根指的是“全部、所有、任何”,如我们所说的潘多拉指的是诸神的礼物的意思,后一个词根指的是“地方”,合起来意思就是“任何地方”或“所有地方”;该词各英文译本都译为“everywhere”,汉语译本则有几种不同的译法,其中邓安庆译本译为“到处”最切合原意。《尼伦》1134b19—20对自然正义的这一界定,汉语版中苗力田译本翻译为“自然的公正对全体的公民都有同一的效力,不管人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廖申白译本翻译为“自然的公正对任何人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认或不承认”;邓安庆译本则译为“自然的公正到处都有同样的效力,不与人们的意见相关”。正是这些学者翻译的差异激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英文W.D.Ross译本为“natural,thatwhicheverywherehasthesameforceanddoesnotexistbypeople'sthinkingthisor that”;RogerCrisp译本为“Whatisnaturaliswhathasthesame forceeverywhereanddoesnotdependonpeople'sthinking”;Robert C.Bartlett和SusanD.Collins的译本为“Thenatural[partofpoliticaljustice]isthatwhichhasthesamecapacityeverywhereandis notdependentonbeingheldtoexistornot”;JohnGillies译本为“Thenatural,isthatwhichhaseverywherethesameforceandauthority”。参见Aristotle,NicomacheanEthics,trans.D.Ross,1980.值得注意的是,亚氏在对自然正义进行界定时,不是说自然正义对任何人都有效,而是只说在任何地方都有效力。亚氏不说自然正义对任何人都有效力,因为他在论述自然正义的前一章已经明确地论证了政治正义不是对任何人都有效力。而他强调自然正义在任何地方都有效力,当然不是对地方上的物品有效力,而是说人们在各自的土地上构建城邦等政治组织,自然正义的这种普遍的效力是通过每个地方的城邦实现的。在每个地方的城邦之中的自由与平等的公民之间才能有政治正义,也才能有自然正义。②关于超出城邦有没有自然正义这一问题,施特劳斯的看法是在城邦之外或先于城邦也是有自然正义的。自然正义在城邦之内,只是说自然正义最充分发达的形式是从同胞公民中间得来的。“只有在同胞公民中间,作为权利或正义主题的此种关系才能达到它们最大的密度和它们最充分的发展。”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60页。此外,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提到一种正义,这种就不限于某一个城邦或政治社会之内,城邦与城邦之间的人之间也应当有,至于这种正义与本文要谈的自然正义的关系,值得探讨,但不是本文探讨的主题。在那里,亚氏说:“然而,很多人在涉及政治时似乎就相信奴隶主对付奴隶的专制为政治家的真本领;人们对于他人(异族异邦的人),往往采取在自己人之间认为不义或不宜的手段而不以为可耻。他们在自己人之间,处理内部事情的权威总要求以正义为依据;逢到自己以外的人们,他们就不谈正义了。这样的行径是荒谬的”。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7页,1324b31—36。另外,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与公民的区分是众所周知的。
此外,关于自然正义与变化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有些人认为所有的正义都是约定的,因为凡是自然的都是不可变更的和始终有效的。”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49页,1134b24。而在他那里,自然正义和约定正义都是可变动的。自然正义虽然是自然的,也是可以变动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正义都是可变的,尽管其中有自然的正义。”④同上,第149页,1134b28。也就是说,在前人那里自然和变动是不能相容的东西,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却是可以相容的。①施特劳斯和亚科等学者都牢牢抓住自然正义是可变的这一论述,给予大多数相信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是永恒、不变的法则的人以痛击。传统的解释把亚氏的自然正义与斯多噶派、经院派以及唯理论者的自然法概念等同起来,所有这些派别都把自然法视为一种永恒、普遍和不变的正义标准。参见[美]列奥·施特劳斯著:《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第158—165页;[美]亚科:《自然正确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城邦与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第57页。
于是,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而且在属人的正义中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是对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
二、何种自然?
如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许多关键术语一样,“自然”一词也在许多意义上被使用。那么,他在谈论自然正义时的“自然”又是在哪种意义上使用?这一部分笔者打算先谈《尼伦》第五卷第七章中亚氏对自然正义的一些探讨,以及他对自然以及人的自然的一般看法,再进行比较。
(一)自然正义是对起初就有重要性的事物的规定
虽然亚里士多德多次提到正义就是德性品质,但要训练、教育人形成某种德性品质,城邦还需要用外在的法律规定去引导。自然正义首先就应被理解为外在的法律规定,其次才形成人内在的德性品质,虽然从逻辑重要性上德性品质这一界定对自然正义更为重要。现在的问题是,自然正义这种规定既然和约定正义同为政治正义,同样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有效力,那么这种自然正义是何种自然?这里笔者打算从美国学者亚科的分析入手。
关于自然正义在哪种意义上是自然,亚科是从与其相对的约定正义的区分来分析的。亚里士多德认为:“约定正义最初是这样定还是那样定并不重要,但一旦定下了,例如囚徒的赎金是一个姆那,献祭时是要献一只山羊而不是两只绵羊,就变得十分重要了。”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49页,1134b20—22。既然约定正义所定的事物起初这样定或那样定都是无关紧要的,那么,自然正义就是对起初就有重要性的东西的规定。
在这种解释中,亚科敏锐地指出了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自然正义是对起初就有重要性的东西的规定,但他却没有举出具体的事例去说明那些事物为什么起初具有重要性。③施特劳斯在《论自然法》一文中,对这种自然正义是什么给出了猜想。他认为这类自然正义的一种是低于约定正义(也即positivelaw)的正义,另一种则是高于约定正义的正义。参见[美]施特劳斯:《论自然法》,杨水兴译,《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3期;另一译本见[美]施特劳斯:《论自然法》,《柏拉图式政治哲学研究》,张缨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86—187页。不过,亚科认为,城邦是如何自然的,那么自然正义就是如何自然的。④亚科说:“亚里士多德所谓自然正确的自然性,在于自然正确所描述的那类判断,而不在于自然正确所包含的特殊标准。亚里士多德强调,政治正义自然存在;他是说,如果自由而相对平等的个体聚而形成共同体,在其中,他们借助法律来统治人且被人统治,那么,他们必‘在大多数情况下’依赖于亚里士多德称为自然正确的那类特殊判断。政治共同体如何是自然的,自然正确也就如何是自然的。自然正确跟城邦一样,多数时候,如果自由而相对平等的个体聚集起来,它就得到发展。”参见[美]亚科:《自然正确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城邦与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第64页。
亚科的另一篇论文对此有进一步论述⑤B.Yack,“CommunityandConflictinAristotle'sPolitical Philosophy”,TheReviewofPolitics,vol.47,No.1.,他把《政治学》的第一卷对城邦自然性的论述和《政治学》第三卷对政体的论述结合起来,给出了对城邦自然性的一个一贯的解释。在亚科看来,亚里士多德关于每一个城邦都是自然的这一论述是成立的⑥而关于城邦的自然性,ClaudiaBaracchi认为这指的不是这种或那种政体,也不是指一个城邦的独特的起源和构成,而仅仅指的是城邦自身。参见ClaudiaBaracchi,Aristotle'sEthicsas FirstPhilosoph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 159.,原因在于人的本性中的逻各斯⑦逻各斯,即“logos”,该词希腊文本身就有多重含义,可以指外部世界的规律,也可以指人的理性、语言机能,还可以指语言和理性对外部世界规律的表述。鉴于其复杂性,本文采用“逻各斯”这一译名。能力,人们借助这种人类不同于其他低等动物的独特能力,去论证“谁应当统治”的问题,最后形成每个地方的独特的政体。政体的形成是借助于人的本性中的逻各斯能力,而政体是一个城邦之所以为城邦的东西。总的看来,城邦的自然性就可以追溯到人的逻各斯能力。亚科认为,自然正义之所以是自然的,在于其所规定的事情是起初就有重要性的,而这种重要性归根结底依赖于人独特的逻各斯的能力。
我们没有看到亚科对自然正义与人的逻各斯能力的具体说明,但笔者想说的是,即使我们承认从人的本性解释伦理学的可行性①威廉姆斯(BernardWilliams)认为,伦理学不能诉诸人的自然。参见BernardWilliams,EthicsandtheLimitsofPhilosoph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5,p.52.,即亚科对城邦自然性的论证是成立的,即使我们也不去追问为什么城邦的自然性和自然正义的自然性存在这种一致性,这里还有一个问题:约定正义作为政治正义的一种,也是存在于城邦之中的,其制定自然也依赖于人类本性中的逻各斯能力,为何这种正义却叫做约定正义?对此,亚科的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至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自然正义指的是与约定正义相对的一种品质,其所规定的事物起初就有重要性。而对自然正义与人的逻各斯的能力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说明。
至于从人的本性去说明城邦的自然性、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两个著名命题,内德门(Cary J.Nederman)和余纪元等学者走得更远,他们两人不约而同地从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论述展开,进而论证上述两个著名命题。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专门谈到自然正义的自然性是何种自然。下面笔者将先简要叙述二者的研究成果,再分别试图应用于对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的解释,看是否解释得通。
(二)自然与人的自然
现在我们来谈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以及人的自然的看法,他对自然的看法主要出现在其《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中,这些已经有不少学者系统梳理过,②参见[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9、117、129、177页。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在亚氏那里,对自然的最权威的定义是:自然是每一个事物自身内部具有的运动和静止的本原③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3页,192b14;另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9页,1015a19。;但在他那里,运动和形式以及目的基本上是一回事。与此相对,自然还有一层较弱的含义,就是质料。
其次,是从自然出发去解读人的自然。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从亚氏对自然的看法去理解他对人的自然的看法。对此,学界一般的看法是,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人是自然事物,人的独特自然就在于人的逻各斯能力,同时亚氏继承了柏拉图的功能论证,认为人的逻各斯能力应该从潜能到现实地实现出来,这一过程要求人在城邦中过德性的生活。这种从潜能到现实的过程要求人在城邦中过德性的生活。④内德门和余纪元等众多学者都提到功能论证,参见内德门(CaryJ.Nederman):《政治动物之谜——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说中的自然与人为》,《城邦与自然:亚里士多德与现代性》,刘小枫编,柯常咏等译,第109—133页,尤其是第115—120页;[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29、95—97、103—111页;斯坦福百科,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aristotle-ethics/.
而在对自然与约定的关系上,内德门认为,亚氏牢牢抓住自然物自身内部包含自身变化的原因这一界定,指出人所特有的关于改变的自然原则就是人的自发选择(prohairesis)。正因为人选择,人的运动才可以回溯到人自身。自发选择是人的自然的规定性标志。人作为行为的始因是欲求和理智的统一。选择依据善的观念,这一观念又来自我们的道德品性。德性行为必须植根于稳定的品性。内德门正确地指出了,不能把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与人为的区分等同于自然与教育的区分。⑤余纪元虽然也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对自然与约定的理解上不同于前人,但同内德门的论述有差异。余纪元这样写道:“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对那种在phusis和nomos之间或在自然与培育之间截然二分观点的潜在批评,那种二分法在智者派中很流行,认为法律是无关任何内部自然物的纯粹发明”。参见[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第184页。那些对人而言自然(自发)的行为,是训练得到的道德品质的结果,行为的自然根源于人自身。这种行为是出于训练和习惯化养成的固定品质,人应当为之负责。
根据内德门,城邦的自然性就体现在城邦为人的稳定的道德品质提供训练和公共教育,城邦作为实现人的自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而自然存在。一方面,作为规定的自然正义之所以是自然的,是因为人根据自身的本性去制定这些规定,而约定正义则不是。这种解释同样说服力不够,不能说明自然正义所规定之物起初就具有重要性。另一方面,作为德性品质的正义是作为规定的自然正义内化的结果,其自然性与作为规定的自然正义相关。但如果作为规定的自然正义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那么另一个也难以得到充分的解释。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非所有的德性品质都是自然的。在《尼伦》第二卷一开头,亚里士多德就声称道德德性不是出于自然的,他说“我们所有的道德德性都不是由自然在我们身上造成的”。解决方案或许是,第二卷第一章讨论的道德德性不是在亚里士多德的已经创新的意义上使用的,或者是这里“道德德性”仅仅指的是习惯化的道德德性,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德性,如同学者博斯托克(DavidBostock)和余纪元所认为的那样。①斯托克(DavidBostock)将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论述区分了三个层次:自然德性、习惯化的德性以及严格意义上的德性。参见DavidBostock,Aristotle'sEthics,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0,p.86。余纪元在《德性之镜》一书中也持这种看法,这里我采用他们二人的区分。参见[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第258页。笔者在这里采用后一种解释。总之,内德门的解释应用于对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的解释时并不奏效。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无论是亚科的论证,还是内德门的论证,这两种论证实质上都是从人性出发对城邦自然性的论述,而且都在逻辑上无法一贯地解决自然正义是何种自然这一问题。这也就无法充分说明亚里士多德对自然正义规定的事物起初就具有重要性。
(三)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
亚里士多德在使用自然正义的“自然”一词时,并不是在他通常使用的事物运动的内在原理这一意义上使用的。那么,亚氏是在哪层意义上使用的呢?下面将结合在亚氏在《尼伦》第六卷的末章提出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这一概念进行分析。
在《尼伦》第六卷的末章,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人们都认为,各种道德德性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赋予的。正义、节制、勇敢,这些品质都是与生俱来的。”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89页,1144b4—6。亚氏是从自然德性与严格意义上的德性(virtueinthestrictsense,又译为completevirtue,“完全德性”)的区分来谈自然德性的。在亚氏看来,二者至少有两大不同:第一,自然德性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第二,自然德性是不完美的,需要发展变化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性。先看第一条: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德性,自然德性是生来就有的③此外,在同一段的靠后部分涉及到德性的统一性问题的讨论时,亚里士多德又提出自然德性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的另一种不同,这就是自然德性的各种德性之间是可分的,而严格意义上的德性则是不可分的。“他们说,德性可以相互分离。他们说,一个人不可能具有所有的德性,所以,他获得了某种德性,而没有获得另一种德性。说到自然的德性,这是可能的。但说到使一个人成为好人的那些德性,这就不可能。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明智的德性,他就有了所有的道德德性。”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90页,1144b34—1145a2。。
明智与聪明不相同,但两者非常相像。自然的德性与严格意义的德性的关系也是这样。人们都认为,各种道德德性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赋予的。正义、节制、勇敢,这些品质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同时,我们又希望以另一种方式弄清楚,在严格意义上的善或此类东西中是否有别的东西产生。因为,甚至儿童和野兽也生来就有某种品质,而如果没有努斯,它们就显然是有害的……然而如果自然的品质上加上了努斯,它们就使得行为完善,原来类似德性的品质也就成了严格意义的德性。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第189页,1144b2—14。
对于亚里士多德,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与节制、勇敢等品质一道是与生俱来的。此外,在《尼伦》中灵魂的状态被划分为三种:感情、能力和品质。德性既不是感情,也不是能力,而是一种品质。⑤同上,第43—45页,1105b20—1106a12。作为一种德性,自然德性是一种品质。自然德性作为德性既然是一种品质,又是与生俱来的品质,那么这种自然德性就与人所特有的言语能力不同。现在我们先把这个结论放在这里,接着讨论第二点:自然德性是不完美的。
自然德性是不完美的,需要发展变化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性。这一点也与作为完美德性的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不同。自然德性需要并且有可能发展到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亚里士多德是从宇宙目的论来论证这一需要的。人的自然目的是幸福,幸福在于理性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对于实现人的幸福来说,自然德性显然是不够的,这种自然德性需要经由习惯化的德性进而发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甚至儿童和野兽也生来就有某种品质(自然德性),而如果没有努斯,它们就显然是有害的。”即使儿童生而具有了这种自然德性,但是因为没有努斯,自然德性显然也是有害的。①而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也说过类似的话:“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悖德(不义)而又武装起来,势必引致世间莫大的祸害;人类恰正生而具备[他所特有的]武装[例如言语机能],这些装备本来应由人类的智虑和善德加以运用,可是,这也未尝不可被运用来逞其狂妄或济其罪恶。于是失德的人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下流而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9页,1253a32—37。此外,至于可能性方面,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简单说来,从自然德性发展到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的可能性,这一方面也在从城邦对人的教育和训练(习惯化)中来实现。现在,我们已经对照完全德性,论述了自然德性的两种性质:一是自然德性是与生俱来的品质;二是自然德性是不完美的,需要发展变化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性。而作为自然德性的那种正义,也是人生来具有的并且是不够完美的一种品质。
(四)自然正义与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
既然自然正义所规定的是一开始对人就具有重要性的正义品质,而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是人与生俱来的,不仅需要而且有可能经过习惯化德性发展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德性的一种品质,那么对比二者可以发现:第一,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而只有所持有的程度的不同,甚至奴隶也可以持有这种正义德性;②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第37—41页,1259b20—1260b7。而自然正义作为政治正义的一种,则只存在城邦中的自由和相对平等的公民之间;前者的范围比较宽广,而后者的范围则更狭窄。第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陈述过第五卷第七章所提的自然正义需要发展,但明确提到自然德性因其不完美和低级,需要发展到完全德性。笔者认为,正是这种与生俱来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是亚氏自然正义之所以为自然的原因。因为自然正义之所以是自然的,是因为自然正义所规定的事物本身就对人很重要,而正是人具有的自然德性品质使人能够感受到那些事物对人本身是重要的。③这里并不是说亚科提到的人区别于动物的逻各斯能力对于自然正义就不重要,而是说除了逻各斯能力之外还有自然德性这种东西也在起作用。在对自然正义的自然性的论述中,除逻各斯这种自然能力之外,自然德性这种品质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概念,而且可能更值得关注,因为自然正义和自然德性都是作为品质来理解的,两者的关系可能更为密切。我们可以设想,自然正义是在自然德性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样,在个体德性的形成过程中,在人的灵魂中至少有两种东西都在起作用:自然德性、自然能力(人的特有的逻各斯机能)。④也有学者如余纪元声称,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一种自然道德感。参见[美]余纪元:《德性之镜: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林航译,第179—180页。因为仅仅从逻各斯机能无法区分政治正义中的自然正义和约定正义,即无法指出自然正义所规定的事物如何起初就具有重要性,而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恰好可以说明这一问题。⑤亚科只提出自然能力在起作用,而没有提及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这是不够全面的。这样自然正义是何种自然的问题也就有了一种答案,也就是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是自然正义之所以自然的原因。这种重要性当然也要通过人的独特的逻各斯能力辨认出来。
三、结 论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对“谁之正义?何种自然?”的问题给出了一种解释。首先,在“谁之正义”方面,自然正义既不是神的,也不是低等动物的,而是属人的正义;而且在属人的正义中不是对所有人有效,而仅仅是在自由和平等的公民之间才有效力,也就是说自然正义是公民的正义。其次,在“何种自然”方面,本文用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来解释自然正义的自然性。这种与生俱来的作为自然德性的正义,恰好就是亚里士多德自然正义之所以为自然的原因。但是,亚氏的这种自然正义中所谓的自然与他的其他著作中的自然的关系,还有这种自然正义与后来自然法的关系等,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 任 之)
B502.233
A
1000-7660(2015)03-0076-07
高健康,河南太康人,(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对《物理学》8.6(259b1- 20)的一种解读
——“自由落体”教学中的物理学史辨
——《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一课的教学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