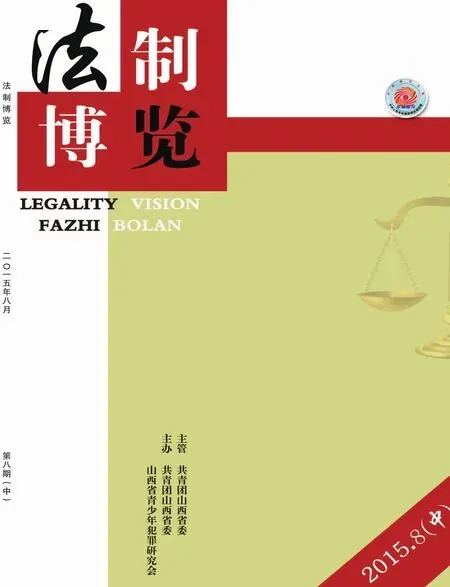清朝文字狱之史鉴
陈燕雯 陈文日
1.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上海 200042;
2.福建福清市人民检察院,福建 福清 350300
在中国历史上,清康乾盛世几可与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相媲美,疆土辽阔、军力强盛、民生安宁,可谓百废俱兴。但在康乾盛世的光辉之下,却暗藏着清王朝衰弱的引子——文化专制。在清初的这段百余年时间内,满人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双重压力之下,为了自己的家天下抑制了人性的觉醒和启蒙,在文化政策上提倡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的八股文、推崇程朱的“存天理灭人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甚至于大兴文字之狱并借修书之名而发大规模禁书运动。文字狱不仅使大清帝国国力日衰,在核心竞争力上落后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逐渐走出中世纪的西欧,而且这文化专制的毒瘤,深埋于国人心中,当时后世,沉渣时泛,遗毒甚深!
一、爱新觉罗氏的毒辣——清朝文字狱的特点
文字狱作为文化专制的表现之一在各个朝代都有所表现,与封建王权统治如影随形,阴魂不散,如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代的杨恽案、宋朝的苏轼乌台诗案等。但清朝文字狱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牵连之广、用刑之酷都是空前的,写下了中国文化专制主义最黑暗、最血腥的一幕:首先,从数量上看,清朝268年时间内竟有200 多起文字狱,数量比其他时期文字狱的总数还多,平均1年半1 起。乾隆期间尤甚,其在位近60年间竟有130 多起文字狱。其次,从牵连范围上看,文字狱的处罚范围也从一人受罪逐渐发展为后期动辄瓜蔓抄式的广泛株连,“往往为兴一案而关联七八省,株连数百人,从发案到最后结案又拖延数十年”。①如顺治时期的庄氏明史案中,十八个参订的人中,活着的17 个全部凌迟,死的也不肯放过,发冢斫棺,断头戮尸。凡是与《明史》有关的人,编撰、作序、刻板、印刷、卖书,读过该书甚至看到或说到过几句有关的话,统统全家拘捕,涉案人数达2000 多人。再次,刑罚严酷。对于异己分子,最简单的办法当然是从肉体上消灭,肉体灭失,思想也就无从产生。而清朝时期却不止于简单的肉体消灭,而是极尽其恫吓之能事,不让人死得痛快。触犯文禁的人如能得个全尸就已是万幸,对主犯多用凌迟、分尸等酷刑来折磨,甚至对已死之人也不放过。查嗣庭案中,主犯查嗣庭在行刑前病逝狱中,依然要将其戮尸。最后,文字狱持续时间长。清朝的文字狱从顺治16年的明史案开始直至清末章太炎等人的《苏报》案,持续时间近200年,其中文祸最烈的顺、康、雍、乾持续时间也达130年左右。如此长时间、持续不断的以文字罪人,可谓绝无仅有。
文字狱无疑是清朝统治者为稳固自己的统治,保住家业而在以汉人为主的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开展的清洗运动。爱新觉罗氏不仅将肉体的折服发挥至极致,而且对文人士大夫实施精神屈辱,他们首创了群众性批判和自我批判。后人不难从中看到“挂牌游行”、“大批判”的历史渊源。如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就与曾、张二主犯就“夷夏之防”“均田制”问题展开争辩,名为辩论自由实则要求他们自证其罪,逐条批驳他们自己对雍正进行过的指责,并将他们的供词及“忏悔录”刊成《大义觉迷录》,雍正亲自作序,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此外,又让曾、张二人穿戴整齐,骑着高头大马,分别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兵部尚书史贻直分别带领他们到江浙一带、陕西等地宣讲,由他们现身说法,自我批判同时颂扬圣主。在钱世明案中雍正还发明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批判。雍正深谙“士可杀不可辱”之道,他对主犯钱世明不杀不关,著作不禁不毁,而是由雍正“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悬其门,以昭鉴戒。复命在京大小臣工,由制科出身者,咸为歌诗以刺其恶”。因此不论是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还是翰林院编修、检讨、内阁中书,直至各部给事中、郎中、员外、主事,凡属科举出身的,几乎在京的所有高级文官都得表态,写诗讨伐,最后形成了385 首批判“诗”,并由钱世明出钱刊印了这本批判自己的《名教罪人》诗集。这些人中有部分本就是参奏弹劾之人或是幸灾乐祸之流而主动请缨,但更多的则是违心表态。而且表态诗写得不好的,轻则革职,重则入罪。侍读陈邦彦、陈邦直兄弟因作诗不称上意而被革职,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作诗“缪妄”而充军宁古塔。这种发动群众大批判的做法,既是对被批判者本人的极大侮辱,又通过强制文人士大夫表态,摧残他们的羞耻心、荣誉感。而雍正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靦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这种不杀而辱之的做法也算是清朝的一大创举。因为清代责罚奴仆,就有一种手段是让受罚者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亦称“掌嘴”。无论是曾静等人的现身说法,还是钱世明自刻《名教罪人》文集都有让文人自己掌嘴的味道,让喜欢摆弄文字的文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诗来奉承拍马就用诗歌来惩罚他;喜欢刻文集来自我标榜,就刻辱骂自己的集子。所以鲁迅说:“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遗迹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②他认为清朝的文化专制手段,实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朱元璋廷杖责辱更具有杀伤力。因为这些只是触及了皮肉,没有触及灵魂。
二、民族与阶级的双重对立——清朝大兴文字狱的原因
历代帝王好兴文字狱的理由无非有二:一来文字是思想的载体,古代中国讲求诛心、“原心论罪”,既然有不好的思想就应该处罚,而不必等到付诸行动。二来以文字入罪大则可以用其遏制思想、稳固政权,小则可以用来挟私报复,排除异己,而且帝王可以捕风捉影,信手拈来,随意上下其手,游刃而有余。美国汉学家史景迁称文字狱不过是“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算是说到点子上。以文字原心论罪,有以下几个方便之处:(1)可以从读音上做文章。如乾隆47年,卓长龄所作的《忆鸣诗集》之“忆鸣”二字被认为有“追忆前明”之意,而使卓家几遭灭门。(2)可以从字形上抓辫子。如查嗣庭案就是从“维民所止”中的“维”“止”二字上作文章,曲意为要砍雍正的头。(3)从词义上找茬。凡文字都有其语境,一旦将这些文字剥离其本身的语境,就可以随意解释、延伸,任意歪曲、附会,然后加于作者之上。如雍正八年,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就因诗中“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句中的“清”“明”被认为是指代清朝、明朝而遭厄运。
当然,清朝文字狱迭兴自有其特殊原因。(1)清王朝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缺乏自信。“武力镇压往往是自身虚弱和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拿不出比对方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③清以一个人口少,文化落后的满族统治人口占绝对优势,经济文化又相对发达的汉族,其内心是诚惶诚恐的,希望其统治能得到汉人的承认。在这场为获得承认而展开的斗争中,其积极的一面表现在清朝执政者主动向汉文化靠拢,学习汉文化,推崇儒教,尊孔子为“至圣先师”,提倡尊孔读经。而其消极一面则表现为急于被统治者从形式上认可满人,认可清朝王朝,对汉人的抵触反应过度。因此,清统治者入关后不久就要求汉人要着满服,发式要剃半月头,稍有反抗便颁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诏令,甚至引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的惨案。而对其入关的历史及清初尚苟延残喘的南明王朝其更是敏感。“一朝去清都”这样的诗词都能引起其警觉,让皇帝老儿大动干戈。这也是文字狱多发生在清朝前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而且多与明史有关,与“明”、“清”二字有关的原因所在。(2)清初政权尚未稳固,汉人的反抗加剧了文字狱的兴起。文化上的不认同、不合作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在改朝换代司空见惯的行为,被视为一种士大夫维护道统的责任担当。清初威权未立,而其又是异族入主中原,各种反抗力量此起彼伏,思想领域非议之声不绝,文人的反抗意识甚为强烈。如黄宗羲、顾炎武不仅参加过抗清战争,而且清朝打下江山后,他们也不愿为清廷服务,拒绝参加康熙征召的“博学鸿儒科”考试,顾炎武还数次拜谒明陵,视己为明朝子民。吕留良也同样拒绝“博学鸿儒科”的考试,后来索性削发为僧,著“华夷之分”之说,鼓吹反满。文人士大夫的这种气节自然让清统治者如鲠在喉,欲除之而后快。(3)满族奴隶制遗风。满人入关以前还是奴隶制,在满人之间原本就严格区分着主奴,“奴才”一词也是从清兵入关后才横行于神州,并将奴性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在这种“做稳了奴隶”与“求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鲁迅语),主奴间的严格界限,使得“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说:主子,您这袍角有些儿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烂,还是补一补好。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胡涂。”④因此,清朝文字狱中出现了数十起其实只能算是疯人疯语或者马屁拍在马腿上的案件,但清帝王对他们却丝毫不手软,轻则杖毙,重则凌迟。这种文字洁癖和几近疯狂的扑杀不能不说是奴隶制的遗风所致。
三、毁法抑道扼启蒙——文字狱的影响
清朝的文字狱,“寻章摘句,吹毛求疵;穿凿比附,诛意攻心;探头探脑,告密成风;疑神疑鬼,保官为上;过犹不及,文网日密;宁严勿弛,诛连日众”。⑤这刀光血影充分展现了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和人性中的阴暗凄凉,破坏了法治,损害了道统,还遏制了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发展乃至“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乾隆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⑥文字狱制造了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极大的破坏了法律的权威。
(一)滥用刑法
“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⑦从中可以看到,许多文字狱或没有主观恶性或属于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疯子根本不该入罪却照单全收,而且对案犯多处以极刑,即多按照十恶中的谋反及谋大逆来定罪处罚处理。根据《大清律例》“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姬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16 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15 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因此,清朝文字狱才会如此惨烈,杀声一片,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当然,历代君王都是集立法、行政、司法于一身者,法律亦不过是皇帝之意,圣意驾驭法律是常有之事。但为了打击文人,不仅法律没有权威,即使是帝王曾经开过的金口也不作数。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当众宣称“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并说“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甚至说,“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但现实却是稍有不慎就入罪。刑罚利剑只是帝王随意拿捏的工具,怎能不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二)广泛株连
正所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好文字之忌,则查办者为了摆脱干系,避免无辜受累,宁枉勿纵,刑罚宁重勿轻,株连范围宁宽勿窄。如庄氏《明史》案中,“一字之连,一词之及,无不就捕。每逮一日,则其家男女百口皆锒铛同缚,杭州狱中至两千余人”。⑧不但担心自己误撞文网,还会因为没有及时查处、告发他人,或因被他人株连而获罪。不但读书人担心文字狱,撑船的、开店的,会因为接待过一个“犯人”而遭受牵连,一字不识、老实务农的良民百姓还会因为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写过“不法诗文”而被满门抄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平民百姓,被炒家、杀头是家常便饭。
(三)破坏程序
在处理文字狱中,就其程序方面而言也多违当时的法律规定。按照《大清律例》,总督、巡抚是地方最高司法审级,刑部是中央审判机构,审核重大刑事案件,“三法司”和“九卿会审”则是中央的最高审级。但由于文字狱的敏感性,造成审理的官员不敢按照普通案件来审理,凡有相关案件最后都由皇帝亲自定罪量刑或定好调子。如乾隆41年严譄私拟奏折请立正宫案中,该案主犯严譄因在奏请立正宫时提到皇后纳氏进谏被处刑自杀之事触及了乾隆的痛处而遭罪。该案在交九卿会审前,乾隆就先断言严譄“妄谈宫中闱”、“诋毁朕躬”、“实为乱民之尤,罪大恶极”、“审理之日即当按律问拟处以极刑。”皇帝圣意,无人敢违,圣言既出,所谓的审判其实就是走过场,最后以“大逆”罪处死。
四、结语
述往事,思来者。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迄今已过百年,回首这百年我们依稀可见封建专制的遗毒及满人统治带给国人的奴性劣根,时不时就要在中华大地上复发。仅就文字狱来说,在国民党统治期间,各种政治势力在东方巨龙病泱泱的躯体上角力,文字之祸自是和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党禁、报禁、因言获罪甚至暗杀等史不绝书,可以编成一本足足20 万言的《现代文坛灾祸录》。解放后,我们自以为已经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历史使命,脱胎换骨走进了新时代。然思想自由的春天依然遥远,文字狱的“恶之花”依然娇艳诱人。反右斗争中知识遭到了清算,大批知识分子因言获罪,卷入了无情的“革命”漩涡。不是被批斗就是被逼着参与批斗,人人要过关,人人要表态,这何尝不是文字狱流毒的回潮泛滥。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浩劫,公然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大改造,批林批孔、批判臭老九、停学停课,古今中外文化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要革整个文化的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宪政的逐渐树立和法治的不断完善,大规模的以文字罪人已失去了社会土壤,但文字之祸依然阴魂不散,改头换面后不时重现人间。2006年重庆公务员秦中飞写了一条名为《沁园春·彭水》的短信针砭时弊却被指影射彭水县领导,被公安机关以“诽谤罪”逮捕关押,40 余人牵连其中(彭水诗案);2009年失地农民王帅网上发帖披露灵宝政府违规征地,后因“诽谤罪”被灵宝警方送进看守所关押8 天(灵宝帖案);2010年甘肃省图书馆职工王鹏因举报官员子女公务员录用作弊而被宁夏警方跨省抓捕(王鹏案)。这些案件无疑是文字狱的现代形态,有权势者动辄利用公权力的力量来压制不利于自己的思想与言论。对此我们当有边沁那样的警醒:“诽谤罪,一旦实行就会摧毁英国人的自由,政府将变为独裁主义”。⑨
[1]韦庆远.重读清代文字狱挡[J].读书,1979(3):93.
[2]鲁迅.买<小学大全>记[A].鲁迅.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63.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21-133.
[3][英]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M].韩光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89.
[4]鲁迅.隔膜[A].鲁迅.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9.
[5]朱维铮.走出中世纪[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45.
[6]原璞.古人谈文字狱[J].学术研究,1979(4):51.
[7]鲁迅.隔膜[A].鲁迅.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48.
[8]胡奇光.中国文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3.
[9][英]菲利普·斯科菲尔德.邪恶利益与民主:边沁的功用主义政治宪法思想[M].翟小波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