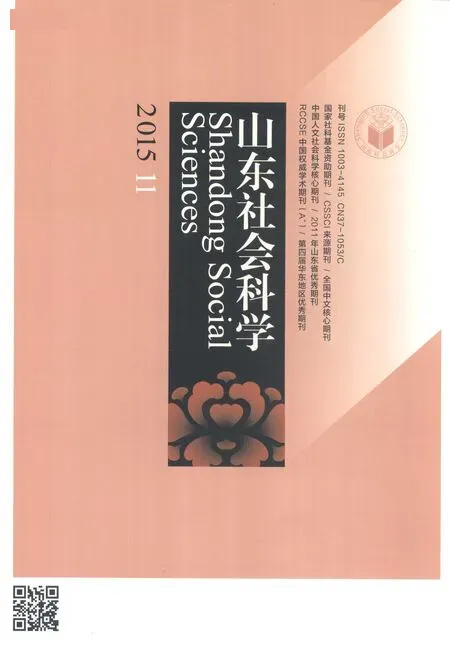中国人自杀行为的传统之根
——典籍中的自杀事件及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分析
李建军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550001)
中国人自杀行为的传统之根
——典籍中的自杀事件及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分析
李建军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550001)
研究自杀的原因是防止自杀行为发生的重要前提。除生理、心理、社会等因素外,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也极为重要。儒、道、墨、法诸家的死亡观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对中国人的自杀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运用文本细读法对传统典籍中的自杀事件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进行了详细梳理和深入剖析,对当下在精神和价值观层面确立防范自杀的规范有一定启示作用。
自杀;传统价值观;历史文化;中国人
研究自杀的原因是防止自杀行为发生的重要前提,自杀行为的多方面因素要求研究者运用多元化、跨学科的综合思维对其展开深入研究。美国自杀学协会主席希尼亚·帕佛指出:“防止自杀最好的办法不是注意自杀本身,而是应当更广泛地注意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自杀的发生”①转引自宋专茂等:《有自杀倾向大学生的人格特征透视》,《青年研究》2012年第10期。。杜尔凯姆称,“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支配着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即外部环境及带有某些共性的社会思潮和道德标准”②[法]爱米尔·杜尔凯姆:《自杀论》,钟旭辉、马磊、林庆新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这一观点至今仍为社会学家普遍接受。
一、传统文化深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
中国人的自杀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从古至今,自杀行为伴随着中华民族进步的历历屐痕。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人,虽然经历了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仍消除不了其内在的文化遗传基因。在社会化过程中,他们自幼耳濡目染,通过家庭、社会和学校等各种渠道,从前辈那里接受了思维习惯、情感模式和行为规范,经过潜移默化的内化过程积淀于潜意识的底层,形成荣格所谓的“集体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他们的行为方式。
具有悠久历史并对世界文明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以其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话语体系和民风民俗著称于世,即便在自杀方面亦显现出其特殊的观念与方式,并将其附着、渗透在文化载体之中代代相传。中国人对自杀所特有的道德评价、源自人际冲突特别是家庭人际冲突的自杀诱因,根植于中国人所独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模式、社会交往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之中。追寻民族文化之本、学会认识自身,深入分析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对在宏观层面和精神观念层面制定预防、控制自杀行为的规范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自杀类型“中国版”:中国历史典籍中的自杀事件
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自杀的态度上与根植于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文化迥然不同,西方文明对自杀持激烈的非难态度,而中国文化对自杀持同情和宽容态度,甚至是鼓励和提倡如杜尔凯姆自杀分类中的“利他型”(altruisticsuicide)、“失范型”或“殉国型”(anom iesuicide)自杀。中国传统价值观对“利他型”、“殉国型”自杀赋予了崇高的道德评价。
(一)自杀主体
1.氏族领袖自杀。中国历史上的自杀事件可谓史不绝书。中华民族载入史册的第一位自杀者据说是远古氏族领袖共公氏(《通鉴外纪》),他“怒而触不周之山”致天倾地斜。①张朝阳:《人类自杀史》,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昔者共工与顓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天文训》)。
2.国君及贵族自杀。《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史籍中有关自杀的记载俯拾即是,公元前1世纪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纪传体通史,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同时也被称为“中国第一部自杀病学的百科全书”。②何兆雄:《自杀病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春秋》所记载的自杀的君王有帝辛(商纣王)鹿台自焚殉社稷(前1066年)、晋平公(前550年)、陈哀公(前534);自杀的贵族有伯夷、叔齐、卫太子余、里克、庆父、申生等;自杀的士大夫有伍员、白公胜、鲁仲连、傅瑕、子玉等。《春秋》还记载秦国两代国君死后,自杀从死者达66—177人之众。《国语》记载的自杀的国君有吴王夫差(前473年)、秦二世胡亥(前207年);贵族有吕不韦(前235年)、项燕(前223年)。
3.大臣自杀。《左传》中,不少历史人物以自杀了结生命。直接描写自杀的即有30余处。自杀“尽忠”的大臣有荀息、董安于,申蒯与仆从因国君被杀,纷纷自杀尽忠。自杀“死节”的有子藏、晋太子申生、弃疾、“烈女”宋伯姬。“绝望”自杀的有莫敷、子玉、楚戊王、吴王夫差、伍子胥、子干、子午、夷姜、陈哀公、里克、成王、太子痤、郜宛、崔杼夫妇、庆父、公孙黑、白公等等。《国语》记载,自杀的大臣有文种(前494年)、屈原(前278年)、白起(前257年);侠客有豫让(约前425年)、聂政(前397年)、荆轲(前227年)。春秋、战国时期自杀身亡的著名历史人物见于诸子典籍中的还有很多,诸如韩非(前233年)、伍子胥(前484)、要离(前5世纪)、粥拳(前675年)、白公胜(前479年)、庞涓(前341年)、樊淤期(前3世纪)、田光(前227年)、项燕(前223年)、巴蔓子等等;汉代自杀的皇后有汉武帝的卫皇后(前91年)、汉成帝皇后赵飞燕(前1年)。《史记》记载,最早为殷末时期抱石沉于河的申徒狄,最迟为汉成帝时御史大夫尹忠因黄河决堤而引咎自杀(前29年)。汉武帝时期,大臣“死节”已经形成风气。
4.百姓自杀。自杀者中更多的是上不了正史的庶民百姓。在《史记》中,司马迁详细描绘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人生结局并阐述了他独特而深邃的死亡观。司马迁义正辞严地弘扬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命价值观,又继承了庄子“贵生”“重生”的自然主义的人生哲学,他对“死节”“死仁”“死义”“死国”的死亡观进行了新的思考和阐释。《史记》所记载的自杀个案除重复之外共有102处,自杀可计数者623人。
5.女性自杀。在古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低下,青史留名的女性可谓凤毛麟角。但自杀殉节的“烈女”却在封建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对宋、元、明正史中的《列女传》自杀女性所做的统计显示,宋代17人,元代116人,明代264人。③陈锋、刘经华:《浙江病态社会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页。明代以后“烈女”数量剧增,自杀者“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明史》卷三零一,《列女传》)。清代“烈女”数量更是更仆难数。有人对雍正时期修纂的山东、广东、浙江三省通志的《列女传》作了分析,三省被列传的自杀“烈女”为416人,其中已婚者397人,自杀者绝大多数为15—30岁的已婚丧夫者。其中“殉节”267人,“夺志”75人,受辱已证清白22人,抗婚14人,其他38人。自杀的主要方式为自缢(244人),绝食(72人),投水(13人),服毒(23人),自刎(17人),投井(13人),自焚(7人)。④刘正刚、唐伟华:《明清鲁浙粤女性自杀探讨》,《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5期。在浩如烟海的地方志中,“烈女”比比皆是。仅乾隆《贵州通志》就记载有宋至清初贵州14府11州31县600余名“贞节列女”。⑤王志跃:《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期。《贵州通志·列女传》对“烈女”立传近200人。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也饱含同情地歌颂了这类自杀的女性,比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桃花扇》中的李香君、《金瓶梅》中的宋惠莲、《红楼梦》中的金钏和尤二姐等。
(二)自杀手段
《春秋》记载的自杀手段有自焚、绝食、自刎、自缢、殉葬。孔子把用剑自刎的称“死”,上吊自杀的称“缢”,投水自杀的称“投东海”,绝食自杀的称“不食周粟”,与国君同死的称“人殉”。孔子在《春秋》中讳言国君逼人自杀,只称“杀”或“某人死”。《史记》记载的自杀手段有如下几种:服毒——“饮鸩”;切刺——“自刎”“自刭”;溺水——“投江”;自缢——“自经”;撞击——“触树”“侵园堧”;自焚——“自燔於火”;吞金——“酎金”;跳车——“投车”等。
最经典的自杀记载除诸如商纣自焚亡朝、屈原怀石自沉汨罗江、项羽兵败垓下而自刎乌江、“田横五百士”血洒孤岛之外,还有一些人因为自杀而名留青史。在此仅择其特例,如秦朝名将蒙恬遭奸佞诬陷,饮鸩自杀(前210年);战国末年韩非革新变法,壮志未酬,服毒自尽(前280年);战国魏将庞涓,兵败马陵道挥剑自刎(前341年);“飞将军”李广失道误战,仰天长啸,慨然自刎(前119年);西汉淮南王刘安,屡遭谗言,谋反事败,自刎而亡(前122年);唐代诗人卢照邻,在师父孙思邈去世后,投颍江自尽(680年);南宋大臣卢秀夫国破家亡之际,背负幼帝投海殉国(1279年);南宋诗人、政治家谢枋得至死不降为元臣,绝食而死,其妻李氏与两个女儿及两婢女亦自尽(1289年);明末宦官魏忠贤专权擅政无恶不作,终获罪自缢(1627年);明朝亡国之君崇祯皇帝,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自缢煤山(1644年);明末大臣倪元璐,严词拒降,自缢暴尸(1644年);明末祁彪佳,清军陷城后,投浅池殉节(1645年);清初大顺军首领李来亨坚持抗清20载,兵败举寨自焚(1664年);秦淮名姝柳如是刚烈不阿,明亡之际投入荷池,身殉未遂,终投缳自尽(1664年);抗英名将裕谦,镇海城破,投泮池殉城(1841年);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北洋海军樯橹灰飞湮灭之际慨然服毒殉国(1895年);清末爱国志士陈天华,为唤醒国民,愤然投身日本大森海湾(1905年),等等。
(三)自杀原因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自杀案例,按自杀的原因可分为:君主在王朝更迭后(如政变)的自杀;发动政变失败后被迫自杀;兵败穷途而自杀;功高震主,被迫自杀;以死言志或用死证明自己的清白;畏罪自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拒虏囚之辱等等。“烈女”殉节一般有如下三种情形:一是殉夫,即丈夫死,该女自杀殉夫;二是为保全名节、不辱于贼寇而自杀殉节,如思南府李承眷长女、三女、四女、媳周氏、表侄女田氏,因“贼兵追急,恐受污辱,五女同坠崖死”①鄂尔泰等:《贵州通志·列女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第133页。;三是为拒强暴或强娶而自杀。
三、自杀背后的死亡观:儒、道、墨、法
在古代中国,随着先秦以后道德体系的建构和日臻完善,对生与死的理性思考日臻成熟,形成了“灵魂不死,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在此基础上衍生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佛家等的生死观,形成了庞杂而系统的生死学说,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恒久的影响。中国人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生前还是身后,都有了周全的理由从容应对一切,这对自杀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死亡观
1.孔子倡导“杀身成仁”
孔子(前551—前479年)代表的儒家把生与死都视为生命发展的必然过程,体现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精神。生则重生,死者安死,唯此方可为仁为义、克己复礼,修身俟死,甚至要求“志士仁人,勿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儒家的忠仁孝悌等人际伦理关系组成的文化价值系统,把所有的生死存亡现象统统归于事先规定或支配之列,任何个体成员都必须赖之以生、归之以死。
一是忠孝与自杀。事亲行孝乃做人之根本。为了事亲行孝,就必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父母全而生之,己当全而归之,故不敢毁伤”(《孝经·开宗明义章》)。“君子无不敬也。身为大身也着,亲之枝也,敢不敬欤?不能其身,是伤其亲;伤其亲是伤其体。伤其体,枝从而亡”(《礼记·哀公问》)。个人的行为要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才能“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中国人把“有辱先人”“愧对列祖列宗”视为奇耻大辱,而“无颜见江东父老”则只有死路一条。儒家把父母放到天、地、君王之后的重要的位置,父母的存在是制止子女自杀行为的重要因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如南宋民族英雄谢枋得身陷囹圄,不屈不挠,在得知自己93岁的老母已寿终正寝的消息后,即慨然自戕。遗书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岁之母在堂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终于正寝,某自今无意人间事矣!”(《上程雪楼御史书》)。
孔子赞美追求“仁”的自杀,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其被其誉为“贤人”,在《论语》中有四个地方赞颂他们,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求仁而得仁的崇高的德行。比干为了劝谏暴虐无道的纣王,愤而剖腹挖心,也被孔子誉为求仁的最高境界。孔子鼓励为了追求“仁”的目标,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这种思想对中国人影响至深至远,“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自赞铭》)。以致后世就有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人生信条。
儒家倡导的“修身以俟死”(《礼记·射义》)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为了尽忠尽孝,一方面,要无可奈何、逆来顺受地实践着“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戒律;另一方面,却又必须笃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这两种看起来是二律悖反的“道德两难”的行为和道德规范,实质上是对个体与群体(国家)矛盾关系的一种平衡或调节。
二是“三不朽”与自杀。儒家提倡以创造不朽抵抗死亡。“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后汉苟爽解释“不朽”为:“其身殁矣,其道犹存,故谓之不朽”(《中论·夭寿第十四》)。《左传》中多次提到的“死而不朽”“死且不朽”“死又何求”,《论语》中所说的“死而无悔”“死而后已”,《孝经》中所说的“死生之义”,都是对“不朽”的诠释。“三不朽”中,第一等“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超越死亡,被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在于生命之上,当道德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取生命以获得至高无上的道德“仁义”之成就。“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二等“立功”,像舜一样,“创业垂统”,“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孟子·离娄》)。第三等“立言”,留下精神财富,亦堪称不朽。把人的生命分为生理的生命和道德的生命,并认为后者在价值取向上必然高于前者,因此,为了道德生命的凸显和不朽,人们应该勇于捐弃在感性上难以割舍的生理生命。要求人们在别无选择的死亡面前,去刻意追求“成仁”“取义”,求得“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
2.孟子提倡“舍生取义”
孟子(前372—前289年),他把自杀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道殉身”,但天下有道的时候以道殉身是不必要的;二是“以身殉道”,天下无道时要以身殉道,这是必要的自杀,因为“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因为“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不所辟也”(《孟子·告子上篇》),还有比生命更重要的追求,所以不能苟且偷生;三是“以道殉人”,这不值得提倡。“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自杀者中,有的是有罪之人,孟子鼓励有罪者知耻自杀,“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离娄》)。
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死亡思想具有积极入世和自觉殉道的特征,倡导生时要奋发有为,明君当政,要有为政以德、兼济天下的宽阔胸襟;邪佞当道,敢于不畏权势、弘扬正义;面对死亡时,成仁取义胜于生命。
(二)道家的“生死齐一”死亡观
道家的生死观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这种生死观源于但又超越于世界万物——有情与无情之物,最终归于“道”。道家认为,天地之间一切有情无情之物皆由道所生,“有情无情,禀道而生”(《太上大道玉清经》卷二慈悲方便品第六),“天地、人物、仙灵、鬼道、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吴筠《玄纲论》)。当然,道并非直接化生出万物,通常是经过“道——元炁——阴阳——人”的途径来实现的。道经云:“道无所不能化,故元气守道,乃行其气,乃生天地,无柱而立,万物无动类而生”。①王明编:《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页。
道家倡导“生死齐一”的观念,把人生的终极价值定位于追求“永生”。一方面,道家认为,人的生命是最为宝贵的。在其看来,人是由“道”所派生的,而非神灵创造的,是大道自然运化的结果,甚至神灵也是由“道”所生。老子认为:“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第三十三章)。《太平经》倡导“重生”“贵生”,认为天地之间“人命最重”、“寿为最善”、乐生恶死、贪生怕死是人的本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二十五章),将“人”放在了与“道、天、地”同等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求人们从“哀死”“痛死”“惧死”的巨大阴影中超脱出来,立于宇宙大化、世界根本之“道”的基点来反观人类之生死,从而获得对生与死处之泰然的豁然开朗,消解人们在情感上对死亡的恐惧与抗拒。庄子云:“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道家的核心生命观是隐世修身,强调的是一种超然物外的人生智慧。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确定了道家见素抱朴、修身养性的自然主义人性基础,以柔克刚、知足不争等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
庄子还认为死亡是最自由最惬意的事,“夫欲免于形者,莫如弃世。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正平则与彼更生,更生则几矣”(《庄子·达生》)。他针对儒家“舍生取义”的自杀观尖锐地指出:“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庄子·骈拇》)庄子将“名利”“仁义”“货财”等均排斥在生命意义之外而超然无我。庄子还指出,“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死生存亡之一体”、“有无死生之一守”。①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9页。生就是死,死就是生,生死齐一。
庄子的生死观给后人印象至深的是庄子死妻而鼓盆而歌的故事。这是庄子超然生死观的具体体现,同样也体现了道家生死辩证的哲理。经过庄子一番阐释,消解了对死亡的恐惧。庄子还借助“骷髅见梦”的寓言,以“死”观“生”,以死去的骷髅来洞察“生”之状态(《庄子·至乐》)。这与儒家之以“生”观“死”的根本区别在于,这一新的视角置之“死”而观“生”,既打破了“未知生,焉知死”的不可知论,也更清醒地认识到生的艰辛、死的价值。这一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中也有阐释:出生入死。这里的“出生入死”并非冒生命危险之意,而是说人有生必有死,相辅相成,相生相死,相得益彰。这不仅仅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不以生喜,不以死痛,生死有命,道法自然。
(三)墨家的“慷慨赴死”死亡观
墨子(前468—前376年),主张“兼爱、非攻、交利”。墨家并不反对自杀,甚至鼓励忠勇的自杀行为。墨子有一弟子,其弟名缓,学习儒学。一家之内儒墨争论达十年之久,最终其弟理屈辞尽被迫自杀(《墨子·后语》)。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据《史记》载:“儒以文犯法,侠以武犯禁”。墨家的成员都自称为“墨者”,其首领被称为“钜子”或“巨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儿子杀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墨家一巨子孟胜守阳城落败自杀,从其自杀的墨者达183人(《吕氏春秋·尚德》)。
墨子盛赞自杀或被杀殉节的比干、孟贲、西施等人,“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墨子·亲士》)。墨家的死亡观还集中在《墨子》中的《明鬼》《节葬》等篇中。
晚清学者陈澧认为:“墨子之学,以死为能,战国时俟烈之风,盖出于此”(《东塾读书记》)。据《史记》载,吴王阖闾欲刺杀出逃在外的吴公子庆忌,伍子胥推荐了要离。后来,要离使出“苦肉计”,杀妻残身,假意投靠庆忌。庆忌身材高大魁梧,力大无比。要离运用智谋,最终刺杀了庆忌。庆忌临死前叹服要离的忠勇执着,交待手下赦免他,但要离却执意自杀身亡,成就了其忠义美名。公元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晋人豫让用墨漆涂身,吞炭使哑,暗伏桥下,谋刺赵襄子未遂,为襄子所捕。临死时,求得赵襄子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伏剑自杀(《史记·刺客列传》)。
墨家慷慨赴死的思想影响了许多先秦时的游侠,墨家思想也成为中国传统游侠产生的滥觞。
(四)法家的“冷酷生死”死亡观
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家的“生死齐一”,墨家“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都更多地从道德层面思考生死,以道德为标准来衡量生死的价值和意义。而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法治”而闻名。如先秦法家著名的代表人物商鞅认为,“任力不任德”“贵法不贵义”(《商君书·画策》)。韩非子指出:“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治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哉,境内不任数,用人不为非也,一国可为治者用善而言寡,古不任德而务法”(《韩非子·定法》)。法家重法治轻德治,在否定了“德育教化”和“以德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理性的生死观,即“法定生死”,就是人之生死的选择必须依据法而行。如此,法家便剔除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和墨家“死不旋踵”的道德内涵,人们的生死被纳入到法律的规定范围内,自杀行为也是如此,官员自杀行为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官员只有在触犯相关法律的情况下才能自杀。
但是,“法定生死”与现代法治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法家生死观显然带有极其浓重的封建政治色彩,其法理思想本质上也是为帝王的独裁统治服务的,所以其死亡观与其说是一种对死亡理性的判断,毋宁说是假借法之名义,掩盖其对待生命的冷酷无情。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辅佐秦孝公“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贾谊《过秦论》),醉心于“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的所谓伟业,全然不顾自己最终被五马分尸的悲惨结局。
儒、道、墨诸家的死亡观都具有价值观的意义,尽管表述各异,都对死亡持一种自然、达观的态度,都从死亡这一角度反映了他们各自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旨趣,对后世中国人的生死观、自杀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比较儒、墨、道诸家的死亡观,儒家从死亡中见“仁”见“礼”;墨家从死亡中见“勇”见“利”;道家从死亡中得“道”成“仙”。儒家的死,要死得有礼、死得大义凛然,死得其所,其死亦安;墨家的死,要死得有勇,死要从俭;道家的死,要死得自然,死得飘逸。儒家死而不休,不朽的是道德、是精神;墨家死而不死,不死的是“死不旋踵”豪气和“兼爱”的情怀;道家“死而不亡”,不亡的是群体的生生不息,永恒的是宇宙大化,死是自然之气散,而大道永存。儒家敬鬼神而远之;墨家敬鬼神以致福,借鬼神行赏罚;道家无鬼神,鬼神即自然。总之,儒家的死亡观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死亡观;墨家的死亡观是功利主义的死亡观;道家的死亡观是死亡的形而上学,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意义。②朱哲:《儒、墨、道死亡观比较》,《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1期。
(责任编辑:陆影)
C912.6
A
1003-4145[2015]11-0092-05
2015-08-12
李建军(1963—),男,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省社会学会会长。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自杀行为的社会文化研究”(项目编号:07BSH057)、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项目“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研究”(立项号:黔省专O8-6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