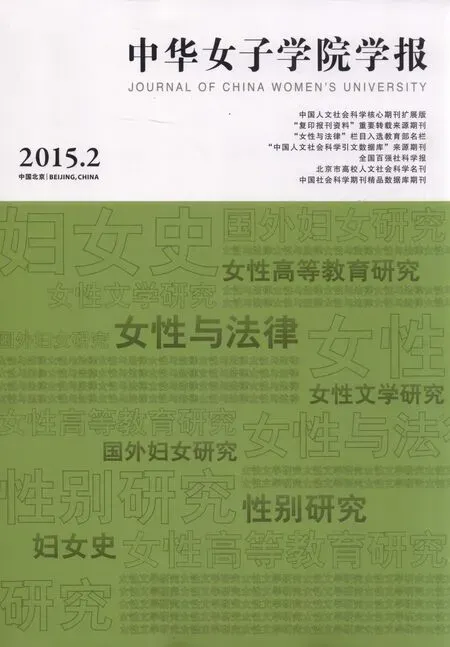张爱玲“非启蒙文学”的几点认识
刘锋杰 潘莉
张爱玲“非启蒙文学”的几点认识
刘锋杰 潘莉
主持人语: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女性主义作家。能在她的身份前加上“女性主义”,是她具有自觉的女性意识,而非身为女性即能如此称谓。虽然关于她的研究在大陆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可转眼就到了“人人争说张爱玲”的状态。有人说这是胡捧乱吹。可她既无家族的裙带,不是什么“二代”;也无子弟的孝敬,没有流派的起哄;更无组织的关怀,站不进现代文学馆前那块绿茵茵的文学草地。究其原因,是读者捧红了张爱玲,说明她的作品给力,吸引人。
时至今日,张爱玲研究面临创新瓶颈。搜索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但老实说,人云亦云成了创新“拦路虎”。在80年代研究张爱玲,是个争议的话题,不论深度如何,都有开创之功。在90年代研究张爱玲,“正名”后面面俱到,说什么好像都有新意。时下再研究张爱玲,当然得在观念上、方法上真正有所突破,才能站得住脚。大体说,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张爱玲的艺术特色研究仍然是个薄弱环节;二是,应当结合文本实证张爱玲的思想内蕴,而非泛泛之谈;三是,张爱玲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增加了什么,必须说个清楚明白。至于眼下关于张爱玲的双语创作及翻译、张爱玲与影像关系等研究,也得建立在前述三个方面之上才有重要意义。
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偏向于从女性叙事角度研究张爱玲,但一篇偏向于从观念上剖析,一篇偏向于从方法上说明。前一篇认为张爱玲通过反思五四启蒙文学,从强调“崇高”、奉行男权叙事、主张“写人生”的启蒙文学转向强调“日常”、建构女性叙事、主张“写人性”的“非启蒙文学”,讨论核心是张爱玲如何区别于鲁迅传统。因为鲁迅一直代表“文学正确”,张爱玲偏离了这个传统,到底怎么评价,就会见仁见智。有学者将张爱玲的创作“鲁迅化”,如模仿“铁屋”意象建构什么“铁闺阁”意象就是一例。可仔细想想,若张爱玲真的成了“女鲁迅”,这多了一名模仿者,却无法拓展文学史的题材与意义空间。后一篇从女性叙事角度分析《霸王别姬》,当是张学的一个新收获。《霸王别姬》虽为少作,但用“少年老成”来形容这篇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一点也不为过。确如研究所指出,它是张爱玲女性叙事的奠基之作,张爱玲在这个文本中发出了“女性的声音”,且分两层发出,一层是发出叙述者的女性声音,一层是发出主人公虞姬的女性声音,两层声音相交融,着实穿透了那个由男权叙事所构造的传奇铁幕,释放了女性的历史压抑。这是张爱玲的贡献,也是研究者的贡献,正是作者与阐释者的联合,才通过这次文本阐释来促成现代女性意识的再出场与再建构。
杰出的作家是说不尽的。张爱玲属于这个说不尽的行列。若只是囿于意识形态的对立而简单否定她,那只是表明一种立场,而非从事学术研究。
张爱玲通过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注重日常生活描写、体现女性的生存态度、追求苍凉的美学风格的“非启蒙文学”路线,实现了从启蒙文学关注人生问题的表现到非启蒙文学关注人性问题的表现的转换,开拓了现代文学的意义创造空间。
张爱玲;五四文学;非启蒙文学;女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中,用启蒙主义来判断作家艺术价值的高低,是一个流行的批评标准,合之则高评,不合之则低评。其实,这是值得反思与探讨的。用启蒙是说不尽现代文学的,只用启蒙的标准会限制认识那些不属于启蒙传统或试图超越启蒙传统的文学创新。张爱玲就属于“非启蒙文学”的一类,代表了现代文学的转型。笔者曾对这一转型做了如下概括:其一,从五四文学的启蒙话语转换到后来的非启蒙话语;其二,从古典的悲剧式创作方式转换到现代的日常式创作方式;其三,从推崇崇高的精神类型转换到表现平凡生活的世俗精神类型;其四,从高雅的审美趣味转换到雅俗兼容的趣味;其五,从男权写作转换到女性写作。由于这五个层面的转型是高度整合的,有着共同的思想观念作基础,在张爱玲的创作中又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张爱玲的转型既全面又彻底。很多学者认为,张爱玲的创作代表了另一种现代性,实际上就是不同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学界曾戏说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祖师爷爷”,又说张爱玲是“祖师奶奶”,就表征了这一转型。有学者认为,鲁迅与张爱玲的创作年代相隔甚远,怎么能够并称?其实,这样说的目的,只是认识到转型而已,强调不能只用鲁迅的传统来概括后来的文学发展,哪怕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确实存在鲁迅的巨大影响。张爱玲的这次转型,是一种双重反拨:既反拨“左翼”文学,又反拨五四文学。前一反拨看似是张爱玲的直接对象,其实后一反拨才是张爱玲的真意所在。正是由前一反拨到后一反拨的深化,才构成了张爱玲此次文学转型既具有针对性又具有深刻性,从而赋予此次转型以重大的文学史意义。面对这种转型,如果再用启蒙文学的标准来加以评价,就会削足适履,看不清张爱玲的创新所在,甚至批判她的价值,而文学是需要永久地创新并接纳创新的。事实是,重复鲁迅的传统,是文学的一种光荣;但能够超越鲁迅,才是文学的更大光荣。
若加以总结的话,笔者认为,张爱玲的这次转型是从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转换到以她为代表的“非启蒙文学”。尽管张爱玲是尊重鲁迅的,但她还是以非启蒙的面目出现,并且开创了以女性的、非启蒙的方式来书写中国故事并着力表现平凡人性的新的文学路线。
一、重评五四文学
张爱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观成为一种新传统与标准之后,并没有简单地给予认同,她敢于直接地非“五四”,说出了“五四”的不恰当,而非说“五四”的完全不必要。张爱玲指出:
“大规模的交响乐自然又不同,那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了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然而交响乐,因为编起来太复杂,作曲者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以后往往就沉溺于训练之中,不能自拔。所以交响乐常有这个毛病:格律的成分过多。为什么隔一阵子就要来这么一套?乐队突然紧张起来,埋头咬牙,进入决战最后阶段,一鼓作气,再鼓三鼓,立志要把全场听众尽数肃清铲除消灭,而观众只是默默抵抗着,都是上等人,有高级的音乐修养,在无数的音乐会里坐过的;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这音乐是会完的。
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劈头劈脑打下来的,再吵些我也能够忍受,但是交响乐的攻势是慢慢来的,需要不少的时间把大喇叭小喇叭钢琴凡哑林一一安排布置,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1]213-214
在这段颇具象征意味的音乐讨论中,张爱玲将五四运动比作一场“大规模的交响乐”,不仅是渲染它的宏大,而且是想揭示它的集中性,即“把每一个人的声音都变成了它的声音……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这是重新解读五四新文化,认为它有过于宏大与集中之嫌,从而淹没了个人声音的独特性与私人性。这说明,张爱玲着意追求的是要从这种个人的被淹没状态中独立出来,显示自我。这种感觉与五四新文化健将周作人的当年感觉相一致。正是基于五四的思想解放最终演变成为一场集体启蒙的狂欢,要求一律,周作人才主张要种“自己的园地”。时过20年,张爱玲接上周作人的话语,也是期望背向集体主义,在面临庞大时代思潮的裹挟下可以跳出来,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风姿绰约的个体。请不要忽略张爱玲在讨论交响乐时用了“格律的成分过多”这句话,它指的就是五四的那种文化模式会束缚人的个性发展。尤其在分析交响乐的效果时,张爱玲认为它的攻势是慢慢来的,四下里埋伏着,最终一起奏效,并用“这样有计划的阴谋我害怕”作结,也是形象地点明“五四”新文化正是通过自己的独特的文化逻辑,规训了文化思想的发展,极有可能将文化的发展打落到统制的陷阱中去。这样一来,就好理解张爱玲喜欢中国音乐的理由了。正因为中国的锣鼓是不问情由地劈头劈脑打下来的,没有交响乐那般的规划,所以也就不用担心它有统制人心的技术“阴谋”。张爱玲喜欢中国的锣鼓,还是喜欢它的那种没有规矩的自由抒发。
在这里,张爱玲关于“交响乐”与“中国锣鼓”的比较,其实是对五四新文化的启蒙主义的一种反思,她为自己确立的方向是一条非启蒙的自由之路。
二、从“崇高”到“日常”
张爱玲喜爱日常生活,所以也喜欢通俗的东西,这样的精神状态,是从崇高、高雅中突围出来。这属于另一种生活空间,而这个生活空间是摆脱了启蒙主义话语的实践领域,张爱玲正是试图建构这样的领域。她说过,最喜欢的古典音乐家里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肖邦,而是较早的巴哈(即巴赫),认为巴哈的曲子里“没有宫样的纤巧,没有庙堂气也没有英雄气,那里面的世界是笨重的,却又得心应手;小木屋里,墙上的挂钟滴答摇摆;从木碗里喝羊奶;女人牵着裙子请安;绿草原上有思想的牛羊与没有思想的白云彩;沉甸甸的喜悦大声敲动像金色的结婚的钟。”[1]217其实,她之所以喜欢巴哈的音乐,是因为这音乐里流淌出来的是平民情调,肯定的是现世安稳的日常生活状态。张爱玲反对“庙堂气”和“英雄气”,一者反对的是流行的意识形态,一者反对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英雄情结。张爱玲喜欢凡俗的日常生活世界,这里有着浓浓的人间味,使人感到亲切、和谐与充实。张爱玲在结束这段话时,还引用了勃朗宁的诗句“上帝在他的天庭里,世间一切都好了”。把“上帝”与“世间”分隔开来,是强调无须“上帝”光顾,“世间”就自有它的好处了。如果我们把“上帝”的光顾视作为“世间”生活注入思想与意义,那么,张爱玲这样说,也就意味着“世间”自有属于它的思想与意义。人类只要在“世间”安稳地生活,就获得了思想与意义,不必抬头仰望星空,渴望神义了。
明了这一点,就会理解张爱玲为什么不讳言她与通俗文学的关系了,因为通俗文学正体现了对于凡俗世界的尊重与喜爱。张爱玲就承认自己的喜好是读毛姆、赫胥黎的小说。近代的西洋戏剧,唐诗,小报和张恨水。[2]并就小报做过说明,认为它体现了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现代的都市文明;不论写什么,写出来都是一样的,可以很清晰地看见作者面目;此外小报作者就是普通的上海市民,性格不孤僻,为人不幻想,由他们来表现人生,当然创作取向也是朴实无华、想法实际的。[3]40实际上,喜欢描述凡俗生活世界的作品,是张爱玲一生的兴趣所在。少年时代,她就阅读并试作通俗文学作品。在美国生活时期,她仍然对“垃圾”小报爱不释手。晚年更用国语翻译《海上花列传》,还是与通俗文学相伴随。不能大度地肯定通俗文学的人,根本就不能大度地肯定张爱玲;不能深入地理解通俗文学的人,根本就不能深入地理解张爱玲的人生观与创作观。
那么,在张爱玲眼里,通俗文学到底具有何种魔力呢?笔者认为集中在如下几点上:其一,通俗文学讲的是人生安稳的故事,与人生飞扬的宏大叙事不相干,前者是非启蒙的,后者是启蒙或革命的。张爱玲认为,正是这些人生安稳的故事代表了人类的永恒追求。所以,活在安稳中,哪怕这个安稳是假象,也对张爱玲有吸引力,并急着去寻找与实践。其二,创作通俗文学的作家,是怀抱真诚的作家,他们写自己所见,写市民所想,创作时有着真情实感,因而避免了假大空的不着边际。其三,张爱玲的交友与生活圈子极窄小,阅读这些通俗文学与小报,为其提供了题材来源,她自己就强调,这些题材是真实可靠的。其实,没有一个作家的创作是不参考别人的书本的,因为生活的无限丰富性,是任何一个作家都无法全部把握的。当然,肯定这种借鉴,不是否定作家熟悉某一方面生活的重要性,这某一方面的生活正是作家取之不竭的源泉。张爱玲在自己的创作中,坚持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这一原则,原因就在此。她说过,文人是园里的一棵树,不能挪动自己的位置,其实说的是作家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去写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中的人与事。张爱玲喜欢通俗文学,是因为她自己活在通俗文学所表现的那个凡俗的世界里,所以,她要从通俗文学关于凡俗的表现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创作。
为什么说回到日常、通俗,就规避了启蒙主义呢?这是因为启蒙主义往往看不起日常与通俗。启蒙主义的目标是改造日常,提高通俗,因而日常与通俗在启蒙主义那里,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是应该被否定的。而张爱玲不一样,她强调了日常与通俗的恒定性,并从日常中去揭示凡人的生活实有状态,而不轻易地宣传生活的应有状态。张爱玲用自己的实践避开了启蒙之锋,走上了非启蒙之路,以深入凡俗的姿态,揭示着凡俗的种种面相。
这是否意味着张爱玲与左翼的大众化相一致呢?绝不相同。左翼的大众化其实是化大众,将大众革命化,还是否定日常生活的正当性而提倡革命生活的正当性。
三、非启蒙的女性叙事
启蒙主义的路线可以说是一条智性的路线。强调个体拥有理性并独立做主,是启蒙的两项任务。在启蒙书写里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成为一个常态。在启蒙主义那里,女人往往成为提高的对象,而非依靠的对象,因为启蒙主义者认为女人既不理性,更不能为自己做主。所以启蒙书写时常讨论女性问题,并将女性定义为启蒙对象。鲁迅所写《伤逝》就讨论了作为“娜拉”的子君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多数论者的结论也是:妇女不能在经济上独立,就不可能在婚姻与社会中独立。这样的创作与这样的解读,可谓典型的启蒙主义思路。
但在张爱玲这里,女人并非启蒙的对象。她将女人视作人生的基础、世界的未来,因为女人有那种社会、男性、知识所难以规范的自然力量存在于女性本体之中。或者说,女人本来就是与男性文明相对立的,甚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颠覆男性文明,这样一来,女性当然也就一并颠覆了启蒙。张爱玲指出:“叫女人来治国平天下,虽然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这荒唐的建议却也有它的科学上的根据。”“女人常常被斥为野蛮,原始性。人类驯服了飞禽走兽,独独不能彻底驯服女人。几千年来女人始终处于教化之外,焉知她们不在那里培养元气,徐图大举?”[4]86
这虽然只是泛论,其中关于“女人治国平天下”等观点,可能借鉴了20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女权活动家Mrs.Inez Hayne的想法,她说:“男子统治的世界,已弄成一团糟了。此后应让女子来试一试统治世界,才有办法。”[5]139可见张爱玲批判男权社会与文明传统的立场是鲜明的,而这个立场就是女性的立场。在张爱玲看来,男性只能代表人类文化的某一种发展倾向,在某一个历史阶段上获得成功。但女性不同,女性代表了文明的基础与永恒性,代表人类文明发展的总体方向。张爱玲这样描述过女人:她们是最普遍的、最基本的,代表着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代表着人类生活的一切基本方面。所以她说,若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女人就是这根根桩。这与张爱玲的另一区分相同,即把男人称着“超人”,女性称着“神”。“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飞越太空”,是进取的,仅仅为生存的某一种功利目标服务,不达这个目标,死不瞑目,达到这个目标,就自认功德圆满。“神”是“踏实的根桩”,安稳地栽在大地上,代表了广大的同情与慈悲,了解与安息。[4]88张爱玲曾说自己不大可能会有信仰,但承认若非得选择信仰的话,她愿选择奥涅尔《大神勃朗》创造的“地母娘娘”作为自己的信仰,因为地母娘娘代表着土地、爱、生命的孕育与创造。张爱玲通过对于男性与女性、“超人”与“神”、理想与现实、代表一种功利目标与代表生存本身等比较,建立了自己的女性观,并运用这一女性观来从事创作,因而得以用女性眼光,以充满同情与理解的态度来展现女性的生活世界与情感世界,体现了为女人说话的一片衷情。
张爱玲在创造了曹七巧以后,之所以一再表白不愿再去创造这样“彻底的人物”,就是担心将人物写得过于彻底会破坏女性人物的思想与情感的复杂性,不够真实。张爱玲在寻找着女性的真实。实际上,比较的看,她笔下的曹七巧,远比左翼作家笔下的同类人物要丰富得多。并且张爱玲也没有通过曹七巧的受压迫命运以证明必须对曹七巧实施启蒙,因为一旦实施启蒙叙事,就意味着要将曹七巧文明化,这正好陷入了男权圈套。张爱玲让曹七巧自我呈现着,在这种自我呈现中站立起来,而非依附于某种启蒙思想,使其成为启蒙对象,在启蒙的理性逻辑中塑造她,引导她,将其推向社会。因而,张爱玲宁可让曹七巧在谢幕时回顾年轻时的健康美丽,感到生命自顾地流走了,却不愿意让她以年老的声音、满腔的悲愤喊出“救救女性”这类启蒙的口号,以提升作品的社会效果。张爱玲在创造了霓喜以后,又为霓喜辩护,也是害怕人们误解霓喜,聚焦于她的不免混乱的两性关系(她是被迫的,被男人买来卖去)就否定霓喜作为女人要求生存的正当性,将她视作道德败类。张爱玲总是带着同情与理解来创造笔下的女人形象,我们也唯有同情与理解才能评价她笔下的女人形象。从这点讲,张爱玲不无性别自私,总是站在女性立场,维护女性生存权利。但张爱玲生于男权社会,男性价值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有时甚至成为社会唯一价值,她有这点小小的过火与夸张,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实存在三种关于女性的叙事方式:启蒙主义的叙事是通过教育女性,希望她们认清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地位,通过学习与实践,能够自主地思考与行动。鲁迅的女性形象创造与丁玲早期的女性形象创造属于这一类。革命化的叙事是通过鼓动女人,希望她们认清自己被压迫的现状,了解社会阶级斗争的实质,加入革命运动,为自己、为阶级而奋斗,解放自己。大量革命文学创作属于这一类。非启蒙叙事告诉女人,希望她们认清自己的生存地位,确信自己代表着人类存在与延续的基本层面。像张爱玲、苏青等人的创作,就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这三种有区别的女性叙事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得其一而否定其二,都会窄化关于女性的思考。启蒙叙事重视的是思想的价值,革命叙事重视的是政治的价值,非启蒙叙事重视的是人性的价值。思想的价值在思想愚昧的状态下体现出来,政治的价值在压迫严重的状态下体现出来,人性的价值在人类的长期生存中体现出来。到张爱玲的出现,她是顶撞着启蒙的话语与革命的话语的重压而艰难前行的,因而首先肯定她的探索是十分必要的,当然这一探索也是可以成为典范的。
四、从写人生到写人性
张爱玲所推崇的美学倾向也体现了“非启蒙”的特征。比如她说:“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性。”[6]18
从张爱玲的创作情况看,她已经实现了从“悲剧”到“传奇”的转换,但她并没有彻底斩断与“悲剧”、“悲壮”的联系,只是改变了它们的内涵,赋予它们以不同的功能,导致她的悲剧意识远非传统悲剧观念所能涵盖。张爱玲的悲剧意识不是指涉人生的某一种生活状态,相反的情况是,如果没有这种压力,人就不会处于悲剧之中。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是指涉人生的整体生存状态,认为悲剧是人生的基本生活方式,强调除了带着悲剧去生存之外,人类并无其他的更好生活方式。也就是在这里,我们能够从张爱玲的作品中读出现代主义的某种意味。因此,张爱玲渲染人生悲剧的时候,已经不必借助传统悲剧的激烈冲突的形式构架来运作,她只要平淡地叙述人生中一个又一个并不圆满的故事,就具有了悲剧实质。但张爱玲相信人类总是要努力生存下去的,所以其悲剧意识又蕴藏着温暖之力,肯定人类的某些努力,哪怕是十分卑微的,只要取得了平凡的生活实绩,也是具有意义的,也应受到作家的拥抱与呵护,承认这是生存的合理追求。张爱玲在创作中不强调力、崇高、紧张、英雄、疯狂等传统悲剧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可以是启蒙美学的要素,也可以是革命美学的要素,但不是张爱玲人生悲剧的钦点要素。张爱玲所主张者与此相反,她认为:“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可正代表人生的根本。所以她不创造悲壮的悲剧,却向人们昭示了人生苍凉是无处不在的。因此,读张爱玲的小说,不要期望关于生生死死的极端描写及由此产生的激烈的悲壮感或悲痛感,但其内蕴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甚至超过了这类悲剧的启示,有着更易深入人心的苍凉意味。张爱玲说过:“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7]6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末世意识,不仅是说二次大战对于人类的巨大威胁,也是说人类发动的每一场战争或造成的破坏,都是对于人类的巨大威胁,用这构成作品的悲剧基调,即使作家不直接描写悲惨的故事,作品也会形成苍凉的美学风格;即使作品中的人物对此毫无知觉,他们的命运也都一律涂上了悲剧色调。张爱玲由此形成的艺术个性,已经将人类日常生活的正当性与人类所处的悲凉境遇关联起来,建立了意义上的张力关系。既写出日常生活形态的亲切感与合理性,又写出日常生活的陌生感与荒诞性,创造了日常生活表现与人类终极思考相统一的文学能指系统。
我认为,把鲁迅拿来比较一番,可深化认识张爱玲。鲁迅主要是写人生的,以人生问题为引导而展开叙事,叙事的主要目的在于人生问题的能否解决,最终指向社会批判与人生启蒙。其作品提出或引发了诸如吃人、救救孩子、“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束缚女人的封建权力、革命者如何才能被认知、如何解决民众的愚昧与不争、我们怎么做父亲等问题。写人生问题,当然会牵涉到人性描写,不过,其主旨还是落在人生问题的如何解决之上。这一创作倾向是启蒙主义的,要求通过启蒙民众来教育民众,从而达到民众可以解决人生问题的现实目标。也易于指向社会斗争,若在解决人生问题时运用社会斗争的方式作为手段的话。从启蒙叙事转向革命叙事一点儿也不难。事实上,很多现代作家就是从启蒙主义走向革命道路的。描写人生问题的作品,容易得到左翼批评的肯定,原因也在这里。所以,尽管从一开始,革命文学主张者曾为难鲁迅,拿他来“祭旗”(李何林语),但后来终于将鲁迅纳入革命文学阵营,就在于鲁迅的解决人生问题的创作选择,已经为其被革命文学所接收提供了相近的精神基因。但张爱玲不同,她写的是人性问题,写人性也会涉及人生背景,如描写顾曼桢时就较多地描写了人生问题。可是,她的总倾向是以探讨人性为目标的,展开必要的人生问题的描写,只是为人性的展示提供背景与基础。如此一来,张爱玲的非启蒙叙事,注定了她无法走向革命,她不会鼓动曹七巧造反,不会鼓动白流苏反抗,也不会鼓动顾曼桢走上革命道路,只要达到了挤压人性的目的,张爱玲就心满意足了。她不会像革命作家那样,会利用这种种不堪,告诉笔下人物,到了你们该反抗的时候了。
总之,依我看来,张爱玲若接着鲁迅的启蒙文学传统往下做,她取得的成绩只会止于《金锁记》一类的作品,甚至会被视为退步了。因为《金锁记》虽然继承了《狂人日记》的一些思想脉络,却已经不是《狂人日记》的全盘承袭了。可她正是试图有所开创,才有了《第一炉香》《倾城之恋》《心经》《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有了《流言》这样的散文。张爱玲是在“非启蒙”的思想与艺术状态下创造了一次文学史的转型,并因这次转型的成功成为另一个传统的代表人物——“非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从而与启蒙文学的路线构成了互补态势,打开了人生与文学的另一个意义空间,丰富与深化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1]张爱玲.谈音乐[A].张爱玲.张爱玲全集(3)[Z].台北:皇冠出版有限公司,2006.
[2]女作家聚谈会[A].张爱玲.张爱玲与苏青[Z].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3]纳凉会记[A].张爱玲.张爱玲与苏青[Z].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4]张爱玲.谈女人[A].张爱玲.张爱玲全集(3)[Z].台北:皇冠出版有限公司,2006.
[5]林语堂.让娘儿们干一下吧![A].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四集)[Z].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张爱玲.自己的文章[A].张爱玲.张爱玲全集(3)[Z].台北:皇冠出版有限公司,2006.
[7]张爱玲.再版自序[A].张爱玲.张爱玲全集(5)[Z].台北:皇冠出版有限公司,2006.
责任编辑:杨春
A Few Thoughts on Eileen Chang’s Non-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LIUFengjie,PANLi
Through reflection on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e Movement, Eileen Chang wrote Non-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which focused on everyday life, showed women’s attitudes toward existence and pursued a desolated aesthetic style. As a result, Eileen embrac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life- oriented literature of the genre to humanity- oriented literature, and blazed a newdimension ofmeaningin modern writing.
Eileen Chang; May Fourth literature; Non- enlightenment Literature; women
10.13277 /j.cnki.jcwu.2015.02.009
2015-01-05
I206
A
1007-3698(2015)02-0054-06
刘锋杰,男,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本理论、中国现代文论史、张爱玲;潘莉,女,苏州大学文学院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张爱玲。21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