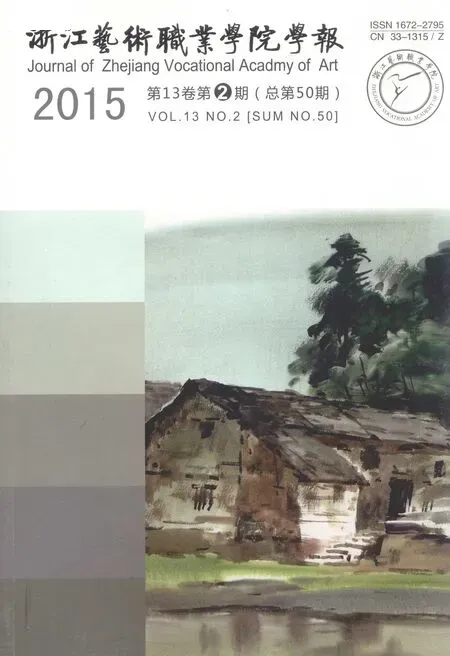从《诗学》看《雷雨》*
王新新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西方第一篇重要的美学文献。近现代西方各主要学术流派及其代表性人物几乎无例外地会涉及对亚氏思想的阐释,或以此为学术原点,构建起自己的学术体系。近年来,我国学界也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回归古典诗学的热潮,以期在中西比较、古今之争中,寻获思想灵感或文化自信,[1]这或许构成了本文的写作背景。从《诗学》看《雷雨》能看出什么?《雷雨》无疑是所有中国话剧中被谈论得最多的剧目,它是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话剧的巅峰之作。卡尔维诺曾说:“一部经典作品是这样一部作品,它不断在它周围制造批评话语的尘云,却也总是把那些微粒抖掉。”[2]《雷雨》就属这样一部作品,即使在今天,在几代评论家竭尽全力的多方挖掘后,《雷雨》依然保持着它最初的神秘感。此话有二层含义:其一,从《雷雨》成功之日起,对《雷雨》或曹禺剧作的评论在中国就成了一门显学。这门显学给曹禺带来的却是灵魂的苦闷与孤独,给曹禺剧作研究带来的是长期的非正常遮蔽与扭曲。一部“曹评”史,庶几就是一部被误读的历史。或者说,以“曹评”方式存在的曹禺剧作,凭借意识形态的强势或主流话语地位,构成“话语的尘云”长期遮蔽了以“文本”方式存在的曹禺剧作。时至今日,“反封建性”、“现实主义传统”等等,仍然占据着“曹评”的主流话语地位,阻碍了真正评论的展开[3]。其实,这一现象又何止出现在“曹评”中?其二,作为经典,《雷雨》总能抖掉这些遮蔽其身的“话语的尘云”,使得新的“话语尘云”不断在其周围聚集。
重读《雷雨》,需要依赖《诗学》。这倒并不是因“上溯的幻想为自己贴上古老的、永久的显学的艳丽标签”[4],而是《诗学》理论与《雷雨》的实际确有许多惊人的暗合。如此隐含西方悲剧精神的作品竟诞生于30年代中国的土壤上也委实有许多待解之谜。以亚里士多德《诗学》并以对《诗学》做历时性探讨的西方美学(悲剧理论)为参照,重新探讨《雷雨》的形式、情节、布局的张力以及隐含在剧作中的作者的悲剧理念,兴许能更深入地解释该剧的悲剧内涵。这不仅有助于看清这出名剧成功的原因及其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意义,也有助于以《雷雨》为个案重新认识曾被时代语境遮蔽的西方悲剧美学对中国现代戏剧究竟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一
作为古典西学的源头,《诗学》的诞生,也如亚氏其他著述一样,与其师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存在与激发有关,属“为诗一辩”之作[5]。刘小枫认为, 《论诗术》是对城邦诗人如何做诗的哲学解说。[6]其所涉及的“诗”的艺术种类有:史诗(叙事诗)、悲剧 (肃剧)、喜剧 (谐剧)和酒神颂,其制作行为或过程是摹仿①见《诗学》罗念生译注p3;刘小枫《诗术与模仿——亚里士多德〈论诗术〉第一章首段绎读》. 《求是学刊》2011年第1 期p25。据刘氏考证,摹仿在诗学中约见80 处。,其中以对悲剧的哲理讨论最为著名,影响也最为深远。从《诗学》的举例可以看出,亚氏的前辈与同辈的悲剧创作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才使得他有条件对悲剧创作的艺术规律进行反思与总结。他努力想要转变对悲剧性质和意义的传统理解,将主要笔墨集于“最好的悲剧”的成分及其相互关系、构造规则等方面,意在为诗人提供一种“理论规定性”。[3]77由于传抄过程中的脱落与篡入,或它仅是一个内部使用的讲稿, 《诗学》对悲剧的六个成分的论述是不平衡的,其中亦不乏抵牾或缺失之处,甚至某些部分含糊其辞,晦涩难懂。但透过其毛糙的表面,仍能从鲜明而连贯的理论框架、前后啮合的论证习惯看出,它是一个成熟的诗歌理论。[7]限于能力和篇幅,笔者当然不能在此对《诗学》做较深入的解读,只能是依傍名家的笺注读原典,对《诗学》与《雷雨》的相关环节做小心而粗略的解读。
对《诗学》的理解亦即对“最好的悲剧”的理解。那么,怎样的悲剧才算得亚氏所言之“最好的悲剧”呢?由于《诗学》在论述上有关联严密、重复强调、简短扼要的特点,为了有个总体的把握,笔者以自己的理解,先试着将其主要内容概述为:
行动是完整的且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
怜悯与恐惧之情是借情节的安排引起的——
情节是亲属之间发生的苦难的事——
苦难是指一个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由于犯了过错而陷于厄运——
厄运由暗含必然或可然关系的“发现”或“突转”引发——
借由“发现”或“突转”构成的“复杂的行动”引达结局——
结局是单一的因而属完美的布局。
这里分涉第六至第十九章的内容。概述中有意识的循环是为了显现《诗学》本身的逻辑脉络。从此逻辑脉络可依次析出情节、布局、观众三个要点。前二者属“悲剧形式”,后者属“接受问题”,而这两个方面在《诗学》中又是纠缠在一起,着实难以区分的。原因就在于:亚氏在讲悲剧形式时,着眼的是观众观剧的效果,即悲剧功能的实现——观剧仅是由摹仿而净化心灵的途径之一。亦即形式不仅仅是个形式的问题,更是个接受问题,唯有注重接受的悲剧形式,方能成其所言之“最好的悲剧”。所以, “悲剧形式本身和悲剧形式跟观众的关系”[8]可看作是《诗学》立论的基础。从中可见其清晰的研究目的。
依据亚氏的理解,“最好的悲剧”必具最完美的悲剧结构。最完美的悲剧结构的要件有三:其一是引起恐惧和怜悯之情,其二是由“发现”或“突转”构成的“复杂的行动”,其三是完整。亚氏在给悲剧下定义和讲悲剧所摹仿的行动时,都提到了“完整”。[8]19-31可见,完整是对悲剧整体布局上的要求,也是对剧中行动的要求。何为“完整”?这得和他在第十八章提到的“结”与“解”这对概念联系起来看。所谓“结”指故事的开头至情势转入顺境(逆境)之前的最后一景之间的部分;所谓“解”指转变的开头至剧尾之间的部分[8]60。粗略看来, “结”与“解”指的是整体情势运转的安排,由行动构成。“结”是矛盾的起因及展开,经“解”转变,改变了顺或逆的走向,矛盾继续发展,直至高潮。由于从“结”到“解”必然隐含因果和时间的关联,故而戴维斯认为,从“结”到“解”的运动是线性的。[9]16由此看, 《雷雨》的结与解的分水在哪里呢?在第二幕周朴园与鲁侍萍重逢处?抑或在第四幕被公认的高潮前?如此理解似乎会成为问题——关键是你很难照此思路理解亚氏下面的那句话:许多诗人善于“结”,不善于“解”。[8]62难道可理解成许多诗人善于编前半段而不善于编后半段?抑或不善于转势而显出布局上的局限?幸好,戴维斯对此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解答,他说:“悲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是综合或发生的——结 (desis)——又是分析或回忆的——解(lusis)。”[9]16“结”指的是制作 (虚构)故事,是组合并展示情节,故称综合或发生,诗人们一般擅长此道。“解”指的是对行动的分析,亦属情节的一部分,故名分析或回忆,是悲剧所特有的,但一般诗人们通常不太擅长。如此, 《雷雨》中的“结”与“解”方能明了:用《序幕》先给出行动的结局,在一个腊月三十的下午回忆(倒叙)十年前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并在这倒叙的故事中又穿插了三十年前的往事,作为夏天故事的起因,最后,在《尾声》中——在同样的音乐声中,回到故事的原点,这就使得整个剧处于一种逆向叙事之中。[10]16尽管它本身是按照从先到后的方式进行的,也呈现出明显的因果关系。与此相应,剧中主要人物间的故事也几乎是在倒叙中提到的:周萍与蘩漪、周朴园与鲁侍萍、乃至周萍与四凤,他们之间的事,实际上都是“曾经发生”的事,剧中只是在这个夏天的故事中穿插交代。可见,四幕剧所展示的行动是“结”,回忆(倒叙)中的往事是“解”—— “曾经发生”的事为“正在发生”的事提供了分析和解答。假如,曹禺算得亚氏所言善“结”善“解”的诗人,那《雷雨》也当得行动完整的佳例了。
二
人们要将亚氏与某剧挂上钩时,最先想到的恐怕便是“突转”与“发现”,并在剧情的复述中点出这是“突转”那是“发现”,比如,人们通常将《雷雨》第二幕中周朴园与鲁侍萍的重逢,理解为“突转”——其实,作为《诗学》论述的重点,“突转”与“发现”并不能如此简单地理解。从《诗学》看《雷雨》也不仅仅是个“突转”与“发现”的问题。它们与《诗学》中的其他核心概念一样,相互之间有更深层次的关联。“突转”与“发现”为何如此重要?“突转”与“发现”是否就成了“最好的悲剧”的标志?通过亚氏的“突转”与“发现”的论述,我们能发现什么?
亚氏将悲剧分为四种,其中复杂剧或“复杂的行动”完全靠“突转”与“发现”构成,且必须由情节的结构中产生,成为前事的必然的或可然的结果。[8]32-60《雷雨》是否属于复杂剧?如果是,那么,其“复杂的行动”又如何体现呢?
无论是亚氏所谓的“必然”或“可然”,都会有一个因前事引发的结果,故存因果关系。只不过必然的因果属显性因果,而可然中隐藏着的是隐性因果,不易被人觉察,故名“看似如此”①必然或可然,刘小枫译成必然如此或看似如此,似更切合亚氏的表述。见《论诗术中篇义疏·中译本前言》p10 -16,[阿拉伯]阿威罗伊著:刘舒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发现”或“突转”都须受看似如此或必然如此这两种因果的制约,于是,它们便成了左右行动的两个法则,并以此将剧中人物与观众的想法区别开来——对剧中人物来说是“看似如此”的行动或后果,对观众来说却是“必然如此”。因为, “必然如此”是观众的判断,但剧中人物往往看不到,或者说,后果对他而言是“意料之外”,而对观众而言乃属“情理之中”。这就使得悲剧形式与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来自于亚氏所言之突转(perpatria)和发现(anagnÔrisis),它们是悲剧的灵魂。②有关“突转”与“发现”的讨论,参见戴维斯《〈诗学〉微》. 载《诗学解诂》p2-20。
从位于第十一章开头的定义看,突转是“意外地发生”的,那么,出乎谁的意外?是剧中人物,抑或观众?戴维斯认为:“突转必定是我们这些观众的发现”。[9]10这似乎是一条不错的线索,由此可理解为,突转是观众的收获,它只能是来自于观众的知觉,是观众发现,而剧中人未发现——于是在必然如此与看似如此的对比中形成剧外和剧中的张力。假如鲁侍萍在第二幕见到周朴园后离开,不再在周公馆意外地出现,周萍与四凤的关系如何被发现?除此谁能发现?也许《雷雨》布局的奥妙缘于此处。
与观众的知觉相对,“发现”属剧中人物的知觉。从亚氏对发现的定义看,这种以“亲属关系和仇敌关系”为内容的发现可分为三种情形:人物(主格)发现……人物被(宾格)……发现,互相“发现”。第一种情形,比如鲁贵在周公馆出于炫耀向四凤讲述了曾经发生在周公馆的闹鬼事,隐约指出了太太(蘩漪)与大少爷 (周萍)的关系,这是鲁贵的发现,也是《雷雨》发现的开始,核心情节由此逐步展示。第二种情形,周萍与四凤的恋情“被”鲁侍萍发现,暗示了高潮将要到来。第三种情形,周萍与四凤相互发现,并伴随着怪笑与惊呼逃离,行动的后果与观众的判断在此交汇,形成高潮。这些都属于人物“从不知到知的转变”,[5](p34 -35)诸种发现共同作用于人物的知觉,使得隐藏的因果及人物关系得以显现,揭示出事件的真相。因此,戴维斯认为,发现是对无知的剥夺。[9]10
由情节而来的发现,亦即自然而然地产生的,既看似如此又暗含因果,且能引发观众的惊奇感。与此相对的是由推断而来的发现。既然发现是人物间的事,那么推断也只能是人物的推断。为什么由推断而来的发现要劣于由情节而来的发现?我们先得区分《雷雨》中这两类发现的例子,才能回答为什么由情节而来的发现比由推断而来的发现要好。例一,在第一幕中,四凤给周冲倒汽水,周冲说,“谢谢你”,四凤红脸。蘩漪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说“冲儿,你们为什么这样客气?”此时,蘩漪由这二人的态度发现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此类发现由推断而来,是蘩漪的偶然发现,前因后果并不明显。例二,在第二幕中,侍萍由家具和照片发现自己竟然又来到了周家。她来是因为蘩漪要她带回四凤,正因此,她方有机会发现周萍与四凤的不伦之恋,此类发现由情节而来,有严密的因果链,是布局的关节点。这二例发现的区别在于:尽管侍萍的发现也不乏推断的成分,由推断而来的发现也绝难与情节分离,但我们不难区分,后者属主要情节,是“由情节的结构中产生”的,更能显出因果的关联,故能引发观众的惊奇,因此,我们须将此处的亚氏此处提及的“情节”理解成“主要情节”,它关乎“前事的必然的或可然的结果”。
因此,最牵动观众的是随着情节的展开,观众发现了他们的发现在剧中的被发现,即“突转”(观众的发现)与“发现” (人物的发现)同时出现,剧中最重大的变故不可逆转地伴随着苦难而来,观众期待而又害怕的一幕终于降临。此时,剧中人物与观众同时经历从不知到知的那一刻,亦是剧中与剧外最具张力的时刻,是最激动人心的——笔者认为俗称的“戏剧性”便由此构成,同时,这也是亚氏自己的一大“发现”,是对戏剧理论的一大贡献。尽管在《诗学》中,他从来没有使用过“戏剧性”这个词。他只是说:悲剧所以能使人惊心动魄,主要靠“突转”与“发现”。[8]22因为,他关注的重点显然在于它们能够引发怜悯或恐惧之情——亦即悲剧摹仿行动的效果所致、目的所在。其实, “突转”与“发现”正是构成“戏剧性”的关键所在,而“戏剧性”也正是观剧效果的比喻性表达——除非惊奇感、怜悯或恐惧之情不能算作观剧的效果。
在第四幕开始前,观众其实已经发现了悲剧的不可避免。但我们似乎在等待剧中的发现——我们还不知道但又想知道,我们所发现的在剧中是如何被发现的。发现的动力似乎来自于绝望中的蘩漪的爆发。蘩漪不惮让众人发现她自己与周萍的恋情,还要众人发现四凤与周萍的恋情。她那充满快意而疯狂的行动,揭开了更深更具悲剧性的一幕——这是她始料不及的。即使是自以为受了周萍情感上的巨大伤害而最具悲惨命运的她,再也不会在乎人世间的任何变故的她,此时,也颤抖地感觉到,被她亲手揭开的那一幕太过残忍,且是无可补救的,即使这当事人是周萍——因爱的绝望,而使她恨到疯癫状态的周萍。尽管其初衷无非是为了借助于周朴园的力量阻止负心的周萍不能撇下她而称心如意地带着心爱的人逃离——作为剧中人,她并不可能“发现”此二人是兄妹关系。
尽管蘩漪愧疚于自己亲手揭开了这生命中无法承受的惨痛一幕,其实,悲剧的发生与被发现,又怎能避免?一切行动都早已指向了这剧中最重大的发现。剧中各种发现——亲属或伦理关系的发现均牵于此,它似乎成了剧中发现的牵引力。区别仅在于有待发现或彼此间的发现与未发现,只是剧中人物不自知罢了。如果说“突转让观众反思一个最初看起来不可能之行动的必然性。”[9]11那么发现的功能仅仅是将观众的反思引入剧中——发现是剧外反思向剧内行动的延续,它似乎在剧中一步步地印证观众的想法。曹禺本人及一些评论者曾认为《雷雨》 “太像戏”,是一个缺陷。其理由也无非是,人物间的关系怎会有如此巧合,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事。但从《诗学》的角度看,这恰恰是《雷雨》的一大优点——既然剧外的人都在反思这种可能性,剧中人又怎能预见呢?这种知与不知,必然如此与看似如此,发现(观众)与发现(剧中人物)的碰撞,不是更能引起亚氏所期待的观众的怜悯或恐惧之情吗?周萍本想通过与四凤的爱来拯救自己逃脱出乱伦的困境,结果却进一步掉入乱伦的深渊,要了他的命——他不可能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究竟做了什么。蘩漪的报复,侍萍的阻拦,周朴园的相认也无不如此。与观众的知觉相比,剧中人物的知觉总是带有可怜的虚假的意味。“他作这种可怕的事时不知道对方是谁,事后才发现他和对方有亲属关系。”[8]44所以,与突转相比,发现便成了“假”发现,当这类虚假的发现被判断成虚假时——即当鲁侍萍发现周萍与四凤兄妹间是情人关系抑或是周萍发现自己的身份是情人的兄长,亦即当突转变成发现时——真相显现,苦难降临,就会引发观众的惊奇感及恐惧与怜悯之情——亚氏重视“突转”与“发现”同时出现的原因也应在此,它们是其所言悲剧形式与观众交流的关键。
三
如果说“悲剧是戏剧中最完善的形式,情节是悲剧的灵魂,而突转和发现是情节的核心”[9]9,那么,苦难就是突转和发现可然或必然的结果,而过错则是苦难的原因并指向唯一的结局。
什么是苦难?亚氏说,苦难是毁灭或痛苦的行动。那么,又是什么构成了《雷雨》的苦难呢?为了论述尽量简明扼要,笔者试着按亚氏的方法将《雷雨》的情节“简化成一个大纲”:
一个家族的长子与后母发生了乱伦关系,为了摆脱这层关系,他爱上了家中的使女。在一个雷雨之夜,他打算带着使女逃离这个让他厌恶的家庭,但遇到了后母的阻拦,此时,他“发现”,自己恋着的使女原是他同母异父的妹妹,于是,拯救自己逃脱乱伦关系的行动只不过使他陷入了更深一层的乱伦的怪圈,他感受到了“命运”的冷酷与残忍,于是开枪自杀。与此同时,在他周围的几个具有亲属关系的人,也因此或死或疯,一个家族在雷雨之夜走向了毁灭。①依据规则,概述时不用专名,以免忽略主要情节,参见罗念生,《诗学》p57 注。
第二阶段,将岗位说明书的覆盖范围扩大至全院,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项目组通过问卷调查法、访谈分析法等方式完成了全部临床科室核心岗位以及职能科室全部岗位的“岗位说明书”编写工作,至2014年9月前又进行了修改与优化工作。
大纲亦即核心情节的概述,其他情节都是辅助性的“穿插”。我很难在概述大纲时用其他人物替下周萍的位置,因为,乱伦似乎构成了《雷雨》的核心情节,摆脱乱伦并以失败告终似构成了剧中的主要行动,同时它也是发现的内容和恐惧的对象。从概述的大纲可见,《雷雨》正是亚氏所言最好的悲剧。即:
情节是“亲属之间发生的苦难的事”[8]44——《雷雨》剧中人物之间都为亲属或有伦理关系。
苦难是指“一个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由于犯了错误而陷于厄运”[8]38——这一人物在剧中以周萍的遭际最具代表性。
他是个私生子——一个非自然的儿子,缺乏家庭亲情。他在种了他后母的地后,又驶入了亲妹妹的港湾。②此句效仿自希利斯·米勒对《俄狄浦斯王》所做的“耕种”与“船只”之隐喻分析,原句为“俄狄浦斯耕种了其母亲之地,驶入了其母亲的港湾。”见〔美〕J. 希利斯·米勒. 《解读叙事》,第一章《亚里士多德的俄狄浦斯情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p23。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不能预见到行动的后果,对需承受的后果也绝非自愿。但他的不自愿至少是不彻底的,因为,他的行动也绝非纯属外力使然,因此,他缺少足够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在第一幕开始前,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并做出了抉择,试图通过逃避及对四凤的爱来拯救自己,从这一行动看,其个性也是善良的,至少,他不愿在乱伦的路上一直滑落下去。但行动的后果却是“可怕的或可怜的”。[8]43毁灭了他最亲近或最爱的人。周萍的遭遇正如伯恩斯所言:“……从他辨认出恶果时的痛苦与悔恨可以看出,他无意行恶或者并没有预见到恶果。他的负罪感和悔恨向我们暗示,他在根本上不是恶的,这样他就有被我们怜悯的资格。……光他的苦难就够赎他对自知之明的匮乏了。”[11]当他发现自己做了什么时,靠人力已无法挽回。于是他发现自己正孤独无助地面对着一个黑暗的世界,发现自己的生存以及抗争是毫无意义与价值的,在发出了人世间最惨绝的一声呐喊—— “您不该生我”[12]后,走向死亡——这似乎已经构成亚氏所言诗人所应追求的悲剧的最好情节。可以认定,假如没有周萍此类人物,没有他所做的事,《雷雨》的苦难是不成立的,恐惧与怜悯也无从谈起。
问题是:《雷雨》的苦难究竟是缘于过错还是命运?如果将苦难理解成是对人物发生过错的惩罚,那么,人所犯的过错是否就成了悲剧行动的决定性力量?朱光潜认为亚氏有此类倾向。他说:“亚里士多德绝不是有意让命运观念复活的人。命运这个概念本身就有害于宇宙的道德秩序,使人丧失自由和责任。正因为如此,他才引入‘过失’这一概念来解释悲剧人物的遭遇。”[13]其基本的理据是,近代西方悲剧在基本精神上来源于欧里庇得斯,而不是埃斯库罗斯或索福克勒斯。它从探索宇宙间的大问题转而探索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从埃斯库罗斯到欧里庇得斯,亦即从神到人,从命运到过失——关注视角发生了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从亚氏开始的。那么,曹禺受到的是哪方面的影响?这得看他发现并试图在剧中表达什么?他说:
……也许是某种模模糊糊的感情的驱使,流露出一种受压抑的愤怒,并对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进行了谴责。可是,最初出现模糊的构思时,使我感到兴奋的,不仅仅是一二个主题和几个人物,也不是因果报应,而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残忍”与“冷酷”。……这个斗争的背后也许存在着某种东西,希伯莱先知们把它称为“神”,希腊剧作家称之为“命运”,近代人则抛弃这类模糊观念,把它叫做“自然法则”。——1936年1月15日于天津。[14]
一般而言,曹禺早期那几篇谈创作的文章更接近于其创作实际和内心的真实。曹禺为何一再强调自己写的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很显然,他当时发现并想表达的并不是中国的家庭和社会之类带有表层性质的事物,而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残忍”与“冷酷”。如果说前者是作者的第一视野的话,那么,经“可是”一转,表达了曹禺的穿越,其第二视野已穿越到对深层抽象问题的思考——这才是曹禺发现与想表达的,它寄寓了作者的存在之思,也便成了《雷雨》的主题。主题是作者对母题的个性化理解,如果说乱伦是《雷雨》的母题,那么,曹禺正是发现并借用乱伦这个母题,表达了对这个“残忍”与“冷酷”世界的认识,而其背后是类似于“命运”之类的东西。
朱光潜说,“尽管人物性格在近代悲剧中越来越重要,但导致悲剧结局的决定性力量往往不是性格本身,而是原始形式或变化了的形式的命运。”[22]97这是否较切合《雷雨》的实际?从周萍等人的遭际看,他们在行动中固然因自身的弱点而犯了过错,陷于厄运,但从人物绝望于世的呼声中,观众仍能体会到“命运”的操纵。当周萍明白要为自己的认事不明的过错付出生命的代价时,“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脱这黑暗的坑”(《雷雨》序)这一支撑全剧基础的理念才体现得分明。过错与命运似乎以一显一隐的方式并存于剧中,左右着情节的走向。
再进一层看,《雷雨》的实际与亚氏的过错说其实并不矛盾。亚氏在说到因过错而遭受厄运时,并没有指明厄运的来源,也没有因此否定命运在悲剧中的作用。他的过错说是不彻底的。朱光潜就曾说过,“亚里士多德的‘过失’概念从严格的审美观点说来是令人难以接受的。”[22]97尽管亚氏所处的时代,已经有别于埃斯库罗斯时代,但命运观念很难彻底消亡,这既是人类的现状,也是悲剧诗人的现状,故而也只能是摹仿人类行动的悲剧的现状。亚氏之所以提出过错说,除了强调人应承担的责任——以有利于观众或人物反思行动的因果外,还是个聪明的办法。因为,他发现观众往往偏爱会犯错误的悲剧人物,因为“容易犯错,大概是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根本特点”。[8]17这暗示的是:亚氏从观众偏爱人物的弱点看到了观众的弱点。“聪明的剧作家于是便承认观众有弱点这一事实,亚里士多德的‘过失’说恰恰是作为一种讲实际的聪明办法,才显出有它的道理来。”[22]99可见,命运与过错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有时甚至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它们共同构成了悲剧苦难的原因,也因此成为恐惧与怜悯的对象。在单个悲剧的观赏中,恐惧与怜悯的对象可以是悲剧人物或我们自己,也可以是弑父或乱伦等行动,但总体而言,总会有个如亚氏所言之人因过错而陷于“不应遭受”的厄运而引发我们的怜悯,同时,也会让我们从情节中察觉到命运与人的对立而产生恐惧——这样表述是否矛盾,抑或悲剧本身就是个矛盾体? “悲剧总是充满了矛盾,使人觉得它难以把握。”[22]185
过错与命运的纠结,是否显示了悲剧的特性——有如《雷雨》中极端的爱与恨?
悲剧有别于宗教或哲学,它并不探寻人类的终极答案,而往往在神秘的哀静中落幕,这是否显现了悲剧的精神——犹如“尾声”中幽远的音乐?
“悲剧把让人类最重要之事显露出来作为其目的,但由于人类最重要之事本质上是不可见的,”[8]15这是否隐喻了悲剧的悖论——如同曹禺当时模糊的憧憬?
四
从《诗学》看《雷雨》,亦即以《雷雨》证《诗学》。《诗学》理论能帮助我们解释《雷雨》情节布局的奥秘,而《雷雨》的实际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诗学》理论的理解。重读《雷雨》可以发现,《雷雨》属亚氏所言之“最好的悲剧”,曹禺即亚氏所称之悲剧诗人,他具有悲剧诗人的激情与品性,悲剧理念与亚氏也高度吻合。尽管在《雷雨》之后,曹禺认为它太像戏而在此后的创作中试图加以改变,以期超越,但事实上,后来的剧作没有一部能超越此剧,为什么?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对悲剧的固有功能特性的认识以及对此功能特性的遵循。是写戏还是写人?是为展示性情而行动还是在行动中附带表现性情?古老的《诗学》能给我们一个遥远的启示。
曹禺强调《雷雨》 “是一首诗”,因为诗可以容纳下他的幻想,抑或是诗的幻想借用剧的形式表达?由此构成了“诗剧”或“剧诗”——这本身就与亚氏的理路是相通的,只不过曹禺的表述兴许更基于其当年那诗般幻想的灵魂。他试图通过时装剧的形式演绎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故事,传递出从远古走来的苦难。为此,他不惜承受长度的困扰,效仿希腊悲剧的“进场歌”与“合唱歌”的功能,苦心孤诣地编排《序幕》及《尾声》,呈现出与正剧截然不同的氛围,兴许就寄寓了这样的深意:给观众一种“辽远”的距离感,使得情节中所传递的思想因此更为可信与清晰,抑或是以沉静的反思与正剧中经历的情感激荡形成互为补充的有机关联——注重观剧的效果,并由观剧而触发“人生的思索”,进而提升人的趣味或教养,正是亚氏悲剧的题中之义。
《雷雨》不仅是用来观的更是应该拿来读的。剧中深刻的悲剧内涵与复杂的人性生态很难用有限的舞台行动来演绎。唯靠重读才能使这些隐藏的东西明晰起来,重获对人物行为的同情性理解。雷雨成功的原因在此,局限与易遭误解之处也在此。此类宜读之作,显然对诗人的情节安排能力和思想内涵有更高的要求。亚氏就曾说过,“这一办法也显出诗人的才能更高明”。[8]42但是否真能做到“不论阅读或看戏,悲剧都能给我们很鲜明的印象”,[8]105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个“悲剧形式”问题,更是个接受的问题。时代语境往往会制约这本该传达的鲜明印象——那几十年来吸附在《雷雨》身上的尘云或微粒,就是明证。
为什么最好的戏剧是悲剧?因为它探寻的是人类的灵魂,摹仿的是人类的行动,展示的是人类的命运。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了解人类自己,还能陶冶并提升我们的德性。它是属于全人类的,不应该仅仅适宜于西方的土壤。由此似可反思我们戏剧创作的生态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是只能谈谈《雷雨》?因为它是中国现代戏剧中唯一一部真正体现悲剧精神的作品,是受西方悲剧理论浇灌而仅存的一颗硕果—— 《雷雨》过后再无《雷雨》。
[1]甘阳,刘小枫,等. 古典西学在中国[J]. 开放时代,2009 (1):5.
[2]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M]. 黄灿然,李桂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5.
[3]丁涛. 戏剧三人行――重读曹禺、田汉、郭沫若[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13-73.
[4]热奈特. 广义文本之导论[M]. 热奈特. 热奈特论文集.史忠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2.
[5]哈里维尔. 《诗学》的背景[M]. 刘小枫,陈少明. 诗学解诂. 陈陌,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42.
[6]刘小枫. 论诗术中篇义疏·中译本前言[M]. 阿威罗伊.论诗术中篇义疏. 巴特沃斯,英译. 刘舒,中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3.
[7]哈里维尔. 《诗学》的背景[M]. 刘小枫,陈少明. 诗学解诂. 陈陌,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67 -71.
[8]亚里士多德. 诗学[M]. 罗念生,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14.
[9]戴维斯《诗学》微[M]. 刘小枫,陈少明. 诗学解诂.陈陌,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6.
[10]查特曼. 逆向叙述[M]. 唐伟胜. 叙事:中国版第二辑.刘丹,译.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63.
[11]伯恩斯. 《〈诗学〉管窥》[A]. 王旭东译. 刘小枫、陈少明主编《诗学解诂》.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0.
[12]曹禺. 《雷雨》[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71.
[13]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M]. 张隆溪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91.
[14]曹禺. 《雷雨》日译本序[M]. 曹禺. 悲剧的精神. 张靖,译.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6:13-14.
——对《物理学》8.6(259b1- 20)的一种解读
——“自由落体”教学中的物理学史辨
——《古希腊文化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一课的教学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