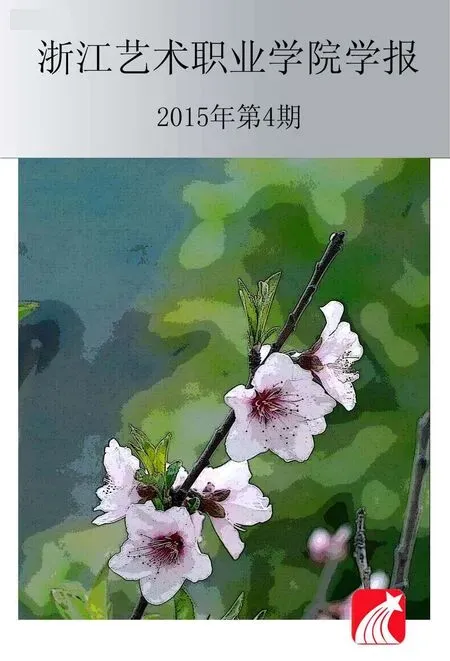论清代戏曲尊体观*
张晓兰
论清代戏曲尊体观*
张晓兰
清人有着明确的戏曲尊体意识。他们反对视戏曲为小道,并且努力将戏曲纳入雅文学的轨道,使戏曲在审美标准、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方面向雅文学靠拢,进而又从各个角度推尊曲体,以提高戏曲的地位。但清人努力推尊曲体,消弭戏曲同诗词文的区别,使得戏曲进一步雅化和案头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戏曲生命力的衰减。
清代戏曲;诗教;雅化;尊体
一、曲非小道
戏曲自诞生之日起,即居于传统文化之下层,不为文人学士所尊。有感于此,历代曲家和曲论家力争使戏曲获得与诗词文乃至经史同等的地位,以获得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明代王学左派的代表李贽即具有很强的戏曲尊体意识,他说:“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也,更说甚么《六经》,更说甚么《语》、《孟》乎?”[1]认为各种文体没有尊卑之别。
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认为戏曲“可以合君臣之节,可以浃父子之恩,可以增长幼之睦,可以动夫妇之欢,可以发宾友之仪,可以释怨毒之结,可以已愁愦之疾,可以浑庸鄙之好……人有此声,家有此道,疫疠不作,天下和平。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2]高度赞扬戏曲为“名教之至乐”。
而清人的戏曲尊体意识尤为明显,他们极力反对视戏曲为“小道”。李渔《闲情偶寄》言:
施耐庵之《水浒》、王实甫之《西厢》’世人尽作戏文、小说看。金圣叹特标其名曰“五才子书”、“六才子书”者’其意何居?盖愤天下之小视其道’不知为古今来绝大文章’故作此等惊人语以标其目。[3]28
李渔在这里声援金圣叹将《水浒》、《西厢》视为“古今绝大文章”的观点。
冯家桢《四韵事》叙曰:“扬子云曰:‘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甚矣,莽大夫之言陋也,盖神龙能伸亦能屈,鹍鸟能高亦能下。……嗟乎!声歌一道,好之为之,皆出寻常,顾可以小技忽乎哉。”[4]955
尤侗亦曰:“而一二俗人,乃以俳优小技目之,不亦异乎?”[5]348
王士禛认为杂剧:“激昂慷慨,可使风云变色,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6]
以上诸人均热情歌颂戏曲的功能和美学品格,将戏曲视作天地之至文,反对以小道视之。
另外一些较为传统的观点,则认为戏曲即使为小道,但也不能轻忽,因戏曲自有其精奥之处。如叶元清《修正增补梨园原》序曰:“呜呼!戏曲小道,精奥乃尔,可轻视乎?”[4]173
郑士毅《红情言》叙曰:“所谓其歌有思,其哭有怀,嬉笑怒骂之间,大都有所激发而作。虽卑事侪俗,以全神及之,选韵发声,必陈言之务去。风云金石,心手天然。雕虫小技,壮夫为之,盖亦大有不侔者也。”[4]1441
戴全德《辋川乐事》、《新调思春》自序曰:“虽雕虫小技,大雅弗尚,而世态人情,颇有谈言微中者。”[4]1103
二、安肯轻提南董笔’替人儿女写相思
有感于戏曲自诞生以来,即其体不尊的现实,各个时期的曲家和曲论家都积极反思其原因。明末曲论家祁彪佳曾言及其原因,较中肯綮,他说:
特后世为曲者’多出于宣邪导淫’为正教者少’故学士大夫遂有讳曲而不道者。且其为辞也’可演之台上’不可置之案头’故谭文家言’有谓词不如诗而曲不如词者’此皆不善为曲之过’而非曲之咎也。[4]2745
他指出戏曲不为“学士大夫”即学者所尊的原因在于后世所作的戏曲多出于宣邪导淫,为正教者少。而不为“谭文家”即文人所尊的原因在于戏曲只能演之台上,不能置之案头。因此,戏曲要想达到尊体的目的,也正是要在这两个方面努力。即从内容和形式上极力向诗词文等正统文学靠拢,回归于雅文学的传统。有鉴于此,清人反对戏曲写男女风情,宣淫导邪,主张戏曲描写忠孝节义的内容,有益风化,羽翼名教;反对戏曲奇幻夸张,主张温柔敦厚;反对戏曲语言鄙俗,主张戏曲文辞典雅。
1.反对儿女风情,主张伦理教化
清人认为元明的戏曲大多以描写儿女风情为主,有伤风化,因而地位不尊。而赞扬同时代人的作品能够描写忠孝节义的内容,羽翼名教。如耿维祜《祷河冰》谱序曰:
今之填词’古之乐府也。有声有调’被之管弦’可以歌颂太平’羽翼名教’关系者甚大。第自元人以降’虽名作如林’大都风云月露’以摹写儿女闺情为能事’风俗人心’贻害不浅’予尝为天下有才者惜之。南昌罗君小隐’雅人也。年甫弱冠’能文章’兼通音律’爱谈气节’常诵其乡蒋清容太史“不肯轻提南董笔’替人儿女写相思”之句。[4]1139
杨悫《吟风阁杂剧》序曰:
词曲之名起于宋’盛于元。胜国以后’文人学士’相继而作’其脍炙人口’传之优孟衣冠者’大抵言情居多’或致有伤风化。求其激昂慷慨’使人感动兴起’以羽翼名教’殆不可得。吟风阁者’悫伯祖笠湖公著书之室也。公严气正性’学道爱人’从宦豫蜀’郡邑俎豆’为学人’为循吏’著作甚富。公余之暇’复取古人忠孝节义足以动天地泣鬼神者’传之金石’播之笙歌’假伶伦之声容’阐圣贤之风教’因事立义’不主故常’务使闻者动心’观者泣下’铿锵鼓舞’凄入心脾’立懦顽廉’而不自觉。刻成’因以吟风阁名之。以是知公之用心良苦’公之劝世良切也。[4]977
清人认为,戏曲只要出之有道,就能够于世道有补,有益风化,可为儒教辅臣。如杜陵睿水生《祭皋陶》弁语曰:“杂剧院本,词家之支流也。然出之有道,要不为无益于世。……故杂剧之效,能使草野闾巷之民,亦知慕君子而恶小人,此庄士之所不废也。”[4]930杨恩寿《词余丛话》:“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古乐不作久矣。……今要民俗返朴还淳,取今之戏本,将妖淫词调删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晓,无意中感发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7]250
2.戏曲应温柔敦厚,反映诗教
此外,清人提倡戏曲内容应合乎诗教,李东阳《钧天乐》序曰:“至于元人杂剧,半属淫哇,近代传奇,尚臻风雅。关、郑、白之外,间有名篇。施、高、汤、沈之余,讵多妍唱,求其怨而不怒,质而有文,续正始之音,合无邪之旨者,诚难数觏也。”[7]250李东阳认为,元、明、清三代戏曲有着根本的不同,元代多“半属淫哇”、即为市井风情之剧,为艺人之曲。明代戏曲“近代传奇,尚臻风雅”,较元代有进步,为风雅之体,仅属文人之曲。这些都不是他心目中戏曲的标准。李认为真正的戏曲应能符合儒家的诗教传统,即求其“怨而不怒,质而有文,续正始之音,合无邪之旨。”怨而不怒要求戏曲表达的感情,平和,适度,符合中庸之道。“质而有文”出自《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要求戏曲文辞文质相称。“正始之音”指纯正的乐声,非邪声,非靡靡之音。《晋书·卫玠传》:“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8]“无邪之旨”出自《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以上均指戏曲要符合儒家诗教、思想纯正。
3.主张戏曲文辞雅化
清人主张戏曲文辞的雅化,即戏曲不但能演之场上,且能置于文人案头,以入“谭文家”眼。孙岱曾《蟾宫操》序认为,戏曲为“古歌风体”,地位崇高,尤贵雅驯,他说:
传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词曲为古歌风体’尤贵雅驯。今登场演剧’非不粲然可观’及索其墨本’则捐之反走。盖照谱填写’与歌工之上尺乙四何异?徒费笔墨耳。[4]1452
在对戏曲的内容和形式按照雅文学的标准进行了自己的重建之后,清人进而又从各个角度来推尊曲体,以使戏曲的地位能够与正统文学相同。
三、清代戏曲错位尊体论
清代戏曲的错位尊体论主要表现在将戏曲比附经史、诗文等位置较尊的文体,以提高戏曲的地位。
1.以戏曲比附经史
为了推尊曲体,清人喜以戏曲比附六经,尤其是《诗》与《乐》,因为中国古代一贯是经学本位主义,经学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最高位置。一旦与经学相比附,戏曲就不言而喻获得了较高的地位,因此清人从各个角度以戏曲来比附六经。
清人认为戏曲功能合于六经。如清儒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曰:“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戏者,此性天中之《诗》与《乐》也,未有不看小说听说书者,此性天中之《书》与《春秋》也。未有不信占卜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与《礼》也。”[9]此是以人之好娱乐之天性与六经之功能相等同,肯定戏曲小说的重要性。
认为戏曲之旨与六经之旨相同。孔尚任《桃花扇》传奇“小引”曰:“传奇虽小道,……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于是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4]1601朱亦东为王懋昭《三星圆》所作序曰:“传奇非小技,以文言道俗情,约六经之旨而成者也。”[4]2062
认为戏曲的创作方法具有六经的特点。如查昌甡《惺斋五种曲》总跋曰:“甡等窃谓物极则反,遇穷必通,填词虽小技,其华藻也似乎《诗》,其变化也似乎《易》,其典重也似乎《书》,其谨恪也似乎《礼》,其予夺进退也似乎《春秋》,有元一代人文,皆从此而造物。”[4]1744
清代曲家还以孔子删诗、不废郑卫之音的理论比附戏曲即使有抒发男女之情的内容,也不应被禁止,而应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李调元《雨村曲话》自序:“予辑《曲话》甫成,客有谓予曰:‘词,诗之余;曲,词之余。大抵皆深闺、永巷、春伤、秋怨之语,岂须眉学士所宜有?况夫雕肾琢肝,纤新淫荡,亦非鼓吹之盛事也,子何为而刺刺不休也?'予应之曰:‘唯,然。然独不见夫尼山删《诗》,不废《郑》、《卫》;鞧轩采风,必及下里乎?夫曲之为道也,达乎情而止乎礼义者也。'”[4]166邹绮《杂剧三集》跋:“自有天地,即有元音。而其言情者,则莫过乎诗。诗《三百篇》,不删《郑》、《卫》。”[4]467
此外清人还以孔子对“艺”的肯定,肯定戏曲存在的合理性。《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阳货》:“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借用以上两则儒家关于“艺”的肯定,清代曲论家论证了戏曲存在的合理性。钱酉山《绣刻西厢》自序:“昔圣人言,心性之功,而终之于游于艺。盖以艺虽末务,而沉潜反复,亦足以发天真之趣,而适性情之安。自六经四子之书垂训而外,而琴瑟诗歌以及博弈,音乐嬉戏之事,古人一一创之,流播人间。学者苟能留心寻绎,则其中之曲折原委,自可通神达化,而其诣因之益纯,而其养因之益密。谁谓典谟经传,呫哔讴吟,把卷兀坐,死煞句下,而遂可云学者哉?……呜呼!天下情文交至者,孰如《西厢》?况游戏神通,为两教之妙用,而游艺功夫,又吾儒之精义耶?”[4]703
刘熙载《艺概》序云:“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各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10]他指出“艺即道”,艺“根极于道”,这样将儒家传统“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的观念进行了修改,将艺与道相等同,提高了艺的地位。因此,他的《艺概》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六种,也寓含着将六种相提并论之意思。这样就将长期被视为小道的词曲的地位大幅度提升。
2.诗词曲同源异体
清代曲论家不但从社会功能和艺术风貌上论证戏曲与诗词文相等同,而且从戏曲的本体上探索戏曲与诗词的关系,认为诗词曲都是音乐文学,源头相同,都是起源于古代的声歌。中国古代的诗体文学的发展轨迹是:上古的歌谣→诗经→楚辞→乐府→诗→词→曲。而且“诗亡而有词,词亡而有曲”或“词为诗余,曲为词余”,这是声歌进化所致。诗词曲一脉相承,没有高下之分,没有雅俗之别,没有贵贱之限。如此合理自然地将曲纳入诗词的范畴,与诗词相等同,彻底打破了诗词曲之间的界域,提升了戏曲的地位,这是戏曲“尊体”观得以实现的最重要的证据与手段。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当时的许多文人都是这样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比附戏曲与诗歌的关系,极力将戏曲纳入到正统文学观念认可的诗词系统,借确立戏曲与传统诗词文的同源同质并且同构的亲缘关系来提升戏曲的地位。”[11]
其实,这一方法也并非清人首创,明人即多有论述,如王士贞《曲藻》自序曰:“曲者,词之变。自金、元入主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4]31
明爱莲道人《鸳鸯绦记》叙曰:“词曲,非小道也。溯所由来,《庚歌》、《五子》,寔为鼻祖,渐变而之《三百》、之《骚》、《辨》、之《河西》、之《十九首》、之郊祀铙歌诸曲,又变而之唐之近体、竹枝、杨枝、清平诸词。夫凡此,犹诗也,而业已曰曲,曰词矣。于是又变而之宋之填词,元之剧曲。至于今而操觚之士,举汉魏以降,胜国以往诸歌、诗、词、曲之可以被弦索者,而总谓之曰乐府。盖诚有见于上下数千年间,同一人物,同一性情,同一音声,而其变也,调变而体不变,体变而意未始变也。而世有訾词曲为风雅罪人,闻曼声而掩耳,望俳场而却步者,吁可悲已。”[4]1380
这一观点到了清代得到了集中的论述,众多清人论述诗词曲同源异体的问题。如钱谦益《眉山秀》题词曰:
自三百篇亡’而后《骚》赋继之。然以之入乐’则节奏未谐。于是《白苎》《子夜》’始为滥觞。然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因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又有南曲’递沿递变。[4]1470
李渔《闲情偶寄》:
由是观之’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3]8
易道人《洛神庙》序:
原夫风雅一变而《离骚》’再变而赋’三变而乐府、古诗’四变而近体’五变而诗余’六变而传奇。[4]1672
民国时代吴梅犹持此种论调,在其《六也曲谱》叙中曰:“盖音声之道,随时势为变迁,汉铙吹兴而诗废,乐府兴而铙吹废,齐梁杂曲兴而乐府废,梨园教坊兴而杂曲废,词兴而教坊废,北曲兴而词废,迨南曲兴而北曲已失其真矣,此变迁之显者也。”[4]191
3.戏曲比附八股时文
清人从戏曲的结构和创作方法上比附八股时文,认为二者有类似之处。八股时文是明清两代士子的进身之阶,地位不低,如此戏曲的地位也相应得到提升,如钱梅溪《题曲目新编》后以杂剧传奇中各剧比附时文中的“八集”:
昔金坛、王罕皆太史’选时艺以训士子’谓之“八集”。八集者何?启蒙、式法、行机、精诣、参变、大观、老境、别情之谓也。试以传奇、杂剧证之:如《佳期》、《学堂》’启蒙也;《规奴》、《盘夫》’式法也;《青门》、《瑶台》’行机也;《寻梦》、《叫画》’精诣也;《扫秦》、《走雨》’参变也;《十面》、《单刀》’大观也;《开眼》、《上路》、《花婆》老境也;《番儿》、《惨睹》、《长亭》’别情也。余以为成宏、正嘉搭题、割裂可废也’而传奇不可废也;淫词、艳曲、小调、新腔可废也’而杂剧不可废也。[4]178
刘师培在其《论文杂记》中也全面考证了“八比文”同戏曲结构的相似之处,他说:
明人袭宋元八比之体’用以取士’律以曲剧’虽有有韵无韵之分’然实曲剧之变体也。如破题小讲’犹曲剧之有引子也;提比、中比、后比’犹曲剧之有套数也;领题、出题、段落’犹曲剧之有宾白也;而描摹口角’以逼肖为能’尤与曲剧相符。乃习之既久’遂诩为代圣贤立言。然金元曲剧之中’其推为正旦者’曷尝非忠臣、孝子、贞夫、义妇耶?故曲剧者’又八比之先导也。古人既以传奇曲剧为进身之媒’则后世以八比为取士之用者’曷足异乎?故知八比之出于曲剧’即知八比之文’皆俳优之文矣。
乃近数百年之间’视八比为至尊’而视曲剧为至卑’谓非一代之功令使之然耶?昔王维奏《郁轮袍》以进身’颇为正直所鄙。明代以降’士人咸凭八比以进身’是趋天下之人而尽为王维也’噫!(注:八比一体’当附入曲剧之后。)[12]
他将戏曲与八股文并列,认为“八比”即八股文或“时文”为戏曲的变体,它们在结构、刻画人物形象、代圣贤立言、和社会功能上完全一致,都是元明清时代的科举进身之阶,反对“视八比为至尊,而视戏曲为至卑”,认为“八比一体,当附入曲剧之后”。这种观点,堪为宏论。
4.戏曲比附西方话剧
中国戏曲地位长期低下,而清末之后打开国门,国人发现同属戏剧体的西方戏剧在其国中处于一流文学的地位,而中国戏曲则截然相反,因而致力于推尊曲体。正如朱自清所言:“中国文学史里,小说和戏剧一直不曾登大雅之堂,士大夫始终只当它们是消遣的玩意儿,不是一本正经。小说戏剧一直不曾脱去俗气,也就是平民气。等到民国初年,我们的现代化的运动开始,知识阶级渐渐形成,他们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接受了欧洲的影响,也接受了‘欧洲文学的主干'的小说和戏剧,小说戏剧这才堂堂正正的成为中国文学。”[13]狄平子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亦曰:
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必以小说家居第一’吾骇焉。吾昔见日人有著《世界百杰传》者’以施耐庵与释迦、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吾骇焉。吾昔见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者’吾益骇焉。继而思之’何骇之有欤?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苟其有之’则小说家之位置’顾可等闲视哉?[14]
亦是受欧洲文学观念中视小说戏曲为最上乘文学之影响,高度推尊小说戏曲之地位。
四、清代戏曲本位尊体论
所谓本位尊体论,即是从戏曲的本质特性上论证戏曲相对其他文体的优胜之处,其论证角度与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点:
1.代有所胜
“代有所胜”是将元曲视为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并与汉赋、唐诗、宋词相媲美,高度推崇了元曲与戏曲。“代有所胜”的观点由来已久,最早如元罗宗信《中原音韵·序》:
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学唐诗者’为其中律也;学宋词者’止依其字数而填之耳;学今之乐府’则不然。儒者每薄之’愚谓:迂阔庸腐之资无能也’非薄之也;必若通儒俊才’乃能造其妙。……此其所以难于宋词也。[4]13
明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曰:
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擅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4]31
清儒焦循明确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他在《易余龠录》中说:
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所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15]
王国维继承了焦循“代有所胜”的观点,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其《宋元戏曲史》自序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至此,唐诗、宋词、元曲便成为并驾齐驱的一代之文学。
2.曲别是一家
清人主张戏曲或曲体的独立性,主张诗词曲有别。如丁野鹤《赤松游·题辞》曰:
唐称乐府’宋称诗余’元称词曲’一渐而分’深浅各别’若使诗余再用乐府’则仍涉唐音’若听词曲再拈诗余’则不为元调。故同一意也诗余必出以尖新’同一语也元曲必求其稳贴。要使登场扮戏’原非取异工文’必令声调谐和’俗雅感动’堂上之高客解颐’堂下之侍儿鼓掌。观侠则雄心血动’话别则泪眼流涕。乃制曲之本意也。[4]1528
认为诗词曲各有本色,诗的风格是高华、庄严,词的风格是妩媚、尖新,而曲的风格是佻达、稳贴,风格不同,不能互相侵犯,互相混淆。
3.曲为“众体之最优”
清人论证作曲难于作诗词文,非高才博学者不能为,从创作的难易程度上否定戏曲较诗词文卑下的观点。尤侗《名词选胜·序》曰:
由诗入词’由词入曲’正如风起青苹’必盛于土囊’水发滥觞’必极于覆舟’势使然也’而说者断欲判而三之’不亦固乎。且今之人’往往高谈诗而卑视曲’词在季孟之间’予独谓能为曲者方能为词’能为词者方能为诗。[5]350
杨恩寿《续词余丛话》曰:
填词诚足乐矣’而其搜索枯肠’捻断吟髭’其苦其万倍于诗文者。[16]
黄周星《制曲枝语》曰:
诗降而为词’词降而为曲’名为愈趋愈下’实则愈趋愈难。何也?诗律宽而词律严’若曲则倍严矣。[4]1488
4.曲易传播
清人认为戏曲较传统诗文具有雅俗共赏、易于传播之社会功效,也因此比诗词文赋乃至经史更容易达到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社会功效。从这一角度言,戏曲理应受到更多重视,更加值得大力提倡。黄周星《人天乐·自序》曰:
少陵云:“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况词曲又文章中之卑卑不足数者。然果出文人之手’则传者十常八九。试观王实甫、高东嘉之戏剧’妇孺辈皆能言之’而名公巨卿之鸿编大集’或毕世不入经生之目’则其它可知矣。虽词曲一道’其难十倍于诗文’而欲求流传近远’断断非此不可。此仆之传奇所为作也。[4]1487
俞樾为余莲村《劝善杂剧》所作序曰:
天下之物最易动人耳目者’最易入人之心。是故老师巨儒’坐皋比而讲学’不如里巷歌谣之感人深也;官府教令’张布于通衢’不如院本平话之移人速也。君子观于此’可以得化民成俗之道矣。《管子》曰:“论卑易行。”此莲村余君所以有《劝善杂剧》之作也。[4]2264
这种观点也是继承明人而来,如傅五峰《义贞记·序》曰:
尝慨伦常贞义之事’载在诗歌’传诸史册’文人学士虽曰为讲诵’而颛孟之启迪’未能家至于而户喻之也。一经优孟登场’声情入目’愚夫愚妇辄为感激涕零’喜谈乐道。声乐之足以动人观感者’何其捷而易哉!夫若是则秦倡侏儒’笑言合道’未始非风教之一助也。[4]1877
杨彝珍《理灵坡·叙》曰:
盖谓世俗不可与庄语’若欲正襟而谈’则听之匪欲卧’即掩耳而走。不如取往事之可歌可泣者’以南北曲谱之’一唱三叹’有遗音焉。直与律吕’应其宫徵。足令读者讽讽乎心动而情移。[4]2401
5.戏曲改良社会
清末戏曲改良思潮呼声很高,当时的曲学界大力强调戏曲作用的重要,要求提高戏曲的社会地位。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曰:
而南都乐部’独于黑暗世界’灼然放一线之光明:翠羽明珰’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召还祖国之魂;美洲三色之旌旗’其飘飘出现于梨园革命军乎!……今以《霓裳羽衣》之曲’演玉树铜驼之史’凡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慆淫’烈士遗民之忠荩’皆绘声写影’倾筐倒箧而出之;华夷之辨既明’报复之谋斯起’其影响捷矣。[17]
陈独秀在署名“三爱”的《论戏曲》一文中曰:
‘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所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耳’苟其入之’则人之思想权未有不握于演戏曲者之手矣。……由是观之’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惟戏曲改良’则可感动全社会’虽聋得见’虽盲可闻’诚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也。[18]
这是从戏曲改良社会的功能角度要求提高戏曲的地位。
除了从“错位尊体”和“本位尊体”两个角度论证曲体之尊,清人还从创作实践上推尊曲体,表现在一些曲家能够严肃为文,非率尔下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阅十余年之久,凡三易稿而成,自是精心结撰。”[4]1609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也指出了这一特点:“万树之词才,足与孔尚任翱翔;其曲律可比洪昇,能兼二者之长者也,然而其曲不见脍炙于人口,后日歌场中即一出亦不见流行,何耶?盖《长生殿》、《桃花扇》皆十数年中,三易稿而成,然如万树之《风流棒》,不半月而成云,则万氏之作,概一任才气,一气呵成,未经深深推敲者,此或即不蒙鉴赏于后人之一原因欤?”[19]
此外,清代朴学盛行,戏曲学术化特色鲜明,清代学者尤其是一些著名的大儒如王夫之、凌廷堪、焦循、俞樾、王国维等参与戏曲创作或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戏曲的学术品格,为清代戏曲尊体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余 论
戏曲尊体论由来已久,可以说,戏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戏曲的尊体史。戏曲的尊体意识到了明代,已经凸现。明人也从各个角度,推尊戏曲。但这种愿望的真正实现,则是到了清代。这与明清人推尊戏曲的方式不同有关。明人侧重于从本位尊体角度推尊戏曲,强调戏曲的个性,即“本色当行”方面,主张曲体的灏烂、通俗的一面,反而使曲体愈为正统文人所不屑。又由于明代学风的空疏和社会风气的风流自赏,明人“十部传奇九相思”,内容多写“男女风月,传悲欢离合际遇”,使得戏曲愈加远离雅文学的标准,因而与他们推尊曲体的愿望适得其反。相对于明人的本位尊体论,清人在错位尊体论方面成就更突出。清人较少强调戏曲的本色当行,多是用戏曲比附经史,比附诗词文。为了推尊戏曲,消弭戏曲和诗词文之间的差距,使得戏曲在社会功能上与诗词文等同,这样的方法使得戏曲尊体意识得到了实现,但最终却造成了曲体本体性的衰减。因此,清人一味取消曲体同诗词文之间的差别,也就使戏曲失去了自身的生命力,导致了清代中后期“雅部衰落,花部兴起”的局面。
[1]李贽.焚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6.
[2]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M]//汤显祖全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1188.
[3]李渔.闲情偶寄[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4]蔡毅.中国古典戏曲序跋汇编[M].济南:齐鲁书社,1989.
[5]吴毓华.中国古典戏曲序跋集[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6]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M]//王士祯.池北偶谈(外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639.
[7]杨恩寿.词余丛话[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8]房玄龄,褚遂良.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067.
[9]刘献廷.广阳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106-107.
[10]刘熙载.艺概序[M]//刘熙载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49.
[11]杜桂萍.清初杂剧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4.
[12]刘师培.论文杂记[M].//申叔先生遗书:第二十册.宁武南氏校印本,1936:19.
[13]朱自清.闻一多先生怎样走着中国文学的道路:《闻一多全集》序[M]//论雅俗共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9.
[14]狄平子.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M]//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27-28.
[15]焦循.易余龠录[M]//丛书集成续编:91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463.
[16]杨恩寿.续词余丛话[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九.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304.
[17]柳亚子.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M]//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175-176.
[18]三爱.论戏曲[M]//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52-55.
[19][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M].王古鲁,译北京:中华书局,1954:396-397.
(责任编辑:周立波)
On Respect for Drama in the Qing Dynasty
ZHANG Xiaolan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have a clear consciousness of respect for drama.They opposed to view drama as the entertainment,and tried to include drama into the elegant literature.They make drama follow the standard of elegant literature in aspects of aesthetic standard,ideological content and social function,and propose the respect for drama in all ways to improve the status of drama.But the effort eliminat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rama and poems,makes drama more refined and like a text,which cause a certain degree of decay of vitality.
drama in the Qing dynasty;poetry education;elegance;respect
J802
A
2015-10-12
张晓兰(1979— ),女,甘肃民勤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南京21009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甘肃省图书馆所藏清代戏曲抄本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BZW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