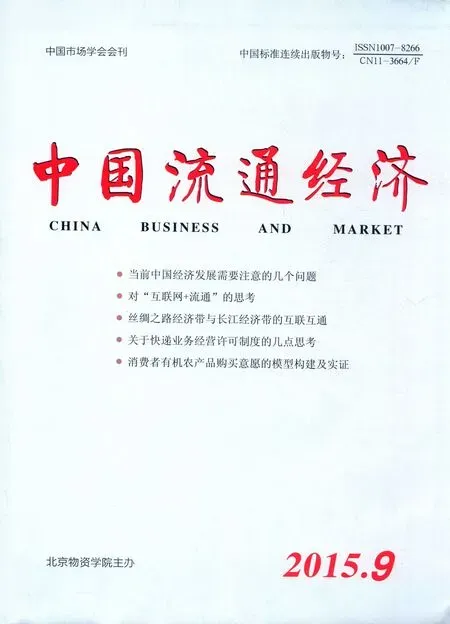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市100871)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厉以宁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市100871)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新常态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当前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实现中高速增长有两个重要条件,即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第二,找到经济下行的真正原因,然后对症下药;第三,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第四,高利率未必能抑制通货膨胀;第五,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企业要千方百计让产品增加新功能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走出国门,打开新的市场,创造新的市场;第六,要重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人”视角,而不能单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考虑问题;第七,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进行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第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国有资产增值更多。
新常态;结构调整;创新;互联网+;第三种调节
一、我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的两个重要条件
关于中国经济下一阶段如何发展,首先要从“新常态”谈起。
对于新常态,我们应该正确认识。“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就会违背市场规律。比如,前些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持续的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也不能够持久。正因如此,我们转入中高速增长,比较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带来五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资源过度消耗;二是生态恶化;三是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四是普遍低效;五是为了促进高速增长而错过了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千方百计从技术创新中寻找未来经济发展之路,而我们则因忙于高速增长而错过了最佳时机,这是我们要认真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新常态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我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一般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速度在6%~7%的区间属于中高速增长。实际上,中高速增长同样不容易,并非转入中高速增长期就真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因为它需要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经济结构调整;二是创新。没有创新,没有结构调整,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找到经济下行的真正原因
当前,我们遇到了经济下行的压力。首先要分析下行压力是如何形成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该怎么办?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再想办法找出对策。
第一,现在不是增长率本身的问题,而是增长速度放慢的问题。同时也要看到,要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代价过大,如近期出现的产能过剩、低效率等问题,就是前几年高速增长过程中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再加上其间很多地方产能过剩等多种因素叠加所产生的后遗症。产能过剩的最大问题,一是造成过度消耗;二是浪费了资源。前几年的超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浪费资源的增长、无效率的增长。
第二,从经济学角度讲,经济稳步增长要看基数是越来越大还是越来越小。目前我国经济的基数与10年前相比(更不要说与20年前相比)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每增长1%难度都很大,而且不可持续,它将会是一个递减的过程。所以说,前几年的高速增长实际上给今天的继续增长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第三,国际市场不稳定带来若干问题。这种不稳定对我国出口和对外贸易造成了一些不利影响,我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与国际经济形势是有关系的。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在高科技产品方面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二是东南亚国家在低端产品方面是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东南亚国家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比我国低,但工资水平低,劳动力便宜。
第四,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要扭转局面困难重重。为什么?结构调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已经形成这么多过度投资,要真正扭转过来并非易事。结构调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也要明白这也会带来损失,但能不能承受、能不能坚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充分认识到结构调整的艰巨性,如果不坚持下去就会前功尽弃。
第五,技术创新问题。技术创新不能急于求成,一个能真正占领市场的技术创新需要经过多年积累。比如深圳的华为公司,它并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就冒出来的,而是一天一天、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走到现在可能已经进入守成期,但还要继续创新,不能止步。
目前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意义重大。我国互联网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正在探索,以后互联网会把我们推到什么地方去,这是经济学界也难以预测的,但可以肯定,这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互联网的作用是巨大的,呈现出很多新技术,可以让结构调整变得更为顺利,但是否能拉动经济发展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正因如此,我们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还是要坚持两点:一是结构调整,结构调整这一关非过不可;二是技术创新,要走群众创新创业的道路。对此,思想要坚定,思路要清晰,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也不要老调重弹,经济的大起大落没有好处,因此,还要进行宏观调控,而且应将重点放在定向调控上,定向调控就是结构性调控,要重视微调和预调,才能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
三、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
高投资未必带来高就业,这是我们遇到的新问题,因此需要我们转变观念。过去一直讲新的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经济增长率高,新出现的工作岗位就多。这在过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那时我国经济还在比较低的层次上运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是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经济增长,而且是通过高科技实现发展。因此,在当前,就业问题不是靠大量投资就可以解决的。
最近我在一家企业考察时,企业负责人介绍说他们进行了大量投资,我问能增加多少就业,他的回答很简单:一个都不增加,还得裁员。为什么?因为现在的投资和过去不一样,技术创新的投资是完全现代化的,比如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效率提高了,但不增加就业,年龄大的工人被重新安排,有的就此退休,年轻职工要进行再培训,新聘员工首先必须是一个技术工人,这就和以前大不一样。
我也问过其他企业负责人,当前的就业问题怎么解决。他们也认为不能靠高投资来解决,而是要把民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民间有创业的积极性,让他们创业,创业增加就业。还有就是把企业很多部门分散开来,一个部门就是一个创新单位。现在很多人的观念都有所改变,就是从农村出来的劳动力,也不像过去那样出去就单纯为了打工,而是首先学习技术,掌握技术以后就可以适应更多地方更多需求,也可以创业(包括回家创业)。民间存在着极大的创业积极性,这就是中国未来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有人预测,20年以后一般企业根本不需要写字楼,因为职员完全可以在自己家里办公,所以我们对就业的观念需要改变。总之,这意味着解决就业未必靠高投资。当然,尽管技术在改进,但适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加强人力资源培训的投资还是需要的。
四、高利率未必能抑制通货膨胀
高利率未必能够抑制通货膨胀,这也是一个新的观点。
传统观念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投资太多、消费太旺等原因导致需求过大而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用紧缩的办法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了滞胀,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另一方面是失业,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按照传统的凯恩斯理论,总需求大了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总需求小了就会出现失业,因此通货膨胀和失业不可能并存。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找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为什么会出现滞胀。主流经济学家说,实际上,当时经济出现了两种垄断力量。一种垄断力量是工会,工会认为自身能够控制工人的行动,坚持工资必须是刚性的,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如果下降就罢工。但同时,经济上还有另一种垄断力量——跨国公司,跨国公司认为自身可以控制价格,所以坚持价格刚性,也是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宁愿将产品销毁掉也不能降价。两种刚性同时存在,于是经济生活中就出现类似小孩子玩的“跳背”游戏那样的现象。主流经济学家主张去按住小孩,如果两只手把两个小孩全按住,那工资和物价就都跳不起来。这完全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但尼克松居然接受了,实行了“新经济政策”,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工资冻结、物价管制措施。后来搞不下去了,尼克松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也就夭折了。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接受了供给学派的观点,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供给,供给有问题才出现这样的结果。只有通过技术创新生产更多新产品,由此形成的创新成果带动经济增长。于是美国从80年代以后经济摆脱了停滞状态,通货膨胀问题也得到解决。
这就告诉我们一定不能短视。今天的通货膨胀,就是投资过多、需求过大造成的,该投资的就得投资,银行该降低利率就要降低利率,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新经济。“钱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为此在浙江专门考察过好几座城市,发现这不是货币供应不足,因为货币M1和货币M2的供应量都很大,“钱荒”的原因主要是贷款难。银行认为民营企业靠不住,如果贷款收不回来就成了大问题,所以找国有大企业贷款,找信得过的国家独资企业贷款。可是这些被银行看好的国有企业并不需要那么多钱,贷款利率又比较低,于是就将贷来的资金转放出去。民营企业贷不到款,就找国有企业分借一部分,并承担高利息,也有很多企业负责人贷不到款就求助于自己的亲友。在浙江流行一句话,叫“现金为王”,即企业最重要的就是把现金拿在手里,有了现金就有了一切,资金链不会断,产业链会顺畅,有投资机会就能下手。每家企业都有超正常的现金储备,结果就是现金储备量增大。所以虽然M1、M2不少,但资金还是紧张。这告诉我们,以后如果发生通货膨胀,一定要多方面考虑,紧缩信贷在新形势下不一定管用。
五、市场是可以创造的
“市场是可以创造的”,这是一个新的命题,任何行业都应该懂得这一点。我在河北沧州考察时去了肃宁县,肃宁以做裘皮生意为主。有些人说,现在生意不好做,以前裘皮主要卖到俄罗斯,但如今卢布的购买力下降,所以肃宁裘皮即使比欧洲裘皮便宜得多俄罗斯人也不买。我向他们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让产品更加个性化”,因为当前的消费和几十年前不一样,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90年代末都属于排浪式消费,赶时髦,现在则不然,是个性化消费;二是“让服务更加人性化”,让顾客的购物体验更愉快;三是树立中国品牌,“把产品品牌打到国外去”,树品牌要靠长期高质量的产品,目前中国产品的品牌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四是“把顾客留在国内”,如果国内能够买到质量好的马桶盖,人们又怎么会到日本去买呢?把顾客留在国内,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自由贸易区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我经常给研究生讲这样一个案例:一家生产木梳的企业招了4个推销员,让他们各带一批样品和订单到指定的寺庙向和尚推销木梳,结果却大不相同。第一个推销员一把也没有卖掉,因为和尚说:光头不需要梳子。第二个推销员跟和尚们说,梳子除了梳头之外还有其他功能,如刮头皮、止痒、活血、明目、清脑、养颜美容等,于是卖出几十把。第三个推销员观察到庙里香客很多,香火很旺,但香客们拜佛磕完头后头发有点乱,有时香灰还会掉到头发上,于是他就去找方丈,说庙里香火旺,香客这么热情,寺庙应该多关心他们,在每个佛堂前面放几把梳子,让他们感觉到寺庙很关心他们,替他们着想,他们就会来得更多更勤,方丈同意了,于是他卖出几百把。第四个推销员直接找方丈聊天,说寺庙出去办事时有公共关系要打通,公关就需要有礼品,而木头梳子正是最好的礼品,在木梳的一面刻上庙里最出名的对联,在木梳的另一面刻上“佛在心中”“积善为本”等字样,把它变成寺庙的名片。于是他一下子就卖出去几千把木梳。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产品功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这就是新功能。企业要把产品打出去,走出国门,一定要让产品增加新功能,一定要让产品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这样才能打开新的市场,创造新的市场。
六、要重视“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人”视角
以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中谈到的都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就是说人是从最低成本、最大收益考虑的,所以一定要符合最低成本和最大收益原则。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的。但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只有“经济人假设”显然是不全面的、不够的,“社会人假设”渐渐抬头。“社会人假设”就是指人不完全从“经济人”角度考虑问题,也会从“社会人”角度考虑问题。
比如,有A和B两个地方都可以进行投资,在A地投资利润高,成本小;在B地投资利润不如A地大,成本却比A地高。如果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人们都会选择在A地投资。实际上,偏偏有人愿意在B地投资。为什么?也许会有各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B地是我的故乡,我已经发展起来了,可故乡还那么穷,因此我愿意在那里投资办厂,解决家乡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从故乡的角度出发。还有人可能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从小在那里生活过,在那里上学、工作时,很多人瞧不起我,认为我没出息。离开那里创业之后,现在有了成绩,我就回来办一个大企业,让你们看看我是不是你们当初想的那么没有出息,我要改变你们过去的成见和对我的看法。”还有人是因为过去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做过一些对不起当地人的事情,包括犯过错误等,后来感到内疚、后悔,所以在创业成功之后就在那里办个工厂,以弥补过去所犯的错误。
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今天进入“互联网+”时代,人们更多地会从“社会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的情形越来越有限了。
七、重视“第三种调节”——文化调节
“第三种调节”,就是通过道德力量进行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过去讲的第一种调节是市场调节,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靠市场规律进行调节。后来有了第二种调节即政府调节。政府调节是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调节,用法律、法规和政策来调节。那么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呢?要知道,市场的出现是在几千年前,出现了商品交换,才产生了市场。政府调节的出现更晚,是有了国家和政府以后才产生的。人类在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出现之前,主要靠道德力量进行调节。有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后,道德调节也在发挥作用。常言道:“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发生小动乱,乡下人到城里投靠亲友,认为城里比较安全,所以小乱居城。大乱居乡是指发生大动乱时城里人都往乡下跑。大乱时,市场是失灵的,政府是瘫痪的,但人类社会还是延续下来了,社会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没有市场不要紧,没有政府也不要紧,还有道德力量在发挥作用,在进行调节。
因此,我们要重视第三种调节,即通过道德力量来进行调节,也就是文化调节。文化调节是指每个人都自律,每个人都遵守公共规则。社区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等,都在促进人们加强自律。这对今后社会经济发展很有好处。
八、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国有资产增值更多
多年以来,经济学中研究的生产效率就是投入产出之比:投入不变,产出增加,生产效率提高;假定产出不变,投入减少,生产效率也会提高。所以生产效率是很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学中出现了第二种效率,叫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前提是:假定投入既定,对配置方式进行调节,就会出现不一样的效果。比如,同样的资源,用A方式配置,产生N效率,用B方式配置则产生N+1效率。于是两种效率并存。生产效率的重点在于微观领域内的企业管理、生产部门管理;资源配置效率的重点则在宏观方面,即如何使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因此,今后要更加重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要让国有资产配置得更好,效率更高,增值更多。
九、结语
实际上,关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其变化远远超过预期;二是急剧变化而且是加速度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预料到30年或50年以后的经济是什么样子,比如,那时还有没有蓝领和白领的区别?大家都在计算机旁工作,分得清谁是白领谁是蓝领?还有,货币的用处还有多大?人们都用信用卡了,谁身上还带货币?企业的规模会不会变得很小?还有人会买汽车吗?人们还像现在这样早上赶去上班,傍晚赶着下班回家吗?很多都是我们今天想不到的。但是,想不到也要想,因为经济生活中的许多重大变化最早往往就是异想天开引发的,经过努力,异想天开最终成为事实。所以说,每个人都在学习的阶段,每个人都在探索的阶段。
*本文系作者2015年6月13日在“2015中国互联网+创新大会·河北峰会”上的演讲,发表时已经作者审阅。
责任编辑:林英泽
The Issues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I Yining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China’s economy is entering the new normal.“The new normal”means operating according to economic laws;and one of the demonstrations of new normal is the medium-high-level economic growth rate.At present,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such issues:first,there are two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realizing the medium-high-level economic growth rate,namely th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innovation;second,we should find out the real reasons for economic downturn,and implement the appropriate measurement;third,high employment is not the necessary result of high investment;fourth,high interest rate can not definit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inflation;fifth,market can be created,and the enterprises should do their best to attach their product with more new functions to meet the consumers’new requirements,take part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enter more new markets and create more new markets;sixth,in considering problems,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angle of“social people”in the era of“internet plus”,but not only the“assumption of economic people”;seventh,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the third adjustment”,namely the adjustment through moral forces(cultural adjustment);and eighth,we shoul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realize the higher level of state-owned asset appreciation.
new normal;restructuring;innovation;internet plus;the third adjustment
F120.4
A
1007-8266(2015)09-0001-05
厉以宁(1930-),男,江苏省仪征市人,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民营经济研究院院长、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等职,曾任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思想史等领域的研究,在对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经济运行实践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非均衡经济理论,并运用这一理论解释了中国的经济运行,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从中国经济改革之初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国经济的构想,并对“转型”进行理论探讨,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孙冶方经济学奖”“金三角”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个人最高奖)、第十五届福冈亚洲文化奖——学术研究奖(日本)等,主要代表作有《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