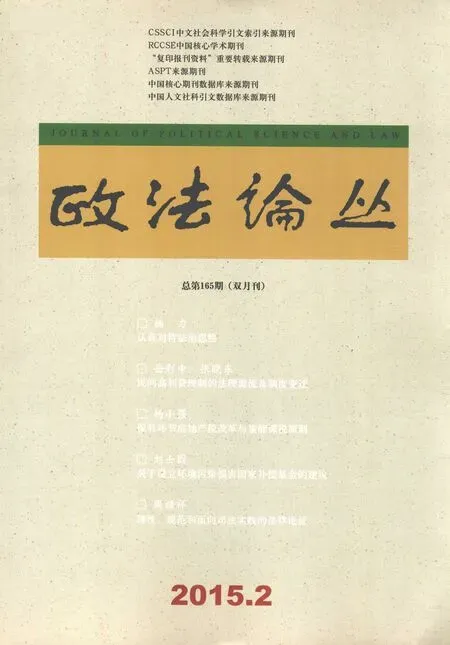认真对待法治思维
杨 力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认真对待法治思维
杨 力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上海 200030)
现实中推动法治建设的当下中国,是一个伴随着持续深化改革而带来的经济和社会转型,以及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多元利益日益趋于差异化、复杂化的“风险社会”。新一轮法治思维的主要取向在于,进一步以良法祛除非法、非份、非常权力,乃至更为彻底地根治制度特权的流弊,藉此撬动国家治理方式逐步走向现代化。而良法的实现基石,就是更多地借助于程序来达成共识,不断确立以法权为中心和寻求法权最大化的法治理念定位,以及相应推动宪法立法适用和宪法监督适用之类的程序性制度创新。与此同时,还应在行政和司法的体系化改革上有所作为,特别是指向以“限制和约束政府公权力”为导向的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让司法通过渐次规范抵牾的整合作业、研磨解释技术和以调解等法律的弹性化方式,来应对风险社会日益生长的分歧和不确定性。此外,削弱制度特权的切入点,乃是从制度设计上减少特权的种类和范围,以及反向借助于制度之维强化社会对权力和特权现象的有效监督,以更好实现良法善治。
法治思维 风险社会 程序正义 制度特权
一、法治建设面临的制度性风险
在我国从邓小平时代的“民主与法制并重”,江泽民时代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胡锦涛时代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到当今习近平时代的“法治中国”,持续性地不断迈向法治已成强音。与之相生的是,世界也正在经历分化和重组的巨变,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代这么重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城市开发、人口流动等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变迁,正在产生越来越多的“人为风险”。这类风险带有明显的决定者与受决定者相分裂、相对抗的特征,对公共事务决策的方式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且势必导致法治范式的转换。所以,风险社会语境中修订法治范式的探讨,必须与面对宪政的恰当判断、公共治理的方式创新以及司法逻辑的重新梳理等密切结合在一起,才可能获得根本性的突破。
毋庸置疑,随着当代中国社会在结构壁垒、体制转型和地位资源含量等方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往整体性相对明显的格局日益走向多元化,已经成为深刻描述社会结构变化的主流。从制度发展的视角来看,这种变化带来了边界清晰的多元利益和问题解决的去中心趋向,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制度上的“公法软法化”及“私法社会化”。不过,相伴而来的利益相对固定的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流动阶层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增强,以及突发公共性的群体事件冲突的概率升级提高等,倒逼了整体的制度安排需要更加关注如何合理分配资源及更高质量实现公平正义,使得“良法善治”意义上的制度设计及其运作需要更进一步的反思和创新。
事实和经验表明,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分化产生的这些问题已有所扩散,而且可能产生结构性破坏,甚至还会在某种程度上超出预警和事后处理能力,因此将之称为贝克意义上的制度化“风险社会”并不过分。换句话说,虽然中国社会的整体制度性安排日益发达,几乎覆盖社会的所有领域,但当现实社会结构分化及冲突所造成的不确定风险来临时,现有的制度资源供应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够既具合法性又有正当性地给予有效应对。更为令人关注的是,当下中国的风险社会对初始微小扰动具有很大的敏感性,印刻上了混沌系统的特征,不少情境里一些貌似偶然却有内在规律的“假随机性”带来的蝴蝶效应,可能还会让危害结果意料之外地持续放大而变得更为严重,甚至难以收拾。很显然,中国如何应对这种风险社会带来的变化,尤其是越来越多地质疑立法或行政决策的正当根据是什么,旨在消解群体冲突的公共选择又怎样进行,以及启动归责机制的因素到底如何确定等,实际上成为了法治中国建设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面对制度性的社会风险,目前理论和实务界讨论较多的是宪政体制下的规范重构、新程序主义的机制更新、刑事政策的趋于宽和以及普遍法制中的地方包容等。毫无疑问,聚焦于制度、政策或司法上的这些主题,都体现出很强的现代反思性,共同期待的是推动制度或机制上的深刻变革。然而,日益受到不断分化的阶层或不同群体之间多方面因素引起的平行或上下流动,以及客观、认同及行动阶层和群体交互错位等因素的影响,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分化后的风险往往难以准确锁定,甚或常规的控制标准已难以把握,乃至风险的散布结果还会经常发生变化,客观上使得制度或机制的设计对于不同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责任认定以及结合情境的考量,变得相较以往更加难以有效计算,随之的风险机率也连续增大而更难控制。进一步的悖论在于,风险社会中推动国家治理方式走向法治化的整体制度因为较难避免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又使得规则模糊、歧义和漏洞的情形时有出现,更加推波助澜地造成何为良法善治这一问题经常性地遭受诘难,比如,涉讼信访的不断加剧就是注脚。
可见,风险社会带来的分歧和不确定性,让法治建设里的中国在法治变革各个环节上不同程度地出现失灵。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跳出以往传统的闭环法治思维窠臼,更为积极地尝试沿着开放的法治化路线去破解。
二、新一轮法治思维的主要取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体委员会聚焦依法治国议题还是首次。不过面对以上的社会风险、研究短板以及制度悖论,亟待更新思路后的新一轮法治思维的主要取向又是什么?
应该中肯承认的是,即使当下中国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人治中国”仍遗留着相当明显的痕迹。而“法治中国”的提出,其意义不仅是吹响了以法治之道,祛除非法、非份、非常权力,乃至根治制度特权之流弊的号角,更加是以全党的最高决策文件这种背书形式,正式向惯性极大的、以人治为轴的传统治理方式发起重大挑战。毕竟“无论是以当代中国数十年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为参照系,还是以现代世界国家治理的基本趋势为参照系,由人治走向法治都是一种合乎规律顺乎民心的选择。”[1]从这个意义上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意味着它是中国的改革步入深水区和推动国家治理方式走向现代化的不二选项。因为围绕市场经济建设向纵深切入,“国家治理在战略上涉及两条道路的抉择: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则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本位主义道路前行,最终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2]
新一届政府的改革雄心已经显现,就像具有改革走向深水区标志性意义的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以及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蛇口和珠海横琴新区三个片区入选广东自贸区,它们在法治构建上的直接意义,即在于让地方政府开始决心以更大开放,倒逼现行的行政体制进行改革,借助类似权力的清单制订,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解决政府支配资源权力过大等问题,试图把直接控制经济的全能型政府逐步改造成为提供公共服务的服务型政府。进一步从法治落实的视角来看,这场指向了伤筯动骨的改革,必然也会更为深层地依赖于涉及地方立法权版图扩张、政府条块权力合理配置,以及推动垂直化司法改革等一系列重大命题的“积极”而“审慎”的突破。毕竟一方面,步伐不大,会让那些寻租中的既得利益者借口法律保守的惯性思维,轻易阻断这一路径;另一方面,缺少稳健,又会遭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们的质疑。
毫无疑问,迈向深水区的改革,以法治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和走向现代化,必然荆棘密布、任重而道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深刻认识到,试图实现善治的首要前提,就是拥有应视为治国之重器的“良法”。而作为新一轮法治思维的核心理念,良法的实现剑指国家权力的适度限缩。除了浅表意义运作机制上的行政决策程序、拟定权力正面清单等一系列创新,更为根本的是要在理念和实体上推动依宪治国和执政,真正把宪法当成党和人民双方意志的浓缩形态,坚持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形成一个以宪法为顶点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及由此进一步构建出整合化的秩序。尤其是改变“某种被放任的自由”而导致的执政者举棋不定的状态,改善“制度之中习惯于还有土制度”的几乎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的潜规则体系,以及避免政出多门、争权诿责所产生的法律秩序不统一的状态。
当然,基于当下中国所处风险社会的分歧和不确定性,这种以宪法为顶点的新秩序整合,短时间内或过渡阶段依然有赖于“主权者的决断”,这又势必会遭遇权力过度集中的指责,以及加剧结构性腐败的危险。于是,逻辑的延长线便转换为,应该对极其强大的主权者意志加以约束,通过行为规范、程序和根据个人权利的各种追诉活动,把权力关到制度的笼子里,这才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日常状态”。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治理的“日常状态”的本质特征是,绝对不能容许任何个人或团体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并以此撕裂规范之网和纵容吞舟之鱼。清晰了这一法治思维的新取向后,进一步规范和约束政府的公权力的格局性举措,便是改变权力配置的法律多元化格局,以法律一元化合理地配置权力资源,但又绝不是贸然推动权力的多元化,而是在坚持单一制的前提下引导“从法律多元、权力一元,到法律一元、权力多元”。[3]P7惟有如此,才能建构起一个泛化意义上的法律共同体,才能树立起一个丝丝入扣、层层相洽的法律体系,以及比较彻底地在思想、制度以及行为等不同层面贯彻规范性的基本原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还要在前述的当局者的决断与普遍遵循的规范之间,达成符合实际情况的平衡。为此,除了限缩权力为导向的行政裁量权恰当行使,还依赖于作为社会正义底线救济的司法改革进一步深化,为法律专业者的裁判保留一定的弹性空间,既防止权力的滥用,又坚守治理的理性。很显然,深化司法改革的取向,即应树立起一种融化在互惠关系中的权威,不仅要强化司法对行政的合法性审查权力,以更有效地防止包括民主制内在的“多数派专制”,[4]P45而且要以拉德布鲁赫提出的著名的“不能忍受公式”,①缓释法律与道德之间可能出现的内在紧张。那么,融化在互惠关系中的“权威”又如何建立起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除了以往着眼于裁判和机制上的修修补补,更为关键的是需从根本上推动司法体制上的改革。其实当下这一波司法改革的主要特征,就是改由中央主导及统筹规划,把影响司法公正的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问题放在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框架内,以破除司法地方化、行政化来抵消弹性司法带来的负面效应,借此重新树立司法权威。当然,为了“去地方化”尝试推动的省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关系和复杂的部门利益,甚至还遭遇上下级司法机构之间,因为原来地方财政支持力度差别,所带来的既得利益者不愿被改革一刀切而让利益受损的内部阻力;“去行政化”上类似深圳福田式的“审判长负责制”,以及上海闵行检察院的“主任检察官制”改革,初步解决了“谁都在办案、谁都不负责”的问题同时,又是否能够比较彻底地摒弃行政力量肆意干预而导致的司法权威不振这一痼疾,仍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还应注重削弱制度上的既定特权。当下中国的不少部门和地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特权,它们以一种“集体理性”的方式,构成了所谓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又以制度的面目,堂而皇之地助长全社会的权力崇拜,以及侵蚀着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往人们更多针对和指责的,都是那种游离于制度之外的缺少监督和约束的法外特权,而忽视了制度以内的特权所带来的危害。制度之内的特权是由长期以来的官僚等级体制,以及由权力、身份和财富所决定的超公民权力,其不少是以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为设置的初衷,堂皇地纳入制度来锁定。一旦这种非常权力被制度加以确认后,由于缺少足够的合理性,以及较少受到制度的监督和制约,因而极易被特权的享有者超越边界地加以运用,必须加以抵制并逐渐削弱。不过削弱制度特权,既要有极为严密的顶层制度设计,让权力在既定的范围和轨道上运行,又要及时根据情况变化,适时增加新制度和完善旧制度,此外还需要形成对特权行使的有效监督机制。不过,那种针对制度特权的过于理想化的“革命式改造”,通常不会有太多积极效果,而且很可能是无果而终,甚至搞不好还会走向反面。所以,以法治之道把制度特权限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应当是改革的目标,它需要在更大推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把创造机会均等作为基本策略。
简单地说,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最为核心的法治思维取向就是如何处理好两个范畴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法律与宪法的关系。比如,全国人大和国务院虽然已被赋予违宪审查权,但从未真正落地行使过一次,而实际当下中国法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不少涉及违宪,因此,应勇于为推动善法善治有所作为,而不是听任法律体系中的问题出现,一味采取“鸵鸟政策”;二是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个中的三味要义是不能轻易以改革为借口,随意挑战和突破法律的底线。其中尤其是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依法执政,尤其是把国家法律体系与党内规则衔接起来,不能出现只是为个别领导人服务的“反法治”现象。
三、法治思维的程序基石及良法向度
法治建设的中国特色之一就是,需要认真对待利益分化的现实社会结构。事实上,风险社会中的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相应地,法治的发展又是否应当选择走向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抑或法团主义?无疑,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已是客观事实,因而如何对多元化的不同诉求进行协调,必定将是以后实现法治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整体制度设计的基本课题。“实现法治民主的关键是,让立法这样一种最典型的公共事务的决定充分反映民意,并非把民意直接编织到执法活动之中,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以局部的民意修改整体的民意。”[5]P8
基于这一格局,为了对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进行公正而有效的协调,法律程序的意义势必得到更进一步的强调。比如,立法的第三方评估和听证,行政决策程序的立法设计、权力的正面清单梳理、政府内部监督的常态化、任意干涉司法裁判的留痕、严防刑事上的冤假错案、司法与行政管辖的分离等。事实上,以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诉讼案件表明,法律程序已经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的竞技场,或者说是调节不同利益的核心装置。“现代国家的法治可以通过程序正义来消弭实质性价值判断的相异所引起的反抗,为决定提供各方承认的正当性;可以通过权利的认定和保障,来防止多数派专制对公民平等、自由的伤害。”[6]P56因此,所谓结构的组合最优化,实际上是以中国社会的关系性为前提、以法律程序为核心、以利益民主主义为动力的。显然,程序正义也就是契约的非契约性因素,“这种意义上的法治包括公平、面向未来以及普遍性、平等适用和确定性等品质”。[7]P152
正是出于这一共识,开放的新法治思维有赖于对法律程序的整体制度性设计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梳理和归纳,从而为有效地进行风险控制提供具有制度上创新意义的对策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首当其冲的是,需从理念定位上讨论法治应以法权为中心,以及寻求法权最大化的制度创新定位。当代风险社会中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制度创新,首要的就是从根本上明确法权是人民权利的法定部分。从法律角度看,法权的体现者在专制制度下通常是君主;在民主制度下则是国民通过由其选举产生的代表制定的法律。所谓立法,就是确认和分配法权、规范法权的运用程序的活动;实施法律,则是具体实现法权、落实法权最大化的要求的程序性活动。法权中心主义主张以有利于实现法权最大化为基点、按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优化法权结构,维持权利与权力的相对平衡。法权中心主义主张实现法权平衡地、可持续地增长,外在的问题式表现就是:妥善地解决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联系与区别、差异与矛盾;三者的统一是否又是与生俱来的;三者的统一到底是有条件的还是无条件的?如果是无条件的,那如何解释不统一的现象,如果是有条件的,条件有哪些;人大制度在“三个统一”中处于何种地位,在实现“三个统一”过程中,人大又应发挥什么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等。解决这一问题之道,主要是进行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实施、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制度方案设计。正如以上所提及的,迈向改革深水区的中国社会由于日益增多的风险因素而出现了不少法律失灵的现象,于是,引入司法违宪审查的“宪法司法化”论调又开始浮出水面。毋宁说,现行宪法从来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可以将之作为裁判依据合法地适用,所以,鼓励“宪法司法化”不仅无助于促进宪法适用,还会妨碍中国宪法适用体制的完善和宪法适用效能的提升。当然,法院审理案件援引宪法与“宪法司法化”没有必然联系,而法院审理案件未援引宪法也并不表明其行为一定不具有“宪法司法化”性质,对于法院援引宪法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此,消解“宪法司法化”的关键在于强化宪法立法适用,落实宪法监督适用,甚至人民法院对宪法做遵守性援用或说理式援引还能在相当程度上促进宪法实施,以维护宪法的权威。
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探讨宪法立法适用和宪法监督适用的程序性制度创新。
一方面,宪法本身已供应了许多有效的监督适用条款,只是因为权力机关面对风险社会中遭遇的重大特定问题时,惯性奉行“鸵鸟政策”而长期闲置。比如,可以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对于类似已蔓延到权力顶层的腐败,激活和设立“人大调查权”,将之作为制度化反腐、法治反腐的治本制度化安排。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特别调查委员会,配以强化《宪法》第67条、第73条等条款已赋予权力机构的质询权、监督权的协同运用。其显著的优势在于,这些权力的行使依据宪法可以不受违法行为本身的限制,同样不受刑事司法程序上的诉讼时效和无罪推定原则的限制,更不受个案限制,因而能够更充分地保障公民知情权。
另一方面,宪法的立法适用在应对风险社会时也同样值得圈点和制度创新。比如,审慎地考虑“预算人大”的制度设计,即贯彻和加强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职能,进而有步骤地把各级人大转化成主要对税收、拨款、津贴以及财政再分配的预算进行实质性审议的公开论坛。换句话说,也就是实施“财税民主”。这样的财税民主不妨首先从直观性较强、与群众利害的相关性也较强的地方开始,自下而上逐步推行。推行预算人大的做法,不仅要改变各级人大的工作重点,而且还必须改变其活动方式和成员构成。通过预算人大的制度设计,可以很好地把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整备以及治理方式的转换有机结合起来,也可以很好地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衔接起来,还有利于各种利益群体和政治势力在编制和审议单纯的财政预算的程序中学会妥协的技巧,逐步提高人民代表从事政策竞争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正是预算人大专业性较强,可以促进围绕权衡不同利益的理性对话,因而能够避免民粹主义、“均富”、外交等容易情绪化的争点成为政治的基本对抗轴,造成民主政治在还不太成熟的初期就夭折。很显然,这一制度设计方案的基本特征,是让代议制的讨论范围尽量限定于那些在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涉及公平分配的租税和财政事务,而暂时对其他政治性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非政治化的冷却处理,即所谓搁置争议,留待在今后的适当时候去解决。
四、程序性的行政和司法改革思维逻辑
以“限制和约束政府公权力”为导向的新行政管理制度格局,无疑是实现以程序公正为基石的法治要义之一,因为“法治在政治美德方面有其独立的价值”。[8]P3-6其中的核心问题在于:当下中国实施风险管理的对象,是以政府为主导、整个社会的相关主体共同参与而形成的公共治理网络,而这种网络又与法治之间存在一种反比例的互动。一般而言,关系的距离越短、网络化的程度越高,往往法治介入的余地就越小。因此,法治语境下的行政管理,通常就不得不在这两者对应的不同治理方式之间进行甄选。一种是借助物理性地撕破、截断和拆除关系网络,使政府的触角长驱直入伸张到家庭和社区之中进行控制,从而贯彻落实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命令;还有一种方式是借助符号操纵及利用关系网络来形成国家秩序,把“类”组织机制纳入法治进程之中,在按照普遍规范制约社会性权力的同时,让它与政府公权力之间达成适当的均衡。
不辄于此,问题的进一步聚焦指向了亟待明确在这个网络里,担负行政法上相应责任的主体到底包括哪些,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以及在此基础上,风险管制又如何能把防范、预警和处理三个主要环节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一个高效的、呼应快捷的治理链。当然,风险管制的决策或多或少地隐含有知识上的不确定性,即便专家出谋划策仍然难以避免风险的“万一”发生,抑或难以避免风险处理的迟滞。因此,到底如何在行政决策程序上设计构造出专家与公众交融性的商谈性场合,既不同于专家决策又不同于简单的公众参与,进而使得风险管制决策能够更好地适应风险社会的情境。不过硬币的另一面是,政府风险管制的执法绝对不是严格形式法治主义的,否则,无法灵活地应对突发的风险;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离法治缰绳的。
除了正面的行政决策程序问题,还有反面的风险管制的行政和政治责任的承担问题。对这两种责任的研究,可以结合行政系统内部对风险管制的监控,以及代表机关对风险管制的监控。因为风险管制往往同时涉及几个部门,风险发生导致损害后,经常会发生相互推诿的情形。另外,风险管制中的知识不确定性,又似乎让行政/政治责任的承担者蒙受了一定的“冤屈”。因而,如何通过有效的行政系统内部/代表机关的监控,在监控主体、监控手段、行政/政治责任的“归责原则”、行政/政治责任的形式等方面进行特殊的安排,便成为需要深入认真研究的问题。
此外,以上所有制度创新之维的新行政管理格局,无疑都离不开信息公开的程序设计,目的是为了防止制度创新的实施“南辕北辙”。毕竟信息公开已是对政府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要求,但风险管制过程中的信息,相比较其它政府信息有着明显的难得性(难以收集)、零碎性(相对于作出风险判断所需的信息量而言许多信息是零碎的)、分散性(在不同管制环节上存在)、不确定性(因为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危险性(信息对市场、社会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等特点。所以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面对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如何做到信息共享、协调,如何建立常规的信息公开机制和应急的信息公开机制,两者之间如何紧密衔接,以及又如何做到准确、及时公布信息,才是符合信息公开的法治要求的。
平行的另一个核心领域是当下令人瞩目的司法改革动向。可以说,以关系网络为特征的中国社会早已融入更多风险性的新司法逻辑及相应制度的更新。现代司法制度以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为基本宗旨,因此,在把个人解放出来之后,司法权的抬头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对社会现状的实证分析表明,在中国这样“关系本位”的国度里,析出的个人并不接近原子形态,也不同于以社群、集体为前提的“鸟笼个人主义”,而是更为显著地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关系性存在”,亦即个人通过不断定义自己和他者之间的各种关系而参与社会秩序的建构。因此,尽管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以及单位体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传统以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以社区为依托的人际关系的内涵,但中国司法改革的逻辑基础能否简单地以个人自由为前提,还是会不断受到来自不同角度的质疑。
实际上,中国法律秩序和审判制度的存在方式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一方面,不得不通过规范的刚性约束力来缩减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流动的局势要求临机应变的决断,使得规范的约束力不得不相对化。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宣告形成,但这是一个多元的、充满张力的结构。“中国特色”意味着本土特殊性,与法律体系内在的普遍性指向和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使命之间其实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社会主义”包含着非市场、非个人自由的契机,与作为现代法律体系之基础的“人格”概念也是方凿圆枘。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旷日经久的民法典编纂一直难以竣工。何况“法律体系”必须具有一定的闭合性,否则就无法保证形式理性和规范效力,而强调“情·理·法”的差异化、组织机制的中国特色以及大民主与强权力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因素,则具有极强的开放性。这样的紧张关系,从围绕三个诉讼法修改的激烈争论中可以略见端倪。
显而易见,实用主义的司法必须拥有“一种可行的普遍价值框架”。[9]P543因此,熨平制度的皱褶、消除规范抵牾的整合作业,除了继续加强立法功能,更重要的是把着力点转移到司法、特别是研磨解释技术上来,在处理个案的过程中不断弥合条文和事实之间的裂缝、填补权利的空白、在一个刚性的基本法律框架中不断应用专业技能进行微调并创造具体的政策和法理。不过令人警惕的的是,当下中国司法系统的现状却在不守底线地加大开放性和弹性,使得法律体系固有的自我完结、自我准据的特征几乎消失殆尽,结果是越来越加重“权大于法”的痼疾。
同时,以同情的态度来分析这种特殊现象背后的逻辑,即可以发现所谓“大调解”方式的导入,是为了换一种法律的弹性化方式来应对社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转型期社会的各种矛盾激化之际,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合法性与非法性的界限也暧昧不清,根据既定的规范进行黑白分明的判断变得比较困难,调解和妥协的确是有助于化解审判尴尬的。另外,具有特定政治含义和行政色彩的“能动司法”口号的提出,也是为了应对回避诉讼、在体制外寻求救济的倾向,其动机或可理解。但是,过犹不及。面对现实,我们还是有必要追问一下,那些随兴所至、侵蚀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司法举措究竟能否达到预期目标、会不会带来更大的流弊,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五、程序以外的制度特权削弱
除了以现存制度为前提的程序性法治思维及改革向度,以法治之道削弱明显带有“人治”色彩的制度特权,乃是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实现“良法”和“善治”的整体性制度改革的重要条件。
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理念,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官僚等级体制,长期以来强化着中国君臣尊卑有序的格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等级制度的适用范围不仅没有缩减,甚至还有了版图扩张之嫌。如果说原来的等级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只是在“干部”中实行,那么现在则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不仅原来党政体系内的官衔和管辖延续存在着省管干部、市管干部、县管干部的分野,而且许多社会组织也开始被套用以官阶,于是有了部级高校、局级医院、副部级院士、师级歌星、厅级社团、处级和尚等称谓。”[10]当然,这种称谓背后实质上代表着所应享受的不同资源等级。即使同级干部都有着严格的座次顺序,毋宁说不同级干部更加有着不可逾越的排名和待遇。级别较高或排名靠前者往往可以倨傲地雄视普通人,享受着特权生活,乃至口含“天宪”,手握“真理”的话语权。
除了以上官本位等级体制的强大惯性,制度特权的另一个主要来源莫过于权力的不当或偏袒行使。比如,饱受质疑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源于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的缴费方式不同,民众的社保待遇被划分出若干的等级,而且,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城镇企业和农村等几个大块之外,各种碎片化的制度更是琳琅满目,形成了城市与农村分割、私人与公共部门分立的多种制度割剧状况,客观上导致不同等级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甚至是倍差式的社会保障标准。“等级化、多轨制、碎片化”实际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标签。尤其是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三个制度之间的养老退休金待遇差所导致的不和谐现象更是日趋突出,为广大民众所憎恶。政府机关作为既得利益者,长期享受着以制度加以固定化的优厚待遇,形成了一种比较典型的制度特权。
制度的特权还来源于身份和阶层的人为划定。以户籍制度为例,曾经作为资源计划配给工具的户籍制度,即使长久以来面临“歧视性”的口诛笔伐,却依然故我难以退出舞台,似乎在反复考验着国民的忍耐力和不得已的“自立”。这项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制度,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中国为了推动重工业领域的资本积累,藉此达到压低农产品价格和提高城市居民福祉待遇的目的而设立的。然而,这一制度让国家仅为拥有城市户口的人员分配财物,同时又限制着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其长期施行以来的根本负面效应是,人编制了户籍,户籍又反过来统治了人,恐怕这就是户籍制度的最大悲哀。城市和农民被横亘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为制度划分成不同阶层,以“统购”和“剪刀差”的不平等交易为特征,形成了农民必须服从体制的整体利益,并为体制的整体利益做出巨大牺牲。客观上讲,这就是一种制度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的特权,是结构性的扭曲和矛盾。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制度的特权还与财富的拥有紧密相关。其典范的样板,正如近年来中国政府掀起的类同反腐式的“苍蝇”、“老虎”一起打的高潮迭起的反垄断浪潮,以及国家发改委开出的一张张巨额罚单,剑锋所指正是那种利用制度赋予的垄断资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制度之内的特权行为。纵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诸如电信体制、电力体制和民航体制等等改革,其目的都在于削弱这种以垄断形式展现的制度特权。当然这些改革也或多或少取得了成效,比如电信体制改革由于打破了电信独家垄断,形成了移动、联通和电信等多家电信企业同台竞争的格局,导致电信价格不断下降及服务质量不断改善。当然即使到了今天,这一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特别是在铁路、石油等领域,彻底打破行政垄断这一制度特权,依然任重而道远。
很显然,上述这些完全由权力、身份和财富决定的超公民权利,由于缺少足够的合理性,进而加大了社会的风险性,必须加以抵制并逐渐削弱。换言之,制度特权需要最大程度地被削弱。因为这类制度之内特权的享有者,先天就相对占有更多的资源,且不少的占有方式悖于法理和公平,甚至涉嫌黑箱操作。很显然,他们都是通常所说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是群众广为诟病乃至痛恨的一类特权。这类特权表面上看似与权力、身份和财富相关,实则背后都有隐秘的制度支持。因此,现在执政党全面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需要重点下大力气削弱这类脱离群众的制度特权,借助于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更为彻底地把简陋的制度平等衍生的特权,关进以机会均等为核心的公平法治之笼,藉此削除特权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降低风险因素,以法治之道削弱制度特权,切入点就是从制度设计上减少特权的种类和范围,以及以制度之维强化社会对权力和特权现象的有效监督。一方面,顶层的制度设计需要尽可能严谨和缜密,以坚持公平公正合理有效的原则为“经”,以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条文为“纬”,为权力设置合理边界,防止制度设计不严密、前后不衔接、标准笼统泛化等不足,把权力的内容和边界加以精确和固化,使权力在既定的范围和轨道上运行,减少外溢的可能,以防止“牛栏关猫”。不仅亟待在很大范围内取消行政等级和特权待遇以及各种新生特权,而且就更为深刻的层面而言,需要大幅度地改革缺乏透明度的公共财政制度、权贵阴影下的人事任免制度、垄断性的国企资源和产品定价制度、官员独享优渥的等级化社会保障制度、仍带歧视性的城乡分割户籍制度等。另一方面,除了制度的顶层设计,制度的笼子能否关住特权,还在于是否能形成对特权的有效监督。比如,政务制度执行公开、健全巡视制度等多元化的有效监督方式,推动特权制度的改革,保证公共权力不被异化,反过来逼使制度之内的特权被限制在越来越狭窄的范围内,乃至终而沦为“被驱逐的劣币”。
无疑法治建设的中国模式,需要对不断变迁的、以关系网络为特征的风险社会有更为深刻反思意义的洞察力。其内在的理路就是,风险社会中的法治实现,必须放在开放、反思的制度创新过程之中,才能有效地、可接受地加以推动。
注释:
① 参见柯岚著:《拉德布鲁赫公式与告密者困境——重思拉德布鲁赫-哈特之争》,《政法论坛》,2009年第5期。
[1] 郑成良.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的关系[J].交大法学,2014,4.
[2] 吴敬链. 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识[N].社会科学报,2013-09-26(3).
[3] 季卫东.通向法治的道路:社会的多元化与权威体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4]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M].董果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 季卫东.通向法治的道路:社会的多元化与权威体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
[6]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伯光,林猛译.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7] [美]布雷恩·塔玛纳哈.论法治(2004年版本)[M].李桂林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8] [美]罗纳德·德沃金.论合法性与法治[A].许章润编.清华法学(第一辑)[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9] [美]肯尼斯·沃伦.政治体制中的行政法[M].王丛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0] 杨力.以法治之道削弱制度特权[J].法学,2014,7.
(责任编辑:唐艳秋)
Take Serious Attitude Towards the Thinking Method of Rule of Law
YangLi
(Koguan Law Schoo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As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the rule of law, the current reality of China is that it is a type of risky society that is upgrading b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whose different social community’s benefits tend to be diversified. A new round of law-based governance thinking method is oriented in the removal of illegal, presumption and abnormal privilege, even radically eradicate the regime privilege abuse, and finally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country’s governance. The corner stone of its implementation is to make consensus by procedure of the law, which most significant point embodied in the systematic reform of the legisl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judicature. Moreover, we need to emphasize the rule of law in order to weaken the regime privilege, so that the good law and governance could be better achieved.
law-based thinking; risky society; procedure justice; regime privilege
1002—6274(2015)02—003—08
杨力(1974-),男,江苏南京人,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社会学、企业法务。
DF0-05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