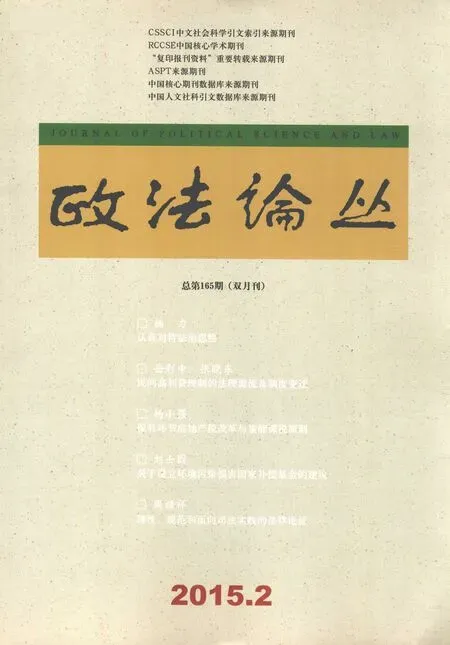见之于行事:梁启超宪法思想的液态属性
喻 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70)
见之于行事:梁启超宪法思想的液态属性
喻 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70)
从总体上说,梁启超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学者,他的宪法思想不是学术研究的结果,不能从体系化与本质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梁启超的宪法思想是对实践过程的表达,是宪法实践在梁启超心镜中的投射。因此,应当根据“见之于行事”的理路来看待梁启超的宪法思想。从19世纪末到1918年,在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段落里,梁启超在不同的时势背景下,分别强调了宪法的多个面相,这些随势赋形的宪法思想,是流淌的宪法思想,是梁启超“见之于行事”的思想结晶,具有鲜明的液态属性。
梁启超 宪法思想 本质主义 法学方法
关于梁启超的宪法思想,学界已经做出了比较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其中既有综合性的研究,①同时也不乏专题性的研究。②不过,无论是哪种取向的研究,都倾向于把梁启超的宪法思想或宪法理论做出某种本质主义的界定,即侧重于回答:梁启超的宪法思想是什么?但是,这样的回答恐怕并不符合梁启超的本意,亦不是理解梁启超宪法思想的有效路径。正如日本学者土屋英雄在论及梁启超的民权理论时所言:“从体系性的角度或从原典的比较的角度讨论梁启超在民权救国期的权利-自由论都是费解的。某种意义上说会让人莫名其妙。问题就在于:第一,梁启超的西方权利-自由论的摄取主要的是通过日本译文以及日本人的论著这一中介(日本式的变形)进行的。第二,梁启超摄取新的权利-自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系统地研究学问,而是要在实践的意义上寻找救国灵药,以充实其时代认识和亡命日本以前的思想理论。”③按照土屋英雄的观点,从体系性的角度讨论梁启超的“权利自由论”是不得要领的。同样,从体系性、本质主义的角度解读梁启超的宪法思想或宪法理论也会面临着相似的陷阱。因为,梁启超的宪法思想也像他的权利自由理论一样,也是他在实践过程中寻找救国灵药的产物,因此,还需要引入新的视角、新的理路、新的法学方法,对梁启超的宪法思想做出新的解释。
什么样的新视角、新理路才能更有效地揭示梁启超宪法思想的本真状态呢?对此,《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的一句孔子之言颇有借鉴的价值。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P944参照孔子的意见,以“见之于行事”的思维方式来审视梁启超的宪法思想,也许是比较恰切、妥帖的。因为,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梁启超在不同阶段、不同语境下反复致意的宪法,其实并没有一个定型化的指向,亦未得出一个本质性的结论。相反,梁启超的宪法思想可谓切玉削金,随势赋形,实为不断变迁的宪法情势在梁启超心镜上的投射,具有鲜明的“见之于行事”的液态属性。有鉴于此,本文且以“见之于行事”作为视角,以考察梁启超的液态宪法思想。就演进过程来看,从1899年到1918年,在大约20年左右的时间段落里,梁启超在不同的时势背景下,分别强调了面相各异的宪法,对于梁启超颇具液态属性的宪法思想,可以分述如下。
一、以议会为核心的宪法:来自孟德斯鸠的启示
梁启超关于宪法的集中论述始于1899年。此前,梁启超虽然也曾论及宪法领域内的相关问题,譬如议会、立法、变法等等,但是,关于宪法的专题论述,却暂付阙如。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于1898年9月流亡日本。“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2]P171在1899年的《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中,他述及自己思想视野的变迁:“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梁启超注意到,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吾中国之治西学者固微矣。其译出各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源之学,几无一书焉。”[2]P176从此,日文世界中质佳量大的思想论著,为梁启超打开了国内不曾有的思想视野,这就是1899年完成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的写作背景。
此文可以视为梁启超宪法思想的真正起点。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理解的宪法是以议会为中心的。他说:“宪法者英语称为Constitution,其义盖谓可为国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苟凡属国家之大典,无论其为专制政体(旧译为君主之国)、为立宪政体(旧译为君民共治之国)、为民主政体(旧译为民主之国),试皆可称为宪法。虽然,近日政治家之通称,惟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乃称为宪法,故今之所论述,亦从其狭义,惟就立宪政体之各国,取其宪法之异同,而比较之云尔。”[3]P318按照这段话,宪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宪法,见之于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无论什么样的国家,都有一个根本性的法律——亦即梁启超所谓的“国家之大典”,无论它是否成文,只要去寻找、总结、提炼,都能找到这样的“大典”。但是,对于这种广义的宪法概念,梁启超自己并不十分自信,因为他随即指出,按照1899年已经出现的很可能是日文世界中的“通称”,只有那些有议会的国家制定的“国典”,才能称为宪法。这种狭义的宪法概念,意味着宪法只属于有议会的国家;没有议会的国家,也就不可能有宪法。梁启超试图比较的各国宪法,也是狭义的宪法。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各国宪法的比较,主要涉及到“政体”(包括立宪君主国与共和国两类)、“行政立法司法之三权”、“国会之权力及选举议员之权利”、“君主及大统领之制与其权力”、“法律命令及预算”、“臣民之权利及义务”、“政府大臣之责任”等几个方面。这样的内容安排意味着:
第一,宪法应当对政体做出规定,要么规定立宪君主国,要么规定共和国。这样的划分,隐藏着梁启超此时的政治价值观:国家不能是专制君主国,专制君主国已经不再具备政治上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只有像英国、日本这样的立宪君主国,以及西方世界中广泛出现的共和国,才具备政治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在立宪君主国中,君主享有的实际政治权力几近于无;在共和国中,根本就没有君主。这就是说,宪法的对立面主要是专制君主。宪法可以接受君主,但君主必须是英国、日本式的虚君。
第二,宪法必须对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进行划分,“今日凡立宪之国,必分三大权。”梁启超承认,这个观点来自孟德斯鸠。在此时,孟德斯鸠的著作对梁启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美国学者列文森所注意到的:“在1898年以前,梁启超著作中出现的‘孟’字,几乎一律代表‘孟子’;而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孟’字通常是‘孟德斯鸠’的意思。”[4]P117-118这个出自法国的新“孟子”,全面取代了中国古代的孟子,成为梁启超的思想导师,塑造了梁启超对于宪法的想象。
第三,既然“有议院之国所定之国典”才能称为宪法,那就意味着,议院才是宪法的核心,议院才是政治的中心。对于此时的梁启超来说,“立宪政府与众不同的只是一个有限政府,它的实质内容可归结为两部分:成文宪法的颁布和立法机关在立宪政府中居首位。换言之,在西方立宪政体中使梁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一思想——政府应该根据颁布的宪法组成和运作,在这当中,民选的立法机关扮演主导角色。”[5]P143这里的民选立法机关就是议会。
大致说来,梁启超在1899年《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表达的宪法思想,客观地比较各国宪法异同的成份比较多。从思想根源上看,此时的梁启超置身日本,通过大量阅读日文世界中的西学知识,形成了自己的宪法思想:宪法须以议会为核心。这样的宪法观念,源于外部世界的启示,具有较强的“读后感”的性质。不过,他的这种以议会为核心的宪法观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
二、追求君主立宪的宪法:保皇运动的折射
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1900年“春夏,先生居檀香山。七月,以勤王事急返国。事败后往新加坡,晤南海先生。”由于参加了康有为主导的保皇运动,试图维护光绪皇帝的政治地位,梁启超受到了慈禧太后主持的清政府的通缉。[2]P195在这样的背景下,梁启超写成了《立宪法议》一文,阐述了新的宪法思想。这篇写于1900年的宪法学论著,修改了他此前的政治价值观。当然,他的政体分类标准依然如故,他说:“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今日全地球号称强国者十数,除俄罗斯为君主专制政体,美利坚、法兰西为民主立宪政体外,自余各国政体则皆君主立宪政体也。”在这三种政体中,君主专制政体当然是价值低下的政体,而君主立宪政体与民主立宪政体在价值上也不等同。所谓“不等同”,并非民主立宪政体优于君主立宪政体,恰恰相反,在二者之间,“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君主立宪政体优于民主立宪政体的原因是,“民主立宪政体,其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于国家幸福,未尝不间有阻力。君主专制政体,朝廷之视民为草芥,而其防之如盗贼,民之畏朝廷如狱吏,而其嫉之如仇雠,故其民极苦。是故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3]P405
在1899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中,只有君主专制政体不具备正当性,无论是君主立宪政体还是民主立宪政体,都是正当的、值得追求的政体。但是,在1900年的《立宪法议》中,只有君主立宪政体才代表了政体与宪法的发展方向,因为只有它才是最优良的政体。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固不必说,民主立宪政体也会对国家幸福造成阻碍,因为它“施政之方略,变易太数,选举总统时,竞争太烈”。在这里,梁启超刻意指出民主立宪政体之负面影响,把君主立宪政体置于民主立宪政体之上,一个最重要的根源,就在于他参加的保皇运动,以及他对光绪皇帝的坚定支持。而且,他对光绪皇帝的支持并非始于1900年的保皇运动,此前的戊戌变法的过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与光绪皇帝结成政治同盟的过程。这样的政治同盟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梁启超此时的宪法思想:既要君主,也要宪法。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这就是梁启超的《立宪法议》旨在表达的宪法思想。
不过,尽管此时的梁启超对光绪皇帝抱有较强的思想认同与情感认同,但他毕竟不愿回到中国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且,即使为了君主,也必须制定宪法。那么,梁启超此时期待的宪法是什么呢?他回答说:“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西语原字为the constitution,译意犹言元气也,盖谓宪法者一国之元气也。”把宪法当作国家的元气,虽然有牵强附会之嫌,却也精到传神。因为在现代世界,宪法确实是一个国家的起点、基础。不过,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梁启超把宪法看作“万世不易”的宪典,并“不是很实在的说法”,是“中国读书人张大其词的老毛病”。[6]
作为国家元气的宪法,到底应当如何创制呢?在《立宪法议》中,梁启超回答说,宪法应当规定三个方面的内容:“首言君主统治之大权,及皇位继袭之典例,明君之权限也。次言政府及地方政治之职分,明官之权限也。次言议会职分及人民自由之事件,明民之权限也。”这就是说,宪法应当规定“君之权”、“官之权”、“民之权”。对于通过宪法“明君之权限”,“我中国学者,骤闻君权有限之义,多有色然而惊者,其意若曰:君也者,一国之尊无二上者也,臣民皆其隶属者也。只闻君能限臣民,岂闻臣民能限君,臣民而限君,不几于叛逆乎?不知君权有限云者,非臣民限之,而宪法限之也。”而且,传统中国一直都有“限君权”的传统。譬如,“王者之立也,郊天而荐之;其崩也,称天而谥之;非以天为限乎?言必称先王,行必法祖宗,非以祖为限乎?然则古来之圣师、哲王,未有不以君权有限,为至当不易之理者;即历代君主,苟非残悍如秦政、隋炀,亦断无敢以君权无限自居者。乃数千年来,虽有其意而未举其实者何也?则以无宪法故也。以天为限,而天不言;以祖宗为限,而祖宗之法不过因袭前代旧规,未尝采天下之公理,因国民之所欲,而勒为至善无弊之大典。是故中国之君权,非无限也,欲有限而不知所以为限之道也。今也内有爱民如子、励精图治之圣君,外有文明先导、可师可法之友国,于以定百世可知之成宪,立万年不拔之远猷,其在斯时乎,其在斯时乎。”[3]P405这段话,阐述了梁启超以君主立宪为核心的宪法观:第一,君权须受制于宪法,由宪法来规定。第二,传统中国已有君权受限的观念与实践,君权受制于天,君权受制于祖宗之法。但是,这些限制君权的安排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因为上天并不说话;祖宗之法只是照搬前代旧规,并没有采纳天下的公理,更没有回应人民群众的需要,因而是不可靠的。这就是说,传统中国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限制君权的办法。第三,如果我们依靠爱民如子、励精图治的圣君(譬如,光绪皇帝),同时学习其他国家的立宪经验,就可以制定出“万年不拔”的优质宪法。
当然,宪法在明确规定君权的同时,还要规定“官权”与“民权”。尤其要规定民权。因为,“民权者,所以拥护宪法而不使败坏者也。……故苟无民权,则虽有至良极美之宪法,亦不过一纸空文,毫无补济,其事至易明也。……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宪法与民权,二者不可相离,此实不易之理,而万国所经验而得之也。”[3]P405-406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牌号”的“三权论”:宪法应当明确规定的君权、官权、民权。当然,这三种权力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君权与官权主要是积极的、扩张性的权力;民权对于个体来说,主要是自由与权利,民权对于人民整体来说,可以转化成为议会之权,以之制约君权与官权。因此,在三权的关系问题上,民权可以充当君权、官权的制约因素。这就是梁启超在参加保皇运动的过程中,为君主立宪政体设想的宪法框架。
三、美式共和政体的宪法:辛亥革命的产物
1912年10月,梁启超从日本回到中国。在国内政治革故鼎新之际,梁启超写成了一篇著名的宪法学论文《宪法之三大精神》,文章指出:“今世之言政者,有三事焉,当冲突而苦于调和。各国皆然,我国为甚。他日制宪者能择善而用中,则新宪法其可以有誉于天下矣。第一,国权与民权调和。第二,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第三,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这几句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宪法构想:“新宪法”的重心在于处理三大关系:国权与民权的关系,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中央权与地方权的关系。
这种新的宪法构想,有两个主要的渊源:第一,辛亥革命的成功,已经排除了君主立宪政体的可能性,因为君主在制度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民国初建的政治现实中,梁启超不再讨论君权、君主立宪问题,从而对“宪法之精神”进行了新的论述、新的建构。这一点,可以支持本文的核心观点:梁启超的宪法思想,是“见之于行事”的液态思想,并非本质主义的固然思想,亦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的结果。第二,从梁启超关于宪法精神的认知来看,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是美国的宪法实践及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梁启超概括的“宪法三大精神”,几乎就是对美国宪法实践的描摹。因为美国的宪法精神,其实就是“三大精神”:联邦与各州之间的平衡,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以及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平衡,至于美国的最高法院,则充当了这三种权力交往关系的总枢纽。
为了说明美国宪法实践对梁启超宪法思想的影响,不妨看看梁启超对国权与民权关系的分析。他说:“何谓国权与民权调和?欧洲当十五六世纪,国家主义萌芽滋长,六七强国以兴焉。……其弊也,国之视民,若无机体构造之原料,民觳而国瘁。于是有十八世纪末之革命,蜩唐沸羹垂百年。革命前后,国家主义屏息,个人主义代兴,时则谓国之建凡以为民耳。甚至谓国家本有害之物,不得已而姑存之。其弊也,则民之视国,若身外之装饰品。国不竞而民亦见陵。逮晚近而反动又生焉。以彼美国,夙称个人主义之根据地,而今之识者,乃日以新国家主义呼号于国中(前大总统罗斯福之言)。此间消息,可以参矣。国权与民权之消长,其表示于政治现象者,则为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之辩争。此虽非尽由宪法所能左右也。然缘宪法所采原则如何,而其演生之结果实至巨。”[3]P2561按照这段话的逻辑,15、16世纪,主要是张扬国权的国家主义盛行;18世纪末期以后,是张扬民权的个人主义盛行;至于“此间”的美国,本来是个人主义的根据地,但是,对国家主义的呼声已越来越高。也就意味着,个人主义与国家主义不可偏废,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不可偏废,因此,国权与民权彼此兼顾应当作为宪法的基本原则。由于美国的宪法实践代表了“此间”的最新“消息”,因而“可以参矣”。由此可见,梁启超关于国权与民权相互调和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是“参考”美国宪法实践的结果。
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的思想同样是参考美国宪法实践的结果。梁启超说:“昔孟德斯鸠倡三权鼎立之义,欲使国会之立法权与政府之行政权,画鸿沟而不相越,此空想耳。国会所应行者不仅立法权,而立法权又不能专属于国会。征以各国之经验,孟说久不攻自破。即墨守孟说之美国,今亦蒙其名而乖其实矣。国会与政府,其职权既相倚而相辅,则当行此职权时,恒不免相轧而相猜。……大抵欲举两机关调和之实,其根本在养成善良之政治习惯。仅恃纸上法理,无当也。使政党运用之妙,能如英国,如美国,则宪法无论作何规定,皆无所不可。虽然,宪法之美恶,其影响于将来政治习惯之美恶者,亦至捷且巨”。[3]P2564在这里,梁启超同样把孟德斯鸠当作权威作家来引证。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学说,强调了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划分,这就为彼此分立的两种国家权力的存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梁启超看来,尽管孟德斯鸠是权威性的经典作家,但他在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画一道鸿沟的理论,却是一种空想。因为各个国家的经验已经证实了在两种权力之间,不可能有彻底的分立。即使是“墨守孟说之美国”,亦没有做到在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画鸿沟而不相越”。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宪法实践,比孟德斯鸠关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划分理论,更具可行性,几乎堪称国会与政府关系模式的最佳样本。由此也可以看到,美国的宪法实践,构成了1912年之际梁启超宪法思想的重要渊源。
在梁启超的这篇宪法学论著中,主要讨论了国权与民权的调和,以及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并没有讨论中央权与地方权的调和。因而,关于中央权与地方权的调和,梁启超只有观点,没有论证。没有论证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梁启超实在太繁忙,无暇完成这篇重要的论文。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当时的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的实践还渺无踪影。就1912年的民国政局来看,中央权处于剧烈的动荡之中,割剧状态下的地方权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在这种现实状况下,虽然理论上应当实现中央权与地方权之间的调和,但“调和”的具体模式,则只好暂付阙如了。这就是梁启超立论之际的政治情势。
在民国初建的特定政治背景下,在美国共和政体的强烈示范下,梁启超形成了“三大精神”的宪法思想。它具有强烈的“见之于行事”的特征。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注意两点:第一,梁启超虽然强调了宪法的“三大精神”及其包含的“六大要素”(国权与民权,立法权与行政权,中央权与地方权),但这三大精神、六大要素并不能等量齐观,其中,国会与政府及其相互关系更具根本性。梁启超说:“吾愿他日制宪者,当常念国会之设,实借以为求得善强政府之一手段,政府譬则发动机。国会譬则制动机。有发而无制,固不可也。缘制而不能发,尤不可也。调和之妙,存乎其人矣。”[3]P2568这就是说,政府是国家的发动机,国会是国家的制动机,这两架机器都需要彼此协调地运转起来。
四、优越于约法的宪法:一个更高的标准
在民国初年,制定宪法一直是政治上的核心议题。1915年,当时的参政院根据《中华民国约法》,选出宪法起草委员会共十人,以之推进宪法的制定工作。梁启超是十人起草委员会之一。对此,《梁启超年谱》是这样记载的:1915年,“七月六日大总统申令宪法起草为约法上制定宪法程序之一,现据参政院呈报,业经依法选举李家驹、汪荣宝、寿达、梁启超、施愚、杨度、严复、马良、王世微、曾彝进为宪法起草委员,自应由委员依法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不过,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于梁启超就任宪法起草委员,他的一些朋友明确表示反对,“而社会舆论尤多诽议之者”,梁启超“为声明他的理由和立场起见”,[2]P719-720专门写下了《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一文。这本是一篇为自己就任宪法起草委员进行辩护、说明的文章,但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同样阐述了自己的宪法思想,其核心观点是区分宪法与约法。
在中国宪法史上,既有宪法,也有约法。从词义看来,约法与宪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学者们一般也把约法作为宪法的另一种说法。④但是,梁启超对宪法与约法进行了严格的界分。他在《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中指出:“宪法之性质,宜期诸永久,而约法之性质,取适于一时。永久适用之宪法,不能不悬一稍完善之理想以为标准,使国民循轨志彀以图进步,而或恐以不能实行之故而成为具文。或强欲实行焉而反不与时势相应,于是乎乃为一时的约法以救济之。质言之,则宪法宜采取纯立宪的精神,而约法不妨略带开明专制的精神。……今制定宪法,若即以约法之精神为精神耶,则约法之名,奚损于尊严,而宪法之名,岂加于崇贵,何必将此种国家根本大法,旋公布而旋弃置,以淆民视听者?若于原约法精神之外而别求新宪法精神耶,学理上之选举,犹为别问题,然试问法之为物,是否求其适应,求其可行,谓约法不适应不可行耶,则宜勿公布,约法既适应可行耶,则与约法异精神之宪法,其不适应不可行,可推见也。谓一年前宜于彼者,一年后即宜于此,天下宁有是理?是故据鄙人私见,谓今日诚无汲汲制定宪法之必要也。”这些关于宪法与约法相互关系的论述,主要强调了宪法与约法的差异。
首先,从时间来看,宪法是追求垂范久远的根本法,约法主要是暂时的、短期的、临时性的根本法。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可以支持梁启超的这种划分,因为这部宪法,就是临时性质的。因此,约法可以经常变更,可以是应急性的,宪法则需要保持足够的稳定性。
其次,从价值来看,宪法应有更高的价值追求,更完善的价值理想,以引导国民不断进步。对于约法,则不必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约法只要能够解决当时的问题就可以了。这就是说,对于应急性的约法来说,其主要的功能在于满足一时之需,属于权宜之计,是一个工具性、手段性的文件。宪法则必须具有足够的价值导向,应当对时代、社会、民众产生相当的引领性。因此,宪法较之于约法,具有更加尊崇的地位。
再次,从精神来看,宪法应当采取“纯立宪”的精神,约法则可以略带开明专制的精神。何谓“纯立宪”的精神?梁启超在此没有解释,不过,把“开明专制”置于“纯立宪”的对立面,大致可以想象“纯立宪”的含义:祛除专制,哪怕是开明的专制,追求民主立宪。这就是说,宪法应当充分体现民众的意志,约法则可以略微体现开明专制者的意志。
最后,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如果制定出来的宪法依然像约法那样得不到有效的实施,那么,宪法的制定,似乎就没有那么迫切。至于此时正在生效的约法,就是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在宪法史上,这部约法又被称为“袁记约法”,因为它是在袁世凯主导下制定的,旨在取代1912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梁启超认为,这部《中华民国约法》自1914颁行以来,根本就形同虚设。梁启超由此表示,尽管自己已经就任宪法起草委员,但自己对于宪法能否得到实施,确实心存疑虑。他说,“法也者,非将以为装饰品也,而实践之之为贵,今约法能实践耶否耶?他勿细论,若第二章人民权利之诸条,若第六章之司法,若第八章之会计,自该法公布以来,何尝有一焉曾经实行者?即将来亦何尝有一焉有意实行者?条文云云,不过为政府公报上多添数行墨点,于实际有何关系?夫约法之效力而仅于数行墨点,其导人民以玩法之心理则既甚矣,试问易其名为宪法,而此态度遂能否一变,苟率此态度以视将来之宪法,则与其汲汲制定,毋宁其已矣。”
尽管梁启超已经注意到《中国民国约法》并未得到有效的实施,但他仍然愿意参与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他的理由是:“吾于现时制定宪法,其所怀疑者如右,然而犹就此职者,则以其所拟者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故,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吾之不舍,犹斯志也。”[3]P2779这就是说,尽管对宪法的未来命运存有种种疑虑,梁启超还是对拟议中的宪法有所期待。尽管舆论界有种种非议,梁启超还是愿意参与宪法的起草,这其实反映了梁启超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积极参与政治的立场。事实上,梁启超作为早期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制定宪法一直抱有热忱。1913年2月24日,梁启超从日本归国还不到半年,就正式加入了共和党。1913年5月,他又组织策划了把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为进步党的活动。梁启超虽然仅仅是进步党的理事,但在实践层面,他是该党的灵魂人物。作为一名“党人”,早在1913年6月15日,梁启超就提出了“先定宪法,后举总统”的主张。[2]P671同年7月25日,梁启超在写给袁世凯的信中又建议:“今最要者,乘此时机,使内阁通过,宪法制定,总统选出,然后国本始固”。[2]P674为了推动宪法的制定,梁启超在1913年就代表进步党起草了“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该宪法草案共计11章、95条。[3]P2615这就是说,梁启超其实是制定宪法的积极推动者。
因此,梁启超在这篇“答客问”中表达的宪法思想,可以做两个方面的分析:第一,他对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不能有效实施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希望无论是约法还是宪法,都能够运用于实践,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第二,应该以更高的标准制定宪法,从而让宪法与已有的约法区别开来。
五、提升国会权能的宪法:以国会约束政府
1916年3月,梁启超写成了一篇《国民浅训》。在序言中,梁启超记载了写作此文的背景:“余以从军,于役邕桂。取道越南,时谍骑四布。乃自匿于山中旬日……。相伴者惟他邦佣保,非特无可与语,即语亦不解也。行箧中挟书数卷,亦既读尽无以自娱。中间复婴热病,委顿二日,几濒于死。病既起,念此闲寂之岁月,在今百忙中殊不易得,不可负,乃旧兴草此书。阅三日夜,得十三章,草成遂行。”[3]P2835这就是说,此篇论著,写于“从军”途中。梁启超在此所说的“从军”,是指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战争的起因是,1915年12月12日,“袁氏接受了所谓的推戴,承认帝位,就待践祚而已。任公知道已无可挽回,即于12月16日自天津乘轮南下,从事实地的反抗运动。……护国之役旋于12月25日爆发于西南。”[7]P62-63
在这篇匆忙草就的《国民浅训》第三章,题为“何谓立宪”。梁启超以此阐述了他的宪法思想。他说:“立宪者,以宪法规定国家之组织,及各机关之权限,与夫人民之权利义务,而全国上下共守之以为治者也。”这就是说,宪法主要在于规定国家机构的权力,以及人民的权利义务。“我国宪法现尚未制定,其内容如何,无从悬说,”而最重要的事务则是:“必有人民所选举之国会与政府对立是也”。国会与政府的对立,并非让国会与政府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而是让国会有效地监督政府。他说,国会有三种权力不可少,“一曰议决法律,二曰监理财政,三曰纠责政府。但使国家能有良好之国会,而国会能公平以行此三项权能,则立宪之实可举,而共和之基可固矣。”梁启超提供的法理依据是:“国家之命,托于政府。而政府所以治民者全赖法律。所以行政者全赖财赋。最患者,政府不恤民情,擅制殃民之法律,则民将不堪其病。今有人民所选举之国会以议决之,政府无从专横。则非福国利民之法律,决无由发布。又官吏舞弊营私,什有九皆由操纵财政,立宪国通例。凡设立新税及增加国库负担,皆须国会议决。政府每年必须编制预算,将国库出入款项,分部分项分目,详细开列。不许滥支,不许挪用,经国会议决然后施行。……夫国会有此两权,其监督政府,既采周密矣。犹恐政府仍有专恣规避,或施行之失当,国会更得随时随事质问之,重则弹劾之。如是则非公忠体国且有才能之人,决不能立于政府。政府得人,则官吏之积弊自廓清。所有一切机关,皆不能不振作精神,替国家办事,替人民兴利除害。如此政治安得不一新,而国家安得不渐强。故立宪之节目虽有多端,而关键全在国会,其事甚明。”[3]P2837
国会建设的关键,一方面,在于国会议员是否得人。由于国会议员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因此,国家的盛衰存亡,就在于人民选出什么样的国会议员。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国会不妥”,国会不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专务捣乱,不管政府政策之良与不良,一概挑持反对,致政府制肘不能办一事。”另一种情况是,“流于腐败,为政府所运动所屈服,不能行其监督之责,致使国会虽有如无。二者有一于此,则国会之作用全失,而立宪之实废,共和之基坏矣。”[3]P2838
按照这篇《国民浅训》,梁启超在此时的宪法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国会是宪法的根基,国会不仅支撑宪法,而且支撑共和。宪法和政治发展的方向,就在于发挥国会的作用。因此,应当以国会为中心,完善宪法与政治。其次,国会的职能就在于制定法律、监督政府。梁启超还强调了国会对于财政的监督职能,但是,监督财政同样是对政府的监督或纠责。再次,国会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加强国会建设,选出适当的国会议员,防止国会腐败,就是宪法上的一个焦点。这种以提升国会权能为中心的宪法,虽然出于一篇“浅训”,但就中国宪法的发展来说,似乎还颇有先见之明。因为,百年中国的议会制度就是沿着制定法律、监督政府的方向发展的。不过,梁启超在此表达的宪法思想,主要还是受到了政治现实的强烈触动。梁启超写作《国民浅训》之际,正是护国战争的紧要关头,他自己也身陷危难之中。追根溯源,护国战争的兴起,是因为袁世凯颠覆民国,复辟帝制。袁世凯之所以能够颠覆民国,当然具有多个方面的原因,但从宪法的角度来看,国会不能对袁世凯及其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约束,亦是背后的原因之一,是国会的无能、无力纵容了袁世凯的政治倒退。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梁启超描绘了提升国会权能的宪法,主张国会对政府的有效监督。
六、以职业选举与国民投票为核心的宪法
1918年,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这篇长文分为两个部分:上篇是“大战前后的欧洲”,下篇是“中国人之自觉”。在下篇的第九节,梁启超专门谈到了“宪法上两要点”。
宪法有哪两个要点?梁启超的回答是:“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大关目,必须切实办到,政治的大本才能立”。这就是说,宪法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职业选举与国民投票。为什么呢?梁启超说:“国家最重要机关,当然是首推国会,但几年以来,国会价值被议员辱没透了。国人对国会的信仰已经一落千丈。非把它恢复过来简单没有办法。怎样才能恢复呢?试问国会为什么有价值,不是因为它代表国民吗?现在议员却代表谁来?但是现在的情形,只是聚着一群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挂上一个头衔便靦然以全国主人翁自命,叫人怎么能对他生出信仰来?即使改选一回,选出来的还不是这一班人?换汤不换药,结果依然一样。这等说来,民意机关终久不得实现,政治终久不得改良,国家可要断送了。”按照梁启超的这番诊断,国会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原因就在于:议员不能代表国民。“要国会恢复价值,根本就要叫国会真正代表国民,我想莫如施行一种职业选举法,两院中虽不妨有一院仍采代表地方主义,必须有一院代表职业主义,将国中种种职业团体由国家赋予法人资格,委任办理选举。选举权、被选举权都以职业为限,像我们这种高等游民,只好在剥夺公权之列。想要恢复,除非赶紧自己寻着个职业来。若用此法,那吃政治饭的政客,就便未能遽报肃清,最少也十去八九,就算是替政界求得一张辟疫符。若用此法,那农、工、商各种有职业人民,为切己利害起见,提出的政治问题自然丝丝入扣。若用此法,那‘国之石民’和国家生出密切关系,民主政治基础自然立于不拔之地。若用此法,将来生产事业发达,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都有相当的代表在最高机关,随时交换意见交换利益,社会革命的惨剧其或可免。”[3]P2983这就是梁启超关于职业选举的设想。
在梁启超看来,职业选举的前提是两院制。其中一院代表不同的地区,由各个地区选出的代表组成。但是,另一院则必须由各个行业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这就是职业选举的要义。按照梁启超的这个观点,国会议员(至少是两院制国会中某一院的议员)不能是专职的“政治人”,必须是专职的工人、农人、商人,等等。梁启超把专职的议员看作是“吃政治饭的无业游民”,甚至他本人,也没有当选议员的资格,因为在他看来,他本人也没有从事某种固定的职业。
如何看待这个职业选举的宪法设想?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职业选举当然有它的正面效应,对此,梁启超已经做出了概括式的说明。在思想史上,19世纪末期兴起的法国工团主义和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就认为,国家应当“以从事同一职业为其结合的根本原因和单位。所以他们主张议员应由职业团体选举产生,以代表各行各业的人民的利益,使议会的组成与社会的组成一致起来,以便应付日趋复杂而专门的立法任务,从而提高议会的威信,一扫政党和政客包办选举的弊端。他们认为,一个地区既含有各种职业不同的选民,则选民的利益也必然不同;不同利益的选民是无法被代表的,所能代表的惟有选民的意志;然而意志本身是可以强加的,于是强奸民意、包办代替的丑闻便流行起来了。他们认为这种弊端是由地域代表制产生的。他们以为只有采用职业代表制才能免除或者补救这种流弊。”[8]P268
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对职业代表制的强调,恰好可以支持梁启超主张的职业选举。从根源上看,梁启超对职业选举的推崇,一方面,很可能受到了当时西方流行的工团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因为梁启超的这个观点出于他的《欧游心影录》,反映了他从欧洲考察回来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根源,恐怕还在于当时中国的国会议员与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民众之间的隔膜与割裂,这种隔膜与割裂,严重消蚀了国会议员的代表性,进而也消蚀了国会本身的价值。正是在这种现实情况的催促下,梁启超提出了职业选举的宪法思想。
历史似乎也证明了梁启超的先见之明,因为,20世纪中叶以后的宪法发展,正好也回应了这种职业选举的观点。在当代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几乎都不是专职的代表,代表们都有他们各自的本职工作,有工人、有农民、有商人、有军人,当然也有学人、公务人员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代表。譬如,在第十届全国人大的2985名代表中,工人农民代表有551名,知识分子代表有631名,干部代表有968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有480名,人民解放军代表有268名,香港代表有36名,澳门代表有12名,归国华侨代表38名。从形式上看,这种偏重于职业的代表构成符合梁启超的宪法预期。但是,这种职业化的代表构成是否达到了梁启超所希望的政治目标?恐怕也难做出肯定性的回答。就当代中国的宪法理论、宪法实践的发展方向来看,似乎不可能完全排斥“吃政治饭”的专职议员(代表)的。相反,当代中国的宪法理论,一直都在论证专职人大代表的正当性与积极意义。⑤
梁启超虽然没有直接反对专职议员,但是,他反对“吃政治饭的无业游民”,已经隐含了对于专职议员的排斥,这恐怕是一个偏颇的论断。因为政治本身也是一种职业,“吃政治饭”的人并非“无业游民”。议员的职业性与议员的代表性是可以兼顾的。一个工人、农人或商人,在他当选议员之前,他是工人、农人或商人;在他当选议员之后,也许就应当转为专职议员,这时候,他就已经成为一个“吃政治饭”的人了。当然,让议会中的一些议员,始终保持兼职状态,让他们的行业代表性更强、政治职业性更弱,也是一种备选方案。这涉及到对代议民主的重新理解,对代表制的重新理解,以及对政治作为职业的重新理解。⑥因为牵涉的法理极其广泛而深刻,这里不再展开讨论。
宪法上的另一个要点是国民投票制度。关于这个制度,梁启超认为:“从前有人说,这制度要小国才能行。这是什么话?现在德国不是广行吗?美国宪法改革前几年不就有人极力提倡此制吗?国民是主人,国会是主人代表,并非我派了代表,就把我的权卖给他了。有时代表作不了主人的事,还须主人亲自出马来。即如这回南北议和,真正民意所在,是有目共见的。天公地道,就是只要一回国民投票一刀两段的解决,却凭那南北军阀派出什么总代表咧来鬼鬼祟祟的分赃。国民看不过,要说几句话,那新旧议员老爷们就瞪起眼睛来,说道:‘这是我国民代表的权限,谁敢多嘴!’你想这不是岂有此理吗!”[3]P2983
梁启超主张的这种国民投票,其实就是全民公投或全民直选。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像“南北议和”这样的大事,以及其他方面的大事,都应当由全民投票来解决,不能由南北军阀的代表来解决,亦不能由议员来决定。从民主的理想状况来看,梁启超的这种观点当然没有问题,但在实践过程中,这种观点就过于理想化了。国民投票或全民公决,并非始终优于代表投票。在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譬如在当代中国,如果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国民投票,那么,一方面,耗费的经济成本及其他方面的成本,就可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以至于整个社会根本就不能承受。另一方面,如果全面推行全民投票制度,就意味着要完全废除代议制度——因为议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但在事实上,这样的绝对民主是很难实现的。
可见,梁启超在1918年强调的“宪法上两要点”,毕竟出于一篇游记《欧游心影录》,此游记并非严格的学术论著,因而,他的“两要点”在学理上可以商榷之处甚多,很难被视为深思熟虑的学术观点。这也恰好可以说明,梁启超的宪法思想,不是他学术研究的产物,而是他面对现实的思想反映,具有直接的现实针对性:1918年之际的南北议和,以及此前的国会议员们的不佳表现。因此,梁启超虽然以“宪法上两要点”为题,论述了他对于宪法的期待,实际上主要还是在于批判当时的议会制状况。
七、见之于行事:解释梁启超宪法思想的方法论
上文以时间作为线索,梳理了梁启超宪法思想在20年间的变迁。由此可以发现,梁启超的宪法思想呈现出明显的“见之于行事”的风格,这就像孔子关于“仁”的论述。
“仁”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论语》中,孔子反复阐述“仁”的含义,但他并没有提供统一的、本质性的界定。孔子总是根据具体的语境阐述“仁”的含义。譬如,“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有一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还有一回,“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还有,“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等等。这些关于“仁”的论述都不相同。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境下,孔子有时候强调仁的这个方面,有时候又强调仁的那个方面。这恰好印证了孔子的夫子自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梁启超关于宪法的论述,就像孔子关于“仁”的论述,较少“载之空言”,大多“见之于行事”。当时的宪法语境是什么,梁启超就强调宪法的某个面相。1899年,梁启超初到日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献,受到了孟德斯鸠等人的启发,阐述了以议会为中心的宪法观,强调了三分权立的宪法框架。1900年,梁启超在参加保皇运动中,对光绪皇帝的尊崇转化为君主立宪的宪法观,相应地,权力结构不再是三权分立,而是君权、官权与民权。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君主已经不复存在,梁启超转而主张美国式的宪法架构,认为宪法应当处理好国权与民权、立法权与行政权、中央权与地方权之间的关系。1915年,梁启超鉴于《中华民国约法》形同虚设,特别强调了宪法应当付诸实践,而且,应当以更高的标准来制定宪法,让宪法优越于约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1916年,在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护国战争中,梁启超鉴于政府得不到约束,以至于民国被颠覆,特别强调了以国会监督政府,表达了提升国会权能的宪法观。1918年,梁启超深感当时的国会腐败,认为宪法的要点在于职业选举与国民投票,这种贬斥议员、不信任国会的宪法思想,其实是对当时的国会及其议员极度失望的产物。
梁启超的宪法思想不是一种固态的宪法思想,无法进行本质主义的概括,无法进行定型化的总结。相反,梁启超的宪法思想是一种液态的宪法思想,梁启超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与宪法情势相当于容器,容器发生了变化,他的液态的宪法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梁启超总是在不同的语境下,强调宪法的不同向度,这就为他的宪法思想,赋予了浓厚的液态属性。这种“见之于行事”的液态化的宪法思想,让梁启超在思维方式上,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遥相呼应。
注释:
① 譬如,邱远猷、王贵松:《梁启超宪法学思想研究》,《法学家》2004年第3期;丁洁林:《梁启超与中国近代宪政》,《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王德志:《论梁启超的宪政学说》,《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等等。
② 譬如,熊月之:《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异同》,《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李秀清:《“梁启超宪草”与民国初期宪政模式的选择》,《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龚培:《梁启超的早期议会思想》,《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程燎原:《法治必以立宪政体盾其后:从商鞅难题到梁启超方案》,《南京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等等。
③ 详见,[日]土屋英雄:《梁启超的“西洋”摄取与权利-自由论》,载[日]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④ 譬如,费春:《中国第一部近代宪法——〈鄂州约法〉》,《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
⑤ 参见,童大焕:《强化人大监督权,期待代表专职化》,《法律与生活》2006年第19期;何鹏程:《专职代表制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理论与改革》2001年第6期;叶中华、常征、王娟:《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专职化》,《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等等。
⑥ 韦伯长篇论文《以政治为业》,对职业政治家进行了专门论述,详见[德]韦伯:《政治与学术》,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54页。
[1] 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8.
[2] 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 [美]列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M].刘伟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5]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6] 耿云志.重读梁启超的《立宪法议》[J].广东社会科学,2014,1.
[7] 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8] 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唐艳秋)
On the Liang Qi-chao’s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from His Acts
YuZhong
(Law School of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 and Businiss,Beijing 100070)
The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can not be understood from the system and essentialist perspective. Liang’s idea of constitution is to express constitutional practice. Therefore, it should be based on "found in the act" to look Liang’s constitutional thought. From the late 1800s until 1918, Liang emphasized a number of face of Constitution, as well as to professional election and vote for the National. The constitution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is flowing and liquid idea.
Liang Qi-chao; constitutional thinking;essentialism;legal method
1002—6274(2015)02—028—10
喻 中(1969-),男,重庆人,法学博士,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法理学。
DF0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