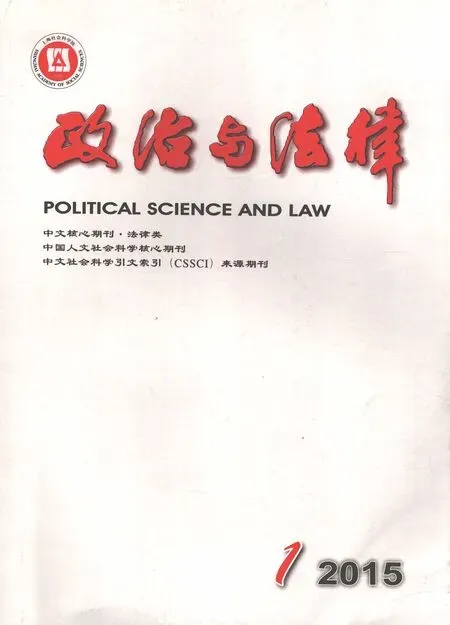被滥用的“滥用职权”*
——行政判决中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语义扩张及其成因
施立栋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被滥用的“滥用职权”*
——行政判决中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语义扩张及其成因
施立栋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学界通说认为,1989年通过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滥用职权”审查标准,其涵义是滥用裁量权。但是,对《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案例选》上刊载的行政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并未采纳这一学理观点。在法定职权、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程序要件的判定中,法官普遍使用了滥用职权标准。甚至在不少案件中,法官还将其泛化理解为“违法”。滥用职权标准之所以会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根源在于该标准本身存在缺陷。一方面,它与《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2项中的其他审查标准之间的划分标准并不同一;另一方面,“滥用职权”的规范涵义又极易与其日常涵义发生混同。为克服上述缺陷,应将滥用职权标准修改为“滥用裁量权”。
行政判决;司法审查标准;滥用职权;行政职权;滥用裁量权
1989年通过的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将“滥用职权”规定为司法审查标准之一,该标准在2014年修改后的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得到了沿用。①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第70条仍保留了“滥用职权”这一审查标准。由于本文是对该法修订实施前“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判决中的运用状况所作的观察和检讨,所以文中所援引的《行政诉讼法》条文序号仍指的是原法中的序号。为显示区别,本文接下来将分别以《行政诉讼法》(1989)和《行政诉讼法》(2014)来指称旧法和新法。按照学界通说,“滥用职权”审查标准针对的是行政权限范围内的裁量问题的评价,因而“滥用职权”的涵义即为滥用裁量权。②参见胡建淼:《有关行政滥用职权的内涵及其表现的学理探讨》,《法学研究》1992年第3期;朱新力:《行政滥用职权的新定义》,《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页。③参见胡康生主编:《行政诉讼法释义》,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上述学理观点可以得到立法原意的支撑。《行政诉讼法》(1989)出台后不久,在一本由全国人大法工委组织编写的释义著作中,就将“滥用职权”的适用对象限定于行政权限范围内的具体行政行为。③至此,“滥用职权”的规范涵义,似乎清晰可辨。然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中的行政判决时,却发现,法官并未采纳“滥用职权就是滥用裁量权”这一学理观点。沈岿教授在对《人民法院案例选》上刊载的行政案例进行阅读后发现,司法判决中所适用的“滥用职权”标准,大多与学理上界定的行政裁量情形无关。④参见沈岿:《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法商研究》2004年第4期。章剑生教授也有类似的观察和观点。⑤参见章剑生:《现代行政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页。但是,关于法官究竟对“滥用职权”这一审查标准秉持何种理解,以及它与学理上界定的涵义差别有多大,上述学者并未做深入的分析,其他学者对此也没有作系统性的实证梳理。有鉴于此,笔者拟对行政审判实践中滥用职权标准的真实运用状况进行梳理,并剖析这种现象在制度层面的形成原因。在研究样本上,笔者选取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和《人民法院案例选》上刊载的行政诉讼(包括行政赔偿)案例。这主要是考虑到,这两本刊物上发布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且它们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跨度,从中获知的“滥用职权”的运用状况,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法官极少在滥用裁量权意义上使用滥用职权标准
滥用裁量权意义上的“滥用职权”,是指具体行政行为在没有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和超越职权等违法情形的前提下,法官对属于行政职权范围内的裁量行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笔者于本文中将其称为狭义的滥用职权。它符合《行政诉讼法》(1989)的立法原意,以及学界通说上所界定的“滥用职权”的涵义。
在行政判决中,确实有法官在滥用裁量权意义上运用了“滥用职权”这一审查标准。在“王丽萍诉中牟县交通局行政赔偿纠纷案”中,被告中牟县交通局在对未缴纳养路费的小四轮拖拉机作出暂扣决定时,没有善尽注意义务,致使车上的生猪因天气炎热受挤压而大量死亡。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仅包括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还包括行政机关在自由裁量领域合理使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明显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构成滥用职权。……县交通局工作人员在执行暂扣车辆决定时的这种行政行为,不符合合理、适当的要求,是滥用职权”,并以滥用职权标准作为唯一的裁判依据,判决确认被告的行为违法。⑥该案具体情况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3年第3期。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使用这种狭义的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比例极低。在笔者搜集到的33个案例中,法官对滥用职权采取狭义理解的,仅有前述“王丽萍诉中牟县交通局行政赔偿纠纷案”这一个案例。法官之所以极少在滥用裁量权意义上使用滥用职权标准,原因可归结为如下两点。
第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法定程序和法定职权等方面均合法,而仅仅是在裁量权的运用上存在瑕疵,要满足这一条件并不容易。事实上,进入诉讼的绝大部分行政案件,均无法满足这一要求。
第二,即便具体行政行为仅仅存在合理性瑕疵,滥用职权审查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也不得不面临来自《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第4项规定的显失公正标准的竞争。因为与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相比,显失公正这一审查标准没有对行政机关进行主观评判的色彩,法官在运用该标准时不易遭致行政机关的强烈抵触。⑦对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主观性评价色彩及其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的实证分析,参见郑春燕:《论“行政裁量理由明显不当”标准——走出行政裁量主观性审查的困境》,《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而且,在适用显失公正标准时,还可以匹配采取变更判决的裁判方式,这能为相对人提供更具实效性的权利保护。因此,对于在行政处罚领域出现的滥用职权行为来说,法官更有可能援引显失公正这一审查标准,而非滥用职权。有关这一点,可以在“郭佳诉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治安管理处罚案”中得到体现。在该案中,原告郭佳通过摩托车驾驶证考试后,在等待颁发驾驶证期间,擅自驾驶摩托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被告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以郭佳无证驾驶为由,依据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5条对其处以最高幅度的15日行政拘留处罚。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认为,西工公安分局没有考虑郭佳已通过驾驶考试这一因素,其作出的顶格处罚决定是显失公正的,并援引《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第4项的显失公正标准,作出了变更判决。但在对该案的评析部分,审理该案的法官明确指出,被告的行为是一种任意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⑧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5年第1辑(总第5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65页。可见,法官虽意识到了本案属于裁量权滥用的情形,但最终还是回避使用滥用职权这一审查标准,转而采用了显失公正标准。类似的回避运用滥用职权标准而使用显失公正标准的情况,还存在于“哈尔滨市规划局与汇丰实业公司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中。⑨在该案中,汇丰公司非法翻建的建筑物,对中央景观大街的建筑物采光造成了影响。对此,哈尔滨市规划局对其作出了责令拆除的处罚决定。一审法院认为,哈尔滨市规划局在作出责令拆除决定时,没有按照“遮挡多少、拆除多少”的原则进行处罚,致使该处罚决定显失公正,判决对该决定进行变更。虽然汇丰公司在上诉中明确提出了该行政处罚决定系滥用职权的主张,但二审判决同样仅援引了显失公正这一标准,而没有使用滥用职权标准。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法公布(2000)第5号]行政判决书。
二、滥用情形之一:与其他标准在适用对象上的交叉
(一)扩张适用的滥用职权
在大量案例中,被法官认定为滥用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存在着诸如超越职权、事实不清、适法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违法情形。此时,滥用职权标准的适用场域,就超出了学理上界定的裁量权范围,而进入了《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第2项的其他四种审查标准的“领地”,与它们在适用对象上发生了交叉。这是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的第一种表现形式。笔者将这种情形中所适用的滥用职权,称为广义的滥用职权。它是指一个在法定职权、事实根据、法律依据或程序要件方面存在违法情形的具体行政行为,由于具有不适当的目的、不正当的考虑、行为反复无常或者结果显失公正等学理上界定的滥用裁量权情形,而被法官认定为同时构成滥用职权。⑩有不少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的“滥用职权”标准仅仅针对的是行政机关不正当目的(动机)的审查。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252页;陈天昊:《行政诉讼中“滥用职权”条款之法教义学解读》,《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理由在于,它不但忽略了不正当的考虑、行为反复无常、结果显失公正等情形,而且因只能适用于对行政机关目的(动机)的分析,将容易使“滥用职权”标准彻底陷入主观性审查的泥潭。
(二)交叉的具体情形
在司法判决中,滥用职权标准在适用对象上与其他审查标准相交叉的情形有如下四种。
第一种是与超越职权标准的交叉。在“黄煌辉诉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中,被上诉人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以举办计划生育国策学习班的名义,非法限制上诉人黄煌辉的人身自由。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上诉人在行使行政职权时没有严格的依照法律和政策,明显带有主观性和随意性,以举办计划生育国策学习班为名,行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之实,破坏了计划生育工作的严肃性和政策性,侵犯了上诉人的人身权,其行为不属于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行为,而系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违法行为。”①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4辑(总第4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63页。在该案中,丰州镇人民政府的行为,系出于非法限制黄煌辉人身自由的不正当目的,同时在客观上又超越了其据以作出行政决定的权限范围,因此法官同时援引了滥用职权和超越职权这两项审查标准。
第二种是与主要证据不足标准的交叉。在“刘冰申请沛县公安局行政赔偿案”中,被告沛县公安局以原告刘冰实施“卖淫”为由,对其强制传唤关押26小时。在刘冰通过医院检查,证明自己处女膜完好之后,沛县公安局又非法对其实施了收容审查。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沛县公安局在无证据的情况下,以‘卖淫’为由于1995年7月25日对上诉人刘冰进行传唤关押,后又以‘流氓’为由采取收容审查强制措施,违法限制人身自由42天,显属滥用职权违法行为”,并判决沛县公安局承担行政赔偿责任。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0年第3辑(总第3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页。在该案中,沛县公安局在欠缺足够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出于打击报复的不正当目的,对刘冰非法进行收容审查,其行为兼具主要证据不足和滥用职权两种情形,因而法官在判决中一并使用了这两项审查标准。
第三种是与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标准的交叉。在“夏飞诉徐州市房产管理局注销房屋所有权证案”中,原告夏飞在申请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其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证明书》存在涂改痕迹。徐州市房产管理局在审查时发现了这一涂改情况,但仍然予以认可,并颁发了房屋所有权证。后来由于他人举报该涂改情况,徐州市房产管理局撤销了其房屋所有权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再审判决中指出“夏飞在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时所提供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证明书》曾经徐州市房产管理局多次审查,并均予以认可,基于信赖保护原则,夏飞提供此《国有土地使用权申报证明书》不应被认定为违反《徐州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二)项的规定,徐州市房产管理局作出的《撤销决定》无法律依据”,并撤销了徐州市房产管理局的撤销决定。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2年第4辑(总第4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397-398页。在该案中,徐州市房产管理局撤销房产证的行为,一方面错误地适用了《徐州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办法》第17条第2项,另一方面在结果上又违背了夏飞的合理信赖,从而兼具适法错误和滥用职权两种情形。因此,法官一并运用了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和滥用职权两项标准作为判决依据。
第四种是与违反法定程序标准的交叉。在“张振隆不服徐州市教育局注销社会办学许可证案”中,徐州市教育局曾向张振隆颁发社会办学许可证,上面载明张振隆为沛县汉台高级中学的法定代表人。后来,徐州市教育局通过向第三人颁发社会办学许可证,实质上变更了张振隆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张振隆不服提起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徐州市教育局主动撤销了向第三人颁发的许可证,张振隆因此撤诉。就在张振隆撤诉后的第二天,徐州市教育局又以张振隆已自愿辞去校长职务,且不再是投资人为由,注销了张振隆的社会办学许可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徐州市教育局“在作出对原举办人、学校负责人张振隆不利的注销通知时,既未提前告知,也未听取其申辩,违反了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徐州市教育局……行政行为反复无常,且导致汉台中学客观上处于无办学许可证违法办学的状态,滥用了行政管理职权”。④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4年行政·国家赔偿专辑(总第5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174页。在该案中,徐州市教育局注销许可证的行为违背了正当程序,且行为反复无常,因此法官在判决书中同时将其认定为违反法定程序和滥用职权。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是通过援引《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中的“违反法定程序”标准,实现对违反正当程序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便是明证。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第3期。
(三)为什么会发生交叉
对于滥用职权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在适用对象上的交叉,事实上已经有学者零星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罗豪才教授在较早时就指出,滥用职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往往兼有适法错误、违反法定程序、主要证据不足等情形。⑥参见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418页。叶必丰教授在梳理行政判决的过程中,则发现了滥用职权标准与超越职权标准之间的交叉。⑦参见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43-344页。但是,对于为何会发生这种现象,上述学者并没有展开深入分析。
《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对行政裁量司法审查标准的规范表述,采取的是“滥用职权”一词,而非域外通行的“滥用裁量权”。⑧在日本和韩国的行政诉讼法典上,对行政裁量司法审查标准的规定,均采取了“滥用裁量权”的表述。参见《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2004年修正)(第30条),王彦译,《行政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韩国行政诉讼法》(2002年修正)(第27条),吴东镐、康贞花译,《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4条规定了行政法院审查裁量问题的两种适用情形:“逾越法定裁量权限”和“以不符合裁量授权目的方式行使裁量权”。学理上认为,后一种情形即为“裁量滥用”。参见《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1960年颁布),载[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2013年修正)第201条虽然采取了“滥用权力”的表述,但明确将这种“权力”限定为“裁量权”。该条规定:“行政机关依裁量权所为之行政处分,以其作为或不作为逾越权限或滥用权力者为限,行政法院得予撤销。”在笔者看来,在司法实践中,滥用职权审查标准之所以会突破裁量权的范围而被滥用,其原因恰恰在于立法者所使用的“职权”一词之上。这一表述具有拓展滥用职权的适用范围的语义空间。
在理论上,行政职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行政管辖权和行政处理权。前者是指行政机关对特定事项进行管辖的权能,后者则指行政机关对该事项作出处理结果的权力。⑨参见何海波:《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兼议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根据的重构》,《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虽然在语词表述上,滥用职权标准和超越职权标准共用了职权一词,但这两个标准中的职权一词的涵义却并不相同。超越职权既可以指超越管辖权,也可以指超越处理权。但是,滥用职权却只可能是滥用处理权,因为在管辖权问题上,须严格遵循法定主义原则,行政机关并无裁量的空间。⑩在有的案件中,法官认为超越管辖权也会存在着滥用职权的问题,这是值得商榷的。例如,在“路世伟不服靖远县人民政府行政决定案”中,靖远县人民政府非法干涉了依法成立的破产企业清算小组的职权。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指出:“县政府无权用这种于法无据的独特关系去影响他人,去为他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去妨碍他人的合法权益。县政府在靖政发(1999)172号文件中实施的这些具体行政行为,不仅超越职权,更是滥用职权。”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3期。尽管职权一词的涵义不同,但在处理权的范围内,滥用职权标准是可能与超越职权标准发生交叉的。例如,在前述“黄煌辉诉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中,丰州镇人民政府以超越处理权的方式,意在达成不适当的目的。此时,既可以认定为是超越职权的行为,也可以被认定为属于滥用职权的情形。
与滥用职权标准发生交叉的情形,还不仅限于超越职权这一标准。行政机关在行使处理权时,必须依据法定的事实、依据和程序作出。行政机关超越处理权,说明该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着事实不清、适法错误或违反法定程序方面的违法问题。①从这一意义上说,“超越职权”这一审查标准中的超越处理权,与“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以及“违反法定程序”三项审查标准在审查事项上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由于滥用职权与超越处理权存在着交叉,它也会与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和违反法定程序这三项标准在适用对象上发生交叉。有关这点,可以在“谢培新诉永和乡人民政府违法要求履行义务案”中得到印证。在该案中,被告永和乡政府违反《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四川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的规定,向原告谢培新提取的村提留费、乡统筹费和社会生产性服务费总额,超过了依法应当负担费用的一倍。四川省乐至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上述两个条例规定的“取之有度、总额控制、定项限额的原则,具有任意性和随意性”,为此撤销了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在判决依据上,法官便同时援引了超越职权、适用法律、法规错误和滥用职权这三项标准。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3年第1期。
在域外法上,同样存在着滥用职权标准与其他审查标准在适用对象上的交叉情况。例如在法国,越权之诉的撤销理由包括无权限、形式上的缺陷、权力滥用和违反法律四种。其中,违反法律是指除其他三种撤销理由之外的一切违法情形,主要包括事实不符合法律规定、法律根据错误和内容直接违反法律。法国行政法院在实践中往往回避适用权力滥用标准,而采用违反法律这一理由。③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8-549页。另可参见[法]古斯塔夫·佩泽尔:《法国行政法》,廖坤明、周洁译,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299-304页。这种审查标准间的游离现象就说明,事实不清和适法错误这两项标准,在适用对象上可以与权力滥用发生交叉。④王名扬教授认为,“权力滥用”与“无权限”、“形式违法”的内涵迥异。参见王名扬:《法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页。这似乎意味着,“权力滥用”不会与这两项标准在适用对象上发生交叉。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理由有二:首先,由于法国的“无权限”是指超越管辖权,所以它不与“权力滥用”发生交叉,这正好印证了笔者的判断;其次,考虑到在我国行政诉讼中,“法定程序”一词已扩展至包含了正当程序的内涵,因而至少在正当程序的范围内,“违反法定程序”标准会与“滥用权力”标准发生交叉。
从深层原因上看,滥用职权之所以会与《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第2项中的其他四种标准发生交叉,根源在于这五种审查标准在逻辑上并未遵循同一划分标准。在理论上,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活动,应区分以下三个范畴:审查事项、审查方式与审查结果。审查事项是指法院所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要素或部件,它解决的是审什么的问题;审查方式是指法院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准据,它针对的是如何审的问题;审查结果则是法院运用审查方式对特定事项进行审查后所得出的结论,即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所作的判定。其中,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事项包括管辖权限、事实认定、法律依据、程序要件和裁量权运用等五种;审查方式则有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两项,它们分别对应于形式合法性审查与实质合法性审查。如前所述,在管辖权限上,只会发生是否超越职权的问题;在裁量权运用中,仅存在是否滥用职权的问题。而对于事实认定、法律依据与程序要件这三项审查事项,则都可以接受滥用职权和超越职权这两项标准的检验。一旦无法通过检验,其结果就相应地体现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以及违反法定程序这三种具体的行政违法情形。行政诉讼中审查事项、审查方式与审查结果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表1来加以说明。
如果以上述审查事项、审查方式和审查结果的三分法加以检视,就可以发现,在《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第2项所规定的五种审查标准中,其实同时存在着审查结果和审查方式这两类划分标准。具体而言,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以及违反法定程序运用的划分标准是审查结果,滥用职权运用的划分标准是和超越职权则是审查方式。同时,由于审查方式是形成审查结果的原因,当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上述三项审查结果之一时,必然意味着其中存在着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的情形。立法者将这两类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一并杂糅规定在《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第2项之中,就同时犯了混淆标准和子项相容的逻辑错误,由此导致了这五种审查标准在适用对象上的相互交叉重合。由此可见,正是由于立法者在设计司法审查标准时所犯的逻辑疏忽,为司法实践中各个审查标准之间的交错运用埋下了伏笔。
三、滥用情形之二:被泛化理解为“违法”
(一)被泛化的“滥用职权”
在一些案件中,法官甚至宽泛地以滥用职权一词来指称行政机关的一种或多种违法行为。此时,滥用职权已经成为其他司法审查标准的上位概念,用于统称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等具体的违法情形。这是滥用职权标准在司法实践中被滥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笔者将这种意义上的滥用职权称为最广义的滥用职权。与广义的滥用职权涵义不同的是,它并无诸如目的不适当、不正当的考虑、行为反复无常、结果显失公正等学理上的滥用职权情形。这种最广义的滥用职权,完全可以与“违法”一词互换使用。
(二)泛化的具体情形
法官使用最广义滥用职权标准的案例,可见之于“薛谊花诉青铜峡市城乡建设局行政赔偿案”中。⑤参见同前注②,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书,第449-454页。在该案中,被告青铜峡市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违法要求原告薛谊花开设的毛衣编织店提前缴纳下一个月的城市卫生费。在遭到薛谊花拒绝后,城建局工作人员不仅扣押了薛谊花的电熨斗,还对她实施了殴打行为。银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城建局工作人员“超标准征收城市卫生费,并提前预收,强行扣押公民个人财产,殴打致伤他人”的行为属于滥用职权行为,并在作出的行政赔偿判决中,援引了《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的滥用职权作为判决依据。该案显示出法官以滥用职权一词囊括城建局各种违法行为的判断思路,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对滥用职权审查标准的涵义采取了宽泛的理解。
在另外一些案件中,当具体行政行为存在着特定的越权违法情形时,在行政机关欠缺学理上的裁量滥用情形的条件下,法官仍选择滥用职权标准作为判决的依据,而非援引《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第2项中的其他审查标准。“秦然等诉薄壁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便是例证。在该案中,被告薄壁镇人民政府为促使原告秦然缴纳车船税,对其驾驶的、所有权为秦小东的机动三轮车实施了扣押。在秦小东出具了车船税完税证明材料之后,被告仍拒绝解除扣押措施。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虽然在判决说理部分指出被告拒绝解除扣押的措施缺乏事实依据,但在判决依据上援引的却是滥用职权这一标准。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2000年第1辑(总第31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47页。而事实上,该案中的行政机关并无任何学理上的裁量滥用情形。在此,我们可以整理一下法官在该案中的判断思路:首先,是将滥用职权标准的涵义宽泛地理解为“违法”;其次,将被告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作出决定的行为视作一种具体的违法情形;最后,以这种最广义的滥用职权审查标准替代主要证据不足标准,进而判决撤销该行为。
与前案审理法官不同的是,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官并没有直接将最广义的滥用职权标准作为判决依据,而是仅仅在判决的评析部分持这种理解。在“仓山白湖印刷厂诉国家商标局恢复审查行为违法案”中,福州台江印刷装潢厂在1992年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如意”商标,但遭到驳回,台江厂未在法定期间内寻求救济。1997年,福州仓山白湖印刷厂申请注册“如意”商标,国家商标局经审定后作出了初步审查公告。之后,国家商标局以对台江厂的驳回决定存在错误为由,恢复了对台江厂申请的审查,并将其认定为在先申请。白湖厂不服提起诉讼。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国家商标局恢复审查申请的程序缺乏法律依据,且未撤销先前的驳回决定即恢复审查的做法有悖于正当程序要求,为此,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确认国家商标局的恢复审查行为违法。但在对该案的评析中,审理该案的饶亚东法官指出:“商标局纠正错误的行为没有法定的事由,也没有法定的程序,更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其纠错行为属于滥用职权的行政行为。”⑦同前注④,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书,第169页。从这段评析意见中也可以看出,法官也是以滥用职权一词来统称其他诸种违法情形。
与法官相比,当事人由于缺乏专业训练,他们更容易从宽泛的“违法”意义上理解滥用职权。在“洛江奇龙石雕厂诉泉州市城建监察支队行政赔偿案”中,泉州洛江奇龙石雕厂因厂房油毛毡被狂风掀起,实施了翻修搭盖。泉州市城建监察支队认为,这一搭盖行为属于原《城市规划法》中的擅自改建行为,在相对人不自行履行拆除义务后实施了强制拆除。泉州洛江奇龙石雕厂在上诉状中诉称:“搭盖行为既没有动到基础,也没有破坏墙体,并非改建项目而需要报批,根本不存在违法建设的问题。被上诉人硬套《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滥用职权,强行拆除上诉人的厂房屋顶铝锌板,是对上诉人合法权益的侵害。”⑧同前注④,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书,第329页。
(三)泛化理解是如何形成的
值得追问的是:上述对滥用职权概念极度宽泛的理解,为何频频地出现于法官和当事人之间?在笔者看来,这是受到了滥用职权一词的日常涵义的影响,并且这种日常理解因具有诸多实定法的支撑而得到了强化。
在日常用语中,“滥用”一词是指“胡乱地或者过度地使用”。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12页。相应地,行政上的滥用职权或者滥用权力,可用以指称行政机关胡乱或过度行使行政权力的行为。⑩行政权力和行政职权是两个具有密切关联的概念。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于,行政权力是在比行政职权更为宏观的层次上使用的,而行政职权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具体化。参见胡建淼:《行政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本文则是在同等意义上使用“滥用职权”和“滥用权力”这两个用语。它们是行政机关实施的各种违法行为的上位概念,用于统称所有的违法情形。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①[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便是诠释这种宽泛意义上的滥用职权或滥用权力涵义的一个生动注脚。就连在更具专业性的行政法教科书中,这种泛化理解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韦德在论述行政法的功能时,就指出:“行政法的最初目的就是要保证权力在法律的范围内行使,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保护公民。”②[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这些著作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支持着普通民众和法律人心目中对滥用职权一词的宽泛理解。
而在实定法上,对滥用职权一词的宽泛理解也颇有市场。《刑法》第397条规定的“滥用职权罪”便是一个明证。根据张明楷教授的总结,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该罪中的滥用职权情形主要有:“一是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③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93页。从这些列举的具体情形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滥用职权一词被用于泛指行政机关的多种违法情形。学者对《刑法》上的滥用职权内涵的宽泛界定,影响到了法官对《行政诉讼法》(1989)上的滥用职权涵义的判断。江必新法官在解释行政审判中滥用职权的低适用率现象时就指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有的法官存有顾虑,认为一旦以滥用职权作为裁判理由,行政机关的相关人员就可能以滥用职权罪被追究刑事责任。④参见江必新:《行政强制司法审查若干问题研究》,《时代法学》2012年第5期。这就证实了学者对《刑法》上滥用职权概念的宽泛界定对行政审判的影响。
即便在行政法规范中,在宽泛意义上使用滥用职权一词的现象同样俯拾皆是。例如,《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7年制定)第27条规定了应受行政处分的违纪违法行为,该条在列举了殴打、体罚等侵害人身权行为、压制批评与打击报复、违法摊派或收取财物、妨碍或干预执行公务这四种情形之后,在其第5项作了“其他滥用职权行为”的兜底规定。可见,立法者是将该条所列举的前四种违法情形视为滥用职权。这便是对滥用职权一词的宽泛理解。
返回《行政诉讼法》(1989)的文本之中时,由于最广义的滥用职权将其视为各种违法情形的上位概念,这就会打破该法第54条第2项中五种审查标准之间相并列的逻辑结构,导致其他四种标准被滥用职权所架空。为克服这种倾向,就出现了法官在不同的场合中使用不同涵义的滥用职权的做法。一方面,为了维持法条的内在逻辑,法官在判决依据中仅仅使用了狭义或者广义上的滥用职权。另一方面,受日常涵义的影响,或者是为了回应当事人提出的最广义的滥用职权主张,法官在较少受到专业用语约束的案例评析部分或自己的日常理解中,又使用了这种最广义的滥用职权,由此偏离了《行政诉讼法》(1989)上滥用职权标准的特定涵义。这充分显示了在运用滥用职权审查标准时,法官游走在专业语意与日常涵义之间的复杂心态。
四、结论
行政判决中所运用的滥用职权审查标准所存在的狭义、广义和最广义三种不同“波段宽度”的涵义是扩张性地适用滥用职权审查标准,不仅挑战了将滥用职权标准的涵义限定为滥用裁量权的主流学说,也与有学者所描绘的法官在司法实践中隐匿适用滥用职权标准的图景构成了鲜明反差。⑤郑春燕副教授通过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黄金成案”和“肇庆外贸公司案”后发现,法官在这两个案件中借助于其他审查标准实现了对行政裁量的审查,从而回避适用了“滥用职权”或“显失公正”的审查标准。参见郑春燕:《“隐匿”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观及其修正——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相关案例为样本的分析》,《法商研究》2013年第1期。之所以会产生上述问题,根源在于《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所采取的“滥用职权”这一表述存在内在缺陷。一方面,立法者在设计《行政诉讼法》(1989)第54条第2项的五种审查标准时,并未遵循同一划分标准,致使滥用职权标准与超越职权,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这四项审查标准在适用对象上发生了交叉。另一方面,滥用职权一词还极易与作为日常用语的“滥用职权”、“滥用权力”发生混同,使得其涵义被宽泛地理解为“违法”。就这样,随着一个个判决的作出,滥用职权这一司法审查标准日益偏离了立法者和学理上所设定的滥用裁量权的特定涵义,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宪法变迁的规范语义变迁现象。⑥“宪法变迁”是解释宪法规范变动现象的一种理论。首提“宪法变迁”这一概念的德国公法学巨擘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在阐释宪法变迁的成因时,就提出了一种“基于司法解释的宪法变迁”,它是指宪法条文虽未曾发生变动,但其规范涵义却因法官在个案判决中作出的解释而发生改变。参见[德]格奥尔格·耶利内克:《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论》,柳建龙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0-27页。借用耶氏的这一分析框架,也可以将本文所揭示的、法官在未修改《行政诉讼法》(1989)条文的情况下变动其规范涵义的现象,称之为“基于司法解释的行政诉讼规范变迁”。
令人遗憾的是,对于滥用职权标准的上述缺陷,并没有引起立法者的应有重视。2014年1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依然保留了原来立法中包括滥用职权在内的五种审查标准。对于一部法典来讲,其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恰恰取决于内在的逻辑自洽性。为了保持各种审查标准之间相对清晰的内涵分界,引导法官正确运用各种司法审查标准,还是有必要在未来对上述五种司法审查标准作进一步的修改。对此,笔者的建议是,将其中的超越职权标准修改为“超越管辖权”,并将滥用职权标准调整为“滥用裁量权”。如此一来,超越管辖权这一标准可以避免在适用对象上与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发生交叉。同时,滥用裁量权的表述,也将使该标准的作用领域回归至学理上所界定的行政裁量领域,而它与日常话语中的滥用职权之间的语义关联,也可以被彻底斩断。
当然,考虑到《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刚刚落下帷幕,可以预期的是,立法者在短期内不会对该法作出再次修正。为避免在新法实施过程中本文揭示的滥用职权标准被滥用的现象再次浮现,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抽象性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或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将滥用职权与超越职权这两项标准的内涵分别明确限定为滥用裁量权和超越管辖权,也是一种可行的弥补方法。
(责任编辑:姚魏)
D F74
A
1005-9512(2015)01-0093-09
施立栋,清华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写作过程中,何海波教授、郑春燕副教授、陈天昊、黄娟等师友先后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