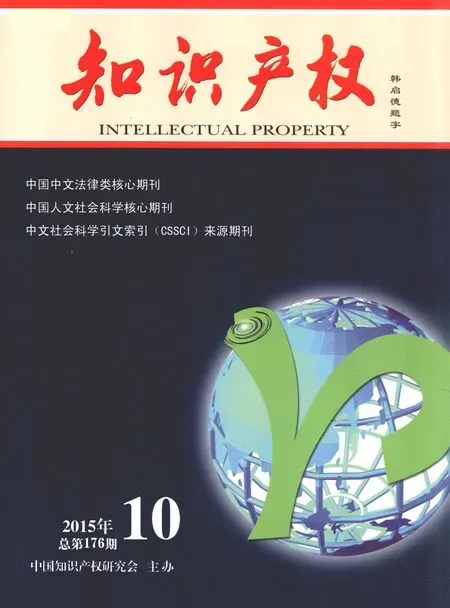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
刘春田
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
刘春田
内容提要:民法总则是人身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制度的总章程。知识产权是与物权属于同一逻辑层次、处于同一位阶的民事财产权,知识产权法是民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法制度应将知识产权位列财产权利之首,这是财产制度漫长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逻辑的,也是实践的。建议我国民事立法转变财产观念,在民法总则中将知识产权列为首要的财产权利,这将成为我国对各国民法典的一个超越。
知识产权 财产权利 民法总则 民法典
民事财产权各有个性,又具共性。民法制度据其根本,择其共性,容其个性,构建组成民法典中的财产制度。其中,民法总则中如何处理好知识产权问题,事关重大。民法总则是个纲,是人身与包括知识产权制度在内的财产制度的总章程。它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将最终决定知识产权的性质与面貌。目前看,民法学界投入的力量,偏重于对人格权制度、民事主体制度和财产制度等传统问题的持久、深入的思考,欠缺对由于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财产领域的革命性变革的新现象、新问题的关注、探索与研究,导致迄今对民法制度的设计忽视了被经济生活日益彰显的以“知识产权”以及“服务“等由“知识、技术”主导的崭新的,并日益增值上升为占主导地位的财产形态的关注。在现有由学者展示的民法总则设计方案中,因陌生与偏见,天然的将它们排斥在民法典的主流财产制度之外。这既是一种失误,也是一种落后。
民法典如何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包括对知识产权的性质、知识产权法的性质的表述以及在立法上的制度安排,如何结构,如何取舍,将影响知识产权法律的命运和实践,反过来也影响民法典,影响民法制度的严整性、系统性、科学性,影响整个民法的面貌和命运。作为“社会重器”的民法制度,在合理与愚蛮、“巧”与“拙”的设计之间,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些许失误,用于实践,足以大大增加制度的运行成本,严重削弱制度的力量,降低国家的竞争力,最终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安全和经济运行与发展。这让人常常回想起20世纪80年代制定的合同制度,囿于认识水平,也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将统一的合同行为分别按主体、地域、标的,设计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这三个合同制度,尽管1999年将其合于一统,但若认真算一笔账,在近20年的时间里,国人为学会和运用这些“器物”,因我们的无知、怯懦,究竟凭白多花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降低了多少发展速度,延缓了多少建设项目,这无疑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今天的中国,经济体量之大,制度设计的任何失误,影响都难以估量,更要慎之又慎。本文认为,民法制度究竟如何安排,尽管要取决于立法者的主观认识和意志,取决于法律学者的学术观点和制度价值取向。但是,法学毕竟是科学,立法毕竟是以遵循科学为前提的技术,制度客观上要求必须与相应的技术匹配。如何规范知识产权,归根结底取决于技术发展的要求,取决于知识产权自身的性质,取决于它所规范的社会关系的客观属性,取决于民法制度的系统化要求。常识告诉我们,科学、理性的认识不会自发产生,它需要我们的探索与研究,需要学界的表达与辩难,需要克服传统知识和观念形成的偏见。而克服与纠正偏见正是创新的重要品性之一。本文认为,民法总则中要厘清的以下几个问题是最终影响民法典与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关键。
一、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
性质是事物分类的根据。权利的属性决定于它所反映和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这种关系是客观的,不因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与传统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中的专利权、商标权等需经过可称之为“要式法律行为”产生的程序方能确立。对中国这种有计划经济历史传统的社会,很容易造成对专利权、商标权性质的误解,甚至影响制度设计。拂去表象,究其本质,知识产权所反映和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因而具备了民事权利的最本质的特征,固为民事权利。民事权利被称作“私权”,民法被称作“私法”,私法调整具有平等地位的私人之间的人身与财产关系,例如民法、商法。这种平等主体之间所发生的“私”的事务,均适用“私法”来调整,它和主体的“公”、“私”性质,以及他们的地位高下没有关系。所以,当国家、政府从事“私”的事务时,比如,政府与自然人、法人发生交易、为市场行为时,也是作为“私法”的主体,适用民法的规则,平等、等价、有偿地进行交易。唯其如此,世界贸易组织《TRIPS协定》前言中,才把“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recognizing that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private rights)作为各成员开宗明义的最重要的共识之一。表面上看,这只是对知识产权属性的客观表述,但对不同经济体之间却意味不同、作用重大。对于具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和成熟的法治传统的社会而言,此话天经地义,充其量不过是对一个不争事实的重述,但是,对于缺乏“私权”和“私法”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无疑具有特殊的、重大的现实作用和长远的历史意义。这一表述所确立的原则和理念,对目前我国现实知识产权制度而言,是一个历史性的超越,若能在《民法典》的制定和知识产权法制建设中得以充分、有效的贯彻,在民法制度中作出恰当的安排,将决定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根本面貌和立法走向,必将有助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整个民法制度整合于一统。
要彻底厘清知识产权的私权本质,必须拂去公权力作用的表象。所谓公权力,就是公法上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国家对于个人、法人的权力,比如征收税金的权力。法治国家,私权是公权的基础。在私权的运行机制中,离不开公权力的辅助,如审查、确认、登记乃至于公示。如同物权中的房地产所有权、车船所有权一样,有些知识产权在权利形成、权利赋予、权利行使、权利请求和权利救济中,也需要公权力的参与。最突出的是专利权、商标权的运行机制,公权力参与其中。若没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对当事人请求事项中的技术问题以及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等问题进行必要的审核,专利权、商标权这种独占的、排他的权利就难以确认。这种现象很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使人对专利权、商标权,以至于整个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产生疑问与动摇,出现了“私权公授”、“知识产权是行政许可”和“知识产权私权公权化的趋势”的错误观点。有必要指出,社会生活中公权力与私权往往交织在一起,但二者却有本质的区别。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植根于私权土壤,生长于私权之树。其间即或有外力干预其生存空间或外在形态,或剪枝,或移植,都不改其存在、价值和生命之本质。在私法体系中,私权和公权力之间,私权始终居于目的、实体、主体、第一性的地位,公权力则居于手段、程序、辅助、第二性的地位。在私法体系中,为保障私权秩序的合理、公平,经常需要借助于公权力的介入,须有公法规范。但是公权力在其中也只是辅助的手段,体现公权力的是程序规范。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公权力具有关键的作用,但是,公权力的作用再突出,也不可能超出或改变法律对私权确认的实体性规定,更不可能主辅颠倒。在知识产权法的机制中,公权力机构,比如商标局或专利局的职能,就是依法确权、私权登记,它们对公民或法人提出的确认私权的请求所作出的决定,依程序规范有义务给出依据,这些依据是商标法或专利法等私权法的规定,而非行政权力。构思该理由的方法也是私法的,而非公法的。按照私法的逻辑,该理由不仅是可以理解的、正当的,而且是可以证明的。这既不会造成私权利与公权力的混合,也不会导致私权属性的变异,更不会出现私权公权化。
知识产权作为民事财产权利的一个类型,与传统民事财产权利,没有本质的区别。知识产权是与物权属于同一逻辑层次、同等重要的民事财产权。
二、知识产权与物权是同一位阶的民事财产权利
现代财产法主要由知识产权法、物权法、债权法这三个相互区别、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部分构成。财产权也是由相应的物权、知识产权和债权组成的。知识产权作为财产权,其内容和特征,既不同于物权,也不同于债权。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虽均作为民事财产权,但又互相区别,原因就在于它们各自的对象不同。按照传统物权理论,物权产生的前提通常是占有一定空间,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能够满足人们一定物质或精神需要,表现为动产和不动产的,有体有形的“物”。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物的范围也在扩大。一些无体无形、却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比如电,也成为物权的对象。债权产生的前提是以作为或不作为方式存在的“行为”。知识产权的产生前提,是以创造成果和工商业标记方式出现的的“知识”。由于债权的对象是特定的“行为”,故决定了其义务主体是特定的人,其权利具有相对权的特征。物权和知识产权分别表现为对“物”和“知识”的控制、利用和支配,其义务主体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因而是法定权利,其权利具有绝对权的性质。可见,债权与知识产权的区别显而易见,毋庸赘言。需要弄清的是同是绝对权利的知识产权与物权的相同与区别。
知识产权发生的前提,或曰对象或标的不同物权。物权的前提是动产和不动产以及其他客观存在的物理学、经济学和法律学意义上的“物”。知识产权的前提是物理学、经济学和法律学上的“知识”,是不含物质实体的思想或情感的表现形式,是非物质的客观存在,在“虚”中之“拟”。
知识产权的独占、排他性程度弱于物权。物权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行为,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利益,不危及社会公众和国家的利益,不违反公认的社会公序良俗,不滥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其行使权利的行为是绝对的和排他的,其他人无权为与物权人相同的行为。法律对物权人权利的限制规定,是个别现象。相比之下,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除了要遵循与物权人行使物权时的相同约束条件之外,法律还明确、具体、广泛地对知识产权人的权利做了合理的“剪裁”,规定了对知识产权的限制制度,主要是“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和“强制许可使用”等制度。也就是说,法律把原本赋予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某些权利领域,通过设立权利限制制度,同时赋予了公众,使其得以与权利人共享。这种情况在物权法中是鲜见的。
知识产权比其他绝对权利更容易受到侵害。物权人的利益既可以借助法律实现对利益的控制,也可以通过事实上对物权对象“物”的占有来实现其利益。知识产权权利人则无法通过对其“知识”实行“占有”来实现其利益,必须仰仗法律的保障。
当知识产权与物权发生冲突时,知识产权通常要让位给物权。在一件实体物之上可以并存着物权与知识产权。但是,对附着于特定物质载体之上的“知识”的权利,同它所附着的载体之物权,是可以分离的。在物权和知识产权分别属于不同权利人的情况下,当两个权利人分别处分物权与知识产权,且不能就此达成一致时,尽管两种权利并无高下、优劣、尊卑之分,但基于物权人依法享有的对实物的独占、排他的支配权,往往导致知识产权因遭到物权的对抗而难以实现。
知识产权的期限不同于物权的期限。作为财产,知识产权具有法定的期限,期限届满,权利便归于消灭,创造成果进入公有领域,成为人人可以无偿利用的公共资源;商业标记的注册,如商标、商号等,也有法定的时间效力,期限届满可以续展注册,法定期限不续展的,也进入公共领域。物权则无此法律品性,物权的期限与物的自然寿命竞合。
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其价值无论是质的规定性还是量的规定性,也都不同于物权。
尽管知识产权与物权等传统财产权在权利发生的前提、权利内容、独占性程度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是在财产性、私权性、权利位阶等本质特征上,又是相同的。知识产权与物权,属于同一父母血缘的私的财产权基因下的同“姓”兄弟,相互之间的差别,不足以改变物权、知识产权等本质上的共同的财产属性和在逻辑上处于同一位阶。
三、知识产权法是民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知识产权为私权。知识产权法为财产法。目前,各国知识产权法多为单行法律形式存在,如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法等。尽管知识产权理论中存在知识产权包含人身权内容的观点,实践中也有这样的立法例,但知识产权本质上是财产权,知识产权法属于财产法却是不争的事实。
应当明确,知识产权法是民事普通法,不是民事特别法(顺便指出,我国新设立的三家知识产权法院也是普通法院系统的组成部分,不是所谓“专门法院”或“特别法院”)。知识产权法就是民法本身,知识产权法与民法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非一般与特别的关系,它与民法的其他内容共同构成民法。所谓特别法,是以某一类别法律的普通体系的存在为前提,由此派生出来的适用于特殊主体、特别地域或特定时段的特别规则体系。比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均以宪法为前提,适用于香港、澳门地区的居民,为期50年的法律,故为宪法特别法。知识产权法是基础性的民事财产法,它不是从传统财产法中派生出来的特别财产法规则,它所调整的,不是个别的、特殊的、局部的民事关系,而是社会生活中普遍适用的基本规则。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法与物权、物权法处于相同的逻辑层次,分别属于民事基本财产权和民事财产基本法。
知识产权、物权、债权,虽然表面驳杂,物象各异,在权利对象等外在形式上,也有明显的差别,本质上却是“性相近,习相远”,属于同一“血缘”的财产权。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是在无制度可延续,无理论可遵循,无实践可参酌,无人才可延揽的情况下,在一个与知识产权制度水土不服的计划经济的土壤上,白手起家,凭空建造起来的。初识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的中国法学的先行者们,更多看到的是知识产权制度与传统财产制度的表面差异,难以形成对其共性和本质认识的理性成果。立法工作分散在不同政府部门起草的基础上完成的。相互间缺乏观照与衔接,更没有系统整合。因而影响了各项单行知识产权法律与同步建设的民法制度的共融性,致知识产权法游离于民法体系之外,给法律实践造成先天的困难。比如,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都曾经长期自设民事主体制度,2001年《商标法》和《著作权法》才作修正。尽管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将知识产权规定于民事权利之中,为从宏观上廓清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提供了思维框架,但是迄今仍有知识产权“去民事权利化”和“去民法化”的倾向,既阻碍了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整合,也影响了知识产权法自身的系统化,给法治建设造成困难。目前,我国再次兴起民法典建设。其中,有关知识产权法是否在民法典中安排、如何安排的问题仍存比较大的争议。其中,不赞成知识产权编入民法典观点的理由之一,笼统地认为,受技术发展的影响,知识产权法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开放式的规范体系。若将其置于相对稳定、系统化的民法典中,会损害民法典的稳定性。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将技术、艺术等日新月异、快速进步和变化的现象,与利益关系的相对稳定,以及规范利益关系的规则的相对稳定,这本属于三个层次的问题,混为一谈。实际上,日新月异的物质产品,随着技术发明创造的推广,不断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只是因为人类已习惯于对物质产品的认识,不假思索地将包罗万象的产品抽象为“物”,进而归为物权的对象。同理,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技术产品、艺术作品推陈出新、气象万千,也都可以被抽象为“知识、技术”,都不超出知识的范畴,在市场条件下,所产生的利益关系并不随技术、艺术的多变而产生质的变化,都可以置于相对稳定的法律关系的调整之中。
技术是进步的,社会是发展的,民事法律必须反映和服务于时代的变迁。民法自罗马法始,历经漫长的形成历程,其间也发生多次变革,才由被恩格斯所称道的“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占统治的社会的生活条件和冲突的十分经典性的法律表现,以致一切后来的法律都不能对它做任何实质性的修改”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卷,第454页。的制度演变为民法。罗马法的精髓是与时俱进的。当年,欧洲的先贤,若顾地窥天,作茧自缚,固守罗马法,便没有后世的《法国民法典》;若固守《法国民法典》,便没有《德国民法典》 。民法典是一个规则系统,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的知识体系,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民事法律的法典化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非一成不变。“体系性工作是一种永续的任务……没有一种体系可以演绎式地支配全部问题;体系必须维持其开放性。它只是暂时的概括总结”②[德]卡尔·拉伦茨著:《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5页。。知识产权是否属于民事权利,应否编纂入民法典,是事物内部自身的本质属性和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错,知识产权作为财产权利,相对于传统物权、债权等财产权而言,的确相对年轻,人类对它的认识、思考、归纳和提炼也还不够成熟,但这些情况都不足以改变知识产权作为类型化了的基本财产权的属性,也不足以否定它和物权居于法律秩序中处于同一位阶的客观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法典中理所当然地应当有知识产权法一席之地。民法典的制定乃是基于法典化的理念,将涉及民众生活的私法关系,在一定原则之下作通盘完整的规范。③参见 王泽鉴著:《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民事立法的形式理性,不仅是逻辑的要求,也是实践的需要。“虽然法律从表面上看起来是非理性的、混乱的和特殊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挖掘得够深,并且知道自己正在寻找什么,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法律其实是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统一的规则体。”我们的“目标是将法律展示为一个以一般性法律原则为基础的系统而又融贯的结构”④[英]马丁·洛克林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7页。。立法既是一种从实践出发的科学研究过程,也是一种技术发明和艺术创造活动,既需要历史知识和科学方法,也需要着眼现实的态度和面向未来的智慧。法律学作为科学,尊重理性。立法作为技术,着眼于效率、性价比。不同制度的投入产出会有不同的性价比。因此,衡量立法的优劣不可以任由主观臆断,而是有客观尺度的。法治应当是理性的,立法应当排除不确定性,法治终将克服一时的认识局限。至于在立法技术上如何处理,建立何种民法典的系统模式,是将知识产权诸项单行法律经编篡独立成篇,全部纳入民法典,还在民法总则中对知识产权的一般性规则作出规定,留出接口,用以指导知识产权的诸项单行法律,以便给各单行法律的修订留出机动、灵活的空间,还是编篡为独立的知识产权法典,都可以作为选项。上述各种模式有俄罗斯、德国、越南等立法先例供参酌。不难看出,不同模式所花费的心力有很大差别,其中,俄罗斯民法典将知识产权法彻底民法典化,既需要立法者的勇气,也需要法学家的理论功底、智慧和一以贯之、坚韧不拔的科学态度,还需要决策者的战略眼光和历史担当。作为现代国家的“基础设施”,民法典是奠定基本的经济秩序,保障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百年大计,俄罗斯民法典开创了民法典的新模式。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处于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已经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民法制度作为基本法律保障,“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披坚执锐,迎潮而上,还是知难而退,我们也面临选择。
四、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
知识是一切财产的源泉与根据。知识财产是人类对财产的真正发现。民法制度将知识产权位列财产权利之首,是财产制度漫长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逻辑的,也是实践的。
知识创造和改变世界。现代社会,知识产权是上述改变的法律保障。众所周知,知识产权是近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它源于长期的贸易习惯而转变成的新型财产制度。创造成果是产业经济的发动机。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知识产权法律创造了以“创新驱动发展”的财富生产的新模式。知识产权制度把个人才智的结晶转化为巨大的社会财富,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对这一发展趋势,大多民法学者的关注是不够的。平心而论,囿于欠缺法治传统,我国大多民法学者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民法学,对于深入认识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现实,已是应接不暇。他们更多地关注对物权等财产制度的思考与设计,很难有剩余的精力旁顾随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出现的新的财产形态——知识产权。但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是,主宰我们这个世界的不是物质,而是人。财产是人的重大发现。使客观世界的物转变为财产的是知识。人对这个世界的唯一贡献是创造知识。如果说物是黄金,知识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点金术”,知识是一切“物”产生的真正原因,“物”是知识的结果。没有知识便没有“物”。知识产权制度发生以来,知识又成为“物权”发生的根据。从宏观上看,在全球三大贸易中,技术与商业标记已成为贸易的主要诱因,其中,知识产权的价值含量在全球贸易的总市值中,已占到绝对的主导地位。今天,知识产权已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无关大局的小角色,而是越来越成为当代财富的“巨无霸”,成为当代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角。知识产权制度已成为现代财产制度的关键与核心,成为财产的主宰。在微观上看,无论市场上,职场中,还是在家里,每一位身处其中的现代人,衣食住行,作息娱乐,从头到脚,品头论足,汽车、飞机、电脑、手机、衣着鞋袜、背包钱袋、沐浴护肤、美容化妆、医疗卫生、健康保健、香烟名酒、干鲜水果、蛋奶饮水、微信微博、网络购物、电影电视、报纸传媒、音乐美术、文学戏剧……我们每个人每日每时都自觉不自觉、主动或被动的被上述生活元素中无数的发明、商业秘密、外观设计、文学艺术和各类商业标记等知识、技术支配、决定、改变、统治和主宰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易言之,没了这些,我们的生活就手足无措,失了方寸。比如,哪怕有几个小时离开手机,就足以让你六神无主,惶惶不安。其间,真正让人在意的是手机所承担的行为功能,而不是作为功能载体的那件“物”。赋予物料以不同形态,组合成为“物”,并使之具有各种功能的是知识、技术,而不是那些物料。可见,知识、技术才是“物”的灵魂,是物质财产的生命、真正价值和存在的原因所在。一言以蔽之,没有知识、技术就没有“物”,就没有我们今天的正常生活。当代世界,没有知识产权就无法建立稳定的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的机制就会难以为继。现代经济生活的实践告诉我们,知识产权日益彰显其财产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对此,我们不可以“徒见金,不见人”,只认黄金,不识“点金术”。
可见,财富的本质是人的发现。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实践上,创造都先于、优于劳动,创造成果都先于、优于劳动成果。精神财产和物质财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精神是物质的主宰。精神创造是一切物质财产的逻辑起点和发生的原因,没有精神创造,便没有物质生产。自然界纯粹的物,如果没有人类的心智介入,没有人类物质与精神的需求,没有知识作为“点金术”赋予死物以生命,赋予物以各种用途,注入价值。原始的单纯的物一无所用,一钱不值。它们始终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不是经济、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是精神创造决定了物质财产的有无,规定了物质财富的样态,决定了物质财产所蕴含的价值的多寡。总之,没有知识,就没有物质财产。精神创造化腐朽为神奇,是一切物质财产的产生、发展、变动的源泉。因此,精神财富必然先于、优于物质财富。按照制度发生的历史,虽然知识产权远远晚于物权。但知识产权自产生之日,就天然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逻辑的、实践的先于物权,优于物权。如果没有偏见,知识产权贵为财产权利体系中“上游权利”作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技术、制度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彰显,作为一个科学发现,昭然若揭。
技术与制度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按照传统理论,技术与制度一个属于生产力,一个是上层建筑,二者泾渭分明、形同云泥。实践中它们如影随形,浑然一体。制度缔造者的任务,就是将制度与技术弥合在一起,让他们形神合一,佑护我们的生活。在我们重启民法典的立法工作之际,应当继续弘扬百多年前《德国民法典》面向实践、面向未来的精神,做出新的开拓。当年,德国法学家面对百年前堪称典范的《法国民法典》,他们没有因循守旧,而是与时俱进,制定出在当代同样堪称典范的《德国民法典》。
中国民法典应当遵循同样的逻辑,没有理由回避现实,无视21世纪技术、经济与社会发展,没有理由抱残守缺,更没有理由从《民法通则》确立了30年的我国财产制度格局上后退。回首1986年,在计划经济时代,当时的立法工作者能够力排众议,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法通则》中采用知识产权这个纯属市场经济的私权法律概念,并将其列为与物权等财产权并列的独立的财产形态,既反映了我国老一代民法学家的远见卓识,也反映了当时立法者的高瞻远瞩,表达了立法机构的担当精神。《民法通则》作为我国民事立法的典范是法学界的共识。《民法通则》对知识产权的安排,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创新,是法治的重大进步。本文特别强调,《民法通则》不是法治建设的负资产,赋予知识产权以独立财产权地位,与物权等财产权利并列,不是《民法通则》的败笔,知识产权不应是被“高抬贵手”,勉强被纳而屈居人下的“侧室”,更不是不登大雅的蛰居“外宅”,它理应与物权等同居财产权利的“正室”。知识产权制度对中国民法典不应成为一个急于要甩掉包袱。今天,民法典的制定应当继承《民法通则》的创新精神,与时俱进,客观、理性、事实求实的面对今天的财产关系现实,对知识产权做出一个与它的地位与作用相匹配的恰当安置。
本文建议,我国民事立法转变财产观念,在民法总则中将知识产权列为首要的财产权利。这既符合我国重视精神创造的传统,也是对各国民法典的一个超越。
此外,本文顺便提及,在技术的推动下,金融、保险、医疗保健、电信、电子商务、海运、空运、快递、会计、工程、咨询、法律等“服务”也作为既有别于物权,也有别于知识产权的新型财产,被列为贸易对象。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1980年到2012年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从7707亿美元上升至85022亿美元,增长十余倍。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0)的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创造的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了70%①参见 仲鑫、丁秀飞 :《服务贸易技术结构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载《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第121页。。世界贸易组织早在20多年前就将“服务”作为独立的贸易对象,与货物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并列为全球三大贸易进行规范与调整。应当看到,社会进步和市场需求将使“服务”的技术附加值日益提高,各种服务及服务产业日渐渗透进入我们的生活,并最终促成“服务”成为一种独立的财产形态和类型化的私权加入财产权利的队伍。这些正在悄然突破传统的财产构成格局,改变着传统的财产观念。对此,民法学必须做好思想准备,适应技术进步,顺应历史潮流。当前,“服务”业在我国蓬勃兴起。我国民法学界应当看到这一趋势,民事立法在重视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应当注意研究、重视对“服务”的规范与调整。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is the general statute of personal system and property system inclu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system. Like real property,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civi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y both belong to the same logic level and the same ra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s an integral part of civil law. Civil law system rank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he fi rst place of property rights,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a long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roperty system, and it is not only logical, but also practical. Chinese civil legislation should change the thinking of property concept, and rank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the primary rights in the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which will be a progress compared to civil code of other countri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perty rights; general rules of civil law; civil code
刘春田,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