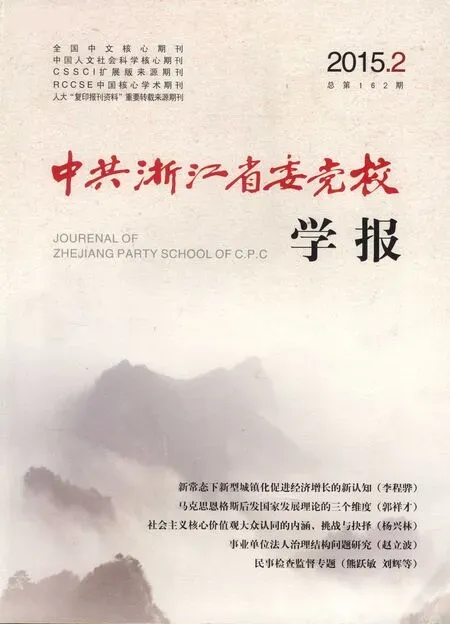论舒芜对“胡风集团”的看法与态度
论舒芜对“胡风集团”的看法与态度

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日报》编辑部编辑,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
②参见“部分‘胡风分子’及受‘胡案’牵连者名单及情况介绍”,晓风:《我的父亲胡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2页。
□孙君
摘要:作为共和国时期涉及人数众多的文艺界冤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键当事人物,对于舒芜的判断学界始终存在争议。而从舒芜自身的心态和思想来看,我们从众多史料中发现,舒芜认为胡风存在宗派主义和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小圈子”的意见始终没有改变,且他认为胡风存在台前幕后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两面,但他对胡风“两面派”行为的揭露和不满表现得十分节制。直至晚年,舒芜虽有反思,但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那个时代的常态,不存在品德问题,已承担应负责任。因此,从舒芜自身的角度来说,当年的胡风事件并不是他一人所能决定,也不是他一人所能承担得起所有责任的。
关键词:舒芜;“胡风集团”;态度
收稿日期:2014-10-08
作者简介:孙君,绍兴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对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指挥部指挥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中图分类号:D232文献标志码:A
60年后,胡风、舒芜等当事人多已作古,但是围绕胡风案件,围绕舒芜,许多观点仍在交锋,可谓争议不止。特别是如何看待舒芜利用私人通信撰写文章公开发表,以及舒芜究竟应该在胡风案件中承担多少责任,舒芜究竟有没有真诚忏悔等等,仍是当代思想史、文化史上一个沉重的话题。作为胡风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舒芜已于2009年8月21日离世。新时期以来,关于胡风、胡风集团的相关事件、相关细节、相关人员,舒芜曾多有撰述,本文试以考察舒芜当年以及1980年以后,乃至晚年的行为、心态和思想状况,解读舒芜眼中的胡风集团及其成员,并力求最大限度、最为逼真地描述、叙说、还原一个真实的舒芜。
一、舒芜认为胡风存在宗派主义和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小圈子”的意见没有改变
舒芜在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中的“贡献”,使其在当时即被胡风及其身边相关人员反感、排斥、谩骂*舒芜自述与绿原交往,“过去,在我发表‘检讨’文章之后,绿原给胡风的信中也曾把我改名为‘吴止’,是‘无耻’的谐音”。《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页。当时胡风与有关人员通信,也每以“无耻”称舒。,胡风集团平反以后,更被广泛诟病。舒芜为什么要写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致路翎的公开信》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这三篇文章,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锻炼成狱,究竟起了多少作用?
《论主观》1945年1月在胡风主编的《希望》第一集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党内理论家对之进行激烈批判,规格之高,力度之大,为作者舒芜始料所不及。1945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负责人冯乃超专门召集会议,集中批判《论主观》和《希望》杂志,茅盾、叶以群、蔡仪等在会上发言。接着周恩来又专门召开会议,批判《论主观》,不过,开会后,“关于《论主观》只谈了几句。因胡风向周恩来声明:他在《希望》上发表《论主观》,‘是想引起批判’,《论主观》‘里面只有一个论点我能够同意,’于是‘总理一听就完全了解了我的态度,马上把问题放开了’”*《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但是事情并没有完,1945年11月,随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胡乔木,又专门约舒芜谈话。据舒芜记述,11月10日下午,“胡乔木说我的《论主观》、《论中庸》是唯心论,我说不是,彼此往复争辩”。“次日上午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接着谈,胡风陪我同去,在座旁听的还有冯乃超、邵荃麟,又是我同胡乔木往复争辩,胡、冯、邵皆未发言。辩到中午,胡乔木激动起来,站起来拍桌说:‘你这简直是荒谬!’”*《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页。对于这次争论,舒芜对胡乔木“两句总结性的判断印象极深刻,一是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之一,是把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同无产阶级革命性区别开来,而你恰恰是把两种革命性混淆起来。’他的另一句判断是:‘毛泽东同志说过:唯物论就是客观,辩证法就是全面。而你的《论主观》恰好是反对客观,《论中庸》恰好是反对全面。’他就这样提纲挈领地把我判断为与毛泽东思想针锋相对的”*《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3页。。
建国以后,舒芜任广西南宁高中校长,当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搞政治,搞思想改造。作为校长,工作重点是掌握政治大课,主要是根据当时各种权威的政治文件精神讲形势*《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215页。,同时,作为建国之初“镇压反革命”、“城市民主革命、”“土地改革”等各项活动的组织者、参与者,舒芜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照舒芜自己的话说,“这些实际的工作,益发使我对改造思想的迫切性有所认识,一边工作,一边就想怎么样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来改造思想”*《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觉得“面对我们自己的政府、自己的政权,理所当然应该特别地保持步调一致,不应该留恋旧的东西”,“不改造”“要落伍”*《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而此时,胡风明确说《论主观》是个公案,“迟早要公诸讨论,主张我由被动变主动,该解释的解释,该做自我批判的做自我批判”。胡风对舒芜准备暴露思想实际以改造思想的方法和体会,极为赞同,一直鼓励舒芜要更加深入下去,学习毛泽东思想。在舒芜看来,胡风的这些意见,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主动改造思想,做自我批评,这对舒芜产生了很大影响*《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这就是舒芜自述的写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缘起。关于写作的动机,牛汉另有一说,“舒芜1938年在老家加入共产党,后来自首,整个支部自首了。建国后,自首的性质和叛徒差不多。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隐患,舒芜内心难免恐慌。要有新表现也在情理之中”*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8页。。而1953年又发表《致路翎的公开信》,正是为了进一步表明态度。为印证自己的判断,上世纪90年代初,牛汉在通电话时试图了解其内心的真实情况,但舒芜回避了*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18页。。不过,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或者各种因素兼而有之,决定、决心检讨,是一定的。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检讨,或者进一步说,这篇检讨文章怎么写?
1951年12月,曾在鲁艺参加延安整风的陆地等人,与舒芜一起参加土改时,向他介绍了延安整风及周扬作检讨过关、重获信任的情况。舒芜由此豁然开朗:做检讨很正常,也很平常,做好了成效很大;“思想改造是无情的,是对事不对人的”,所以用词得重,下手得狠,否则起不到效果*《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4-225页。。对自己当然得下狠手,光是对自己呢,还是要牵扯别人,如果涉及到别人,那么,怎么分配“火力”?好在乔冠华提供了现成的经验。1945年3月初,胡风在给舒芜的信中转述,乔冠华直接从德文翻译马克思《费尔巴哈论纲》,重申“‘感性’的原则非强调不可”,说明乔冠华“这时的观点同1943年他们提出要重视‘感觉’还是一致的”*《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但在1948年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因以于潮笔名写作《方生未死之间》而作检讨的乔冠华,却是以批评胡风来取代自我批评,即使在行文中实在回避不了自己时,也只批于潮而不涉及乔冠华,即没有承认甚至没有点破于即是乔。舒芜当时就看到了这些文章,这种文章笔法,舒芜可能确实前所未闻,但今日一见,这种金蝉脱壳式的洗刷上岸抑或立地成佛,是否对舒芜产生了某种触动呢?甚至于是否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呢?或者说是给年轻的舒芜上了一课呢?胡风女儿在对乔冠华这一做法表示气愤的同时,也看到了乔、舒之间的“渊源”:“用批判胡风来做‘自我批评’,这可真是滑稽!况且,全文也并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的味道,连将‘于潮’明确承认为‘我’都没有,这叫什么‘自我批评’呢?可是这种做法却能得到‘肯定’,难怪几年后舒芜也就如法炮制,用批评胡风和路翎等人来做‘自我批评’了”*晓风:《我的父亲胡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笔法已经确定,接下来的问题是自我批评文章的主题,即批评自己从何入手。舒芜觉得自己承受的最大压力,就是《论主观》和《论中庸》两篇文章,因为胡乔木曾经明确指出“这两篇文章和毛泽东思想是完全针锋相对”*《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的,更严重的说法是,《论主观》就是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牛汉在其口述自传《我仍在苦苦跋涉》中,说舒芜的《论主观》“发表前和胡风商讨过,但后来他不敢承认。《论主观》是针对1942年毛的‘讲话’的。”牛汉明确指出《论主观》是反毛“讲话”的,但没有提到这样立论的依据,从他的语气看似乎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情。这里提到的后来不敢承认的“他”,不知是指胡还是舒,如是舒,则舒明确说此文是在胡“鼓励支持之下写成的,是他看过提过意见的”,那么这个后来不敢承认的“他”应是胡了。。因此,要检讨,就直接检讨自己对《讲话》的认识问题,于是《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应运而生。
第三,企业审计人员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无法准确界定被审计企业的经济责任时,要咨询这方面的权威专家,这样可以提高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结果的准确性与合理性。
通过1945年8月在重庆整整两个半天面对面的辩论,胡乔木对舒芜有了了解,一方面对舒的颇富学养和辩才不无好感,另一方面,对舒顽固坚持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十分气愤。舒芜这篇态度诚恳的自我检讨文章,算是为当年重庆争论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胡乔木十分满意。加诸由胡风的人来批评胡风的人,堡垒从内部攻破,无疑更有教育意义和说服力,效果显然不同于一般的斗争批评。于是,胡乔木决定由《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全文转载。而这个编者按最大的“亮点”,就是点出了“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
当然,胡乔木说存在“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是本诸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因为在舒文中,提到存在一个“我们”,“所以说‘我们’,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曾经具有相同的思想”,而且直接点出“几个人”是指“吕荧、路翎和其他几个人”*舒芜:《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283页。。虽然没有直接点胡风,但这个“我们”,“主心骨”为胡,“召集人”为胡,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早在1950年3月14日,周扬在文化部大礼堂向京津地区文艺干部做报告时已率先点出胡风“小集团”。参见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第383页;晓风《我的父亲胡风》,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胡乔木说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文艺上的小集团是出诸周杨呢还是本诸舒芜,抑或两者皆有“贡献”,以笔者目前占有的材料来看,还不能作出判断。但当时的舒芜因为不知道周扬已有此说,因此心里难免有些愧疚。不过,在行文中用“我们”与直接点出“小集团”毕竟有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小集团”新鲜出炉,影响深广,功在胡乔木。。
对于胡乔木说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舒芜后来回忆,“老实说也有点后悔,觉得毕竟搞出一个‘小集团’的概念,影响太大了,脑子里不能够接受这种上纲上线的提法。可那个时候的社会思想状况明摆着,也不可能有什么补救措施。反过来想想,《人民日报》说的话,个人还能有什么辩解的?再说你找谁去辩解?所谓‘小集团’又不是什么军事组织,它不过是一种认定,认就认定吧,本来我对于我们的内部‘小圈子’的宗派倾向,就一直有感觉,也曾经跟胡风提过的”*《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232页。。在舒芜看来,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确实是有的,而且是胡风有意识的组织的结果,这是胡风的一种斗争策略。舒芜在致胡风信中曾经提到“集束手榴弹”,并专门作了解释:“胡风1945年1月18日来信说他自己多年来用的是集束手榴弹的战术,意思是致力于期刊、丛书等等的编辑工作,把志同道合的作者的力量集合起来,好像把自己作为一根绳子把几个手榴弹捆绑在一起投掷出去,可以比单个手榴弹力量更大”*《舒芜致胡风书信全编》,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87-88页。。
至于“小圈子”的宗派倾向,舒芜认为也是存在的,而且他也是不满的。如胡风对文坛一向批评较多,而舒芜却对这些被批评的作家作品印象不错。胡风对文艺界看得一团漆黑,不愿意身边的作者跟进步文坛有什么接触,一涉及具体文坛,总是看得太差,而舒芜就自己所知道的点滴情况分析,觉得似乎并非像胡风所说的那样,于是慢慢产生了怀疑,而把这些想法和胡风一说,“他火得很,结果引起极大的不满”*《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219页。。
如果说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上,还只是说有一个“曾经有过相同思想的我们”,那么在《致路翎的公开信中》,舒芜已完全按“人民日报编者按”的口径,明确指出“我们的错误思想,使我们在文艺活动上形成了一个排斥一切的小集团,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
虽然关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一文的出笼经过,存在不同的说法,但无论是主动交信还是被动借信,率先使用胡风给自己的私信撰文,都是不争的事实。舒芜引证的本意是用来批判胡风的宗派主义,但由于林默涵的“慧眼识宝”和毛泽东的“独具只眼”,终于由“小集团”而变为“反革命集团”,由人民内部矛盾而成为敌我矛盾。对于舒芜而言是否有“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之叹呢?
晚年舒芜编选自己“五十多年来关于文化、思想、哲学的论文的选集”*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页。时,仍收入《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致路翎的公开信》,说明舒芜认为胡风存在宗派主义和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的意见没有改变。不过,虽然舒芜曾经明确指出“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于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共文艺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舒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页。,但是,对于把这个在文艺活动上形成的“排斥一切的”、“发展着恶劣的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打成反革命集团,恐怕也不是舒芜的本意,因为这是林默涵的面授机宜,舒芜是权宜,是苟且偷生,是不得不为。
二、 舒芜认为胡风存在台前幕后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的两面
晚年舒芜,曾经有过这样的反思:“由我的《关于胡风集团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尽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90页。。这里明确了舒芜眼中胡风的角色和身份定位——“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好友”。
从舒芜致胡风书信来看,确以兄弟相称为多,在《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则称“胡风先生”,署名也由“管”而为“舒芜”。舒芜并不避讳胡风对其的提携,但要说胡风是舒芜的老师,舒芜叫不出口,恐怕胡风也应不出声。但是,为把舒芜视同犹大,那么,首先得让舒芜成为胡风的学生。何满子的理由是“舒芜在《材料》后面的按语里,不是说他曾把胡风的信当作指导他的宝贵文献吗?”*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认为以此认定胡、舒为师徒关系,不能算错。而聂绀弩则认为,把舒比作犹大不通,“他和胡风怎么会是师徒关系呢?”再说,就算是“犹大”,人们谴责的也应是总督*何满子:《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
事实上舒芜对胡风的感情很复杂,对胡风的认识和看法也很复杂,甚至认为胡风言行上有两面性,人格上是两面派。舒芜认为,“《论主观》的写作是在胡风先生指导下酝酿和写作的”,胡风甚至还撰写文章予以呼应*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8页。,但是当《论主观》遭到批判时,胡风竟说文章中只有一个论点他能够同意,而且发表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为了供批判之用*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4页。。更令舒芜不快的是,就算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在文章遭受批评后,也应把真实情况告诉他,而不是一方面对周恩来等领导表态说,他只同意文中一个观点,发表是为了批判,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励舒芜加紧研究,再接再厉,准备迎战,而且“一直指导我写‘迎战’文章,一直恨我‘迎战’无力”*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6页。,并指导舒芜应对批评,帮助修改反批评文章,有时还认为舒的反批评文章“口气不够冷、态度不够轻蔑,气派不大”*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9页。。舒芜认为正是胡风的这些做法,使他蒙在鼓里,从而成为党领导的进步文艺阵营批评的对象,甚至有对立激化的趋势。解放以后,胡风又认为《论主观》是一大公案,迟早要引起讨论,教舒芜向领导和老干部学习,对文章中引起曲解的地方进行解释,对不足的地方加以自我批判。而舒芜也就自我检讨的体会多次与胡风、路翎商量,但在背后,胡风却说舒芜患得患失、是“想用别人的血洗自己的手”。
为证实胡风类似的两面派手法*舒芜在《回归五四·后序》“又附记”先引林贤治的说法,即胡风先生作了“台前幕后不相一致的近于两面人的表演”,又引长沙“一位先生”信中说“舒芜信中并未明说胡风耍‘两面派’手法,但显然有这样的暗示。”最后明确自己没有说胡风是“两面人”或“两面派”,但要读者相信他说的是事实,事情确实有两面。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11页。,舒芜还另举胡风一方面主张和推荐自己到东北的大学去当教员,一方面又说舒芜“依然梦想做教授,或者以理论家被重用”*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09-711页。。再有,1952年9月,中宣部点名要求舒芜到北京参加帮助胡风检查文艺思想的座谈会,期间林默涵和严文井关照舒芜,要他找胡风谈谈,多沟通沟通。于是,舒芜第二天就去胡风那里。舒芜后来回忆,“在交谈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点,胡风一直不大说话,不像过去那样,凡事都有态度,这次不一样,主要是问我,问了以后,还动笔做笔记,我讲他记”。问的都是理论方面的问题,如“我们过去的理论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舒芜说自己则是“老老实实一一回答”。对此,舒芜认为,“现在看来,他是在了解我的底细”*《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36-237页。。为什么这样说呢?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中,对这次谈话有专门记载,胡风认为舒芜此来,是“从负责同志们得到了审判我的权利的”,自己则“高兴有人完全用敌性感情来检查我的文字” 。胡风反映,“舒芜还告诉了我几件党内情况,其中有关于毛主席的”,又说舒芜之后又用提问的形式带有恐吓意味的暗示自己,“你断定了政治家不懂文艺,你看不起政治家,你是反抗党的领导的,当心我要把这揭发出来” 。胡风认为这次谈话,是舒芜给他上了一课*《胡风全集》(6),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328页。。事后两人可能都庆幸没有说让对方拿住把柄的话,而胡风对舒芜的恶意、敌意是确凿无误的,而舒芜自认是真诚的、友好的,在了解实情后,对胡风这种心理和方式,显然十分不满,甚至有些气愤和不屑。
如果说当初舒芜对胡风的遭遇带有深深的不安、愧疚和同情,那么,晚年舒芜在看到关于胡风事件的大量文献,特别是细读了胡风《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等文字之后,舒芜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其由此而震动,也不为过。
因为在“三十万言”书中,有专章“谈关于舒芜问题”,说舒芜对路翎是“造谣攻击”;1951年初就“已与中宣部有联系,并寄了长文阐扬胡乔木同志在鲁讯纪念会上的演话”;在广西经常看得到党内刊物《宣传通讯》,而自己“到这时候才晓得有这个内部刊物”,言下之意,舒芜之所以思想转变比较快并被文艺界领导所信任,一是奉承讨好胡乔木,二是看得到内部刊物,知道内情,有投机成份。揭发舒芜,这次“北京打电话要他来北京参加讨论我的思想,他动身之前告诉人‘北京没有办法了,我这次是去当大夫,开刀!’”胡风的言下之意是,舒一方面诬蔑、低估党对文艺的领导能力,另一方面又洋洋得意的自我标榜。胡风同时说明,自己已经透彻地看清楚了舒芜“给党和文艺事业带来的损害作用”,而自己因为“被同志们做成了没有发言权的罪人”,虽然看清楚了,却“无法可想”。事实上,胡风对舒芜的侮辱与谩骂不仅在背后,甚至当面也曾直斥舒是“混帐东西”*《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
不过,舒芜对胡风“两面派”行为的揭露和不满表现得十分节制,一方面是因为胡风的悲惨遭遇,令人扼腕,另一方面,舒芜的经历和文艺界、思想界对他的评价与看法,也容不得他过多的进行批评。事实上,舒芜为证明他之所言不虚,在得到自己致胡风的信的复印件后,即交付出版,而且并不忌讳当年发表《材料》时对私信加以注释而遭人诟议的先例,对发表的所有145封信件同样详加注释。这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也足证在舒芜眼里,兹事体大,不能不辩,当然,也曲折表明,当年自己对私信注释发表,并无大错*其实以传统习惯,直接公开、发表书信,并不鲜见。建国后因集权政治据此直接定罪,造成重大后果,始痛诟这种行为,时至今日,则更为现代社会所不容。。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1954年7月22日,由作者本人面交当时的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同志转中央政治局、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在最高领导人面前这样反映、检举、揭发舒芜的问题,认定、判定舒芜的为人、品质、行为均极其恶劣,一旦收信人中的任何一位听信胡风的意见,作出相应批示,那么“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的首先就是舒芜们了。要知道,舒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是1955年5月13日公开发表,几乎是在胡风递呈“三十万言”书10个月之后,而期间对于胡风的批判已是如火如荼。当然,摧毁胡风的是毛的宏文,是战无不胜的领袖威权和专政铁拳,但说舒芜的文章是给胡风重重的一击,甚至击倒在地的一击,应该说并不为过。
三、舒芜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那个时代的常态,不存在品德问题,已承担应负责任
正是基于对胡风集团及胡风本人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对于胡风之外的胡风集团其他成员,舒芜同样认为:“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尽的一份沉重的责任”。这样的反思和道歉,在舒芜看来,自己已经承担了应负的责任,但显然没有达到胡风集团成员的预期,因此也就没有得到他们的谅解和接受*钱理群:《晚年坚持五四精神》——“最重要的是,他作了反省,我觉得,舒芜在晚年已经对自己的行为作了反省,这就已经够了,至于达不到某些人的‘反省’要求,那是另外一回事请,对他也不公平。”《东方早报》,2009年8月24日。钱的这段话,堪称解人,也是公允之论。。而舒芜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是有其原因的:一是舒芜认为当时形势下由他不得,二是在舒芜眼里,胡风集团或者小集团、宗派主义应该说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建国后,作为自觉改造得好、受党信任、被组织重用的舒芜来说,对路翎等人“还保持着知识分子某些自由思想、自由作风”,“觉得看不惯”,是反感的。而此时的自己“已经开始从一个‘政治领导’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舒芜:《回归五四·后序》,见《回归五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47页。。在反复钻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舒芜认为当初自己主观上是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不自觉地走上了斯大林主义。“这就是说,我在政治信念与思想实际的关系方面,隐隐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继承‘五四’的道路,追求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另一方面,又崇拜斯大林主义,相信政治决定一切”*《舒芜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舒芜这样的自我思想剖析,显然是为了解释自己撰写《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等文章,是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信仰斯大林主义的结果,而不是人品、人格的原因。
胡风集团案平反以后,舒芜是渴望与胡风及其他成员交流、交往乃至再度融入、融合、融洽的。牛汉回忆,“1983年,在中国作协开过有关胡风问题的座谈会。事后舒芜找过胡风,胡风没让他进太平巷的门。胡风拒绝见他”*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2008年版,第119页。。而其他胡风集团成员,大都对他口诛笔伐,用词也多尖酸刻薄、挖苦嘲弄甚至肆意谩骂*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提到,“文革”后,舒芜作《四皓新咏》讥刺冯友兰、魏建功、林庚和周一良这四个“梁效”人物。何满子竟云,“我在周一良的自传中,发现有扒手从此事捞一把的记述。任何人出于对四人帮的憎恨,对四教授被迫失足加以讽刺,都无话可说,唯独舒芜其人没有资格。此人是开国后第一起文字狱冤案卖友求荣自甘为虎作伥的丧德败行之徒,亦是一代士风堕落的始作俑者。他的作恶不象四教授的被胁迫而是出于自告奋勇,品格上大有等差。这样的人讽刺别人,正如老妓自夸贞节,骗子鼓吹诚实,本身就是滑稽之至的丑恶表演。”,而舒芜除了与有关事实不符时才动笔说明、澄清、反驳外*每当觉得与事实不符,使其令誉受损时,舒芜一般都第一时间去信更正、说明。此类信件甚多。如舒芜《对张僖〈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一文的来信》,《舒芜晚年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页。舒芜:《关于章怡和女士文章中几段文字的说明》(此处“诒”错成“怡”,不知是舒芜之误还是编校之错),《牺牲的享与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161页。,大都不发一言,即使不能不辩,也表现得十分克制。
晚年舒芜,除了和聂绀弩交好,与绿原、牛汉等少数成员保持一定联系外,与其他成员几乎没有来往,反而时有文字上的争论,甚至争执。典型事件之一,即关于“贾拒认舒”事件。所谓“贾拒认舒”,大致是说舒芜、牛汉和绿原共同做东,在京请贾植芳夫妇吃饭,随后,舒芜去拜会贾植芳,贾植芳对着伸出的手说“我不认识你”,事后还有人问贾植芳,饭都吃了,怎说不认识?贾植芳则说,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舒芜:《贾拒认舒版本考》,《万象》第八卷第二期,2006年5月;张业松:《“贾拒认舒”材料补》,《万象》第八卷第九期,2006年12月。。这段绘声绘色的描写,对于仇恨、仇视舒芜的人来说确实很痛快、很解气,对于塑造贾植芳先生形象也确实很有作用。而此事究竟有无,只有两位当事人明白,事实上,两人在世时,一人说有,一人说无,各有理据,已是难以定谳,现在两位当事人均已作古,真相究竟如何,只能任人评说。但综观各家叙说,有两点却是引人思考的:一是贾说“饭可以吃,手却是不能握的”,这样的话语多少有些江湖习气;二是贾方说出当年任敏刚自国民党监狱放出,无处栖身,此时舒芜从安徽老家出来,经过上海,知道贾植芳还身陷囹圄,于是,临走时留下50元钱给任敏,而这钱是舒芜卖掉他父亲的股票筹来的。对于这样的朋友,贾氏夫妇既怀感激之情,专门奉访,而且共进午餐,稍后舒芜来访,一般不大可能仍会说出“我不认识你”之类的话语,如果真有其事,高下立判,恐怕得分的是舒。其实,舒芜对一些胡风集团成员是有保留意见的,甚至很不以为然。特别是新时期以后,因曾经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从而引以为傲,动辄以自己的苦难说事,并以此来侮辱、谩骂他的人物,舒芜自有分寸。
在舒芜看来,如果说他引用私信、“出卖朋友”是“无耻”,那么出卖朋友的是否只他一人呢?牛汉回忆妻子吴平时说到:“‘文革’中,吴平因鲁煤写的大字报被打得浑身是伤,几乎被造反派打死,打了九次。鲁煤说她抄写了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1页。。就是胡风自己,“三十万言”书中“无中生有”说范泉是“南京政府的密探”,而使范“受尽了苦难”*贾植芳:《一个不能忘却的朋友——范泉》,《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至于历次政治运动中,朋友背叛、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等更是司空见惯,已是那个时代的常态,而且这些行为的发生,都是出于革命的需要,是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是听党的话、听组织的话、听毛主席的话的结果。谁会想到这样崇高的目的之下所做的一切,竟然会是错误的呢?即使聂绀弩这样颇具风骨的人物,同样在1955年5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第二批材料后,给周扬写信揭发胡风*徐庆全:《1955年:历史扭曲了人格——聂绀弩揭发胡风》,《名家书札与文坛风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133页。,足见在极权政治统治下的人性扭曲。从历史的视角看,之所以产生胡风及胡风集团成员处于“鱼游沸鼎之中,燕巢飞幕之上”的结局,岂是舒芜及他的几篇文章所造成的?
晚年舒芜并非如人所谓的“永远尴尬,或者隐痛”*李辉:《永远尴尬着,或者隐痛》,《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13日。,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文化自信、学术自信或者说学识自信。其实,一些胡风集团成员,虽然自我、门人或者亲友评价很高,客观地说,却没有多少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即使贵为教授、博导,担任很多学术职务,实际上还是名则名矣,却是“一个让人费神想上半天也说不出其扛鼎之作的‘大家’”*陈远:《贾植芳:负伤的知识人》,《负伤的知识人》,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33页。陈文中“扛鼎”的“扛”误作“抗”。。而舒芜则不同,且不论其古典文学修养深得学界认可*如1984年,舒芜应程千帆之邀参加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砺锋博士论文答辩会。与会专家中,除舒芜外,南大之外的有傅璇琮、霍松林、钱仲联、徐中玉,本校的老师是程千帆、陈瘦竹、周勋初,均是第一流的学者,从座位安排看,舒在居中的程千帆左侧,钱仲联在程的右侧,高于其他学者。,其周作人研究,也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人*钱理群:《晚年坚持五四精神》,“很可贵的是,舒芜晚年在学术和写作上做出了大量成就,比如他对周作人艺术、思想的研究,我曾经就认为他是国内第一人。此外,他晚年写了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这一写作实际上秉承了五四对妇女问题关注的思想脉络。”《东方早报》,2009年8月24日。。而他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许多意见,也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舒芜自己也显示了自己的学术、学识自信,如指摘季羡林的错记*舒芜:《关于〈昼锦堂记〉的开头及其他》,《舒芜晚年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2013年版,第17页。,王蒙的误读*舒芜:《关于陈寅恪诗的误读》,《舒芜晚年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2013年版,第13页。,批评文怀沙的为老不尊*舒芜:《老吾老》,《万象》第十卷第十期,2008年10月。,都得到了文化知识界的认同、好评。这种极具正面意义的文化、学术、思想地位及其影响,给老年舒芜带来了许多满足,也使他可以无须在乎一些人的恶评。□
(责任编辑:熊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