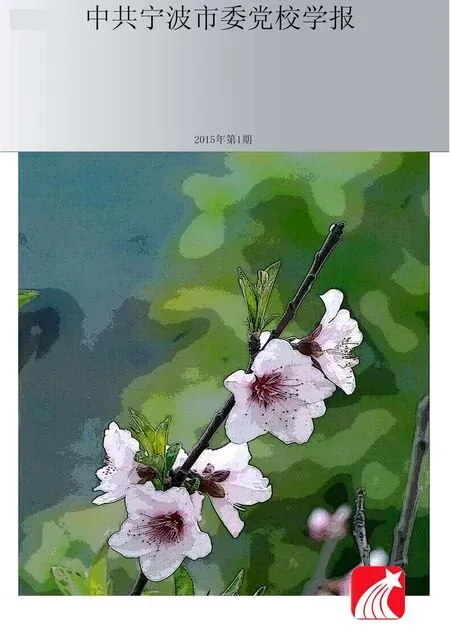中国文化的“基因”
吕嘉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4)
中国文化的“基因”
吕嘉
(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北京100084)
中国文化的“基因”即阐述以良知为本的人的真理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基因”包含着文化生命赖以延续的遗传信息──人的真理。世界诸多文化都孕育、形成、维系于某种宗教,因为宗教信条天然适合承载文化生命的“基因”。中国文化是世界诸主要文化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化。中国文化复兴需要中国人的文化自觉,需要思想界进一步解放思想。
文化;中国文化;基因
一
基因是生命的密码,记录和传递着生命赖以延续的遗传信息。文化亦有生命。文化的“基因”承载着文化生命赖以延续的遗传信息──人的真理。
文化的生命标志是实现人的生命转化。动物没有文化,也不需要文化。猩猩生来就是猩猩,不需要再通过某种方式将自己教化为猩猩。没有文化或离开文化,人类却不能成长为区别于动物的人。文化如何从物质运动中产生出来?人类或许永远无法知道。当代人类学只是告诉我们:“文化模式是在历史上产生的,我们用来为自己的生活赋予形式、秩序、目的和方向和意义系统”。[1]在历史上产生的文化亦有生命。文化的生命显现于实现人的生命转化,将生而为动物个体的人类转化为超越于动物的人。如果某种文化不能再将生而为生物个体的人转化为承载自己的人,尽管这种文化仍是文化,却已经没有生命。今天不再有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中极为懒惰却嗜好征战,厌恶和平的日耳曼人,因为那种日耳曼文化已经失去生命力,不能再将人们培育成为承载它的日耳曼人。没有生命的文化也没有可以经验到的传统,不再影响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文化生命赖以随人群繁衍而世代延续的遗传信息是“人的真理”──关于人的生命法则的真理。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人的生命转化,将生而为动物个体的人类转化为区别于动物的人,就在于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真理”,能够通过文明教化使“人的真理”在人群繁衍中世代传承。文明教化首先在于“教”,将人的真理“教”于生而为动物个体的人。人类起源于生物进化,“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2],但同时也拥有形成于生物进化的发达意识,讲道理,亦能够服从自己真心信服的道理,作为大脑的属性与机能的意识能够升华出人的精神世界。文明教化其次在于人可“化”。“人的真理”同时也是文明秩序的根本。人们在文明中成长成人,从自然个体转化为文明的个人,是所有人成长成人的必由之路。“成为人类就是成为个人,我们在文化模式的指导下成为个人”[3]。文化承载于人的生命,传承于人群繁衍。
“人的真理”最初由谁提出,正如文化最初如何产生,对人类或许永远是个谜,但原始社会的图腾信仰中已显然存在关于“人的真理”的原始形态。人们生而为氏族部落的成员,无条件地接受氏族部落的图腾信仰,原本只能意识到本能的意识随生命成长而自然发展为“人”的身份意识,在人们头脑中自然确立起超越现实物质生活追求的精神追求。当然,最初的“人的真理”是狭隘的,带有人类脱胎而出的动物属性,血缘族群甚至地域都成为人与非人的界限标志。人类学家在考察爪哇文化时发现,“当地人非常坦率地说:‘做一个人就是做一个爪哇人’”[4]。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文明在轴心时代(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00年前后)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印度及地中海地区的伟大思想家,孔子、佛陀、苏格拉底、耶稣等,在继承各自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先后创立了几种普世性的“人的真理”──具有适用于人类所有成员的普遍意义的“人的真理”,使得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种族、地域的区别,只要其自觉以这种人的真理为生命准绳,就都可以成为具有“人”的身份的文明人。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人们以自己所属文明界定自己“人”的身份:中国人、印度人、西方人……。
二
轴心时代的突破性进展孕育于意识觉醒带来的挑战与危机。由此,宗教信条成为适合于承载文化的“基因”。“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5]。
文化生命维系于“人的真理”而在人群繁衍中世代传承,然而“人的真理”能否为人们所认同并进而成为人们的生命准绳,又决定于人的自觉意识,人类意识的状况因此也就同文化的兴衰密切相连,正所谓“意识既是最高的善又是最大的恶”[6]。氏族部落制度解体,人们没有了无条件接受的图腾信仰;人们意识到真理并开始追求真理,希望以自己发现的真理为自己的生命准绳,不再听从未知的神秘力量。但是,人们越是追问“人的真理”,却越是不知道自己是谁。希腊城邦末期,成文法和习惯皆被破坏,世风急转直下。“已无人知道自己身处何乡;聪明人颠来倒去得倒腾每一件事情,老实人则感到他们自己已变得跟不上时代了。论及美德会招致这样的回答,‘一切都基于你对美德的定义’,没有人知道美德的真正含义”[7]。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人类如何摆脱危机?老子感慨于“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惟有“绝圣弃智”(《老子·十九章》),力图返回蒙昧的远古时代,“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者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但意识已经觉醒,覆水难收。
何以人们越是探究人的真理却越困惑于自己的存在?“人的真理”对人具有绝对性与终极性,但是,刚刚觉醒的意识既觉醒于变革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也仅仅知道因此而获得的真理──以事物的真理为原形、具有相对性的真理,并且片面地以为一切真理都是如此。事物的真理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人类对于物质世界的认识永无止境。“人的真理”彰显人的生命区别于动物生命的本质,对人具有绝对性与终极性。无论何人,都需要在生命的某一时刻领悟“人的真理”并以为自己生命的准绳,不能永无休止地探求。如果人们像追求事物的真理那样追问“人的真理”,从一种相对真理奔向另一种相对真理,不仅不是在日益接近揭示自己生命本质的终极真理,反而等于虚度自己人生的有限光阴,永远不能自觉自己究竟是谁,精神也永远不能找到归宿。说到底,人之所以作为人而存在,就在于人的生命不为自然本能所主宰,而以“人的真理”为准绳。刚刚觉醒的意识无休止地追问“人的真理”,犹如动物坚持验证本能合理之后才肯服从本能,似乎是拒绝迷信,其实却十足幼稚,使人类自己陷入最深刻的危机。
宗教信条是承载人的真理的某种形式,犹如黄金是货币的某种形式。宗教现象学认为,“信仰──一个人格化的、人们在其宗教体验中与之接触的‘超自然存在’,是所有宗教的典型特征”[8]。宗教信仰者在宗教体验中接触到的“人格化的超自然存在”,并非以无限力量主宰万物而让人类不能不匍匐于其脚下的神灵,而是人原本就应当如此、作为一切人类美德化身的人的完善形态,即形象化的生命真理。世界诸主要文化大都孕育、成型、维系于某种宗教,如基督教之于西方文化,佛教之于印度文化,伊斯兰教之于伊斯兰文化……,并非偶然。
三
中国文化是世界诸主要文化中唯一的非宗教性文化,因为中国文化的生命遗传信息不承载于任何宗教信条。中国文化的“基因”,就是阐述以良知为本的人的真理的儒家思想。
良知是文明孕育于人的生命的文明基因。人生为自然个体,意识中本无良知。然而人们在文明中成长成人,生命承载文化,意识随生命成长而发展,自然形成基于“人”的立场而审视“我”的自觉意识即良知——人人不虑而知。正如当代人类学的揭示:“我们的观念、价值、行动甚至我们的感情,如同我们的神经系统本身,都是文化的产物”[10]。
良知即天理──人的天然之理。人在文明中成长成人,人的存在不再是动物的自然存在而成为承载文化的历史存在,人的精神世界也区别于为本能所束缚的动物意识,而为良知所无形主宰。自然科学家发现:人类是唯一会脸红的动物[11]。无论何人,即便获得梦寐以求的利益、地位、名誉,只要违背良知,都会不由自主地内疚、惭愧、羞耻、自责,寝食不安,甚至惟有自己终结自己的生命才能最终解脱。一个人无论曾经怎样,一旦天良发现,也可以立即开始生命转化,“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政治权力不容冒犯,法律尊严不容藐视,科学规律不可违背,公众舆论不可罔闻,生命宝贵不能再生,但人有良知,就可以统统不管不顾,知其不可而为之,文明因此生生不息。当然,对于只相信经验事实与实证科学的科学家、哲学家,良知只不过是缺乏实证根据的假设[12]。不过,科学家、哲学家作为人,生活在众人之中,谁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真以良知为假设──那就等于认定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假设的人,只为本能驱使的人,这样他就无法同其他人正常交往,不能享有文明生活。
儒学先哲深知将生而为动物个体的人类教化为文明人的艰难,同时洞悉人的精神世界的必然法则:你在文明中成长成人,良知就在你心中,无须论证,你亦不会质疑,但你要成为真正的人,又需培育、巩固、强化心中已有良知,使良知成为时刻审视自己思想言行的生命准绳,使自然生命转化为承载文化的历史过程。孔子以个人思想言行最先彰显儒学思想精髓。《论语》只讨论何谓君子,如何成为君子,并不探讨人为什么一定要成为君子,人为什么一定不能做小人。孟子将孔子思想凝练表述为人性本善,教化成人的儒家教化理念:“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四端扩充”,“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尽心下》)。《大学》讲“止于至善”,《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宋儒主张“存天理”,王阳明论述“致良知”,家喻户晓之《三字经》传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始终贯穿共同的思想。立足文明教化的实践,儒学思想并非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13]。作为文明教化的对象,无论学生还是民众,聆听先哲教诲时,头脑都早已不是一张白纸。在他们或长或短的人生经历中,文明基因早已通过长辈教诲、乡间传说、民间戏剧等途径,悄然潜入头脑。毕竟,“中国哲学本是出自忧患意识的生活智慧”[14],不会像西方哲学那样“为知识而知识”地追问一般人性。
中国文化“以道德代宗教”[15],是以良知为生命之本的人的文化。“经”为中国文化的经典,阐明中国人以为天经地义的真理,论述中国人以良知为本的生命原则──仁、义、礼、智、信,表述中国人即以良知为本的自我意识即中国人的“人”的意识。“史”记载中国人──以本于良知的真理为生命准绳的人──的历史,为中国文化的终极评价体系,并非探索历史规律的历史科学。“子”即百家之说,记叙以良知为真理的中国人的精神探索。“集”为诗歌、小说、散文、笔记等所结文集,展现以良知为生命之本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
四
人类文明进入新的轴心时代。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预言:“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16]。
发展现代知识是社会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人类文化也经历严峻考验。以学科为标志的现代知识以揭示世界万物的本质与规律为目的,遵循实证原则,不承认任何不言而喻的真理。文化赖以传承的遗传信息却必须是人所确信的绝对真理。于是,现代化以来,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人的幸福也演变为“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17]。“生态危机和社群瓦解正在世界各地发生”[18]。“现代人已经失去了他中世纪的同胞所拥有的形而上的安全感与确定感”[19]。世界的荒谬与人生的虚无成为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思考的主题。哲学家们开始反思科学和理性。“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进入21世纪,人类进入新的轴心时代,人类文化开始反顾传统的宗教信仰与思想体系。
现代化是中国文化命定的劫数。现代化是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被动做出的抉择,中国人的良知还是孕育于农业文明的良知,中国人却为生存所迫而不得不追求工业文明。发展现代知识以取代四书五经,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然举措,却也从根本阻断了中国文化的遗传信息。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儒学被归结为哲学──探讨宇宙万物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之方法的科学,并进而被归结为错误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被逐出正规教育渠道。儒学的核心思想保存于中国的语言文字、历史文献及文艺作品,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中国人仍是中国人,却已经没有天经地义的真理,精神发展处于缺乏有效引导的自发状态,心灵囿于种种相互冲突的“主义”,精神世界日益狭隘、功利。17世纪荷兰思想家格劳秀斯曾这样论述中国文化:“大同主义的体系构成其顶点,中国的精神文化能够发展至此。唯一能够销蚀并阻挠它的力量是科学。如果人们严肃地从事科学的时代来到,那必定无疑出现中国全部精神生活中的一种完全变革,通过它,中国或者必定四分五裂或者将经历再生,此后中国将不再是中国,中国人将不再是中国人”[20]。并非妄言。
今天,中国初步实现现代化,中国人的良知在逐步确立的现代中国文明中孕育、成型,中国文化的劫数即将转而为复兴。兰晓龙、康红雷的《士兵突击》表明:当代中国人可以重新以良知为自己的生命准绳。“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就是好好活”。什么是有意义的?每个人凭良知早已清清楚楚:修路是有意义的,学习是有意义的,尽职尽责是有意义的,追求上进是有意义的,遵守规则是有意义的,信守承诺是有意义的,孝敬父母是有意义的……,无须解释,无须论证,天经地义,不言而喻。“天不变,道亦不变”。
“九九归真,少得一难,劫数未完”。中国文化还有最后一难──现代学科制度的束缚。现代学科制度形成于科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贯穿自然科学的真理观,不能容纳具有绝对性与终极性的“人的真理”。然而人类必然在文化模式指导下不断完成从动物个体到文明人的生命转化,而当代文化赖以传承的“基因”,必须是人民以为天经地义的“人的真理”。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中国文化需要承载自己“绝对真理”的经典。我们还需要不断解放思想。
[注释]
[1][3][10][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57~5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2页。
[4][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5]参阅[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6][瑞士]荣格“心理学的现代意义”,《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
[7][英]基·托《希腊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2页。
[8][意大利]马利亚苏塞·达瓦马尼《宗教现象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0、314~317页。
[9]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11]陈末《人是惟一会脸红的动物》,载《南方周末》,2009年6月24日。
[12]参阅崔大华《儒学面临的挑战》,载《孔子研究》2000年第1期;程志华:《论良知的呈现》,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8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73页。
[14]《沈清松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4页。
[1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96页。
[16][德]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17]转引自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3页。
[18][美]杜维明《超越启蒙心态》,载《哲学译丛》2001年第2期。
[19]《荣格文集》,改革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20]转引自《卡尔·雅斯贝斯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81页。
责任编辑:梁一群
G112
A
1008-4479(2015)01-0056-04
2014-07-12
吕嘉,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