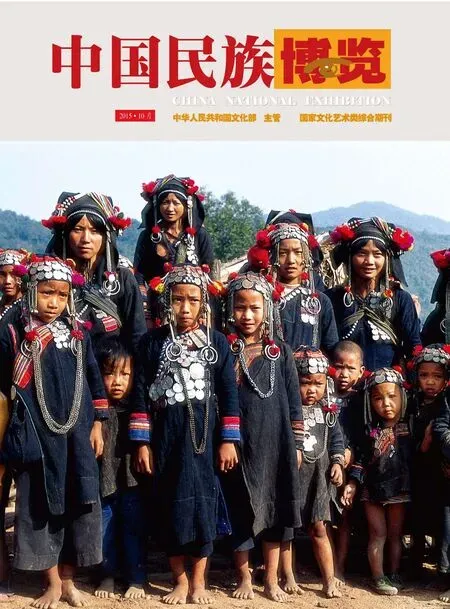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与继承
孟祥娟(新疆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与继承
孟祥娟
(新疆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葛兰西的思想,从理论的源流上看其中意大利本土的政治文化对其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其中,葛兰西所说“国家是披上强制甲胄的霸权”完全可以归于马基雅维利的智慧。本文就葛兰西在《现代君主》中对马基雅维利的认识做出解读,以探析两人的思想关系。
葛兰西;马基雅维利;现代君主
葛兰西的思想理论具有意大利本土的理论渊源,在葛兰西那里,这个理论渊源主要是马基雅维利的理论成果。他们的思想之间有家族相似性,研究他们的理论内涵之间的逻辑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葛兰西思想形成的路径。
一、葛兰西对《君主论》的解读
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对君主论的解读。首先,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当中的君主是集体意志的形象化和拟人化,而最后的呼吁的结尾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君主论》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是什么成体系的论述,而是“活生生的”书: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科学在这里以戏剧性的“神话”形式融为一体。与乌托邦和经院学术论文不同,就是说,与政治科学在巴基雅维利之前所采用的那些表现形式不同,这样的论述给他的观念赋予了纪想和艺术的形式,从而把说教和理性的因素都凝结在了一位雇佣军首领的身上,此人形象而“拟人化”地表现为“集体意志”的象征。马基雅维利对人民力量的重视在民兵思想中可以看出,并体现出一种雅各宾主义,这也是马基雅维利的民族革命观的来源,没有人民的政治参与,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不可能形成。这一点从《君主论》描述的投票的民主政治形式中可以体现得出。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主张政治具有道德和宗教截然不同的原则和规律,并引入一种新的道德观和宗教观——君主是道德和宗教的组织者和宣扬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其真实的意图上并不是写给当时的任何一位君主看的,而是写给正在崛起的人民大众看的,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曾经说过“我们由此可以推想,马基雅维利真正考虑的是‘那些不谙此道的’,他的用意是要在政治上教育‘那些不谙此道的’。这种教育并不像福斯科洛看上去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消极的、痛恨暴君的政治教育,而是一种积极的教育,它教会人们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就必须承认某些必要的手段——哪怕是暴君的手段也在所不辞。生长在统治者世家的人,几乎自动地就带有现实主义政治家的特征,这是因为他的家庭环境给了他一整套复杂的教育,因为在这里支配一切的,只有王朝的或世袭的利益。那么,谁是‘那些不谙此道的’呢?是当时的革命阶级、意大利‘人民’和‘民族’、市民民主派,从他们中间产生了福斯科洛和皮耶罗·索得里尼,却产生不了卡斯特鲁乔和瓦伦蒂诺。可以认为,马基雅维利就是要劝说这些力量,使他们相信必须有一位不仅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得到它的‘领袖’,使他们满怀热情地接受这样的‘领袖’,哪怕他的行为可能与当时人们普遍拥有的意识形态——宗教——相对立,或貌似对立。”[1]另外,卢梭也曾经说过:“马基雅维利自称是在给君主讲课,其实他是在给大众讲课。”[2]由此可见,那种将马基雅维利看作是邪恶的导师,凶残的马基雅维利的人或许是没有懂得马基雅维利的良苦用心。当然,这种认为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主要写给民众的看法未必就是正确的,毕竟还不是占主流的,但是在那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在那个个人追求发展的时代,马基雅维利完全有可能有这样的写作动机。
二、葛兰西对索列尔和克罗齐的批评
(一)克罗齐对葛兰西的影响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渊源主要是马基雅维利和克罗齐的理论成果,而对马基雅维利的认识,又是通过对克罗齐马基雅维利学的讨论而来。在《君主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基雅维利虽然看重市民、臣民但他更看重力量统治的地位,在《君主论》的第十七章“论残酷与仁慈,被人爱戴是否被人畏惧来得好些”时,马基雅维利认为最好两者兼得,如果不能两者兼得,“被人畏惧比受人爱戴是安全得多的”[3],这是马基雅维利人性恶论的很重要表现之一,而当时就有学者反对,认为这里,道德没有得到伸张。但克罗齐是反对这种对马基雅维利的道德批判的,这也使得克罗齐产生了强调实践精神的重要性,而克罗齐从黑格尔哲学而来的对马基雅维利的讨论,使得葛兰西对霸权理论的理解更为清晰,葛兰西沿用马基雅维利的说法,认为必须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当代机遇,写出一本《现代君主》。首先现代君主不再是某个个人,而是政党;其次现代君主与普遍意识的关系;最后点出现代君主的两个要素:民族人民集体意志的形成和精神和道德的改革。这就弥补了克罗齐的政党缺失。葛兰西对克罗齐将政治与伦理、国家与道德断然二分的做法很是不满,认为这是克罗齐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学的误读,马基雅维利实质上一直是不遗余力地论证权利与智识的二元平衡:狐狸与狮子、暴力与法律、野兽与人、强制与认可、武力与说服。如此看来,葛兰西所说的“国家是披上强制甲胄的霸权”完全可以归于马基雅维利的智慧。
(二)对索列尔的批评
葛兰西在文中同时批判了索列尔。葛兰西批判了索列尔的神话意识形态只停留在工会的概念上,没有进一步成为对政党的认识,其中所谓的神话意识就是集体意志,索列尔想通过罢工实现集体意志。但是在这一部分索列尔犯了忽视政党这一错误,他对罢工,暴力革命热情但忽视政党的作用,这一部分葛兰西对索列尔的单纯暴力进行了批判,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暴力革命胜利后的结果。
“假如按照索列尔的设想,利用分化——哪怕这种分化是暴力的,也就是说,摧毁现存的道德关系和法律关系——来使集体意志停留在其最初形成时的那种原始低级阶段上,那么这种手段又怎么可能被认为是有效的呢?”这种发育不良的集体意志会不会就此夭折而分散成无数个在当时的积极阶段上各奔前程的个体意识呢?……”[4]
葛兰西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暴力革命不具有持久性,批判索列尔的观点是在自发性背后有纯粹机械论的设想,在自由(意志—生命力)背后有最大的宿命论,在唯心主义背后有绝对的唯物主义。在这一部分葛兰西提出预见性的讨论,我认为预见本身就是计划的一部分,计划本身应该包括偶然性或自发性的可能性,像罢工这种运动最后如何收场,如果没有政党的组织,那只有听凭非理性的干涉,偶然性(即柏格森所称“生命冲动”)或自发性去发挥作用,那么机会主义就成了唯一可能的政治路线,这样罢工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由此葛兰西在批判前人如索列尔对于马基雅维利的解读的基础上,将“君主”之一观念提升至“政党”的层面。
三、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的继承
对葛兰西来说,马克思以前的年代中令人信服的先辈,必然不是一位经典的哲学家,而是像他自己那样的政治理论家。但是葛兰西向马基雅维利所借用的东西,其范围和类型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其他思想家们是完全类似的。他的术语和主题也是直接从过去的佛罗伦萨体系中取来并放进他自己的作品中去的。在《狱中札记》中,革命党本身成了现代的“君主”,它的独一无二的权力正是马基雅维利所要求的,改良主义被解释为一种同意大利城市相类似的“各阶级合作的”观点,马基雅维利曾经痛骂它的涣散的狭隘性。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形成一个“历史集团”的问题,可以从他关于建立一支佛罗伦萨“民兵”的计划中找到其雏形。对资产阶级统治机制的分析,则始终披着“武力”与“欺骗”(马基雅维利的“半人半马怪兽”的两种形态)的外衣。国家制度的类型学,来自他的“领土”、“权威”和“同意”三者的组合。对葛兰西来说,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也可以被称为‘实践的哲学’”——这是葛兰西在狱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因此,甚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伟大的和最不典型的代表,都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生规律相一致。
阿尔都塞认为葛兰西真正理解马基雅维利:“葛兰西把《君主论》说成是一种政治宣言,一种活生生的,没有体系的语言,他是最先把这本书的特性和跟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对自己所鼓吹的政治任务的意识联系起来的人。”“也许只有一个思想体系通过他的拒绝、他的立场得以接近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把他从孤独中拯救出来,这就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的思想体系。” 丰塔纳对葛兰西与马基雅维利之间的思想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比较研究,他的结论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可以看作葛兰西霸权概念的‘预示’与‘原型’。”
总之,葛兰西的思想传承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思想,并且是最能接近马基雅维利思想的人,就如同阿尔都塞所说,葛兰西真正理解马基雅维利,因此才能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而马基雅维利的思想无论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还是市民王国等思想中都可以寻到印记。
[1][意]马基雅维利.惠全,译.君主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陈越,译.现代君主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仰海峰.实践哲学与霸权——当代语境中的葛兰西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李惠斌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报告[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B089
A
孟祥娟,女,研究生,新疆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君主论》献词隐义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