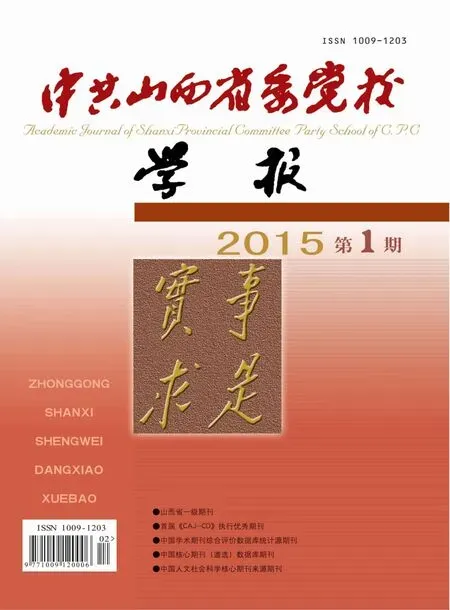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
董业东
(中共临沂市委党校兰山分校,山东 临沂 276005)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
董业东
(中共临沂市委党校兰山分校,山东 临沂 276005)
提高管党治党的水平,必须注重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与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互联互动,要树立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的法治理念,重视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的立法衔接,厘清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适用的边界,健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的处理机制,进而实现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的有机统一。
党内法规;国家法律;立法协调;适用边界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在党,坚持党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领导,必然要求依法治党、从严管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1〕健全的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内法规建设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妥善解决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问题,增强两者的叠加效应,不断提高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互联互动的权威性、严肃性,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有机统一。
一、树立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的法治理念
法治理念是公众对法律的实施状态、价值意义以及效用功能所持有的态度和信念。法治即依照法律对国家与社会事务进行治理,强调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法律不仅是社会治理的工具,还是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理念意味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2〕。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法治理念与不同社会发展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联系,凸显了法治实施的价值维度,主导着国家法律的建构,并决定着司法、执法、守法的思想理论基础,其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法治的动因以及法治实现的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刻反映了党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探索,适应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构成这一理念的核心要素是依法治国,基本要素是依法治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要求党要始终坚持依法执政,严格按照党内法规来管党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执行力,完成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依法治国必先依法治党,这是国家法治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也是国家秩序和党内秩序赢得正统性的标志。树立治国必先治党的法治理念,首要的就是把党的全部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把党的权威融入国家法律的权威,形成符合人民意志和时代趋势的完备法律规范体系,在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同步推进依法治党与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法治文明和政党法治文明的共生共荣。
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法治具有引领和规范功能,用党内法规调整党内秩序、用法律治理国家,是提升党的执政水平,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现政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和社会公正的正确路径。《党章》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3〕这些规定意味着各级党组织的活动包括制定的党内法规,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不能与宪法和法律相冲突。依法治国,在理念上奉行宪法和法律的最终效力和最高权威,要求任何组织的规章制度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界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政治组织,作为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毫无疑义既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主体,又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客体。依法治国所秉承的法律至上精神延展到各级党组织,则要求树立党内法规的绝对权威和效力,党内法规面前人人平等,各级党组织以及全体党员都必须毫无例外地自觉遵守和坚决执行。同时,广大党员干部又是推进依法治国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党员干部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实质上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提高对全社会具有重要的示范引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依法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国在党内的自然逻辑延伸。只有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不断提高管党治党的制度化水平,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二、促进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的相互协调
应明确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的不同主体,充分尊重和维护国家立法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定机制是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的重要任务,党内法规制定既应在形式上与国家立法的总体规划相适应,又需在内容上与国家立法实现对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严格界定了党内法规制定的主体与权限,即“中央党内法规按其内容一般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各部门起草,综合性党内法规由中央办公厅协调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有关部门起草或者成立专门起草小组起草”〔4〕。这些原则性的规定保证了党内法规制定的权威性和统一性,有利于从顶层设计上减少或避免无序制定、越权制定、无权制定和重复制定等现象的发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立法先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严格界定了享有立法权的主体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各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和范围,任何党内法规都不能逾越这些权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党的领导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最根本的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可以确保立法符合宪法精神,真正反映人民意志,体现公正、公平、公开的立法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法规制定可以干涉由国家立法规范的行为、调整的事项和确立的制度,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在严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方面应该是有机统一的。加强党内法规建设,对完善国家法律体系来说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在党内法规制定的实践中,要坚决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所拥有的专属立法权,党内法规制定不得干涉有关国家机关权限与职责的立法,党内法规无权限制或剥夺党员基于个体公民应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不能以党内法规的力量影响有关民事和刑事诉讼的程序与实体法律制度。
促进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的相互协调,必须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建立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从当前的实践情况分析,现存的部分党内法规在制定的时候就与国家一些立法出现了抵触,以至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其中较为典型的如各级人大对领导干部的依法任命程序与党的干部选拔调动制度的衔接问题。要解决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的交叉重叠问题,党内法规制定机关应该注重与政府法制机构和人大法规部门的经常性工作联系,建立定期的协调沟通程序,通过不断协商妥善解决。一是对需要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进行双重调整的重大问题协同调查论证,建立由社会团体、有关国家机关和专家学者等参与的论证咨询机制,增强法律法规制定流程的科学性、民主性和系统性。二是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两种手段的优势,对分歧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广泛征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意见建议,拓宽公民有序参与路径,凝聚社会共识,适时引入第三方评估,从机制与工作程序上防止特定群体利益的法律化。三是推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两者在党的建设和国家社会领域的功能。由于党内法规严于国家法律的特点,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既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又要不打折扣地遵守党内法规,推动全民守法用法。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既有助于切实保障党内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又能切实维护国家立法的公正性、权威性和完整性。
第二,推进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的良性互联互动。党内法规完备的程度是一个政党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从依法治党的现状来看,由于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建设,党内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实现了有规可依和有章可循。但不可否认,当前,党内法规制定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表现为党内法规制定的统筹规划不够,制定工作滞后于党的工作实践和时代发展,某些党内法规可操作性不强等。要积极借鉴国家立法的成功经验,严格依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的要求提高党内法规制定的水平和质量。一方面党内法规的制定必须严格遵循宪法法律的精神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总结党内法规制定的经验规律和好的做法,把党内法规中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制度经由法定程序及时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法律法规,这样既提升了党内法规的长效性,又增进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顺畅衔接。以财产申报制度为例,目前,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实行财产申报制与金融实名制证明了其强大的震慑力和约束力,把官员个人和家庭的收入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其成为反腐倡廉的锐利武器。与此相对照,我国当前规定领导干部必须申报财产的主要依据是《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等,规定较为模糊,缺乏刚性约束和可操作性,因而实践成效大打折扣。放眼世界,英国议会1883年就通过了世界上首部涉及财产申报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美国国会1978年通过了《政府行为道德法》,明确规定公务人员必须公开财产状况,从而促进了官员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有鉴于此,应把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从党内法规的层次上升为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确认,可喜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加速推进《财产申报法》的国家立法。实现党内法规制定与国家立法的衔接,发挥各自在党的建设和依法治国理政中的优势,使其有机统一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进程中。
三、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适用的边界
依法治党与依法治国并行不悖的关键在于确立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适用的边界。所谓法律法规的适用,指相关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权与程序运用一般规定解决具体问题的活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适用领域有很大不同:党内法规适用于各级党组织与全体党员,以党严格的纪律为保证,致力于规范党内生活与党内关系;国家法律以国家的强制力为保障,适用于全体中国公民、所有的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以及所有的政党社团和企事业单位,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是否厘清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适用的边界,直接影响到到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成效的发挥。例如,1996年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和2004年全国人大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都有对“地方重大事项的决定权”的原则规定,但在具体的适用过程中,哪个规定享有更高的法律效力,让人无所适从。有关人大决定权的行使和党委决策权的行使怎样协调亦缺乏明确界定,无形中导致了地方党委与地方人大之间的职能分工不明,出现了权限重叠、繁琐现象,造成了问题解决的滞后和效率的低下。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适用分界不明引发的问题较为突出的还有,地方人大很难开展对同级党委甚至是下级党委的依法监督工作。如在处理2004年湖南省“嘉禾事件”的过程中,当时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致函嘉禾县政府,要求立即纠正错误行政行为,以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而嘉禾县委的反应却是视而不见,这充分说明地方人大对下级党委监督的软弱无力。
明确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适用的边界,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和谐统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历程考量,发展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基础和工作重点都在基层。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2010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支持村民委员会行使职权;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5〕上述法律规定在实际执行中遇到了瓶颈,原因在于村党委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边界不清楚,致使不少地方的村“两委”在解决重大村务决策与村财务管理问题时纠纷不断。基层民主建设从党的十六大以来呈现出了基层人民民主与基层党内民主交融式发展的新趋势,各地长期探索出的较为有效的模式主要有“四议两公开”、公推直选和党内民主恳谈等。尤其是“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实现了决策的组织权、审议权、决定权、建议权和监督权有机衔接,成功化解了基层群众自治过程中出现的矛盾。这些模式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增强了基层民主发展的活力,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有效路径选择。但随之各地也出现了党在基层的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行使之间的交叉,它成为基层民主深入发展的羁绊。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对这些在实际工作中卓有成效的探索反应滞后,对党的领导权与村民自治权之间争议的法律法规的适用问题亦没有明确界定。基层党组织运行和基层民主建设中存在的此类问题有其共性,应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从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适用边界的层面加以区分、规范,依据党规国法,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发展的有效路径。
四、健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抵触的处理机制
党内法规不得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是党章的明确要求,也是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但在实践过程中,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的事情仍有发生,“红头文件”与国家法律法规“打架”的现象降低了党内法规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因此,要逐步健全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处理机制:一是要提高党内法规制定的科学化水平,把党内法规可能与国家法律的冲突性降到最低。确立党内法规制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编订党内法规制定整体推进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与国家的长期立法规划相呼应。强化党内法规起草阶段的调研论证,采用多种形式注意征询相关专家学者和党代表大会代表的看法,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党内法规草案,要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定的前置审核程序,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是否同党章以及上位党内法规相抵触,更重要的是看是否同宪法法律不一致,确保党内法规不会与宪法法律冲突,不会“带病”上会。严格执行党内法规的公开发布制度,始终做到以不公开为例外,以公开为原则,扩大党内法规的知晓率。二是要对党内法规进行及时的清理和评估。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制定了大量的党内法规,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制度基础。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党内法规到底有多少,哪些仍然适用,哪些已经同现行的宪法法律产生了抵触,这些都需要对党内法规进行全面的清理评估。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开展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意见》,清理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效化解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不协调、不适应和不衔接问题,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构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项工作应随着法治国家建设的不断推进而持续进行。三是要落实党内法规的违宪审查制度。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法治经验,建立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规备案审查室,专门负责审查下位法与上位法是否存在冲突。当前,要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审查党内法规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同时建立党内法规备案审查与国家法律备案审查的衔接联动机制,做到有备必审和有错必纠,从而维护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统一协调。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53.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199.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
〔4〕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5.
〔5〕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3.
On Cohes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Inner-party Regulation and National Law
DONGYe-dong
(Lanshan Branch of the CPC Linyi Committee Party School,Linyi 276005,China)
In order to improve level of managing and governing party,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hesion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inner-party regulation and national law,forming complete system of legal norm and perfect system of inner-party regulation.An idea that ruling countryby law is based on ruling party by law to push forward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inner-party regulation and national law,besides,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legislative cohesion between them,make clear their boundary of application,perfect treatment mechanism when they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then realizing unity between ruling country by law and ruling party by law.
inner-party regulation;national law;legislative coordination;boundary of application
D920
A
1009-1203(2015)01-0082-04
责任编辑 李 雯
2014-12-17
董业东(1972-),男,山东临沂人,中共临沂市委党校兰山分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