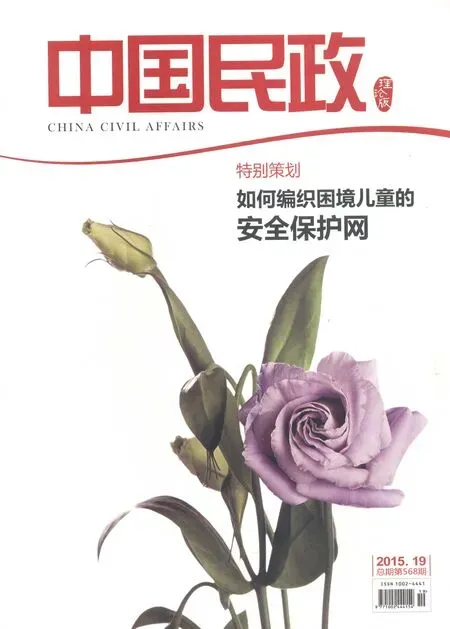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方 芳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方 芳
近年来,因家庭监护不当、监护失职等导致的未成年人权益遭受严重侵害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冲击了社会道德底线,甚至引发公众对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质疑。这种现象的存在,反映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暴露出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及监管力度存在一定缺失。笔者就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工作建议谈一些想法。
一、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现状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父母监护失职但国家干预缺位
媒体报道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别是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中,如“南京饿死女童案”“南京女童裸身乞讨案”“深圳父亲教训儿子致死案”“福建莆田‘饮料男孩’案”等,充分反映了父母监护的严重失职。除了父母的失职外,法律对父母的监护责任疏于规范,国家干预缺位也是重要原因。
家庭自治是人类个体家庭的常态模式,但受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速、价值观念冲击、离婚率增高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留守儿童、流浪儿童、不完整家庭子女、农民工二代等特殊未成年人群体的教育、监护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超出原来家庭自治的范围,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国家对脱离家庭监护的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缺乏有效的补救机制,不能及时发现、介入、跟进、弥补家庭监护不足。
但也正是这种力求稳健不为异说的治学态度使得董氏的儒学思想虽无发明,然而平实妥帖,易为学者所接受。如他讲解《孟子》“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这一章时说:
(二)分管部门繁多但具体职责不明
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处理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国家机关或权力机构,各部门的职能交叉重合,职责难以厘清,责任无法划分,最终形成“名义上都管但实际都不管”的问题,无法积极有效地参与维权和监督。“南京饿死女童案”就集中暴露了这一问题。
(三)监护事件频发但司法介入极少
虽然民法通则自1987年就确立了监护权撤销制度,但近30年来,撤销监护权的案例却寥寥无几。原因有很多:一是时代矛盾的折射和反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家庭监护问题随之凸显,出现了大量留守儿童缺少父母关爱,一些贫困家庭缺乏养育子女的能力,少数有吸毒、酗酒恶习的父母甚至虐待子女等现象。二是传统观念的制约。传统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父母殴打孩子是家务事,外人不便干预,因此,受到家庭监护侵害的孩子经常难以得到有效救济。三是立法比较原则。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规定,特定情形下人民法院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但没有对申请人资格、可以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作出细化规定。四是司法解释规定不够具体。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申请人的资格和诉讼程序,对“不履行监护职责、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法律规定没有进一步具体化。五是行政机关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政府有关规定没有明确各职能部门在介入未成年人家庭监护侵害方面的职责、分工等。以上种种,致使相关法律规定无法落实。
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
通过分析未成年人监护的现状,可以看出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监护的监督主体不清楚
我国法律仅仅规定上述主体“有权”对监护人的监护行为进行监督,未规定强制性的监督义务,更未明确各主体进行监督的先后顺序、主次关系和职责分工,导致具体承担责任的监护监督责任长期得不到落实。
(二)监督职责不明确
对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监督,我国法律仅笼统地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既没有明确监护监督主体的地位作用,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更没有规定不履行监护监督职责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
(三)行政保护和司法审判程序衔接不畅
发生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的案件后,发现报告程序、部门分工、如何移交、如何启动司法审查及司法审查的后接程序等均不完备。
(四)司法审查程序不完善
对监护案件的审理缺乏必要的保护程序设置,仅笼统要求坚持“特殊、优先”保护原则,但缺乏“实质性”程序规范。
(五)监护落实效果不理想
民政部门实际上是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的直接实施主体,承担着国家监护的“兜底”职能。但是,受法律规定、资金、人员、技术、管理、配套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民政部门目前所承担监护职能非常有限,尚无法充分发挥国家监护的“兜底”功能。
三、建立健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对策建议
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是弥补家庭监护不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有效社会保障机制,应当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进行外部监督,切实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健康成长;二是如果未成年人家庭监护不力或者出现不能监护情形时,国家应迅速采取必要补救措施;三是对于丧失亲权监护或其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穷尽必要措施仍无法找到合适近亲属作为监护人的情形,由国家专门监护机构直接代行监护职能。
(一)完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立法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我国宪法、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是国家和政府的重要职责,政府是未成年人的最终保护主体,政府应当切实履行责任,在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四大保护体系,但唯独缺乏“政府保护”这一极其重要和关键的内容,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许多难题。一是“谁来有效监督家庭监护”。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监护主体和职责,但对于监护人履职情况的监督缺乏明确规定。法律既没有明确负有发现报告义务的主体,也没有赋予哪些人员、单位具备上门监督、评估的法定权限,导致相对“私密”的失职监护行为无人监督、发现或举报,未成年人一旦陷入家庭监护危机时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二是“谁来介入家庭监护”。南京饿死女童事件等类似悲剧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这些孩子长期受虐待或者被忽视。虽然邻居、基层群众组织甚至政府相关部门都知道,也都有一定的救助行为,但始终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代表孩子去维护自身的利益,其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立法没有明确承担监护监督职责的部门和机构,使相关部门遇到上述问题时无所适从,难以有效介入。因此,有必要对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修订,完善涉及未成年人监护的法律规定,使其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三是明确强制报告义务,既要明确每个社会成员和单位都有对监护侵害行为的监督和举报义务,也要明确明知不报的责任。建议“学校、医院、村(居)民委员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强制报告主体,并明确相应罚则。其他社会公众作为普通报告主体,均“有权劝阻、制止或者举报”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
(二)强化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监护职责
一是设立专门工作机构统管国家监护事务。建议政府确定民政部门统管家庭监护指导与监督、监护事件应急处置、报告受理和案件分流、家庭监护能力调查评估等工作。时机成熟时在民政部门内设青少年事务管理局,具体负责国家监护的实施。
二是明确专门工作机构跨部门工作的权限。建议民政部门专门机构具体职能包括:未成年人信息的动态监控;重点家庭的监护监督指导;接受家庭监护事件报告;对带离家庭的被监护人进行临时安置保护;家庭监护的调查评估;代表国家提出中止、撤销监护人资格申请;接收安置涉案未成年人;担任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人;对工作对象家庭进行回访调查;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其他工作。同时建议引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参与未成年人接收托管、潜在问题家庭的社会观护、家庭监护的支持与指导等工作。
三是建立家庭监护分层监督制度。第一层次:对社会普通家庭的一般监督。一般监督主要是了解掌握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常规静态及动态信息,将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涉及到未成年人的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信息整合为国家监护的基础数据库,包括儿童基本身份信息、家庭情况、个体需求、值得注意的特殊需求。民政、公安部门通过儿童信息采集和分析研判,对儿童面临的风险做出预警,对儿童保护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对策,开展满足儿童需求的活动,并对需要特殊帮助的儿童提供保护服务。一般监督主要起到监护侵害初级预防的作用。第二层次:对潜在问题家庭的重点监督。重点监督主要针对单亲家庭、吸毒人员家庭、服刑人员家庭、有暴力记录的家庭、流浪儿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贫困家庭,重点监督被监护人是否获得适当家庭养育、是否接受义务教育、是否存在情感忽视、监护人是否具备抚养监管能力、是否存在监护侵害行为。重点监督主要起到监护侵害次级预防的作用。第三层次:对监护失能家庭的介入干预。第三层次监督是指将家庭监护问题移交司法审查,由人民法院判决暂时中止或者永久剥夺监护人资格、由民政部门或者其他相关主体代替父母承担监护职责。
(三)完善监护案件的司法审查制度
一是遵循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人民法院审理撤销监护人资格案件应当给予未成年人特殊、优先保护,对于年满十周岁、具有一定理解和表达能力的未成年人,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应当听取他们的意见。可以考虑赋予未成年人在诉讼中的独立地位。申请人为向人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的个人或单位,被申请人为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如果出现申请人在诉讼过程中撤回申请,而未成年人坚持要求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人民法院可以就未成年人提出的请求继续审理。
二是建立适合成年人参与诉讼制度。人民法院受理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未成年人没有其他监护人的,可以由临时照管人、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其他成年亲属等作为合适成年人,帮助未成年人完成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可以建议未成年人住所地民政部门指派人员担任合适成年人,也可以指定共青团干部、司法社工、教师、居住地基层组织代表、律师和其他热心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人员担任合适成年人。人民法院还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并可以委托专业机构或人员对未成年人及被申请人进行心理疏导。
三是规范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相关单位或个人申请、也可以依职权作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并向被监护人、临时照管人住所地公安机关送达,由公安机关加强对被监护人、临时照管人的人身保护。裁定内容还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近亲属、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单位,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知悉裁定内容的单位或者个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有必要将被监护人带离家庭的,可以向被监护人住所地民政部门、公安机关提出建议,由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将被监护人带离家庭并予以妥善安置。
四是强化法院在事实查明中的司法能动作用。人民法院可以走访当事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学校、工作单位、辖区派出所等,核实相关情况。民政部门、相关单位或组织接受人民法院委托开展社会调查的,应当形成书面调查评估报告,由参加社会调查的人员签名并加盖调查机构公章,经当事人质证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人民法院审理申请恢复监护人资格案件,可以委托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监护能力和条件进行调查评估,民政部门做出的调查评估报告应当作为确定是否恢复监护人资格的重要依据。
五是强调监护救济案件的执行对接。人民法院作出撤销监护人资格判决后,应当依职权将案件移送由执行庭执行。案件执行需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配合或者协助的,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可以向有关个人或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负有监护职责的个人或者单位拒不履行判决,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适用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公权力逐步介入未成年人监护领域,是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强化政府在国家监护制度中的主导作用是大势所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
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未来的希望,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就是“最大的民生”。当然,未成年人国家监护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儿童福利、少年司法等多个领域,其建立和完善并非朝夕之功,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制度设计。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及其他任何公私主体,在处理与未成年人有关的事务时,尤其在涉及制度建设、资源分配时,都要以未成年人的最大利益为优先考虑。只有秉持这样的理念,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才能真正建立。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副主任)